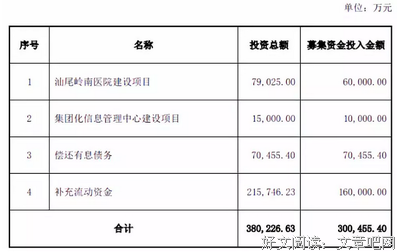
《医疗与帝国》是一本由[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3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19世界才兴起以实验、研究致病成分的医学,不到200年,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还有疾病无解。
●看了本页“居然是一本必读的历史书”这篇书评才决定买的,个人感觉远没有达到这篇书评称赞的高度,总体上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全球史视角的研究,对现代医学发展史的概述(这个概述还不完整,美洲和澳洲都阙如),相关内容没有太多溢出大部头近代通史之外
●现代医学的后殖民理论解释。从16世纪~20世纪初,分成三个阶段,总的来说,中规中矩,行文偏于艰涩,强调分析殖民现代性因素,在全球化进程里,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巴斯德主义”一词反映了西方知识主张在社会学建构里的权力地位,部分地形塑了东方对西方的接受史。
●全球五百年的殖民帝国与医学的互动,主要是对当前研究成果与方向的总结性探讨,可视为这一领域的入门。对我而言是将之前较为零散的印度,拉美知识(非洲知识储备则是0)勾联起来,另外所引书目可作为进一步参考。然鹅主要是这三块地区,作者并未关注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北美情况。为了写论文又读一遍决定降一星(说实话那篇“必读”真不是嘲讽么...
●从殖民时期的医学发展开始,对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展开了梳理。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将医学与殖民挂钩,继而建构起有关政治、经济的社会史学。此部著作仍是宏观史学下的一次尝试。
●不过两百年前,西方人也是相信“四体液说”的,相信放血疗法的,但他们对新世界的扩张之路,也让医学走上了从无知经过试错到达科学的胜利之路,西方医学所走过的路在文化上大获全胜。
●一部对于医疗史宏观概述,算是入门的书,缺点和优点大都在译后记里
●西方医学原本是体液说占主导地位,也用植物来治病。殖民活动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新世界的植物,西方的博物学传统让他们研究并给植物分类。拉瓦锡的化学研究,让西方科学家寻找到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开创了现代药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第二,欧洲人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一直承受着高死亡率的代价。如何降低死亡率?他们一边用预防和防疫手段,一边展开细菌研究,进行微生物捕猎,西方现代医学与传统的体液说分道扬镳,欧洲人探索未知世界,寻找病原体和病媒,西方现代医学逐渐成为全世界主流的医学。 第三,西医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态度是取用;接下来是统治,只有西医培养出来的医生才能叫医生,剩下的传统医生是走方医,西医要占统治地位;最后是贬低和排挤。印度传统医学一方面开始反抗,另一方面也开始和西方现代医学融合。
《医疗与帝国》读后感(一):扫雷
1. 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全球经济竞争以取得更多的资源和土地,追逐帝国的威望和领土以及传播欧洲文明的渴望,导致在1880年代“瓜分非洲”。
2. 欧洲医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更为专科化,来为殖民的目标与利益服务,特别是热带医学的诞生。
3. 就非洲大多数区域而言,19世纪下半叶才是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大卫·利文斯顿的赞比西探险(Zembezi Expedition)之后,欧洲的地理学家和自然学者开始搜集中非的动植物,然后送到欧洲的博物馆研究与展示。
4. 法国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通过对病毒的部分减毒制造疫苗。他在1885年试验出狂犬疫苗,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突破。
《医疗与帝国》读后感(二):编辑差错案例集
1. 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全球经济竞争以取得更多的资源和土地,追逐帝国的威望和领土以及传播欧洲文明的渴望,导致在1880年代“瓜分非洲”。
2. 欧洲医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更为专科化,来为殖民的目标与利益服务,特别是热带医学的诞生。
3. 就非洲大多数区域而言,19世纪下半叶才是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大卫·利文斯顿的赞比西探险(Zembezi Expedition)之后,欧洲的地理学家和自然学者开始搜集中非的动植物,然后送到欧洲的博物馆研究与展示。
4. 法国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通过对病毒的部分减毒制造疫苗。他在1885年试验出狂犬疫苗,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突破。
5. 世界卫生组织在1950、1960年代的主要活动是推动针对麻疹、小儿麻痹和天花的全球疫苗接种运动、防疟调查、处理贫穷与卫生的问题,以及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
6. 20世纪的全球卫生计划与政策,是与殖民医疗措施合作下发展,并保留了很多殖民的色彩。
7. 如果没有使用这些范畴而只使用“医学”一词,就无法理解医学的发展以及医生与科学家运作的不同脉络。而这也可能导致接受并回到19世纪的实证论定义,将现代医学与科学视为单一、普遍与进步的。
8. 历史学者对这些范畴有一些重大的辩论,辩论中反映出对这些历史过程与脉络的讨论。
9. 本书稍后会说明更多医学与科学的社会史,进而理解不需要只以“内史”的标准或研究方法来界定医学或科学。
10. 舒拉·马克斯、郎达·施宾格等历史学者已经指出,殖民医学深深涉入宣扬种族、性别与阶级差异的观念。我们要探讨差异的观念如何在现代医学与殖民政策至关重要。
11. 通过博览帝国主义与医学的文献来分析这些辩论,提供我们理解医学与帝国之间关联的方法。
《医疗与帝国》读后感(三):医学的发展是各领域协同进步的结果
“自然界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人类医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个规则。”俗话说:生老病死。这些都要和医院,医学扯上关系,虽然我们经常接触,但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平时和人聊天,我发现很多人对发烧和感冒的成因都不太了解。令我觉得医学科普这事真是任道重远。
回到本书的内容,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里面的两部分:
1:医药学的发展历程:
“17、18世纪的植物学是现代医学出现的关键,在19世纪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化学。”下面就沿着这条思路去整理下全球医学史的发展历程
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同时也开启了所谓的 “殖民生物,植物探勘。欧洲的自然学者、传教士、旅行者、外科医生对亚洲及美洲植物和草药的探索、观察与利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吐根、金鸡纳树、罂粟(鸦片)等)
这种对植物的关注投入,改变了欧洲医疗。 从18世纪开始,植物的研究、分类和实验成为欧洲医学训练重要的一部分。新的药用植物进人欧洲医学,出现新的药学实践,产生新的药典和医学文献同期,还确立了科学医疗的观察方法:双盲测试。比较出名的实验就是大航海时期对坏血病的治疗,确认了多吃水果(维生素C)对坏血病的治疗方案。
还有就是殖民时代,为了各区部队更好地适应当地水土,克服各地传染病传播,卫生医疗服务,监控的管理雏形也出现了。
19世纪,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诞生的药学科,这基于本草植物学的形式也凸显一个问题,就是植物的培植和有效成分无法为大规模为现代制药工业服务,为了将有效成分剂量标准化,以及在实验室中制造含有有效成分的药丸。工业化学制药这门学科出现了。(如阿司匹林)
同期,疫苗和病菌学说成为医学的两大支柱,影响了公共卫生政策、兽医学、农业和食品 工业。(如天花接种疫苗,巴氏杀菌法)
可以说医药学历史在 17、18世纪是全球化的生物,植物勘探观察与经验主义,而19、20 世纪更多的是实验室里的实验。
2:所谓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旧西方传统医学其实就是传承自古希腊那一套,借由瘴气和体液来理解疾病,其中那套所谓的放血疗法,连美国总统华盛顿也死在它手上,可见是多么的荒诞。
而我们现在更多津津乐道的所谓传统医学更多是一个被重新发明的概念,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一些表面似乎古老或永恒的科学观念与传统,其实往往是晚近的发明,而且是有意让它们看似古典而恒久,如医生毕业典礼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20世纪中叶才创造出来,为现代的目的和伦理关切服务。现代的医疗,更多的是依赖统计学、诊断试验等标准化流程,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民俗医疗元素再对症治疗诊断和用药。
其中中医这一块,在市场上比较有吸引力,原因之一是当现代生物医学越来越不具有个人面貌,更多受到大型药厂的利益控制,而中医更具有“人文”关怀,这算是另外一种“特别”治疗。
当然本书覆盖内容比较广,我就简单拿出两点出来讨论,这本书火不起来,着实有点可惜。
《医疗与帝国》读后感(四):现代医学的殖民黑历史:破除现代医学知识起源的欧洲中心主义
《医疗与帝国》这本书的特色,在于作者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医学的诞生。读这本书你会意识到,医学史的重大变迁,几乎都能和帝国主义的各个阶段明显地对应起来,二者在知识上和物质上都有直接关联。要叙述现代医学的进步,就不能不谈帝国主义的历史。
《医疗与帝国》的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是18至20世纪的英国殖民科学史和医学史领域的专家。他的故事从16世纪开始讲起,此时,西欧一些小国开始建立全球帝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欧洲医学从殖民地获得金鸡纳、加拉藤、烟草、吐根等新材料,获得了有关它们用途的医学洞见。19世纪的帝国时代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漫长的越洋航程,艰苦的殖民前哨与战场,使欧洲外科医生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而所谓现代医学的“全面转向”,亦即现代医学开始整合环境、气候与流行病学的因素,正是与欧洲在炎热气候中得到关于热带的热病、害虫与病媒的医学经验有关。
其中,“热带医学”尤为典型。欧洲的工业化与实验室的发展,对现代药品的生产很重要,也有助于现代制药产业的出现,从1880年代起,以法国和德国为主的实验室研究,发展出病菌学说(germ theory)。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病菌学说在热带地区崭露头角。这段时间,欧洲人认为热带的气候环境是不健康的,这些区域充满了疾病。对热带气候的关切结合了病菌学说,在19世纪末带来了“热带医学”这个新的医学传统。这个医学传统,将热带与热带地区的人体视为是致命病原体的天然住所,欧洲的病菌学说与实验室医学也被呈现为对抗疾病、病菌与社会/文化偏见的十字军。
由此来看,现代医疗的发展绝非一个和谐向上的人类进步故事,而是充斥着苦涩与残酷的西方殖民史:欧洲人与其他种族相遇,在现代医学思想中建立了种族与人类演化的观念;殖民军队与帝国主义的“文明开化使命”,也同样造成了疾病的全球化;现代医学通过降低欧洲军队和移民的死亡率,推进了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欧洲的医生、旅行者和传教士,把他们的医药提供给遭到殖民的种族,并将这样的行为当成慈善与种族优越性的表征。
《医疗与帝国》这本书的论点等于宣示:欧洲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是造就现代西方医学的关键之一,过去只关注西欧本土发展的现代西方医学史,如今必须改写。而此前,现代医学知识的起源与中心在欧洲。在19世纪,医学史的写作几乎都是由医生执笔,而非历史学者。这段时期所写的殖民医学史,是英勇的白人医生对殖民疾病、流行病与偏见进行奋战的故事,倾向于以进步的叙事以及伟人成就的故事来描绘医学史。
查克拉巴提是印度训练培养出来的历史学者,他在尼赫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印度任教,后来才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并在肯特大学任教。《医疗与帝国》参照了1960年代以来的医学史与科学史的新写作趋势,这种传统把医学描述为一种“社会知识论”。
对于帝国主义史反思的潮流影响了医学史的书写,它们将帝国主义呈现为负面角色,尤其是在当地社区传播疫病、摧毁地方医疗体制,以及将殖民地转变为昂贵的欧洲药物与疫苗的市场等方面。历史学者开始怀疑,与其说医学是赠予殖民地的礼物,或许不如说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工具”。或者说,欧洲医学在殖民征服的阶段,只保护欧洲士兵与平民的健康,而实际上促进了殖民;同时,殖民移民所带来的新疾病,通过毁灭当地人口而实际上帮助了殖民。
顶尖医学史学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总结这种探讨方式时写道:“欧洲人所到之处,便为当地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而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人口带来可怕的流行病——天花、伤寒和结核病。”当然,历史学者也在探问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西方医学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传播,是否也促进了福利,减少了病痛、疫病与死亡率?此外,如果医疗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换互动过程产生,那还能将之简单定义为西方或东方吗?
《医疗与帝国》为我们梳理了自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发展脉络,为我们理解危害全球的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尽管作者并未描述太多东亚和东南亚的情况。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卫生计划与政策,也在与殖民医疗措施合作下得到发展,并保留了很多殖民的色彩。对我们来说,了解殖民医学史,对于认识全球卫生的当代挑战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医疗与帝国》读后感(五):简体中文版自序
很高兴拙著能够出版简体中文版,非常感谢李尚仁研究员的翻译,让更多研究者和非专业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这篇自序让我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思本书及医学与帝国主义这个主题,尤其可以分析中国医学史上的帝国元素。
尽管中国有着强大的本土医学传统,且未像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那样成为殖民地,中国的医学经验还是受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将从四个独特的片段,探索帝国医学影响中国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贸易时代(1600~1800)。在欧洲对外殖民之前,通过丝绸、茶叶等商品的贸易,中国与欧洲建立了悠久的联系。与西欧诸强更直接的接触始于17世纪,欧洲商人来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当时的主要贸易网络从印度和东南亚来到中国。为了从中国获得贸易品,英国人在整个19世纪将印度种植的鸦片贩运到中国。这不仅引发了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而且还导致鸦片上瘾成为中国的主要健康问题。除了茶叶这些商品,欧洲商人还对中国的草药很有兴趣。被称为“中国根”(China root)的土茯苓对欧洲医疗至关重要,用它来治疗梅毒。18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亦对中国的手术工具深感兴趣。因此,从贸易时代开始,中药材被整合进入欧洲医学。
第二个片段是现代欧洲医学介入中国,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列强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欧洲医学的引进,如引入预防天花的詹纳疫苗(Jennerian vaccine)。中国有各种地方性的天花疫苗接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法”,即从患天花的病人身上提取出的痘,将其传给另一个人,希望能产生轻微但具有保护性的感染。詹纳疫苗不同,提取感染了天花的牛出的痘(牛在拉丁文中是“vacca”,所以此后这种方法被称为“vaccination”)给人接种疫苗。这种方法是由英格兰内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18世纪末发现的。疫苗接种这种现代技术在19世纪初由欧洲人引入殖民地。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主要城市,大规模疫苗接种也在19世纪引入,与此相伴的是欧洲“文明”观念的传播、更广泛卫生措施的引入和香港1857年的传染病立法。
第三个片段是19、20世纪西医在中国的持续存在。中国可以被视为热带医学的发源地之一,万巴德(Patrick Manson)这位“热带医学之父”1871年在厦门海关工作时有了关键发现。他当时还在教会医院兼职,观察到寄生虫丝虫病(引起被称为“象皮病”的寄生虫病)是由蚊子传播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科学上第一次确定某些疾病是由蚊子等媒介传播,这对疟疾的研究与预防以及一般的热带医学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一发现导致了在国际和地方专家的帮助下,从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实施疟疾根除运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成了“1950年代世界热带医学的中心”。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片段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整顿和振兴中医。本书在传统医学部分做了简略的介绍。“文革”期间,中国的传染病死亡率高,缺乏药品、医生和医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于是“赤脚医生”孕育而生,此举对中国和全球卫生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赤脚医生接受了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的培训,使用抗生素和疫苗成功降低了流行疾病,如麻疹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农村的死亡率。中国在1960年代还消灭了天花。
赤脚医生还成为当时全球医疗的典范,尤其对于几个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国家。赤脚医生成为20世纪全球卫生的基本原则,为大量人口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初级医疗服务(PHC),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这项制度。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匮乏的成功范例,成为1978年该组织《阿拉木图宣言》关于“全民健康”的典范。
我提到这些片段,是为了表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部分有着全球和帝国的联系。此外,传统的帝国历史书写,如热带医学其实中国贡献良多。因此,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中国医学史上的“全球”或“帝国”是什么?中国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大国,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
把中国历史与帝国历史看作是部分重叠的圆或许是有用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讲述这些关于鸦片、病媒、热带医学、疫苗接种和赤脚医生的故事,以及本书讨论的其他几个片段,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帝国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在两者中定位权力、剥削和边缘的历史也很重要。地方的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史和帝国史,反之亦然。
2019年7月 14日于曼彻斯特大学
李期耀 译;李尚仁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