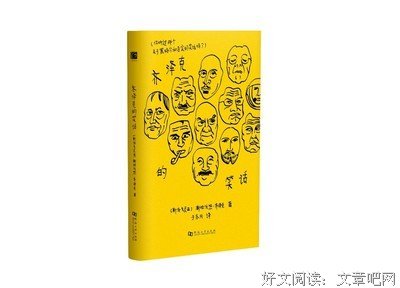
《齐泽克的笑话》是一本由[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1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一):来,笑一下,茄子~
作为现代还活着的这么大牌的一个大牌还愿意写书出书,我是抱着感恩、朝圣的心情捧读这本书的。
在读大学之前,还不明白哲学到底是怎么成为一个学科的,学哲学的是不是都是高考分数低被调剂过去的可怜人。慢慢的从黑格尔开始看,对学哲学的所有人又开始学渣崇拜高数满分的学神一样,真是旱的旱死涝得涝死……
这本书是8月读到的最喜欢的一本,以至于小小的一本手掌书上面画满了我的标记线和读书感想。
幽默越来越被人看重,甚至女明星们的择偶标准里,都开始出现他要幽默,能逗我笑这样的条件。但是笑话有没有作者,笑话为什么能让人笑,笑话的地域性,政治笑话……看毕《齐泽克的笑话》,这些问题的答案你都得不到~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二):读《齐泽克的笑话》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八个人住一间屋。因为年轻,因为想尽快让我们熟悉业务,单位出差的任务尽量派我们去;因为住一起,所以大家交流多。全国各地跑下来,晚上熄灯后,大家交流的多是各地听来的顺口溜,荤段子,也有政治笑话,但少。当时上新东方,在中关村出没,认识很多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听到很多笑话,政治的,讽刺性的多。有个同事,麻友,有心人,听到有趣的段子,笑话等等,都要记上一笔,这些年过去了,如果他持之以恒的话,应该是很大的一笔财富。随着阅历见广,看书见多,发现很多有趣的段子总是有着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比如,有个老和尚敲鼓的故事,就出自明朝的黄色小说《昭阳趣史》;再比如,有个流传东北的“算命”的故事,看徐铸成的回忆录,早在民国时期就流传了;这本书中的一个传自中国的笑话,我也听过;海峡那边政治性的讽刺笑话改头换面来到了海峡这边;还有,就像历史或神话的沉积一样,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每个段子的增减也是有迹可寻,日益丰满。这本书中的很多段子眼熟,新鲜的少,开始微感不适,自己八卦了,后来想想未必,与我们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科技进步相比,知识分子们编撰段子,荤段子的能力进步甚微,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这一小开本的一百多页的小书,居然卖价58元,可见人民多么需要段子,多么需要荤段子。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三):《齐泽克的笑话》摘录
莫墨斯,在《齐泽克的笑话》编后记中,设计了一个关于洋娃娃的笑话:
路易莎在抱怨她爹,借走一个叫汉娜的洋娃娃,还回来个破的。
“这是最糟糕的事儿,”路易莎说。“起初他告诉我他从来没借过汉娜,然后又说汉娜还我的时候没破。之后又说是借的时候汉娜已经破了,还有什么一个破娃娃实际上比好娃娃更迷人,因此要是汉娜没破,就太丢人了……”
“但她破了!”
“对,她破了就对了。然后他告诉我,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破娃娃都是完整的,每个好娃娃都是支离破碎的。”
“他是个疯子!”
“对,他是个疯子。他顺着那股疯劲,说汉娜破了也没破,取决于你怎么看它。然后他说,虽然娃娃是我的,破的部分是他的,还有他弄破汉娜是为她自己好。然后爸爸就开始哭,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我的破汉娜,所以「这就是没有东西」,然后他就做得好像递给了我没有东西。”
“老实说!欠抽的!”
“他还没完。他告诉我——非常严肃的——现在重要的不是破娃娃,而是娃娃她如何伤了我们的心,因而让我们结为一体并和我们同在。「我们都已经被这个不正常的娃娃汉娜伤了心,」他说,「她也因此治愈了我们。」听到这个我也开始哽咽了。我爹,他是个聪明的老混蛋。”
“他的确也是这样。”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四):哲学科普的一个范例
这本不足200页的笑话书,足足让我死了上亿的脑细胞。全因他的作者是——斯拉沃热·齐泽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猥琐油腻中年男”哲学家。
开篇就是三个女囚犯和五个男的有“深度”故事,要多三俗就有多三俗,看完觉得郭德纲和二人转都是清纯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若把这本书单单当成黄笑话集似乎也未尝不可,黄霑不也写过《不文集》么。然而齐泽克笔锋一转,开始认真分析起撅起的屁股背后蕴涵的概率论、博弈论、逻辑学,然后再升华成他最擅长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能把深奥的哲学理论蕴含在少儿不宜的段子里,这当然是大师的能力,但也是一种曲高和寡的无奈。纯理论的书籍必然无人问津,当做助眠教材或许不错。现代人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弃思考,做娱乐的奴隶,看上去已经有异化的趋势:身体好的运动员、头脑好的科学家以及普通人。须知,吾辈高中的理化知识大概只在17世纪左右,当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连科普都办不到,因为知识储备的差距大概和人与黑猩猩的差距差不多。更何况从诞生起就可以称为“天书”的哲学了。
所幸我经过多年的求学生涯和政治生活,拥有了一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勉强可以看懂一部分哲学命题——至少否定之否定还是听说过的,所以想要买来钻研的童鞋可要三思了。不过你要是仅仅把他当作特殊用途,别犹豫,可以说全是惯例了。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五):我们的恋物式分裂
1/约会后,男子送女子回家,在公寓入口处,女士问,要进来喝杯咖啡吗?男子回答,“有个问题,我不喝咖啡。”她笑着反驳道:“那不是问题,我根本没有咖啡。”
2/当初,美国问欧洲小伙伴,“你们要考虑加入我们一起进攻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吗?”欧洲郑重回复道:“有个问题,我们没有寻找那种武器的设备。”美国佬不屑道:“没关系,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
3/在社会主义波兰,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道:“你们大概没有黄油卖吧,抑或你们有?”店员回答:“不好意思,可我们商店不是没黄油卖,而是没卫生纸卖。那个没有黄油卖的商店在马路对面。”
4/一战时,柏林的德国人给维也纳的奥地利人发送消息说,“在我们负责的前线,战事严峻但还不至于是灾难性的。”奥地利人对此回复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是灾难性的,但不算严峻。”
5/在恩斯特·刘别谦的《妮诺契卡》中,男主造访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不加奶油的咖啡。侍应生回答:“不好意思,我们的奶油用完了,我们只有牛奶。我能给你上一杯没有牛奶的咖啡吗?”
6/齐泽克认为侍应生的回答正确无比,因为,没有奶油的咖啡和没有牛奶的咖啡,不是同一种东西。你得不到的东西,是你得到的东西的一部份。当你不拥有(比如咖啡没有奶油或牛奶),你得到的不是零,而是另一种东西。
7/齐泽克是个讲段子的高手。上述所有段子,讲双重否定,讲意识形态,讲意识形态的恋物功能,讲恋物式分裂。
8/所谓恋物式分裂,即你知道一个事实,同时拒绝接受它。明知灾难即降,但不知怎的,就是不重视。试图通过恋物,制造一个拒绝接受真相的距离,以便不用认真面对事实。
9/穷忙的人,感受最深。一年忙到头,时间没了,钱也没了。装做忙,是穷人的恋物式分裂。
10/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提供事实,铺天盖地的偏见和谎言,是当权者的恋物式分裂。
11/尚未获得世俗成功的一切项目,都是创业者的恋物式分裂。
12/名气、财富、消费、新闻、广场舞、微信、抖音......是普罗大众的恋物式分裂。
13/咖啡、阿森纳、阅读......是我特有的恋物式分裂。
14/事物是什么,很重要。事物不是什么,更重要。可恋,就好。
15/“理性来说”、“客观来说”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世界从未失去理性,只是不曾拥有过。
16/美国几十位精神病专家,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声称特朗普有精神问题。这是谁的恋物式分裂?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六):深刻的段子
2007年,齐泽克应邀来南京大学讲学。他不修边幅貌似一个“邋遢猥琐”的东欧大叔,却因思想深奥,写作富有特色而成为当代学术界备受追捧的明星。然而,一场场讲座下来,往往开场几百人,一时闪光灯齐亮,听众纷纷要求签名合影,到最后只剩几十号忠实粉丝硬撑着。大师遭到冷遇兴许是常有之事,思想明星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无法赢得人人发疯般热爱。 在最后一场讲座里,齐泽克终于按捺不住,决心上演拿手好戏:用段子,尤其是黄段子来阐释哲学。黄段子,他张口就来。他演讲的要旨和思路,多数人依旧跟不上节奏。不过收获还是有的,至少还记住了几个“深刻”的黄段子,以及英俊可爱的翻译在译人类某些器官和某些行为时,脸上突然一阵阵发红。 一个思想大师的犀利演讲,最终只被人记住几个段子。这个场面饶有趣味又令人略感无奈,它也告诉我们:思想和段子,人往往会爱段子多一点。对思想,我们可能要强打精神来爱,爱得很勉强,而段子才是我们的“真爱”。试问,谁在私底下没被几个段子弄得欢腾,即便明知它趣味恶俗,我们却欲罢不能?尽管大家在公众场合通常对此讳莫如深。 有个家伙买来所有齐泽克的书,只为了欣赏段子。他推己及人,想把散落各处的段子收集编辑成书。当他把主意告诉齐泽克,齐泽克激动地连喊:太棒了!于是,《齐泽克笑话集》自然而然问世了。 显而易见,我也说了个段子。但不管怎样,这本令段子爱好者欣喜的书诞生了。 如果非要对《齐泽克笑话集》的笑话中分类,我会分成两种:一,与性有关的,即多少沾点黄的;二,与性无关,却依旧促狭刻薄的。 先来个和中国有关的,据说确实是齐泽克在南京的饭局听来的:时下中国有个笑话,是两个还在娘胎里的双胞胎兄弟的对话。其中一个和他兄弟说:“我喜欢咱爹来看我们,可他每次到最后都很粗鲁,吐我俩一身。”另一回应说:“可不是嘛!咱叔就好得多:每次都戴个挺好的橡胶帽,这样就不会吐到我们了。”(见中译本第51页) 性,是人类生活里最隐秘的部分,在文明世界里总被掩饰装扮起来,披上面纱,形成禁忌。在若隐若现,朦朦胧胧里,人的猎奇心理泛滥。撩拨这层面纱,是齐泽克的绝技,他总以此来挑逗主导意识形态。 宗教一贯被视为与圣洁、善、博爱与庄严神圣相连,但齐泽克偏偏也喜欢拿宗教开涮。 他开起了耶稣的玩笑:耶稣的门徒不忍看到耶稣死前还是处男,没有享受过性爱。于是,找来妓女抹大拉的玛利亚,让她陪耶稣过夜。但是,耶稣执意认为她的阴道是巨大的伤口,试图帮她愈合。齐泽克以此为例,谴责西方列强试图强行愈合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伤口”,而再次给他们带来新灾难。(见中译本第14页) 许多事物已经形成固见,不容新的意见引入。笑话的促狭和刻薄,就像清洁剂,可清洗意识形态的污垢。 俄尔甫斯与妻子的爱情故事,往往使世人悲戚心碎。齐泽克却认为俄尔甫斯失去她后,并不会真正绝望,他只需通过联想和怀念来完成爱情,而省去朝夕相处的麻烦,妻子仅仅是满足他自恋的对象。齐泽克不仅颠覆了这一凄美的神话,甚至更进一步在“伤口上撒盐”:欧律狄克察觉到俄尔甫斯的伟大诗人命运,为成全他,主动引诱他回头,导致自己消失。哈,在齐泽克笔下,他们的爱情神话活生生变成一出肥皂剧的烂俗情节。 段子,是种很神奇的东西,它恰恰因上不了台面而更具吸引力。崇拜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它“从群众来,也到群众中去”,是广大民众智慧的结晶。它揭开了一本正经的假面具,解构嘲讽庄严的权威,也暴露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屁股”。因此,鬼才齐泽克十分看重这些被学术界漠视却广为流传的话语。他用富有洞察力的文笔,将那些段子编织进他的深奥文本中。齐泽克再晦涩的思想,也用笑话进行阐释,令人在戏谑的欢笑中,跟随他一针见血地直指时代的弊端和困局,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漏洞。 《齐泽克笑话集》看似轻松诙谐,内里却翻滚着齐泽克思想的炽热激情。他断然不会止步于段子本身,他总将段子“点石成金”,一下就转入严肃的思辨中,我们会措手不及地掉进由黑格尔辩证法、拉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哲学交织而成的思想网罗中。正因如此,除了那些篇幅极短,仅寥寥数语的笑话,很多依然不好理解。 在齐泽克的理论观照下,段子如此意味深长。现实和段子有一种精妙的关系,彼此相互映射。 但是,段子的确为批判和思考提供引子和材料,也应警惕其局限和无力。因此,齐泽克在序言里一上来即提醒:笑话还有积极维稳作用,让人在政治高压之下,还能偷着乐乐,让民众产生至少还可以用笑来还击暴虐统治的幻觉,而继续忍受不堪的境遇。须知,用笑从来瓦解不了暴政,笑顶多是批判的一种武器,根本不可能替代武器的批判。 但现在我们该笑时还是得笑。 最近一个最大的段子,是美国几十位精神病专家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声称特朗普有精神问题。 世界的“大哥大”选了个精神病人做总统,齐泽克老师,你怎么看?
作者:嵇心 刊于《周末画报》
《齐泽克的笑话》读后感(七):英国作家批齐泽克新作:生命短暂,读齐泽克是浪费生命
近日,思想家齐泽克最新著作《无望的勇气》(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出版。在书中,齐泽克认为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境况是彻底绝望的,然而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痼疾,是否依然有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
作家威尔·赛尔夫第一时间为《无望的勇气》撰写书评,刊于《卫报》。在文中,他认为生命有限,阅读齐泽克这种陈词滥调是一种浪费。
《无望的勇气》
尽管医学进步寿命延长,但人生还是太短暂了,来不及浪费任何时间去读那些过时的无稽之谈。不幸的是,上帝给我们送来了齐泽克这尊大神。齐泽克需要被严肃对待:在他洋洋万言的理论著作背后,他手持西方理论的大炮,唯一的意图就是集中火力开炮。
但《无望的勇气》其实是奥巴马应者寥寥的多元文化主义路演尾声的一场小丑般的亮相,齐泽克的表演方式是脱下裤子,伪装成滑稽戏演员。没错!生命太短暂,阅读那些老掉牙的东西真是一场浪费,尤其是那些从理论百宝箱里,左手掏出一把辩证法扳手,右手操着弗洛伊德主义(加了一点“拉康主义”的改良)螺丝刀的人。就算不是笑话的话,也是蛮好笑的。
就像在那部《变态电影指南》里旁征博引一样,在这本新书里,他从晦涩的中国科幻小说扯到舒伯特的《冬之旅》,翻来覆去地扯,因此齐泽克变成了英国学界那些左到不能再左的人眼中的万人迷。因为当他那些满嘴跑火车的理论大话说完之后,他的东西就显得既肤浅又不切实际。实际上阅读《无望的勇气》的时候,我经常想起那些老掉牙的关于经济学的笑话。
《变态电影指南》
“实践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在理论里也同样适用吗?”
在2013年那本《极度虚无》(Less Than Nothing)里,齐泽克用1000页的篇幅总结了他那种伪装在黑格尔主义下的齐氏世界观。在这本《无望的勇气》里,他开始应用他扭曲的世界观:好像他真的想让我们抛弃我们的价值系统,与他一起向那些有待建设的路障行进。对2016这个左翼的灾难年进行了一番检视后,齐泽克回忆了十月革命的后果——很快就变得清楚,遍及欧洲的革命不会发生,然而“要是这种完全无望的情势,通过激励工人和农民戮力同心,可以给我们机会创造一种和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又如何呢?”
然而,按照齐泽克的说法,20世纪的教训是“我们要集中全力来承担我们的绝望”。我承认,我不是很理解齐泽克这句话跟实际的当代政治的关联。但我怀疑他其实只是说给一小部分受众听的:就是那些充满自恨情绪的自由派人文主义者,他们可以充当知识工人无产阶级的护卫者,这些无产阶级是齐泽克想象的革命的主力。他们发现自己受困于历史的隧道,被主人命令去接受“寻找替代性道路的迷梦不过是理论上的懦弱的迹象”,然而“真实的勇气意味着承认隧道尽头的光亮可能就是另一辆到来的火车车头灯的光亮”。
齐泽克和另一位当代哲学家约翰·格雷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齐泽克是他的反对者。在给《纽约书评》为《极度虚无》写的书评里,格雷大肆抨击齐泽克对暴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痴迷。格雷认为齐泽克在知识上的源流是乔治·索雷尔。
《极度虚无》
齐泽克似乎永远在喋喋不休地向他那些基本上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读者们灌输反抗的理念的理念:我们在面对他揭示出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四张面孔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宗教原教旨主义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在希腊和西班牙发生的“新的激进解放运动”以及难民危机。但我们的绝望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虚假意识:一旦我们接受了2016年我们所做的抉择(特朗普VS希拉里·克林顿、脱欧VS不脱欧等)的似是而非的本质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接受其他人了,两者同样糟糕。
不过,现在我们必须加以纠正:一旦齐泽克辩证法的神经元被清除,那么我们就辨识出在《无望的勇气》中,他对左翼自由派如何回应我们当下境况的批评。齐泽克描绘了养尊处优的、自我放纵的烂好人形象,他们一边对要采取何种行动踌躇不前,一边沉溺于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充当键盘侠,为是否应该设置中性厕所伤透脑筋。他对性少数群体和身份政治如何给左翼设下魔咒这类问题的探讨通常归结为下述粗疏好笑的结论:当罗马城在燃烧时,我们却在掩耳盗铃。齐泽克关心罗马,关心所有自我运动的绝对论上的那些西方标签:他鄙视后殖民主义视角,他认为正在兴起的“creative commons”和互联网上的新事物预设着一场新的也是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的到来。
正因为我们对于“激进政治的误读”才使我们受制于两难的境地——全身泳衣还是裸胸?阿萨德还是伊斯兰国?那些不过是伪冲突而已。当我们读完《无望的勇气》之后,这种错误理解烟消云散,我们将加入希腊极左反对联盟、桑德斯失望的拥趸、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阵营,尽管齐泽克对于作为一种独特政治文化的英国未置一词。
这让我感到意外。前面的行文中我说过可能是因为他的幽默(其实他可以成为一个妙语连珠的作家)为齐泽克在英语国家收割了为数众多的拥趸,当然还有他的博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驾轻就熟,让我们正视吧,所有这些都可以博人一笑。但说真的,不论齐泽克如何在各个地方对美国大放厥词,他的观点在美国并没有比在英国更受待见,尽管他在英国媒体上的亮相屈指可数。在欧洲大陆也是这样——那里有一本叫《齐泽克国际研究》的刊物,但主要编辑团队都是英国人。就我所知,只有在英国学界,学者们才把自己定位在那些法国理论家的标准之下,这些法国理论家的理念构成了齐泽克富有生气的想象播下了种子,于是我们有阿尔杜塞主义者、德里达主义者、德勒兹主义者、拉康主义者们,尽管对于法国人自己来说,这种穿凿附会着实荒谬。
对我来说,一开始我对他如何从文化边缘冉冉升起没有明晰的印象,直到他有一天来我教书的大学做演讲,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思想界的摇滚明星:教室无法容纳鱼贯而入的他的崇拜者,演讲只好安排在体育场,100米的跑道上排着十排座椅,座无虚席——那是一千米长的拉康主义者啊!齐泽克演讲时,全场全神贯注屏息聆听。
当时(五年前),我很困惑,观众到底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我的同事们和其他英国学术界同行一样都对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感到无能为力,忙着剪掉他们身上那些破破烂烂的布料,适应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寻找大部分像我们这些全球化奢侈品网上专卖店(Net-a-Porter)购物者一样的革命者。
齐泽克
在格雷的文章中,他对齐泽克的哲学资质不屑一顾,认为齐泽克不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不合格的。但是在齐泽克的思想中,我确实辨识出来一条可行的理论脉络,将我们可能知道的和我们可以做的联系起来。唯一的问题是,“革命”仍然是一个完全空洞的范畴:仅仅是一群肆无忌惮的乌合之众。 格雷进一步表明,整个齐泽克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功能,它是因为标新立异而大行其道,因此,齐泽克的高调完全归功于他自己批判的体制。格雷还暗示了齐泽克有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态度:煽动他的疲惫读者和听众去进行他们仅在HBO迷你剧中见过的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对于格雷来说,由于齐泽克费尽心机试图与我们这种读《卫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保持距离,他代表了典型的后启蒙式的科学的政治进步的谬见。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两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所共享的却是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悲观主义,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虚无主义。
在前面的行文中,我说过齐泽克可能是一个非常幽默诙谐的作家,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弗洛伊德(或拉康)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真的没有这样的笑话。 很快我要在伦敦一个足够大的场地与齐泽克对谈,那位组织这场盛事的老兄得知我要给《无望的勇气》写书评时,战战兢兢地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希望我不要对这本书做出太负面的评价。
齐泽克的许多黄色笑话并不是他独创的,而是各种受害者所讲述的,在《无望的勇气》一书中,他复述了这样一个苏联时期流行的荤段子,十五世纪的俄国(当时在蒙古统治下),一个农夫和妻子正走在尘土小路上,被一名蒙古武士喝住。该武士就地强奸了农夫之妻,并因地上太多尘土而命令农夫托住他的睾丸,使之不至弄脏。完事后武士纵马绝尘而去,待其背影完全消失于路尽头,农夫起身放声大笑。他的妻子惊问:“你自己的老婆刚被强奸,怎么还能笑得出?”农夫回答道:“你没看见吗?我在托他蛋蛋前先暗地里蹭了一手脏泥,现在他蛋蛋上已经沾满泥巴。”延伸开来就是深夜讽刺节目主持人们的无能,他们只是往特朗普的睾丸上擦泥巴;进一步延伸,也是在揭示像我们这种读《卫报》的自由派的无能。我想知道,齐泽克是否有足够的幽默感来和我辩论无望的潜能,又或者他感兴趣的只是让那些他的衣食父母们用手高举他的睾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