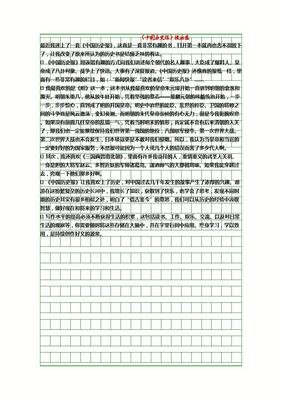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是一本由刘志伟 孙歌著作,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0.00,页数:2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精选点评:
●很震撼的著作!
●终于出了简体字的正式版,挺怀念两年前读的繁体字口袋本,为了讲课用,还动手扫描了一本。对比了一下,两版的内容似没有变动,书的个头也差不多。
●方法论部分需要细细品读。一条鞭法那块惊为天人。关于国家认同与地方社会的看法颇有启发。
●很多地方是充满洞见的。
●典型的刘老师语言风格。读此书,更能理解华南研究群体的作品及背后理念、关怀。
●治社会史的刘志伟老师与治文学和思想史的孙歌老师之间的学术对话实录,基本上涵盖了以刘志伟老师为代表的华南学派的主要学术脉络与观点。其关于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区分和界定,让人大开眼界,受益颇深。很有含金量的小册子。
●以国家制度为代表的稳定的整体框架不再作为区域研究的前提出现,承认地方的差异性,且从个体差异性逻辑出发,去寻找解释——充满差异性的地方动力如何将国家融入地方,如何形成完整的国家结构,个体如何具有及怎样的国家意识。
●妙语连珠,见解洞明
●社会史给思想史提供军火,思想史给社会史开脑洞,阴阳互补的学术对话集。还是刘志伟主侃的篇幅多些,说了些在严肃文章中不方便说的话,例如170页“宗族不是氏族残余,是在明清人身依附松懈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可以作为学术文章的补充。
●刘志伟和孙歌的对谈,比较散漫,但很有启发。重点讨论了以人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普遍与特殊及形而下之理、区域研究的整体性以及如何通过区域体现中国原理。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读后感(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这不是书评,只是部分摘抄。
非常好的访谈,孙歌的提问和追问很到位,刘志伟的回答收获很大,在很多方面,说出了自己有模糊感觉但完全说不出的话来。
访谈的核心之一是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以往我们讨论应该关注民众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应该关注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还是重视基层自治,这些都是从国家为主进行观察的历史。在刘志伟看来,如果转到以人为主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这种争论意义不大。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那么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政府机构也好,民间组织也好,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限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
所有的边缘叙述,它由于过于把自己设定在和中心对抗的那个位置上,导致了它完全是在复制中心的逻辑。
区域的概念,以往我对于区域的认识,基本是“自整体出发分割形成的概念,是王朝体系中的内在构成”,研究区域也是为了管中窥豹。刘志伟指出,施坚雅的区域应该是人的互动的空间形构,是以理性人的交换与交往行为作为论证的逻辑出发点。
我是做制度史的,刘志伟关于制度的不少观点对我也很有启发。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是从在制度之下人的行为,不是从当时流动的社会现实中去认识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用今天的知识和处境去理解过去的制度。制度的历史情境和实践形态,也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得到解释。“下有对策”,我们往往理解为对制度的抵制或偏离,其实这也是一种制度适用的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制度的实践机制。所谓“对策”,一旦呈现为一种结构性和规范化的方式或运作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东西,或者可以直接视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可能与文字所载不同,甚至对立,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来说,可能更重要。
其他有启发的地方尚多,需要常刷。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读后感(二):多元的“一”:复数的中国与希望
前几日与同学一起用餐,席间有人发问:“你来北京四年了,北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当然,这话并不是指向我。随后,身边的友人思索片刻,答道:“这太难说了。你站在二环以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故宫、天安门,这是北京。但我坐车一个半小时到昌平的一个乡村小学去考教师资格证,那里也是北京。”
如果用孙老师在书中的概括,可将我们上边的对话视为寻找“代表性/典型性”的惰性思维。实际上,将“北京”换成“中国”,问题同样成立,但答案不再是寻找空洞的符号抑或典型象征,而是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刘老师和孙老师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一个“一”,但这个“一”同时也是“多”,且二者并不矛盾,我们需要寻找复数的中国。具体怎么实践?刘老师认为,国家就存在于社会当中,并通过社会中的人、人际关系展现国家的制度、礼仪、赋税等等。概言之,就是从国家的历史走向人的历史,摆脱国家/社会,中央/地方,精英/民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的二元对立,历史就是活生生的人,制度、国家、社会都蕴藏其中。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这样一番景象,那么现代中国在刘老师看来,未免有些僵硬而悲观。以礼制和科举制为例,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基础上的“礼”可视作中国原理的核心内涵,也正是在这种不平等之上,中国发展出了一系列以“均平”为目的的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天赋人权或法律文化,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士大夫所推崇的礼制文化,但同时也诞生了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科举制,不过这种流动和自由是一种固化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等级社会,但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希望。这种千百年来的制度反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惯性和传统,而孙老师也认为,中国由此才没有爆发类似于法国的大革命,进而确立人人平等的法权观念。然而,相比于古代中国,现代社会似乎失去了曾有的有机性和能动性。在刘老师看来,如今的国人不再有那么多丰富的发展路径,反而都在循着自己领域内的一条道路,不断往上走,愈来愈狭窄、僵化。反观中国的当下的农村,那种曾经将国家制度巧妙地实践于地方中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仅仅留下了死的的基层政权。那么,我们的希望何在?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谈到,三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和中国,虽然世道不定,民族抗战,但人们却很自由,更满怀对生活的希望,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且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故而,我们今日阅读《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发现我们的中国原理,依然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性。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读后感(三):指引者
2018年10月11日,张老师推给我一篇刘志伟与孙歌的访谈,其中便是这本书的节选,深夜读罢便基本将中大的历史人类学确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正如读书笔记上有些傻傻的话语“欣喜不已而久久不能入眠”。
不过,过了这么久才在愿望即将实现与否的时刻前才真正翻开原书完整读下来,还是很感慨:历史的本质是人而非国家;普遍性真理其实只是一种伪事实的表述,关注过程内在动态探究比定性静态更根本;“中心” 与“边缘”是流动的,随着研究的问题或行为主体而改变;不将区域与国家视作局部与整体,而是将研究单位视作整体,以整体史进行把握为目的;不同区域研究中的“国家”不同,借用华德英的自觉意识模型,是因为人们通过重新建构理想观念模型来拉近与自身的近身模型的距离;中国原理即“礼”,是中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维系的核心范畴,其基础为差序化,因而平等观念难以深入人心;科举看似带来社会流动性,实际上仅为个体的身份流动,对打破社会的等级结构僵化无益,且等级结构由礼仪秩序规范着,进言之,流动与僵化两者并存且互相加强。借此,刘提出的“梯子之喻”是十分精妙的,大抵含义是:人人都可爬梯,爬到上面的可以踹下面的,下面的人则努力向上爬,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有梯子的存在,他们都有成为最顶层的可能性,而不会质疑梯子存在的合理性,更不会推翻梯子。引用其原话作为总结,即“在自己可以流动的社会中,没有人会真正批判甚至企图去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当今社会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比科举制更加单一化,我甚是期待更详细的论述,可惜因与主题关联不大戛然而止,也许是刻意所为。
最后附录部分的访谈录,对于刘的学术轨迹有所了解,我的脑子可能真的对经济史完全无感,即使我知道作为基本制度的经济制度相当重要,略微以一条鞭法为切口理解了明初到明中后期国家的转变。我以往在关注赋税制度变革对经济与贸易的促进作用外,忽略了其导致社会与国家之间中介力量的出现与壮大(如宗族、士绅)。刘志伟对其学术与郑振满“对立”的看法做以解释,指出两者及其两校的研究地域、切口、传统等方面的相异之处,但两者皆总体重视制度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并无迥异之处,只是个人学术路径的偏好而已。
最后的最后“历史学永远向所有学科开放”,看得我莫名其妙地感动。
“她谈的东西,我都是不懂装懂、夸夸其谈地回应;我谈的话题,她却总是努力放进她的思想框架中。” 刘志伟对此次对谈的评价在阅读过程中还是深有同感的,毕竟两个不同领域的学者沟通完全互相理解也并不现实。
可能因为对谈形式,相比北师版的赵世瑜所著的《历史人类学的旨趣》更清晰易懂,可以视作其基础版,后者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三个主要的历史人类学概念与详细研究过程,提及华南研究之外兼顾以山西为主的华北区域史研究。
还想再讲讲这本书与《历史学家的技艺》、《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数次让我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接受对历史事实唯一论的厌恶,回答反复怀疑历史学与自我在其中的意义。
可是我困了。
晚安!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读后感(四):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当然可能存在精英、民众的区别,但在整体历史观上,两者又可以表现出相同的史观和方法论,分歧在于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事实上,社会成员区分为精英和民众,是从国家历史的角度建立并定义这些范畴,视其为有既定内涵、清晰边界,固定指向的概念。因此,研究无论是突出“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还是着重“重视社会基层的自治”,都没有逃脱国家的框架。历史认知应该是以人为出发点,无论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政府机构也好,社会组织也好,不过是人的行为在交往中制度化、单元化的单元。当然,这影响并规限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以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进程。所以,理解中国只能在传统中国观念上去理解。以乡村民主选举为例。中国乡村社会“自治”和“民主”形式下,实质存在“礼法”的秩序,在乡村推行民主越是顺利,越是给予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机制,就越不可能出现现代的民主。
在此基础上重新感受“中心—边缘”模式,研究问题、研究对象能够通过空间表达或呈现,但随着问题、对象的变化,中心可以是多元的、流动的,本质是由人的活动形成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和交往空间。因此,部分群体的边缘叙述,把自己设定为和中心对抗的核心位置上,实质上是在复制中心的逻辑,把自己中心化。
区域研究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一个研究手段。在确定一个研究区域时,首先是基于其整体性,但也不能忘了其是更大整体局部的属性。在那些规模比国家小的单位里,国家不仅是外在的政治权力,也内在于这个整体中,具体以权力、意识、礼仪等不同方式存在和表达。因此,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实体,不是向下互动和渗透。
那么,在不同区域中,中国是一个不同的中国,中国是如何成为一个整体?根据华德英的模型,人通过两种模型理解自身和他人,一是自觉意识模型,一是观察者模型。前者又细分为他们的近身模型,即基于直接生活经验的意识建构;他们的理想模型,即对自己身份属性应该如何的意识建构;他们作为观察者模型,即看到其他社群的意识建构。每个人都有一套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同时接受了一种身份属性后,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型,并拉近两套模型的距离。这个距离的拉近,既可以改变自身模型,也可以对理想模型理解的再建构。而小规模区域研究,是因为从中看到国家的存在,进而理解国家在不同时空的存在和表达方式,而非从不同区域中提取共性。这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史观,即人的行为、影响人的行为和影响人们行为的结果视为具有整体性联系的事实,从整体性联系中把握和理解。
至此,可以理解在主体和客体的有限性下,我们根本不能追求超越时空的所谓“普遍性”。每个人对“普遍性”的想象,实质上是一种个体的事实,形式是具体的,但在知识结构上赋予了认知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所以,历史认知既不追求普遍性,也不认可碎片化,追求的是对人在既有结构下,行动并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认知。区域研究普遍性的意义是作为方法论上的意义,追求作为前提和工具的普遍性而非终极的真相。
同样,“是什么”是研究的工具,是作为工具对认知的分析限度和理解空间,而非研究的终点。因为其表述和定义在研究中随时空变化、视角变化。否定“是什么”作为研究的终点,并非与历史虚无主义划等号。可以说,在方法论上,两者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的理性是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动力,而非把真相当宗教。
以制度史为例。下有对策,呈现出结构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文字写下的条文规定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被直接套用在现实中,而在于现实中一再从这些规定出发衍生的种种变通做法,是在实践中由条文和应对条文的对策之间互动形成的结构。明初,赋税制度是通过把实物和力役摊分在编户齐民上实现的。 出于均平原则以及实物和力役在价值上的难以核对,随着明中后期后的社会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为户口成为了纳税户口提供了可能。白银进入国家的运作系统,使国家可以依靠社会中间层力量达到乡村的自治。这是国家的转型,而非力量的弱化。但同时,也使本来趋向于瓦解的社会获得了一种在新机制下延续的条件,更深层次的结构却保留稳定下来了。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读后感(五):当我们就方法论谈方法论的时候就会想起……
相比于孙歌借助“形而下之理”在理论层面对抗抽象的普遍性之艰难,刘志伟以及华南学派仅仅将普遍性理解为一种分析历史的结构过程时人为的认知结构。因此双方尽管“共享”了对于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中心与边缘等诸种宏大叙事的批判,但在各自的研究中却迈向了不同的道路。后者在本书中成功展示了华南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结论,无疑成为了本书的主角。我以为这种研究或可视作被多种现代理论所重构了的中国古代史,在其中可以看到如结构主义、年鉴学派、制度经济学等社会经济理论理论的深刻影响。
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刘所展现的“方法论自觉”其实是一种韦伯式的方法论谦抑。也就是说,悬置普遍性与本体的关系,普遍性在研究起点和过程中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在终点上以观念的形式呈现为某种结构,他甚至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终极的普遍性乃上帝之事。而他们所致力的区域研究之意义仍然在于方法论。个案的经验研究的普遍性,是通过揭示能动的主体在既定结构中交往、实践产生的集体性结果,为社会变迁过程的机制提供一种因果解释,而这些机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价值中立和“理解社会学”的,它们最终是在方法论和人认识自身行动的层面对于普遍性的丰富。
具体来说,从有目的的人之行动作为逻辑起点,描述在人的交往活动中被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构单元和社会网络,这种结构单元既制约着人的选择,又成为人赖以行动的根据。在此,国家历史被置换为人的历史。而他所强调的总体史视野,非借助这一系列社会、经济研究方法的重构而无法抵达。这里的原因或许并不复杂,因为要是仍然习惯于国家视角和普遍主义,那么唯有国家和普遍主义才具有整体性。而总体史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国家或者制度,恰恰是在个体行动与地方社会的逻辑中“创建”起来的。与通过国家正式机构颁布、用文字写下的法律(类似于“静态切片”)相比,唯有经历民间的“下有对策”主动适用的“制度”,才值得被作为讨论的对象。这就引出了关于“institution”的理解,即惯性化的运作机制和规范化的行为方式。
在他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此种制度实践所带来的是堪称神奇的后果。人们通过主动将国家纳入自己的生活选择中,以既隐蔽(国家视角下)又现实地再生产种种“被统治的艺术”,从而维持了正式法律文本存续的体面,二者的共生关系使得生存之艺术“无意于”直接改变国初祖宗之法在国家层面的表达。
其次,无论在整体史或是中心——边缘的构想,他都坚持了“将…作为方法”,总体或中心只是我们将一个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时必要的预设。他因此将国家视为地方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观察其在乡村如何以权力、秩序和观念仪式的方式展示自身的存在。这里面可能存在的解释困境又被“礼”这一根本性的支配秩序所统合。当然我们可以就此提出疑问(也许这超越了严守理解的任务),即是否存在过于强大的暴力,以至于其外在于被我们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或者说,地方社会为何要“主动”将国家作为安排与理解自身生活的一个要素?
从他的研究来看,明代的户籍制度中“户”的概念,从明初编户齐民之下承担赋役主体演变为一条鞭法后一个类似账户的登记单位,这一制度的变革为明清宗族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中介性的空间。这一历史进程又与白银“偶然”地大量流入息息相关。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来看,赋税财政制度是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而朱元璋“理想”设计的实物贡赋、强制纳粮当差制度,由于货币和市场介入权力运作体系,成为资源配置中主要支付手段,进而改变了赋税的手段、方式和对象,并在这背后是王朝与编户民权力关系的变革。这些研究对于“制度史”的意义在于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而这里再次抬出的国家与社会二分并不与前文的表述相冲突,因为我们只要再次将这一模式作为工具对待(而消除其潜在的现代性或自由主义预设),那么这一地域的历史就可以作为理解国家在地方何以可能的支点,或者说,社会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国家。而且在他的论述中,这一进程并没有明确地指向某种近代化的契机,而是因为给一个崩溃的结构续命,将文本层面或者说初始状态的治国理念、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体系保存了下来。(但由于本人不懂经济社会史无法评价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