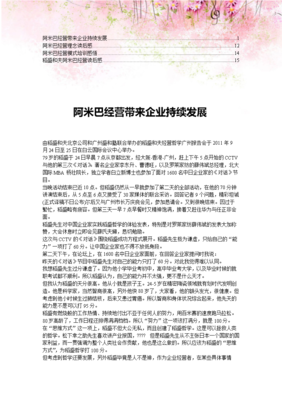
《讨厌的京都》是一本由井上章一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讨厌的京都》读后感(一):写书只是为说些孩子气的话
一度觉得这个封面很好看这本书挺小只的,一天就能读完。书的颜值也是在线的,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日本那个满是青枫与苍苔的千年古都。 作为一本充满着日式文学风格的作品,这本书的语言就很平实随意,像是在一个夏日有风的夜晚,吃着西瓜听一名老顽童在闲聊些“反抗京都”的孩子气的话。因为本就是闲聊,所以也就不求什么严谨的辩证过程和最终的讨论结果。但又因为所述皆是事实,作者似乎又想让大家以此评评理,为自己所受的地域歧视讨个公道。没错,不像冰心《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这本书并没有赞美与宣扬,只有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事后的愤愤不平,为了反对而反对。作者通过这样有趣的情感流露,带领我们了解了一名京都郊区居民的真实看法。 作为一名出生在嵯峨,后生活在宇治的“京都洛外人”,作者感受到来自京都市中心的“ 洛中人”的鄙夷,并坚持写下这本书,作为对洛中人高高在上的心理的反击。这种地域歧视让人很容易想到我们的北京和上海,只要把其中的地点、人物、情感逐一替换,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真是有着神奇的相似之处。 不像北京有一圈一圈的地铁线可以作为界线,轻松就能划分“北京血统”,上海的鄙视链要复杂的多。上海有核心城区与郊区的区分,有浦东浦西的区分,有苏州河南北的区分,有上只角下只角的区分。区和区之间,甚至一个区之间都免不了要暗搓搓比较一番。就像前两年并入静安区的闸北,仍旧是“新静安”;而吃下南市与卢湾的黄浦区也不是一个整块。引用书里作者的分析就是:“近代化让社会阶级变得更加平等,逐渐不再允许恶意对待下层阶级的人,但人类一旦处在优越的境地中,内心潜伏的天性便会肆意作祟,生出践踏劣势种群的欲望。这是一种难以杜绝的原始本能。人们默认在某些无伤大雅的场合可以将这种本能释放出来,而且不会有人出面制止……过于严重的歧视行为已逐渐从社会的表层消除,但人类产生歧视的心理本质上却没有一并消失。这样的心理一旦找到‘轻度歧视’的突破口,或是遇上连‘歧视’都算不上的小小的负面因素,就会肆意向外蔓延……正因如此,瞧不起洛外的言论更容易大行其道。” 我觉得作者的分析很是到位,他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地域歧视现象的新的解释。而且根据这个解释,这种现象暗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而很难消除。既然不能消除,那只好加入反抗的大军。或许会有人通过搜集材料进行详细严谨的辩证,但更多人也就是像作者一样只能愤愤不平地讲几句孩子气一般的气话。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东西是人主观的认知,是绕指柔,再锋利的理性武器也拿它没有办法。而且,就像作者发现的,这些反抗者的心中似乎也多少掺杂这类似的认可,反抗这种歧视也是在反抗自己。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性别、父母、家乡都是早已固定好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公平是永远都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这些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定义了我们是谁,而且通过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思想,间接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是谁?把所有信息都抛开后我们是谁?那些信息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难道要把思想也抛开么?
除此之外,书里也讨论了日本僧人逛花街的现象,对此,作者的一番解释也吸引到我:“过度的信仰往往容易带来恐怖主义。相较之下,穿着僧袍和艺妓玩乐的京都僧人们,说不定反而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或许只要像他们一样沉溺于享乐之中,信仰就不会走向极端。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至少不会因为过度的崇拜而引发争端。”这种说法很是新奇,但转念一想也不无道理。清规戒律不是常人的生活,或许走下神坛沾染上人间烟火气,也是僧侣们削弱自身力量的一场和平献祭。
我很喜欢在不同的书中看到别人不同的观点。这将是我们开拓自己视野,转换角度思考这个世界的良机。如果只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而如果能够体验不同人思考的方式,我们将获得一次又一次重新生活的乐趣。
《讨厌的京都》读后感(二):千年唐宋遗韵之外,京都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有一些景意,在京都,恰好最宜以唐诗呼唤出来。如“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如那些茶庵小店矢意保持的“竹径有时风为扫,柴门无事日常关”的竹篱茅舍。
台湾最受欢迎的散文家舒国治对京都的描写,让人立刻就理解了他的“每兴起出游之念,最先想到的常是京都。”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将唐宋古韵保留在桥、寺、溪、树的细节之中,成就了京都独特的魅力。尽管已不知去过多少次,身为游客,舒国治自称京都的“门外汉”。对于生活在京都几十年的当地人眼里,它又是怎样的呢?
日本建筑史学家、民俗文化学者井上章一的《讨厌的京都》,让我们看到京都风雅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井上章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史,因提出“美人论”、“关西文化论”而广为人知。代表作有《美人论》、《现代建筑家》、《打造出来的桂离宫神话》等。
洛中洛外,究竟是谁的京都
自平安京时代,京都已时不时被比喻为“洛阳”,由此衍生出了将都市中心称为“洛中”,都市外缘称为“洛外”的说法。
作者第一次感受到“洛中”人的高高在上,是在京都大学建筑学系的上田笃研究室时,为町屋研究项目,拜访京都下京区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杉本家旧宅。
杉本家第九代当家人听说作者是右京区嵯峨人后,揶揄道:真令人怀念啊。以前那一带的农民经常来我家帮忙挑粪。
身为“洛中名门”,第一次见面就如此不友好,作者还反思是否自己失礼在先,但随着接触的洛中人越来越多,他意识到这是每个洛中人都有的“强烈的唯我独尊”。
这种毫不遮掩的歧视不仅对普通人,小有名气的洛外人也是同等“待遇”。作者接着讲述了他的另一见闻。2000年夏,上京区的KBS大厅里举行的全日本职业摔角联赛上,当一位宇治选手说“京都出身的自己能回到京都这个擂台,很荣幸”,立刻招来观众们此起彼伏的嘘声和倒彩:“区区一个宇治人就别冒充京都人了!”
更有甚者,大龄单身的洛中人在感叹过了三十就不会有像样的婚事找上门时,对“不像样”的解释是,相亲对象居然是洛外人。
一面对洛中人的傲慢深恶痛绝,坚定地不说自己是京都人,一面沾染了洛中人的习气,瞧不起地理位置更偏远的“乡下”。被歧视并不好过,却又不由地歧视别人。作者说因为“人类一旦处于优越境地,便会生出践踏劣势种群的原始本能”。或许吧,否则各种“歧视链”层出不穷,要如何解释呢?
吐槽洛中人,讨厌京都,坦承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并将这无奈归结为本能就完了吗?当然不是。在第一章第十节《巴西的“KIOTO”》里,作者跳开去,幽了京都一默。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有家著名的专业除虫公司叫“KIOTO”。至于为什么用跟“京都”罗马音相同的名字,经了解是为了纪念传授除虫配方的日本人。
洛中人无比自豪的京都名号,在里约市民的印象中,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却是蟑螂等害虫。 就算是自尊自大的京都人来到此处,也要被迫沦为和蟑螂同等的联想对象。或许这种贬低京都的说法令我十分开心,我逐渐不再抗拒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来自京都”了,甚至会抢在别人询问前就开口。这“复仇的快意”令人忍俊不禁,它好像也隐含了些许言外之意。
花街、寺院与传统文化
提起日本,最先想到的除了富士山、樱花,就是歌舞伎和有着禅意庭院的寺庙。第二章《和尚与舞伎》和第三章《佛教不为人知的一面》介绍了京都仍保留浓重的传统文化的根源。
花街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栖息地,它不仅很好地保留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和服与传统发式,传统建筑数寄屋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除了花街,寺院在延续正统日本庭院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在京都,身披袈裟的僧侣们和艺伎堂而皇之厮混在一起不是什么新鲜事。”
虽然对“酒肉和尚”感到羞愧,作者又宽容地说“过度的信仰往往容易带来恐怖主义。相较之下,穿着僧袍和艺伎玩乐的京都僧人们,说不定反而能给人们带来希望。”
其实,寺院世俗化的体现不仅在于流连花街的和尚。还有观光寺院在赏枫时节对白天场和夜间场分别收费的贪婪,对门票收入征收“古都税”的抗争。
对寺院考究的庭院造景和仿荤素斋,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据资料记载,从十四五世纪开始,京都的寺院就承担了今天酒店的功能。当然不是招待普通人。武将和随从才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富于禅意的庭院美学为了抚慰武将们的心灵。
哪怕只有片刻光阴也好,他们也要让这些明日可能又要投入战场的武人,在美景中偷得浮生半日闲。为满足武士客人们对食物的要求,口感与外形近似肉类的精进料理在努力摸索中越来越色香味俱佳。
传统与信仰,欲望与修行,令京都的古韵别有一番滋味。
公元794年到1868年,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平安京发生了许多朝代更迭的故事,书的最后两章讲述了关于那段历史的见闻及其引发的思考。
“写别人不敢写”的有个性的内容,不仅让这本书激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一时“洛阳纸贵”,更让我们从这位在京都生活了60年的文化学者笔下,见识了古雅之都的傲慢与烟火气。
《讨厌的京都》读后感(三):不为人知的京都,原来你那么“讨厌”!
最近听一位日本朋友提到京都,因为东京奥运会,京都有一大批酒店客栈翻新,花了很多钱,可是由于去年的特殊事情,那些酒店不能开业,好多都关门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惋惜,因为我对京都有一种莫名的情节,感觉那里才是真正的日本。
当初去大阪玩,还特意找了一天去了趟京都,虽然只逛了一个伏见稻荷已经把我累得半死,没住上京都死贵的日式酒店,但是仍旧很知足。就算只吃到一个糯米团子,我都很开心,因为总感觉我呼吸着京都的空气吃着京都的食物,我真的来到了日本。
直到我看到了这本《讨厌的京都》,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
作者井上章一,是日本建筑史学家,民俗文化学者,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看到这些是不是感觉跟讨厌京都这件事情怎么都挂不上边呢?
或许这是作者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呢?
洛外人
作者从开篇就提到他到了20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京都人,他出生在京都市右京区,生长在嵯峨,在嵯峨生活了20年,但是京都市里的人却不赞同他是京都人的说法。
因为京都人把京都划分的很清楚,除了京都市以内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洛中人”以外,其他地方的人都属于洛外,换言之他们都不能称得上是京都人。
虽然作者已经习惯了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正是他不喜欢京都的根本原因。他耿耿于怀到在作者简介中仍旧称自己是嵯峨人。
作者还把京都人瞧不起洛外人归结到东京媒体的吹捧上,正是因为他们的纵容、抬举,才造成了京都人的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的性格。想一想的确如此,我不也认为京都才能代表真正的日本吗?可是谁叫其他地区都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唯独京都保持着日本古时候原本的样子呢?
京都的古建筑、寺庙那么多,给我留下了古典高贵气质的印象。如果想感受一下日本文化的气息何人不会推荐京都呢?
京都的和尚
说到寺庙,我想起来一部日剧,《5-9私に恋したお坊さん》(朝五晚九帅气和尚爱上我),这部剧中山p(山下智久)扮演了一个呆萌的和尚,他爱上了石原里美扮演的英语教师。
对,没错,你没看错。日本的和尚是可以恋爱、结婚、生子的。他们的人生太完美了,完美到日本的和尚都超有钱。
在本书中井上先生也提到了京都的僧侣,他们会沉迷于夜生活,有时候也会穿着袈裟去茶屋,甚至堂而皇之的跟艺伎们玩“翻和尚”。翻和尚是一种花牌,作者认为是一种对僧侣不敬的游戏,在游戏中,大家都不希望抽到和尚的牌,因为会丢掉手中所有的牌。
“他们并不介意穿着袈裟光临,应该是觉得没什么好愧对世人的吧。”
京都的茶屋似乎也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了,而且十分欢迎和尚的光临。
“不管是祗园还是先斗町,都是靠我们撑着的。要是我们都不去光顾的话,大概那些供养艺伎和舞伎的店家都要关门大吉了。”
京都的和尚对自己的认知也完全符合“京都”这个地方人的特点,自大、狂妄、不可一世。
作者对这些酒肉和尚的行为感到羞愧,不愿意让国外的人看到如此景象。我最初以为这只是一种文化上面的差异,但是看过这本书发现日本地域差异也如此之大。
对于和尚不能成家,有一种解释。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年纪轻轻就后宫佳丽三千,但是他厌倦了这种生活,也受够了女人,所以选择了出家。如此一来便产生一种说法,唯有彻底经历过,甚至到了厌倦的地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出家人。
如果这么说的话,京都的和尚们才是能真正理解佛祖的人,他们为了更加贴近佛祖,才故意沉迷于酒色之中。这无形中将自己置于万恶之源,等待凤凰磐涅,达到超脱境界。说起来很高大上,很无私,其实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佛教不为人知的一面
京都除了和尚十分有名以外,寺庙也很有名。我当初只去了伏见稻荷,爬了好久的山,走了好多的路,终究没能走到山顶,听到弟弟说很快就爬上去了,至今后悔不已。
逛京都的寺庙需要交门票,白天和晚上的门票还不一样。如果有媒体采访需要拍照的话,拍摄照片也需要交钱。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和尚都很有钱的原因吧!而且交给寺庙的门票钱不用纳税哦!为了寺庙纳税的事情,还发生过“古都税”之争。寺院为了不纳税,便关门大吉,直接影响了观光旅游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结果以市政府放弃征税而收场。
最后我不禁感叹一句:“すごい!”
写在最后,作者从始至终都“讨厌”着京都,批判着京都人唯我独尊、高傲自大的性格,他以自己是嵯峨人为傲,从各个方面来证实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在意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地方,是不会注入那么多的精力来思考的,所以我仍旧觉得作者是对京都“爱之深,责之切”。通过这本书,我对京都加深了了解,想到我把这本书给日本朋友看的时候,她的那个不可思议的表情,似乎不了解京都真正面貌的人还大有人在呢!
《讨厌的京都》读后感(四):对于地理优越感,其实全世界的看法都一样
这本《讨厌的京都》是日本作家井上章一的一本散文集。井上章一是日本的建筑史学家和民俗文化学者,是国际日本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史。
井上章一出生在京都的嵯峨。可是他为什么把这本书起名叫做《讨厌的京都》呢?
说起来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虽然嵯峨归属于京都,但是京都人却常常认为嵯峨是乡下。嵯峨出生的人自然也就不配称自己为京都人了。
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了井上章一年轻时候的一个经历。井上章一因为学建筑的关系去拜访了京都一个比较古老的家族山本家。在两人闲聊的时候,山本先生问他是哪儿人,作者老老实实的回答是嵯峨人。结果山本先生说了一句话,以前那一带的农民经常来我家帮忙挑粪。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笑了。即使隔着书也能感觉到井上章一的尴尬。山本先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这句话里面透出来满满的都是“嵯峨人不过就是帮我挑粪的农村人嘛。”这样的一种清高感。这个鄙视的意思太明显,以至于这句话给井上章一带来的自尊上的伤害,让他把这句话记了几十年。对于当时收到的不经意的恶意,作者的怨恨,从头到尾都记录在这本《讨厌的京都》里。
看这一段我就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地理优越感”真的是不分地域,存在于世界各地。就这一点,日本人和我们也没什么两样。
我身边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学刚开学的时候,我一位室友非常积极地在班里面寻找自己的同乡。终于寻到了一位同学和他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他很热情地跑上去和人打招呼说:“你是XX的吗?我也是啊。”结果对方对他说了一句:“我是XX城里的。”气氛瞬间冷场。我的这位室友就犹如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从此之后,他对寻找同乡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所生活的城市,虽然不是在帝都魔都之类的地方,但二十几年前地理优越感还是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省内经济发展不太均衡。省南部的人往往就觉得省北都是乡下地区。这种地理优越感一直贯穿到我上大学之后。工作之后有的同事即使工作能力十分的强,都已经升到了副总的位置,也不太愿意说自己来自于省北地区。
虽然当时因为省内发展慢慢均衡了,人员流动也比较频繁,大家已经不介意地理上的差距了。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朋友和同事对于自己来自于哪里心存芥蒂。
我看了这本吐槽这种优越感的《讨厌的京都》之后,我才能对那时候来自省北的同学有一点感同身受。
来自魔都和帝都的同学,对于地理优越感这件事情可能更能有体会。我曾经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因为口音问题被司机问是不是从魔都来的。我们说不是。司机就说,还好你们不是,不然我就不做这单生意,把你们赶下去了。可想而知,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京都的人在京都之外,依然散发着自己的地理优越感,这种行为确实是容易让人厌烦。
每个京都人都有强烈的唯我独尊的意识,甚至有人当着作者的面大放厥词,瞧不起你们嵯峨人,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曾经也在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年纪大的日本老人翻过白眼儿。那就是一种国家地理的优越感了。
实际上看这本书作者的自序,你能感觉到井上章一的性格并不是那种传统日本人隐忍的性格。他可以在书的前言中陈述自己这本书卖得特别好,已经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如此大言不惭的日本人,说真的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性格的井上章一对于地理优越感的怨念,几乎贯穿了整本散文集。无论在哪个话题之中都可以让人联想到他曾经被地理优越感伤害过。
有时候你又会觉得作者还是挺可爱的。因为他可以把这点抱怨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我想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卖得好的原因,因为他把这点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心思专门写成的一本书,让有同样感受的人看了之后心有戚戚。
整本散文集基本上就是作者的一本吐槽集。除了这第一章吐槽了京都人的地理优越感之外。在第二章还吐槽了现在京都的和尚喜欢寻花问柳的现象。
很明显作者是看不惯僧侣和艺伎或者女公关一起玩耍的风气。甚至发出了“也只有日本的和尚才会毫不顾忌地和艺伎一起谈笑风生吧。”的感慨。
然而实际上各国的僧侣可能都比之前的苦修时候要现代化得多。中国不也有喜欢时尚的网红僧人吗?
吐槽完和尚之后井上章一又开始吐槽寺庙。对于寺庙收门票,白天票和晚上票还分开来卖,不交税这一点。井上章一觉得作为寺庙还沉迷于金钱这种事情,完全不像是佛门清净地应该做出的事情。
在最后两章作者终于回归了自己的本职,建筑史和和日本民俗。
在这两章中你可以了解到京东的一些简史和当时皇室内的勾心斗角。
这本《讨厌的京都》曾经获得2016年新书大赏第一名。书封上的那句话,基本上可以概括了这本书的基调。
是京都把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不可理喻,带着有色眼镜的人,是京都这座城市,让人无法平等待人。井上章一虽然厌恶京都中部的人对于嵯峨的地理优越感。但他自己其实也是身为广义的京都人,对于更远地方的人,也抱有一种同样的微妙的优越心理。
换句话说,作者其实意识到了,这样的地理优越感是人的一种本性,他一方面讨厌别人对自己有这样的优越感,一方面也不能控制自己,对其他人也带有同样的眼光。这其实是一种人性,而作者把自己的这点小私心写出来,让有同样遭遇的人感觉到一种不能说出隐秘的畅快。
《讨厌的京都》这一本散文集是非常轻松和愉悦的。你可以带着一起吐槽的心理看这本书。看完之后你可能会产生和作者一起骂过街的革命认同。这种阅读体验其实还是挺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