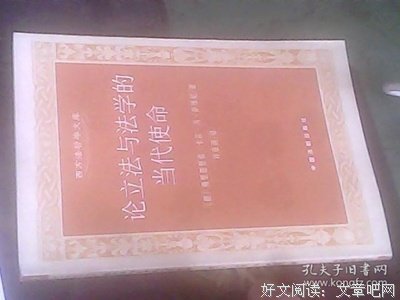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是一本由[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作,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1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精选点评:
●巨擘中的巨擘,偶像中的偶像呀= =
●可以看看英译本
●不要因为自己文言文能力差 就指责许老师的翻译 受益匪浅 感谢许老师
●没那种命
●还以为只有我觉得翻译有一点尴尬 虽然我的水平是远远不及译者了 但是看到结语许先生说法语部分译自清华法学院的学生 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不过确实在我眼里觉得这本书论述过于晦涩了 初学者如我 其实不应该选这本书做主要读书报告 不过既然读完 再多看看论文和大家的评价吧 祝好~
●擦,忍不住来点一下,翻译你妹的,正常说话不行?文绉绉的看了都觉得费眼力!
●迷迷糊糊
●翻译如果再直白一些就好了
●划时代意义的一场论战,历史法学自此开山立派,萨维尼成就不朽之名的开端。可惜德语汉译的表达总归怪异,许章润的翻译风格作学术研究又略显赘余,整体阅读体验并不佳。
●果然都在吐槽翻译的事儿,这翻译白白扣了一颗星。。但书是很好的,只是不习惯这样的翻译,读起来费力。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读后感(一):读《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11.2
这是我读萨维尼的第一本著作,序言部分了解了这本小册子的背景系与蒂博关于是否应制定统一的法典之论战(终于知道了,蒂博是干嘛的,此前我了解的名字是蒂堡)。 萨维尼在强调法律应与民族生活完美结合(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在表明他自己观点的时候,它既说明了不赞成统一法典的原因,也论证了统一法典的种种不现实之处,但即使是论战,谦谦君子亦说明与蒂博“我们心中所竭诚向往的,乃为同一目标,而朝思夕虑者实现此目标之手段也”。 小册子虽短,出现了极大的阅读障碍,一则,没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不熟悉萨维尼的说理方式,阅读吃力;二则翻译教授文言文功底太扎实了,全文读来有数字不认识(例如“嚆、窳”)[捂脸],“职是之故、极相轩轾”这种出现多次的表达也感到十分的生疏,特别喜欢“圆融自洽”,很想知道在德文和英文里是如何的。 总的来说,我大概没有读懂。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读后感(二):被需要的和被提供的
在被大革命吓坏的日耳曼人中出现历史法学派是很正常的。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促使他们意识到法律并不纯是思辨的产物,还可以从历史渐变角度探讨。在萨维尼眼中,法律由民族精神决定。但是,任何有志于独裁的统治者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国情在此"和"自古以来""传统美德",他们一面扼杀任何异见,堵住反对者的嘴;一面利用喉舌以常用手段为独裁政策辩护,这样的结果是独裁者为了获得法理的正当性必须亲自界定他们的辩护工具,他们说民族精神是什么民族精神就是什么,他们说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什么,学者和体系外的人一旦对他们的定义产生质疑,会招来他们的注意,或者他们的质疑压根不会掀起风浪。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法学派这么好用为什么当代赵国压根就不怎么提他呢。那个主义是舶来品,将他们和赵国传统糅合是很困难的事,任何国师都做不了,他们的法理只是为政治辩护而存在,不存在逻辑的闭合性。赵国传统和那个主义都是为了服务而存在的,他们吸收了赵国传统中利于统治的部分,又扭曲了xx,你能想象赵国传统和大胡子的理论媾和产下了多美的崽吗?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读后感(三):说两句吧
在阅读上,我是个很没有斗志的人,常常会羞愧地掩卷而逃.比如说,读小说的时候更喜欢奥斯丁、毛姆、梅里美这样的作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敬而远之——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他比前三位更伟大。读伯林的时候也非常过瘾,他是一个文字清晰,思想同样显白的作家(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伯林特别爱好分类,比如积极自由vs消极自由,刺猬vs.狐狸,伤感的作家vs.素朴的作家,这样就会让他的读者轻松很多)。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也是不让我那么头疼的作家,他的政治哲学作品写得有诗人的气息,语言当然没话说——一个热爱卢梭、莎士比亚的人,在文字上怎么会让我们失望呢?当然还得感谢秦露的翻译,将布鲁姆对几篇评注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的既典雅又晓白。
当然,有时候让我望而却步的作品,不是文字的原因,而是自己的理解力不够。所以,还是要迎难而上阿。就好比托克维尔和海德格尔,前者比较好懂,但是后者更深刻,更难懂,当然读起来也更刺激。
闲话少说,回到我们这本书。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的译者许章润老师可能是国学爱好者,用非常古典的文字来翻译本书.但是,这种译文读起来真的让人费解啊.非常期待该书的白话文版!就算给点福利我们的青年学生也好阿。
另外,该书导论部分,有一处似乎翻译得有些容易引起误解。第三页最后一段“关于法律的制定,有两种观点,鄙人甚为熟悉。一种观点倾向于恢复旧有制度,另一种观点倾向于为德国诸邦继受一部统一的法典。为了说明这第二种观点,此处有必要略作一番考察;而且,必得在双重历史联系中对它进行思考。”接下来两段就是“就第一种观点”和“就第二种观点”如果不反复阅读,很容易以为,“就第一种观点”这点讲的是前面提到的“倾向于恢复旧有制度的观点”,而“就第二种观点”讲的是“倾向于为德国诸邦继受一部统一的法典”。但是,实际上,这两段讨论的是“倾向于德国诸邦继受一部统一的法典”这种观点的两种思想渊源——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和法律实证主义。译者用“就第一种观点”和“就第二种观点”很容易让读者误解,也许结合上下文换种表述,更好。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读后感(四):给一位老师的读书笔记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我算是读过了。之所以说“算是”,一是因为该书的最后几部分主要是罗列拿破仑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的内容,将其与罗马法民法内容作对比,涉及大量民法理论,我只好将该部分草草跳过;另外,许章润老师翻译本书时,文风偏向于文言,我虽然能懂,但不喜欢通篇都是这种风格的译作;而且他还标示出,这本书是从英译本译出的,因此对于文章的准确性,我更是抱有一定的疑虑。然而我还是读完了。
这本书最前面分别是英译者和中译者的序,然后才是萨维尼的正文。总共一百六十余页的规模,两个序占据了1/4,其中许章润老师撰写的中译者序更长些。在其中,许章润老师援引本书的一些语句,对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观点作了一些介绍——而我读完此书之后的感觉是,若要从这本书中“抽出”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观点,可能只看许章润老师写的序就可以了。
萨维尼的正文,系一篇驳论文,其背景是德国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和法国民法典的颁布,针对的是当时德国一些学者建议通过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来促成德意志的统一。在我看来,萨维尼首先追溯了罗马法和德国法的历史,然后对三部法律(拿破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和普鲁士法典)进行了评价,得出的结论是不从历史中寻找法律必将失败。然后他针对德国各邦国有无法典情况不一的现象,回答了在“有法典处”和在“无法典处”应该如何做的问题,最终得出不能草率立法,“一蹴而就”,而要慢慢研究、待时机成熟再行立法的结论。
其总体的思路,认为从历史上来说罗马法和德意志古代习惯互相糅合,经过德意志民族生活的锤炼,最终成为现在德意志民族共同遵行的习惯。因此,而若要制定民法典,需要仔细考察这种民族生活的习惯,寻找其背后的历史中的法,乃至于这种法背后的精神和理念,然后才能“制定”(用现代法理学的语言来说,毋宁说是“认可”)成文法。针对当时所谓的从某种(些)原则,经由人类的理性推论而出的自然法,萨维尼认为,这种推论及自然法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因为作出这种推论的那些原则和推论的过程其实也是由本民族的习惯法所决定的(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很有道理:马里旦的自然法,首先从上帝开始推;秋风之类的“儒家宪政”则从孔子开始推,这两个绝无互换的可能;而且我觉得,如果没有西学东渐,只是从儒家理论开始推的话,应该是推不出正当程序之类的“自然法”来的)。套用哈耶克的术语来说,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和当时的“自然法”相比,很像是哈耶克所谓“理性建构”和“自发秩序”之间的对立。
另外,我倾向于将这本书归类为一种“(已经变成)历史的著作”。这个归类法我倒没有在哪里看到过,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说明它,只是我早先读叶必丰老师的《行政法的人文精神》的时候的一点感受。叶老师的那本书,讲的是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它是当时行政法学界反思行政法立论之根本的大讨论中诞生的,但是当时论战的喧嚣早已平息,“平衡论”和“控权论”成为主流,事到如今,其论述的问题和描述的状况,早已成为陈年旧事;而其所倡导的理论,现在也无人服膺。除此之外,书中几乎每页都会出现高中的马哲和政经词汇,十分“硌牙(刘心武以此喻书中的错别字)”。总而言之,书中的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除了研究本部门法学说的历史之外,似乎已经没有读的必要。读本书中萨维尼的正文,给我的感受,与此相差不多。无论是其对罗马法历史的考察,还是对德意志习惯的说明,抑或是“在有/无法典处”该如何做的探讨,还是对德国该如何立法的结论,(当然,对三部法典的考察更不必说)都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朦胧感,隔着部门法不同行业的“山”和数百年历史的烟雾,看不真切。
而要说这本书中的理论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我想,以我区区之学,恐怕难说得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国的情况,很是复杂。从理性建构和自发秩序来说,好比说底子是历史的、自发的,而面儿上却是建构出来的。说到底,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终究是一种“理性建构”的意识形态,它的理论是倾向于“改造社会”的。但是我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的精神中,总还有些残存的民族性格,比如畏讼的传统、向往远离政治的“桃花源”的传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莫大冲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甚至是“多子多福”这种与“基本国策”、“基本义务”直接对立的观念,即便经法律“改造”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依然故我。但是我国立法者,倘若抱持着自认为“真理”的指导思想,恐怕未必会对民间习惯加以尊重,比如宋显忠老师曾经对我们讲,说中国人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至民国尤未改变,其先进与否先不说;且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有同性婚姻之规定,但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原则,以及禁止同性婚姻,却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来规定的,这应该不属于是经过了萨维尼所说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且,我国现在人群差异如此巨大,制定统一的法律也尤为困难:守土重迁的农民和流动性大的城市人群的婚姻理念,多有不同;中青年追求安分、远离政治,而90、00后的新青年却可能不那么追求“铁饭碗”和安定的生活;帝都和魔都的商人白领月入上万甚至成百上千万,他们对保护财产权和个人隐私的看法与西藏、蒙古的牧民又怎么可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别说“理性建构”凶多吉少,就连研究“自发秩序”用习惯来立法也难度很大。套用一个用滥的词儿,当今这个“转型时代”,恐怕是给我国的立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难题。而再往下说,可能不管是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体制,还是在司法中判例与成文法的作用,甚至是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都时刻面临着被重新检讨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我读完本书后的一点感想,不敢说有多么准确,只是发其所思。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