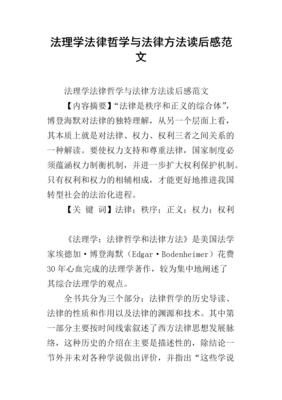
《立法者的法理学》是一本由强世功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立法者的法理学》精选点评:
●为什么都只看到了强提的不成文宪法。就像许德风说的,强在这本书里的很多论述都是“教义学的杰作”,虽然强自己称之为“道可道,非常道”。
●前面写得最好,论述清晰、有说服力。虽然强世功的理论我也不是都认可,但就他认为法学前提需要对主权绝对维护的这种思想也没有引起反感,因为能感受到他是想在现有的体制下找到一条最实际也最理想的法学出路,实现真正的以法治国,达到最终的民主目的。但是我仍然觉得,他的理论是明显缺少补丁的。 曾经我们的一府两院是地位平等的,这也是宪法章程,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法低于政,法院对市院已经成为了汇报关系。 国情上,现在确实富强了,却没有为民主与自由提供出路,反而是封堵。强世功希望能在维护绝对主权的条件下达到民主共和,但是绝对主权肯定需要绝对力量,而这个力量跟民主就一定有相悖性,而这一点他没有解决。这也是我能理解却很难全部认可的原因,无论走一条民主道路还是强制主权道路,如果社会建制的目的没有让人变得更幸福都没有意义
●傻逼强世功!TG的一条狗!
●学习
●鹰犬教授、打手学者。一分滚粗。
●补记:两年前读罢,因强师广博的知识而难以把握基本脉络,尔后时常翻阅,逐渐理解本书的意图与关怀。
●读了最后三章
●左得很。不过说理还是很强悍的。
●寻找立法者的法理学。
●老强一家之言的文字。
《立法者的法理学》读后感(一):法律与主权国家
要怎么来评价这本书呢?
书是一本论文集,在其它地方,很多章节断断续续有看过,这让我最开始有些怀疑这本书的完整性。强世功的写作总是有着急的激情的,但就这本书的某些章节而言,又让我有些担心激情多过细致分析。
所以,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印象不是太好。出于做论文的目的,年前我还是买下来了,并翻阅了一遍。昨天重点挑选一些章节看了。感觉比上一次要好一些,可以也深化了上一次读的一些疑问,并有些新的问题跑出来。
书的导言“法理学与民族命运”可以转化成“现代性背景下的法律与主权国家”。因此也可能使得强世功落到那种对“主权视角”进行批判的主张的对立面,尽管强世功也一直在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那一面。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明国家的传承之间存在着紧张吗?
在整个现代性规划中,就一国国内而言,法律所扮演的角色大抵就是强世功所说的那样——当然,要除开那些传承着宗教法律合一传统的国家(这些法律体系对实证主义法学提供了一个对照物)——用法律来驯服政治,但是在国际层面,或者更为精确的世界层面和全球层面,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并没有穷尽。在这个世界的治理越来越技术化、程序化的时候,法律可能需要反对去政治化才能实现国际层面的驯服政治——甚至是要超出这一点——的作用。
这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立法者的法理学》读后感(二):小批判一则
无论法理学是否形式上放逐国家,法律本身实施,就是国家。不一定是某个人理想的国家。何况法理学,真的能够放逐国家吗?喊着主权与国家,就是立法者的法理学了? 强调新旧传统继承,标榜传统文明国家实际是国家主义,自相矛盾之余,实际上否认了当代可以开创当代的传统的合理性。所谓传统,不过是当时的人所做的事而已。 法律人,或者法学者可以成为城邦的守护者?哲学家?哲人王?
作者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的治理状况,但直接把古希腊小国寡民的理想打算搬到当代大中国。古典的追求整全的知识立场,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考,就是合格的治国术了么?我很欣赏这样的知识立场。这是培养有教养的人的立场。 虽然法律是帝国的技艺(美帝国的技艺?文明中国是帝国吗?),然而现代的前法律世界,不是法律而是政治,是政策,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工作是由职业的政治家和社会团体进行的,这也是一项专门的技艺。正如主席所言:政策是党的生命。 现代国家治理是高度精密复杂的技术,由不同的技术人士分工,现代社会的不断加剧的分工趋势,就算蕴藏着风险,也很难逆转。治国不再只是传统的哲人法律人的事业。
如果放弃守望社会的本职,那法律人究竟如何才能治国呢?在缺乏顺利转职成为政治家的渠道下,除了向当局和权力献媚,可有更合适的途径? 真正的国家利益,除了少量当国者操局以外,到底如何才能发现?如何确定个体思辨的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这种法理学,是否有能力去发现真正的国家利益?更何况它实质放弃本该首要保护的个体权益的话! 躲到法律解释学里,是法律人斗争的一种策略。撕掉这层外衣固然磊落,也丧失了自己唯一有力的武器。
就算法律就是政治,政治家和法律人也是两个职业,两种工作。
作者对没有政治的法学非常不满,最终他投向了政治,成为了幕僚,而非立法者。 诗人,或许才是真的立法者吧。
《立法者的法理学》读后感(三):立法者的法理学摘录
9.当代法理学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即倡导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强调法律背后的阶级统治和国家暴力之类的政治要素,强调法律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性特征,那么这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事实上强调法律自身的内在特性。从形式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一种“法制主义”,即从形式合理性、普遍适用性、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这些法律规则本身的内在特征入手来理解法律,从实质上说,这种法律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即把权利保护作为思考法律的出发点。
11.如果“没有国家的法律观”仅仅是法律移植这种立法行动的意识形态外衣,那么一旦法律移植的政治任务完成之后,这种法律观就如同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一样,难免遭到被遗忘的命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落迹象,反而更加生机勃勃,这既不是因为法律移植仍在进行,也不是这种法律观在理论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是由于这种法律观已成为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成为法律共同体自主意识的表达。其生命力不再来源于外在的法律移植,而是来自法律共同体本身。
19.国家并不是空洞的法律机器,而是由文明加以充实的伦理实体。“法理学中重新找回国家”就是要采取这种现实历史的和政治的方法论视角,把国家作为法理学思考的出发点,这种思考方法并没有排斥对个人权利的考虑,反而尤其看重对人权的保护。只不过对人权的保护不是由于个人权利在逻辑上的先天价值优先性,或者说把人权保护这种理论逻辑的可能性变成政治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个人权利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保护,同时个人的权利的保护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强大和现代文明得以提升的重要内容。
68.尽管在法律层面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但是在这个转型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是另一套法政治的法则,由此导致改革路线与宪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形成了所谓的“良性违宪”的问题,这恰恰构成了改革宪法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学家习惯于法律政策学,而不是法律解释学,我们的宪法学中流行的是抽象的宪法理念以及如何修改宪法,而不是对具体宪法文本或者条款的研究。
之所以出现这种对宪法文本的轻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习惯把宪法理解成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而不是政治的构成或政制,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04.既然国家的政治统治可以用成文宪法的方式确认和规定下来,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并不是神话,政治也不是偶然力量的操纵之物。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把握政治和国家,尤其是可以用法律科学和技艺理性的方法来把握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宪法的法律文本特征意味着政治成为技艺的一部分,宪法就包含了构造国家或者政治统治秩序的技术原理。宪法文本对宪法条款的规定,绝不是简单的将人民统治自己的具体规则罗列在一起或杂乱无章地随机排列在一起,而是包含了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的艺术性构想和塑造,即从理性的角度想象和筹划如何用法则的“形式”来确认、规定、建构和塑造政治秩序。这种从法律技艺的思路来建构国家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政治正确是可以想象、分析、控制和筹划的,而且意味着只要符合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原则,按照宪法作为法律的技术原理,可以创生一个人民永远统治自己的不会腐朽死亡的共和国,造就一个会自我繁衍、自我更新的政治生命。
106.如果宪法确立了国家权力合理运行的机构框架,原来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也会在这些国家机构的政治运作中创造出来,反之如果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本身不合理,或者国家权力之间没有制约机制,那么无论列举多么充分的公民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公民的权利可能受到了侵害、限制甚至剥夺,却没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或机构对这些行为加以制止或矫正。因此对于政治有机体而言,如何设计合理的、科学的、有利于共和国健康的国家机构比规定广泛的公民权利更为重要,国家机构的政治骨架往往决定了政体的性质,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不是用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不同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国家机构设计的不同原理来区分的。毕竟公民的法定权利只是一些“主观权利”,它只有在政治机构框架的运行中才能变成“客观权利”。
256.对于司法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司法权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侵犯,从而保持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进而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因为无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挟持了司法权,公民的自由权就不复存在,因此防止司法部门被侵犯的最好方法就是保保持司法独立,而司法审查就包含在司法独立之中。
《立法者的法理学》读后感(四):立法者的法理学摘录
9.当代法理学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即倡导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强调法律背后的阶级统治和国家暴力之类的政治要素,强调法律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性特征,那么这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事实上强调法律自身的内在特性。从形式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一种“法制主义”,即从形式合理性、普遍适用性、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这些法律规则本身的内在特征入手来理解法律,从实质上说,这种法律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即把权利保护作为思考法律的出发点。
11.如果“没有国家的法律观”仅仅是法律移植这种立法行动的意识形态外衣,那么一旦法律移植的政治任务完成之后,这种法律观就如同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一样,难免遭到被遗忘的命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落迹象,反而更加生机勃勃,这既不是因为法律移植仍在进行,也不是这种法律观在理论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是由于这种法律观已成为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成为法律共同体自主意识的表达。其生命力不再来源于外在的法律移植,而是来自法律共同体本身。
19.国家并不是空洞的法律机器,而是由文明加以充实的伦理实体。“法理学中重新找回国家”就是要采取这种现实历史的和政治的方法论视角,把国家作为法理学思考的出发点,这种思考方法并没有排斥对个人权利的考虑,反而尤其看重对人权的保护。只不过对人权的保护不是由于个人权利在逻辑上的先天价值优先性,或者说把人权保护这种理论逻辑的可能性变成政治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个人权利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保护,同时个人的权利的保护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强大和现代文明得以提升的重要内容。
68.尽管在法律层面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但是在这个转型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是另一套法政治的法则,由此导致改革路线与宪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形成了所谓的“良性违宪”的问题,这恰恰构成了改革宪法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学家习惯于法律政策学,而不是法律解释学,我们的宪法学中流行的是抽象的宪法理念以及如何修改宪法,而不是对具体宪法文本或者条款的研究。
之所以出现这种对宪法文本的轻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习惯把宪法理解成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而不是政治的构成或政制,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04.既然国家的政治统治可以用成文宪法的方式确认和规定下来,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并不是神话,政治也不是偶然力量的操纵之物。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把握政治和国家,尤其是可以用法律科学和技艺理性的方法来把握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宪法的法律文本特征意味着政治成为技艺的一部分,宪法就包含了构造国家或者政治统治秩序的技术原理。宪法文本对宪法条款的规定,绝不是简单的将人民统治自己的具体规则罗列在一起或杂乱无章地随机排列在一起,而是包含了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的艺术性构想和塑造,即从理性的角度想象和筹划如何用法则的“形式”来确认、规定、建构和塑造政治秩序。这种从法律技艺的思路来建构国家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政治正确是可以想象、分析、控制和筹划的,而且意味着只要符合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原则,按照宪法作为法律的技术原理,可以创生一个人民永远统治自己的不会腐朽死亡的共和国,造就一个会自我繁衍、自我更新的政治生命。
106.如果宪法确立了国家权力合理运行的机构框架,原来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也会在这些国家机构的政治运作中创造出来,反之如果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本身不合理,或者国家权力之间没有制约机制,那么无论列举多么充分的公民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公民的权利可能受到了侵害、限制甚至剥夺,却没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或机构对这些行为加以制止或矫正。因此对于政治有机体而言,如何设计合理的、科学的、有利于共和国健康的国家机构比规定广泛的公民权利更为重要,国家机构的政治骨架往往决定了政体的性质,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不是用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不同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国家机构设计的不同原理来区分的。毕竟公民的法定权利只是一些“主观权利”,它只有在政治机构框架的运行中才能变成“客观权利”。
256.对于司法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司法权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侵犯,从而保持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进而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因为无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挟持了司法权,公民的自由权就不复存在,因此防止司法部门被侵犯的最好方法就是保保持司法独立,而司法审查就包含在司法独立之中。
《立法者的法理学》读后感(五):从法理学中找回“国家”
作者:丁国强 来源:中华读书报 整理日期:2008-2-1
强世功所谓的“立法者”不是现代立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定者,而是指古典意义上的创建政体的立国者或者立法者,说到底就是国家政治的设计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者的法理学也就是关于国家的法律观和治理技术的学问,是宏大叙事的法理学,是“法律人政治家”的哲学。强世功强调法理学必须对民族命运有所担当,并非是大而无当的豪言壮语,国家作为法律主体需要奠定其合法性基础。法学界所热衷的“法律移植说”痴迷于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而忽略了对“法律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法律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法律与人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密切相关。法律的意义不是在法律自我封闭运行中产生的,如果脱离整个政治国家的建构,法律根本就无法自圆其说。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维辛斯基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影响,研究者过分强调法律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文化解释、现代化模式的万能性,形成了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是建立在法律无国界的假设和对英美法律制度的亲和的基础之上的。
在司法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中,“与国际接轨”几乎成了一种技术共识。确立了国际通例的权威之后,一旦偏离国际轨道就会被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在法治语境中,人们似乎已经足够有耐性。其实,所谓“与国际接轨”,只不过是对常识的恢复和接近而已,这些基础性真理并不能包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只有形成自己的知识立场,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富有建设性,而不是在复制和跟风之中疲惫不堪。法律不仅为人们提供一种利益平衡、纠纷化解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支持了一种成熟、理智的价值判断。法律既是一种现实需求,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用法律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麻烦,而不是从内心折服于法律的精神力量,就只能漂浮在法律的表层。无论是法学人、还是法律人,对法理的兴趣都是十分有限的,人们因为害怕被指责为“纸上谈兵”而对法理不予深究。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浅薄。
法律是治国之道,将法律从政治语境中剔除出来,单纯讨论纠纷的解决之类的具体问题,未必就是一种务实态度,人为割断法律与政治的联系,将法律提炼为一种精湛的技艺,通过制造法学知识壁垒,来建构一种话语霸权,最终会限制法学的眼界和关怀。国家治理是由法律所调整的各种细节组成的。将“法律人”完全从“政治人”的角色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不问政治,不谈国情,认为可以单纯靠法律信仰和法律技术来构建通往公平正义的法律帝国是虚幻的。这种以法律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激发了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热情,从佘祥林案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人们关注着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追问着法律的强制力和公信力。法律的普适价值在回答这些“中国特色”的问题和矛盾时,不免面临尴尬。苏力对通过“送法下乡”的方式完成国家治理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给予了充分同情和理解。一面是法律移植,一面是本土化,说到底还是中西之争的延续。而强世功则企图从法理学中找回国家,呼吁法律人承担起完善民族国家、构思文明国家的政治使命。这种构想不仅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政治修辞,一种问题视角,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世界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参与精神。
强世功的本意不是将法律意识形态化,而是努力纠正将法律问题非政治化所带来的难题。宪法是现代国家中政治游戏的规则,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运行规则,宪法和法律奠定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使得国家权力得以正常运作,司法的正当性也必须放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来考察,而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则在其中得以实现。强世功说:“宪法包含了人民对一个真正的人所能享有的自由状态的全部想象。”法治国家的理想图景是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国家利益高度契合,国家是公民一切权利的归属。法律的权威不仅来自公民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而且也与其对国家的尊重密不可分。法治启蒙的重要任务就是确立人们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法治是一项最高的国家福利。正如强世功所言:“国家主权不是外来强加的力量,而恰恰是个人自由的产物,它来自每个人身上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意志,它是人民主权的法律表现。”可见,绕开“国家”来讨论法律问题和公民权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