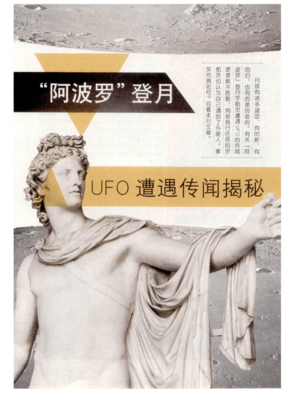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是一本由萧兵 / 插画师 :雪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5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读后感(一):一本“颜值”与“内涵”双高的神话故事集
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茅盾这样定义神话:
神话是一种流传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颂,却确信以为是真的。
茅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神话,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从超越的审美范畴来欣赏、玩味先民们留下的传说故事。近年来的一些动画电影,比如《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以其充满中国美学的视觉想象力令人着迷。最近翻看的《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就是一本十分“好看”的神话故事集。
首先是满书都是赏心悦目的插图,一部分来自于文物或者古籍中,由古人绘制而成的神话形象,以现在的眼光看,当然有些简略,但却充满一种原生的、质朴的美感,甚至是可爱的。而大部分则来自于插画师雪鱼,对线条掌握得非常好,营造出一种流动感十足的视觉魅力,传递出了神话故事那种丰盈的质感。比如我特别喜欢的这张大拉页“黄帝大战蚩尤”。
两军对垒,各驱猛兽,摇旗吹角,两军统帅各自身先士卒,大战拉开帷幕。黄帝大军占据左下角,斜刺前方;蚩尤大军压住右上角,扑向敌阵。背景是似乎高速流动的云气,加剧画面的紧张感。而黄帝方以红蓝色调为主,蚩尤方以黑灰色调为主,碰撞激烈。显然黄帝方占据了更多的画面,这也预示着这场战争中黄帝是更强大的一方,他将取得最终的胜利。画面下方中间偏右的位置,罩着红圈的撒欢奔跑、龇牙咧嘴的小孩,显得野趣十足,颇有些画龙点睛的意味,仿佛这人神共举的大战战场,却是他玩耍打闹的乐园。
还有一张“夸父逐日”图,也颇为精彩。
画面成橙红色,远处背景仿佛是史前的巨兽死后留下的遗骸。夸父如田径运动员一般矫健,身后却是凶恶的豺狼,再仔细看,似乎是水的形状,这应该是画家从神话中汲取的灵感——传说夸父逐日,口渴难耐,“河、渭不足,北饮大泽”,被喝干的河水们“寻仇”来了!夸父发须皆白,又遇险境。画家给夸父逐日的神话增添了更多的悲壮感。
除了插画漂亮,内容方面干货也不少。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中华民族”的神话与传说集,汉民族、傣族、彝族、回族、高山族等中国各民族的神话故事被平等地加以展现。因此,你不仅能读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也能读到不太熟悉的故事,比如彝族的创世神话“支格阿龙改造万物”,别有一番趣味。
每一篇神话都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致是先简介神话传说人物的名字、事迹,再讲一些有趣故事”,第二部分“延伸阅读”则对第一部分的某些话题做拓展,“交代故事的背景、意义或问题”。既有趣味性,又富知识性。比如第一章《“混沌”的破解》,就介绍了各民族对于世界诞生之初的想象,有纳西族的“气态混沌”,景颇族的“雾态混沌”,满族的“水体混沌”,以及大家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的“卵形混沌”,还有其他文明中的混沌想象。这其实提示了人类文明的某种同构性。
作者将中国各民族的神话列在一起,我们能看到这些神话故事很多时候分享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作者写道:
南北方兄弟民族,不但有相互类同的月蚀、日蚀,还有跟嫦娥十分相似的“奔月”故事。有些独立发生,大多数似是相互影响。可见中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可见,神话绝对不只是无来由的幻想,它的根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是我们在看神话的时候,应该注意思索和解读的。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读后感(二):从远古到今天的叙事
原载于《文学报》2020.11.12期
作者 | 舒芙蕾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宇宙一片混沌,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沉睡了一万八千年后,突然苏醒,他见周遭一片漆黑,无边无际,于是他拿起手斧,向黑暗劈去……
这是小时候的我们在村里古榕树下听到的第一个神话,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创世神话,更是一个记载着人们潜意识里从混沌蒙昧走向光明智慧的故事。
在这片浩瀚星河里,中国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总是那么悠扬和玄妙,让每一个厌倦当下与此生的人都能顺势搭上时光列车,从今日辗转到远古,解锁中国上古的文化密码,重观战壕遗迹下的历史传奇,目睹古老人类的文明图腾——阅读神话与传说的过程,就像是建造一条从远古心灵通往现代心灵的悠悠隧道。萧兵著述的《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就是一本让人踏上追寻远古文明旅途的著作。
为什么在倡导科学与理性的今天,还要读神话?这是许多人共同的问题——时下生活,似乎更直接地呈现出与时俱进、科学创新的一面,阅读极具想象力的中国传统神话与传说似乎是无用的?但所有人都会同意的是,神话与传说和一个民族息息相关,它面对着一个永恒的疑问: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人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切断与神话的联结,就等于切断文化中最富有心灵意义的部分。
作为身居喧嚣城市、享受刷屏快感的现代人,神话和传说是一片净土,是远古时期极富想象力的传世之作。在它奇诡运行的文字、声色并茂的图画里,记录着许多或已进化,或已绝迹,或仅仅存在于幻想里的远古生命。通过神话,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触碰到我们祖先几千年前的生活和思想。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人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验和感受,产生的认识和体验可能是全然不同的。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神话都在异口同声地讲述着一些恒久的母题,比如天地起源、人与自然、困难与命运、善与恶、罪与罚、勤劳与收获等等,就像坎贝尔在神话学著作《千面英雄》中毫不吝啬地写道:“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
因为,神话从不只是讲述神仙的故事,而是讲述人类自己的故事,那是经由世人心灵折射后的“城池”——各民族在神话中表达的真正主题,并不是神仙世界的秩序与情感,而是人类自身的处境,以及他们对自然世界,甚至宇宙存在的看法。
神话是应人类的困境和困惑而生的,越遥远的故事越能折射出人类共有的思考与理解——去向天询问什么时候能下雨,为何今年颗粒无收,什么是和善温柔、高洁无暇;又或者,我们能够通过阅读神话,得到高于生活的体验,让我们有机会和众神一起经历史诗般的冒险。
神话,往往用最逼近生活以及生命的本真的一切,彰显蕴含在古老岁月里的深远哲理与寓意。那是能让人初探并思考生命最本质的东西的媒介,如果解读得法,神话非但不是“不知何所用的老朽”,而是能够穿越时空,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精神文化的向导。
中国首部创世史诗《山海经》的想象力无穷无尽,完全不受限于天地困境,只要笔尖耕耘,就能创造出世间不存在却极为浪漫的事物。其中虚构的神兽和怪物凭空而起,比如生于冰湖的“横公鱼”,白天是鱼身,晚上则化作人形;状如鲤里而添鸟翼,常年游于西海,夜间可以飞行的“文鳐”;还有九头怪蛇“九婴”,以及壮如虎、有翼的神兽的“穷奇”。这些奇形异兽在古代用于标记图腾族氏,在现代用于编织幻想世界。但《山海经》并非仅仅是一本记载上古神兽的神话图鉴,更是一本记载远古知识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一直把它当史书看待,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参考过它。
多元纵横的神话与传说帮助人们了解我们民族的思想源泉,了解与我们朝暮相处的祖辈流淌在血液里的行为准则,甚至探幽埋藏在现今许多文艺作品中的深层意蕴。近年来现象级的《大圣归来》《魔童哪咤》《大鱼海棠》等影片,无不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想象。在《九歌》《汉赋》《左传》等古籍里,都能找到与有关的神话元素,只是很多时候,因承载它们的是古文形式,安放它们的是古籍,加之很多元素是碎片化的,散落在杂记、文献、典故当中,因此与现代人的认知有了隔阂。
“仓颉造字”一图绘制草稿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解答传说故事里的“神怪”元素从何而来的神话百科,一座能够横跨古今中外、连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让我们一伸手就能触摸到上古文化雕刻在时空中的铭文。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不只是书页装帧风格的仿传统化,或是故事新编,更不是将作者扮成一个装在线装书里的“活古人”,而是真挚、真诚地“以书为友”,引领读者感受传统文化的张力。但要找出这样一本书谈何容易?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作者是人类学家、神话学家萧兵,他在耄耋之年创作了这部“中国神话通识读本”。神话学作为文学、人类学的分支,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跨学科性,却鲜有一本书能因一个“词”“句”“典故”而延伸到更多的学科知识,甚至结合现代生活,让人们重新认识流传千年的文化脉络,这或许正是萧兵编写《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目的。这也是讲述“万物有灵”的神话给人最深触达——它总能在故事里蕴藏古老的民间智慧和知识。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不应只是学术和文化的象牙塔,就会大胆地去接受内心对神话和传说的评判和赏析。当我们阅读不同书籍,与不同文化交叠的过程中,到底是因为某个引人入胜的文化元素先于书籍俘获我们内心,还是它早已在生活中给过我们微不足道的启示?故事,与其间扮演的角色,是未知世界的一扇门,还是未知世界本身?
我们一定听说过许多“创造万物”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故事,不仅从神话的角度讲述世界的由来,还阐述了神话与传说的创造性与文学性,这类英雄故事在“展演”与传诵的过程中,总是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其间不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它们的共同性是展示了人类对“创造”的共同期待与描摹。
在这些故事里,人可以自然地接触到永恒,发现自我,参悟生死,体观神性,这也是科技无法取代它们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人与生俱来不仅有“人性”,还会有“神性”。
世界并不存在于绝对的善与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当其中一方得到普遍重视时,另一方就会变换形式隐藏起来继续存活。某种程度上,人们觉察自己的内心活动、真实感受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神话能够帮助人们“发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原因。
现代人并未真正失去远古神话与传说,陌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解读它们的本能。不要单纯为了听故事而读神话,更要照见其中的“意义”,这就是《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价值所在。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读后感(三):神话起源:中华民族骨血中的文明信仰
如果说探究那些未曾知晓的神秘力量和不曾涉足的远方是人类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原始的动力,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如此复杂繁冗的民族、语言、地域的隔绝下却有着共同的神话传说让他们各自的后人共同继承和传颂,又何以在那些故事中往往会涉及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来处,以及世界因何如此,这些科学尚无法解释插足的地方。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潜意识里他们始终是一种追求自身安全感的物种,照亮黑夜的火堆,抵御寒冷的山洞,防备野兽的武器,温饱的衣物和食物,会让他们身心倍感舒适。同样,任何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不确定性都足以让人类产生不安全感,比如我们从何而来,天地因何而在,我们终将何去何从,这才有了天地混沌如鸡子,一个叫“盘古”的巨人斧劈黑夜的传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真实,而是足够令人心安,需求决定供给,不确定性意味着随时随地隐藏的危机。
于是我们回过头就不难发现,何以盘古要分天地,双目化为日月,方成天下;何以夸父要逐日盗火,“净化”世界;何以后羿射日,人定胜天;何以愚公移山,重整山河。茅盾先生在他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提出:“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者原始时代生活和思想的产物。它们是上古时代流行的民间故事,讲的是超越于人自身能力之外的神的种种事迹,人们口耳相传,虽然显得有些荒诞,但当时的人们却信以为真,而这些都是与原始人的宇宙观密切相关的。”对于拥有最朴素的探索精神,又同时缺少自然科学启迪的上古人类来说,任何一种客观发生又无法解释的事物总需要以某种方法的来加以注释,并从中找寻到其可能的内在规律与触发逻辑。这时候,“想象”才是最好的工具,在古人看来辽阔的土地,无垠的天空,风雨雷电,云雾霜雪,鸟兽鱼虫,花草树木,所有目之所阅,耳之所闻,触之所及的事物,通通需要一个个完美的解释,想象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最后种种传说应运而生。对那些生存于斯的人来说,传说即万物,传说即天地,传说即真理。
而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有必要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去阅读神话?夜晚凝望,浩瀚星海,想象插上翅膀,遨游物外,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依旧会因为故事中的每一位英雄主义而慷慨激昂,每一次矢志不渝而潸然泪下,每一场旷世绝恋而心有戚戚,每一回舍生忘死而荡气回肠。于是,我们终究会发现尽管时代在变迁,技术在进步,环境在更迭,而我们心中那些为之赞叹的追寻的努力的呐喊的东西,却始终没变,让那些传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不是文字书写,不是口口相传,有的是故事中那些与任何一个时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文化上的一次次共鸣与呼应。阅读过去,是一种追溯自我,探索心灵的最佳方式,解锁藏匿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密码,解构那些早已漫漶了的历史传说。如何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会有相当多的答案和方法,去阅读和熟悉他们曾经通过想象流传下来的传说会是一条不错的捷径,天地传说,人类起源,自然命运,困难险阻,风餐露宿,因果报应,善恶循环,如同《千面英雄》中的那句话:“人生下来并不是一块白板,会先天遗传一种种族记忆,是人类自远古时代以来积淀和遗传下来的全部心理经验,超越个人,贯穿所有的地域和所有的文化。”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最初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何谓“神话传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从他的意思中不难看出,所谓神话,就是古人以用来解释天地万物无常变异的缘由。如果依此来看,明代的古典小说《镜花缘》、《封神演义》、《西游记》就不能被归类为神话范畴,至于如今仙侠神魔一类的小说,例如《诛仙》、《佛本是道》等,更甚之,这些被冠之以神话的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一种神话传说的某种衍生产物,以古人的框架讲今人的故事,它们所具有的文学意义更接近于创作者之于当时社会价值的某种投影,而非传说本身。而从本书《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选材上,不难看出致力于此项研究的学者兼任作者萧兵老师,相当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本书几乎把传说的选取内容集中在上古夏商时期,哪怕最为有名的“牛郎织女”也是汉朝《古诗十九首》的产物。
中华民族拥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而各个民族之间又会因为文化的差异,繁衍出各自的传说起源,只是很遗憾的是,在“小说”这种文体大行其道之前,神话故事更多的时候被大量记载于《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淮南子》以及《搜神记》等古籍之中,却始终未能有一部完整全面的典籍来讲零散于各个书籍中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整合梳理,甚至如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一般完成全体谱系的汇总,而后人也只能在一星半点支离破碎的故事中找寻曾经的信仰。萧兵老师的这本书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作为神话学家、楚辞学家、人类学家,并有“怪杰”之称的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整理以华夏文明为主干的中华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在他看来“神话主要是讲人类与自然复杂关系的幻想性故事,传说主要是远古或上古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民间传闻,也带幻想性或虚构性,但‘真实’的成分也不少。”英国著名作家托尔金也有类似于“传奇和神话,大多源自真相”的论断。本书中,作者由故事入手,引申延展,夹叙夹议,由表及里的解析蕴藏在故事表层下的思想内核,剥离于儒家思想,剥离于政治诉求,剥离于时代粉饰之后,还原出最原始的故事本身,让读者重新去看待过去的我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生存。至于,神话到底对后来的我们有着如何大影响,与其说后来的帝王统治方式将中国神话的某种政治化修改,不如说是政治统治的方式始终在不断地模仿着中国的神话。
本书另一个值得夸耀的地方在于年轻插画师雪鱼出色地为本书贡献了几十副精美的插画,优雅的线条,舒缓的流动感,还有细致的考据,冲击力到爆的色彩搭配都让本书增色不少,在很多插画中甚至能看到近乎于原生态的质朴美感,和风吹云动草木摇曳的运动感。茅盾先生认为原始人会去创作神话,在于古人始终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宇宙观,而在雪鱼笔下相当完美的诠释了“万物皆有生机”的真实画面,透过画面我看到了这位八零后画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多年来的沉浸与研究。
天圆地方,日月星辰,亘古万物,始终不绝。无论是一日千里的现代科技,还是纸醉金迷的物质世界,都不足以影响每个中国人内心那些共同的传说故事,在那里寻找自我,堪破生死,乾坤自在,物我两忘。《列子》中有文:“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梦自消。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而神话传说,大概就是中华民族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读后感(四):古老的《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蕴藏着中国5000年以来的精神信仰
1、中华民族神话永远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相信每个人都有听老一辈人将神话传说的经历。一群小朋友坐在树下,听着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或善良、或狡诈的神话人物, 这已经成为了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在我们的心中久久难以忘怀。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匆匆的脚步背后,人们瞄准的目标都是星辰与大海。你已经多久没有好好坐下来听听故老相传的故事了?中国神话作为人类历史上璀璨的明珠,在外来文化、现代艺术的冲击下,仿佛已经渐渐式微,已经成为小朋友们启蒙教育的素材,与主流社会已经脱节。神话耀眼的光芒,仿佛也已经成为历史尘封的一枚琥珀,所有的美好只能在博物馆与文献中得以展示。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其实神话传说从未离我们远去。
幼年时候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一句“俺老孙来也”铸就多少儿童的童年记忆;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哪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让多少情窦初开的少年热泪盈眶;
《悟空传》中那句:“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伴我们走过了豪情壮志的大学时代;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他们说我死了,那些贪新的,念旧的一本正经说鬼话的,苟活的,正腐烂的,不敢开始更不敢结束的,阳奉的,阴违的,粉饰明天,篡改昨天的,来路去路都全部依稀的,他们愿意听到我死去。他们,也包括你吗?”让步入中年的我们,那已经逐渐冰冷的血液再次沸腾!
神话传说,从未离我们远去,而且会在未来,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价值观。
而且有意思的是,在高科技领域,以中国神话命名的高端制造产品不胜枚举。
载人空间试验平台“天宫一号”、登月探测器 “嫦娥”、月球车 “玉兔”、中兴的通讯芯片“朱雀”、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华为操作系统“鸿蒙”,无不体现了对神话典故炉火纯青的运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时代也能熠熠生辉,让冰冷的科技也能体现出极富生命力的浪漫主义情怀。
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从未离开,神话典故在世界上的传播与推广,更加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文化自信,一种对传统文化价值回归的展示。
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永远会有着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一席之地;这些古老雄浑的故事,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2、以神话读神画,以神画解神话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作者是著名的学者萧兵,号称学界 “怪杰”,他是神话学家、楚辞学家、人类学家,著作等身。
萧兵先生一直致力于研究以华夏一族为骨干的中华民族神话传说故事,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平时很少能见到的少数民族神话,体现了华夏各民族一家亲,通过对各民族神话传说的比较,以不同时空各类神话形象的异同,展现神话传说故事发展的历程。
在叙事的过程中,萧老师采用了边叙边议的一种方式,让读者不仅知道神话故事的“表”,更能知道神话的“里”。点与面结合,时间空间交映,微观宏观呈现,让读者从本源上对华夏各民族的神话故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知。
另外萧老师一直对神话的“神画”念念不忘,他认为,如果只讲述各民族的神话故事,略显单调,不能做到高质量、图文并茂地欣赏神话。即使个别的著作带有一些图画,又显得有些简陋模糊,很难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把神话文学与神话艺术融合,一起进行研究。
“以神话读神画,以神画解神话,在研究领域发挥图像的威力。”
《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的插画师雪鱼,虽然岁数不大,但是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精神内核理解极为透彻,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叙事性”,又兼具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
以大禹治水为例,雪鱼先是把相关的神话故事全都通读一遍,然后又找到画像砖、雕刻等文物中大禹相关的形象,提炼出最能表现大禹的符号特征,形成了具有牵动人心力量的插画。
神秘优美的中华民族神话传说故事,与有灵魂的精美插画相得益彰,真是体现了以神画解神话。
3、中华民族神话的起源与象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神话,是这样写的:“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也就是说,当先民们面对着未知的自然现象时,面对着可怕的世界时,他们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抗争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神话传说故事。
可以说,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的根骨所在,不但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信仰,更是与其他民族文化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处处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一种无畏、抗争的本质,也是中国民族数千年以来的精神支柱。
古人们很早就发现了这种特质,并用诗歌加以赞扬。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些威武的诗歌,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到现代。
中国的神话,神仙往往是非常善良的,他们有着非凡的神力,并且有着悲叹悯人的一种情怀。比如说女娲补天,比如说夸父逐日,比如说大禹治水,比如说傣族的泼水节祈雨等等,都体现了神话故事的尚德精神。
这些与西方神话中的人物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随着近些年来世界文化融合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神话传说人物形像被世界所认知、被世界所接受。比如说《哪咤之魔童降世》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比如说《花木兰》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一方面角色非常具有代表性,丰富的个性与多变的性格让西方观众感受东方故事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文化自信,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神话的接受程度。
神话故事的精神信仰力量,加以新时代的新艺术表现形式,想必会焕发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4、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神话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大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些故事长时间以来并不为众人所知,并没有纳入中国神话体系。相比于汉民族那些流传甚广的神话,少数民族神话可以说相当小众。
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发展的时间差不多,在神话的原型上有着某种共通性。比如说世界的起源,汉民族讲的盘古开天辟地,但是在古苗人的传说中,同样有“盘古分天地”的传说,傣族的“英叭创造世界”,彝族的“支格阿龙改造万物”;比如为人类引入火源,带来生的希望的火源,汉族就有“夸父盗火”,而羌族则有“羌族取火者—猴子冉必娃”;汉族有女娲捏土造人,而苗人同样有“伏羲与女娲”的故事。这也说明了中华56各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也说明了自古就有极深的文化认同感。
但是由于民族发展的差异,对世界认知的差异,使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又与汉民族的神话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拿最初的世界混沌状态来说,汉族认为世界是一种“气态混沌”,而“气”与“道”,则是汉族神话中最核心的部分;景颇族的史诗《目瑙斋瓦》、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以及古苗歌《苗族古歌》中认为世界的初始状态是一种“雾状混沌”;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和满族的萨满教认为世界起源于“水体混沌”……
虽然有着差异性,但是中国各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变。中华民族炎黄二帝中的炎帝其实就是羌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自古中华民族就有着“天下大同”的思想境界,各个民族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力,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内核。
想必在读完《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后,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有更深的理解。
5、豹尾虎齿到雍容华贵:从西王母形象看神话的演变
西王母又称“王母”、“王母娘娘”,在道教中是女神之首,也是中国神话中影响极广的一位神仙。
说起对西王母的兴趣,还要从四川博物院中的一件文物说起。
就是这件东汉时期西王母石棺,是在郫县出土的,上面刻着西王母、九尾狐、乌鸦等图像。
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看有关西王母石刻画,对于古代人的艺术水平、想象能力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同时也带来一个疑问,在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中出现过西王母的形象,在古人的壁画、石刻中西王母的画像也是屡见不鲜,西王母的形象是怎样演变的呢?
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对于西王母的形象是这样描写的:“又西三百五十里,日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卷二《西山三经》)”
从《山海经》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西王母是兽身人面的形象,“豹尾虎齿”,十分凶残,主管“五残”,即五刑残杀之气。
这哪是温柔可人的女子形象啊,简直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女“兰博”。唯一有点女性特征的,也就是“戴胜”,头发上戴着“玉胜”这种装饰品。“戴胜”是西王母比较典型的一种式样,在《山海经》中数次提到了“有人戴胜”、“蓬发戴胜”、“梯几而戴胜”。可见西王母对于“玉胜”钟爱有加。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史记·赵世家》中有一段提到了西王母:“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自称是天帝之女,在瑶池与周穆王相见并饮宴。西王母知道相会时间有限,“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只要有机会,还要再跟周穆王相见。周穆王答应以三年为期,西王母“中心翱翔”,喜悦之情难以自制。
到了唐代诗人的笔下,西王母逐渐变成了一位雍容华贵、美丽动人的女神。与西王母有关的仙药、蟠桃、青鸟等,也成为唐诗中经久不衰的素材。
李商隐做过一首与西王母有关的诗,非常有名。这首诗名为《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李白写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之一就写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玉华容。若非群玉山头见。便是瑶台月下逢。”
诗人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将西王母优雅、美丽、高贵、神秘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其经典文章《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中,给宗教做了如下的定义:“宗教象征在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了基本的一致,因而综合成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审美方式、风气和精神品质——和他们的宇宙观,即包括具体生活方式与特定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最全面的思想。”
从西王母的形象及民间信仰的演变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的古代,西王母的信仰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无论从这种信仰的产生,发展,到兴盛,都有其演变的过程和时代内涵。
6、中华民族神话与北欧神话的比较
神话故事是先人们对于世界起源、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东西方民族而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种族,对于神话体系的构建是不一样的。
最近正好在读茅盾先生的《北欧神话》。读完后,再对比中国的神话传说,会发现这两种神话传说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方面,这体现了人类民族发展的差异化。
《北欧神话》的开篇,《天地创造的神话》,会发现北欧神话是巨人创造世界。在世界之初,北欧也是没有地,没有海,没有空气,一切都包孕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混沌状态,冰霜巨人伊米尔劈开了这一切,成为创世者。而在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形成了天地,才有了后来的人类。从这一点上来看,东西方的先民们对于世界的初始认知非常相同。
不过毕竟是不同的种族,随后的发展剧情就很不一样了。中国神话中的巨人盘古是一个至善之神,为了人类的存在而牺牲了自己。在北欧的神话中,巨人是一个种族,是作为神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神为了创造世界而杀死了伊米尔,伊米尔的身体与血液化为了世间的万物与星辰。从创世的故事就能看出,北欧神话中战争是贯穿整个体系的始终的。
在古代中国,皇帝是神的化身,神话中的神仙必然是完美无缺的人物,于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基本上是道德完美的人物,他们拥有着超人一等的能力,也就是“道行”。神是悲悯世人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向神仙去诉说。
但是在北欧神话中,神界充斥着欺诈、争斗,神族、巨人的战争,是永恒的主题,“诸神的黄昏”是一种宿命,对世界的毁灭浓墨重彩的描绘,表现得极为悲怆。与万事大同的中国神仙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
在媒体形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使得神话传说的多元化传播成为一种趋势。
读完《中华民族神话与传说》之后,当你欣赏完瑰丽神奇的艺术插画后,想必在经历心灵震撼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思考与认知。
无论是“以神话读神画,以神画解神话”的绘画媒介传播,还是动画、电影的多媒体传播,神话故事不但不会消亡,反而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越来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