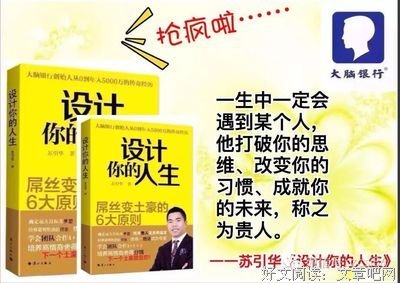
《陶瓷一生》是一本由[英]托尼·伯克斯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256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17-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陶瓷一生》精选点评:
●高足碗很美
●当然推荐
●简略看了一遍,总体来说图片精美,人物生平描写并不十分出彩
●图美
●呦! 这个系列出新书了,码了再说
●征服三宅一生和乔纳森·安德森 20世纪传奇陶艺大师 三获女王授勋,80岁仍创作不辍 作品打动无数眼光挑剔的收藏家 “我不是艺术家,只是个做陶的人。”
●精准且古朴,明媚且阴郁~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我永远都在学习。
●拙朴之美
●一直想要了解Lucie Rie的创作和人生,读了之后获得了一些启发
《陶瓷一生》读后感(一):膜拜的理由
怎么就那么好看呢。。
露西·里的拿手标志之作,黑色都是用锰料做釉,白色器皿用锌料做釉,都算常规安全。但偶尔有黄色器皿,竟用铀料做釉(没错,就是放射性元素的那个铀),也是惊呆此刻的我了。
想了想为什么会喜欢她的作品,除了老太太的风骨优雅坚定外,还有其作品的外在轮廓都是节制简约弧度圆融自然的,可迷人处又是高度的几何秩序美。
这与看完她的传记的感受是一样的,曾出身优越,少女时眼界便得家族中很有艺术修养还到处旅行的收藏家舅舅启蒙,懵懂时结婚,后志趣不投友好分开,其后再未结婚。有过爱人,是个那时候的斜杠青年,给她念诗和剧本,还会做玻璃器皿。不幸早逝,照片一直挂在她的卧室,直到自己离世。
但一生最滋养她的并非亲情爱情,而是友情。那些志趣相投或婚或单的男人,都是她感念一生的朋友。她经历过战争,也为生计而打工做过扣子,甚至当过放哨灭火员,但最终,只要坐到拉坯机面前,她就幸福无比。有段时间,她被聘为大学教授,但却严苛无比,在一次陶艺展览选作时,在不知道作者的前提下,将已是知名陶艺家某某的作品竟然也淘汰了。
在她随便一件作品在艺廊轻轻松松可以卖到1000美金时,对于登门来买她作品的普通人则会偷偷降价,拿着一个本子站到角落假装在看价格。
她也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自己作品有什么艺术理念哲学或内涵,只是说自己就是个做陶人。
看传记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部分共振的能量,猜她大概是处女座成分更多,夹一些水瓶成分。以其平生秉性,及作品风格。传记作者还提到她平时基本上都穿男性化的白色系衣服,非常重视朋友。
看到结尾,有提到她的出生日期地点,便好奇了去查她星盘,竟然是日火双鱼10宫,月海冥双子12宫,金水木水瓶9宫,南交金牛11宫,北交天蝎5宫。——艾玛,她不成艺术家谁成啊?!而且基本上能对应她的传记里记载的所有特征。但,强烈的处女座感觉从哪里来,难道是时辰不知道,升处女?
蛮神奇。
《陶瓷一生》读后感(二):低温燃烧的制陶人
作为一个非陶瓷专业、之前也从未听说过露西•里名字的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为什么同一件事她做了近七十年?从1922年进入维也纳工艺美术学院学习陶艺,到1992年最终因病被迫终止做陶。
陶瓷不是绘画或其他单纯的艺术,它诞生于人的使用需求,“先用而后美”。有客观条件(原料、烧制温度)限制,有规定技巧的要求和重复性的劳动,其次才是创作和个性的表达。偏重实用的陶瓷更像是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练泥、拉坯、上釉、烧制各个环节很容易拆分开来,比如中国古代的官窑、民窑陶瓷,创作者个人是湮没于集体中的,对使用者来说,创作者的名字也无关紧要。偏向艺术的陶瓷又很难与雕塑划清界限,个性和意涵往往只能通过造型传达,如此,陶瓷就只是一种被利用的素材,脱离实用,成为摆件。
露西•里做的陶瓷几乎都是实用器皿,碗、花器、茶壶、水罐……几十年如一日,表达和诉说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可以想象能从中获取的新鲜感和刺激也是有限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一个电窑要升至烧陶的温度需要至少22小时,从装窑到开窑需要三天时间,所需温度更高的瓷则耗时更久也更难。等待泥料干燥、等待坯体干燥、等待釉料干燥、等待窑炉升温、等待开窑……是每一次制作必经的枯燥过程。
她当然有过其他的选择。父亲是维也纳小有名气的耳鼻喉科医生,曾与弗洛伊德共事;母亲来自一个显赫的犹太家族,家中拥有葡萄酒厂和牧场。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成为一名陶工显然并不是什么体面的职业选择。20岁之前她和家人一样以为自己会学习一门自然科学,而后加入医学行业。
毕业当年她便嫁给了滑雪时结识的汉斯•里。如果两人更志趣相投一些,或者家庭事务不那么琐碎而令人厌烦的话,露西或许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主妇”。毕竟在朋友们看来,她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真诚而好客,何况还做得一手好菜。
不过幸有哥哥保罗、“桑多尔舅舅”和绘画老师的引导,她学习了艺术,并在维也纳工艺美术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受到其领军者的指导和赏识,作品参展欧洲各地,屡获奖项。也多亏了二十世纪初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她自身的独立性格,她看重自己的职业,并坚持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即使是做陶瓷,她也并非未曾产生过一点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流亡至英国,她在欧洲大陆的成就变得一文不值。为获得制作陶瓷的许可,她拜访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威廉•斯泰特-默里,对方甚至不愿同她握手。而当时已是著名陶艺家的伯纳德•利奇,对她的作品也颇有微词。这很大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四十年代她一度放弃自己精致的现代风格陶瓷设计,转而模仿利奇粗犷的民艺风器皿。托尼•伯克斯毫不客气地称这是露西创作中的一段倒退。
战争带来的物资限制,使得露西转而制作陶瓷纽扣获取收入。随着战事深入,陶瓷纽扣的制作也告中止。战争结束之时,她招募了几个助手,重启制作陶瓷纽扣的工坊。或许这会是另一个选择,在为品牌服装制作定制产品的道路上走下去。
此时,同样是伯纳德•利奇,令露西重新意识到陶瓷器皿制作的意义,并确定应该认真将其作为一项事业。1948年,汉斯•考柏的加入也改变了她的创作轨迹。“汉斯对事物有很好的的判断力,他会评论我的作品,他的观点都很敏锐。”她重新找回自己的风格,并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除了战争和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阻止过她做陶瓷。她对自己的感觉产生过怀疑,手却并没有因此停下。曾猜想这背后的支持力一定是巨大的热爱,就像心里有一团不灭的火,熊熊燃烧。她确实也形容1922年在学校第一次见到拉坯机的情形,像是“一见钟情”。但九十年代初,当她大病初愈被人问及将来的打算时,却反问道:“难道我做得还不够多吗?”没有宣言、没有感伤,多少是个有点令人意外的冷淡回复。
她曾自认“不是艺术家,只是个做器皿的人”。人们对这句话津津乐道,因为其中显示出一种谦逊的美德,但在露西,这可能并非单纯的自谦之语。“艺术家”靠的是瞬间的灵感迸发,混合着天才的火花;“做器皿的人”靠的是长年的累积和劳动,熟能生巧。那种“冷淡”并非因为时间将热情磨成了习惯,支持她不断创作的从来不只是一腔热爱。她看重勤奋,这大概也是她认定的自己有所成就的原因。
学院出身,获过肯定,有过迷茫,做陶之路走得循规蹈矩。只是不断思考突破设备限制的方法,用化学知识实现各种釉色的变化,尝试不同工具(甚至米粒、笔帽)的效果,在传统作品中寻找器形和工艺的灵感,实践在下一次的制作中。比起迫切情感的倾诉,这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实验,在穷尽所有可能之前,除非外力强迫,不会终止。
所以人们会听到她说“我不算什么,汉斯才是天才。”“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端,而我永远都在学习。”六十年代,她在坎伯韦尔授课时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不否定也不过于支持”,相信他们只要经过年复一年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陶人”。依然有一团火,只是烧得不疾不徐,持久地保持着温度。
从她的器皿上也能反映出这一点。技术纯熟后个性的揉入几乎是无意识的,她能以“经验”感知拉坯停手的时刻,决定怎样是最佳或最美。她的器皿有诸多条件限制,不同作品间也不乏相互承继之处,但却没有两个作品完全一样,每一件都充满个性与存在感。无怪很多人都说,她的东西虽然产自精密的设计,却不是无机质的,有种令人想要伸手触摸的神奇魔力。后来者想要模仿只能仿造其形,却不得其旨。
当然,露西•里一生都很少谈及自己的创作或对陶瓷的看法,这些只是揣测。在如今市面可见的两本比较完整的露西•里传记中,也少有具体事件细节和心境的摹画。托尼•伯克斯这本由她本人生前参与的传记,更像极她本人的作风,大块面的生平概述,关键事件的事实陈列,一句写过几十年,随后是大量作品的展示。即使碍于照片年代久远,有些已模糊,或是黑白色彩无法准确传达出那些个性鲜明的色彩,也依然可以从中捕捉到那些器皿坚实的骨架与柔和的轮廓。
她也无须再解释什么,有这些作品代为诉说足矣。
:标题偷自NHKいま裸にしたい男たち20010221
《陶瓷一生》读后感(三):“名物是思想诗意的瞬间”
在读《陶瓷一生》的时候,收到在网上订购的一个手工陶瓷碗。釉料是青花,碗面上有几处缩料的创面,露出底下灰白的坯子。我向卖家询问,他满不在乎地回应,手工制的东西就是这样不可控。你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退回来。我当然不满意这个说辞,但也没有退货。
在“民艺”风泛滥于陶瓷界的今天,似乎提到手工制瓷,就必须拙朴、不规整、有瑕疵,如此,才够天然和纯粹。其实,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反映出来的只是制瓷者的不专业,而不是赤子之心。如果把日用陶瓷上升到工艺美术的高度,一件称得上作品的日用瓷,必须是精湛手艺和高度审美的结合,缺一不可。
如果对“什么是日用陶瓷的美”有疑虑,推荐你打开《陶瓷一生》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介绍的是欧洲陶瓷大师露西·里和她的作品。
露西是个出生优渥的贵族小姐,在维也纳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父亲是著名的医生,跟弗洛伊德关系密切,母亲家世显赫。舅舅不仅经营着庞大的家族业务,还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她夏天去母亲家族的庄园度假,冬天去瑞士滑雪。上大学的时候,她选择了看似不务正业的维也纳工艺美术学院。上学第一天,露西看到拉坯机便一见钟情,从此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陶瓷。大三的时候,她的作品入选了德意志制造联盟在巴黎的展览;她的毕业作品参加过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
露西不但才华横溢,还有着不自知的美貌。年轻的时候她有多美——同住一栋楼的维也纳著名摄影师梅特纳格拉芙在电梯里偶遇她,便托朋友联络她,想为她拍照。如果没有战争,可以预见露西这一生平顺无忧。可是战争来了。作为犹太人的她,只能逃难逃到英国伦敦,理想国的世界就此坍塌。
在英国,露西与结婚十多年的丈夫分道扬镳。她留在英国,继续她的陶瓷事业。丈夫独自前往美国。
露西把工作室设在海德公园旁一个马厩改造的房子里,她为工作室买了一个烧窑的电炉。伦敦没人认得她,更没人会买她的瓷器,最初她只能做扣子。谁能想到,现在这些陶瓷扣子,也成了收藏家们竞相收藏的对象。而在当时,是她生计的来源。
在英国,她就是一个陶瓷工匠。青年时代的她在陶瓷上就显露出了过人天赋。即便在维也纳工艺美术学院求学时期,她的作品也没有迎合当时工艺瓷的主流——有着民俗风的工艺小品,她学生时代的作品就以家居器皿为主,线条简单明了,釉色富有创新精神,整体具有很强的功用性。她对陶瓷的审美,一开始就是坚定且执着的。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匠,需要的是长期刻苦的反复练习;但成为一名大师,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天赋,需要对美的直觉。
在伦敦,她结识了一帮好友。首先是伯纳德·利奇。利奇是奥地利人,出生于香港,在英国学习美术,曾在日本定居并开始制陶。利奇当时已经是欧洲手工陶艺界的大牛。虽然两个人对“陶瓷之美”的认知差异巨大,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交往,他们的友谊维持了一生。然后诗人、玻璃吹制大师,同样来自维也纳的弗里茨·兰普尔。这是她深爱的男人。他的照片一直悬挂在她的卧室里。
最重要的是她的工作伙伴,德国难民汉斯·考柏。这个最初只是来她工作室找份做扣子工作的人,最终成了她制瓷生涯最重要的搭档。他们联名制作的作品,已成收藏市场上的珍稀之物。他们对手工工艺陶瓷审美有着超乎寻常的默契,在技艺上,两个人势均力敌又各有所长。
露西的陶瓷生涯逐渐展开,艺术品画廊开始展出她的作品。即便在当时,她的作品价格也并不便宜。她制作的都是生活用瓷,一生之中唯一一件装饰品,还是在大学阶段制作的。她声名鹊起,却并没有抱守陈规。她不断从艺术中汲取灵感,运用到新的陶瓷制作中。例如,后来成为她风格代表的工艺手法——剔釉,就是从史前美术受到启发。她和汉斯联名制作的沙拉碗,在器型上对传统沙拉碗做了一个改变,增加了一个倾倒沙拉对出口,这又成为一个经典。
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意识到她的价值。英国著名陶瓷商韦奇伍德曾邀请她制作茶具及咖啡具。但因为工艺难度太大,韦奇伍德放弃了这次合作。手作和批量生产之间也许确实存在着鸿沟,但如果这次合作能够成功,对英国当代制陶工业,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六十年代,露西也曾在伦敦的坎伯韦尔大学里授课,但由于她过于严格,这段经历并不愉悦。作为设计协会选拔委员会的成员,她在匿名挑选作品时,否定了同辈杰出陶艺家卡迪尤的作品。她与那个时代,存在着误解和不调和。也许,从到达伦敦的那一刻,她就注定是孤独的。天才都是超前的。
露西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制作陶瓷上。就算到了七十岁,她仍有旺盛的创作精力。如果不是健康阻碍了她继续工作的步伐,她不会停下拉坯的手。
如今,露西的作品被国家级的美术馆收藏,和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光辉灿烂的艺术品陈列在一块。当我在大都会博物馆无意中路过一排陶瓷展架时,我一眼看见了陈列在其中的露西的作品。它们是那么与众不同,即便是当代的日用瓷,仍然美得严谨而优雅,克制而又光芒四射。这种日用瓷,只能与丰沛、低调、内敛、从容的生活相得益彰。我不能想象,在金碧辉煌的巴洛克豪宅中,露西的餐具被使用、被传颂。这种直击当代日常生活最高级的审美形式,是露西在上个世纪就已认定并坚守的。她天生具有好品位,也具有能实现这种品位的技艺。她一直强调自己不是艺术家,只是个做陶的人。她会为研究借鉴利奇的釉料配方,重新购置温度更高的电炉。她会一遍遍试验釉料和温度的关系,一遍遍尝试实现新的工艺所要求的最佳温度。她痴迷手工拉坯,痴迷釉料的多端变化。她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严苛。同时代的艺术家最能理解和感受到她的魅力。她一生的知己,是玻璃吹制家兰普尔和陶艺家汉斯。三宅一生对她推崇备至,邀请安藤忠雄为她设计日本巡展对展厅。日本陶艺家“人间国宝”滨田庄思与她心心相惜。她的作品里,有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这种单纯和伟大又为日常生活所使用,是摆脱了喧嚣、庸俗生活的美。
露西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各种生活陶瓷器皿。花瓶、碗、杯子、碟子。它们当初被制作出来,是希望能被使用的。壁炉上摆放着花瓶,下午茶用她的茶具。晚餐的桌子上,有她做的碗。这种平淡却真实的生活图景,大概是露西完美童年的再现。那时她和表哥表弟们躺在庄园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流云蓝天,时光停滞。如今,露西离去。她母亲家族的旧居,已经成为当地州府的博物馆。而那个曾在旧居中生活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陈列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博物馆里。文化的脉络从来不曾中断,哪怕从维也纳颠沛到伦敦,哪怕失去母语,失去家园,哪怕要在战争的炮火里、在坚硬的水泥里开出花朵,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从最早谁都不曾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陶瓷一生》读后感(四):《陶瓷一生》| 做一件永远不退休的事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端,而我永远在学习。——露西·里
《陶瓷一生》介绍了女陶艺家露西·里的生平。作者尽力为我们勾画了露西完整的艺术生涯,包括她小时候学习绘画,到后来学习陶艺的所有经历。文中多处涉及陶艺制作的过程,让我意识到陶艺并不是用土捏个罐子那么简单,而把一生都贡献给陶艺事业的露西也有许多让我惊叹的品质。
一、不再享乐 “十五岁的露西从一个派对回来后得知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发誓不再享乐。露西深爱这位充满艺术气息又讨人喜欢的哥哥,正是保罗帮露西找到了绘画老师,并竭力说服相对保守的医科父亲,发展露西的艺术天赋——将她培养成艺术家。” 露西的二哥保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不仅关注妹妹的成长,在战争时期粮食紧缺,他还会在自己家地里种菜,并且把卖菜转来的钱接济穷人。但就在他入伍两周后就因为嘴部中枪而丧生。失去了哥哥保罗,让露西意识到生活的无常,并且开始思考享乐在人生中的意义。宝贵的生命如此易逝,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做些比享乐更重要的事情。“不再享乐”这四个字是一种有力的论调,我的生活虽然也并没有以享乐为目的,但我也会选择有趣但有害的事情,而不是无趣而有益的事情来做。比如挑食。比如宁愿躺在沙发里看电影也不愿意起身运动。现代家庭当中的装修大都朝着越来越舒适的方向走,但是在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目标上,如果我们有需要一些辛苦才能达成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把享乐设立为路标。 二、做一件永远不用退休的事 “露西在七十年代非常高产,也参加过许多展览,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也证明了她作为一名陶人的专业性,她能意识到离开公众视野就意味着失去关注。” “持续的订单对于露西作品的销售已经不再重要,但对她而言仍旧意义重大。在经历了长久的不安定之后,订单让露西获得安全感,证明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世界的关注。这些订单也构成了切实的理由,让她坚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全天都投身于工作,而非慵懒度日或陷在椅子里读书。露西对“退休”的想法嗤之以鼻,这正如朋友们心中对她的印象:露西是位积极创作的陶艺家,创作是她生活的目的,也是她的生活本身。做饭、烤蛋糕、熬果酱、社交,这些日常琐碎不可避免,但创作才是基本,它们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必须适应创作的安排。” “对于露西来说,青春就是财富,决不可浪费。虽然出身中产阶级,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学会了节俭,这也成了她人生的指导原则。”
在露西长达93年的生命里,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在奥地利的家。失去哥哥之后,露西还在生命中相继失去了好几位心爱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爱人。接连不断的失去让露西很渴望安全感,而安全感的来源就是她的陶艺事业。她虽然有很多朋友,但她并没有孩子,第一次婚姻也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她在维也纳工艺美术学院读陶瓷专业的时候就开始制作各种陶瓷作品,并且获得称赞,但她真正成为声誉全球的陶艺家却是在“大多数英国人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纪”,在这漫长艰难的过程中,她好像从来没考虑过要放弃陶艺这件事,她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陶艺事业,她把生活中的时间都用来创作,探索和精进自己的技巧。对于那些我们想一直从事、不想退休的事,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专注”这样的建议,但在露西身上我看到了如何实践“专注”的榜样。 三、朋友眼中的露西 “她是个非常慷慨的主人,做饭尤其好吃,总是穿些简单的、几乎是男性化的白色系衣服。对于她爱的人们,她是一位真挚的友人。而且一旦成为朋友,便是一生的朋友。”
这段评价来自于露西的好朋友兼藏家的亨利·罗斯柴尔德。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只顾着创作的冷淡艺术家形象。当然啦,做饭好吃在哪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品质!
四、露西的签名 露西在陶艺作品上的签名是由她很好的制陶伙伴汉斯·考柏设计的,能看出一些甲骨文甚至是篆书的风格。 本书封面上简洁优美的手写签名看似不费力气,但也是露西经过了两百多次尝试之后才完成的。有的时候我总是会抱怨自己交出来的作品不尽人意,但我尝试的次数其实很少,有的时候是一两次,连重复三次的其实都很少,更别说反复地修改和改进了。诗人玛丽·奥利弗说她的一首诗有时候会修改一百五十稿,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做一件事做的不好,也许可以再多练习几次。 最后让我们以本书作者托尼·伯克斯对露西的一段记忆结束: “我个人对露西的记忆历久弥新:一旦被委以一项任务,她便会尽全力完成。为了本书封面的签名,她反复尝试了超过二百五十次。晚年,瘦弱的露西时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仍旧穿着一身白衣,但两次中风之后她已经无法言语。我努力试图不让这样的画面占据回忆,而将她那动人而友善的微笑永留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