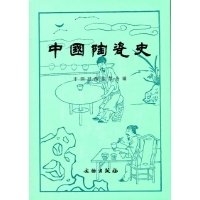
《中国陶瓷史》是一本由中国硅酸盐学会著作,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0元,页数:4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陶瓷史》精选点评:
●这本书我有发言权,
●原始陶瓷和宋瓷的部分讲的很好!元明清有些简略,但重点也足矣把握~
●当年在景德镇时,认真地看过此书。
●看完我好想把家里的花瓶啥的全换掉!
●我真怀疑自己买的是盗版,为什么别字那么多?
●和韧勉一起在福州路买的
●陶瓷史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陶瓷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学院派,太学院了。但实在很系统。工具书,时常翻阅每次都有收获
●考古学生必读
●玩瓷器必读的吧
《中国陶瓷史》读后感(一):很好的基础书
这本书是必须要看的陶瓷类教课书,应该和冯先铭的《中国陶瓷》配套看。此本着重于陶瓷的发展历史。冯老的那本着重于鉴定,比较简略。建议先看完硅酸盐出的这本,再看冯老的那本。对于想了解陶瓷史发展的人来说是本不错的读物。
《中国陶瓷史》读后感(二):淘瓷茶具
看上去蛮时尚一样!支持~~~~~大家有好东西一起分享分享交流交流~~~我的淘瓷茶具店欢迎大家光临提点意见http://hurenzhi.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ItZ1n8
《中国陶瓷史》读后感(三):瓷艺生活
现在的我,每天都很开心,也很充实,因为我有我的桔子。
那年,递完辞呈,满身疲惫的我回到景德镇。游走在街头,不敢给家里打电话,不是窘迫,而是害怕听到爸妈口中那满满的担忧与关怀。大学毕业已是多年,我早该为自己的生活买单。父母可以呵我护我,却已没有义务。我又怎忍心让他们现在还日日生活在对女儿的担忧中,茶饭无味。
想起当初和沈姑娘的约定,我再次来到游玩时遇到的赵师傅家门口,不知道当初的戏言,老师傅还记不记得,还当不当真?
“小姑娘,回来啦!老头我可等你们很久了。再不来,我怕老头我都制不动陶了,那可是要爽约喽”
“我知道赵师傅你最讨厌爽约的人了,我怎么可能让我们都变成你最讨厌的人呢?”
我想当时赵师傅一定看出了我状态有多糟糕,只是没有点破而已。
几乎花尽所有积蓄,桔子印象DIY工坊开业。没有忐忑,只有满满的喜悦与踏实。
“师傅,你看,我们的桔子印象!”
“没想到当初我们三个人的戏言居然成真了,还好老头我手艺还没生疏。对了,沈丫头知道了么?”
“我给她发照片了,嘿嘿,师傅,你说她要是辞职,她老板会不会怪我吖?”
现在的桔子印象,已不再是只有我和赵师傅两个人。赵师傅找来了自己的同行老友张师傅,然后两人陆续收了几个年轻徒弟。而我,每天在桔子印象打理他们新制作出的瓷器,闲暇时,用我们自己制作出的茶具喝喝茶,聊聊天;或是跟两个老师傅学学制陶,虽然目前我做的瓷器还只敢带回家或赠好友。
昨天给家里打电话,老妈说,每天在家闲闲的有点无聊。
想把老爸老妈接过来,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我的桔子,会不会喜欢工坊里的师傅们?先接过来再说吧,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中国陶瓷史》读后感(四):中国陶瓷史读记
2012年3月,我从亚马逊上买入此书。
买此书的目的无疑是装逼,因为在博物馆工作,怎么也得弄一本儿回家隔着,心里面还得想着自己是他妈个文化人。
买书伊始,看过头4节,真是认认真真看的,看的时候手边就放着一本《新华字典》,有不认识的字立刻就查,还依然有查不到的字,因为旁边还缺少一本书——《怎样查字典》。后来天气热了,在我那时的住所地下室里喧闹难受,因此阅读进度搁浅了。挑着看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五大名窑。后来不住地下室了,把这本书放在家里书柜中,纯粹当成一本工具书查阅。一有陶瓷方面的问题就翻阅,然后就发现了,此书如果定义为工具书也多有不妥,因为他并非以查阅为检索编排。这就是一本纯粹的历史书,化学陶瓷的历史书。
2014年10月,我前往杭州旅行,期间参观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陶瓷馆的时候,突然想应该好好从头到尾的阅读一遍《中国陶瓷史》,因为参观博物馆之时,面对展板上的叙述及陈列在面前的文物,我发现自己是那样无知。即不知道他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要到何处而去。特别是看到婺州窑时,这种想法特别强烈。我是一个北平人,很少到南方去,更别提对南方历史器物的了解,基本为零;因此书中看到和想象的差距,甚至从未知道的世界,都给自己莫大的好奇感和冲击。因此结束度假以后,我就要好好读一遍此书。
从10月18日起,到12月20日,中间有一周出差在外,其余基本以每天一节的速度阅读。书中已经画满了红笔的曲线,即便这样,在读完此书的今天,回忆之前的内容依然有诸多已经忘却,混淆。这肯定不会是自己最后一次阅读《中国陶瓷史》,读此书的前三节,就有了一个想法,即将书中的内容作成表格形式,提炼精华,便于查阅。这项工作,想在日后完成,就必然要再仔细如今次这样阅读一遍书中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配上图片,尤其走访各个博物馆留下的资料,这样书中的内容才能真正掌握。
其实掌握了也他妈没用,里面没一件东西我买得起,历史上任何一样东西,我也他妈买不起。
《中国陶瓷史》读后感(五):【转帖】怀冯先铭先生(刘涛)
我与冯先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
1992年底,我在新成立的深圳文物商店“试工”期间,当地一家报纸向我约稿,希望我写点古玩收藏鉴赏或文博圈内名人逸事之类的小文章。恰好这时我到北京出差,而店里本来就有考虑,想延聘京城几位文博界名流作顾问,以求其庇荫,大树之下好乘凉。这样我便动了心思,打算顺便采写几篇“人物专访”。那时我对出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今更名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冯先铭仰慕已久,于是头一个采访对象就选定了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求见,这好像也更有面子不是。
那天,我先摸到冯先铭工作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他不在,见到也在这里从事研究的他的女儿冯小琦。小琦说,她父亲要去台湾讲学,过几天就走,现正在家里忙着准备,不一定有空会客。不过小琦还是给她父亲打了个电话。也许是看在“记者”面上,冯先铭同意见面,请我马上就到他家去。
我按小琦画的路线,找到小石桥附近一栋故宫宿舍后,冯先铭已在楼下迎候了。早听说冯先铭是故宫有名的美男子,果不其然,年逾古稀的他,依然风度潇洒,一表人才。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溜倚壁而立的书橱上层层摆满古陶瓷,其又以“老窑”居多。一室的“南青北白”、唐风宋韵,更让人感受到主人品位、身世和学问的不凡。“我不是收藏家,只因研究需要,才收集了这些标本。它们也不值什么钱,大都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冯先铭首先声明。我知道,个人收藏文物,对文博工作者来说还是有些忌讳的。私人不收藏文物,“考古不藏古”,这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当年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的共同约定,作为职业准则,今对海峡两岸业内人士仍有一定约束力。对此,冯先铭当然清楚,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收藏一些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物,只要途径正当,还是应当鼓励的,因为这对研究有帮助。常到市场上转转,真的假的对比着看,也有助于提高鉴别水平。现在文博单位专业人员大都不会鉴别真假,就是因为脱离市场。
冯先铭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遵从父命(其父冯承钧,著名历史学家,在汉学译介方面“既多且精”,于西北及南洋史地研究上亦有功焉),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故宫正清理院藏物品,请来一些精于鉴别的古董商和前清遗老,冯先铭随他们一起工作,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在古陶瓷方面,由于早就喜欢,更是多有所获。不过,研治古物在过去算是“冷门”、“小道”,要选择古陶瓷作为自己终身治学的对象,对喝了一肚子洋墨水、曾发愿秉承父志而从事汉学传译(这在当时可是“热门”)的冯先铭来说,内心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五十年代初,主持全国文物工作的郑振铎提议在故宫建一座陶瓷馆,并捐出自己收藏的两千余件古陶瓷。冯先铭又被“指名”参与了陶瓷馆的筹备工作。我们知道,故宫的瓷器旧藏,以明清官窑和“五大名窑”为主,精则精矣,但不足以反映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全貌。因此,陶瓷馆建立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故宫又从全国各地收购和“调拨”了不少出土或传世的古陶瓷。南京、上海多见的六朝青瓷,洛阳、西安出土的唐三彩和白瓷,以及过去不被看重的磁州窑瓷器等,纷纷被“请”进昔日的皇宫。加之海内外收藏家的不断捐赠,至五十年代末,故宫的古陶瓷收藏已是“官民并集”,蔚为大观了。而此时的冯先铭,也终于不再犹豫,决意走“冷门”,在古陶瓷研究上一展身手了。
1982年问世的《中国陶瓷史》,可说是一项功彪史册的浩大工程。作为牵头人,冯先铭为此做了大量筹划组织工作,并独自或与人合作撰写了其中分量较重的两个篇章(唐、五代,宋)。说起这本书,冯先铭不无得意:编写一本内容详确的陶瓷史,是我们这代人的夙愿。过去人们对古陶瓷多满足于赏玩,好古而不知古,仅有的几本陶瓷著述也几乎都是古董鉴赏家之言,其中疏漏和问题自然不少。这与我们这个“瓷国”的身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为改变这一状况,自1954年起,在老一辈古陶瓷学者陈万里的带领下,我们故宫就开始了古窑址调查工作。四十年来,已调查了大半个中国两百多个市、县的数百处古窑址,解决了不少问题。后来考古、科技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关注到古陶瓷,特别是中国硅酸盐学会的同志尤为热心,他们借助科技手段对古陶瓷制作工艺展开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这样,一部寄托两代古陶瓷学人梦想并汇聚多个学科成果的大书才得以面世。该书在海外也引起关注,日本的东洋陶瓷学会随即组织翻译出版,为表彰中国同行的工作,去年他们还向我授予了“小山富士夫纪念奖”(小山为日本著名中国古陶瓷学者)。冯先铭说着取出一枚精致的奖章和一部装帧华贵的日版《中国陶瓷史》给我看。“小山富士夫是日本‘古陶瓷之父’,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奖是日本陶瓷学界的最高荣誉。这个奖可是第一次授予中国人呵。”冯先铭又补充道。
在我登门之前,冯先铭正紧着编选这次赴台讲学所需的图像资料,案头上堆满各种古陶瓷图册,其中多半是国外和港台出版的。他说,这次到台湾是讲古陶瓷鉴定,过去我很少讲这个,主要兴趣还是在学术课题上,这次讲鉴定,是对方主动要求的。近年来台湾出现“收藏热”,不少人从大陆或香港市场上收东西。由于两岸交流不畅,他们对大陆这边仿古瓷的情况不很了解,所以常常上当。谈到这个话题时,我顺便取过一本近年在大陆流行甚广的台湾版宋元陶瓷图册,就自己看不大明白的几件“宋瓷”,请冯先铭过过法眼。这几件瓷器好像都是清宫旧物,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件“北宋定窑白釉柳斗杯”,我还曾写过评介文章发表在小报上,可后来我越来越怀疑书上把它们的年代和窑口搞错了。对这几件瓷器,冯先铭似乎早已洞悉若明,照眼一看,立马定谳。对“定窑柳斗杯”,他认为不是宋物,亦非定器,实为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所制,其刻花柳斗纹是仿唐宋的,但造型及工艺却与唐宋风格相去甚远。这时的冯先铭似乎更来了兴致,由此及彼,他打开一本国外的图册,指着一件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磁州窑风格的花瓶说,这件“刘家花瓶”也有问题,过去认为是宋代的,其实是民国仿,它的最大破绽是龙纹为五爪,触犯了宋代民间画龙只能画三爪的戒律,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花瓶刘家造”的铭文也不对,“花瓶”一词在宋代还没出现。关于这件瓷器的鉴别,他说他已写成文章,这次到台湾也要讲。——他的这篇文章后以《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为题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除他认为是“破绽”的龙纹和铭文外,文中还罗列了“刘家花瓶”的其他“疑点”,如“比例失调,颈部过长,足又撇得过大,与宋代瓶的造型不同”等。不过,这里还是要说,在“刘家花瓶”的鉴别上,冯先铭可能失之于臆解和武断了。扬之水、秦大树及笔者等人都曾写文章,依据实物和文献资料,证实“刘家花瓶”确属宋金之物,而且这类产品可能出自豫北地区窑场。笔者还曾亲赴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通过近距离观察并与该馆专家切磋,更确信“刘家花瓶”绝真无疑。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可惜冯先铭泉下已不能知矣。
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告别时,冯先铭一直送我到楼下,还说欢迎我以后常来做客,不料这一别竟成隔世。回到深圳后,“人物专访”因忙碌一拖再拖,直到来年开春才动笔,可文章还没见报,冯先铭就走了,听说是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遽逝。本来,冯先铭已作好安排,开春后到山西考察古代黑釉瓷遗存,然后出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再就是循环往复的讲学、写文章、编书、筹备协会年会等等。他还答应我,在暑天到来之前,抽时间飞一趟深圳,接受我们的聘请,再看看特区的古玩市场和博物馆。可他再没有时间了。我还清楚记得,他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既兴奋又有些无奈和焦虑,一再感慨要做的事太多而时间又太少。
冯先铭故去瞬已廿载。作为我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仍活在他所开创的事业中。直到今天,他三十年前主持编修的那部《中国陶瓷史》,还是被普遍认可的“权威”著述,尽管实际上该书的权威性已被时间大大消解——这丝毫没有唐突前辈之意。在陶瓷史研究方面,三十年一部书,如果说有点寒碜,也有点悲哀的话,那么这也全怨不得逝者。我相信,假如冯先铭在世,这部书早就不止一次地修订了,甚至另起炉灶重修都有可能。因为在我看来,冯先铭是一位想要做事而又特别能做事的人。诚然,不必为尊者讳,冯先铭由于“半路出家”(非文物考古专业出身)且受限于“文革”年代的政治及学科环境,出掌古陶瓷研究会后又事繁鹜博,故在研究上可能未尽其才,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卓越的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他的主要贡献也确乎集中在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规划实施方面。当年冯先铭的搭档,同为《中国陶瓷史》主编的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朱伯谦生前也都曾对我说,冯先铭为陶瓷史的编撰与出版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他是极富感召力亲和力的“灵魂人物”,是主编中的主编,没有他,也就没有这部陶瓷史。
斯人往矣。“闻鼓鼙而思将帅”,而今我们还会再有一个冯先铭吗?
刊于《中国文物报》2013年4月10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