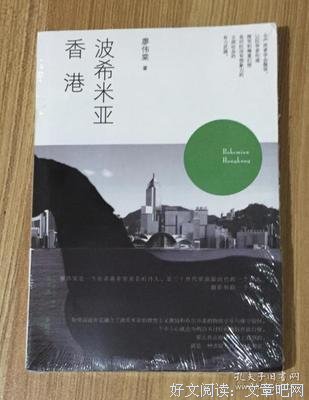
《波希米亚香港》是一本由廖伟棠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波希米亚香港》精选点评:
●“香港之成为我的我城,是因为它的书店、老区、人情和散漫”
● 不好看,不知所云。
●香港亚文化一瞥,离它这么近却感觉不到,真是前现代的生活困窘了,像文本寻找波西米亚的香港吧,只是这不是完整的香港。
●看不下去
●好久看书没有因为强烈认同感而激动了。不过怀疑有删节。真正的城市是看不见的 ❤
●有些东西越了解兴趣越是浓厚 有些反之。讲音乐的部分因为看过天与地且很爱所以看得有滋有味有能融入书中人物的情绪;将本土文学诗歌的部分却是第一次接触,我想这是几年来香港人对于自己社会的过大变迁难以适应所带来惶恐不安乃至愤怒是我们同样这些年同样这些事却都是欢天喜地对待的大陆人所不能理解的...
●书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写香港文化(亚文化),第四部分是关于香港/文学的诗歌。个人不怎么喜欢诗歌部分,不是不好,而是因为指涉比较私人,我领会到的“诗意”不多。前三部分虽然是专栏文字,但文笔好,见解独到,我蛮喜欢。书中插了不少摄影作品,但印刷很差,影响观瞻。
●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外人不能切身体会的,也不会对这个城市的苦难感同身受。很多文人用文章和诗歌来发声,最终目的还是唤起社会大众对本土城市的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在中国,似乎没有哪一个城市的文化工作者不寂寞不孤独,而这恰恰也是他们的选择和理想。
●一本介绍香港文化与艺的书被他写得如此具有蛊惑力。前面有印刷小瑕疵。后面的诗很棒。
●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往事,还有他们的流离失所,灿烂又哀伤,尽管惶恐却保持着固有的尊严;经历过一场场文化运动与艺术生活,在香港这座看不见的城市中,这是一代人的故事;最后,诚品书店终于没有开在南京
《波希米亚香港》读后感(一):诗人眼中的“波希米亚香港”与安那其情怀
短评廖伟棠《波希米亚香港》
杨津涛
刊于9月5日《南都周刊》
恐怕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香港都只是一座金钱堆起来的文化沙漠。但通过廖伟棠的讲述,我们却会发现香港文化的灿烂多姿。香港自身固然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因其未曾有被意识形态所掌控的历史,文人和艺术家们得以自由挥洒,发展出独立的本土文化。看那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往事、南丫岛上的诗人狂欢、勉力维持的“二楼书店”……构成的就是诗人眼中的“波希米亚香港”。
同时,作为诗人和摄影师的廖伟棠,其实长期以来都在关注着两岸三地的时政与民生。这不是一本谈论政治的书,但书中对香港反叛青年和“摩罗诗人”的赞许,却自然流露出作者的安那其情怀。
《波希米亚香港》读后感(二):读书序
序由好友李照兴执笔,俩人同日出生,就北京或香港的今昔交流、感慨。在故乡和异乡之间,充沛地介入,冷静地察言观色,始终对两地抱有热爱和熟稔。
文字有言“他(廖伟棠)有感而发的那一首诗,侧面折射出我曾那么熟悉的城市之新生。而这种隔岸观火般回望香港的感觉确然有点怪异。”城市的更新如流水线般,永不停歇,把握其命脉的企图很快便遭到打击,甚至受到重挫,正如某人的自嘲式改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一只用来寻找光明,一只用来翻白眼”。
多年前,李的说法是“在自己的城市中流亡”这明确表示的归属和不言而明的命运让个体在城市中奔逃,也许是无方向的,散漫的,在显然的自我边界中消失,融入,挣脱,游离。
李的兴趣所在,“波西米亚,带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性”。但李书写的波西米亚更接近经过某种“不同程度计算过的安全感”,争取着一点”布尔乔亚的物质享乐与保守情怀“式的”进取入世的波西米亚“。
廖的诗句”一首诗挡不了一辆坦克,但一首诗可以创造的东西,肯定比一辆坦克摧毁的要多得多“。
李口中的”诗人的生活“:”保持一种对世界的陌生感,认真对待生活,真诚抒发感觉“。
《波希米亚香港》读后感(三):大陆波西米亚?
做文化是痛苦的。理想主义之花愈美,其刺便也更尖利。
我不敢去看廖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的诗作,原因只是怕,害怕念及大陆诗歌创作的窘境——89年后,中国诗歌就“死”掉了。其实又何止是诗歌呢?小说、散文,大陆方面的取材许多仍停留在知青下乡时期抑或黄土高坡的环境底下,读者寥寥并非难以理解(窃以为王小波已把知青年代写至顶峰,无人能及)。当代些的便是官场揭黑,看多了也乏味。反观港台作品,小说、散文有西方尚哲思的痕迹,又不失古中国一脉相承的底蕴,读来舒服而不厌烦。朱氏姊妹、简媜、鹿桥、董桥、舒国治、骆以军、马家辉、林行止、止庵、董启章、李欧梵……我以为大陆鲜有出其右者,即便有似木心者多已早早留洋,或已故去或过了隐士般的生活。
一直以来,我很惶惑也忧心忡忡。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侧身其间、不愿北上的文人骨子里的波西米亚情怀是否更能承袭和显现古中国文化的智慧呢?
香港回归十年有余,大陆和香港相望之间,香港的文人似乎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空气。于是梁文道们北上“传经授道”似乎已成时尚,单前月的上海书展和最近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便慕者如云。我等措大自不必探明他们内里究竟有多少墨水,身在大陆应该细究的是相形之下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的境遇。新世纪以来,余杰的声音以来难得听见,许知远、李海鹏们的勃兴自然值得欣慰的,但他们到底能走多远,能否到达萨义德、萨特、加缪的高度仍然值得斟酌,毕竟他们都还年轻,所看到问题的多维性和深度都还有欠缺。
曾将大陆香港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和凤凰两大媒体中的读书栏目粗略比较。中央十套自“子午书简”到“读书”,节目形式由单纯朗读到主持人与书评人的对谈,所荐图书思想深度难以让人满意,本身也缺乏张力,节目收视率便也惨淡,虽然坚持做了十余年读书栏目的主持人李潘自身已属不易。而凤凰的“开卷八分钟”,一周五天,每天短短八分钟,考虑到香港快节奏的同时,却紧凑而不乏轻松和最重要的思想性。梁文道、何亮亮、马鼎盛诸人四百八十秒的滔滔不绝已算得上饕餮,否则《我读》系列便出不到第三辑也难有这许多拥趸了。
《独立书店,你好》一书中称台北为“书店之城”,而同样作为“民国”“都城”的南京竟只一家先锋书店入选,令人唏嘘喟叹。拜金、实用在大陆泛滥已成不争事实。“911”十周年纪念日前夕,麦家曾在某书友会上反复强调大陆人文关怀的缺失。待到笔者提问曰:现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自省并将东方之传统价值取向传至普罗大众时,麦家很巧妙地指出自己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仅是一介写作者。一个写作者最低限度的能力、责任自然就仅仅是那被说滥了的“我手写我心”,以期共鸣罢了。这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有相当差距的。
不见“无双国士”之壮烈已有千年,不见箫心剑气之豪情也过百年。然今大陆知识分子之气节安在?大陆波西米亚安在?
《波希米亚香港》读后感(四):作为手抄本的香港——读廖伟棠《波希米亚香港》
我周围很多人口头都知道且喜欢使用“波希米亚”这个词汇,却没有几个了解波希米亚的含义,更别说它的来源了。在历史上,波希米亚人过着漂泊生活,生活潦倒,资源贫乏,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仅靠自己的手艺谋取最简陋的生活。甚至,波希米亚人因不信仰上帝,而被天主教视为异教徒,遭受长达数个世纪的迫害。而欧洲艺术家们,或许因为自身的落魄,而无法看到波希米亚人生活的困窘,却意外地发现了他们的自由和随性。当自由遭遇艺术家,无疑是求之不得的精神支柱。流风之下,波希米亚之风迅速波及整个艺术家群体。1849年,缪尔热的《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被搬上舞台,“波希米亚”正式风行世界。在此之后,遵行“波希米亚”的人们,几乎全都追求另类、反叛、自由、个性张扬,不信仰一切主流精神。
60年代的香港,经济虽然复苏,文人却很落魄,读者阅读水平也低,文人为求稿费维生也只能迁就写通俗、速食的作品;70年代的香港,文化界蓬勃发展,实验性先锋性更显现;80年代的香港,音乐创作冒出头来。对于世人来说,八十年代的香港最让人津津乐道。Beyond、达明一派等乐坛盛事的蓬勃发展让香港声名远播, 那些有灵魂、有血肉的音乐,至今仍让人无法忘怀。而今,香港再度成为物欲横流的欲望都市,裹挟其中的香港公民为精神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需求较之以前更为迫切。然而,物质必然颓败,精神终将永存。在物欲之下,香港的波希米亚人,他们可以在牛棚、废墟之上进行精神性的反抗,无论失败与否。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流亡者,也是城市精神的摧毁者与塑造者。他们所摧毁的,是部分人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他们所塑造的,是这座城市流动甚至漂泊的灵魂。这种双重身份,正如廖伟棠的诗歌:“一首诗挡不住坦克,但一首诗可以创造的东西,肯定比一辆坦克摧毁的东西要多得多。”
要认识一座城市,仅从政策、经济等宏大元素去认识,无疑徒劳无获。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如此描绘马可波罗给忽必烈形容的梦想城市:“无论我怎么描述采拉这个有许多巍峨碉堡的城,都是徒劳无功的。我可以告诉你,像楼梯一样升高的街道有多少级,拱廊的弯度多大,屋顶上铺着怎样的锌片;可是我已经知道,那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城市是无法依靠如广场、政府大楼、地标建筑等宏伟建筑物来获得认识,因为城市的灵魂永远都在静静地流淌,它是看不见的。真正的城市精神,无法如商业物品般拉出来叫卖,而如蹲在地下室不断被传抄的神秘手抄本。近几年,廖伟棠如凯鲁亚克式“达摩流浪者”般,行走在香港,成为了一个关注社会、投入“行动”的“异乡人”。廖伟棠的《波希米亚香港》一书,展现的就是作为手抄本的香港。
香港,作为世人眼中的“金融中心”, 它的面目已被消费文化所遮盖,一般人只认为香港是旅游购物的地方。廖伟棠将自己在香港生活的见闻感悟形成文字,结集成书,取名“波希米亚香港”。很显然,廖伟棠是在将香港的另一面展现出来,告诉大家一个看不见的香港。而他所要呈现的那个“看不见的香港”,如同历史上的波西米亚民族或波西米亚艺术家一样,试图通过他的文字,让大家去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波希米亚,这个词语置放在香港前面,很显然与繁华都市的欲望横流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种与商业文化对比之下显得如此边缘化的底层精神。那些生活在香港,为自己而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种过着有想象力生活的人,都成了廖伟棠笔下的香港波西米亚人。香港在制造了商业繁华的时候,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独立思考的先锋人物,这些先锋人物影响了香港的文化元素、社会元素,甚至政治元素,乃至影响到了香港以外的地区。最近几年,香港文人北上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廖伟棠在描述作为手抄本的香港时,他认为,拜金都市、商业游乐场之外的香港,“那是一个耐心潜沉到生活的深处、着眼于城市文化诡异的细节的人才能发现的世界”。如同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都市般,石头城中必定隐藏着无数游客看不见的小纽约、小伦敦、小巴黎和小东京这类地下社会,廖伟棠将游客无法看到的“小香港”美其名曰“波希米亚香港”。廖伟棠笔下的“波希米亚香港”,试图给读者一种解码香港边缘精神的脉络,去透视一个真正的香港之另一面。它的笔端流溢出来的,是在诉说只有地道香港人和来港的冒险家门才能够感受到的火辣辣快感——她是怎样赢得她挑剔的情人的心的?她是怎样留下她的爱人们,同时让他们自由的?这就是香港“后青年”积极捍卫的理想主义理念之下的“香港价值”。这种被商业掩盖的“香港价值”,可以令严肃者微笑,可以令庙堂人幻想。想象力是一切专制的天敌,也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刺刀,这种带着微笑的幻想,如同嘻哈对抗严肃般,成为了对抗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而携带这种有力武器的香港波希米亚人,艺术家们如同野牛般,可以在大牛棚里嬉笑怒骂做逍遥游,即使面临屠杀,也比那些天天被榨得一干二净的肥壮奶牛逍遥得多;文学家们、舞蹈家们、实验话剧团可以在被推土机铲平的菜园村废墟中,占据一间早已拆毁并被涂鸦的废屋中草莽开唱,在隐忍中爆发戏谑,在戏谑中爆发愤怒,以一种决眦欲裂的姿态,对抗着香港的社会现实。
和波希米亚人一样,廖伟棠笔下的香港波希米亚人,姿态是反叛的、浪漫的,他们崇尚的是自由、解放、想象力和潜能发挥,生活总要跟大众的主流、社会的常规、中产的拘谨格格不入,对物质主义、歧视和不公投以不屑的藐视与愤怒。这些香港波希米亚人,如同本雅明的理解,“波希米亚人”涵盖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时代的关系: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时代,却是以一种玩世不恭、孤芳自赏的姿态来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们生活动荡,充满偶然,充分享有自由,但是他们需要付出与时代分离,甚至被时代抛弃的代价;他们率性、激烈、立场游移的言行里洋溢着反抗时代的气息,但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甚至寄生者,使得反抗成为抽象的“为反抗而反抗”。
当然,谈及香港,不能忘记香港的电影。但是,较之香港的电影,更值得言说的是香港电影节。廖伟棠在《在电影节重省生活》中写道:“香港电影节最令我赞赏的,是它一直坚持成为独立电影的支持者,而且,曾经相对于两岸的保守,香港成为不少话语独立电影最佳的首映地和讨论场所,也是佳话。”的确如此,如果没有香港电影节,大陆独立电影又怎能让世人知晓与传播呢?《克拉玛依》又怎么能够在纪录片史上留下沉痛而悲壮的一幕呢?而香港文学最近几年不断北上,香港文人的笔端,也是香港波希米亚精神的一种流露。在本书中,廖伟棠通过对作家黄碧云、西西、董启章,诗人蔡炎培、陈灭,导演李照兴,摄影家谢至德,等等人物的交往或者著作评述,来展现香港波希米亚精神在笔端纸上的现实照应。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廖伟棠收录了自己关于香港的诗歌,用诗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对香港的解读。或许,廖伟棠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自己也定格在香港的波希米亚版图之上。
读完《波希米亚香港》之后,是否能够去想象一下自己所处的大陆?既然香港拥有一个波希米亚香港港,所谓“地火不息”,大陆是否也存在着一个波希米亚大陆?或者将范围缩小至我所生活的南昌,这座将“中正大桥”改为“八一大桥”,将“国立中正大学”改为“江西师范大学”的英雄城,是否也存在着一座“波希米亚南昌”,期待着细心的南昌生活者去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