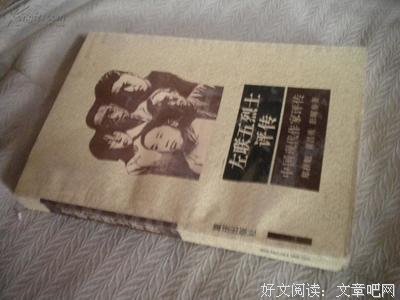
《昌耀评传》是一本由燎原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4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昌耀评传》精选点评:
●独行在路上
●这位喜欢李白的诗人,一生坎壈如杜甫。
●(僧人)最佳的自我观照,(大山的囚徒)在生命的最后有了(良宵)。那十指纤纤的素手终牵你走完了命运多舛的一生。
●要知道我用这个网名是因为读了昌耀的一首诗么。
●昌耀的诗很不错,但这本传记不如《海子评传》犀利
●黎明的河岸,有一驭夫,向着太阳,顶礼!无奈生的强音,竟落在招魂之鼓!
●可能是因为篇幅的冗长,《海子评传》中那种燃烧的激情始终没有喷发出来;可能因为内容太过庞杂、信息量太大,不见那种集中深入的剖析,没有读《高地上的奴隶和圣者》一文时的感受;可能因为作者和传主太过熟稔,因而文风趋于平淡乃至琐碎。不管怎样,这仍是一部好书,对于每个喜爱昌耀的人来说,通过这本书认识以及更好地认识昌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此书部分地方有滥情主义的伤痕,但总体对昌耀算是个告慰!
●读罢此书,始知此人。
●首创总是有意义的,资料很新,论述有情怀
《昌耀评传》读后感(一):贴地而终又如何
一个人,是不是活到了他(她)精神体验的极致,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也很残忍。
就理论而言,落地的才能称做人。人的肉体,就是贴地而终的命。贫富无非都以八九十年告一段落。本质上没什么差异。差异在意识层面。
昌耀。2001年8月,我在青海西宁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极厚的书,《昌耀的诗》,想也没想,看也没看,直接跑到邮局寄回了长沙。此后,往格尔木,在可可西里呆了一个月。那时,我不知道昌耀是谁,不知道这个人在2000年已跳楼,不知道他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湖南。在当当上买《昌耀评传》,因为作者是燎原。燎原,2001年5月吧?我在福州晓风书店(?)买了他写的《海子评传》,返长的硬座火车上,20多个小时,几乎一动不动地翻完。那种感觉是什么?不必说。
看《昌耀评传》的感觉我也不想说。对于他的诗,更无意评价。
“万物把手撒开。”这是书里引的一句诗,也不是昌耀的。我认为这一句里有瞬间的钝痛和持久的隐痛,有死地,或最后一丝侥幸,幻相。再言说不尽的一生,也有句号。书中反复宣称昌耀的“大”,因为被挤压(被社会、人心、自身连环挤压)的贴地之命(所以有过那么多可笑,可叹,可怜和缺陷),事实上,最后当得起“大”这个词,他的理由(我也这么认为)是其精神体验所抵达的一种极致,极限,且通过才华进行了表达(我往往会认为这点都不重要)。竭尽所能,在贴地的命运里,活到了自己的顶点。并非人人都具备这种纯洁的勇气。
所以,此书没有读后感,一切用词都多余。只给五星。
《昌耀评传》读后感(二):精神的标本
作者:白垩
人的一生是一种成就。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生成就自己。结出生命的果实,成色各异。昌耀用苦难、思考和歌吟,成就了自己,他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本。
他的一生正如他的一首诗——《慈航》。在诗的路上,昌耀是我的教父,导师。接引菩提。
燎原作为我的师长,朋友,以淋漓深情的笔触,评述了他的诗歌人生,精神成就的历程。
燎原——阿难陀。
生死之交和最后的托付。如同阿难完成佛涅盘后的第一次佛经的集结。《海子评传》和《昌耀评传》,是一次怀念和精神的集结。和酿蜜。
燎原和昌耀,和以高原湖泊——海子(子轻声》命名的海子一样,同是青海高原的一架高车,他们的承载,让我想起一句话——派什么人去受难。基督说,跟我来的,背上你的十字架。
燎原作为昌耀生命最后时刻的托付者。一个大胡子雄性,他习惯斜睨的眼神,有诡异的透视力,他是佛陀身边的智者阿难陀。
蜜蜂是花朵的最好阐释者。燎原是一只土蜂,一只能蜇煞一头牛的马蜂,他的蜜在精神,思想和深情的蜂巢里。
每一位品尝和采蜜者都是一场屏住呼吸的历险的采割。
http://comm.dangdang.com/member/4020319557227/reviewdetail/1569866/
《昌耀评传》读后感(三):高原:昌耀的精神故乡
每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都会有一个终身与之相伴的主题,和一个让他赋予灵魂的意象。高原之于昌耀,就如同拜占庭之于叶芝,如同麦地之于海子。的确是这样,自从1956年青年昌耀怀着青春的热血与梦想踏入高原的土地,数十年间,命运的翻云覆雨手将昌耀拍打的如雨后的小草,曾经轻狂的理想难再续,曾经挺直的腰板不再有。昌耀老了,慨叹着“孩子笑我下颏已生出几枝棘手的白刺”(《巨灵》),然而不论怎样他都不曾离开高原,这将一生赋予的多情土地。可以这样说,在生活中,高原是昌耀脚下的土地;而在诗歌中,高原就是昌耀的精神根柢。昌耀曾经说:“青海既哺育了我,也造就了我” 。这是发自内心的自白。
梁淑敏先生曾经将人类面临的问题分为了三个层次,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要解决的是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而在诗歌中,诗人与高原也有过三个层次的关系。换句话说,对待高原,诗人曾有过三种姿态,而这种姿态是随着主观境遇和处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也有论者将“高原”的形象分为作为自然的,作为生命的和作为灵魂的三个层次 。1956年,昌耀从河北荣军学校进入青海工作,即开始接触青海的高原及民俗。高原坚韧、粗犷与雄壮的外表与青藏异族的同胞都成为昌耀笔下艺术形象的源泉。结合者“开发大西北”的国家号召,在随后的数年中华,昌耀以高原为母体抒发自己的青年理想与革命热情。诗人写出了《高原散诗》、《鲁沙尔灯节速写》等组诗及《边城》等富有洛尔加谣曲风格的民谣短制 ,成为最早时期的代表作。年轻的诗人在这时期还没有来得及体味这苍茫的草原带个他真正的意义,而陶醉于与内地迥异的风貌与民俗,“没有深入了解底层劳动者们生活的艰辛苦涩” ,故而多写作优美、纯净的高原风情写生作品。高原之于诗人,仅仅是一个对象,从这个对象中获得艺术的灵感。这一阶段,诗人与高原的关系,可以看作“人”与“自然”。1957年之后,诗人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被发配到祁连山腹地劳教,劳改。从此之后,一直到1978年昌耀平反,回归到“人间”,成为大山的囚徒。经历反抗、死亡、绝望。而在这过程中,“渐渐”不单单成为“高原”,而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自称左派而为认定“右派”,年轻不更世是单纯的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渐湮灭。面对大山,昌耀渐渐不懂得说话。“当原先他所热衷的那些诗歌题旨路径,被他自己逐渐关闭,很难有什么再能对他形成内心上的召唤,而他又必须在写作中寻求呼唤时,其精神机制才会本能性地朝向大自然,集合出这唯一的心灵方向” 。燎原的这一段话,完整的演绎了在这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昌耀将“高原”作为心灵依托的缘由。任何人,没有心灵的支撑,都形同槁木。正是高原,维持着昌耀“人”的精神。信仰的空洞与关闭,让诗人觉出来自内心的焦渴,“我渴,给我入水的丝竹之颤动”(《给我如水的丝竹》),而目光本能性的转移到他所唯一能够依托的力量之源——高原。这时候的“高原”早已不像年轻时期那般轻松与壮美,而更多的承担了一种支撑心灵的力量。在同命运的搏斗中,高原成为昌耀的“利剑”,挥舞着支撑与前进。
我喜欢望山。望着山的顶巅,
我为说不确切的缘由而长久激动。
而无所措。
——《断章》
我不走了。
这里,有无垠的处女地。
——《荒甸》
这块土地
被造化所雕刻……
我们被这土地所雕刻。
是背部古老森林的义子。
——《家族》
这一时期,“高原”几乎成为昌耀唯一的讴歌对象,成为塑造“自我精神”的神笔,成为反抗力量的唯一源泉。这一时期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达为“人”与“人”之间。因为,“高原”作为一个意志念力,成为昌耀支撑精神获得力量的源泉,而与之对抗的命运苦厄,又未尝不是“人祸”而非“天灾”呢。
经过“失声”的十年动乱,昌耀于1978年平反成为公民。而十余年的压抑,一旦除却了枷锁,创作进去了“井喷期”。严格的讲,从复出之后开始,昌耀的诗歌文本本身就呈现这浓郁的“高原”色彩,譬如他的“流放四部曲”,从主体骨架上支撑起这些诗歌的,就是“高原的山川风物”与“独特历史”物象。而《所思:在西部高原》是诗人诗歌创作的一个临界点,这标志着诗人脱离拒绝回忆与遭遇而向未来看去。从此之后,昌耀开始塑造他“大时空的高原”形体。在这一时期,高原成为一个近乎宗教的象征。那是一个包含了时间与空间,包含了人类的起始与灭亡的永恒存在,而对于大时空的表述与认知,成为昌耀体认“大生命力”的核心。此时,昌耀笔下的“西部写作”(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已经是一种圣化的书写,由此为通道进入哲学的层面,诗人去弥合生与死的距离。这一时期,诗人与高原的关系,就如同梁先生所说“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而“自己内心”最大的困惑,即是生与死,有限与无限。而诗人这一时期大时空的塑造,近乎于将高原视作宗教,从中寻找人生的谜底。
天才诗人海子在他的论文《一份诗学提纲》中,将艺术家的创造性人格分为三类:母性诗的、王子式的和父性式的。在他看来,木星代表着大地,具有幽暗、敏感。深刻、复杂,有着死亡的天然趋向。譬如卡夫卡、尼采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性则代表着“原始生命力与大地合二为一的主体力量” ,彰显着人类生命的“上升趋向” 。父性人格的建立,是对于沉溺性人格的挣脱,对于大地束缚力的反驳,直观地讲,就是崛起于大地而指向天空。如果昌耀能够当得上“父性人格”的艺术家,我想,其重要原因也是高原给了他以雄性的强劲力量,给了他以史诗般的雄伟人格。由此,昌耀将自己一生的追寻与支撑交付于“高原”,并完成了互相塑造的过程。可以说,是“高原”给予了昌耀以诗人的桂冠,也是昌耀,使高原成为 “精神的家园”。
在1987年写就的《艰难之思》一文中,记写道:
我是如此偏执地信仰:作家之存在、之造就,其秘诀惟在生活磨练或命运之困扰。
果真如此。
1昌耀,《答记者张晓颖问》,《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0页。
2梁漱溟口述:《后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页。
3张文刚:《高原:昌耀诗魂》,《求索》,2002年第3期,第125页。
4昌耀早期受到洛尔加诗歌的影响,这是其创作的一条思路。
5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6 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7燎原:《海子评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同上。
9昌耀,《艰难之思》,《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昌耀评传》读后感(四):远人的江湖早就无家可归
远人的江湖早就无家可归
——写给昌耀,或者燎原,和我自己
一。
无奈笔下生涩。有位名人曾经说过:写不出,就如拉不出。那不是一般的难受。
多少文章来写昌耀了,老来福的他晚年实在是不缺乏人追捧,我也不必再来添砖加瓦为人垒高墙了。然而昌耀对于我,却真又影响甚大。不算这本《昌耀评传》。燎原心思是细腻的,然而文笔是乏味的。实话实说,所以说阅读堪称“遭罪”。文笔乏善可陈乏善可陈,然而内容却不可多得。资料详实的不一般,果然是以死相托的人物啊。
“远人的江湖早就无家可归”,出自昌耀《江湖远人》。我想昌耀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尝过什么叫顺境。早年(十四岁吧)离家远走跟着大人们干革命,跨国鸭绿江当了志愿军,不久右派下青海,转战非人农场。改革春风吹满地,右派帽子丢出门。昌耀的好日子算是来了,这也是仅有的“较好”的日子了。有过几分荣誉,有过几段恋情。做过土伯特人的赘婿,走过回回女子的床褥,见识过江南女子的薄情,写下一十一朵玫瑰花。
我总觉的生活太幸福,即成就不了诗人。读着昌耀的诗就会不断地意淫,自己也在农场过着欢天喜地每天劳动二十五个小时的日子,然而勇气这个东西啊,是真难找。别说去农场看看,就连去支教一番,也犹犹豫豫不得所终。
我羡慕昌耀。
我羡慕昌耀,能被命运裹挟着走入不复之地。这能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怎么又不是整个人类的喜剧呢?我宁愿他损毁整个的肉体和百年的生活,换取一册薄薄的诗集。更何况《昌耀诗文总集》页码逾千。让我来遭受着苦难吧,我必当死以报。
尼采狗日的曾经说过:我爱这样的人:他创造了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并因此而毁灭。我不熟悉尼采呀,但是他一个手指点中了我心里已经不隐秘的悲剧情节。如果可能,我要用命换创造。然而问题在于,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前些天看从豆豆处借的的翁彪君囤积居奇冯志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一封信里里尔克就扇了我一巴掌:“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诶呀,老实说我回答不出我是不是必须写,这让人感到惶恐。先不说我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诗人,先说我有没有资格成为。如果不是必须呢?我就是一个爱慕虚荣影影灼灼闪烁其词遮遮掩掩的以诗标榜的人。这可真是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事实啊,我是不是这样呢?
我是怎样目前我还想不明白。然而昌耀却不是,你看得明白他的诗是命运修筑,在巨石上凿刻一刀一刀带血而出的生命。仿佛每一刻生活中罪孽的种子都会在他的笔下成为改换了面目的遒劲大树。早年的昌耀(就说是六几年吧),下放农场,入赘藏家。生活或悲或喜然而诗歌都不曾断却,你看得出有一种生命力在这些或短或长的诗篇中。随便抓来一首当做例子:
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
更永无百倍。
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
上面是来自,可以说是在八十年代让昌耀高调复出的惊世第一弹《慈航》中的开篇。如果觉得这个已经被引用太多,我在摘一首: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忍受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不,今夜没有月光,没有花朵,也没有天鹅,
我的手指染着细雨和青草气息,
但即使是这样的雨夜也完全是属于你的吗?
是的,全部属于我。
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
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
我的须髭如同箭毛,
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啊,你自夜中与我对语的朋友
请递给我十指纤纤的你的素手。
此首名曰《良宵》。(这里我插一句,我写这篇小东西实在是自不量力的事情,尤其是干引用若干。因为已经有了燎原的前车之鉴:随便谁的文章跟昌耀的放在一起基本上可利用率已经低于垃圾的价值了。此前还有一个例证:当秦阿眠君看过卢文丽几年昌耀的文章后说里面的字不论谁的都比她自己的好,而她主要引用的就是昌耀的。所以我已经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准备。)
虽然这首《良宵》是首爱情诗,算是吧,在早期昌耀作品中不多见,然而一贯的那种生命感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从那种刚性的变成了这种“柔情蜜意”的低诉了。
下面这三句比较符合昌耀风格: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他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这是来自《踏着蚀洞斑驳的苔原》,62年产出。
在我看完昌耀评传之后,再翻来看这些诗作,感觉起了变化,从欣赏文法的奇绝和表述上的特质以外,会不自觉的想窥探昌耀当时的想法。譬如说上面那首《良宵》。我在05年第一次看到这首诗,而有欲望亲近昌耀。在当时看来,这果真是一首文辞别致的情事,尤其是一句“请递给我十指纤纤的你的素手”,甚至我在课堂朗诵过这首情诗而不觉肉麻。但是现在再看来,我就会知道,原来这诗歌是写谁,哦,原来是这个女人…是不是类似八卦和邪恶的求知欲?
也是这首诗让我从诗歌的外在面貌上觉得昌耀这个人有些特别,你目力所及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且看看“诗坛”中的人们已经从脑袋里进入了复制黏贴时代,就好像当年朦胧诗末期,也好像政治抒情诗末期一般缺乏生命力,然而在昌耀这里,他有意规避了公共的语言资源,非常聪明的把自己深处的藏回汉犬牙交错的文化与语言当做自己的资源来运用。譬如一个“土波特”让我知道了原来语言上的陌生化效果如此明显。庞德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恕我再次引用)。问题在昌耀这里变成了:我有一种生活然后创造一种语言。无疑,这是创举。因为作为“归来者”,同辈诗人要么在沉默中沉默,要么在沉默中成为教材上的诗人。昌耀却是个例外,他没成为教材上的诗人(煞有介事,提了一提),他却成为最有生命力的诗人,再次成为诗人。根基当然是他注入异质资源的语言。是不是因为这点,让他自信到甚至在任何当代所谓流派中看不到他的身影,然后就秘密的从任何人的和书本的语言中消失了。这可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笑话,评论家都去请客吃饭座谈会了,昌耀呆呆地站在这里无人问津。
我的语言特别无力,所以只能再引里尔克:艺术品都是源于无穷的寂寞,没有比批评更难望其边际的了。他说出这句话的前提是劝人“少读审美批评的文字”了。
二。
哎,羡慕归羡慕。读诗中的一种共鸣也让人激动不已。当年读《平凡的世界》,把人看的稀里哗啦,厚如字典的一本,愣是让我一周看完。昌耀的诗虽没让我稀里哗啦然而心中多的是好几份庄重和精神的神合。当我最终得知,俄罗斯之于昌耀也如她之于我时,这种秘密的冲动就好像是两个孩子在后院某处藏下宝贵的玩具一般的神秘和令人欣喜。当然,这欣喜是我的,也是我的臆想,谁知道昌耀会怎么想,更何况在去过俄国之后留下的诗歌让我沮丧,会不会果如箴言,俄罗斯本也就是“莫斯科”。
在零六年一个月份,我写过一首诗,《是夜,我独坐灯前》。那晚上,我真个独坐灯前,手中拿的是昌耀的诗集。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白色的灯光如夜色中不被打搅的月光
放肆地把我年轻的脸庞勾画出
手中昌耀的诗集我已然不再想馈赠友人
然而年轻时的诺言也如岩石般不能动摇
十四年前,昌耀端坐祁连山写下了在今天
让我心潮不静的诗篇
我打开弟弟的文具盒,用彩色的铅笔写下自己
沉默的诗
沉睡让夜晚总会安详,有如
北方广阔而寂静的草原,也在夜晚
放下了威严的拳,静谧主宰了大地和
星如密语的天盖
四十年间的情怀会因为几行歪歪扭扭的汉字得以联系
以至于若有少女前来向问:
为什么总如此忧伤的吟唱北方的山河
定有此复
可愿与我一同,在
青海沉甸甸的草场,放牧天上的羊群?
2006.1.30
看来这种一厢情愿的神交从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距离昌耀过世五年十个月。又有一个小兄弟从在无数个小兄弟之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你的敬仰,希望你不会我说咱俩有神交而晚上来找我。我会十分的不安。
这可如何说起呢,似乎昌耀的命运也暗合了我的一丝心思。昌耀生命悲苦,而流露出尴尬和寒碜也似乎已经成为习惯,在他以五十载之身躯狂热的追求着远在杭州的卢文丽,并且在信中夹着一百块大钞(公元一九九二年,其时昌耀工资三百七。),并附下说明,让女同志“买几瓶‘雪碧’消渴”的时候,我可真是可笑可悲啊,这该怎么形容呢,想来想去,我只能想到一个词“寒碜”。寒碜不是昌耀的好习惯,而也拜生活所赐。给你个数据你参考下,昌耀去世的时候存款四万三千人民币,四万留给儿女,三千善后。四万三千是昌耀从七十年代末复出到新世纪第一年去世二十多年的积蓄。对一个生活在杭州,且有借昌耀之名“上位”,再且日后事业也有所成的女士来说,可真是小菜一碟啊。因为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过上了可以闲来无事马泰游得安逸生活了,而此时的昌耀,基本上还不知手机为何物。(哦,这可真是跨时代的恋情啊!)
在了解到此背景之时,我不能不说昌耀的确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寒碜,太寒碜了。更寒碜的是,这一百大元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一个寒碜者的自尊心又一次被打击到了。
不掩饰得说,虽不至那么严重,但是他的寒碜击中了我的寒碜。于是,我动容了。
昌耀的悲苦和寒碜隐藏在他不停的失败当中,八零前,昌耀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八零后,昌耀的失败亦是不难发现的。譬如说诗集的屡次流产,婚姻生活不幸福,甚至被正处叛逆期的大儿子殴打而斯文扫地尊严无存,再譬如经济上的落魄甚至说过“”的话,情感经历上的屡次受挫让他无所依靠。应该说昌耀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他成为一个寒碜的人,也正是这样的捉襟见肘,让他成了只能睡在文联办公室的诗人昌耀,成了西宁的“大街看守”。也正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昌耀只能成为诗人昌耀而无法改变,正如在《我们无可回归》中那两句箴言的诗句:
是的,那火焰之裸舞固然异常美妙魅人。
而我们无忧归去的路。
那真是悲怆啊。昌耀让我觉得任何失败的人都可能是英雄,只要他能在失败中发现美丽。
我想,这正是对我一贯的“偏见”恢复名誉的时候了。我曾说,我常隐秘的希望失败,意见不曾努力或急于努力的事,在无可挽回的时候失败而亡。这大概是因为,在昌耀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平衡:但凡一种失败,一定会有一种成功赶来补救。这法则是永恒不变的,于每人而言,补救的成功当然各有所不同,然而成功是一定会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促成一种失败,然而发现,这失败的价值。
晚年的昌耀,内心焦虑而终日惶惶,为了躲避无聊和焦虑开始习字“我的生活并不如意。……我中日都难摆脱焦虑,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练习写大楷…..”
当人们看到,昌耀穿着自己永恒的一身夹克站在书法家画家当中写下几个大字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正是一种痛苦才催生出了他另一颗艺术种子。谁能否认呢,失败和痛苦一定会有一种宣泄,我大约会以诗为利器。
所以嘛,我说,余华来了浙江拿工资,基本上也就和“杰作”二字说拜拜了。更何况他的“杰作”又怎么能和昌耀的诗相提并论呢。
三
半个月时间,拖拖拉拉读完了《昌耀评传》;四年时间,我习惯把昌耀的诗作为厕所书;六十年的时间,昌耀习惯用诗挣扎,把自己变成一块石板,上面写着“故显考王公昌耀大人之墓”。我隐约觉得,心中有走上“不归路”的冲动,然而简单说出“为现实所累”是妥协责任的做法。每当我看到昌耀,就看到一丝希望,或是命运的巨力,或是人生的小喜大悲,再或是艺术的静花总在岩石罅隙默默钻出。每当我看到昌耀,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我的终日惶惶焦虑不安早在那么多年前,就有人尝试过了,且在这境遇中,他成为苦难的圣咏者。多想耶稣啊,难怪有人要把他与宗教扯在一起。
我曾经说过:写不出,就如拉不出。即便内容关乎昌耀,感受发之于心,一番不能避免。烂笔头一阵翻腾,匆忙作完一文。不知是写给昌耀,还是写给燎原和评传,再或是写给自己。大概都有吧。于是副题题为“写给昌耀,或者燎原,和我自己”。
果真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
不悔 于望月小屋 2009.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