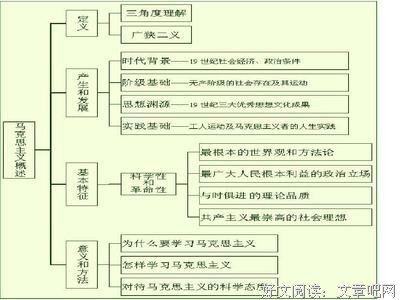
《哲学纲要》是一本由李泽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哲学纲要》精选点评:
●实力炒冷饭
●李泽厚中西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人类在具体时代环境下,为了维持人类群体的存在而制定的共同行为方式或者标准。道德是人类做出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充分体现了人的自觉和理性。| 李泽厚认为认得自觉性和主动性是运用自由意志做出正确决定的行为。| 道德产生在具体时代环境下,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人认识世界、做人处事独特的思维方式——实用理性:既强调实用,又强调理性,主张以理节情,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实用理性是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又清醒冷静的思维态度。| 实用理性和西方的纯粹理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实用理性既强调理性,又生活,而且生活大于理性,理性是为生活服务的。|不要去超越人世之外的地方去寻求人生的真理,因为人生的真相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柴米油盐之中,在七情六欲中。
●好!
●之所以还是可以买还是可以读,是因为其实书读百遍,理解都是可以常变得。
●书中所言“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之异同以及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背叛失败的分析实在精彩。
●老先生有点意思
●原来是精选集。之前只看过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比较本书中的中国传统的述说,发现精选的文章有点压缩过度,上下文不连贯,概念也解释不清,没有原文的精彩。
●没弄懂这本书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情本体”。之前没读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所以读下来还是很有收获的。
●恨晚相见,释疑解惑,醍醐灌顶。李泽厚将哲学讲述的很透彻,对中西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之前我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思考,也有所得,但都不系统且片面。特别是《伦理学纲要》和《存在论纲要》,给了我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读完就觉得自己整个的心灵都充盈起来。
《哲学纲要》读后感(一):半本好书
各种李泽厚的不同地方的文章的串烧,所以各种重复和车轱辘话,严重觉得只看前两篇,最后一篇完全可以不用看了,而且最后一篇文字多有文学性而缺乏哲学性,拉低了整本书的评分。
我个人对国学没有任何兴趣,微言大义的含义就是可以瞎鸡儿阐释,一点都不符合我理科生的思维。将自己的哲学非要从中国古代文本中寻找证据的意图是必然会得到满足的,因为那些微言大义的文字如何解释都能帮你圆回来,但是也是必然没啥意义的。
我思才是根本,寻找其他证据只能削弱自己思想的正当性。
除此之外我觉得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不够深刻,明明就应该是实践本体论嘛,历史不过是人类实践随时间的积分而已,如果按历史本体论,就有厚古薄今的嫌疑,而实践本体论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一视同仁,实践本体论才是正解。主观客观的合题,实践作为世界的本质,一点毛病都没有。心物一体,主客一元,世界分层,以人为本。
在我的行道哲学中我对此有较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签名中的博客网站。
说回到书,只看前两篇可以马马虎虎算个五星,但是编排和第三篇拉低了评分,合一起没打三星都算给面子了。
但是,如果你只看前两篇的话,还是建议阅读的。
《哲学纲要》读后感(二):关于图书本身
三月份买的,今天翻出来再看,还是恼火。
内容不说,喜欢李泽厚的人自然明了;说的是书本身。
版权页上,组稿及责任编辑叫王炜烨,李先生在序言中还特地感谢了此人,我觉得李先生看走了眼。理由:
一、除新增一篇关于“度”的答问外,此书篇目基本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无甚差别,买了书的人难免会有些失望。李先生说此书是自己“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的纪念,但我怀疑这是编辑炒作的产物,因为此书出版前,《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收录了李先生的《美学四讲》中的一篇文章,对出版者而言,实在是可以趁机炒作一番的,所以难得一见的是在版权页上会特意注明组稿人。我对炒作并无意见,市场嘛。但是……
二、炒作也该厚道些,而这本书真是不厚道:定价59元,395页,够贵了吧(对比《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价38元,390页)?喜欢李泽厚,贵就贵,买了吧。可气的是,过些时候,又出了精装版,定价69,出版社究竟什么意思?好吧,这也算了,你定价高,书也做得精致些啊,用纸一般不说,错字错刊还不少,最严重的是第205页重刊了一段,倒数第7行至倒数第2行:“因为与以住任何时代不同……作为哲学第一命题的确当性”,“确当性”后接着是重复这一段。简直是触目惊心。
组稿编辑兼责任编辑王炜烨先生想钱想疯了吧?把读者当取款机了吧?好意思吗?我要是他,我就自杀。
不建议购买。
《哲学纲要》读后感(三):潭州故人知未知
李泽厚先生是当代中国知名哲人中少有的有自己一套话语体系,而不是忙着复述西方大哲语录的哲学家,八十年代同样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哲人们,比如甘刘,亦或者其他一群人,不论在小圈子里影响力有多大,给当代中国建立怎样的路标,都很难说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根本摆脱不了西方哲人的幽灵晃荡,或许他们胸中藏着十万甲兵,但给人的感觉是欲语还休,却就是说不出来。但李泽厚就是能说出来,云淡风轻,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就这样自然地带出来。
读多了他的作品,总会让人觉得他的思想翻来覆去永远是那一套,但细细梳理却能发现其实他一直有所增益,只是变更的幅度不大,却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看清时代所关注的命题,并对此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一如他对自己的看法,接近云淡风轻的康有为,而不是一惊一乍的梁启超,后者转变自己观念之快,在刻薄的人眼里,就像人生赢家换女朋友,没事换着玩。
丁耘认为他是当代中国唯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其实不是谬赞,只是他无意像德国哲人一样厚厚三大卷还只是称之为导论,他更喜欢给人指出某些有意思的视角,让人惊讶地感叹:原来对世界还可以这样看。这些视角仔细琢磨常会让人感觉其实自己早有这样的感觉,但就是说不出来,直到被他点醒才恍然大悟。更好玩的是,他从来都是点到为止,剩下技术性的工作便交给其他人来做。
八十年代的人谁也想不到居然有人可以用马克思来理解康德,用康德理解马克思,互相出入却水乳交融,或许并没有多少人觉得他对康德的理解在中国数一数二,但凡是接受过他思想恩泽的后学末进,都要感激他对中国哲学指的新方向。“但开风气不为师”,此之谓也。他将主体性轻轻往前一推,使人看到了人的存在,而这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却早已被忘却。
迈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李泽厚地位不再如此显著,但依然非常重要。他的告别革命不仅破除了某些积旧范式,更重要的是他是尝试以经验experience说话。自宋明理学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坚持唯理主义传统,相信理性的演绎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的一切。他的吃饭哲学并不被许多人重视,因此少有人注意他一直试图换一种唯理主义之外的视角看问题,只是积习已久,他的思想里有浓厚的康德与马克思的痕迹,导致迟迟摆脱不了理性主义的束缚,比如强烈的大一统情结。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其实应该是,为什么一个精研两大理性主义宗师的人,却有经验主义的某种气质和直观诉求。
这在跨进新世纪的一系列谈论政治哲学的著作里,越发明显,虽然美国保守主义语境里异乡人知识分子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却越来越凸显契合盎格鲁-撒克逊政法一系的气质和面貌。或许是保守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始终有某种精神上的共鸣,哪怕起初是不同系谱的保守主义者。汪晖在形容鲁迅的时候,重新发明了历史中间物的概念,以此形容李泽厚其实也很妥当,他的实用理性的概念,便是在力图调和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就好像他的思想渊源之一康德。
这一身浓厚的康德气质,不尴不尬,决定了为什么他的美学观念依然受到许多人的认同推崇,他最看重的政治哲学却始终被人忽略,这里不是想说中国的思想界分化到彼此无法交流,而是由于近代以前中国的思想底色恰好是康德式的,用康德的语言完全可以通译朱熹。朱熹对中国政治束手无策,康德其实也不会有多少成效。除非引入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否则根本无以为继,甚至洛克这样理性色彩浓厚的人都不行,必须追索到苏格兰启蒙学派,接受柏克与休谟。但问题是,经验主义人力根本无法引入,如果能够引入也就称不上经验主义了,唯有天命可恃。
这话说来太过心酸,不妨谈点不那么沉重的话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倒是不那么重视的美学领域,情本体的概念却有开天辟地的重要性,这一信手拈来的概念,用禅宗的语言形容,便是接下了孔子的衣钵,真正开山立派,成佛作祖了。我一向不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哲学,但高考前有幸读过他的《哲学纲要》,却真的感觉,或许,真的轮到中国哲学登场了?
华中吃饭大学 陈毓秀 陈升和罗大佑脑残粉
《哲学纲要》读后感(四):何为良好生活 ——读李泽厚《哲学纲要》
在李泽厚的《哲学纲要》中他分别从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和存在论纲要三个方面谈起,在总序中他说到“三书均系旧货,并无新作,为以更醒目之书名,重新组装出版而已”,旨在“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留作纪念是实”。在《伦理学纲要》中李泽厚继承中国情本体传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视角下,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将道德和伦理作内外二分,道德被分为宗教性和社会性,人性被分为能力、情感和观念,并且提出“共同人性”、“新一轮‘儒法互用’”等来讨论伦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而在《认识论纲要》中则主要表达了对于认识论中某些问题的看法,首先是中国实用理性作为一种“生存的智慧”有忽视逻辑和思辨的缺失因而需要自我改善。其次是“度”作为第一范畴在认识论需重视“数”的补充,阴阳、中庸和反馈系统的思维方式需强调抽象思辨之优长以脱出经验制限。而“秩序感”作为“以美启真”和“自由直观”更值得深入探究。在《存在论纲要》中李泽厚提出中国本无存在论,即本体论,主要是将著作中有关“人活着”及某些宗教—美学论议摘取汇编,与前二《纲要》合成三位一体,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顺理成章地开出一条普世性的“后哲学”之路。
相比于《认识论纲要》和《存在论纲要》,《伦理学纲要》离生活更近也更具实用价值,特别是在谈论何为良好生活这一话题时,伦理学似乎更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社会风气纷繁复杂的现况下阅读《伦理学纲要》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或许通过梳理李泽厚对于伦理学的论述能够为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在论述伦理学时所运用的方法论原则是对于中西哲学的转化性创造,即用“孔老夫子来消化kant、Marx和Heidegger,并希望这个方向对人类未来有所献益。”
在李泽厚看来伦理学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即以“公正”、“权利”为主题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和以“善”为主题的宗教哲学—伦理学。近代哲学从kant开始,伦理道德被认为是人之所所以为人(人的本体)之所在。它高于认识论所对应和处理的现象界,从而这个崇高的“伦理本体”作为我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便应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李泽厚认为,作为人类伦理行为的主要形式的“自由意志”,其基本特征在于:人意识到自己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个体最终自觉牺牲一己的利益、权利、幸福以至生存和生命,以服从某种群体的要求、义务、指令或利益。因此,所谓“自由意志”首先是个体自觉意识的行动、作为和态度。其次,个体是不顾因果利害而如此行为动作的。人的这种“自由意志”本身具有崇高价值,它为人类对自己和对他人(包括对后人)培育了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普遍性的心理形式,使人获得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性生存,这就是所谓高于现象界的“伦理本体”。
在李泽厚看来,要成为一个人,必须要有内在的自觉的理性品德。概括到哲学上,就是塑造作为“伦理本体”的“人性”心理,也就是我所讲的“内在自然的人化”中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在于天理,而在于人心,此“心”是经历史(就人类说)和教育(就个体说)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积淀。李泽厚认为Kant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人的伦理行为这一理性主宰的特征,以“绝对律令”的崇高话语表达出来,并以之为超越因果现象界的先验的普遍立法原则,于是伦理话语有如神的旨意,即使无理可说也必须绝对服从。
而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康德的伦理学在于黑格尔认为康德的伦理学是空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因为康德描述谈论的实际上伦理行为的心理形式(理主宰欲)的特征,康德把这一特征当作伦理行为普遍性的“立法原则”,落实到具体规范上,如举出不说谎、勿自杀等等便突出地显示由于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情境而难以成立。任何个体都处在一定的家庭、氏族、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具体人群关系,这些具体人群被各个制约在特定时空条件,从地理环境、生产水平、经济状况到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他们所具体实现的伦理关系和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常常各有特征,并不一致,有时还尖锐矛盾和冲突。
由此,李泽厚从康德的绝对主义伦理主义引向相对主义伦理学,所谓相对主义伦理学认为伦理从属于历史,只有历史主义,不可能有独立的伦理学主义,不存在康德所谓的超经验、超时空条件,防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验的“绝对律令”。所有道德都与特定的因果、利害相关联,都只能有条件地服从,并无绝对的神圣性,时空条件的变迁,使道德义务也变迁。
而李泽厚认为伦理学特别是伦理绝对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超越一切相对事物的绝对存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承认并重视它的意义,但是认为它不是来自于上帝,也不是来自天理、良知或先验理性,它仍然来自“人”,即作为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或无限延长的人类总体,即“大写的人”。这“大写的人”的生存延续便是康德所宣讲的“应当”父兄的“绝对律令”或“先验原则”的根源,因为它代表的是人类总体的存在和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绝对原则(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是理性的,与个体的经验和情感可以无关,所以也如康德所尖锐指出的“绝对律令”在前,道德感情在后。这从具体经验的道德情感上揭示出了上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特征,即人应当以强大的自觉理性而不是任何经验型的感情,包括爱的感情来战胜个体的所有物欲和私利,包括战胜动物性的巨大生存本能。“自由意志”是理性原则,而不是爱的感情。
李泽厚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绝对主义所审验的这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绝对律令”有其合理内核,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对传统进行转化性创造的重要资源。首先,任何时空条件的人群作为人类总体生存延续的一个部分,就其一般而言(虽有特殊或例外),大体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要求和规范。第二,在各种即使不同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中,都同样是要求个体自觉用理性来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感性行为,直至牺牲自己的感性存在(生命)。第三,其结果却是通过各种相对伦理,历史地积淀出人类这一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即“自由意志”,它是“内在自然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关键,这就是成就。第四,这个心理形式被称为“伦理本体”或“自由意志”,是以人类总体(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存延续为根本背景、依据和条件,也在根本上服务于这个“总体”,从而它的“普遍必然”如同认识论的逻辑形式和自由直观的“普遍必然”一样,是以人类总体为限度,它实际是由“经验”上升而来的所谓“先验”,它作为似乎超越时空条件的“宗教性道德”(先验原则)的“绝对伦理”,是以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性道德的相对伦理为其真实的产生基地。这也就是“绝对伦理”和“相对伦理”的辩证法。
在李泽厚看来,相对主义伦理学和绝对主义伦理学并非截然分裂,而是相互转化,相对主义伦理学以其历史的具体经验性的社会性道德,来不断构造、组建和积淀作为绝对伦理主义寓所的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或伦理本体。“绝对”通过“相对”来构建,即“经验变‘先验’(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康德认为“自由意志”和“绝对律令”有关,他指出必须使你的行为具有普遍性才是道德,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先验的,但这种先验性源于维护人类总体(不是任何特定时空中的群体)的生存和延续。因此实践理性高于一切,它所代表的是人类总体的生存,它就是“天”、“神”、“上帝”。在这种宗教性道德面前,任何个体都无限渺小,从而才会产生那无比敬重的道德感情。但历史行程总是具体的,因此这种绝对律令只是某种形式性的建构,它的具体内容常常来之于具遗体的时代、社会、民族、集团、阶级等等背景、环境而与特定群体的经验、利益、幸福相互关联,从而具有极大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由此李泽厚引出了两种道德即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二者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在中西比较视野中,西方文化传统更多聚焦于宗教性道德,而中国文化语境中则聚焦于社会性道德,李泽厚认为这是由于前者受宗教影响更深,而后者则是情本体的缘故。
在《伦理学纲要》中最能体现李泽厚的创造性转化是将康德绝对律令与儒学中的“仁”相联系。在李泽厚看来,康德的绝对律令的来源是超乎经验的“先验理性”,其中不容许存留任何经验性的情感。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讲“绝对律令”的依据,是经验性的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因之,这个理性原则和“绝对律令”由于不脱离感性存在的人类,便可以渗入经验和感情。虽然它本身仍然是理性的,却可以与人的经验、情感相联系相交融,这就是李泽厚一再解说的儒学的“仁”。康德的伦理学有极高的神圣性,却很难有具体的操作性,但将中国儒学的“仁”灌注于伦理的理性本体,就可为操作性奠定基础,这即是将天理落实到人情,将理性情感化。
最后李泽厚总结到人类历史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儒学相融会而成的“自然人化”理论,它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第一,它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视作人类伦理本体的建造,并具体化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这“心理”并非是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仍是哲学假定。第二,它将中国儒学的“仁”的情感性注入这一伦理本体,使得“先验”理性具有经验性的操作可能成为“实用理性”。第三,为区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