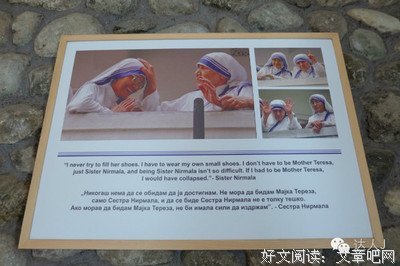
《杜鲁与妮尔》是一本由[美]格雷格·内里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鲁与妮尔》精选点评:
●格雷格·内里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角度讲述了两位作家儿时的小镇生活,痛苦中有欢笑,迷茫中有期望,孤独中有陪伴,迷人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
●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感觉有些平淡。不过很能理解故事中的孩子们对故事的追寻与喜爱,大概每个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
●那时,知更鸟还在歌唱,菊花还在咆哮。
●儿童的世界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纵然杜鲁缺少了父母的爱,但是他身边却多了一群爱他的人,包括对其影响至深的妮尔。两个孩子,性格互补,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最珍贵的一笔。这部小说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对这一笔进行了细致的还原!同时,吸引人的是,作者以全知视觉描写了一对两小无猜的孩童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交替、融合,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品尝着这一切带来的快乐。
●特别喜欢A.C.在给妮尔的字典上写的话:“文字的力量可以引起战争或带来和平,明智地运用你的文字。”带着两位大师自传色彩的童年侦探故事,不算完美,也不妨一看。
●那年,他们遇见彼此。于是,生命有了交集,他们成为对方最美的意外!
《杜鲁与妮尔》读后感(一):梦想起飞,童年坠落
《杜鲁与妮尔》这本儿童文学作品以史实为基础,讲述了美国两大文学巨匠杜鲁门·卡波特和妮尔·哈珀·李之间动人的童年故事,具有强烈的传记色彩。
几天前,我以“知更鸟飞起的地方”为主题在读书会上和朋友们分享了这本书,也是暗喻了两位作家的文学诞生地——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小镇门罗维尔,这里是哈珀·李的家乡。
杜鲁门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首府新奥尔良,儿时父母离婚,被寄养在门罗维尔的亲戚家,长相白净、穿着考究的纤瘦小子杜鲁门,很快和高个儿、短发、穿着脏兮兮的背带裤的假小子妮尔成为了挚交好友:
“他俩是绝配,因为两人都不太合群——他太娘娘腔,不适合和男孩子一起疯,而她是假小子,也不适合和女孩子一起玩。他俩做伴,倒也正好。”(P142)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分享图书,更因为都喜欢看《福尔摩斯》,便一起组团玩破案游戏,直到一个真实的盗窃案发生,让他们一展才华的时刻来了!
杜鲁聪明绝顶,机智过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对于一个内心深藏着自卑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却十分自信。在这个小小的破案故事里,杜鲁是绝对的领导者,不断发现新的线索,引导破案的走向,而妮尔则一直在她的身边担任助手,并提醒他可能出现的危险。
他们的勇敢和脆弱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却刚好可以互补,妮尔虽然害怕那些恶霸,但为了救杜鲁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当妮尔想放弃破案的时候,杜鲁则认真地说:“作为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从来不放弃破案。既然这次你扮华生,你当然也不能放弃”,并积极地鼓励妮尔写作。
不同于大量的研究资料和传记,小说着重于他们的童年友谊,以这场破案为主体,生动地塑造了两位主人公的童年形象。故事之外,这段真实的经历不断成为两人此后的创作源泉:妮尔的原型出现在了杜鲁门·卡波特23岁的代表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而杜鲁的原型则出现在了妮尔·哈珀·李的传世名作《杀死一只知更鸟》中。
然而,当这两只都经历了童年伤痕的鸟儿在文坛展翅高飞之时,危险依然伴随着他们,只是他们再也无法轻易化解。1959年,在沉迷声名、灵感下降中痛苦不堪的杜鲁门·卡波特,转身投入《冷血》的写作,好朋友的大力辅助本是如虎添翼,但1961年哈珀·李凭《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举拿下普利策奖对他的打击却是雪上加霜,更酝酿了几年以后的友情裂痕。1966年《冷血》出版,在作者序言中,妮尔的贡献被轻描淡写成了“秘书工作”。
此后,妮尔一生再未写作,回到他们文学梦想起飞的地方门罗维尔过起隐居生活,拒绝任何采访。而杜鲁门,即便是《冷血》也未能让他摘得普利策的桂冠,对案件过于投入又让他一直难以忘怀,在继续沉沦中于1984年死于用药过度。
从童年情谊,到声名鹊起,至半生唏嘘。成人世界里再没有那么一座树屋,为懵懂的他们遮蔽刺眼的阳光和社会的浮华动荡。蓦然回首,是两个孩童,一面矮墙,互相好奇地问候,是妮尔的父亲A.C.在给她的字典上写下:"文字的力量可以引起战争或带来和平,明智地运用你的文字。"
《杜鲁与妮尔》是一部写给孩子的儿童小说,是引领我们认识杜鲁门·卡波特与妮尔·哈珀·李的领路人,也是一个让人羡慕怀恋的童年故事,这不仅在每一个读者的眼中,也在杜鲁和妮尔的心里。
《杜鲁与妮尔》读后感(二):黄金时代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孤独的童年,所以我们才需要儿童文学。——题记。
我的童年似乎也是孤独的,来到乡村奶奶身边的我,总是无法接触到别的小朋友,只能远远看着她们跳绳、玩耍,或者回家看手边两本读物《中篇小说选刊》、《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到这本《杜鲁与妮尔》中杜鲁的生活,不禁失笑,原来有这样暗合的童年,原来不只有我一个拥有孤独的童年,但是没能成为大作家的原因,难道是因为我没能碰上我的妮尔吗?
书中的杜鲁与妮尔是一对共同生活在门罗维尔的童年好友,长大后则都成为美国著名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与妮尔·哈珀·李,前者以《蒂凡尼的早餐》扬名,而后者则铸就了普利策奖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他们的友情一直延续到两个人成年,而妮尔更是终身生活在门罗维尔。共同成长的岁月与门罗维尔成为了他们一生的灵感来源,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格雷格·内里则敏锐地撷取了这一段岁月,完成了这部可爱的儿童文学作品《杜鲁与妮尔》,并创造了两个可爱的人物形象——内向腼腆的男孩杜鲁与假小子一般的妮尔,他们的与众不同无法与周围的环境相容,却让彼此成为了最好的玩伴。书中充满了童年的快乐与趣味,以及友谊与亲情的陪伴,杜鲁与妮尔一起扮演福尔摩斯与华生侦破案件,一起在树屋里读书,一起看惊险的斗蛇,一起举办令人难以忘怀的晚会,在那略显无聊的门罗维尔,他们自己创造了无尽的乐趣,虽然孤独,他们却一起度过了有意义的童年,并永远铭记。而那烟火般绚烂的晚会后即将起飞的“飞机”,更是对于两人之间友谊与未来的期许。
但是书中也并未回避社会写实的一面,杜鲁与妮尔的童年伴随着大萧条、南北战争后对于黑人的歧视、3K党横行以及人们不可避免的偏见,这些现在看来冰冷的社会现实,依然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加之成人世界的无奈、父母亲的缺席,为两个人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们在彼此陪伴中,给彼此带来了力量与勇气,应该说两个个性契合的朋友,互相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在杜鲁怯懦的时候,妮尔鼓舞他勇敢,当杜鲁痛苦的时候,妮尔努力逗他开心,当两个人写作故事的时候,互相鼓励一起创作。或许就是这样的写实,让我们感觉更加触碰到真实的世界,也更感觉到这份友谊是多么可贵。
作家完全从儿童的视角去写这部小说,每个孩子都是主角,他们带领我们回到了童年生活,那是恣意想象的日子,也是将很小的事情看得很重大的日子,是在身边充满可怕巨人的日子,但那也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是可以用想象力战胜一切的日子,只有过去之后,才会明白曾经度过的是多么闪耀的黄金时代,而童年就是这样的黄金时代,纵然童年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无法获得的父母之爱,没有朋友的孤独,却依然造就了一生中最初的美梦,成为一生的力量之源。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关于阅读这件小事儿
《杜鲁与妮尔》读后感(三):遇见彼此,是他们童年的最美意外
《杜鲁与妮尔》文/文小妖
他俩是绝配,因为两人都不太合群——他太娘娘腔,不适合和男孩子一起疯,而她是个假小子,也不适合和女孩子一起玩。他俩做伴,倒是正好。一对在许多人眼里属于异端的孩子,性格成为互补,在彼此的陪伴下,组成一对有趣奇妙的侦探组合,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童年时光,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最珍贵的一笔。这两个孩子,一个是以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而享誉全球的美国女作家妮尔·哈珀·李;而另一个太“娘娘腔”的男孩,则是以中篇小说《蒂凡尼的早餐》而成名的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
两位文学大师的童年究竟是怎样的?两人儿时相伴的时光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这无疑深深地吸引着一众喜欢他们的读者。然而,关于两人童年时的故事,大都是碎不成章的片段。是以,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格雷格·内里的长篇小说《杜鲁与妮尔》以极富童趣,真挚动人的故事情节,贴切细致地还原了两位文学大师孩童时的珍贵友谊。
小说中,格雷格·内里以全知视觉描写了一对两小无猜的孩童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交替、融合中,不断在枯燥的生活里发掘乐趣的过程。其间,内里对儿童心理、语言以及动作的描写,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盎然有趣的叙述中带着一丝悬疑色彩,很容易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将两个小主人公杜鲁和妮尔塑造得生动,有个性,并将他们内心强烈的独立意识、冒险精神和创造欲望刻画得淋漓尽致。
《杜鲁与妮尔》所展现出来的是一段美妙的童年时光,也是一种真挚的孩童情谊,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抛开种种偏见而往好的方向努力发展的状态。小说中,以杜鲁和妮尔为侦破学校盗窃案而四处“破案”为主线,格雷格·内里从中加入了许多生动的场面。诚如找线索的途中,杜鲁被小恶霸博斯狠揍一顿;杜鲁和妮尔不顾恐惧和危险,深入蛇窝,见证三K党的恶行;大小子被长得很可怕的索尼·波勒“抓住”后,杜鲁因害怕忙逃命,而妮尔则奋起迎难而上去“救”大小子;以及妮尔那帅气的律师爸爸A.C.的每一次出现,带着睿智、机警和一身正气等场面的写实描写,无疑丰盈了整条故事主线,丰富地展示了儿童宽广的情感世界。
与此同时,小说通过杜鲁和妮尔对“破案”的热忱也寄寓着他们对未来憧憬的动人理想,使他们与其他同龄人、成人的世界建立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两个孩子不断地克服弱点,其能动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锻炼。
格雷格·内里笔下的杜鲁和妮尔的冒险经历,很容易把读者带回到自己的儿童时代。他的笔触一直跟着杜鲁和妮尔的思想和行动走,将他们的外部行动和内心思想把握得恰到好处,生动展现了童真的本质和传递出友情的美好,很能打动人心。
在我看来,格雷格·内里的《杜鲁与妮尔》不仅是向两位伟大的文学大师致敬,更是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某些无形隔阂,他了却了两位作家的一份心愿,用文学完成了这段无以复制的童年时光应有的神圣、纯真而美好的使命。
“我会想你的,杜鲁·史崔克。”“我会更想你的,妮尔·哈珀!”起风了,两位好友坐着飞机三轮车向前方冲去……风声把他们对彼此间的想念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撒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经年后,也许已物是人非,但童年的这份情谊已定格成永恒,以最美的姿态!
《杜鲁与妮尔》《杜鲁与妮尔》读后感(四):那时,知更鸟还在歌唱,菊花还在咆哮
2016年2月,妮尔·哈珀·李在亚拉巴马州门罗维尔的一家养老院安然离世,享年89岁。这位凭借《杀死一只知更鸟》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在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之后,便选择了沉默,在家乡门罗维尔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她不写作,也不接受采访,一辈子保持独身,就连前往白宫接受布什总统的荣誉奖章时,也定下了严格的条件:不回答问题,不发表演讲。从小就对《杀死一只知更鸟》痴迷不已的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芙瑞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被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拒绝的事实。在离世前一年,哈珀·李突然同意出版了五十年前的手稿《设立守望者》。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与种族隔离作斗争的芬奇律师在本书中却变成了一个参加过三K党的种族主义者。埋藏在两者背后的秘密令人们再次对离群索居多年的哈珀·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那无数的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到作家本人的解答。
巧合的是,也在2016年,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格雷格·内里出版了自己根据哈珀·李与另一位文学大师杜鲁门·卡波特之间真实的童年经历创作的小说《杜鲁与妮尔》。曾经获得过科丽塔·斯库特·金奖(以马丁·路德·金的妻子命名)的内里是哈珀·李与卡波特的忠实书迷。他在2014年观看电影《卡波特》后,对两位文学大师的成长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却发现没有一本书详细讲述过两位文学大师的童年。“事情就摆在那里,我不敢相信竟然没有人发现它们。”内里感叹道。他开始从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内里发现卡波特和哈珀·李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南方偏僻、守旧的小城里。那里也成为了他们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无论是《圣诞忆旧集》中“冲着黄昏时低垂的青色天幕燃烧、咆哮的菊花”还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那只落单的站在我们头顶高处的黑暗中,不断地翻唱着自己曲目的知更鸟”,都是令人难忘的童年记忆在文学世界中的复活。内里认为两人真实的人生经历“生动有趣,极富人性的悲哀与浪漫”,并萌发了将他们的友谊讲给孩子们听的念头
于是,这两位在数不清的传记与电影中出现的文学大师,这两位有着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的童年玩伴第一次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相聚在一本儿童小说里面。
某个夏天,在美国小城门罗维尔,争强好胜的假小子妮尔遇到了穿着考究、喜欢看书、也喜欢恶作剧的捣蛋鬼杜鲁。性格古怪的两个人和其他人都玩不到一起去,只能互相作伴,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有时会在树屋里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打发漫长的时间;有时会在妮尔父亲的打字机上将自己幻想出来的故事写出来。他们曾一起教训欺负弱小的恶霸,在对一起商店失窃案的调查中朦胧地知道了种族主义的可怕。最后,在一场盛大的告别狂欢会之后,杜鲁与妮尔约定以后要继续写作,并把自己的故事寄给对方。
不可否认,《杜鲁与妮尔》中的很多情节和人物都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似曾相识。妮尔之于斯库特、杜鲁之于迪儿、波勒·索尼之于怪人拉德利,甚至连妮尔的父亲A.C.严厉斥责三K党也很明显地带有阿蒂克斯·芬奇律师的影子。但我们与其说这是格雷格·内里在向哈珀·李致敬,倒不如说时隔六十年之后,又一位作家对那段真实存在的门罗维尔的纯真岁月产生了强烈的诉说的欲望,并最终选择以一种尽可能贴近现实的小说形态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内里将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按照自己的顺序排列,加以夸张与渲染。他朴素的写作风格准确地还原了那个略显保守的时代氛围:大萧条、种族隔离等重要事件的影子在小说中若隐若现,为整个文本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同时有节制的想象力又赋予了故事轻盈的翅膀,使之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不会完全受困于现实的锁链。通过孩童好奇的眼睛,杜鲁与妮尔用自己的逻辑自信地解释着小城里发生的一切,有时,他们能够从苍白的现实里暂时溜了出来,钻到他们自己编织的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里。而这个幻想世界在现实中也并非是毫无痕迹可循的,那搭在茂密枝丫间的树屋,那伴随着手指的敲击,发出清脆声响的打字机都是他们打开幻想世界大门的钥匙。
在整部小说中,最吸引人的无疑是两个主人公杜鲁与妮尔。形象上,内里参照了一些记录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尽可能贴近卡波特与哈珀·李的身材相貌:妮尔光着脚丫,剃着短短的男孩头,穿着一条背带裤;而杜鲁则有着尖细的嗓音,淡黄色的头发,穿着雪白的水手服。
从性格上,妮尔被塑造成了一个大大咧咧、勇敢、富有正义感的男孩子气很重的女孩,而杜鲁虽然看上去羞涩,但骨子里却很骄傲,有些怯懦,但也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尽管生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但遥远的时空并不会妨碍孩子在身边的朋友,或是自己身上找到杜鲁与妮尔的影子。与所有七八岁的孩子一样,他们对一切的未知都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些被大人们禁止的事情,无论是想尽方法调查药店盗窃案,还是监视闭门不出、神秘兮兮的波勒·索尼;他们生性善良,乐于帮助弱势者;无论是杜鲁与妮尔在埃迪森受到其他孩子欺凌时施以援手,还是妮尔带着“大小子”为了安慰被父母扔下的杜鲁,为他搭建了一座树屋。当然,他们也有着七八岁孩子的烦恼。对杜鲁来说,是不断在父亲的空头许诺中体会着希望与失望;对妮尔来说,是家庭残破与缺少朋友带来的孤独;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则是第一次经历了与好朋友分别的悲伤。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将斯库特的父亲——阿蒂克斯·芬奇律师塑造成了一个反抗种族主义的英雄形象,《杜鲁与妮尔》将全副笔墨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而这不同的选择也标志着两部虽然素材来源大体相仿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杀死一只知更鸟》常常令人称道的是哈珀·李通过儿童的纯真的眼睛来讲述一个有些残酷的故事。而她之所以要使用儿童视角,第一是为了反衬出成人世界的丑陋与荒谬,第二则是树立芬奇律师这个正义英雄的榜样。哈珀·李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告诫阅读此书的读者,尤其是成人读者:究竟该如何坚持心中的光明,又该如何正视自己孩子的眼睛讲出什么是正义。因此,《杀死一只知更鸟》看似是用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但真正的核心人物并非是孩子,而是芬奇律师。正如有人对哈珀·李的评价:“她有从孩子视角解释世界的天赋,却在成人世界中寻找英雄。”
《杜鲁与妮尔》虽然没有使用儿童的第一人称视角,但其整个故事却都是在杜鲁与妮尔的主动行为的驱使下发展。内里有意识地将重心全部放在了讲述两个孩子的成长与彼此的友谊上,对种族主义与三k党对黑人的迫害进行了极大的弱化,将其只是看作他们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除了最后的狂欢舞会上的短暂对峙之外,整部小说几乎没有正面表现这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冲突。因此,当我们看完小说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妮尔帮助杜鲁与博斯打架,是妮尔和“大小子”为了安慰杜鲁受伤的心为他搭了一座树屋,是在妮尔与杜鲁在月光下乘着玩具飞机冲向远方的背影,而非有关种族主义的描写。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妮尔的爸爸A.C.律师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功能性人物,负责解决那些超出孩子能力与认知范围的问题,而非像《杀死一只知更鸟》的芬奇律师那样身居核心人物之位。如此一来,《杜鲁与妮尔》也就没有了非常明显的道德说教。两个孩子在最后也没有对应该反抗种族主义的正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妮尔之所以跟着爸爸站出来,是因为她一贯帮助弱者的正义感,一如杜鲁挨打,杜鲁之所以跟着妮尔站出来,是因为他是狂欢舞会的主人,当然也是因为他的身前站着A.C.与妮尔。这是孩子出于本能的善意与勇气,无论谁处于弱者的地方,他们都会站出来施以援手。从这个角度来说,《杜鲁与妮尔》中展现出来的所谓正义比《杀死一只知更鸟》更为普世与天真。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是通过两个孩子携手成长的故事灌注到读者心中的。
《杜鲁与妮尔》的结尾,杜鲁被她的妈妈接去纽约生活,离开了妮尔,离开了小城门罗维尔。但这并不是一切真正的终结。现实生活帮助这部根据真实经历创作的小说又续写了几十年。此后,杜鲁仍然会在夏天的时候回到门罗维尔暂时生活,他与妮尔的生活与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交织在一起。杜鲁以“杜鲁门·卡波特”之名在24岁写出了《蒂凡尼的早餐》。而妮尔则在他的鼓励下,在23岁时搬到纽约进行写作,并在34岁时写出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该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还获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此时卡波特看着昔日的好友,如今已经跻身文坛大家行列的妮尔·哈珀·李,心情颇为复杂。1966年,卡波特凭借非虚构作品《冷血》声名鹊起,但他只是草草地感谢了哈珀·李在其创作过程中提供的诸多帮助。两人也渐行渐远。最终,杜鲁门·卡波特在1984年去世,妮尔·哈珀·李则在2016年永远地离开了她深爱的门罗维尔。
没有人能想象,假如没有童年的经历,美国文坛上是不是会缺少两位如此光辉灿烂的大作家,也没有人能猜出,这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友谊究竟对两位意味着什么?也许如哈珀·李所说是共同的痛苦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最珍贵的友谊都在《杜鲁与妮尔》得到了弥补与永久的珍藏。在那里,“知更鸟还在歌唱,菊花还在咆哮”。真希望无论重复多少次,在那个门罗维尔的夏天,假小子妮尔总能遇到有着尖细的嗓音,淡黄色的头发,穿着雪白的水手服的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