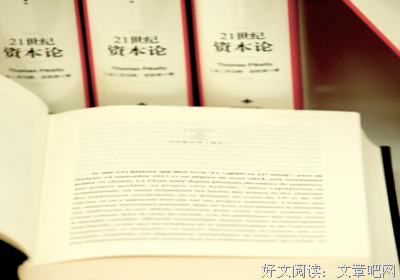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是一本由[美]罗伯特·诺奇克 著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4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诺奇克太喜欢较真,相比罗尔斯少了很多人情温暖。他所吹嘘的持有正义其实是一个伪概念,这种思想不但无利,反而有害。
●虽说读完诺奇克的论述,我仍然更加倾向于罗尔斯那套公平正义的理念。但不得不说,当下的福利国家已体现出罗尔斯理念延伸出来的种种弊端,诺奇克这种极端强调人的自由权利与最小限度国家的主张,或许也起到了矫枉的效果。
●理不清,翻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第四章,还是一团浆糊……感觉诺奇克大爷在写第四章时的心态是:绕死你丫的!
●Smart but naive.《正义论》虽略显呆板,但不失厚重,更有悲天悯人之心怀,诺奇克此书则不严肃、毫无崇高感;论证局部细密乃至枝蔓丛生,整体却散乱,与康德、罗尔斯等艰苦的体系工作比差远了。以及姚大志同志翻译插入句从来不知道调整语序,且不同部分翻译质量参差,不知道是翻译心态时紧时松还是叫学生译的。以及最喜欢赔偿原则的应该是中国拆迁队。
●诺齐克稀里糊涂的
●读完才知道,Nozick在此书驳斥Rawls的正义论同时,也回应了Rothbard等人的市场无政府主义言说,为受严格限制的最小国家做了强有力的辩护。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习惯把此书归入Libertarian一类。
●姚大志的表达能力一定有问题,看前言的时候还以为是编辑疏忽了,看到正文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么奇怪和拗口,比如“一个人可以自己强行他的权利”乍一看还以为少了个动词
●版本评价见何译本。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由于诺齐克无意构建体系而使书的内容有点乱,就像何说的,像是一棵树上长出的很多枝桠,但他不做不确定论断,倾向于存疑的风格还是给人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当然也很具迷惑性和吸引力,如果说自由至上主义有一大批拥趸,这并非没有道理的。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后感(一):没评分给的那么好
看了20几页,个人感觉的的确确没有正义论说得在理,多数论证有点像强盗一样,我说对就对,而且有点小孩子逞口舌之快之感,反正读来颇感失望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后感(二):问一个问题……
诺齐克说从自然状态到最低限度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就算是侵犯了都得到了补偿,但是当保护机构禁止独立人具有大风险的强行正义的时候,确实利用垄断权侵犯了独立人的权利,这个的补偿就是免费为独立人提供保护服务,但是。。但是如果独立人根本就不愿意加入保护机构怎么办?这样就变成了保护机构禁止其强行正义侵犯了独立人的权利,又强制把独立人纳入了保护,再次侵犯了其权利啊,想不明白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后感(三):自己朗读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有声书(mp3)
很喜欢这本书,就自己读了有声书放在MP3里时不时听一下。
不专业,喜欢听书的朋友们可勉强一听,比看书轻松一些。
音频放在我的小站里了,可下载,还在读的过程中:
http://site.douban.com/wenxiaonuan/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后感(四):一种乌托邦的框架
第十章独立成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标题为乌托邦,第十章的标题叫一种乌托邦的框架,乌托邦是一个具体的梦想,而框架仅仅是最起码的简笔画,两者是不同的,本章,不,全书就是为了证明最低限度国家就是一种人类乌托邦的框架。 关于乌托邦的问题我首先想说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进入这个理想社会的素质,因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进入这个理想社会的资格。乌托邦的想象不仅对环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还应当对其中的人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人来说,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和世界观是不同的,所以应当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乌托邦,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个理想国的最高支配者,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其最高负责人,或许有的人愿意在一堆沙子中当唯一的金子,或许有的人更愿意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平等交流,然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强加给别人,但是存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基础框架,这种框架是如此的原始,但是无论是谁的乌托邦都拥有一些共同基础,比如,这是个物质世界,精神和生命是存在的,有一些建筑无论是什么样子,还存在一些简单的制度无论这种制度是自由还是道德等等,这种基本的框架一直达到每个人的乌托邦的共同底线,再往上的话就开始不同了,而这个共同基础的框架,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在不侵犯其他人的需求的条件下最大化的社会,也许每个人都得不到想要的整个蛋糕,但是他们都得到了蛋糕的一部分,这种乌托邦的框架中应该有很多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就像许多社团,大的乌托邦由许多小的各异的乌托邦构成,每个小的社团都聚集一部分有共同梦想的人,比如错字一些同性恋的乌托邦,在性问题上很自由的乌托邦,赌徒的乌托邦,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辩论家的乌托邦等等无数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都是从一个唯一的共同的大的最低限度国家,一个基本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就像同在地球上的不同国家。要说的就是这个,第一部分证明了最低限度国家的形成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在道德上是合法的,第二部分证明任何更多功能的国家都是不道德的,第三部分证明最低限度的国家就是乌托邦的框架。这本书非常好。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后感(五):诺齐克与个人权利至上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声势滔天,强烈地冲击了主流的西方政治与道德哲学。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大纛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19世纪末经功利主义的修正后更保守诟病,特别是1968年欧美各地频生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充分暴露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的挑战与压力重重。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背景与理论世界,罗尔斯以作为公平的正义既回应了福利国家的挑战,又申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成功地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主题从自由转换到正义。诺齐克看到了罗尔斯思想中潜伏的危险,直面国家做大做强时出现的个人自由流失问题,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和有关国家限度的主张。1974年发表的政治哲学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契合了时代的社会政治主题,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次重要而及时的理论重构。他的思想在实践中成为“里根-撒切尔”的所谓“新自由经济政策”等的理论资源。
不同于罗尔斯的正义意味着平等,任何不平等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纠正的。诺奇克认为,正义意味着权利,而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诺齐克捍卫的权利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权利,特别是洛克所说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个人的权利成为人们所要采取的行动的边界约束。与把权利纳入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相反,人们可以把权利当做对所要从事的行为的边界约束——不要违犯约束。其他人的权利决定了对你的行为所施加的约束,边界约束的观点禁止人们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违反这些道德约束,同时也拒绝权利的功利主义。
为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并构成了对所有行为的“边界约束”?归根到底,诺齐克强调,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约束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表达了义务论的命令:不得以任何方式来利用他人。对行为的边界约束反映了康德主义的根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没有他们的同意,他们不能被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边界约束在其所规定的方式中,表达了他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对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道德边界约束反映了我们各别存在的事实:存在着不同的个人,他们拥有各别的生命,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为了他人而被牺牲,这是一个根本的理念,是道德边界约束之存在的基础,也导向一种禁止侵害别人的自由意志主义的(libertarian)边界约束。
一个国家的权利就是个人权利的综合,国家没有超出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诺齐克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形成不仰赖任何对总体模式或计划的“构想”,试图超越契约论和功利主义提出国家理论,效仿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来证明“一个正当的国家是如何可能的”。每个人的意图仅在于促进他自己的利益,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正如许多其他人也在这样做的时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促进了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并不是其意图的一部分。
从个人走向国家主要包括两个转变过程。首先,从个人联合形式的起点 “私人的保护机构制度”到一种“超低限度的国家”,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以道德上可允许的方式发生,而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私人的保护性社团组织由于允许一些人强行他们的权利以及并不能保护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个人,而且私人的保护性社团制度如果不做任何道德上不合法的事情就缺少垄断性,从而也就无法构成一个国家或包含一个国家,更遑论该制度下保护和强行人们 的权利难免沦为一种由市场提供的经济商品。然后,从超低限度国家必然转变至最低限度的国家。在超低限度的国家中,人们维持这种垄断权而又不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保护服务,这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即使这要求某种特别的“再分配”。超低限度的国家的运营者在道德上有义务制造出最低限度的国家。
而后关注坐标轴另一个方向,诺齐克又论证了,比最低限度的国家具有更多权力或功能的任何国家都不是合法的或能够得到证明的,主要武器是他的资格理论和持有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相对立,诺齐克将自己的分配理论成为“资格理论”。资格理论的核心是“持有正义”,涉及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主物的获取,持有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让,对最初持有和转让中的不正义的矫正。持有正义理论的一般纲领是:如果一个人根据获取和转让的正义原则或者根据不正义的矫正原则(由头两个原则所规定的)对其持有是有资格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一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分配)就是正义。
持有正义的资格原则是历史的正义原则,即主张过去的状况和人们的行为能够产生对事物的不同资格或不同应得。在诺齐克看来,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的倡导者只关注确定谁应得到什么的标准,只愿意考虑那种支持某些人应该拥有某些东西的理由,以及那种支持总体持有图景的理由。无论给予是否好于接受,都完全忽视了给予。这就导致,当分配正义的目的—结果原则被纳入社会的法律结构的时候,像大多数模式化原则那样使每位公民对个别地和共同地制造出来的产品总额的某些部分产生出一种强制性的所有权要求。分配正义的最终—状态原则和大多数模式化原则创制了别人对人们及其行为和劳动的(部分)所有权。这些原则涉及一种转换,即从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观念转换为对其他人们的(部分)所有权观念。最终—状态原则和其他的模式化正义观念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为达到所选模式而必需的行为本身是不是没有违反道德的边界约束。至此,诺齐克完成了从个人权利至上出发到最低限度国家的内在逻辑贯通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