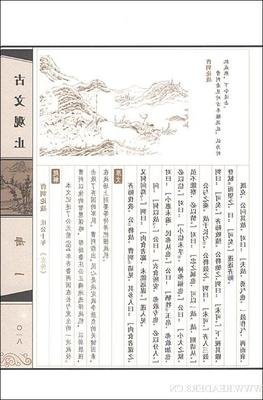
《刘伯温与哪吒城》是一本由陈学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篇梳理北京城市史,下篇利用各代资料开始对传说源流展开考索,力图寻找传说每个情节和要素被糅合进来的原因与途径。只是,信仰基础、社会思潮等提供的不过是传说产生的合理性推考,而非一定如此的充要条件。其实就我看来,这则个案的材料积累和演变脉络都不算上佳,作者完全轻信了金受申的记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从民间文学来说,本书对文献记录与口头流传情况的关系也没有充分的自觉,只集中于文本分析,忽视了传说前世今生的生产、传播和主流化过程,留下不小的遗憾。
●掐头去尾,中间不多。为了介绍一个遗产的我还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民间故事,这是已经成了膝跳反射么。。。
●刘伯温与哪吒为何会与建城联系起来呢,外在的环境,民众的心理
●中规中矩。
●这本书在国图,先看的香港版,再看的大陆版
●比较细致地梳理了北京城建城传说和异文,另2020年施爱东新文提到“清末民初,北京城墙开始一段段遭到损毁,……1952年开始,北京城墙被陆续拆除。”东西便门在外城,不能和都城九门并论,金受申版的哪吒城传说里将其当作哪吒双臂并不合理。所以他提出刘伯温建八臂哪吒城的传说基于北京城的改制,不会早于40年代。
●北京的建城传说与政治与社会
●严正批评三联对这本书的处理,太欺负读者了吧。全书就那么点篇幅,直接出个小册子也就得了,搞得这么煞有介事,结果一翻开才发现撑死了就是一篇比较水的论文,真是堪忧之至了。原论文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可言,叙述性太强,拿来做科普还可以,学术论文哪有这么敷衍的?还有啊,既然是谈民间传说,干嘛还非要加一个和它没有任何关系、且在其他写北京城市历史的书籍中每每能见到的建城沿革?总之,这书出成这样,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底下的书评,有给四五星的,而且冠冕堂皇地扯了一大堆,真想知道现在写书评的人都什么心态,服了。
●看了吐槽的点,觉得陈学霖先生委屈了,毕竟先生已去了这么多年了。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就是“北京城建城沿革”这章。因为个论述主题关系不大。删掉这章后是本不错的小书。
哪吒城,关于北京城市史的重要传说,本来是很期待这部著作,能够透过对这个传说的梳理,显示出北京城市史的有趣侧面,然而读完却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比如讲到主要事迹发生在南京的刘伯温为何会成为北京建城的主角,陈公仅以一句永乐时期南方人口的迁徙以及商贸的作用就一笔带过,使他前面对于传说如何一步步从姚广孝转移到刘伯温身上所做的繁密的考证,落脚处未免太窄,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
书的前半部分所做的考证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然而如何将这个传说的变迁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相联系,本书显然还做得不够。
另外,在前面的插图中,用了一张来自插图西游记的图片,图片上分明写着“红孩儿”,作者却在说明中说是哪吒,虽然哪吒有时是被称为红孩儿不错,但是在西游记中还是不同的吧。
《刘伯温与哪吒城》读后感(二):短评《刘伯温与哪吒城》
由奥运带动的“北京出版热”中,这本由香港学者撰写的著作并非跟风之作,早在12年前,我已读过台湾版。当时已赞叹作者的巧思,而今大陆版推出,较诸当年的思考环境又有不同,更能看出作者的先见之明。
除了必要的介绍“北京城建置的沿革”外,作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自元至清“北京(大都)建造的传说”,梳理在这一传说谱系中,建城主人公如何从刘秉忠到刘伯温,建城型态如何从“三头六臂”到“八臂哪吒城”,传说的层积生成,又是如何从民间说唱流传,到秘密会党寄托排满理想,再到民初传教士的撷要记录,终于落到了金受申等民俗史家的详实纪录,并论述这段传奇后“所蕴藏着代表以儒家为基础、天人合一的人伦社会价值观念”。至此,史家的任务似乎已经了结,然而作者尚有“余论”,论及新中国民俗整理者对建城传说的“变形”,将刘伯温看作“设计建筑北京城的许多无名英雄的总代表”,从而让建城传说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取得新的合法性——虽然没有详细的论述,我却以为可算得上一条“豹尾”。至于书后附的“资料”,蒐集各类传说文本,更是提供了读者与作者对话的平台。
《刘伯温与哪吒城》读后感(三):大传统与小传统
有关北京这座城市的书籍可以用车拉,而有关北京城建的书,依着北京作为首都和文化名城的地位,这两年也是十分走俏。其中比较有知名度的书籍,包括王军的《城记》,以及后来的《采访本上的城市》。然而如果这类书仅仅算作是建设历史的散文的话,那么陈学霖的这本《刘伯温与哪吒城》则是不折不扣的学术作品。
关于北京的城建,民国初兴起一个说法,即老北京城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依照哪吒的三头六臂(亦有三头八臂之说)来设计的。北京城就是哪吒城。依照这个传说,北京的前门就是哪吒的头部,除此之外,老北京的另外几个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宣武崇文门以及东便门西便门,则分别对应的是哪吒的八臂两脚,而我们所说的皇城,则毫无疑问的对应是哪吒的胴体五脏。有好事者还进一步细分,比如说天安门是肺脏,午门是心脏,城墙是哪吒的红绫,而直通南北的中轴线则是哪吒的气管。不仅如此,出了紫禁城的一些地方也纷纷被对号入座,比如说,什刹海成了哪吒的膀胱,而地安门的西压桥则代表哪吒的阴茎。
一切听起来神乎其神,然而作者要追问的恰恰是,这种神到底从何而来?
疑问很容易就产生了。众所周之,刘伯温是明朝开国元勋,辅佐的是朱元璋,而北京都城的建立则是明成祖朱棣那辈子的事情,所以,北京建城肯定与刘伯温无关,哪吒城的事情也就谈不上了,但是我们今天又看到这样的故事,于是问题进一步具体,这一切是怎样糅杂在一起的呢?
好在作者用整本书在给我们提供答案。原来故事的来龙去脉是,京城之地原本水患严重,而传说中水是龙王所管,于是除了修龙王庙求他发慈悲,当地人也想到一手软另一手要硬。龙王怕谁?大家都知道怕哪吒了。于是乎,元朝时修建北京城时,设计者就考虑到了把哪吒的三头八臂造型运用到了建筑设计中。而主持修建的人刘秉忠,恰恰与另外一个出名的人刘伯温同姓,于是乎不知怎么得经过了多少年,此刘变成彼刘。最后,在元朝修建北京城之后的几百年之后,就成了刘伯温修建哪吒城了。
作为学术著作,作者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而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来解释此事的来龙去脉,对于作者来说,也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白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雷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中国演绎。此理论认为,大传统为上层社会传播创造,而小传统则在民间与下层劳动人民中间传播。两个传统互相依存与转化。许多在大传统中消逝的东西往往会在小的传统里寻找到一些影子,尽管这个影子可能已经是千变万化了。
而刘伯温修建哪吒城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刘伯温本是明初政治家,而后世则转变为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二世;而城市建设本身也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但就是在时间的洗涤中,经过多少年的加工转变,最终北京的城建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但是生动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成为小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理论貌似简单但的确很引发思考,因为我们身边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往往缺乏发现他们的眼睛,更不用谈要向本书作者一样,去理解它去研究它了。
《刘伯温与哪吒城》读后感(四):由北京建城传说所见大小传统的交融
北京城文脉悠长,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令这座古城充满神秘色彩,关于它的传说亦不胜枚举。陈学霖先生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考察的正是有关北京城建的一个传说。
著书缘起于陈先生偶然获悉北京城是明代军师刘伯温仿照哪吒模样建得,为探析其中缘由及典故,陈先生多方网罗史料,历经二十寒暑,终完成此力作。这本书涉及北京城的建置,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著作,而是兼采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运用史学的架构,进行的生动详实、通俗易懂的学术考证。
此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版块,分别是北京城建置的沿革、元大都城建造的传说、明北京城建造的传说。作者通过各种史籍文集、释典、小说笔记,海内外专书论著,对这个传说存在的种种疑问,力求进行诠释。读到书尾处,我们大致可将作者的考证结果作简要阐释。北京地区自古旱涝两灾盛行,龙王传说由此滋生,正值释教密宗的故事流行,哪吒变成了民众心中治理水患的膜拜。 元代,忽必烈辅臣刘秉忠被民众神话,传其仿照哪吒修筑北京城。而明初,刘伯温成为民众新的膜拜,加以传说的基本事实如北京的水患仍然存在,传说故以新的面貌呈现,即刘伯温修筑哪吒城。关于元代为何会盛行这个传说以及对刘秉忠、刘伯温自身,作者都给出了详实的考证,这部分内容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然而作者在其余论中提到,对这个传说的考证不仅仅是说明传说的渊源流程,诠释相关的历史事实,而是由传说可以管窥大小传统的交融,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本文中笔者也将主要针对作者的这个观点谈一下看法。
西方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大小传统理论上强调二者的依存与交流,大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观念起源于民间,而地方性的民间文化也需要从上层文化中汲取。 作者继而提到中国古代即有此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的大传统以礼乐为主,而礼乐很多来自民间。关于二者的互相渗透,作者以《诗》、《书》、《左传》等里面所载文字加以例证。正如书中所说:“大传统渊源渗透于民间,而小传统基本上是大传统在民间的变相,二者关系密切,交融频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创造力。”
在诠释了此传说的理论架构后,作者进一步具体论述了传说所见的大小传统的交融。这个传说的胚胎始于元代,将刘秉忠神话体现了民众祈求被护佑、攘除灾难的心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大传统中崇拜英雄的意识,大小传统的价值观由此不谋而合。朝代更替,明兴元亡,昔日传说中的英雄退隐出主角的舞台,延续下来的是民间对英雄的崇拜,刘伯温由此摇身一变为新一任的传奇。百年间此传说的延续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跟随作者去探寻传说背后的文化意义,可发现其不仅反映了北京城民俗信仰发展的轨迹,对研究大小传统的交流融汇亦可作启示。
首先,刘伯温建哪吒城的传说故事是延续前代故事基础上的更新发展,这与刘伯温本人自身传奇故事的发展密不可分。刘伯温在民间传奇色彩的愈见浓重,为其成为故事的主角更添几分自然色彩,而这又是民间英雄膜拜意识的表现。关于这点,笔者认为这是作者从大传统方面对传说的发展作的诠释。
其次,传说的广远不衰,还由于京师作为都城,不断受外来媒介的冲击,由是南京建城的传说、刘伯温在江浙的轶闻等与当地传闻融会,使传说发展为全国性的传奇。
综合上述,我们看到刘伯温建哪吒城的传说反映的价值观因时代变迁,但总体却反映了民众的心声以及对英雄的崇拜。民间艺术家及民众的饭后谈资令刘伯温等类人物神话奇异,加之上层价值观作用,这些人物形象遂提炼成大传统塑造下人物的典型。
如果说作者考证这个传说不仅局限于“考证”本身,还涉及对传说背后文化价值观的探究,笔者认为更进一步,由此传说体现的大小传统可联想到整个中国文化里大小传统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提到:“在以儒家为基础的固有中国文化里,由于大传统根植深厚,上层因子渗透于民间称为小传统,远较小传统(尤其与大传统隔阂的)升华到高层为容易。” 古代中国,文化因子由下而上发展往往迎合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甚至统治阶级的力量。当今中国,旧社会的大传统又何尝不是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支配。刘伯温建城的传说,不再是“个人英雄崇拜”,而成为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果。通过政治教条力量得以承续的中国传统文化传说,一方面得以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文化里蓬勃生存,一方面却也在偏离其原有价值观路径的基础上孤立前行。
陈学霖先生的这本书的精华处未能详细列举,比如其对各类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图文并茂的行文,尤其是由史学的眼光考证民俗传说的发展脉络,是此书的鲜明特色之一。由此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自元明发展下来的北京城建的鲜活传说,各类民间英雄的奇闻轶事,不啻为读者视觉的盛宴。陈先生谦虚道此书是通俗历史读物,笔者认为这不是因为书的疏于考察,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学术性极高的著作。如果真说它“通俗”,或许是因为它避开了传统史学的樊篱,生动丰满地展现了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令读者不致枯烦。而这也正是此书的“不俗”之处,创新亮彩之处。
回归本篇文章的主题,即传说所见的大小传统的交融。作者并未明显地花较多笔墨集中于此部分,并且在当今传说的发展以及时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方面,并未多作点评。或是由于不便,或是碍于这里原书的主旨偏颇较远。但笔者从字里行间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的唏嘘感叹,百年传承、鲜活生动的传说,经历早先的文化动乱,能传承至今不知是“幸运”或否。毕竟,这是被加以了多许主观性。“随着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逐渐放松,或甚有以外的转变;这些变革如何影响民俗文艺观,会否产生对传统多元化的诠释,且拭目以待。”作者的这句话透漏的对民俗文化发展新趋向的期冀不置可否。
一座哪吒城笑看风云,一个古传说曲折神秘,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其背后社会的多维度,我们在谈笑之余,更添的是对今日实况之思考。
《刘伯温与哪吒城》读后感(五):有感(作业)
1. 北京城传说的溯源与“巧合”
书中指出,北京素有“北京湾”之称,是南北通道的集合处,是最适宜产生城市聚落的地点。在远古时期,北京平原东南一带水网稠密,货物运输经过主要河流,今日称为永定河。在金代定都北京之前,北京作为诸侯国都邑,也曾开凿过一些运河,但不成系统。
到了金代,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提高,漕运任务的大量增加,开始了以北京为漕运中心的人工运河体系的营建。金代的统治者先后在北运河水系和永定河水系疏浚开凿了漕河、闸河和金口河,但始终都没有解决好北京运河的水源问题,货物运输量受到很大限制。
到了元代,忽必烈兴建元大都。元代充分利用北京的水资源,改善了航运条件,保证了运河的通畅和漕运的效率,先后开凿坝河、通惠河通漕,后又开金口新河济运,使北京的水路运输一度兴盛。 坝河由大都城北到通州,通惠河由城南至通州,坝河、通惠河两大漕运动脉一北一南,为大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物资。元代的“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前身)作为漕运的终点码头也呈现出“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但仍由于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水工技术上的难题,新河的失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明代时,由于对北京城及皇城都进行了改建,北京城市运河河道也随之发生变化,一部分运河称为了护城河的一部分,通州驶来的漕船不能进入城内,此外,明代还在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加凿南海,并开凿内外金水河,与通惠河争抢水源,从而造成明清时期北京城市运河水源不足、影响漕运的问题。 明清时期,由于多种原因,京郊的山泉水量减少,有的甚至断流。
正是上述问题,北京的水源至今仍是大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北京的繁荣,其得益于政治,正因为是首都,使得部分江南富户、蒙古居民的留驻,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也使得北京成为朝贡之地,货物流通也迫切需要水路交通的便捷。清朝也同样如此,满、蒙、藏大量人口居住京城,对于物质的需要日益庞大,让市场、文化富有生气起来。
文化发达起来之时,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的水问题,不可避免需要说辞,故有传说孽龙埋伏于北京城下控制水源,而降服者究竟谁能胜任?于是,释教密宗里的神毗沙门天王的第三个儿子哪吒出现了,其足以胜任如此英雄角色:镇伏孽龙。同时,这符合大传统由上层人士创造的论点,而再中国化一些,转化托塔李天王的三子哪吒也恰到好处。
从刘伯温角度而言,出于一般民众对于英雄的崇拜,下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顺从与迎合,出现像他这样的草根人物,无可厚非。时势造“英雄”,正好元朝大都的建设者刘秉忠也姓刘,再将神话主角安插到明初奇人刘伯温身上,所谓天时地利,名号也变得恰如其分起来。
2. 大小传统和中国
既然北京有这样的传说,那么传说的意义何在?陈先生在书的最后提及传说是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融会,是在以儒家为基础的固有中国文化里,由于大传统根治身后,上层因子渗透于民间成为小传统,由上至下的过程中,如何将小传统落实,一般而言,需依靠地方官吏的辛勤教化。同时,大传统又时常受到小传统的感染。
陈先生也指出,大小传统的理论极强调大小传统的彼此依存、互相交流的关系,而由于和西方在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有异,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也不同,故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并非西方学者一向推想上层与下层的文化或思想。中国文化领域中“大传统”和“小传统”多元的融会交流,大传统由少数有思考能力的上层人士所创造,如中国的儒家或道家,小传统则由大多数知识肤浅,或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
笔者认为,中国在儒家文化中浸淫已久,如果大传统是有少数思考能力的上层人士创造的话,那么原创性的作者屈指可数,对于四书五经的过分解读,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都笼罩在三纲五常的氛围之中。所谓小传统,也正是对左右君权的宰执,感通天地、攘除万难异才的崇拜,衍生出的传说故事也不无弥漫着对于统治阶级的迎合气息。
所以,将大小传统通过阶级来划分,私以为,这在中国是不适用。农业大国的中国本来的阶级在门第消失之后,便变得不是那么明显,有点也只是君臣、内外族划分,儒家思维下的中国人民,传播的脍炙人口的故事也必然是儒家的形式,而传说本为艺术文化的一种形式,自然也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但就大小传统而言,不恰当。不如说,大传统就是儒家思想。
那么,像白娘子许仙和西湖、孙悟空花果山、愚公太行山、黑龙玄武湖、孟姜女长城,这些传说故事对于地方有何意义?现今这些传说成为了城市的名片之一,神秘感、历史的厚重感之余,也为城市的旅游业做出了贡献。而大多通过民间艺术流传下来的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一代代教化人民学会勤良恭俭让。
3. 传说的传播途径
这些传说在塑造城市记忆,形成城市文化,竞相成为旅游胜地的同时,通过的途径可以分为文字、口述、表演3种方式。
宋朝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图书出版渐渐盛行。在明末年间,王阳明心学盛行,民间思潮涌动,思想的繁盛与图书的出版是相互促进的,此外,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图书的出版成本的降低,民众接触书籍的范围也日益宽广,彼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皆为畅销小说,《刘伯温与哪吒城》书中提及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亦在明朝盛行。文字的传承让一代代人熟读四书五经之外,也了解了种种稗官野史、乡野趣闻。
思潮涌动也带动了民谣舆论的发展,口述方面,传说故事通常由长辈、说书人等主体代言,所谓一传十十传百也是这样的道理,除此之外,艺术表现,如手工艺品、绘画,戏剧等形式也不可缺少,仅地方性戏剧便有京剧、越剧、昆曲、淮剧等等,常有曲目如杨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牡丹亭等等,艺人的对于传说的推动做出了很大贡献。无论何种形式的传播,地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传说故事回归为文字形式,载入地方志中,这样的循环传播途径使得传说故事源远流长。
不管传播的形式如何,传说故事大多属于“俗文学”,就思想内容而论,仍然脱不了大传统的忠孝信义,善恶报应等观念的传统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