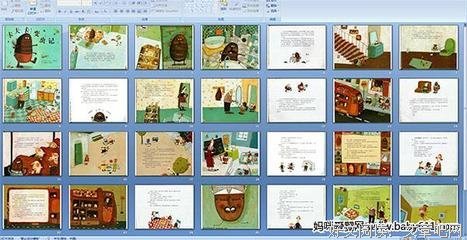
《卡夫卡变虫记》是一本由(美)劳伦斯·大卫|译者:邢培健|绘画:(法)戴勒菲妮·杜朗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根据卡夫卡《变形记》改编,给那种悲凉的寓意一个不乏新意的解读:缺乏爱,会让人异化,也只有爱才能弥补和改变这一切。最后的结局很阳光。但也许是原作给我的震撼太大了,我始终内怀悲凉。
●画风很好,但小心被泛滥。。。
●http://v.yupoo.com/photos/shawxx/albums/1807732/
●寓意是家庭中对小朋友关心的不足挺深刻的,画面有趣。不过故事太长了,讲起来挺累的……
●这本书更像是写给大人的,提醒我们时刻记得要关注孩子,倾听孩子。这本书陪伴Momo度过了今年春季的发热感冒,陪伴她消耗掉一些在妈妈单位的无聊时光。
平淡无奇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的重复着,其中的人们渐渐变得麻木,或许仅能看到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早已失去了那些年对新生命来到自己生活所带来的新鲜感。这样的漠视与冷淡就发生在看似和谐平静的家庭生活中,让失望的孩子发出了“会不会我本来就是只虫子”的疑问。又有多少父母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才潘然醒悟,孩子怎么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变成了这个样子?年轻的父母,放下手机,关掉社交网络,多些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吧,一起享受成长的过程,别让你们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卡夫卡变虫记》读后感(二):《卡夫卡变虫记》孩童版的心理寓言
一个小男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但谁都没有发现,除了他的好朋友。
当家人终于发现他变成虫子,接受他并且依然爱他后,他也就恢复了人形。
故事的情感内核是孩子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关注。想起《瑞克和莫蒂》第一季的一集中,莫蒂和性爱机器人生了个外星小孩,外星小孩长大后写了本书埋怨父亲和自己糟糕的童年。深爱孩子的莫蒂目瞪口呆,他的父母却淡定地说:“当父母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忽视父母的孩子占了所有父母的几成呢?我一直以为是少数吧。不过转念一想,真正了解并理解孩子的恐怕又是少数。
那么,这本绘本是给成人和父母看的吗?孩子读这本绘本能收获些什么?我想应该是一个扩大了的情感内核:人需要真正的关注和关爱,否则内心会荒芜得如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一只虫子,自我感觉被漠视、孤独而荒诞。
《卡夫卡变虫记》读后感(三):做父母的是否忽略孩子的成长?
今天给女儿讲故事《卡夫卡变虫记》
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早上,小男孩卡夫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棕紫色的超级大甲虫。但是没人注意到他变形了——他的父母、他的小妹妹、他的老师——除了他最好的朋友迈克尔,谁都没注意到。 他感到很孤独,而除了他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孤独,包括他深爱的父母。
这个故事或许对女儿来说有些不那么好理解,她只是好奇卡夫卡为什么会变成甲虫?不过这个故事让我思考:我对孩子成长和变化的关注是不是也忽略一些什么?或者我是不是也没与那么耐心去关注女儿成长。可能女儿在婴儿的时候,我对她的一点点变化和成长都会惊喜,而慢慢的,她渐渐长大,对她的一些变化变得麻木,或者司空见惯了?不再用一种惊喜、赞美的眼光去看待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这会不会让女儿在心理上感觉爸爸不再重视她了,忽视她一点一滴的成长,也同时没有调整好来适应女儿的变化。对于她成长过程所要面对的那么多未知的困难,对于她的孤独,我有没有做好准备和她一起来面对?
《卡夫卡变虫记》读后感(四):穿越的甲壳虫——近百年后的经典改编
绘本既然是给孩子看的图画故事书,除了原创,自然也存在着大量的改编问题,从流传已久的童谣、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或文学作品中提取素材,大多数在文字和图画的重新阐释中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使之变成了具有独特气质的绘本作品。
根据文学作品和寓言改编的绘本改编意味更浓,因为其改编的对象有原始的文本可以考量,相较之下,分野自出。根据弗兰兹•卡夫卡《变形记》改编的《卡夫卡变虫记》即是其中之一。
弗兰兹•卡夫卡,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他在其作品中讽刺了资本主义的诸多方面,就《变形记》这篇小说来说,其主题之一就是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并把这种在工业社会和金钱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置放在家庭关系,这个本该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体中,扩张了其与人伦情感之间的矛盾,散发一种刺骨的、荒诞的悲凉。而经由劳伦斯•大卫和戴勒菲妮•杜朗之手改编的《卡夫卡变虫记》则给了这种悲凉一个不乏新意的解读——缺乏爱,会让孩子异化,给予爱,才能让孩子成为真正的孩子。
由于父母、路人、校车司机都没有发现卡夫卡变成了一只大甲壳虫,所以卡夫卡只得按照平时的生活步骤循规蹈矩地洗漱上学。绘本比原作温馨的地方在于,卡夫卡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也更容易快乐:虽然变成了虫子且人们都没发现,但变成虫子也有很多乐趣,拿书包的时候更省力,答数学和踢足球的时候也更有优势,这让他一度洋洋得意,何况这一切迈克尔都知道,真正的友谊并未离他远去。好朋友迈克尔不仅第一眼就发现了变成虫子的卡夫卡,还在这一天里陪伴着他,分担他的苦恼,帮他想办法,在图书馆和他一起找他是变成了哪一种虫子。这份“爱”让卡夫卡没有那么孤单绝望,甚至还可以享受一点乐趣,他想要安心做一只虫子了,而家人在看到天花板上的卡夫卡时才恍然发现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此刻,人虫对峙,分外紧张,双方你来我往,彼此试探。随着卡夫卡委屈失落的泪水,之前的反讽和荒诞一下子做泪腺状崩溃,爸爸妈妈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是如此了忽略了孩子,他们再次拥抱了他,变成虫子的卡夫卡放心了,即使他是一只大甲虫,爸爸妈妈妹妹也还会爱他,这就够了,做虫子又能怎么样呢?
我本以为故事就会这样结束,但高明的作者并不满意这个略显俗气肤浅的寓意,他让这只安心的虫子在第二天醒来以后变回了人,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满怀欣喜。于是,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作者是在说:长期缺乏关爱的孩子会慢慢异化,变成一个人中之虫,也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当家长发现孩子的异样之后不应该斥责孩子,而是应该反省自身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然后用爱去包容他现在的样子,也只有宽容的、真诚的、自省的爱才能让孩子找回自我。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找回并不会像卡夫卡一样一夜还原,而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在这本绘本中,改编作者吸取了弗兰茨•卡夫卡的创意和寓意,把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的问题进一步集中锁定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并且是双向互动的开放性结构。在内容和风格的处理上,不仅保留了原作的反讽和悲凉,也融入了童话的离奇和幽默,结尾更是不仅满足了童话的阳光圆满,也实现了寓意的突破。
另外,绘本的画风稚嫩诙谐,也很有意思,尤其是卡夫卡穿上衣服以后,如果不仔细看他的触角和多出来的两只手,乍一看和其他人也没有太大差别。不禁想,画家这又是想暗示什么呢?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猜测吧。
《卡夫卡变虫记》读后感(五):看绘本:卡夫卡变虫记
关于变形的故事或许最早可见于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奥维德以诗歌的形式记叙了大量古罗马和希腊关于变形的神话,其中较为流传深远的有斯库拉因为女巫喀尔刻的迁怒而变成一只六头海妖、达佛涅因逃避阿波罗的追求而变成了一株月桂树、猎人阿克泰翁因为无意中看到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沐浴而被阿尔忒弥斯施法变成了一头牡鹿等等。出现人/神人变成另一种生命体,或动物或植物,甚至是变成非生物,如石头、回声、石碑的神话传说,是因为古人相信生命轮回之说和灵魂的不朽,这在古希腊哲学和佛教思想中都有所体现。
奥维德之后一千多年,文学史上出现了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中篇小说《变形记》,讲的也是变形的故事。小说讲述了旅游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以后如何逐渐被家人唾弃,以致最终病逝于又脏又臭的房中。那是一个既锥心又恶心的故事,卡夫卡表现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被疏离,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异化的人,注定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毁灭似乎成了唯一的下场。
而劳伦斯.大卫(Lawrence David)的《卡夫卡变虫记》则一改这场悲剧为喜剧,让故事更适合于孩童阅读,至少不那么令人后怕!《卡夫卡变虫记》的故事灵感即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英文版的书名比较可爱、清新——Beetle Boy,保留了《变形记》主人公的名字格里高尔,中文版则直接把格里高尔改为卡夫卡。全书文风诙谐,行文不拖沓,和法国插画家戴勒菲妮.杜朗(Delphine Durand)那带点怀旧气息、丰富细腻的画风搭配在一起,构成了绘本的风趣和可爱。戴勒菲妮让所有人物都像一具具的木偶,有着长鼻子,大多细手细腿,还穿着带孔的皮鞋。要么憨厚可掬,要么表情木然,总之他们都是性情温和、乐天的。
劳伦斯是美国波士顿人,生于1963年,后来移居纽约。他先后曾担任纽约一所学校的教师助理和一家出版社的助理,自1993年起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劳伦斯最早写的是给成人读者阅读的小说,两部小说(Family Values和Need)表现的都是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后来转向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发现似乎那里才是他的天地。《卡夫卡变虫记》和另一本绘本《好心的小女孩》,同样表现了孩子在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注之下所发生的“变形”:温顺的小女孩米兰达变成了无礼、惹人厌恶的卢克利西亚;卡夫卡变成了一只超级大甲虫。
卡夫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棕紫色的超级大甲虫。可是除了好朋友迈克尔,没有人发现这个事实。由于卡夫卡平时便是个淘气、爱搞怪的男孩,所以即使他一本正经地向家人宣布这件事,大家还是不予理会。卡夫卡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他甚至怀疑自己原来就是只虫子……他沮丧极了,因为竟然没有人在乎他是人还是虫子!
好在迈克尔还是很在乎他的。迈克尔热心地陪卡夫卡在图书馆里看关于昆虫的书籍,而卡夫卡也很积极,即使成了虫子也想弄清楚自己是什么虫子。
不过话说回头,当一只虫子也不是毫无好处的。在数学课上,卡夫卡用自己的腿算出了2X3=6;体育课时,他利用触角成功将球射进龙门,这一切都令单纯的卡夫卡感到快乐。但他最终还是想回到过去,变回男孩,他要和家人、迈克尔在一起。和《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结局不同,小男孩卡夫卡终于唤起了家人的关注,在家人宣告对他的爱以后,他的甲虫日子也随着结束了。
借着卡夫卡的故事,劳伦斯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多久没有认真聆听孩子的声音了?纷扰的生活总是很容易让人忘记渺小的孩子,因着他们单纯、随性,甚至经常大意的性情,大人也就不怎么认真对待他们所讲的话。几天前我到一家美国学校代课,正好给孩子讲《好饿的毛毛虫》。一个男孩站起来,告诉我那天是他姐姐的生日,他也跟书里的毛毛虫一样,回家就要吃蛋糕了。当时人声沸腾,我礼节性地回应了一句“啊,好啊”,转头便把这事儿给忘了。第二天的点心时间,男孩手里捧着个饭盒,快乐地告诉我那是他姐姐的生日蛋糕。几分钟后,他又跑到我跟前,对着我表演不用餐具吃蛋糕的功夫。我当时就在想,天哪,他真的是很认真对待吃蛋糕这回事的!
那小男孩卡夫卡呢?他会不会从变回男孩的那天起便再也不搞怪,不撒谎说自己是宇航员或超人了呢?
一直到故事结束了,我还是没能看见卡夫卡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从家里墙上挂的全家福看来,他应该还算是个快乐的小男生吧。当然,他一定是。因为他会站在床头的那扇窗前,对着正好路过的虫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