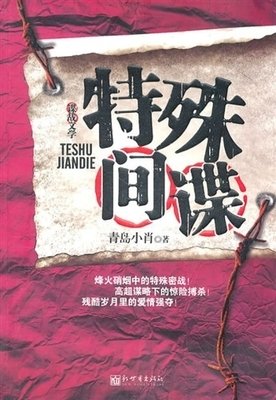
《间谍的遗产》是一本由[英] 约翰·勒卡雷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84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7-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间谍的遗产》读后感(一):支离不破碎
支离不破碎
——史迈利系列四部曲之终章《间谍的遗产》导读
文泽尔
记得《间谍的遗产》全书译稿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在去年端午节后不久,没想到,因为一系列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直到今年端午节吃过粽子了,印刷好的实书才陆续现身于大家手边。忙碌季节,时间永远过得飞快,若要问那史迈利系列是否还有下一部,约翰·勒卡雷老师恐怕就要扬一扬他那对矍铄老人独具的白眉毛,用德语或法语大喊一声:“这次真没有了!”
真的吗?事实或许依旧存疑。作为本书与《鸽子隧道》这两部勒卡雷最新作品的译者,倒是可以斗胆替他老人家多讲一句:兴许答案就藏在《间谍的遗产》一书的字里行间。虽然《间谍的遗产》大致看来确实无底可泄,但这本书中的情节安排是如此有趣,以致于在隔了一年之后,此刻写起译后感时,我竟舍不得向读者们透露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初回阅读体验的关键细节。所以,即便书中确实藏有“四部曲是否终结”问题的答案,那也得靠大家亲自去开卷查验了。
至于可以透露的部分有哪些。嗯,首先是风格:再强调一遍——本书是史迈利系列正统续作,是接续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生》《史迈利的人马》这三部之后的故事。因此,延续前三部纷繁复杂的人物与情节,本书在叙述风格上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史迈利系列多年来的一致性。前段读过《鸽子隧道》的读者们可能会觉得老爷子近年来文风有些絮叨,用文字重现画面时跳跃感太强,进而担心《间谍的遗产》这部新作读来怕是会有些支离破碎感。实话实说,毕竟(很可能)是系列大结局,回顾前三部中的各种“名场面”虽显俗套,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通过本书补齐汉斯-迪爱特·蒙特与“圆场”之间恩怨情仇先前一度缺失的最重要一环,或许也因此要去再补一遍《柏林谍影》(好吧,我承认自己到现在才cue《柏林谍影》就是故意的——情感上而言,我更愿意将本书视作史迈利四部曲的终章,而非《柏林谍影》的番外,尽管同时享有这两重身份,也不算多矛盾);我们会发现那位老朋友亚历克·利玛斯的身影笼罩在整本书构筑而成的巨大密林或者雪地上空,他在某人的回忆中有一大段动作戏,以及大家喜爱的铁汉柔情戏码;我们会以管中窥豹的方式重温“圆场”当年找鼹鼠的全过程,并且知道《间谍的遗产》实际上真的是一部纯粹为读过前三部的粉丝们服务的作品——倘若是完全没有读过前三部的读者,一上来就直接挑战这本,那么恐怕是无法享受到阅读处处玩梗作品时所特有的醍醐味的。没错,读勒卡雷说到底就是个食髓知味、循序渐进的过程。诚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劳伦斯·布洛克这样的系列作大师,他们在创作时都会特别留意单部作品的独立可读性,但史迈利系列却并非如此。勒卡雷在创作时,首先必定要让人物统统裹挟进时代、回忆与大事件所酝酿而成的洪流之中,让读者们先明白“过去未来俱为一体”的道理,然后才开始让齿轮逐渐转动起来,碾压、研磨这些可怜的角色,手段兼具无情与悲悯。纵观史迈利四部曲多年来的布局,尽管每一部都切实存在着至少一位主要的、形象丰满的对手,但每本几百页的篇幅读下来,越是读到最后,却越能感受到勒卡雷式创作规则的残忍:人物重要吗?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重要。尽管你有一位第一人称主角,比如彼得·吉勒姆,以他的视角道出疑惑,推进剧情,有时一夜风流,有时刻薄毒舌,有时愤慨无奈。但这些都不是重点。你会发现这一系列作品中充斥着某种完全矛盾对立的创作观:一方面,随着剧情的推进,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画面似乎极其想要揭露一些之前提出的疑问;另一方面,同样随着剧情的推进,所有的疑问、疑惑却都没有得到完整的解答——我们真正看到的,只是过客式的来去匆匆。所有人物,包括贯穿整个系列的那些重要人物、那几位苦心孤诣的反面角色,你能从阅读当中得到的,也不过是惊鸿一瞥的几帧画面罢了。勒卡雷究竟想让我们读到些什么?没有罪,没有罚,偶尔短暂的快乐,最终却是长久的孤独与惆怅。确实,有些角色得到了着力刻划,对话很多,描写很多,但也只是登台那么几次,随我们的第一人称视角在比如伦敦或者柏林一日游的情节中献上几个回合的完美表演,便突如其来地谢幕离开、消失不见了。史迈利系列几乎没有上帝视角的陈述,一切都是通过代入人物主观的观察来获得的,包括阅读那些报告和书信,也尽是些雪泥鸿爪、只言片语的集合。作为读者,我们能够从书中得到的线索,就跟真实世界里一样,芜杂而纤细,极微小处往往藏匿着魔鬼,至于错过的,往往就化作不可知:纵使遗憾,却也无计可施。
创作本书时已年近九十高龄的这位英国绅士就是这样的,对待读者时坏得很,尤其是对系列老读者——或者至少是看过加里·奥德曼出演史迈利的那版《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影的谍战片爱好者们,出手就是一系列杀招。讲真,第一时间冲进书店买来并且翻开《间谍的遗产》的读者们,心中惦记最多的无非也就是下面这灵魂三问:
乔治·史迈利还活着吗?彼得·吉勒姆还活着吗?吉姆·普里多还活着吗?
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影版里三位对应卡司的影迷圈黑话套用一下,也即:狗爹怎样了?卷福怎样了?马强怎样了?
我也不怕告诉大家:这三位都有戏份,且戏份有多有少;多的贯穿全书,少的也就在章节里现个身露个脸,起一份引线搭桥的功用,顺带告诉大家“我还行”或者“不怎么好”。至于狗爹在正序时间线里按年龄算下来已经一百多岁,是单纯活在回忆里,还是突然跑出来跟卷福对线,帮他解决实际问题?卷福这次究竟是不是主角,有没有开启新一轮风流韵事,他眼下这年龄还行不行?马强退休了能干嘛,他的狙击枪用得是否还跟过去一样好?那都是要读完全书才知道答案的——注意!上面这段文字可并没有剧透什么,也并没有诱导读者在开卷前即自行展开各种画面。反正,老爷子给糖撒盐的手段诚不我欺,这是世所公认的,所以这里只能最后再透露一点:这三位在本书中的戏份符合我们关于系列终章的全部想象,不多一分,亦不少一毫。即便是最苛刻的系列死忠,读罢闭卷之后,也不得不对勒卡雷老爷子的处理方式表示认可——否则还能怎么样呢?这样的终章仍旧是十分史迈利的,毕竟连《史迈利的人马》都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作品,因此,仅仅是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所以还是回到开篇点题的那个问题:《间谍的遗产》读起来是否会有些许如《鸽子隧道》般的支离破碎感?答案是“不会”。确实这本书很支离,包括大量引用报告内容,以及不断闪回过去场景,都会给人以一种支离感,但也就到处为止了——回忆若即若离,画面若隐若现,但并没有破碎掉。虽然细节一如既往的繁琐,阅读却依旧渐入佳境,依旧是原汁原味的史迈利系列,那种“我逐渐理解一切”的浸入式体验,是除了勒卡雷老爷子之外,其他谍战小说作者根本不可能给予的。
(本文发表于《文学报》2020年7月22日)
《间谍的遗产》读后感(二):情报人生的序章与终曲
原文发表于《文汇报》2020年9月30日
1999年9月11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英国老太太在位于伦敦东南角贝克斯利希斯的自家花园开了一场简短却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这位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名叫梅利塔·诺伍德(Melita Norwood),当时已经87岁高龄,慈眉善目、戴着老花镜,对着蜂拥而至的媒体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在声明中,梅利塔承认她曾是苏联间谍,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一直为莫斯科提供核武器研发的相关情报。在1972年退休前,她一直是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秘书,有机会接触大量涉及英国核研究的机密文件。20世纪90年底啊后,随着苏联的土崩瓦解,大量原克格勃情报人员叛逃至西方并带去了相当多机密文件,其中就有梅利塔的档案,她的代号是“霍拉(Hola)”。于是,在远离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和间谍生涯近30年后,梅利塔的真实身份被突然曝光,乃至引发媒体关注和意外的政治风波。
当翻开勒卡雷2017年出版的小说《间谍的遗产》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梅利塔的故事。一位退休几十年的老间谍,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被重新牵扯进当年的不堪往事。在小说开头,隐居法国、金盆洗手多年的彼得·吉勒姆为了自己的退休金,不得不重返“圆场”。在哪儿,他无奈地接受了“马戏团”年轻一代有关60年前“横财行动”细节的种种问询。而所谓“横财行动”正是《柏林谍影》中所讲述的那桩诡谲悲剧。纵然过去了数十载,但那场悲剧依旧“阴魂不散”,受害者的后人们居然找上了门。而21世纪的“圆场”年轻一代却只是想把这个陈年的“老麻烦”丢给同样老迈的彼得·吉勒姆,让他发挥“余热”充当组织的替罪羊。
尽管《间谍的遗产》被宣传为《柏林谍影》的续作,但其实也可以称其为《柏林谍影》的前传。年逾九十的勒卡雷新作中的大量篇幅都是为《柏林谍影》故事所做的铺垫,而五六十年后的故事与其说是“续集”,莫不如说是一场事与愿违的追忆。另一方面,若没有读过《柏林谍影》又或是“史迈利系列”的前作,倒还是可以直接捧起《间谍的遗产》。虽然会错过一些致敬前作的典故和无关主旨的细节,但同样也可以回避掉一些叙述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史迈利的登场。在此之前,史迈利的上一次出现还得追溯到1990年出版的《史迈利的告别》(又译为《神秘朝圣者》)。在《间谍的遗产》中,2015年时彼得·吉勒姆本人已经是78岁的老人,但依旧可以跟新同事们玩“捉迷藏”的间谍游戏。若根据《召唤死者》中的描述,身为大学生的史迈利是1926年加入了“马戏团”,那么他应该是在1905年前后出生的。这就意味着在《间谍的遗产》的故事中,史迈利高龄已经超过110岁。而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勒卡雷把史迈利加入的年龄推迟到了1937年,但即便如此,史迈利在《间谍的遗产》中也成了一位超过100岁的超级寿星。有鉴于此,新读者的一大优势就是在阅读时可以不用背负这类前作设定上的尴尬,只需享受文字和智识上的冒险。勒卡雷也巧妙地将《柏林谍影》的故事折叠塞入了新作之中,让人有了重温当年这部经典之作的兴趣。
初看起来,《间谍的遗产》可能是勒卡雷诸多作品中,较为好读的一部,以至于能让人产生可以一个晚上轻松翻完的错觉。然而,若细细探究,却能发现作者布下的暗线与冲突。例如小说中,往往以档案文件和私人回忆彼此交织的方式来回溯五六十年前的那个冷酷故事。因此你甚至可以把《间谍的遗产》当作一本“书信体小说”来读。档案与回忆之间彼此补充,却又充满矛盾,而所谓“真相”似乎就隐藏其中,但又让人时不时掩卷思考与质疑。而现实的情报工作,除了极少部分“剥头皮组”那样的外勤任务外,绝大部分都是在文字、言辞、回忆中互相比中查找线索,进而抽丝剥茧发现如碎片般的些许“真相”。在小说中,彼得·吉勒姆即便曾目睹、经历过当年柏林冷夜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但确实中难窥全貌。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重读档案,他也不过是尝试着拼凑历史碎片。真正洞悉整个事件的只有当年的“老总”和史迈利本人。然而,你也别指望在小说的最后就能抵达勒卡雷间谍世界的终点,整个故事可能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旅程,亦如他之前回忆录的书名《鸽子隧道》。
勒卡雷间谍小说的悬疑背后实则都隐藏着一个母题:极端环境下,每个人的道德选择及其代价。哪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哪怕档案都已残缺不全,哪怕当代人早已淡忘,但他笔下的人物依旧要为当年的选择承担后果,或早或晚付出各自的代价。在没有信念支撑的牺牲在“圆场”年轻一代看来,自然是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冷战时代的种种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可以在“审讯”吉勒姆时可以轻松地吐槽:在你们那个时候,无辜者的死亡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背负这个“诅咒”的吉勒姆却是直面背后冷酷的老特工,而能解除这项道德枷锁者正是他当年的上司史迈利。
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的“叛国者”都不是为了金钱,正如现实中的“剑桥五杰”、 梅利塔·诺伍德,大多都是处于信念与理想而选择此道。毕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英国知识分子来说始终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直到冷战愈演愈烈的60年代才开始逐步退潮。2005年,梅利塔·诺伍德以93岁高龄去世,死前也从未对自己的间谍行为表示后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之所以会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阻止一个新制度的失败”。其实,他们与史迈利终究都是同一类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纵然立场水火不容,但史迈利、吉勒姆或许反而会能理解梅利塔们当年的动机。面对帝国衰败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的情报机关自身也在不断地堕落,变得更加卑劣与虚伪。借彼得·吉勒姆之口,勒卡雷还吐槽了如今的“圆场”。在他看来,如今“圆场”的情报工作无非是官僚化的重复,丧失灵魂与信念。经历、目睹这一切的史迈利或许真需要有一种“欧洲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
2017年9月7日,新书《间谍的遗产》发布会上,当时86岁的勒卡雷直率表达了他对当今时代的忧虑。在他看来,“某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理应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口中的“糟糕之事”包括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民众对欧洲精神的背离,也可能还有他对当代英国人丧失崇高目标感的失望。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勒卡雷指出: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让他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欧洲辩护。
不过,也如《经济学人》评价的那样:在勒卡雷的《间谍的遗产》中,虽然史迈利一再强调他身负欧洲精神的宝贵价值,但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形象。
《间谍的遗产》读后感(三):间谍之眼 ——约翰·勒卡雷与现代社会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在2017年创作的《间谍的遗产》收获了评论界的好评如潮,也为他笔下的“圆场”传奇划上了句号。勒卡雷以间谍小说享誉于世,这一看似富于娱乐价值的题材并没有减损他在文学评论界的声誉,正相反,很多评论家敏锐地捕捉到他在创作这一题材时赋予其的严肃意味。在格雷厄姆·格林之前,间谍小说往往意味着爱国主义的英雄传奇,正直的年轻人捍卫着国家的安全,与各种外国势力斗智斗勇。勒卡雷严格来说亦是这一文学传统的一份子,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者,笔触中流露出对于祖国深沉的爱,但另一方面勒卡雷也很清楚,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一去不返,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信念原则,现今的英国社会都已不复昨日的荣光,在他的笔下若即若离地抒写着对于曾经信念的淡淡讽刺。由此来看,勒卡雷所创造的间谍世界不仅满足了我们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梦想(我看过有国内学者在论文中将勒卡雷比作英国金庸,不失为比较文学的有趣尝试),更提供了我们审视观察当代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 勒卡雷曾经在一次广播节目中自陈心曲,他并非简单将间谍视为惊险小说的主角,对于他而言,间谍世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一个隐喻,“是我们社会态度与虚荣心的缩影,亦是英国状况的缩影”,不仅如此,这一文学上的选择亦浓缩了作者和读者与现今社会互动的复杂况味,因为间谍世界不仅反映了现今社会的种种弊病,还为身处在这个堕落和冷漠的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选择,勒卡雷的魅力在于他最终会指出这一替代方案的荒谬,《间谍的遗产》正是通过圆场两代人的追寻和争辩,一步步颠覆了“间谍世界”这个迷魅的幻象。这部作品情节上承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沿着退休情报人员彼得·吉勒姆的足迹,揭开了柏林悬案的迷雾,同时也道出了圆场精英们风流云散、黯然落幕的结局。 在这部作品中,勒卡雷笔下的主角们如史迈利、海顿、利马斯、威斯特贝像与观众道别一般悉数登场,熟悉勒卡雷的读者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会回想起圆场缔造的一幕幕传奇。对于读者而言,较之这些人物鲜明各异的性格,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们殊途同归的生活信念。勒卡雷认为,间谍世界的吸引力在于其面对生活复杂性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的最终失败,如同韦伯所说,现今世界是一个“多神”的世界,充满着各种价值和信念的冲突,生活正是由这些相互冲突、极难调和的主张构成,而间谍们面对这一世界的优长在于他们摒弃了自身柔弱敏感的个人情感,将自己和他人均视为庞大机械上的齿轮,因而能够运转由心、物尽其用,必要时弃子取势更是题中之义。但勒卡雷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这些行为最终的代价,做出如此选择的间谍们不但牺牲了自身的情感,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非人化。由此,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世界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呈现出这个世界内在蕴含的荒诞悖论。 在勒卡雷的妙笔描绘之下,背叛、欺骗、隐瞒、疏离,间谍世界的这些特质,亦是整个当代社会的缩影。勒卡雷指出,腐朽的源头在于颓废的统治阶级,其曾经的权威建立在严格的道德责任、自制的尊严以及对他人的义务感之上,这些品质现今成为了无源之水,甚至堕落为了自我欺骗与沉迷,就像康妮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为海顿与史迈利而发的悲鸣:“可怜的人,你们曾经所受的那些训练,统治帝国,统治海洋,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是最后一代了”。权力则掌握在一些冷漠的利己主义者手上,他们唯一关心的也只有权力本身,正如《德国小镇》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的夫子自道:“我非常信仰虚伪,这是我们离美德最近的地方,它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像宗教,像艺术,像法律,像婚姻。我为事物的外表服务……我不在乎自己服务的是不是个有德的国家。所有权力都是腐化的,但失去权力会让人腐化得更甚”。上流阶级的腐朽背叛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推导出的必然结论,亦是现今社会个人道德状况的鲜明写照。我个人更欣赏乔治·史迈利妻子安恩的名言,“没有背叛就没有忠诚”,轻描淡写但又掷地有声。 勒卡雷的小说中充满了感情受挫的孤独男女,他们的孤独感来源于爱情中的失望,也来源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疏离,对于这些人来说,间谍世界提供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选择,因为在这里,爱情不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掩饰自己弱点、进而去利用他人弱点的捷径,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被教导去进行背叛而不是被背叛。我们会想到勒卡雷笔下海顿和史迈利的较量,海顿企图通过与安的婚外情来破坏史迈利的判断,但并不成功。这件事给史迈利造成了至深的创痛与羞辱,但他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分寸,最终发现了海顿是圆场内奸的线索。在情感世界里,史迈利忍受着莫大的痛苦,而在谍报战场上,他冷静地思考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政府主管奥利弗·拉康对史迈利作了一个同情而残忍的总结:“如果安是你的间谍而不是你的妻子,你可能会把她管理得很好”。 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世界因此具有了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简单有效的行为准则,将道德视为方法,将情感塑造为手段,在这个简明扼要的框架中,个人可以完美地实现某些难以达成的目标。例如,乔治·史迈利在处理档案(有时他认为档案是 “唯一的真相”)和进行审讯这两个方面是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从一个可悲可怜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 另一方面,这个隐秘的世界是如此具有吸引力,甚至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阴谋已经取代了宗教... .它是我们神秘信仰的替代品”。 然而,尽管间谍世界如此具有魅力,但勒卡雷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虚假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生活的选择。间谍们无法解决这个冷漠颓废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正如情报总部圆场“Circus”的另一个译名“马戏团”说明的,他们的活动归根结底是一场表演,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幻觉。尽管在这一世界中的人们可以逃避现实,隐藏情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这种满足是虚假的,人们为了融入这个世界不得不将自己塑造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执着于事实,执着于现存的体制、价值、行为,他们认定现存的事态是唯一可能的事态,因此他们只能跟随现存制度及秩序已经决定在先的目标、规范和方向走下去。在马尔库塞看来,曾经18世纪欧洲的市民社会与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中都蕴含着变革的契机,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先进工业社会已经彻底化解掉了社会内部的这种变革力量,达到了高度的稳定与整合,最终这种社会在结构上、思想上都不再得见异端的力量。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们正是维系这种社会运转的齿轮与螺丝钉。《间谍的遗产》最终揭开了《柏林谍影》的真相,圆场“总管”(Control)视万物为刍狗的原则与史迈利、利马斯等人脆弱的人道主义立场之间的碰撞,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间谍的遗产》反映了勒卡雷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痛苦反省,但较之以往,这部作品中又透露出一种坦然面对废墟与黑暗的坚定气质,利马斯、威斯特贝以及史迈利等人的抉择与牺牲,既是他们试图逃离这个世界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捍卫这个世界而必须挺身承担的责任。尽管现存的这个世界充满痛苦和困难,但人们仍然必须在这里寻求救赎。勒卡雷笔下的圆场传奇——乔治·史迈利在全书结尾发表了一段让人惊讶的演讲:“我是个欧洲人,彼得。如果我有一项使命——如果说,我知道有什么是凌驾于我们与敌人之间那些事务之上的,那就是欧洲。倘若我冷血无情,那也是为了欧洲而冷血无情。如果说,我有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那就是想要引领欧洲走出黑暗,走向理性的新时代。我现在仍抱有这样的理想”。在现今世界,“欧洲”代表着什么呢?希腊的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启蒙主义的哲学理念?亦或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也许我们可以回顾欧盟创始人之一康德霍夫·卡利吉的名言:“朋友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欧洲是一种手段,没有目的”。 在《间谍的遗产》繁复迷人的叙述中,勒卡雷向我们表明,真相与现实在本质上是多元的,正像他爱好的德国古典作家席勒所说,感性与理性是难以调和的,甚至不可能调和,试图退回到单向度的世界中因而是徒劳一场,自称的现实主义往往都不现实,有时理想主义者反而是更好的现实主义者。勒卡雷通过对于间谍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分析,他至少指出了,只有接受现实的多元性,寻求自发与纪律、理智与情感、个人与集体的平衡,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恰当地融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实际有效地做出思考与行动。这个看似冷酷苦涩的结论也正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间谍的遗产”。
原载于《深港书评》
《间谍的遗产》读后感(四):这本或许就是史迈利系列的收官之作了
说起好看的间谍小说,少不了英国国宝级作家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这部1963年出版的作品令当时依然从事情报工作的文坛新人勒卡雷一举成名。2005年,《柏林谍影》荣获英国推理作家协会评出的“五十年最佳”,足证其经久不衰的魅力。
一代代读者为《柏林谍影》的故事洒泪唏嘘,勒卡雷本人也始终牵挂着那段谍报往事。在八十五岁,勒卡雷推出了该书的续篇——《间谍的遗产》,重回柏林的寒夜。
《间谍的遗产》简体中文版,世纪文景出品重回起点的史迈利传奇最终章
《间谍的遗产》追随史迈利爱将彼得·吉勒姆的视角展开。故事开篇细数吉勒姆错综复杂的家庭背景与加入情报局前后的往事,与勒卡雷1958年处女作《召唤死者》的第一章“乔治·史迈利简史”遥相呼应。这位挂靴老间谍在法国的安逸生活被一封密函打断,不得不连夜赶往伦敦的情报总部(又名“圆场”)报到。沧海桑田,圆场已从“造型浮夸的维多利亚风格红砖建筑”搬至“泰晤士河畔的某座怪诞堡垒”,圆场的旧人也已散落各处,踪影全无。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乔治·史迈利(右,加里·奥德曼饰)和彼得·吉勒姆(左,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饰)然而,过去对当下投下的阴影无可避免。在咄咄逼人的新一代圆场法务面前,已生华发的吉勒姆作为他们唯一能联系上的元老,作为关键证人(或者说,替罪羊)被推到一场一触即发的诉讼前。这一次,吉勒姆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昔日同僚的后裔——其父母有着老一代情报员无法忘记的名字:利玛斯与丽兹。
《柏林谍影》中失控的情报事件要追溯到近半个世纪前,但忠实情报官与爱人命陨柏林墙下的惨状依然历历在目。是什么导致了两人的死?是圆场故意弃子,还是另有隐情?故人的鲜血已在历史长河中锈迹斑斑,时代的伤痕却在个体的身上诉说着全新的伤痛。两个冷战遗孤意欲拿起法律的武器,向圆场提出巨额索赔。事件的关键人物史迈利下落不明,他的左右手吉勒姆必须在官方记录与私人记忆的交叠与错位之处,在见证了往昔血雨腥风、而今荣光不再的安全屋中,去试图回答:曾经的正义在当下语境中是否依然成立?老一代的行为是否可以得到下一代的理解?当真相撵上你时,是逞英雄,还是快逃?
《柏林谍影》,世纪文景出品以下内容皆真实可信,我将尽己所能,陈述我本人在代号为“横财”的英国欺诈行动中所饰角色的亲身经历。该行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针对东德情报局(斯塔西)展开并执行,行动导致我曾合作过的最杰出的英国特工死亡,该英国特工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无辜女性,亦随之香消玉殒。——《间谍的遗产》《间谍的遗产》是史迈利系列的第九本,也是大概率的收官之作,用勒卡雷的话说就是:“毕竟,史迈利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勒卡雷献给粉丝的礼物
1958年,二十六岁的大卫·康威尔在伦敦西区柯曾街莱肯菲尔德大楼三楼一间狭小的里屋中,创造出“约翰·勒卡雷”这个笔名,与之同时诞生的,还有乔治·史迈利这个英国人。史迈利“五短身材,臃肿体态,外加一副温顺脾性”,和007特工之类潇洒多金的间谍形象搭不上边(用安恩女士的话,便是“普通得令人心动”)。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日后深入人心,被誉为“战后小说中最丰满、聪明、吸引人”的角色之一,常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人物之林。
勒卡雷基于情报局的工作经历,虚构出一家情报机构,因其地处剑桥圆场而取名“圆场”(Circus)。在英文中,圆场也有“马戏团”之意。“还有什么比‘马戏团’更适合形容一群精于表演艺术的间谍呢?”勒卡雷说。
在任何一场审讯中,否认就是临界点。不要在意之前的谈话有多么礼貌客气。从否认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就一个秘密警察的普遍水平而言,否认可能会招致报复行为,因为秘密警察普遍都要比他们的审讯对象蠢一些。与此相对的,那些老练的审讯员一旦发现面前原本开着的门突然砰的一下关上了,并不会选择马上去进行正面击破。他们更愿意重整旗鼓,尝试从不同角度接近目标。——《间谍的遗产》《间谍的遗产》中,勒卡雷书迷熟悉的配方随处可见,让人耳熟能详、爱恨交织的人物也一一登场:吉勒姆、普莱多、米莉、海顿……普莱多在暗杀变节者后何去何从?史迈利与卡拉的纠葛如何落幕?书中 “彩蛋”甚多,只待有心人去发现。
交稿令人神伤,提笔满血复活
《柏林谍影》的出版令勒卡雷名声大噪,但他作为间谍的身份也随之暴露,好在文学造诣过硬,让他得以靠写字营生。迄今为止,勒卡雷已创作小说二十五部以及一部名为《鸽子隧道》的回忆录,文学影响力早已超出了类型小说的范畴。《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认为:“勒卡雷早已不是类型小说作家,他很可能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
约翰·勒卡雷与老当益壮的史迈利一样,勒卡雷对于观察、记录这个时代有着不竭的热情。对于他来说,交稿并不意味着如释重负,而是“深深的沮丧”。只有当“旧作中升起新鲜灵感,如凤凰从灰烬中重生”之时,生活方能“恢复正常”。因此,当八十八岁的勒卡雷与妻子在位于英格兰西南角的康沃尔郡面朝大海的宅子里“隔离”时,不难猜到勒卡雷在忙什么。
“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人,这仿佛是一场悬崖边缘的蜜月。我每天九点开工,若是不写点新东西,实在愧对了这么好的创作环境。写得非常顺利。”勒卡雷如是说。
作者介绍
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 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1963年,第三本小说《柏林谍影》问世,一举奠定文坛大师地位。迄今共著小说25部、回忆录1部,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
评论
最佳的勒卡雷。智慧、迷人。《柏林谍影》之后,鲜见勒卡雷一展这样的叙事才能,这部作品达到了令人激动的高度。——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
这本书读来乐趣多多,不仅因为本身写得好,是一部高水准的勒卡雷作品,更因为它让读者在漫长的54年后,终于可以补上失缺的部分,完成那幅拼图……勒卡雷虽然不再年轻,但他的创作好比美酒,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醇香。——《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