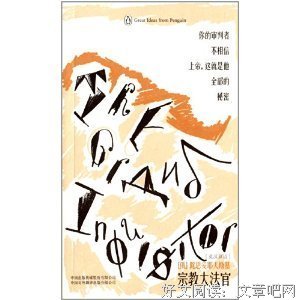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一本由罗赞诺夫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1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精选点评:
●若天主教是对基督教罗曼人的理解,新教是对基督教日耳曼人式的理解,东正教是对基督教斯拉夫人的理解,那么“爱国会”等一定是对基督教汉族式理解了。。。
●"你们没有听说过一位疯子的故事吗?他在天光亮的早上,点起一盏灯笼,跑到市场上去,不停地大叫着:'我要找上帝!我要找上帝!" "上帝到哪去了!"他叫道,"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是你们和我,把他杀死了。我们大家都是谋杀他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太痛苦,审视整个人类的灵魂深渊。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与俄国作家相比起来,欧洲的作家更像花花公子.你必须有所信,才能有所依靠,才能交付。可你要信什么?这世间真有所谓彼岸的至善吗?如果实现善要使用恶的手段,那这算是善吗?不用恶的手段如何铲除恶?连耶稣自己都说,我带来的不是和平,是战争。这是一个悖论。可我还是相信来人世间走一遭,若发现人生并非虚无那我就拥有了结果,若发现人生的真相是一无所有,那我就拥有过程,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后半本不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指向并停留在规范与秩序建构起的人类生活的界限后,界限后面是什么?佐西马长老说,那是个“另外的世界”,是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伊万感受到的世界。对没有违反秩序未闯入这个世界的人而言,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还没有被意识到或还是模糊的,对他们封闭着的这个世界的知识使罪犯超越了他们。如果别的小说家写一个从预定道路上偏离并灭亡的人物形象,那陀会让这些人物堕落犯罪,从行将死去的旧生命里获得再生:颤栗的被造物将一切外部法律内部律令通通抛弃,在混乱与痛苦中追问“为什么上帝创造的世界如此歪曲和不和谐”。死了的麦子要怎么结出新的?罪犯、地下室人的再生如何自身发生?作家在关键章节提出了疑问,却把答案永远带进了坟墓。罗赞诺夫的思考结果是,人被赋予意志的自由走出乐园,带着原罪成了黑暗与光明争斗的场所。
●罗赞诺夫的解读无非还是老套路,“人生在世,为自己的罪受罚,怎能说是苦呢”,源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一种近似补赎的观念。作为新宗教意识运动旗手的他在本篇中并未过于离经叛道,由他后来倒向了多神教,可知人短暂的一生充满何等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精神化的人根本不可能不爱神,否则灵魂会因极度的缺憾而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天主的正义不是人的正义,许多枯竭的人都可以看作灵命的枯竭,而宗教大法官是自由地否定了神,选择了卑弱化的人,他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但这并不可以指代天主教会,若然,便是一种轻浅的理解。有一种悲哀是人无论如何也要爱神,即使他叛逆无比,他内在的核心也在呼吁神,这是分裂的灵魂的痛苦。除了祷告,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但致命的是沮丧。不善用恩宠,可是会被褫夺的。
●遣词造句气势十足,可以掩盖分析立论上的不足。将普遍性与罗曼人/天主教会、个体性独特性与日耳曼人/新教联系,还有许多可阐发的余地。
●我看完了,但是我几乎完全没看透~~(滚去准备论文)
●候机室里一下子就看了1/3,从来没有这么有效率过~上海期间重读了一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在候机室里再次看这本书时,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一时间找不到感觉,几十页过后终于又跟上思路了。最后的几页,突然转入了一种奇怪的语境——罗曼人的基督教如何如何,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如何如何,而我们斯拉夫人则二者皆非却又可二者兼备blablabla,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抒发情怀,与宗教大法官全没什么关系。。。
●大概有一半是草草看过
●翻译不错,很顺畅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读后感(一):为什么我看不懂宗教
从开始总觉得作者在有意或无意地复杂化,试图把陀套进自己的理论中去。看了一半,终于发现了他的解释就是以无法辩驳的宗教说教让人无从下手,可惜愚钝的我最恶心那种“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陈词滥调。
卫道士罗赞诺夫在殚精竭虑试图应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质疑时显得力不从心,只能给出一些模棱两可十分牵强的解释,这些解释根本无需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多费口舌,重读原著就会发现这本书中所极力维护的宗教说辞是多么苍白无力。
的确很失望,不过还是希望在这本书里能看懂点什么。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读后感(二):搬家总是很累人
之前,我一直认为人应该有信仰,应该有经过长时间独立思索得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无论这些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站在怎样角度的都不重要,这世上原本也没有哪一种观念是绝对正确的);失去信仰的人的灵魂是孤独的,心灵是痛苦的;而没有信仰的人则根本没有灵魂,只是一具具“行尸走肉”。读完《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我忽然觉得自己醒悟了,或者说是应该醒悟了。或许,没有信仰的人才是幸福的,没有信仰的人的灵魂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是一大群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纪;没有信仰的人的心灵也不会痛苦,因为一切可能引起痛苦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都不再是问题。没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失去信仰的人是幸运的,不再信仰的人是该恭喜的,执迷不悟仍然保持信仰的人才是不幸的。我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是可笑的,因为心灵经常觉得痛苦的正是我自己。“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以为上帝之所以笑是因为生活中本就不缺少痛苦的人类还在自找苦吃。其实我也不能说是忽然醒悟了,这问题我以前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只是我一直不愿承认它的存在,一直不愿妥协罢。我不应该高估自己,更不应该低估别人。愿意思考的人与不愿思考的人本质上或许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反而,思考的人往往不能摆脱俯视不思考的人的心态;思考的人总是在不断地折磨自己的心灵,不断地忍受着思考带来的痛苦的煎熬,这种自虐性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变态。
我对宗教没有什么兴趣,对基督教的了解只是皮毛,打小儿接受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让我很难对唯心的思想产生好感。但没有好感并不意味着排斥,“虚怀若谷”的包容心我还是有的。我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还包括本书作者罗赞诺夫)对基督教(东正教)的坚定的信仰以及对信仰的力量的肯定,但他们对信仰丧失的忧虑让我觉得悲观。我还是很矛盾,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时而觉得人应该有信仰,时而又觉得有没有信仰或许并不重要。
“真理、善和自由是主要的和永久的理想……因为这些理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认为是愚蠢的,那么人的本性在其原初基础中也应该被认为是善良的和美好的。”
我个人相信人性本善,用有现代感的话讲,是遗传基因直接决定了人的本性,后天因素起间接作用。我觉得真正善良的人大都就是安于平凡生活的人,但是即便生活多么普通平淡,那颗有爱的心却不会变。爱身边的人,爱大自然,爱小动物,爱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这世界上真正的好人确实不多,人在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时大都心冷似铁;然而也总是有一些人的心像豆腐一样柔软易碎,或许早已碎成豆腐渣,还仍然把自己碎裂的心一块块地掏出来献给别人。(这句是在模仿乔瑜的小说《大生活》中的一句)这世界就是如此架构的,像金字塔那样,他们才是站在人类世界的顶峰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讲,在遇到与自己的利益无关的事情时,大多数人可以说还是好人。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读后感(三):“你的罪恶鲜红必将变得洁白如雪”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
1
作为俄罗斯文化史上"白银时代"最著名的代表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俄罗斯"新宗教意识"(或新基督教)的创始人,罗赞诺夫无疑是一个独特的、个性极强的思想家。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也不同于同时代的时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这种将陀氏思想条分缕析归纳的大部头专著,而是通过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论宗教大法官”一个重要章节,进而来诠释陀氏的整个思想,可谓非哲人不能为。
作者认为《论宗教大法官》可以看做是一部独立作品,并且完全可视作是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乃至所有作品的核心。(p4)借用马克思评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真正伟大秘密之所在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经”.
近代俄罗斯是苦难深重的,饱经苦难的大地孕育出了一批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前期思想界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洛斯基这一批思想家们都面临着社会精神危机,追问信仰的合理性。在所有这些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早的发问者----他一生都被这一问题所折磨,直至濒临疯狂。 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他将这一问题提升到最极端最尖锐的程度。如果基督教是以最后的天国、最终的和谐来补偿人间的恶与苦难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问的是:为什么人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付出这样的代价又是否值得?
罗赞诺夫认为,“在这个《传说》里,正是这个恶以无可比拟的伟大力量被表达出来了。”(p63)“无论美的世界有多么吸引人,还有某种比它更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堕落,生活的奇怪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深刻地淹没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和谐的音符。人类几千年的命运就发生在这个不和谐的各种形式中,而任何其他人的视线都没有如陀氏般如此深刻地指向这种不和谐的原因。”(P29)陀氏作品的病态基调以及不和谐的形式结构之中恰恰蕴含着其对于世界上的苦难的深刻思考与追问,“对他来说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是:人的痛苦及其与生命的一般意义的联系”。(p36)
他带着全部兴趣关注恶,这恶隐藏在历史地产生的生活的一般建制之中;他对企图通过个别的改变而改善什么东西的一切希望的厌恶和蔑视就由此而来,他对进步党派和西方派的敌视就由此而来。由于只观察一般的东西,他便从现实直接过渡到思想中的极限,他在这里找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p36)而“历史的根本之恶就在于其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不正确的关系”。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但这个批判第一次而且是最详细的表述在《地下室手记》里----那位“地下室人”是个走进自己深处的人,他痛恨生活,恶毒地批判理性的乌托邦分子的思想,其依据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确知识,他从对自己和历史的孤独和长期的观察中获得了这个知识:就自己的完整性来说,人是非理性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的彻底解释是理性所无法达到的,它也无法实现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无论思想的工作是多么的顽强,它永远也不能覆盖整个现实,它将适合虚假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在人身上隐藏着创造的行为,正是这个行为把生命带给他,也给他带来痛苦和喜悦。
2
对最终理想的可能性的批判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完成的任务的前一半。展示了人的本性的非理性,因此也是终极目的的虚幻性之后,他出来保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而是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两大中心问题:终极目的的虚幻性、个性的绝对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宗教思想都与此有关。“在其对人的本性的公正分析的结果和斗争任务所需要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巧合,这个巧合是出色的和幸福的。前者在展示了人的本质的非理性之后,揭示了其中神秘的东西的存在,这个神秘的东西无疑在创造的行为自身里向他显现过。这一点与如下的必要性完全一致----即必须把人看作是比我们关于他所想的无比高尚的东西,看作是宗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东西。在承认了人的神秘的来源和神秘的本性之后,我们在他身上发现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他具有自己的造物主的反光,其身上有上帝的面孔,它不会暗淡,也不会服从任何东西,但却是珍贵的和应该受保护的。”因此,只有在宗教里才能显现人的个性的意义。在法律中,个性只是功能,是约定的义务都针对它的那个必要的中心,是财产的归属性等等,个性的意义在这里没有被显现出来;在政治经济学里个性完全消失:这里只有劳动力,针对劳动力来说,人是完全不需要的附属物,仅仅具有相对性。宗教给这个相对性,及动摇和犹豫都设置了界限:每个活生生的个性都是绝对的,是上帝的形象,是不可侵犯的。
3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人类心灵天才的分析家在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向我们展示了新生命从行将死去的旧生命里的再生。根据无法解释和神秘的规律,整个自然界都将获得这样的再生;如果死不发生,那么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作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的题词,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解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 12:24)(p61)“堕落,死亡,瓦解——这只是新的﹑更好的生命的保证。我们就应该这样看待历史;在看待我们周围生命中的瓦解因素时,我们应该习惯于这个观点:只有这个观点才能拯救我们于绝望之中,当对任何信仰而言仿佛已经出现了终结时,只有这个观点才能给人以最坚定的信仰。只有它才符合现实的和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支配时间的流程),而不是我们理性的微弱地闪烁的光,也不是我们的恐惧和忧虑,我们正是用这些东西填充历史,但根本不是在支配历史。”-----“大法官”所宣布的人的本性与历史进程的“真相”就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法官”的传说》中表现了对人的弱点的深刻意识和对历史上宗教的深深迷惑的话,那么,罗赞诺夫在他对这一传说的解释中则重新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宗教的价值并让自己的心安息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之中。
“真理﹑善和自由是主要的和永久的理想,人的本性在其主要的因素中——理性﹑情感和意志,就指向对这些理想的实现。在这些理想和人的原初组织构造之间有一种一致性,由于这个一致性人的本性不可遏止地追求这些理想。因为这些理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认为是愚蠢的,那么人的本性在其原初基础中也应该被认为是善良的和美好的。”( p149)号召所有的人在爱里紧密结合,让人自由地效仿最好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全部意义最深刻地符合人的原初本性,透过千年的罪恶重新唤起人的本性,这罪恶用沉重的和可恨的桎梏压迫者人的本性。(p150)
4
伊凡•卡拉马佐夫是以个性的名义否定了永恒生命与最后审判,而“大法官”则是借所谓人类的本性来抹杀自由的追求。的确,自由与其说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一件轻松的礼物,而不如说是一项沉重的使命。所以,“大法官”断言:只有少数选民会乐意接受自由,而大多数人会弃之如敝履。“我们修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秘密和权威之上。人们也很喜欢,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样被人带领着,从他们的心上终于卸下了如此可怕的、给他们带来了众多痛苦的恩赐。”《大法官的传说》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弱点及其表现的讽刺性寓言性描述:人类要么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要么滥用了自己的自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前一种情形是中世纪天主教所一手导演的。中世纪天主教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而接受了魔鬼的诱惑,依靠奇迹、秘密、权威来进行统治。后一种景象则是近代以来反宗教运动的成果。但这样概括的两幅图景也许并不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全部事实。所以,罗赞诺夫要接着说:“在看见自己时代的堕落和卑鄙并使愤怒成为合法的之后:谁能诽谤整个人类历史,谁能否定在自己的整体上这个历史是神圣的和高尚的显现,如果不是显现人的智慧(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也是显现对真理的无私的渴望和实现某种真理的无力的愿望?”
在肯定了历史整体上的神圣性和高尚性之后,罗赞诺夫进而肯定人本性原初的纯洁性,“真理,善和自由是主要的永久的理想,人的本性在其主要因素中——理性、情感和意志,就指向这些理想的实现。”在认知方面,真理是在先的,谎言是在后的;“讳言的来源在历史里,真理的来源则在人身上。”在情感方面,“善是人的情感迷恋的第一个东西,恶则总是次要的和来自外部的东西。”在意志方面,人倾向于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就是人的意志与人所追求的伟大理想处于一致之中,而决不是任意妄为。如果这些理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认为是愚蠢的,那么人的本性在其原初基础中也应该被认为是善良的和美好的。对本性的坚持和理想的追求是否过于艰辛与沉重呢?不是,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30)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尘世一切的放弃呢?也不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至此,“大法官”所宣布的人的本性与历史进程的“真相”就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法官”的传说》中表现了对人的弱点的深刻意识和对历史上宗教的深深迷惑的话,那么,罗赞诺夫在他对这一传说的解释中则重新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宗教的价值并让自己的心安息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之中。
5
故事还没有完。
罗赞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一起,反抗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在人的意识里,下面这两个东西哪一个在先——是谎言在真理之前,还是真理在谎言之前?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它的解决还将为整个人的本性问题的必然解决奠定基础。我们在这里不能动摇:谎言自身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对真理的破坏,明显的是,在被破坏之前,真理应该先存在。这样,真理是原生的,一开始就产生了的东西;谎言则是带来的,后来出现的东西。谎言的来源在历史里,真理的来源则在人身上。”正如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所揭示的:历史理性最终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罗赞诺夫则反其道而行之,捍卫个人的价值。
如此一来,罗赞诺夫的这段看似惊人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对待我们的历史生活的态度方面,传说是最具毒性的一滴毒液,它终于从我们已经走了两个世纪的精神发展阶段中流了出来,分离了出来。”(p169)当代的“宗教大法官”就是启蒙知识分子们,他们不再像苏格拉底般站在被告席上,而是成为了人类的立法者与“监护者”。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表达的正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要批判的。
人性中的弱点以惊人的方式表现在这个《传说》里。而阿廖沙,这个“庞大的腐烂着的生命种子里的一个小萌芽的真正化身”,则仿佛是被恶的强大的宣传,被“荒漠里聪明的、死亡的和破坏的魂灵”的坦白给伤害和压垮了。他惊慌失措,找不到生命的支柱;然而,“他却在我们所无法认识的、神秘的生命之美里找到了这个反对恶的魂灵的支柱 现在完全是孤独一人,只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罪,在自己的心灵上还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克服这个黑暗,帮助这个光明——这就是人在自己人间旅途中所能做的一切,是他应该做的一切,以便安慰自己惊慌的良心,这良心如此地沉重,如此地病态,它已经无法再忍受自己的痛苦了。清楚地认识,这光明是从哪里来,这黑暗是从哪里来,这最能用希望巩固人,因为他并不是注定要永远成为光明与黑暗争斗的场所。”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读后感(四):译文商榷
14
《见习修士》当为莱蒙托夫的《童僧》(Мцырь)。
20
涅塔奇卡 · 涅茨万诺夫娜(Неточка Незвановна)当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Неточка Незванова)(误将姓作父称,括号后的原文亦引错)。
奥斯杰里茨克(Аустерлицк)田野当为奥斯特里茨战场(Аустерлицкое поле),原文为形容词形式,Аустерлицк系错误地推导名词形式所致。
28
《漫画潮雪》“漫画”当为“漫话”。
29
埃琉西斯秘密(Элевзинские таинства),埃琉西斯农庆(Элевзинии)两者都应为“厄琉西斯秘仪”。
31
魏特察贝里(Вайтчапель)当为伦敦的“白教堂区”(White Chapel)。
34
盖—马尔凯特(Гай—Маркет)当为伦敦的“干草市场”(Haymarket)。
44
那么,这样的规定将(不一一译者所加)是首要的 ,而是派生的原文:... значение ее не выяснено и не обосновано здесь, и если она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то подобн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ичным, произвольным
“派生的”,当为“随意的”,此处显然是将произвольный误看成производный使然(不排除是印刷错误),这样一来,前面的первичный就应解作“初级的,原始的”,也就不必自行加个“不”上去了。全句应为:“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原始的、随意的”。
50
如果在这部小说里有为犯罪证明的辩证法证明,оправдывающая,即justifying,译作“证明”显然不确切,作“正名”倒是接近了。全书中对оправдать一词的把握多少有些问题。比如P145,“保卫自己一一在这里仿佛就意味着感觉不到形象的神圣性,仅仅是一个证明的企图一一就将丧失对神圣形象的一切权利”同理。P170,“被证明的人”,оправданные,其实指的是P114—115,“我们引用约翰启示录,就是关于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被拣选的人和义人是很少的’”中的“义人”。这句话在启示录中其实并没有,俄语圣经中也未使用过оправданный一词(有动词形式,在和合本中一般译作“以…为义”)。不过总的来说用“义人”来译不算有问题。
"颤栗的被造物",在这里有两次这样称呼一个人,无论是他自己犯罪的微不足道,还是其无益的美德,正好配得上这个称呼,不多也不少。原文:«Дрожащая тварь»,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здесь раза два человек, ни мелочностью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своих, ни своими бесполезными добродетелями н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ни больше этого, ни меньше.
“配得上”应为“配不上”。全书译文有许多理解性的错误似乎都和多一个“不”或少一个“不”字有关,不排除是选用的版本不佳,印刷错误所致。
“颤栗的被造物”涉及《罪与罚》中的一个核心公式:“我是颤抖的造物,还是我有权利”。Тварь一词从词源可看出,本义是“被造物”,但这一义项现已很少使用,通常使用转义“畜生,混蛋”(cf. 沪语“众生”)。《罪与罚》的这一公式中用的恰好是本义(具体分析此处不展开),这里张老师译对了,倒是小说译者多不能译对(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语境很复杂)。可惜张老师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之后P101的同一词组就译成了“战栗的人”。
51
他所受的教育全面而广博,没有祖上传下的地产,除了艺术之外对任何东西都报以冷淡的态度……“没有祖上传下的地产”,отсутствие первородной крепости,应为“缺乏根深蒂固的坚定”,要译成现在这样真的要绕好几道弯,懂俄语的读者可以思考一下……
56
已成为圣徒的我们的叙利亚的伊萨克Иже во святых отца нашего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我们的”之后漏了“神父”。“叙利亚的伊萨克”倒是译对了,非常不容易,看了一下小说译本,只有荣本译对,其余皆直接音译“伊萨克·西林”。
最后还有他从自己的袜子里掏出的一叠纸熟悉小说的话应该知道这里的“一叠纸”(пачка бумажек)应该是“一叠钞票”。
68
可爱的东西一一已经不再死亡Любимое - уже умирает,“可爱的已垂死”,又是“不”的问题。
70
要合理地 、真诚地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不违反自己的知识,而只是遵照它们,按照造物主把它们安排在他身上的那个样子, 宗教自身教导的就是这个“自己的知识”,сво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своения,“自己的掌握能力”。
在这里,上帝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反驳,这种反驳是根本无法制止的“无法制止的”,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ющее,主动态,所以指的并非这种反驳无法(被)制止,而是这种反驳无法制止他者(这里应该是指理性)。
71
从人的思维的这个相对性出发, 伊万拒绝评断关于这样一种东西的宗教断言是否正确,它是一切存 在的根源和一切思维的支配者和立法者。Иван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судить, правы или нет утвер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о Том, Кто есть источник всякого бытия и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 вся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原文大写,指上帝,此处译文中却被降格成了“东西”和“它”……
72
在这个创造的秩序中有一种与被造物自身的被造本性不相容的东西“被造本性”,как именно сама она сотворена,不确,全句应为“在这个创造的秩序中有一种恰恰与如何被造所不相容的东西”。
73
任何人也不痛恨自己的肉体,每个人都喂养它 ,温暖它此句为圣经引文:“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弗5:29)。
出于一种惊恐的忙乱不确切,от какой-то смятенной торопливости,“出于某种慌乱的仓促”。
75
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和野蛮人,而且是在进行忙乱的起义时,仍然抽出时间“进行忙乱的起义”,занятые хлопотливым восстанием,“忙于麻烦的起义”,如果熟悉小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肯定知道土耳其人并不是在忙着“进行起义”,而是忙着镇压起义。
76
就像 《哈姆雷特》的波罗尼(Полоний)一样波罗尼,当为“波洛涅斯”。
78
想尽办法违法这些规律“违法”当为“违反”。
80
受人尊敬的、有教养的和宦官家的父母不知为什么痛恨自己的小孩好吧,宦官和官宦是有区别的……
斯帕索维奇先生的维护性的言论……“维护性的言论”,защитительная речь,“辩护词”。
84
即宗教的来源被认为是神秘的,只是在这样的层次上,人的心灵自身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才是 神秘的,仅此而已。Т. е. их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ризнается мисическим только лишь в той степени, в какой мисична самая душа человека, но не более.
句法理解有些问题。应为:“也就是说,人的心灵本身有多神秘,宗教的来源才会被认为有多神秘,不会更多”(感觉我的译法也不是最好,期待更好的译法)。
86
阿辽沙,不是我不理解(原文如此,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此处的"理解"应为"接受")上帝权威的版本并没有此问题:Не Бога я не принимаю, Алеша。“接受”(принимаю)和“理解”(понимаю)之别,多半又是印刷错误所致。
88
这就是堕落的行为:它解释的是,什么存在;还有救赎的行为:它在人所是的东西里巩固人原文:Это - акт грехопадения: он объяснет то, чтО есть; акт искупления: он укрепля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首先акт在本书中的意思显然不像“动作”,姑且译作“现象”,其次句法理解错了。全句应为:“这是堕落[指偷食禁果——译按]现象:它解释了既有的;救赎现象:它于既有的之中巩固人”。
90
一旦出现这个奖赏 ,消除痛苦的要求就将消失,痛苦所带来的伤痛将成为无法忍受的 。“消除痛苦的要求就将消失”,原文исчезает утоление,“(痛苦的)缓和就将消失”,原文并无“要求”。
奖赏完全能取代以前的痛苦原文:оно вовсе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а место прежней горечи,完全不能取代。
93
假定他残害了一个小孩残害,原文为растлил,奸污。
95
存在的只是幻想,人必须靠幻想才能成为被欺骗的,以便不论怎样在人间安排好原文:... есть лишь иллюзия, которою необходимо человеку быть обманутым, чтобы хоть как-нибудь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земле. 全句应为:……有的只是幻想,人必须被幻想欺骗,才能凑合着在大地上安顿下来。
98及以下各处
全书中的“和撒那”都被译作“奥莎那”并附原文,非常费解。要说张老师不知道“和撒那”,实在不太可能,但这样处理又实在多此一举(正教似乎也没有将“和撒那”译成“奥莎那”的习惯)。同样匪夷所思的还有所有的马尔萨斯都被译成“马里图斯(Мальтус,即马尔萨斯)”,这就好比某个英语译者将列宁都译为“莱宁(Lenin,即列宁)”,可张老师自己也没把黑格尔译成“盖盖利(Гегель,即黑格尔)”啊。
116
为数不多的人需要“自由的空闲时间”,仿佛他们能够“制造科学和艺术” (贫穷的人和生活在经常性的劳动中的人确实不能创造它们)。括号里面,又是“不”的问题,这次是多了一个“不”。原文:их истинно возделывают люди бедные и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труде живущие——“它们确实是贫穷和活在恒常劳作中的人耕耘出来的”。
通过艰难获得拯救,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过分的;另一方面,在为自己和他们担忧时,杀害他们。原文:... спасаются через трудное, что, будучи чрезмерно для многих, и, между тем, ломая о себя и их, - губит их. “(一部分人)通过对许多人而言过度的难来获救,与此同时,通过用自己来摧折他们(直译:通过把他们撞自己来折断他们),从而毁掉他们。
不过这些其余的人并不像没有受过教育的、堕落的大众那样,聚集在这儿十个人的周围。原文:... около которых остальные толпятся менее, чем только непросвещенною массою - массою равращенною. 其他人在他们周围聚集时,已不至于仅仅作为没受过教育的大众——(而是作为)被腐化的大众。
119
天主数文明在“compel intrare”——“迫使他们 ( 被召的人)进来”这个说法(在未婚夫娶亲宴席上,在《关子被召的和没有被召的寓言》里)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存在法律……原文: ... На выражении "compelle intrare" - "понудь их (позванных) войти" (на брачный пир жениха, в "Притче о званых и незваных") основывала свое право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инквизиция.
“天主教文明”应为“天主教异端裁判所”。“Compel intrare”应为“compelle intrare”,典出路14:23,和合本作“勉强人进来”。“关子被召的和没有被召的寓言”外应用引号而非书名号。此外句法上也有不少问题。全句应为:“天主教异端裁判所将'compelle intrare'——‘勉强(被召的)人进来’(来未婚夫娶亲的宴席,典出“被召者和未被召者的比喻”)这一表述作为其存在之根据”。
124
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讲话》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句话,以及《有一次在荒漠上漫步》等诗……原文:... см.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б этом духе у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Речи о Пушкине", по поводу стихов: "Однажды странствуя среди пустыни дикой" и проч.
《“有一次在荒漠上漫步……”》(《朝圣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演讲中提及的普希金的一首诗,而译者似乎将其理解成了陀氏的作品。全句应为:“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中关于《“有一次在荒漠上漫步……”》一诗等内容的几句话。”
135
乔·斯·穆勒应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43
他如此明显地站在阿辽沙的一边原文:который так ясно стоит за ним,只说“站在他身后”,但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他”显然是指伊万而非阿廖沙。
我们上边指出过一封个人的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完小说前的很长时间以前写的,这封信里有一个坦白,在死前的很长时间以前,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下的一句话 :“我的奥莎那(Осанна)穿过考验的熔炉来到了。”原文:Признание в частном письме, которое делает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задолго до написания романа и которое мы указали выше, и слова, написанные им в своей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е незадолго до своей смерти: «моя осанна сквозь горнило испытаний прошла»...显然,信和笔记本是两回事情,被译者混淆了。全句应为:“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那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完长篇小说前很久所写的私信中的自白,以及他在自己死前不久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话:‘我的和撒那穿过考验的熔炉来到了’。”
162
新教的无限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мистицизм,应为“神秘主义”。
170
回到对无法认识者的宣传所获得的稳定结果“宣传,исповедание,应为“信仰”(估计是把исповедание和проповедание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