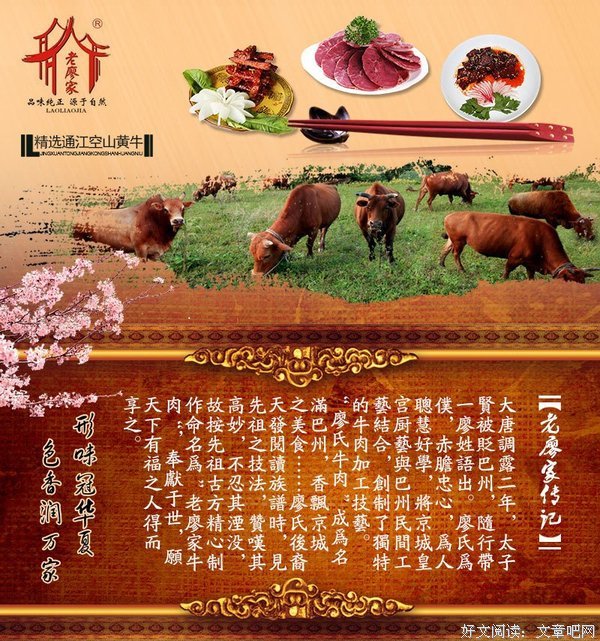
老廖先生
提起老廖先生的医术,那可是四方闻名,无人不晓的。本地人无论得了什么病,身上那不舒服,总是“找廖先生瞧瞧”,“送廖先生看看”,似乎那远近的公家医院是根本不值一提的。
廖先生看病,从来没有人指摘。就是经过他看过后死掉的,也是说:“廖先生跟前都治不好,肯定没办法了。”廖先生之外,再没有起死回生的医生了。
就凭着,廖先生解放时虽戴了顶“地主”的帽子,可谁也没有为难过它,他家也从来没有拮据过。三年自然灾害,死人到处是,廖先生家居然没有损失一个人;文化大革命,揪这个斗那个,他家除二儿子因“地主”帽子,大学分配不好外, 全家也都平安度过。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求他的时候。
廖先生子孙繁庶:三子二女。孙儿辈中,除外孙外,尚有五男五女。重孙大的也上小学了。年已九十的廖先生,凭着带儿挈孙的功劳,在全家赢得了一致尊敬的地位。
九十了,本来一直很健壮的身子骨,去年一下子就觉得垮了下来。他知道这是真的老了。老了就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九十多的人了,哪一天伸腿都不算憾事。当然,人不可能一点憾事都没有,老先生到现在还有一桩事心里很不安呢。
这就是他的医术到现在还没有“传人”。
廖家的儿孙经常说:“只要记住父亲(爷爷)的那些方子,就可以远近扬名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继承廖先生的衣钵。大儿子和小儿子刚学了点皮毛, 就被区县医院要去,紧接着就是成家,就是养家糊口,就是经营安逸的家庭,在没有功夫也没有必要深学下去了;二儿子是他指定去上大学的,以后也是公家的人了,不需要他这高超的本领去养家糊口;女儿是人家的人,用不着担心她们的饭碗。
儿辈是没指望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了。当然,外人谁也别想得到真传,这是廖家的规矩。否则,宁可把他带进棺材去。老廖先生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
首先考虑的是长孙。长孙呢,对此却不屑一顾。“爷爷,赚大钱不能指靠它, 靠它一生发不起来。”大孙儿不愿在穷乡旮旯过一辈子,大城市大码头的繁华富庶强烈吸引着他。只有赚大钱才能达到这一切,他当然对学医没有兴趣。老廖先生一生不想强迫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孙。
于是另找目标。
“二呀,”爷爷喊着二孙子,“爷爷把它传给你。学好它,你会受用一辈子的。”二孙子倒也不拒绝,只是,他跟念过音乐学院的二伯伯学拉二胡风琴之类的一学就会,《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戏一唱到头,可是对学医简直是一窍不通。廖先生教他记药方子,字倒是写得工工整整的,可要他配药,常常连药名也分辨不清。弄得老廖先生不断地唉声叹气。愁着苦脸,最后不得不放弃。倒是二子记下的方子不知怎么给姑姑家的表兄搞去后,表兄虽不像廖老先生那样名闻遐迩,倒也在他那一地方小有名气的。
廖老先生忽然发现,最小的孙子虽然才十岁,却是绝顶的聪明。背唐诗,不过三遍,便能滔滔背出;很复杂的帐,也能够很快心算出来。特别让廖老先生高兴的是,由于长时间在自己身边玩,他不但记住了那些众多的药名,还能记住那些复杂的配方,有时还能给老迈的自己提醒几句呢。嗯,小孙子是块好料,是个能继承自己衣钵的人才。对,就选定他了!
“他爷爷,孙子还小,最要紧的还是给他念书呢。”小孙子他妈妈笑着提醒老廖先生。
“这倒也对,不识字干什么都不行。现时什么不讲究个知识?学不来知识,什么都是扯淡,当然也学不好医。“那就再等几年吧,让他念完了书再教他。”于是,在小孙子念书期间,他绝口不提这事,好使他更专心的去学习呀。
小孙子不负重望。初中念完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重点高中。廖先生想,念高中好,多学点知识不错。至于那事,再过一段时间,等他念完了高中再说吧。一晃,高中又毕业了,小孙子只以一分之差落选,未能升上大学。老廖先生说:“没考上就没考上吧,学好医,也够你享用一辈子的。”可小孙子不同意,“今年我要是稍微留心一点就不会落选,明年我绝不放过这个机会!”
好,好。廖先生心里话,强扭的瓜不甜。你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再干一年吧。
可廖先生却再也等不起了。近百岁的高龄了呀!这一年的春上,廖先生夜里上茅房,忽然犯了高血压。好在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可毕竟岁数大了,抵抗力跟不上来,只能躺在床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儿孙们陆陆续续地来看望他,他很少有反应。只有小孙子来到他床前时,他的嘴蠕动了几下,手想抬起来。但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什么也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