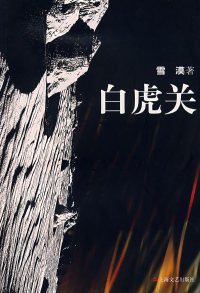
《白虎关》是一本由雪漠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5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唯有精神,才能薪火相承。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与他人无关。即使在看似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是绝望,是希望,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有时候,困难其实是另一种动力,你要享受它,享受厄运,享受所有命运的留难。当你静静的观察、品味并享受它们时,它们就成了你灵魂的营养。
●乡土气息浓郁。对人生的意义,诠释的比较到位。人物个性鲜明,但各个人物鲜有自己语言,略微不足。俗语、谚语的运用,与农村的时代变迁,交相呼应,颇为恰当。正是——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看到最后,一声长叹,赞其精彩
●我很少看刻画农民的作品,在读之前以为这部作品不过也只能让我感叹一番农民的愚昧无知落后迷信。虽然我在这书中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愚昧,可是就如雪漠所说的,我们活着的观念不一样,而这种观念缺少沟通,就会造成东部人看西部人的一种落差,把他们看作是愚昧的了,恰好,西部人也觉得东部人很愚昧。这段话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想象的苦难强加于别人的生活之中,单纯怜悯他们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而没有换位思考加以理解。也许这就是人和人的矛盾吧。整部作品读下来,我边读边把他们生活的场景,所说的话,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于是便能更好地感受到了西部农民生活的纯粹以及他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这种精神境界与格局,并非单纯物质的满足可以实现的。
●2017.12.02下午四点,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放下kindle,思考了一下,心想,我一定要写一篇书评。
●不如大漠祭。
●比之前的两本多了一份灵魂的拷问。人生中总要经历一些“大事”,在现实残酷的挤压下,我们不得不过人生的一道道坎。这部小说给我震撼无疑是巨大的。
●写的最好的人物竟然是猛子妈,剩下两颗星给猛子和月儿。
《白虎关》读后感(一):有感于雪漠小说《白虎关》中的《引子》【作者:融宇】
雪漠一开笔就用具有诱惑力的语言,让读者对两个女性人物拥有牵挂的心情,使你不得不把这部小说完整的读下去,比如:他在《引子》的开头就写“莹儿和兰兰死也想不到,踏入沙漠不久,她们就会遇上豺狗子。”同时你还会从中读到雪漠平时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关于豺狗子的可怕之处,他在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关于它们的可怕,你可以去采访那些叫豺狗子抽过肠子的动物,不过,它们大多都已进了阴司。”从短短的《引子》中,读者还会从中获知雪漠平时涉猎了很多古典关于玄学方面的文学书籍,比如他在小说《引子》中这样写到:“按照老祖宗的说法,动物的中阴身最多四十九天,四十九天之后,多笨的动物都会找到归宿的……”
在雪漠写的关于玄学方面的文学内容,使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的关于宋朝忠臣岳飞和大奸臣秦桧的故事,说岳飞和秦桧在轮回中,它们和很多各路修行者都在西天如来佛祖那里听经,那时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而秦桧是放屁虫,佛最讲究的是平等和因果,放屁虫(秦桧)因为愚痴而不懂礼貌,所以就在佛祖讲经的时候放里一个又响又臭的屁,于是蹲在房梁上听经的大鹏金翅鸟(岳飞)就飞身下来将坐在地上听经的放屁虫(秦桧)啄死,并且一边啄还一边说:“大家都在听经,你却在这里放屁,一点也没有礼貌。”正因为大鹏金翅鸟(岳飞)将坐放屁虫(秦桧)啄死的因缘,所以佛祖让他们来人间演义一段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的果报。
关于写玄学方面的文学内容,无论真实与否,总是有看头的,因为作者的很多思想都会从玄学的文字中表现出来,使读者进入一个更深刻且更宽阔的思想领域中,并从中得到更深更宽的思考。雪漠开篇就写到豺狗子,并从豺狗子联想到小人,说明小人尽管“小”,但却是最可怕的,说明小人的厉害程度是伤害你的内脏且会致于人死地。比如他在《引子》中这样写到:“可见那可怕跟形体无关。正象人类中最可怕的那类其实跟他的形体和力量也无关,只要其心灵有了能叫你足够害怕的东西,你就得怕他。比如,我就害怕那些小人们。”
关于《引子》中回答的两个弱女子为啥要到豺狗子的地方去,他回答得很简单,那就是:“两个女子各有自己的生命‘盼头’,现实却总是在强暴她们。她们不甘被强暴。”其实我觉得雪漠写的这两个生活在底层弱女子,不仅仅指的是两个不甘被强暴弱女子,而是指很多个不甘被强暴弱女子,就从这个简短的《引子》中,我们就可以读到雪漠用一种善良悲悯的大胸怀来写作的。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些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白虎关》读后感(二):《白虎关》给我的困惑
看了几天,终于把这本三十六章的书看完了。
先说一下书的优点:
1. 很佩服作者的文笔。因为看书的时候,感觉很流畅,一点不费力,我觉得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功力的。
2. 大量的“土话”很有意思,贴近生活,让人拍手称赞啊。
3. 书中也有大量对于西部沙漠的精彩描写,尤其是莹儿和兰兰在沙漠中的一段,细节之多,非常吸引人,不是有切身的经历感觉写不出来。
4. 我比较认同作者的价值观(之后会提一下)。
不过看到最后,感觉有点困惑,对于几个女性人物的处理感觉有点愤怒,写在这里,希望之后看到的人能和我交流一下啊。
困惑是关于书中的几个女性人物:
莹儿:一心爱着灵官,中间经历了盐场的头儿和大牛的追求,但是灵官是心中的真爱,大量的描写都写了莹儿对灵官的思念,最后,因为还是被迫嫁给了屠夫赵三,选择自杀(虽然书中结局未直接说明莹儿的结局。)不管长的多美,还是为爱情守贞。(虽然自己也是和小叔子偷情)暂且认为这里代表了作者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兰兰:被丈夫殴打家暴,孩子被丈夫杀死,在金刚亥母那里寻找生命的力量和解脱。
月儿:真惨,进城想改变在农村的生活,但是被老板骗了,就做“错”这一件事,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但是得了梅毒。而最后真爱上了猛子,爱得以“升华”。但是反观她的丈夫猛子,之前偷情了人家的老婆,并在书最开始就说和别的女人做爱了,也是婚前性行为,经历了这么多“错”事,但是毫发无伤,依旧健康,得到了月儿投入的爱情。
双福老婆秀秀:开始时候看事情挺明白潇洒的,说要看着双福毁灭,和其他女性角色比明事理,不软弱。秀秀开始自己也偷情,但是最后双福因为强奸被关进大牢,秀秀却为双福守起贞操来,这里我真的困惑了??
感觉这本书,作者或许在无意中带入了大量男性主义的立场,除了兰兰正常点以外,别的女性都有点惨。当然,在中国的农村,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在很多地方依旧存在,书中也表达出男性有多个女人就是“有本事”,女性就贬值等等。我暂且把这些当成是书中角色的观点。我不想讨论这些,因为这在观点在农村地区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可单从可以安排的人物设置来看,作者是不是有点太男性主义了?
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书中的包括作者一贯的观点,比如作者在后记中说的:
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岁月的飓风正在吹走我们的肉体,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很快地消融于巨大的虚空里。你可能留下的,也许只是你独有的那点儿精神。所以,每一个有灵魂和信仰的个体,都应当明确地告诉心外的花花世界:我不在乎你。等等大量的作者的价值观,我是很认同的,也会继续读他的其他作品。但是我觉得我上面说的可能来自于作者的一些局限,如果我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并跟我讨论一下,谢谢!
《白虎关》读后感(三):写给雪漠
我跟甘肃作家雪漠的缘分始于06年某个春天。那天,妈妈随手买回了一本《小说界》,主打长篇便是雪漠的《凉州令》。翻开读上几页,我的思绪便随着雪漠的笔风,飞向了他笔下的西部农村,那个生活着兰兰莹儿灵官的沙漠边缘的沙湾村。由大漠三部曲最后一曲《白虎关》删减而来,《凉州令》聚焦的是老顺一家因被换亲的女儿忍不了家庭暴力回了娘家,亲家叫刚刚新寡的女儿改嫁而不再平淡的平淡生活。往细里说,具体情节也不过是两家人分别在莹儿妈与灵官妈这两个愚昧农妇带领下的数次口头、肢体冲突,以及与小叔子灵官深陷不伦之恋的莹儿对远走高飞的前者的思念心理。如何平衡这截然相反的粗鄙世俗与缠绵真挚,如何用同一支笔写出乡野农妇们毫无廉耻之心的脏话谩骂以及莹儿对情郎各种诗意的抒情,非常非常考验作者的水平。幸好,寄情于大西北的苍茫大地,雪漠成功地描绘出了妈妈们咬牙切齿的那么多对决与莹儿们不眠难安的无数个日与夜,鲜活得就好像腾格里的风沙飘到了我的眼前。正是这份鲜活,才让莹儿兰兰这些不幸的西北女人在我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了那么多年。 莹儿是不幸的。作为女儿,被父母作为工具,拿去换亲给哥哥;作为妻子,丈夫憨头老实腼腆,不能人道,最后还因肝癌英年早逝;作为母亲,因为被娘家强迫改嫁,只能与儿子分离;作为最本真的女人,真正的爱人灵官因与嫂子偷情而对兄长心怀愧疚,在憨头去世的打击下离家出走,撇下了情深似海的她。第二女主角兰兰,在婚姻子女爱情上同样多有不幸,最终选择堕入空门,以求解脱。除了俩位命运多舛的女主角,这个闭塞的凉州村落里还有无数对苦难人生业已麻木或者胡乱折腾的人,比如总把“人活着不过是个物件"挂嘴边劝自己劝他人的老顺,无论面对长子早逝还是女儿要离婚,都是得过且过,一脸麻木;又比如掐尖要强一辈子,而丈夫窝囊愚蠢儿子女儿不听话,根本没有资本好强的莹儿妈,为了拿到女儿再嫁的彩礼给儿子娶后妻,屡次登门与亲家母对殴抢回女儿,甚至不惜与媒人上床作为让对方尽心尽力说媒的贿赂;还比如头脑简单、血气方刚的猛子,因为家境贫寒,亲事没有着落,只能与留守妇人鬼混发泄欲火,被对方丈夫捉奸后一句话“你给找个(媳妇)”就能把气头上的父亲老顺噎个半死……这么一数,好像雪漠落笔几十万字,写的全是不堪与丑恶。甚至对集合了真善美的“花儿仙子”莹儿(小学生的我就是从《凉州令》知道花儿这种西部民歌的),他也赐给她一个在婚礼上以鸦片自戕的结局,让读者们的心凉得就跟刮过黑夜里的沙洼的风一样。然而,与那些以渲染阴暗为卖点的二流作家不同,雪漠如实地写出这些丑恶与不幸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是西部农村无数家庭中真实存在的人与事。它们如此真实,就如同荒漠中干枯的草木,无论你想不想看见,那些垂死的或者已死的生命,它们始终都在那里。莹儿的死亡也是一样,无论读者能否接受,那只能是她最好的结局。掩卷之余,除了叹息这些不幸而愚昧的人们,只剩下敬佩雪漠的笔力。 时光荏苒,《凉州令》在06年那个懵懂的我心里刻下了永恒的印记,而在孔夫子旧书网的牵线下,多年后,我再一次领略了雪漠笔下的落后西部的别样风情。
《白虎关》读后感(四):“善”的传递与弘扬---《白虎关》读书随笔(2)
● 古之草
“善”的传递与弘扬---《白虎关》读书随笔(2)
《白虎关》中“老顺一家”代表着真善美,这是人类自古以来薪火相传的灵魂滋养和精神财富。这种“善”的精神以一种很质朴,很特有的形式存在着,它隐含在民间和俗众中,是一种有待于挖掘、研究、弘扬的隐文化。这种文化以“善”为载体散落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只因为太普通了,也往往被忽略了。所以雪漠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诗意的能力。这诗意,或是人物,或是故事,或是生活画面,或是一个世界。”
只要人类存在,世界上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苦难与超脱、希望与绝望等每时每刻都在不断上演着。但不管外界恶的势力多么嚣张,黑暗多么漫长,苦难多么沉重,光明又是多么的稀少,都无法剥夺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时代可以阉割人的肉体,却无法令强者的心灵荒芜。
《白虎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刚出校门的富强子对凉州的民歌情有独钟,他的理想很简单:先当沙娃,挣些钱,当路费,去凉州各地搜集民歌,将来出一本书。他说:“这茬儿人一死,民歌就没了,我也算是抢救文化吧。”
时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已频临淹没的边缘,像雪漠作品中写到的凉州贤孝、西部民歌、香巴噶举文化及那些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曳的民间善文化。而时代的喧嚣又使现代人的心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迷茫,物质的极度糜烂却带不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其心灵的焦渴和灵魂的飘荡急需要得到滋养和依怙。读了《白虎关》这部小说,也许能带来清凉和启迪。
在小说中“老顺一家”是善的坚守者和捍卫者,不管外界的风浪有多高,苦难有多重,恶的势力有多强,其善的力量一次次地战胜了恶,包容了恶,成为了光明的火把,照耀着周边的一切。小说中有很多的象征,如兰兰和莹儿身处沙漠中一直伴随她们的马灯,马灯在一定意义上是老顺身上的零件,象征着善的光明。兰兰已点了马灯。那团光晕虽小,但光总是光。有光就好。莹儿想,自家的盼头不也是生命的光吗?它虽然小,但没它,生命就黑成一团了。就是这盏很微弱的灯给她们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让她们摆脱了豺狗子的围袭,驱赶了孤独和恐惧,战胜了自己,也升华了自己。在那个凄风寒冷的雨夜里,她们点燃了马灯,也点燃了唯一能点燃的东西。马灯真好。那热虽然很有限,但总是热,姑嫂俩弯了腰,边为马灯遮雨,边烤起“火”来。她们之所以能走出流沙,之所以没被寒风阴死,就因了那马灯。
“善”有小善、中善、大善三个层面。雪漠这样诠释“善”:小善层面是物质,中善层面是精神,大善是灵魂和信仰的层面。 大善,就把这种物质的、精神的,变成一种文化和信仰,文化可以传承,可以信仰,不求回报,这才是人类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大善心,做大善行,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大善无我,善行天下。
在《白虎关》里善与恶总在搏斗着,同时人们对善恶的评价标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猛子和北柱挖坟时的对话就能反映出两人对善恶,对人格,对价值等的认识及微妙变化。双福发财之后回到家乡出资捐建学校,看似是为了教育,为了后代,但实质上那是为满足自己更大私欲的“伪善”,结果还是在强奸女学生的“小事”上出事了。在掘坟的时候,猛子能意识到双福发财并不是祖坟的原因,而是心的问题。但北柱却善恶难分,愚昧又糊涂,对做人、道德、良心、人格等混淆不清、颠倒是非,“钱”让他严重扭曲了自己的心灵,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莹儿再次被“卖掉”,逼迫嫁给屠夫赵三,更是说明了父母对儿女的“爱”与“善”出现了严重的曲解和极端化,这是一股很强很坚韧的世俗力量,也代表了那些被“异化”了的灵魂。正如莹儿哭诉地:“明知道这是无间地狱,我还是欣然地进吧。母亲,我信你的话,我知道妈为我好。那么,就让我的灵魂,去诅咒自己吧。”
人性都有善恶的两方面,人的心也有真妄两面。趋向真心的时候,趋向善的时候,人的心自然就趋向了高尚和完美。相反的,如果滑向了恶的一面,人的堕落和毁灭也是极快的。月儿和菊儿就是很好的例子。月儿曾受人欺骗患上了“杨梅大疮”,但她嫁给了猛子趋向了善的一面,自然也就升华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的人格。但菊儿掉进污泥中却浑然不知,即使面对猛子这一“善”的化身时也没有阻止她毁灭的脚步。这完全在于心的改变,如果心不改变,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猛子妈起初对待莹儿很“残忍”,是让莹儿打腿软的“恶”婆婆,猛子妈也是被环境所逼迫的,但本性还是善良的,她后来对待月儿却如亲孩子一般,积极地为月儿抓药治病,她知道月儿是善良的, 这就是善的力量的召唤,善的力量的回归。月儿临走时留下的信封里除了留给猛子的信,还有猛子妈刚送来的八千块钱,她用不上了,信里她很感激婆婆,说那些钱的真正用处,是她有了另一个“妈”。
这就是善与恶的转化,善与恶的较量,善与恶是很难一棍子打死的,人的心总在随着环境,随着外境在变,人们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例如《白虎关》中的双福女人,以前她对双福真的是“恨”,天天诅咒他“败”。一旦双福真出事了,她又表现出了大度和宽容。双福不管怎么的跋扈和嚣张,但他还是把最重要的“名单”交给了自己的女人,只因为双福女人还是靠得住的人。那靠得住的永远是一个人的真、善、美。正如猛子说到: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对于善恶的标准都发生了倾斜,人类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颠倒,到处都弥漫着善恶不分的局面,很多所谓的成功都是通过恶的手段取得的,而人类也习惯了这种所谓的成功,于是恶的东西在急剧滋长着,很多人是意识不到的,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因此雪漠说:但我们仍需要警醒这种“集体无意识”,保持一种警觉,发现恶的风气在抬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力弘扬。哪怕这种弘扬,只能发出萤火虫这样的光明,只要萤火虫所在的地方,就消除了黑暗。如果有一个火把,火把所在的地方,就有了光明。不断地点燃,不断地传递,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善的力量在这里。火把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照亮,但可以让人们看到方向、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别人就会走向这个光明,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白虎关》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善恶的思考。
《白虎关》读后感(五):完整的“神”——《白虎关》读书笔记6
最近在看《别林斯基选集》,不免有点汗颜。之所以脸会发烧,是因为我还没有一颗真正评论者的心,说得再白些没有一个“人”应该有的那颗心。因为在我眼里人的神性占据着绝对的地位,我只能从这一层来看自己与世界。自从明白了人本有的神性后,就再也无法退回了。也许正如雪漠所言,一旦明白了,就再也不愿糊涂着过。
与别林斯基相较,我的笔软软的。其实软软的笔后是软软的心。平庸常常从骨头缝里迸出来。我就好像《白虎关》里的屠夫赵三。祖辈是屠夫,今生是屠夫,说屠夫话,穿屠夫的衣服,屠夫早淹了他,他想不屠夫也不可能。假如他想从屠夫里裂变出来,就得有足够的信心和毅力。因此,如果说苦修需要忍,那么于我而言,忍的不仅是寂寞更是平庸。
别林斯基能剖文解诗,但这都不是他最拿手的。他最拿手的是剖自己。不是吗?那就看他这个人——文。什么是人文?别林斯基意味着真正的人文。人以文表,文以人存。当二者结合为一时,会显得十分悲壮。这种悲壮绝不是假以某种姿态,显现在大众的面前。而是灵魂中神性的爆发。你可以想像,一个向上的灵魂,与黑暗反复地较量,无数次地撞击平庸之壳,每一次撞击就流一次血,文章正来源于热血。雪漠就曾有那样的经历。他曾掌握了一些从文的技巧,而且小有成就。但他很快地发现了自己的浮夸。当他放弃了熟练的笔法后,就再也没写出什么东西。有五年的时间里,他像祥林嫂谈阿毛一样地谈文学,但没有指路的老师,也没有同道志友。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苦苦地求索了五年。从他书中的序、跋或是话访谈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在那五年中,总想拿把刀捅在胸口。直到有一天,他豁然开朗,苦尽甘来。但不是每个人的苦都会换来甘。比如那写死了的路遥。雪漠也曾谈起过他。他是苦死的,但他还没有苦透。同时,他也缺少宗教修养。而相反地,因为有了宗教修养,雪漠熬过了那苦,并升华了苦,化苦为乐。试看那些伟大作品的作者们,都信仰着某种精神,那精神是宗教精神更是文学精神。因此,我们不要轻飘飘地理解那悲壮。许多时候,许多人就是在悲壮中消失了。现在想来,能够悲壮确确实实是一件苦事,但能选择这样的苦事,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当求索的光明突破了外壳,就会像朝阳般,冉冉而起,红了大片。当光明最终化了心时,悲壮消失了。假如你登高观过日出,必会记得令人惊叹万分朝阳红起来的过程。但转而却是一片纯净。仿佛那血染一般的壮观从未发生。原本就是那个样子——宁静、自然。甚至是不经意的。它不是含泥的珍珠,也不是包尘的黄金,没有什么奇特,但本自清明、高贵、神采奕奕。
然而,我们坚决不能“大看”光明的乍现,甚至以为那宁静唾手可得,仿佛不经“修炼”,就“一口吞三江”。且看,坐在亥母洞里,不多时便有了超然宁静,甚至有了妙妙禅乐的兰兰。她最初觉得“生命里有了神。神是什么?神就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有祸,神替你化。有罪,神替你灭。有苦,神替你消。有病,神替你治。神是求星。神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神还是裁判官呢。神高悬明镜,洞察秋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白虎关》雪漠)于是,她把性命、命运统统地放到了神的手里。有了神的相助,她多年来内心的纷争熄了。她苦苦的婚姻,早令她忘记了啥是爱。有的除了被合法强暴的肉体,就是像席子一样的遍体抽痕。最令她痛心的,莫过于女儿引弟的死。我想,女儿那可爱的脸蛋儿,就像插满了万颗针的砧板,她的心就是板上的肉。每想到一次,“肉”就被“剁”一次。就这样,苦无边的她想要结束这些……现在,神来了,神会裁判。神释放了她的苦,她的相思,她的爱,也释放了善与恶。为此,她有一颗能坐来下的坚心,有了一份心量,一种眼界,更高地审视了她曾经的灵魂。她有了一个盼头,一个希望——金刚亥母——救命的灵芝。
也许你要问,这就是人性中的神?这就是救了兰兰的药吗?别急,不妨把这些当个引子,试看看那兰兰的心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兰兰静极的灵魂在流淌。由你淌吧,流吧。那不是兰兰,兰兰已空灵了。身奇异地空灵,心也奇异地空灵,没有杂念,没有念想,没有自己,没有‘没有’。那神也罢,仙也罢,是遥远到心外的事。”(白虎关》雪漠)
神不见了。刚才她死命抓着的神不见了。但她不再慌张四顾,不再绝望。不,那慌张、绝望根本就没存在过。
随着兰兰的清明,她明白了所谓的那个神,并不与自己对立的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身中的神性需要通过像筛子一样的东西,细细地品察。兰兰妈也信金刚亥母,但当老伴老顺问她,我打你时,亥母在哪里?她就一脸木然了。是啊,那个能保佑你的神哪里去了?对于这个疑问,你可能在书中找不到什么明确的答案。你也可能想知道作者有怎样的心思。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最初。我们需要细细地研、磨式的阅读。文中当然有答案,但你得先研了自己焦燥的心,粉碎浮燥和纷飞的念头,静静地坐下来,再磨炼那颗心,守住那份静。这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这是在读一本书的精神,更是在读你心中本有的神性。没了这种精神,任你看遍所有图书,也只是知晓了一些知识罢了。而那知识不仅成不你的助缘,反而会害了你。但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言,“读得懂的才算是伟大”。这句话多么具有二面性。没有那种精神的书,不需要“读者”。而无法读出好书中精神的人,也不需要好书。什么是好书?不要问别人,请问自己是否有那个研、磨的心,有没有对那种精神的追求。没有,无疑你不是好的读者,你甚至不需要读。
对于无知的人,答案是助长其傲慢的毒水。因此,放下概念式的答案,先静静地读。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作者可能会非常欣慰。当然,我们不是为作者而读,更不需要他的欣慰来填补自己。我们只会感到灵魂的这次撞击,是如此地深刻,它甚至还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兰兰的命运就是这样变的。与我们不同的是,她并没有通过“读”这个形式,而是坐禅。由此可见,能承载精神的一切表象,包括文学作品等等,都具有同样共性:让人正视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灵魂。而一切能接近明白的种种形式,包括读、坐禅等等,都会带领着人们由具象到无形,由混沌至清凉,由方法到“观月”。为此,我们会打破所有的概念,而直趋本质。然而,这一点正是大部人最缺乏的美德。这种缺乏从不因你是高官、富有者、知名人士而比常人更健全。事实恰恰相反,越是与心外之物靠近的人,离那美德就发的遥远。
那个神,指的绝不只是人最后升华的那个光鲜的刹那,完美地人神合一。真正完整的“神”,包涵了整个“修炼”的过程。只有那个过程才说明了其价值,人神合一的价值。否则我们就不必追寻。还记得菩提树下苦修成就的佛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他们的那个过程远比他们证道的结果更能说服人。如果与此相反,那么无疑你还执着着那个光鲜的结果。也许他们不必说什么,只稍稍地展示一下自己曾走过的路,便能让信仰之人获得解脱。也许宗教还赞美着那种信仰与追寻的过程,而文学却已经少有这样的精神。记得雪漠曾说,你可以没宗教信仰,但你不能没有宗教精神。
我想起了那段花儿,尽管不是我写的,但我却想唱: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