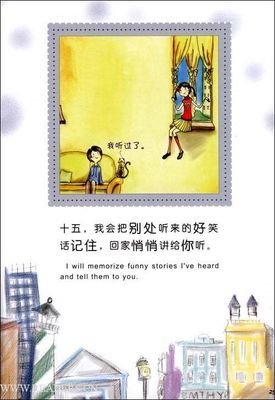
《海鸥墓园》是一本由郑然著作,后浪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鸥墓园》读后感(一):关于《海鸥墓园》的随想
我看见男人与女人情感关联的脆弱地带,我看见了沉重现实的轻盈倒影,我看见了一条通向蜘蛛蜕变为蝴蝶所在的隐秘小径,我看见潮湿这种感觉悄无声息地吞没所有小说人物最终吞没我……但是——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是一座真实的《海鸥墓园》了吗?并非如此,因为“客观的真实”在此并无意义,那犹如蜃景般的一切在我合上书的时候,产生的影响不是外向的爆炸而是内向的坍缩,一种沉默表象下的剧烈颤动。似乎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小说变成一副地图,每个人物乃至每种感觉都有清楚的坐标,可实际上做不到,一切都在缓慢地漂浮中挪动位置,我必须跟随这种漂浮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所在。作者从内心切割出的诸多部分形成诸多小说,并没有让其肆意朝着魔幻生长,以一种难得的自制力让一切停留在暧昧的边界上。整个阅读过程就像是游泳,在潜入水下屏息与浮出水面呼吸之间切换,在沉与浮之间用并不确定的目光认知着并不确定的一切。
《海鸥墓园》读后感(二):《海鸥墓园》华丽荒寂的不安与暧昧,在都市的孤岛中肆意游走
在9月初的一个午后出门带上了这本《海鸥墓园》放在侧身的小挂包里露出三分之一的书身,很美。在河畔的草坪上我找了处阴凉地翻阅了起来,书体很轻,单手拿着很舒适,读到“海鸥墓园”那篇时,当文中写道“在塔上筑巢的海鸟们受到惊吓,扑棱着翅膀,成群的飞到空中,遮住她纤细的身影。”我眼前的河面上一群飞鸟划过水面,一阵风吹过,令秋天的味道随着文字中的孤独瞬间浓郁,人与人之间那些细腻的,不确定的,袒露的,遮蔽的一切一切影响着通达彼此的信号,令似乎亲密的不能更多的关系里充满了易碎的脆弱气泡,美妙时无与伦比,消失时分崩离析。敏感的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真实弥漫,作者对困惑和感知有直面的勇气和细腻耐心的刻画能力,令人感慨。于是,初秋的整个下午便是在窗风和光影摇曳的光线中阅读这本书度过,仿佛跟随人物穿越不同的人生梦境,真实又诡秘,像是一趟近在身旁的短暂旅行,结识了一些孤独敏感又真诚的城市幽魂,打了个招呼,彼此关注却并不熟悉,正如现实中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在专属自我的空间脉络里与所有人交错,盼作者能与笔下的人物交集更深,带来更成熟美妙的作品。
《海鸥墓园》读后感(三):测不准的天气,测不准的摄影 ——读郑然《海鸥墓园》
读郑然的小说,可能需要一点对画面的想象力,否则很容易遗漏小说中的一些暗扣。比如,在短篇小说《海鸥墓园》中,男主角送给女朋友的相机正是海鸥牌的。到了小说结尾,女主角面对成群的海鸟(以及鸟巢、鸟粪、鸟类骸骨),并用相机拍照时,真实的海鸟与相机上的“海鸥”厂牌,恰好形成有趣的映照。类似的暗扣,多次出现在小说的各个地方。
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对年轻的恋人因为某种原因,买下一套孤岛上的别墅,搬到岛上居住,而这座孤岛无法在任何地图上被找到。两人在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决定分手,分手前女朋友要求一起去岛的另一侧看看。他们到了那里,那里是海鸟的天堂,也是海鸟的墓园。在鸟翅翻飞中,女朋友掏出了相机,准备给“我”(还是“我们”?)拍摄最后一张照片。小说除了对恋爱往事的回忆,剩下的就是他们去往岛屿另一侧的过程。内容关乎爱情,却不能以惯常的爱情小说标准来看待。
首先是对孤岛的设置。当男主角和女友的感情因一次流产而无法再回正轨时,他选择搬到孤岛居住,这座孤岛除了不存在于任何地图上,还有着恶劣的天气,“仅有的一座信号塔在岛的另一端”,“说不定它早就被无常的天气损毁”。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座孤岛是两人关系的隐喻。他们已经走入困境,打了死结。这座岛只是一个尴尬的缓冲。岛上的天气变幻莫测,时而暴雨,时而狂风,岛屿被肆虐的雨水和连夜的波涛所包围。他们在搬去岛上居住之前,男主角求助了一次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的结果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流雾。这场雾甚至蔓延了大半个地球。这不但加重了小说的超现实主义意味,也印证了孤岛的隐喻性。要说天气预报测准了大雾,倒不如说天气预报已经失效了。如果孤岛是两人关系的隐喻,那么失控的天气便是这段关系中偶尔迸发的情绪波动。在这里,信号塔远在另一端,没有人去光顾,而且很可能已经成为破铜烂铁,彻底失去信号。
其次是相机的设置。女主角喜欢拍照,尤其喜欢拍“自己亲手埋葬的东西”。照片是记忆的缩写,是对存在的证明。按下按钮,一方面是决绝地推开,以示自己已与过去隔离;另一方面,也是将过去收编,将其化为薄薄的一片信息,让过去更好地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关于过去,小说中那个被打掉的孩子是关键所在,男主角认为应该“抹掉那个孩子所有存在过的痕迹”,女主角却偷偷拍了照片。“过去”如何作用于“现在”的生活?如何才能真正“重新开始生活”?我猜这是作者想问的。
小说结尾,女主角又端起了相机,她“恢复了昔日的美丽”,但风暴也重新聚集起来了。最后一次快门,究竟是和解,还是激烈的告别(按苏珊·桑塔格的说法,摄影也是某种射击),我们无从得知。但海鸥死于此处,形成墓园,正是因为海鸥生于此处。无论如何,这个开放性的结局,都呼应了他们曾存在过的过去,都是对这段测不准的关系最好的收尾。
本文作者:ZEN
《海鸥墓园》读后感(四):薄雾中的蜃景
初读郑然的《夏日图景》,正好也是夏天。在炎热的空气中,食物迅速变质,就连毛发的生长和脱落都更快一些。故事起始于夏天,终结于夏天,好像是最自然的选择。夏天仿佛是现实空间中另外开辟出来的一个来的“虚时空”,存放着年轻人过剩的热望和能量。
开篇,《夏日图景》便散发出“虚时空”的意味。郑然并不想用现实的外衣去装点这层建构,在引言中,他便坦诚公布了答案,一切都是虚妄:“一切古典意义上的忧愁都被戏谑和自我调侃消解殆尽。——柯赞《生活与戏剧集》”。这是该小说悬疑链中最为关键的线索,不过现实中并没有什么柯赞,更不存在《生活与戏剧集》这样的巨著。这是郑然和我们开的玩笑,他乐于用文字编织出一道风景,它与我们隔着一层薄雾,当读者拨开雾气伸手触摸时,不难发现那只不过是他打造的美轮美奂的蜃景而已。
小说的主人公霄是一名戏剧演员,他不幸被日渐衰落的剧团开除。他的人生走入了一个困局之中,然而读者被告知,这个困局亦是戏剧的一部分。每个人生来都是演员,在不同的现实链条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出是否成功,就要看演员是否擅于模仿生活,是否尽全力沉溺在这出戏剧之中。显然霄是失败的,在隐约的破碎和抵抗中,他不断游荡,不断出戏,这是年轻人精神困境的的隐喻。
霄是破碎的。剧院不景气,他一开始便放弃了,不做挣扎。他是所有失意年轻人的缩影。巧巧更是破碎的,她是一个鲜嫩的少女,就像夏日里最诱人的果实。但她迷失了,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果实的彻底碎裂由一场意外彻底触发——一个神秘的男人死在了她的床上,于是她开启了一场漫无目的的逃亡。也许巧巧并不清楚为什么要逃亡,甚至不知道追捕她的对象具体是谁。她的行为更像是一场青春梦游。失眠者和梦游者在某个截点相遇——碎片之间找到了彼此,却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完整,而是完成破碎之后的融合。就像夏末掉落的浆果,它们滚到一起,直到被人踩碎,不分彼此。老蒋是这场融合的一个突破口。他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似乎不该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该有什么抱怨了,但他却是按动爆炸按钮的关键人物。虽然是他启动了这出疯狂的戏剧,但他却是最清醒的那个人。故事一开始就进入了急速的坠落之中,但郑然的叙述却是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的。就像那些好莱坞工厂制作的精品电影一样,不露痕迹,又引人入胜。它总能在合适的地方让读者顺利进入下一个幕,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时空上安之若素,直到他们自然地相遇,故事顺利进入了高潮部分。
郑然的笔触是热烈的,虽然夹杂着的忧郁。但这种忧郁背后,是严肃的主题。他在小说中坦言:“谁的忧愁都不值钱,尤其是年轻人的忧愁,他们在经验上天生处于下风。他们热情,冲动,愿意为一位注定都得不到女人或是一件荒唐事付出足以摧毁他们的代价和勇气,但同时他们又无法与更庞大的时代抗衡,于是,他们的忧愁从时代快速更迭的齿轮间隙悄悄溜出来,随即又被碾压,周而复始。”他的小说也有几分这样的决心,似乎不怕暴露出缺点。它是勇敢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一场献祭。
顺着小说中的空间漫游,其中出现的剧院、街道,连同整座城市都是被虚构出来的,包括男女主人公途经的地铁站:无头骑士街、漂亮河、箭鱼码头、沉落太阳沙漠、顽童银行、四手佛寺、大白鹿门、小白鹿门、纸信封机场、烟蒂博物馆、还有深巷街。无一例外,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对应的实景。郑然好像故意让我们脱离现实层面,让读者通往他精心打造的文字迷宫之中。但仔细想来,这些奇怪的地标真的找不到吗?它们就像是潜伏在作者潜意识中的精灵,跃然纸上,变幻模样。可能是一篇小说的名字,可能是某句歌词,也可能只是烟盒上的某个词语。最终我们会知道,它们同样来自于现实世界,只不过呈现一种悠然的变形状态而已。我更愿意称之为“小说蜃景”。我们触摸不到,因为它是现实的映射。好的小说并不完全模仿生活,它们更像是生活的镜像,是可以找到对应、无限逼近生活的状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反映着世界,并以严格的整合对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和阐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独一无二的“世界线”。在这条世界线上,人们涉足的空间和所经历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促使小说向着无数枝节延伸出去,成为绚丽的、难以解释的宇宙。何谓真实?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是现实主义。即便主人公忽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他也是真实的;即便主人公在战争中被劈开,成为分成两半的男人,我们也只能接受他不可逆转的分裂。我们之所以迷恋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卡塔萨尔,正是因为他们抵达了更高维度的真实。这并不是一种轻盈的、讨巧的笔调,而是一种无法规避的选择。在作者起笔抒写之前,他的审美趣味和阅读经验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便已经注定了这种写法。
郑然的小说并不日常,或者说他并不耽于书写日常。他迷恋的是“奇观世界”,并擅长在自己的小说里打造奇观。小说并非有意逃避日常,我愿意把它看作是作者的一种神秘趣味。作者迷恋的是那种不寻常的事物,即使在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也要不断挖掘秘道,当这个口子挖得越来越深时,便会出现一个蜃景。它看似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一对应,可以以假乱真,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法则。在郑然的另一篇小说《海鸥墓园》中,他创造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岛屿。一对失去孩子的恋人抵达这里,似乎想要祭奠什么。没有什么真正的流血事件,但通篇都散发着一种死亡和墓地的气息。为什么要到这个绝境般的岛屿来?为什么要将两颗绝望的心彻底捏碎?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孤岛是真实存在的,是内心的困顿岛屿,比我们实际踏足过的任何土地都要更具体。这种切肤之痛比脚踏实地的存在更为真实。
在郑然的小说《晚宴》中,出现一座疑云重重的古宅。哥特的气息蔓延开来,当主人公丹徒看到自己的血液不断交融汇聚,她觉得要它们是相互邀约的异教徒,要通往幽深隐秘的地下祭坛……小说通过诡谲的比喻顺利进入了极为有趣的部分。精心布置的吸血鬼故事不禁让人想起科塔萨尔的小说《吸血鬼的儿子》。不过再次品读之后不难发现,小说中的“现实”部分依然有迹可循,郑然并没有完全抛弃现实,而是在“现实”中劈开一道黑色的大门,放入他瑰丽、隐秘的想象。它们就像划过天际的火流星,即使化成碎片散落各处,但依然会在坚硬的大地上砸出明确的坑洞。正是这些坑洞,形成了小说中隐秘的线索。我们寻着这些线索,不仅能抵达郑然的文学秘境,也能抵达另一种“真实”。亦即“虚时间线”上的真实。丹徒独自租住在大城市多年,她的故乡已然模糊,只出现在回忆之中。当她走入一栋古老的租界洋房,那种被割裂的气氛愈加浓重。读者很快被包裹中,进入郑然编织的故事谜团之中。在神秘、难解的画作中,她奋力辨认的身影便是自己……我们看到某种自我涉指,在嘈杂的都市生活中,有多少像丹徒一样的年轻人正在走入孤立无援的生活。虽然他们的生活不像小说中那样步步惊心,但是那种孤独也一样危险。无法逃离的是这个时代的喧嚣和焦虑。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作家已经很自然地吸收了世界文学的资源,他们面向外界的眼光开阔了,但又似乎只是在中国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的影子,“故乡”已然只是符号。而在郑然的小说中,那个故乡似乎是“远山淡影”而已。他没有被这片土壤攫住脚步,而是放手创造了薄雾中的蜃景,让它们在晃动的气流中自由沉浮。
《海鸥墓园》读后感(五):小说是有关记忆的坟墓——《海鸥墓园》三人谈
《海鸥墓园》书影“小说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有关记忆的坟墓”
陆支羽:你的这本书,我也是前段时间疫情期间看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完全看完。然后当时我就说海鸥墓园这个名字还挺符合今年的这种氛围的,有点末日的感觉。
郑然:其实取这个名字,它首先是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其次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这里面的所有小说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有关记忆的坟墓,那么它放的这个小说集里,其实也是放在墓园当中。当时想的是,很多时候我会对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坟墓比较感兴趣,但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我会觉得说在这些石碑上面刻下来的字,在底下掩埋的人,他们也是一些活生生的人,那么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呢?他们在过去的时光,我们没有经历的那些过去的时光当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可能是很平凡的,也可能是创造过伟业的,到最后都排在同一片土地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境场、景观,我看很多人去旅行,可能到日本去一些很有名的名人的坟墓,包括像法国的拉雪兹,也还有公园中埋了很多艺术家,之类的有很多,它们其实逐渐成为一种旅游的景观。
陆支羽:像一些艺术家、作家或者导演之类,他们去世之后,但他们作品留下来了,其实也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活着的,所以我对死亡的想法还是比较释然的一种态度,就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啊,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对于普通人,对于像今年疫情期间去世了那么多人,这种又是一种很有末日感的感觉,他们是猝然离世的,什么也没留下来,所以死亡是一个很纠结的事,但是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这个东西。
“怀念所有形式的废墟”
陆支羽:我当时看到你这本书,我看到你的简介里你说,“并怀念所有形式的废墟”,我想问一下对废墟这个词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会把它作为一个简介放在这里?
郑然:废墟的话,我脑子里的想法其实也是一种废墟,它其实也是一种,因为废墟其实首先是被人遗忘。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死亡死去的人,他也是会被人遗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很多实体来看,可能我们看到一些浪费,包括我每周上下班的地方在郊区,我会打车,到路上就会看到很多还没有完工的工地,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工地,路过一个工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一个空间里头其实给人会有一种悲剧感。包括可能像在之前的一些对对齐的教堂,或者是山庄山村,哪怕说是水下的一些遗迹,我对废墟比较感兴趣和喜欢,正是因为它们被人忘记了,我才对它感兴趣。但是它们是存在的,它们因为也是在时间的时间当中是存在的,很有可能会兴盛过,比如说像古罗马的庞贝,包括像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样子。我可能会更感兴趣它们以前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发生故事。然后还有内在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也会建造变成一种废墟,比如说一种关系可能到最后分手了或者是离婚了,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前他们有过那些过往的记忆就成为了废墟,包括可能是一些亲人的葬礼,他跟这个人没有没办法再真的去接触,那么他们之间这种记忆,其实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在《海鸥墓园》这些小说当中,其实用了照片这个手段,照片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显现,所以说我说怀念所有形式的废墟,就是说也包括内心对记忆的这种废墟的怀念。
“《海鸥墓园》,如果有一个导演的话,我想可能会是赫尔索格”
索耳:《海鸥墓园》同名的小说,其实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一对情侣相互纠缠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我发现你是给设置了一个出口,你这对夫妇因为某些生活上的一些原因,稍微相冲突,然后这个男的就给她买了一个别墅,他们就到了这个场域,相当于是给他们遭遇了一个出口。最后结尾是这个女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之后,看到在寻找别墅,然后在别墅的上面,拍照就最后一个镜头,好像是得到了解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动机,就是一个解放、一个出路的动机在里面。
郑然:其实我理解出路就是说,女主人公做了最终的决定,因为她其实在故事当中有一句话讲,她很喜欢去给自己亲手埋下的东西拍照留下记忆,所以说她给最后男主拍照,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把你变成我的过去了,苏珊.桑塔格《论摄影》有一个说法,其实摄影也是一种射击,有一个枪的寓意在这里,这是一个诡计,是一种谋杀的象征。她给他拍照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男人在她的生活当中杀死了,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记忆。女生又首先获得了一种,你说的出口,她能重新变得美丽起来了,不在这这段关系当中。虽然我其实是用男主人公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的,但是最后是我想解放的是女性角色。
陆支羽:《海鸥墓园》是我看的你这本书里面第一篇小说。 我个人的感觉《海鸥墓园》,我容易投入一些电影的画面感到里面。所以看这篇小说的时候,可能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就想到一些南美洲的电影。我看到这种有点异域情调的,然后又能够带入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命题,包括死亡,包括一些很永恒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而且我觉得挺适合改编成电影,对,当然不适合太写实的导演来拍了,肯定还是相对诗意一些的那种感觉,这篇《海鸥墓园》,如果有一个导演的话,我想可能会是赫尔索格。
“通过看电影延伸人生的旅程”
索耳:郑然他也是拍电影的,他是学电影专业的,然后不知道你对于因为我看你这个小说其实有些很片段,甚至有些是可能有几千字,有些是比较长,就有些长短不一,你集子里面,好像是你对于一个小说的影像化,就是对于一个画面的理解会非常深刻,你可能更加去抓住一个画面的进度。
陆支羽:很多地方你会不会带入,就是说拍电影的那种感觉,会从镜头语言去考虑?
郑然:其实会有按照做拍电影的方式,可能是调度感,确实,我也是学电影出身的,现在也是相关的电影工作,就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抛开这些外在因素,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从小很喜欢看电影的人。佳片有约,那个节目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有一些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部叫《疯女胡安娜》,她讲的是西班牙的一个王后的故事,那个故事我觉得是说她跟她丈夫之间掺杂了权力的斗争,对吧?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从小其实是接受影像化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其实在写作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刻意去想,可能在写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融合到自己的创作当中,我感觉,我们很多写作者其实也会有电影感,真正喜欢看书写小说的人其实大部分也是喜欢电影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通过看电影延伸人生的旅程,或者说完成各种各样的旅程,而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写作是一种自我修炼”
郑然:我想知道你们平时自己去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习惯?我知道海明威喜欢很嘈杂的咖啡馆去写小说,比如说陆老师你去写影评的时候,或者是索耳去进行一些思考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陆支羽:我感觉我有拖延症。我写东西我总是会在呆在那里最后的那时刻,然后才把那个事情去完成,我觉得这样挺不好的。虽然我心里老惦记着这个事儿,而且我越有活的时候,我越会去干一些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儿,但是总感觉把这个弄完了,我就去做这个,但是做完又觉得还有其他事儿,我还可以再再拖延一会儿,我觉得挺不好。其实我觉得写作更多还是体力,我觉得是体力活是很大的一部分,它可能对于其他事情来说,需要你去投入,你要主动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拖延的一个原因。
索耳:其实我写作也具有非常重的这种拖延症,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我写作慢,而是我写作了之后发现我加深了我的拖延症。因为写作像你说的,确实就是一个体力活,一篇小说,我不是属于那种天才宣泄型的那种作家,可能一下子下笔如神,可能一个下午可能就写一万字,我不行。像莫言在四十天就写了四十万字,他是属于那种宣泄型的,但是我是可能就写一万字的小说,可能每天也就写个五百字左右,然后每天下班晚上回来写,你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得花两个小时,然后你写的时候,真正写的时间可能一个星期里,一个小时都不到。
陆支羽:现在爆炸性的东西很多,你手机只要放在旁边,时刻有人跟你微信或者是各种新闻的推送什么的,对,我给你经常发微信,也会打乱你的心思。
索耳:我是觉得写作它是一个考验你的耐性的东西,写作是一种自我修炼,像我之前采访过一个艺术家,他每天都有画画,我问他说你对于画画你每天是不是有什么题材上的追求,你有没有什么创新之类的东西?他说没有,他说每他已经把它当成一种每天的一种修行了,他是一种修行,像我们写作也也是训练,实际上是在陶冶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写了什么,而是说写的内容反作用于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心性变得更加忍耐,作家就可能是一个写作困难的人,像托马斯.曼说的,要善于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