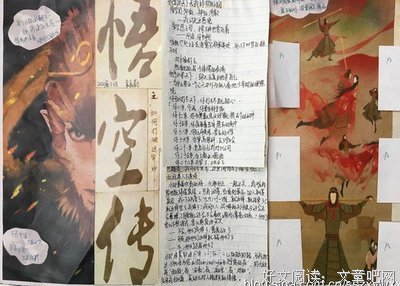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一本由陈平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真滴佩服脆皮鸭老师,博士论文,体量是787本(篇)晚清到五四的小说,晚清的起码一半,怎么读下来的,我跪了,这么难看的东西我一本都看不下来,而且还是竖排的,他的毅力从何而来…其实深度一般,narratology的限度也就在这儿了,陈老师在后记里有反思。后来引入文化研究的路子,研究文学外部体制,看了这期《读书》知道陈老师又有新著了,脐带!
●1.5-4=-2.5
●功力深湛。
●关于叙事角度转变的部分讨论得很有趣,但显得有些生硬,缺乏更深层次的探讨,为什么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视角能长时期占据主流?新小说和五四小说大部分水准都不行,可能在学术上很有研究意义,对读者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2019年已读019。32.3万字。此书为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作于三十多年前。今天读来,论点已不新鲜,但“采铜于山”的写作方式让人敬佩,不费大力气,这本书成不了现在的模样。读完后最大的感受是,一是作者读书之多让人惊叹,二是论述十分严谨,不做绝对判断,三是文风清和,不冒进、不张扬。
●理论工具题中之义即为手段,而不是借论述和脚注来自我证明,本书就是这样,点滴之间乾坤自现。
●对于理解五四至二十世纪末乃至当下的小说传统走向都极有启发。虽然作者自陈理论框架简陋,但“简陋”大概是梳理脉络的必然,若进一步微观和复杂的理论分析,恐怕这段时期的作品承受不了。尤其是作为外行来读,还是很受益的。
●平原君博论 喜欢上编多过下编
●高峰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后感(一):纯属短评多了几个字又不想删减
脉络非常清楚,陈老师对概念、方法的界定很明了;强调“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共同指向转变(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小说形式感的加强和小说人物的心理化),泾渭分明又齐头并进的“史传”和“诗骚”两大传统,在西洋小说的输入之下,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在这过程中如何古典文学的两大传统,两股合力的推动下共同完成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陈老师颇为学术关怀的两段话在导言和最后一章: “在这里,中国小说拐了个弯,从此进入新的河道,在本书的论述范围内,即指采用了新的叙述模式。不难想象,就在这转弯处,会有许多值得仔细辨认的先驱者的足迹、迷路者的身影与牺牲者的躯体。” 末章引用伍尔夫的一段话“世界是广袤无垠的,而除了虚伪和做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禁忌的。”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后感(二):自己的笔记
1987年,陈平原在北大的博士论文。导师,王瑶
着力点:在西方和传统的叙事对比
自身要求:尽量减少情感色彩、思想火花
顺序:西方小说的启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作用
基本理解:史传、诗骚传统
提出问题:小说现代化 概念or价值尺度
理论模式:次序、延续、频率、心境、语态
手段:叙事时间、语态、语式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三方面:时间、角度、结构
看古代
倒桩叙述
唐·李复言《虚幽怪录》中《薛伟》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中《女侠》
第一人称限制叙事
唐·王度《古镜记》 清·王晫《看花述异记》
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躺·《补江总白猿传》 蒲松龄·《聊斋》中 崂山道士
以个性或背景为结构中心
婴宁
古代:基本为连贯叙述 角度:全知 结构:以情节为中心
现代 倒装、交错 一、三,纯客观 性格、背景
两代作家
梁启超、林纾、吴
鲁迅、郁达夫、叶圣陶
五个时期抽样分析
(待添加 看到11%)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后感(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阅读笔记
本书的论述中心是小说的叙事模式,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并未对这些理论作出严谨的肃清,而只是将其大致分成了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种叙事模式。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
根据小说叙事模式三个层次的不同变项,陈平原抽样分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797部,从而描述出这一转变的大致运动轨迹,确定1898至1927年为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由“新小说”一代作家和“五四”一代作家共同完成的,为了较为准确地描绘着两代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陈平原分五个时期抽样分析,其中每一时期都选取代表性杂志。此外,陈平原把这两个阶段五个时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各个变项综合起来并加以比例化,使之具备可比性。
通过大量作品实证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轨迹。并且能够看出,在整个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叙事时间的转变起步最早,叙事角度次之,叙事结构最为艰难;但从转变的幅度看,叙事角度最大,叙事时间反而最小。在突破连贯叙述的叙事时间时,倒装叙述起主要作用;在突破全知叙事的叙事角度时,限制叙事(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起主要作用;在突破情节中心的叙事结构时,性格(实为心理、情绪)中心起主要作用。此外,“新小说”家的译作比创作更偏离传统小说叙事模式。“五四”小说家则反之。
陈平原不仅仅是要指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具体样态,同时也是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陈平原认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而发生变化。陈平原将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作用分成上下两编,但他强调,造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这两种移位,并非孤立地发生,平行地发展,而是不断地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陈平原老师的这本书在研究方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上编,关于西方小说的启迪所造成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假如我要研究新时期外国文学的引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或许我也应该把研究的角度缩小,正如陈平原老师把重点放在小说叙事模式上一样。我觉得叙事学研究,相对而言操作性比较强,所以陈平原老师可以做出表格、图标,使得分析更为清晰,也更为客观。但是,他以叙事模式为角度切入,可能还是与当时的文学特色有关,而新时期文学更大的变化也许在其他方面?假如我把新时期文学界定在1980年至1983年,并且我要研究的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引入,我肯定也需要像陈平原老师一样,选取这一阶段最相关的杂志、出版社的译介资料。但不同于陈平原老师只研究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除了小说以外,其他文学作品也要涉及,另外理论也是甚至更是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后感(四):《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书笔记】
第一章:导语
1.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
3
2.1897年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8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标志着中国作家开始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并创作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
6
3.因此,我把主要活动于1898至1916年的小说家通称为“新小说家”,而把主要活动于1917至1927年的小说家通称为“五四小说家”。
7
4.1922至1927年的小说创作中有大约百分之七十九的作品突破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已经基本完成叙事模式转变的最明显标志。
13
5.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
19
6.大致言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在“新小说”家是政治学知识,在“五四”作家则是心理学知识。
23
第二章:《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1.“五四”作家的真正贡献在于,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过去的故事之所以进入现在的故事,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于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50
2.如果说逆溯式或包孕式的时间处理方法,容易使小说结构更加紧凑,扩大小说表现的时空容量的话,上述不同时空场面的交错叙述,突出的是每两个对应场面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依靠不同时空场面的“叠印”来制造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更好地体现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这种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的“蒙太奇”。
56
第三章:《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1.真正自觉把视角理论运用到小说批评中去的,在“五四”时代大概只有夏丏尊一人。
79
2.如果按编年阅读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对小说视角的运用,都大略经历了一个从全知视角到第一人称叙事,再到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过程。证之以整个小说界的创作倾向,更说明第一人称叙事作为过渡桥梁的作用。
81
第四章:《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
1.并非“五四”作家重外国小说而轻外国诗歌,而是情节的叙述要比场景的描绘、情感的抒发更易于译成另一种语言并基本保持原作的韵味。
102
2.并不是“五四”作家缺乏构思情节的能力,而是他们把淡化情节作为改造中国读者欣赏趣味并提高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关键一环,自觉摆脱故事的诱惑,在小说中寻求新的结构重心。
111
3.从注重“事实”到注重“风格”,这不只是“小说界的进步”,也是评论家和一般读者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即意味着非情节因素越来越被推到小说表现的前景。
114
4.从读“情节”转为读“细节”,并于“细节”中味出从前仅属于诗文的“情趣”,这是“五四”小说得以突飞猛进的关键。
123
5.“五四”作家借助白话文运动,综合晚清白话文的“口语”、新文体的“新名词”、章回小说中的“方言土语”,以及从古典诗文中吸取“古语”、从西洋文学中借鉴“西洋文法”,熔铸成一种新型的小说语言。
125
第五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1.起码到1907年,小说杂志的稿酬已完全制度化。1910年,满清政府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著作权律”。
140
2.“新小说”注重“史传”,故更热衷于引轶闻、游记入小说;“五四”作家注重“诗骚”,故对引日记、书信入小说更感兴趣。“新小说”与“五四”小说的基本面貌,跟这两代作家对这两种文学精神的不同选择大有关系。
147
第六章:《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
1.从《笑林》算起,中国文人有意识写作、编辑笑话已有一千七百年历史。有叫“启颜”的,有叫“解颐”的,有叫“雅谑”的,有叫“绝倒”的,有叫“轩渠”的,有叫“拊掌”的;可“录”,可“集”,可“史”,可“记”,可“语”,可“编”。
2.在20世纪初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叙事时间的转变起步最早,叙事角度的转变成效最大,而起决定作用的叙事结构的转变却始终步履蹒跚。而在这一些系列歪歪扭扭的足迹中,我把抛弃曲折有趣的情节的尝试,作为可以辨认的第一个脚印。
174
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1.“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
199
2.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得以在中国长期独占鳌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读者受“史传”传统影响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真实性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是病态的。
209
3.“五四”作家大多不善于编故事,却善于捕捉一种属于自己、并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有“情调”。一个简单的叙事框架,经过作家再三的点拨渲染,居然调成一篇颇有韵味的“散文诗”。
218
4.从李贺、李商隐的诗,李煜、李清照的词,到戏剧《桃花扇》、《长生殿》,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善于表现“凄冷”情调的传统。
219
5.中国小说在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以诗文为盟主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学,这就决定了凄冷悲凉情调对“五四”小说的渗透。
219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后感(五):陈平原思勉原创奖演说︱在范式转移与常规建设之间
世上好书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一是机缘凑合,别开生面。若是后者,往往与特定时代氛围有关。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属于后者,故谈论此书的得失,必须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与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作为必要的参照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大量西方新旧学说被译介进来,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需要一个辨析、沉淀、转化、接纳的过程。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革”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逐渐登上舞台,一个生机勃勃、激情洋溢的文化热及学术变革时代开始了。我不是弄潮儿,只是这个大潮的追随者与获益者。谈论中国小说而从“叙事模式”入手,若非这个大潮,我不会这么提问题,也没有相关的理论准备。
在中国,将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从事研究,是上世纪初才开始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五四”先驱借助于十九世纪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清儒家法,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根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小说史家越来越注重小说的社会内涵。五十年代起,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成了小说研究的中心课题乃至“指导思想”。八十年代学术范式的转移,落实在小说研究中便是将重心从“写什么”转为“怎么写”。不再借小说研究构建社会史,而是努力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来展开论述。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选择“叙事模式的转变”作为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关键来辨析,且在具体论述中,努力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借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在此书的初版自序中,我谈及“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采的例证”。这一学术立场,使得我在具体操作层面,更接近于常规研究。赶上了文化及学术变革的大潮,但因另一种力量的牵制,导致我比较谨慎,没有过多地随风起舞。打个比喻,起风了,没有翅膀的小猪,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观察、思考、选择,而不是凑到风口上硬起飞;这样,也就不至于一旦风停下来,摔死在百里之外。
这个牵制我不至于四处漂流的锚,就是那时刚建立不久的博士培养制度。我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个博士生之一,入学当初是被寄予厚望的,自己也感觉责任重大。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和我联名发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及“三人谈”,一时风生水起,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不时被提及。可风头正健时,我没有趁热打铁,而是赶紧抽身,沉下心来经营我的博士论文。我始终记得,博士招生考试前,钱理群将我的一篇论文交给王瑶先生,据说王先生看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表扬:“才气横溢”;第二句则是警戒:“有才气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即便在最得意的时候,我也牢记这个警戒:就这么点小才气,千万不要“横溢”了。
与同时代众多很有才情的同道相比,我的好处是及早受到学院体制的规训,强调沉潜与积累,不争一时之短长,因此能走得比较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开山祖,王瑶先生早年治古典文学,有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传世。平日聊天,王先生要求我借鉴古典文学的研究思路、立场及方法。理由是,现代文学根基浅,研究者大都倾向于现实关怀,在当下思想解放大潮中可以发挥很好作用,但长远看,是个缺憾。当初,《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好几位日本学者对我自序中这段话感兴趣:“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采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时代年轻气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都思辨性强而实证性弱,接近文学创作而非学术研究,而我的书有点特别。了解师承后,当即释然。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后,读者一般关注上编的“输入新知”,我则更看重下编的“转化传统”。这里牵涉一个小八卦,若你到北大图书馆查我的博士论文,会发现题目不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是《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好笑,当年北大很穷,规定博士论文只能打印十万字左右。我和王先生商量,上编见功夫,但下编更具创见,因而裁剪成这个样子。答辩时,樊骏先生说我忽略一个问题,我说有的,在上编,接着哇啦哇啦说了一通;再提一个问题,还是在上编,又哇啦哇啦一通。大家都笑了,说你们北大不能这么抠门,既然都写出来了,不要藏着掖着,让答辩委员猜谜。记得第二年起,这个制度就改了,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全文打印,不限字数。不过,这一不得已的裁剪,也可见我们师生的趣味。日后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下编的好多论述,直到今天仍有生命力。
得益于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的时代潮流,但又因学院体制的保守性,对此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与警惕,防止走向另一种“以论带史”——在一个学术革命的时代,带入常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这或许是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好处所在。
这就说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是八十年代我喜欢读的书。他谈的是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问题,可我以为对于人文学者同样有启示。库恩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一旦旧范式解决不了新问题,科学家们必定锐意创新,经由多年努力,若在理论、观念及方法上有大调整,且成果明显,那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没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可也正是这一观念,导致我的小说史研究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十年间写了五本书,除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较大的还有《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此书流播甚广,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刊行了英译本。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不再从事小说研究,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常规建设,好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我需要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及话题。
因此,最近二十年,我左冲右突,力图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处耕耘。像《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都因其在学术立场、理论设计及研究方法上略有创新,而在中外学界获得好评。可我很清醒,已经不是八十年代的语境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影响力。一方面好手如林,学问的领域、技术与境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课题优先,数字为王,个人特立独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在学术革命的时代保持对于传统的极大敬意,而在常规建设时期又老是突发奇想,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上的冒险性格,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精神遗存。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进入常规建设,还有一点我必须调整,那就是如何处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学界开始分化,有人埋头学问,不问窗外的风声雨声;有人进入大众传媒,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书斋。九十年代初,我有一篇流传很广的随笔,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谈的便是这种艰难的抉择。如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经由一番摸索,我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介入现实、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特殊窗口,那就是大学史与大学研究。二十年间,先后出版七八种相关书籍,若《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都是兼及学问与文章、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在教育界及大众中有很好的口碑。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在回应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
《大学何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获奖,促使我反省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利弊。谈不上特立独行,同样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只是略有规避与调整,不至于太随波逐流而已。接下来的日子,还有若干著作在认真经营,希望对得起这个奖项以及广大读者的期许。
本文为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