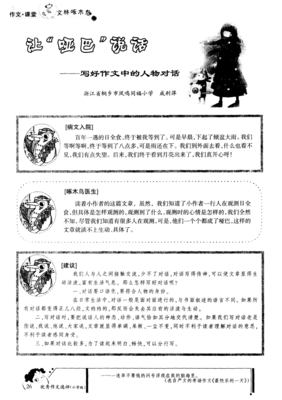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学生能言善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生动幽默,招人喜欢。但如果是让他把自己与别人说的话变成文字,却一下子犯了难,不知该如何下手,即使勉为其难,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人物对话也如瘪三,又枯又瘦,令人不忍卒读,与他从口中说出的话简直有天壤之别。
同一个人,同是说话,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口头语言,一个是书面语言,为什么会反差如此之大呢?看来,要把人物对话从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如何才能把我们生动的口头语言原汁原味地转化为精彩的书面语言呢?下面,我想通过例文的修改来说明。
例文:
那是三年级的时候,大舅来我家,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对我说:“兰华呀,你也七八岁了,还不会骑自行车,别人会笑话你。”我说:“舅舅,你对我太好了,谢谢你!”舅舅对我说:“那你就开始学吧。”
上文是“我”与“舅舅”的一段对话。小作者把人物的“声音”成功地转化为了“文字”,似乎人物的对话就是这么写。但我们读完之后,不免会觉得在这个对话中好像少些什么,至少是不生动,不传神。
这么说,小作者可能觉得很是委屈,会说“我”和“舅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么说的啊!为什么一写出来就变味了呢?
那么,在这个人物对话中,究竟流失了些什么呢?应该找回点什么才能再现“我”与“舅舅”真实的对话场景,使我们既“闻其声”,又“见其人”呢?
在做出修改之前,还是先来看看我们初中课本中两位“大家”笔下的人物对话片段,并以我们学生常用的口吻来修改一下吧。
片段一: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改写后: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我问。
改写后,一问一答,人物的语言还在。可“我”问先生时的特定情境和先生回答是不高兴的神态却不见了。
片段二: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们睒了睒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张洁《拣麦穗》
改写后:
有一天,二姨对我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问:“你要嫁谁嘛?”
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改写后,文字变成了“录音机”,只留了“二姨”和“我”的“声音”。人物说话时的“场景”,“我”和“二姨”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却荡然无存了,不免给人单调之感。
通过上面“大家”笔下的人物对话与改写后人物对话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大家”们“点石成金”的秘密在哪里了。
下面我们再来修改一下例文中的人物对话,看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那是三年级的时候,大舅来我家,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进门就笑着对我说:“兰华呀,你也七八岁了,不会骑自行车,人家笑话你。”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一下子扑倒在舅舅的怀里,说:“舅舅,你对我太好了,谢谢你!”舅舅用手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说:“那你就开始学吧。”
改写后,人物对话中,舅舅的一“笑”一“摸”, “我”的一一“蹦”一“扑”再现了人物说话时的生活场景,使我们不仅听到了“舅舅”和“我”说的话,而且还看到了“舅舅”和“我”说话时的神态与动作。这样,这段文字就不再是“留声机”,而是“录像机”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要写活人物对话其实并不难,就是把人物对话的真实场景用文字还原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用文字把说话人说话时的神态、动作细节传达出来。这样,也就能做到既“闻其声,又“见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