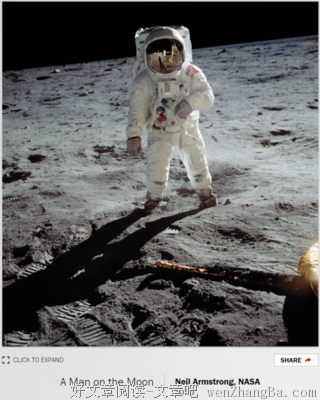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许多人都患有“知识焦虑症”,唯恐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
跟上现实的脚步尚且不易,我们还有必要学习历史吗?或者说,学习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用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关乎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今年,我们邀请台湾作家、著名的“经典摆渡人”杨照开设了一堂讲史记的音频课程——《古今:杨照史记百讲》。
杨照是孜孜不倦的经典引介者。同为经典导读者的梁文道对他评价“无论是中西各种典籍、无论哪一部吓坏人的经典巨著,他都可以娓娓道来,讲得深入浅出”。
白岩松也是他的读者和听众,他说“面对浩瀚的经典,杨照是个很好的‘导游’”。
目前《古今:杨照史记百讲》已经更新完毕,我们向听众和读者朋友们征集了一些听课过程中的问题,并邀请杨照对部分问题进行了回答。
这些问题所反映出的困惑,很具有代表性;杨照老师的回答也很精彩。
关于为什么要阅读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即使你没收听过这个节目,相信看完这篇文章也会有收获。
本文约5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文章很长,但很值。
讲述 | 杨照
1.司马迁式史学,提醒我们凝视时代的少数人
@ 六月
国士之风也好,文人风骨也好,前朝前代有许多的文字记载,克服了时代的局限、人性的弱点,光照古今。为什么信息传播越来越快的当代,这样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思想行为肯定是有其时代的印记,这种缺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吗?
@ 梅菲
从我个人不那么多的经验来看,不管是被很多人向往的古典时期,还是现在所谓人心不古的时代,其实都有很多仁者、智者和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往往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受难、被淹没,所以生活在当下的很多人就会觉得,怎么过去有那么多这样值得尊敬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呢?
然而其实可能并不是没有,而是他们也在这个时代受难,正在被淹没。也许到两百年之后,他们的品行才能昭彰。想请问杨照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不埋没英雄的好时代?
杨照:我觉得这两个读者的提问,构成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对比对照。甚至 @梅菲 的提问,几乎就可以帮助我回答 @六月的问题。
容我这样讲,在历史给我们的经验上,我想有一件事情近乎是宿命。每一个时代,要让社会能够运作,这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固定的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当它越是能够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符合,它也就必然对不那么能够按照这种价值观去行事的人,产生越大的压抑。
换句话说,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运行,必然有着集体跟个体这种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基本的冲突。
从来不存在一个时代,真正能够让所有的个体,都能发挥他的自由和个性。
德国的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有一个基本的理想。回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时代,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所进行的那种政治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保有了每一个人的复数性。
什么叫做保有每一个人的复数性?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
苏格拉底所想象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如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找到一个哲人王,找到一个最聪明的人,让他设计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所有其他人都按照这套制度来行事就好了。
苏格拉底不相信这个,或者说这不是苏格拉底对政治的基本概念和看法,苏格拉底要的是什么?
他在街上用他的对话法问每一个人——“你在想什么,你真的相信什么”,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跟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民调又不一样,因为苏格拉底念兹在兹、用心用意,不只是要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更进一步地问你:“你真的这样想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吗?”
用这种方式,每个人内在的个人性,被苏格拉底给凸显出来。
苏格拉底相信,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弄清楚我们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我们支持什么、我们要什么,把各个不同的人的意志全部集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秩序。
这个集体秩序是在每一个人的个别的意志下,所综合调配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实现过,但是对这个理想,我们仍然应该要有所关心或有所重视。
因为从这样的理想,我们就可以对照出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现实的时代、现实的社会,它必然形成了一个主流的观念想法和行为模式。
而在主流的压抑下,也就必然有许许多多的少数人,他们一定会被牺牲。
这里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太史公式的(司马迁式的)史学的自觉。
历史应该要做什么事?这就是因为我们明明白白知道,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种少数意志被压抑被淹没了,所以历史要去挖掘,要去记录这些少数者。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史记》跟我们以为的,或者是我们过去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历史著作,就是如此不一样。
司马迁就是没有要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大潮流是什么,它的主流是什么。
如果历史只看大潮流,只看主流,就不需要史学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由过去所留下来的记忆,这(主流)是最容易被记得的东西。
需要有一个史学家,他必须要消化这么多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眼光——史学家的眼光。
历史之所以存在,就是努力依照“梅菲”在她的问题里问我的,也就是我们努力在历史中创造的——不埋没英雄的记录。
同时这也就解答了@六月所提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时代发展的必然,如果有一个必然的话,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淹没这种少数人。
这牵涉到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认为反正主流就是对的,我跟随着主流就没问题的话,说老实话,那我们不需要历史,不需要司马迁式的历史。
可是如果你认为,一个大的潮流、一个主流,它抹煞了所有其他的多样性,所有其他可能的话,那这个时候,司马迁式的史学概念,就发挥了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它提醒我们去凝视,跟我们相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少数人。
这些少数人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因而可能必须要接受被惩罚、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种种不良遭遇,为什么他们还是如此选择?
我们要去看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如果我们被他们感动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把他们不一样的生命情调,让更多人理解、知道。
这种司马迁式的史学观念,还可以发挥另一个作用,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历史,因为在历史里面记录了人类的多样性。
同一个时代,有各种不一样的人;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开,跨越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人的多样性,当然就更多。
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刻意地去寻找,不是寻找跟我们当下现实主流类同的行为,相反,我们要去看除了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主流行为模式之外,人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可能性?
因而我们对于人性、对于人的认知和理解,就可以打开来。
2.现实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约束能力
@ 大鲵啊
在听杨照老师讲《史记》的过程中,我多次被《史记》中所记载的人物的人格精神所感动。我想请问杨照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从《史记》中获得的历史经验,与生活认识之间产生的冲突?在阅读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发现史书中的谬误之处?
杨照: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历史经验和生活认识之间会产生冲突。
如果会有冲突,我认为那不过就是我们把现实生活看得太严重了。
所谓把现实生活看得太严重,也就是我们以为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跟随着现实、考虑现实、符合社会的一般大众主流的期待,是我们生命唯一的选择。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如果你那么尊重现实,那么害怕现实,不敢面对现实而做自己不一样的选择,那当然,不只是历史知识,所有的不符合这种现实主流的知识,都会让你感觉到有所间隔。
但是重点是,现实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约束能力。
因为那是取消我们个人自我的一股强制力量。
你还是一定要问,或者至少保留问这样一个问题的基本空间——我自己是谁?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行为和道德标准作为我的原则,是让我最自在的?
如果你用这种态度,而不是必然依循着现实给你的标准答案,那你就会发现,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方式所得到的历史经验,跟生活认识,一点都不冲突。
历史经验应该是不断在帮我们扩充生活认识的。
@大鲵啊所问的第二个问题,牵涉到的是史学方法论。阅读历史的过程当中,怎么发现史书当中的谬误之处,容我分三个方向来回答。
第一个方向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一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养成一种犬儒的态度,这种犬儒的态度经常会说:“反正历史都是假的,反正历史都是人编出来的。”
历史都是人编出来的,那为什么要史学专业?为什么要史学方法论?也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标准,在不一样的记录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去分辨它的事实性,相对的事实性。所以这是第一个,不要用虚无犬儒的方式来看待历史。
第二个,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分辨历史当中的事实和应该存疑的地方,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常识。所谓的常识就是你怎么认识人,你能不能认识人的多样性。
这个是像蛋生鸡,鸡生蛋一样的循环,如果你读越多的历史,读越多的小说,读越多跟人类行为有关的东西,包括心理学、精神分析,累积了越多这样的经验和知识,你所看到你所认识的人越来越复杂,但同时他在复杂当中有越来越清楚的行为逻辑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用这种常识去判断,在历史的记录上面,有哪些事是违背逻辑,是不合常理的。
在现实的人生中,在对人的基本理解上,没有那么多单面的人,没有单面的纯粹的好人,也不会有单面的纯粹的坏人,所有的人一定都有各种复杂的面向。
单纯的好人,纯粹的坏人,我想在历史上面,如果用这种方式记载下来,都不值得被相信。
第三件事情,我所要说的就是,如果你还要更在意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历史材料的比对当中。这种历史材料的比对,就没有办法三言两语地去说,因为它牵扯到功夫。
例如,你面对所有的历史资料,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必定是要了解它背后的记录者。就如同当我面对《史记》,我一定要认识司马迁是谁,我要知道司马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还有我要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司马迁基于什么用心,为了回答什么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记录他所写下来的这些历史。
你只要能够找到越多关于这个记录者的资料,你就越能够用你的自主判断,去看待这些记录到底哪一些是可信的,哪一些是值得被放进括号里,值得被进一步探究的。
另外,同样的时代会有不一样的人留下记录,同样都是汉朝,我们可以从贾谊的书里面,从扬雄的书里面,从各种不同的其他书籍留下的资料中,去进行比对。
同一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掌握了越多的史料,就可以越精确地透过史料之间彼此的对比对照,去做这种事实和存疑的判断。
这就是历史学所不断强调、不断精进的基本功夫。
我们永远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史学所要做的事情,那就要做ever reaching star,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到天上,可是我们会尽量趋近那个理想中的境界,那个远在天边的星星。这是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
3.延宕那种把历史和现实对照的冲动
@ 璋
您觉得读史,尤其是拿史书跟现实对照,这是一种阅读的深化,还是对于理解的妨碍?
杨照:如果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单纯的对照,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把它拿来对照现实,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一种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妨碍。
例如说,当我们看到历史上有暴君,你就说“现实里也有暴君”,历史的暴君跟现实的暴君,应该怎么样对比对照。
或者当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欺诈,现实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欺诈,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对比。
这种简单的对比,是出于我们对现实的关心,所以它必然产生的一个效果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安下心来,有耐心地去理解历史。
历史最大。让我再提醒一下,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它不是现实。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那是一种不同的社会,那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他会环环相扣,扣出不一样的因果。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放掉许许多多现实给予我们的刻板印象。
人是如何,什么样的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必须先把现实里面的这些习惯的印象放掉。我们要尽量回到历史的时空来认识历史,所以在这样的阶段,在这样理解的过程中,我会希望提醒大家、劝大家,不要那么快把历史跟现实对应对照上。
我知道,“璋”试图要问的是“但我们好像很难抗拒这种冲动”。我们可以延宕这种冲动。
什么叫做延宕这种冲动呢?那就是当我们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想要认识的是什么,我们真正想要认识的是,借由历史所展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多样性,更深刻地了解人的动机、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这彼此之间的一环一环复杂的因果关系。
如果你用这种用心去了解历史的话,那你再倒回来,当你已经从历史当中能够对人性人心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你再回来对照现实,这个时候这两者之间,就能够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构成了妨碍。
我一方面还是希望不要那么简单地古为今用,这是一个提醒。
但是我也同意,我也承认,如果我们学历史,不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的话,这样的历史知识,它也是空洞的,甚至是浪费的。
古今:杨照史记百讲
“一个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知道世界有多大。《史记》跟很多经典一样,它在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的现实。”
——杨照
订阅收听方法
“听理想”系列节目已开通在微信公号收听的功能,具体使用方法请看下方说明。
【订阅&收听方法说明】
1.如果你 想在“看理想”微信公众号购买、收听:
扫码下方二维码or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进入“看理想”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视频音频”-“杨照史记百讲”即可收听。
2.如果你 想在豆瓣APP购买、收听:
打开豆瓣APP,搜索“杨照”,点击搜索结果“古今:杨照史记百讲”,即可购买、收听。
3.如果你 已在豆瓣APP购买,想在“看理想”微信公号收听:
搜索、进入微信公众号“豆瓣时间”,点击菜单栏“我的时间”-“绑定豆瓣”,完成账号同步,即可在看理想微信公号中收听已购买的节目。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lwx@imaginist.com.cn
转载:微信后台回复“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