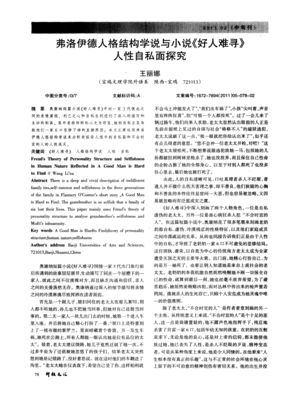
《好人难寻》是一本由[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好人难寻》读后感(一):评《好人难寻》
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几个短篇的结局总是有很大的留白,并且是在故事极度转折或是主人公遭受巨大痛苦之后的留白,而十分不适;没有想到读完全本竟意犹未尽并喜爱起那些无奈的残忍的结局来了。作者用夸张(文章内容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但或许对于那个紧张的时代而言,这是真实的一个缩影)而细腻的方式写生活的残缺身体的痛苦内心的挣扎,来讨论来揭露宗教,欧洲难民,奴隶制结束后遗留的种族问题。
读书时直面着他人的痛苦,悲愤无奈的同时又不愿停止阅读这些有力的文字。
《好人难寻》读后感(二):三块广告牌
奥奖前无意中看了三块广告牌的电影图解,鬼使神差的留意到女主第一次付款给广告公司老板时,老板在看的,就是这本“好人难寻”。就这样买来看了。现在差不多看了一半的故事,最明显的感受是,人活一世,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不必失望,不必受伤,因为人的复杂性,已经让身为同类的我们丧失了一颗真正明白的头脑。所以没关系,彻底放松下来好了,承认人类的复杂性,做好防御,尽量理解,尽量周全,尽量漂亮一点点,活下去。
《好人难寻》读后感(三):《好人难寻》一把普通的布椅下隐藏着一根带毒的针
读了一半才发现这是个女作家。真是完全感觉不出来啊。我最近对性别的判断真是都是反着来的。
《一次好运》在爬楼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爬楼的过程漫长的像一个世纪。她认为保持年轻、不老长寿的秘诀是,不生小孩。她毕生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以诺与大猩猩》失败的人生不需要过多解释。世界的冰冷和冷漠让他宁可去做一个猩猩。
《好人难寻》自私、冷冷的恶意,我想出不其他的词来形容这个老太太,就像平常的布椅子上的一根带毒的针,她一步一步带领全家走向死亡。
《临终遇敌》虚荣的落空。活在虚荣里的萨许“将军”和他62岁的孙女的虚荣的梦境的破碎。
《救人就是救自己》农夫与蛇的故事。救人害自己。人心险恶。
《河》在这这冷漠的世间,走入河里走向死亡竟然悲催的不是他最坏的结局,是他最好的结局。
《火之怪圈》使我想起了《午后四点》,不想被打扰和死皮赖脸的打扰之间简直是场噩梦。
《流离失所的人》使我想起了《一场实现。。》结局是毁人不利己系列。
《圣灵之神殿》关于宗教,身体与灵魂,这个孩子是有前世的记忆吗。
《黑人雕像》喔喔,来大城市的恐惧和慌乱。每个人一生中仅仅是对抗身边最亲的人的伤害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善良的乡下人》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善良的乡下人,每个人都是复杂甚至恶毒的。以窥视别人的弱点缺陷为乐趣。
《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活着的人更可怜。
《好人难寻》读后感(四):奥康纳的“邪恶”与基督信仰
奥康纳是我继远藤周作之后第二位极为欣赏和推崇的小说家。不愧是在大名鼎鼎的爱荷华工作坊学习过的人,精致、简洁、善用比喻,你能感受到作者的对叙事节奏完美的控制力。一些事件经过变形和捏合之后,而在一条宽阔的河床里随意自在地流淌着。
奥康纳热衷于且擅长写人性之暗之恶,对待这样的黑暗与邪恶,她的小说如手术刀一般锋利,绝不手软全无怜悯。出身南方传统天主教家庭的她,是一名虔诚但理性的天主教徒,在美国新教徒包围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小说无一不和基督宗教信仰有关,但绝不是福音宣传品,更不是护教文学(如果是的话我也不会向非基督徒推荐了),她始终拒绝在小说中直接传递正统的信仰告白,反而经常用一种disturbing的“暴力”手段,把信仰与人性的尖锐冲突以一种近乎无情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刺激读者的神经,挑战读者的道德良知与信仰反思力。
如果对基督宗教没有相当的认识,对新旧约故事缺乏了解的话,中国读者有可能会把奥康纳的小说看作是敌基督的作品。但事实上这正正是奥康纳对信仰和人性极度深刻理解之后的产物。
最近因为山大学伴事件,我想起了奥康纳的小说,因此想要重读。出身南方富裕家庭的她,在多篇小说中涉及种族问题,尤其善于揭露一部分基督徒的伪善。奥康纳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表达她对信仰的认识:“人们意识不到的是为宗教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们以为信仰不过是一条热毛毯,但其实它是十字架。信比不信更艰难。”她毫不掩饰地指出:“每个人都以信仰为情感依托懒散度日,这种想法让我讨厌。”
《好人难寻》读后感(五):冷血的书写多像暴风雪
奥康纳是个冷血写手。
她不写性。这可能与其信仰和教育有关,但是完全没有情欲的润滑,小说显得像一颗核桃一样庄严而有质感,适合雕刻,刀刀虽则不见血,你是否也能感到疼?!
她不写故事。你以为她在跟你讲故事?!她才不。她挥挥她修女的衣袖,翻云翻雨,不翻彩虹。她拿起笔:
在阴暗树林的延伸带,一屋檐下的人呆坐,阴蒙的脸微低着,让人看不清,越看不清你越想看清,渐渐地,看的人转入一场奇妙的幻境:在阴暗树林的延伸带,一屋檐下的人呆坐,阴蒙的脸微低着,让人看不清,越看不清你越想看清,渐渐地,看的人转入下一场奇妙的幻境……
她不写诗。诗是浪漫的,她写的是现实,以诗的语言写非诗的现实。刷刷刷几笔,一幅速成涂鸦,怪诞的象征,魔怔般惹人在脑门里周而复始地播放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虚幻得不真实,又真实得可怕。
她不怜爱谁。她笔下的人物,似乎从不需要人的怜爱,得胜的得胜,活该的活该。她似乎在说:你如果没有为人的力量,何必做人?!
十篇小说,死掉十个,却似乎还没死够。她模仿着真主的表情,阴冷而诡异地咧开嘴,慢慢微笑,你不知道她在笑什么,也不知道她下一个笑里会晕开一朵怎样的血花。
她不老实。她从不老老实实写一个事,她总带着放大镜近距离去看浮世。她要看得螳螂的腿大如大象,干掉大象,最后,螳螂之腿也会因过度被光线聚焦而灰飞烟灭。她极想借这或真或幻的螳螂之腿翘起我们星球的良知。
《好人难寻》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
《好人难寻》读后感(六):噢好的
又是一本持久战,“有始无终”似乎是我打小以来的阅读模式,记忆中除了武打书和几本犯罪/推理小说是没有拉锯的,其他几乎都是同时和另几本读物一起“这本看不进去了拿起那本再那本再那本”… 购书网站的推荐文读来颇合我的心思--没有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每个人的出发/行为动机都是因为利益,或者欲望,或者社会规范,父母对孩子也是如此--人之初性本恶论;“看透人并不难,但于己无益”;很想看奥康纳如何撇去“没有文学只有自传”来绘述;~其人正文未读已有二三想象。 等书到手读了两篇后觉得她的文风并非售书网站所宣,却使我产生新的兴趣,她的故事对我来说有些奇异猎奇,虽然如此,但隐约觉得世上某个角落确实发生着这样的事,比起那些令人匪夷所思但因“司空见惯”而不那么“大恶”的“大恶”,有时“小恶”似乎更令人接受无力些。譬如书名篇中的老太太,老太太也就算了,大概人近末年总得找些事情来维系对生活的“参与感”,其行为轨迹思想形态也大概算是屡见不鲜,可两个孙子孙女对她的“接口令”却是让我“耳目一新”,几次读到对俩孩子的描写,散漫游走的元神“为之一振”,又能再次“融入”进去。再是那位“流浪汉”和“其妻之母”。对奥康纳最大的想法在于,她笔下人物之恶仿佛是自然而然是理所应当的,她完全没有批判没有怜悯,这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大概因为太自然才透着些诡异。不知奥康纳是在听来的故事中运用主观想象将其写就为奥康纳式故事,还是事件本就如此她只是复原出来--此二种来自昨天在饮品店座位上的突然发散--这书大概真的是有些魔法书的意思,在家看联起一众小说电影,在外看,我昨天人生第一次觉得我能一气写个长篇小说--是奥康纳洇蕴在她读者身上的“咒语”之一么?经常想人只要有个基础两千字的词汇,再只要有心有闲,谁都可以写出个传记体或者传记瞎掰五五开的什么,集体住房的可以繁花式米格尔大院,独自沉默的可以好邻居人生拼图,无甚,扔时间而已。
《好人难寻》读后感(七):从对立的人物距离到讲述角度的位移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短篇小说多是从人物的相遇写起,从人物的截然对立。在对立的两极中,暗暗铺陈,填满其间的全部距离。在人物面对面的距离之间,在惊奇的故事和沉着的讲述之间,在残酷的情节与悲悯的内心之间,展开情节的转折与内心的顿悟。
在《比诺与大猩猩》中,到处遭人嘲笑的狼狈怪小孩比诺夺取了电影明星大猩猩的皮囊,期待着可以像电影明星那样,接受众人排队握手。讲述者一边展开故事,一边介绍人物。却在抢夺的激烈时刻退后一步,从遥远的距离之外观看着比诺变身的过程,再步步走近。故事以人物的身处其境作为收尾,将人物对外界的感知作为镜像,折射比诺变身之后的吃惊,失望与再次的孤独,落寞。
在《圣灵神殿》里,一边是喜爱恶作剧,顽皮而虔诚的孩子;一边是两个对修道院教育嗤之以鼻的轻浮刻薄的女孩。讲述者从始至终紧贴着孩子的角度,呈现她由面临宗教对自身的怀疑变为认识到宗教机制也并非理想化,人物的对立关系逐步弱化。在情节之上的又一层面铺陈的宗教象征——找寻的光,也从耀眼的象牙色烈日,变为鲜血般浓烈的夕阳,在象征层面展现孩子内心的变化,对信仰的抽象化与升华。
然而在《火中之圈》中人物的对立更体现为隔阂与冲突,结局也另有含意。不受欢迎的三个顽劣少年来到农场,与主人不欢而散后,纵火点燃了整个农场。讲述者一直从女主人的角度叙述少年越轨行为的不断升级,却在故事的结尾离开女主人的角度,转向中间人物,打破了两边人物的严格对立,甚至转向对少年的理解。如文末所言,故事里所有人的共同之处是“痛苦”,痛苦源于对农场的热爱:少年对农场的热爱体现为纵情玩耍,久留不愿离去;女主人的热爱体现为责任和忧虑,两者的对立彷佛硬币的两面。结尾之后,反观故事中的少年,三人的轻慢与放纵同时亦是敏感,骄傲和倔强叛逆,而女主人的感恩之心也不免冷漠与严厉。
《临终遇敌》的结尾则似乎推翻了故事全篇。爷爷和孙女有着同一个荣誉计划:老将军要出席老师的毕业典礼。孙女要借此自豪地向世人展示她“身后的一切”;爷爷早忘了过去,只一心想站在台上。然而面对眼前黑压压的队伍,耳畔的音乐与历史词语,过去并未像将军声称的那样无足轻重,早已抛之脑后,反而汇聚在一起,再次来袭。讲述者贴近爷爷这一人物,详细描述了记忆如何再度步步逼近,使得老人在台上身陷枪林弹雨,而后又瞬间跳跃到台上自豪的孙女的角度,轻描淡写地交代了爷爷的逝去——过去并不像爷爷说的那样早已遗忘,孙女也许并不关心这“身后的一切”的含义。两个人物在结尾都发生了反转,同时爷孙二人构成了对立关系。
向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致敬,向译者老师致敬。
《好人难寻》读后感(八):有些道理总要在临死前懂得
这是本独特的小说集,但我直到最近才听说它的名头。我在很多书里看到评论家对《好人难寻》这篇文评头论足,说它结构好,文笔好,但是邪恶,邪恶得令人难忘。这些评论一再激发我对好人难寻这篇文章的兴趣,直到我得到奥康纳作品集才终于得以一探究竟。
奥康纳是个不幸的女人,家族遗传性红斑狼疮在她39岁那年就夺去了她的生命,而死前她一直在家乡依靠养孔雀为生。特殊的身世背景使她的作品戴上一层悲观与不幸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命运的不公与宗教的无用感。
就拿好人难寻这篇文为例。主人公是个精明刁钻,爱耍滑头,虚荣,浮夸的老太太,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是不幸的命运偏偏选择了她。她想去田纳西州,她儿子却要去佛罗里达,于是她绞尽脑汁与儿子媳妇以及孙子孙女周旋,她设法引导他们回想田纳西州的美好风光,诱骗他们更改路线去某个她实际上记错了位置的庄园,结果不幸的翻车并在求援过程中遇到了通缉犯,到最后佛罗里达没去成,倒丢了全家人的性命。
与平常好人有好报类的作品不同,奥康纳作品里的主人公的命运大多是不幸的死亡,而且是并未犯多少错误或犯了一些微小错误引起的死亡。老太太犯的错是诱骗家人更改路线,偷藏猫咪上路,直接喊出通缉犯的身份,虽然罪不至死,但在奥康纳笔下,这些不幸的巧合足以使他们毁灭。
可笑的是,老太太明明对宗教并未有多少了解,却口口声声在死前希望罪犯能够念在基督的面上放过他们。她试图劝导对方,可口里的言辞毫无信服力。罪犯倒说出了不少值得人深思的句子,正应了“肤浅的好人与深沉的罪犯”这两种独特身份的对立。
不过老太太在死前还是领悟到了自己的错误,作者借用罪犯的话点明了这点:
“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格格不入”说,“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全文就在罪犯说人生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这句话里戛然而止,粗看之下这篇文就是讲了个小故事,但细读时感觉作者表露了很多。
有些人活一辈子也不会问生活是什么,有些人却要知道生活的意义。文中提到这句话,前者令人想到老太太一家人,后者令人想到这批罪犯。作者没提到罪犯的确切罪行,或许罪犯原本就无罪,但是硬加的罪使他们成为了被逮捕的对象。而他们想要寻求的意义,也正是他们想要活下去的目的与勇气。
整篇文虽然短小,但每一句都精辟到极致,没有一句废话,就连写景都是恰到好处的描写,令我忍不住看完以后想再多看几遍。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
我不太喜欢周嘉宁把罪犯的称号“格格不入”翻译作不和谐的人,还是格格不入这个代称更容易令人在头脑里产生罪犯的形象,看着和常人无异,却散发着独特的令人心惊胆寒的气场。
《好人难寻》读后感(九):奥康纳的恩典时刻
如果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那么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大约是因为对信仰和死亡的时刻有困惑,想看看这个成长在天主教家庭,自幼祈祷着“我们死亡的时刻”的作者,如何在故事的结构里处理最后时刻的顿悟。
奥康纳几乎全部的创作生涯里,都被病魔困于自己的肉身,但意志始终惊人地凶猛。对我们这些常人来说,死亡的必然性由于看似遥远,总是会被淡忘在生存的惯性里,但对于长期深陷于病痛的人来说,这种将死的紧迫感必定时刻在神经的末梢步步紧逼。就像菲茨杰拉德说,“这使她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将最终在死亡的语境下明晰。”所以,《好人难寻》这本书里有很多死亡的时刻,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太的死,《临终遇敌》中老将军的死,《河》里孩子的死,《流离失所的人》中波兰人的死,而最后一篇干脆就叫《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怪异凶恶的故事背后,她写的是人获得救赎的时刻,或者说上帝现身的时刻。在我存储不多的阅读经验里,我不记得读到过其它的女作者能够把人性的恶如此赤裸地直逼到地狱的路口。
读《好人难寻》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电影里见过的荒漠小镇上的武林高人,一个喘息间刀光出鞘,一剑封喉,四下仍是毫无生机的肃静,夏虫不敢鸣叫。奥康纳迅猛却不恋战,不屑抒情不做逗留,一击间迅即地将你一把扔出舒适区。奥康纳常被描述成极端邪恶和怪异的典型南方作家,但大约是因为接触奥康纳是先从她的大学讲稿和《生存的习惯》这本论文集开始,事先了解天主教教义中的殉难和必朽是其哥特式故事宽厚的精神地基,所以到开始读她的短篇时对邪恶和扭曲的情节多少有了心理准备,并不如心理预设地那么恐怖,和同为南方哥特门派的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比起来甚至相当温和。
奥康纳的大部分短篇,都在处理“恩典”的时刻,人从自己的肉身和心魔里醒来。所以在这层意义上,她的好友菲兹杰拉德说,她的故事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虔诚的宗教背景则保证了她对神秘性的严肃和尊重,这就像梅洛庞蒂谈人如何找回知觉的世界,提醒我们“思维健全的人”能从孩子、疯子和动物对世界的反应里获得新的认知体验,奥康纳对怪诞和残忍的敏感也有这样一层淬炼的意义,最终生命的向光性不可磨灭。虽然对我们的认知来说这恩典的时刻充满怪异和陌生,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纬度,它不是自我表达,不是世界的镜像,更不是寓言。我想起有一日给孩子读一个绘本《淘气的拉拉》,讲了一个喜欢捉弄人的孩子有一天在衣橱里睡着,进入全是妖魔鬼怪的恶作剧王国。奥康纳的小说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衣橱,带你去往另一个世界,当你从那里回来的时候,也很难向人描述究竟有没有带回真相,但你看到了另一维度的世界,懂得视野的局限。衣橱另一头梦魇般的世界也是实在,它诞生恶,原始和蒙昧,也诞生诗,它和我们的非理性根源在地心深处汇合成炙热的核。阅读有很多面向,同质的作者带来的舒适的心灵安抚,异质的作者带来醍醐灌顶的冲击,带着人性温情的引领型作者和用冷酷强健的大脑压迫你的作者,一样能成为黑夜里的导师。
《好人难寻》读后感(十):暴力对抗利己主义/女性的抗拒/。。。/待续
跟着书单开始看书的,发现居然是严歌苓推荐,第一次读的云里雾里,查阅了很多资料明白一些了。
《救他人就是救自己》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流浪汉谢弗特利特出现在一个略有财富的寡妇和她的傻女的庄院里,以帮忙干活的名义留下来了,老妇起了嫁女儿的心思,并如愿以偿了。但流浪汉登记后把女孩丢在了路边餐馆里扬长而去。那么谁救了人呢?为什么说救他人就是救自己? 流浪汉这个人应该代表的是一种每个人都有的无法逃避的人性, 奥康纳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些史福特利特的模样:逃离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口是心非,却伤感于童年和对母亲的回忆,不会遵守任何标准 ”他抛弃了自己没有行为能力的妻子,企图通过这种邪恶的暴力行为去对抗他认为已经腐烂的世界, 但“暴力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最能明细地显示我们本质的极端情境 ”。他把搭车的男孩认为是同行的知己,却遭到了暴力言语的攻击,此时他对之前的看法产生了强烈动摇,他渴望着乌云落下。我认为他上路后开始注意到乌云其实就是他内心对自己所作所为后产生惶恐不安的质疑。于是这个时候乌云落下,他得到了自己的救赎。这个人的彻底崩溃解构,其实就是奥康纳想要表达的,救他人就是救自己。 另外,文中出现的人物就五个,主要角色三人,实际上这三人的名字也是有所深意的。看相关文献说, 史福特利特(Shiftlet)中的“Shift”意为转变。我猜想他是曾经持有最大的善意来面对世界的,如今却使用一场暴力来处理这一切事实;露西奈尔(Lucynell)中的“Lucy”词源意为光明和智慧,一种讽刺吧;克里特(Crater)表示弹坑或毁灭,预示着这位老妇人得到的只是绝望的余烬。
《一次好运》
这篇很有意思。开始看第三视角讲述,让读者一开始就对主人公有所反感,而后接主人公第一人称,以她爬楼梯的视角讲故事。 我特别注意到的一点:八十七号公路认识的祖丽达太太觉得对鲁比来说怀孕是她的“好运”,而实际上呢,她为自己怀孕的事实想作呕,当然最后她因为熊孩子的冲撞流产了,不知她心里是喜大于忧吗。女性拒绝生育这一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唤醒。但作者却以常规的世俗男性的看法来写这件事情,让读者会下意识代入觉得鲁比确是有了一次“好运”,所有人都在祝福她拥有了“好运”。只有她觉得世界天塌地陷了。
《好人难寻》
这个故事其实挺好理解的,作者写的并不晦涩。老妇人是怎么一个自私自利、漠不关心他人、虚荣、爱撒谎的形象通过故事的细节和情节写的很清楚。前文就一直铺垫,她为了见熟人一直想去另一个地方,临时编造谎言导致翻车后又说谎说自己受伤了,之后她的儿子、儿媳及孙子孙女被拉去杀死她也只是祈祷耶稣,企图感化暴徒。面对暴力的恐吓,她一直在祈祷上帝。这不是说她是一个多么虔诚的信徒,这是她认为,我给了你信任,你就要给我我要的安全,保佑我。最后快轮到她的时候,她才忍痛说愿意给钱,因为免费的庇护她得不到,她只能用钱财换命一条,当最后她绝望了,她才撕下面具,说了最真诚的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啊”,然后迅速被杀。这也是奥康纳想表达的:暴力与利己主义的碰撞。只有暴力能让虚伪的人吐露真言。
本文最精彩的一定是“好人难寻”主题。就是那句话“她应该是一个好人,如果每分钟有人给他一枪的话”。每一分钟有人逼她说真话的时候,她才会撕开自己虚伪的面具。
《河》
耶稣、河流、天国与骷髅、猪,看似很邪恶,实际上是讲述缺乏与宗教接触的一个孤独的小男孩的灵魂错误的自我暴力救赎。正如奥康纳自己所言,贝弗尔的无知不仅仅因为他极其年幼而且也源于他完全与宗教精神生活的隔绝。
他来自一个对他漠不关心的家庭,然后最后死于对灵魂的解放。这种死亡带有暴力却不邪恶,但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最后旁观的老人出现的意义是什么,他的冷漠是表明人们对小男孩的死无动于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