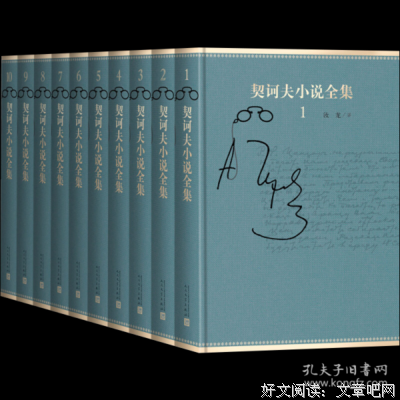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是一本由[俄] 契诃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6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点评:
●1987年后的契诃夫,真好啊
●从作家到读者好像没人不喜欢他的
●1903年,契诃夫写出短篇小说《新娘》。他在故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精神。我总提防着《新娘》的故事情节,担心契诃夫会在某一个时刻话锋一转,自另一个角度将故事重新拖回到泥淖中去——毕竟,我想任何一个读者在将这篇近七十万字的选集阅读到它的最后十页时,应该多少都已经对契诃夫的态度有所了解。《新娘》拥有着一幕动人的结局:“重要的是把生活翻转过来”;“整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缩成了一小团”;“她觉得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契诃夫说。以后,与虚伪、暴力和丑恶抗争了一辈子的契诃夫,在写出了《新娘》以后就此停笔,并在与哮喘和心力衰竭展开的三年斗争过后,与世长辞。事实确实是这样——面对契诃夫对生活表现出的乐观情绪,生活慷慨地将死亡作为礼物回报给他,回报给写作了《新娘》的他。这难道不是生活的幽默吗?我说。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契诃夫小说集里……
●这版中国翻译家译丛定价装帧用纸都是极有良心的,轻型纸带不来的那种厚重感,一些文字应该是带有重量的。通篇下来,上学时课文摘选的自然是经典中的经典。《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套中人》等,上学时候看出了什么呢,现在回看,真是赞叹。契诃夫的短篇写的真是太好了,这一本书中所节选的,还真没那篇差的,短篇看的人有精神,想一直看下去。结果后大半本都是中篇和近长篇... 中篇就不是那么喜欢了,感觉契诃夫这本书里的中篇都是紧紧围绕核心的,但就是看的不怎么愉快以至于拖拖踏踏看了二十天。契诃夫的妙还是识不到啊,恳请懂得豆友推荐两本。
●按时间排序可以清楚的看到契诃夫小说的变化发展,早期看的很有趣,后来时期的作品则多了许多沉重
●可以。
●只读到了“苦恼”,唉
●契诃夫,身边似乎没有喜欢他的作品的,其实他就是人人都知道,但都没去读的作家。
●没看完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感(一):《第六病室》一点读后感
我想说不定这小说探讨的是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当然人生在宏观上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医生身体力行的诠释了顺其自然的犬儒主义,他的结局虽说是料想之中的死亡,是否也让读者感到某种怅然若失,如果明知人生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是否还需要反抗?
契柯夫其实在大多数小说中都提到了空虚这个词,与其说讽刺,不如说提出了疑问,人生空虚在所难免啊。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感(二):契诃夫就是完美的标准
契诃夫的文字就像鸦片,少许就是快感,高度浓缩的菁华;笔下尤其二十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居多,他们各自纠缠在没有真理的矛盾里。契诃夫是以一种探讨式的悲悯之心解释人,一方面其笔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方面这些小人物所深陷的困境又是整个人类所不可解的难题。理性、权威、道德、价值与意义,这些东西都被无情的怀疑,都被人的荒诞所嘲讽。文风辛辣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极度理智者在这个世界是没法生存的,《第六病室》《精神错乱》,是最好的写照,一些关于人最基本的问题在所谓的当权派,和不当权派面前,探讨本身都很荒谬,人们一方面无限苦闷,一方面又在苦闷里无限矛盾,又在矛盾里深陷自我怀疑。人对于一切问题探讨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我否定,关于自我的打压并不是来自外界,年轻人就像站在荒原里,面对一片空白,无休止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个世界甚至对他什么都没做,他却陷入无形的文化里继而覆灭。这些形形色色的青年男女,关于世界、关于自我的苦闷异常相似,一个是文化的枷锁,一个便是穷困的枷锁。文化像是一个囚笼,永远绑缚着文化链中的最底层那批人,他们是文化的信仰者和追随者,同时亦是文化的牺牲者,在其面临生存矛盾时,必然会怀疑长久以来关于信仰的真理性,可是这些问题在真实的生活面前多么无力,又常常无解,这些年轻人的苦闷不会被世界看见,它们被现实隐藏掉了,这些人甚至都不屑于自我怜悯,自我怜悯本身似乎都变得可耻。所以,年轻人的苦闷只存在于艺术里,只会被人类的艺术家所看见;文学家以其嘲讽的视角、戏谑的方式向一部分人呈现另一部分人,人们在这种有选择性的呈现下,彼此才相互了解,才会看见关于人的真正真相。人的真相并不在现实里,现实的真相永远是模糊的、极特殊的、又被快速遗忘的这么一种存在。契诃夫本人就是一位医生,所以他的视角可以冷静到就是在冷眼旁观,旁观整个俄罗斯民族的苦闷,这些苦闷又高度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而这些年轻人的苦闷又普遍是全人类的苦闷,这是一种令人想要膜拜的高度,从对于某个具体对象的悲悯上升到对于所有人的思考,而故事的结局并不总是美好,契诃夫在探讨人生存卑微的困境的同时,在文字的暗流下又涌动着一种人人都不屑于在乎的隐秘力量,那就是劳动,最真实的劳动,和其戏剧《三姊妹》结尾里伤感的力量一样,人必须去工作,努力的工作,人所有关于幸福的感触就在工作里,就在自己真实的劳动里。长期以来我们都高度怀疑着奋斗的必要性,嘲笑别人卑微的努力,但契诃夫相信,相信最真实汗水的力量,人的解脱就在其中。从这个层面上讲,契诃夫的文字是健康、诚挚、有一种春风拂面的纯净之力,这种力量像是从淤泥里长出的莲花,高洁淡雅,却又排山倒海,一洁足以遮全污。契诃夫的文字有着关于人最本质的触动,这种文字是文化荼毒下的莲花,却滤净了毒素,我们只需好好享用就行,但这样的文字绝不不宜贪多,一次一小口,就足以受用好久好久,多了就像鸦片,会致死!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感(三):无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套翻译家译丛系列都特别棒!绝对是值得收藏在家里随时细品的,可恨我的无知让我知道的太晚了,现在很难买全了,尤其查良铮的到处都买不到,懊悔万分!
《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感(四):献给契诃夫 | 我们弄丢了上帝的地址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为某个艺术家疯狂的人。即便他再有才华,再迷人,散发着恒星一般的引力,我也不会像失控的小行星一样朝向他粉身碎骨。若是音乐家,我就止于他的音乐;是导演,就止于他的电影;是作家,就止于他的作品。我总是习惯在艺术面前保持机警,甚至一点懒惰,不是饿狗扑食地大口吞咽,而是猫一样轻盈地靠近,像松开一团线球一样,慢慢松开一部作品。一边松,一边嗅,时刻准备着全身而退。我大概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是远亲,和日神阿波罗是近亲。
后来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去年夏天,我和剧社的狐朋狗友在酒吧喝酒,喝了几种不同口味的洋酒,醒来之后有点断片,好多夜晚的细节都模糊了。听人说,我才知道那晚打车离开,我在车里五迷三道,说了一路契诃夫。大概是说到了《草原》,我手舞足蹈,描绘九岁男孩叶戈尔在草原上的见闻,暮色如何像蒲公英一样降临,雷电如何像原始时代一样威严神秘。后来下车之后,还表演了一段走直线猫步。
此处我的脸上应该“飞来一片红霞”。确实,对于自己失态的样子,我总有隐隐的羞愧。就像《小王子》当中那个孤独星球上的酒鬼。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喝酒?酒鬼说——因为我羞愧。小王子又问——你为什么羞愧?酒鬼回答——我羞愧我喝酒。一个宿命般的怪圈。
那个夏天的事件之后,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清醒而克制的人。我的体内深藏着一个更真实的我,他莽撞、迷醉、倾心于自我浪费。而表面上那个灵活、持重、汲汲于秩序的形象,可能只是一个笼子。像里尔克的《豹》所描述的,笼子中,“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而把这个昏眩、放纵的形象关押起来的,也许不是我,而是整个文明。
契诃夫把那个我释放了出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对任何作家都全副武装的聪明读者。至少在契诃夫面前,我缴械投降了,变成了一个傻瓜。到那个夏天的夜晚为止,一直是阿波罗的坚甲维持着我的体面罢了。而内在那个“一杯一杯复一杯”的我,恐怕早已经匍在地上,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小儿子阿辽沙亲吻俄罗斯大地一样,哭泣着亲吻契诃夫的脚了。
夏天很快过去,那年快要深秋的时候,在师大课堂,我又一次遭遇了契诃夫。是李洱老师的作家课,在下课前的几分钟,他朗诵了契诃夫自己最满意的小说,《大学生》。很短,只有两千多字。结尾,契诃夫让他的主人公说出了神启一样的顿悟:“过去同现在,”他暗想,“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
听到这一句,我在听课笔记上写下:我的心快要停住了。
契诃夫像摄魂怪一样,轻而易举地摄取了我的魂魄。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生理反应,当然,现在我可以从各种意义上解释。但当时我明白,恰恰是这种“不清不楚”,这种“无形的触碰”,才是文学之中最为秘密的交流形式。这种致命的体验,于我只有两次。《大学生》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万卡》。
《万卡》我们太熟悉了,但又太陌生了。它侧身在中学教科书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隐约记得,那时候比万卡大不了多少的自己,读完之后特别感动,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感动。等语文老师讲完,感动彻底灰飞烟灭了。《万卡》变成了一个控诉不公、揭露底层苦难的批评作品。——《万卡》的魂儿被讲丢了。
直到昨晚,我重新翻看契诃夫的小说集,从早期的《公务员之死》,到《苦恼》,到《农民》,到《第六病室》,心都基本平静。读到《万卡》,我凛然一颤。我发现之前自己从来没有读懂过《万卡》,一直在误会《万卡》,误会契诃夫。我们得意洋洋地把契诃夫和他的珍宝列入各种主义、观念的福尔马林当中,妄图永久霸占。但我们只得到了契诃夫和《万卡》的尸体。
寄完信,万卡“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在一个专属于孩子的清澈梦境里,万卡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
回过头,屏住呼吸,让我们去看他在信封上留下的地址:寄交乡下祖父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这是任何一个邮递员都无法寄到的地址。第一次拼尽全力学习写信的万卡,什么都学会了:买信封、落款、找邮筒……但偏偏没有学会留下清晰的地址。你和我,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读者,都知道这封信不可能寄到祖父手中了,祖父也不会披着冬衣,牵着小狗,在寒夜赶来抱起瘦弱的小万卡回家了。万卡依旧在滑向命运的深渊,滑向下一次的毒打、下一次的饥饿、下一次的绝望……所有人都知道故事的走向是怎样的了——只有可怜的万卡不知道。这会儿万卡依偎着梦中的祖父,在炉火旁睡着了。
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悲剧中,总会让旁观者感叹:碎吧,心。《万卡》又何尝不是一个令人彻底心碎的故事?但我的颤栗还没有出现。我的颤栗在下一秒:我突然感觉到,深陷苦难的万卡乞求拯救的信无法寄给祖父,不正像人类乞求上帝拯救的信,无法寄给上帝一样吗?
万卡的处境,也就是人类的处境:我们离开伊甸园的同时,便忘记了伊甸园的所在。上帝的地址被我们永远弄丢了。我们永失了来路。——《万卡》的悲怆,就是我们最为彻骨、最为根本的悲怆。
我坚信,契诃夫在写《万卡》的时候,他的声音一定融化在了《圣经》的声音之中,融化在了人类共同的噪音之中。《万卡》就是现代版的《逐出伊甸》。万卡就是亚当和夏娃最弱小的那个孩子。如同梵高《向日葵》当中,最弱小的那一朵花。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契诃夫的原因。这就是我不止一次地为他昏眩、迷醉、甘愿浪费掉自己整个一生的原因。他让我明白,即便如今他已经辞世一百多年,他依然没有离开过我们哪怕一步。他就在他的小说当中等待着我们,等着我们像万卡一样“在幽暗中捱着时光”的时候,一打开小说就能看到他,看到他披着西伯利亚的温暖冬衣,走上前来,轻轻抱起我们瘦弱的灵魂。上帝的地址我们弄丢了,不怕,他的地址还在——就在那些薄薄的、闪着微光的纸上。
2018.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