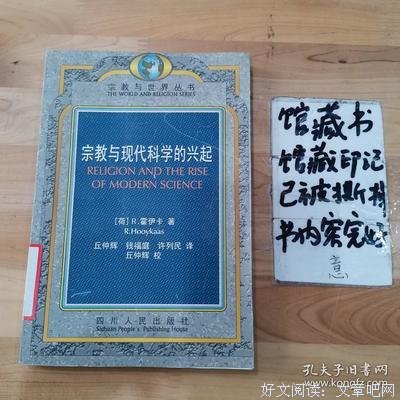
《宗教与科学》是一本由罗素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页数:1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宗教与科学》精选点评:
●宇宙的目的是什么?或许人类的产生也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羅索「沒有信仰的人不該談論人生議題」的這句話,讓我以為他是個基督徒哲學家。沒想到老先生的這本書把我遠遠地推離了信。邏輯和敘述能力極好,
●英国哲人的厉害之处就是能把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各种简单明了的是非问题,罗素更是其中佼佼者,难怪陈波老师将其推为史上最重要的八个逻辑学家之一。对科学和宗教的分歧,我和罗素的看法基本相同:各有各的领域,科学在价值领域之外。而罗素在伦理学领域则更进一步:善恶不包含真伪判断;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皆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畴。所以罗素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对分析哲学而言,世界本源这样的问题根本不算是科学问题。
●这是一部伟大的小册子。我爱他。
●我曾经以为学习足够多的数学和物理就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罗素才明白我所学到的不过是一些数字和方程式而已。
●很清楚深刻的研讨了宗教经不起科学的质疑 作者做好的是自己客观犀利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就这这个样子,不用试图解释
●还是有偏见的。。
●启蒙书籍,被当时宗教学老师说不是很有体系意义。
●russell,膜拜之~~~通才大牛现在是出不了了~~
●后两章非常好,尤其是最后一章。“自由”的个体,与群体(统计学)规律性之间是如何达到协调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各个不同的case应该有不同的机制。
《宗教与科学》读后感(一):宗教是个什么玩意儿?
前面那些不想承认宗教问题的,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缺乏信仰,他们一提到“宗教”两个字就自己切割定义到落后迷信那边去了。其实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根本价值观,也可以叫你所谓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技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是通过实践研究在试图解释世界的根本原理并学习运用它们,但是这两者本质上都没有区别,现代西方科学越发展越实践就更加会向传统宗教根本见解靠拢。举例来说,传统宗教和现代科学就好像是从两条不同公路行驶的两辆汽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一切存在的根本意义,通俗讲就是“搞清楚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宗教与科学》读后感(二):大哲学家的小册子
啃完了人类的知识,再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伯特兰勋爵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前面开头部分是对科学与宗教斗争史的一个简单回顾,后面提供了他自己对宗教和科学之争的个人看法。其实颇有点子不语的意味:由于科学只对事实认定,宗教则多涉及伦理判断,所以科学即使发展到最后,也只能把宗教中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比如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亚当命名的,神七天创造世界)证伪,而无力进入伦理领域。
后面很多地方在这里没有展开说,如果嫌罗素对时间、空间等问题发挥不够的朋友,欢迎去啃人类的知识。反过来说,如果大家没时间去读那个的话,这个算是某种缩写本吧。
《宗教与科学》读后感(三):宗教与科学之争
还记得本科时的一节外教课上,外教问一位男生为何不信仰任何宗教。该男生的回答引来了哄堂大笑,他说because I believe in science。言下之意,信科学的就无法信仰宗教,信仰宗教和科学似乎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罗素论述了最近几百年来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战争,他把主要的冲突划分为几个学科领域来进行讨论,比如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在这些领域里,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胜者总是科学。随着人类的认知的推进和对各种自然社会规律的了解的加深,原来由神学所统治和主导的领域,已经被科学所占领。在今天,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概也会相信地球是圆的,自然界存在进化的这种现象等这些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进而成为常识的一些陈述。
在面对这些对于科学极其有利的事实面前,宗教信仰者的处境似乎有些尴尬。曾参加过一次禅夏令营,在茶会上,寺庙里德高望重的和尚面对着夏令营的学生提出的尖锐指明宗教论述里明显不科学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也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宗教,走到现代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宗教与科学》读后感(四):真理是谦卑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上帝”的死活是个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主宰世间一切的一切的“上帝”似乎根本就没存在过。与西方不同,宗教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占据过统治地位,虽然曾抱持着“天人合一”式的自然神崇拜生活了数千年,但我们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民族,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惨痛轮回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支配天下苍生命途的只是那些恰巧拥有了足够智慧、勇气、武力或者好运的人类同胞及其创建的人间秩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我们很早就发出了对“上天”的反叛式诘问。
1949年后,唯物论的压制性传播洪水般地洗礼了这片国土上的一切宗教,也挤占了人们心中本就不大的供神灵存活的空间。当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到来时,共产革命的信仰被残酷的现实冲垮,接受了数十年红色教育的国人虽然发现“心灵空虚”、“道德沦丧”与信仰缺失不无关系,却已很难让“上帝”在头脑中安家了。
在西方,是另外一番景象:时至今日仍拥有大量信众的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教会建立起了自己在人间作为上帝代言人的权威。黑暗的中世纪更是宗教统治的世纪,这一时期基督教会支配着人间的一切事务,也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就连君王登基也须教皇加冕,正因如此,神权与世俗君权之间便一直冲突不断。庆幸的是,自十六世纪肇始,科学进步引发的宗教与科学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英国人伯特兰·罗素1935年的著作《宗教与科学》记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原由,对我们反思历史,认识人类命运,理解宗教和科学,均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诚如罗素所言,在宗教与科学的战争中,科学已经取得明显的胜利,而引发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
1)通过对特殊事物的观测和依据观测的推理,科学总是试图发现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规律,这种规律能够使人们不仅看清眼前的现象而且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的联合为人类创造出了以往所不曾有过的消费品,正是由于技术的一面,使人们普遍地赋予科学巨大的重要性。
2)每一种历史上著名的大宗教都具有三个方面:教会、教义和个人道德准则。而教义是宗教与科学冲突的理智上的原因,但对立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教会、教义和道德准则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教义的怀疑消弱了教会的权力和教士们的收入;同时,还被认为削弱了人们的道德基础,因为道德义务是教士根据教义推断出来的。
3)宗教宣扬一种上帝的意志于万物之中的逻辑统一性,这体现在教会制定的教义之中,教义能够演绎出指导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准则。这种逻辑统一性既使所有的教义铁板一块,又使宗教面临只要一个环节断裂则整个信仰体系分崩离析的危险。
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罗素认为二者现已“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事实的确如此吗?
在现代科技发达的西方社会,宗教仍然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究其原因,个人对人生价值、人类命运、宇宙目的的感受是同宗教信条相联系的,关于“价值”判断,可以肯定,“科学是不够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关乎个体的主观倾向,符合期望的便是有价值的,是善的,期望因人而异,因此,“价值”、“善恶”一类的伦理问题不存在可供参照客观标准,理应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相反,伦理道德领域将是宗教长期的活动场所。当然,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宗教不得不放弃对类似“太阳绕地球转”这样的客观事实的管辖权,而把注意力转入个人的心灵世界,采用这种放弃外垒保内核的办法,从而“变得纯净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益”。
已然如此,罗素翻旧账、重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的意义何在呢?书中,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把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共产苏联等量齐观,“认为两个国家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思想统治’,是比传统宗教还要厉害的‘新宗教’,呼吁人们要警惕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再一次降临人间。”
众所周知,宗教与政治的联姻早在人类的幼年就成为了事实,因为二者的目的皆是建立某种人间秩序,因此政治向来很是看重宗教的伦理色彩,也因此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几乎都带有政治色彩。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密切联系的主要产物便是意识形态,特定的伦理价值观与现实中的权力斗争相结合会产生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宗教相比,科学与政治之间发生亲密关系则晚近得多,但是,随着科学的异军突起,政治家们很快就学会了把科学当作一种新式武器,希特勒如此,斯大林如此,他们都宣称自己所奉行的理论是科学的,起码,在多数人看来,共产革命是反宗教的。
难道,罗素错了?
这显然关乎对宗教与科学的认识。宗教教义与科学理论的明显分歧在于:1、宗教建立在先验的假设基础上,而科学理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2、对真理的理解不同,教义自称含有永恒的和绝对可靠的真理,而科学却总是暂时的,被认为是真实的观测结果经归纳便成为一项前提假设,并依此推导出一系列的命题,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理论。科学史告诉我们,随着观测精确度的不断提高(归纳的不完全性意味着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科学理论都须经历不断的补充与修正,直至面目全非甚至被全新的理论所替代,虽然依据先前的理论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在造福于人类,就像相对论的出现并未全盘地否定牛顿三定律对人类的贡献。此外,科学史中有很多案例表明,科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比如欧氏几何中的第五公理,在非欧几何中被其否命题所取代。又如在牛顿引力定理中作为基本物理实体的万有引力,在广义相对论中被解释为空间曲率,成为一个不必要的概念。因而,所谓公理,并不具有先验的绝对正确性。
宗教的危险在于,从先验的普遍原则(例如上帝创世说)出发,进行演绎,同时排斥其他一切对世界的解释。而科学的局限在于归纳的不完整性,遑论主观世界,人类甚至永远都无法做到用科学手段穷尽客观真理。即使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宣扬某一理论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身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因为,如同宗教,科学也只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已,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解释理应是多元的。
无论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联,将对人类历史(姑且不论所谓的“历史”是否真实)的简单归纳而得出的结果作为普遍原则是程式化地应用于社会现实,并武断自大地排斥其他人类智慧的结晶,将其统统视为异端,究其实质,是将自己摆上了神坛。可怕并且可悲的是,这些不可检验的、独断的、超验的理论通过强权予以实践,以致要控制和左右其他可检验的东西,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制造了既空前又很可能是绝后的人类悲剧。
科学不是万能的,现实纷繁芜杂,历史更是多因多果,科学理应具备的态度是谨慎、尝试、尊重事实,从而揭示真实的世界,真理是谦卑的,武断、自大、排外只能导致对真理乃至人类幸福的伤害。宗教也并非一无是处,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罗素说,决定个人不幸的两大因素是社会制度和不健康的心理。而对群体而言,专制绝对是戕贼人类福祉的最大祸害。
林子
2010年11月30日
《宗教与科学》读后感(五):商务的这版删掉了麦克·罗斯写的引言(书中的正文第一页是从原文排版的第七页开始的),在这里可以看到
商务的这版删掉了麦克·罗斯写的引言(书中的正文第一页是从原文排版的第七页开始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引言及该书全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f4c0070102e5j4.html
[转载]伯特兰.罗素《宗教与科学》(上)
(第一章) 冲突的根源
(第二章) 哥白尼学说的革命
(第三章) 演化与进化
(第四章) 拜魔与医学
(第五章) 灵魂和肉体
(第六章) 决定论与宿命论
(第七章) 神秘主义
(第八章) 宇宙目的论
(第九章) 科学与伦理学
(第十章) 结论
原著:罗素
翻译:霍林河
校正:抽刀断水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生于英格兰。罗素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以98岁高龄去世。《宗教与科学》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引言
麦克.罗斯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 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的孙子,1872年生于英格兰。儿童时代的罗素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后来被送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罗素的兴趣从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专业的学术探讨,他常常卷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在那之后的二十年中,他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哲学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以他坦率的反战立场而受到关注,并因此而坐了六个月的监狱。战争结束后,罗素的活动日益激进,声名鹊起。创建革新学校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的目的是使天才儿童能够自由发挥,摆脱传统教育的束缚。在此期间,罗素撰写了一系列著名的作品,并依此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在1931年世袭了伯爵爵位的罗素再次陷入困境,纽约市立大学就因为他危险的非正统立场,拒绝邀请他去讲学。后来他沉寂了一段 时间。罗素的天才最后获得承认,是在他荣获英国平民最高荣誉的一等勋章和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但是争议并没有就此结束,罗素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致力于谴 责核武器带来的危害,他也非常公开地抗议美国对越南的战争。1970年,在朋友、家人以及第四任妻子的陪伴下,高龄的罗素在威尔士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伯特兰.罗素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可 以无愧地与罗基(Locke)、休莫(Hume)以及他自己的(非宗教的)教父约翰.斯陶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并列。他的主要成就,特别是他与剑桥同事、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合作成果,是在较早的时期完成的。在合着的三卷权威名著《数学原理》中,他们试图论证一种称之为「逻辑主义」的哲学。按照逻辑主 义,追根求源,数学真理是遵循逻辑规则、通过演绎和推理获得的。不幸的是,由于某些佯谬的存在,这种哲学显然无法得到证实,至少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证明方 法。而克服那些佯谬,则需要对「逻辑规则」的适应范围进行几乎不可能的推广。在有些时候失败比成功还具有更多的价值,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逻辑及其关的 领域中,罗素的成果,对本世纪的哲学和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和他的周围的人,直接地改变了我们思维的方向。
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职业哲学家往往对罗素通俗的作品给予较少的关注,然而却正是这些作品使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罗素写作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他一天可 以打出三千个字,而不需要作一个字的改动,他在三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完成一本65000字的书!他快速的写作从来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他的作品清晰、直率、 布局协调,不失大师手笔。诺贝尔奖可谓实至名归,而《宗教与科学》是为他赢得奖项的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在1935年第一次出版,至今虽然已经再版二十 多次,但是读起来仍然是那么新颖。
为了弄清文章的条理,我们首先综述一下科学与宗教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罗素看来,科学是遵循法则了解经验世界的一种尝试,而宗教作为一个复杂的现象,则先验地断定(一种教条)存在一个终极的东西和一种道德准则。对待宗教与科学的立场,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种立场认为科学与宗教处于一种对立的战争状态,两个系统对现实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拘泥于对圣经字面理解的创世派和进化论者的冲突,就是这种立场的一 个典型例子,这种冲突在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前者认为,《创世记》头几章的记载,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六天、亚当和夏娃、堕落和大洪水,世界上的一切都 是在过去的六千年中出现的。而进化论者则人为,世界已经存在数十亿年了,所有现存的生命都是缓慢的自然进化的产物,或者是从某些简单的、完全不同的生命形 式演化而来的。
第二种立场则企图把科学与宗教完全分开。坚持这种立场的人辩称,由于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探讨、解答不同的问题,因此根本不应该存在冲突。 今天新教的神学家所代表的就是这种立场,尽管他们在注重宗教礼拜和道德方面与正统宗教有着相似的态度。对于像《创世记》这样的问题,信徒们则直接避免与科 学家进行争论。他们宣称,科学处理的是「怎么样」的问题,而宗教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出现的,而是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特别是我们人类与地球及其地球上的其它生物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是动物和植物的绝对拥有者,还是仅仅是它们的服务员,并且对它们承担着随之而来的责任?
第三种立场则倡导「对话」。持这种立场的人,相信科学与宗教对待的问题是不同的,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的东西并且互相作用。因此双方都需要和谐地调整自己。这种立场由来以久,在所谓「自然神学」的基督教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自然神学」试图通过理性来理解上帝和他的作品,生活在耶稣时代四百年之后的圣奥古斯汀(Augustine)就曾经警告说,拘泥于对《圣经》咬文嚼字的理解,只能导致与不相信它的人的冲突和争论。今天,主张对话的人接受关于人的进化理论,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蓄意背叛了上帝。
最后一种立场企图把科学和宗教容为一体。他们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只是被人为地分开了。在当今时代中,天主教(耶稣会)神父、资深的古生物学家派尔.泰阿德.德.查丁(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就是这种立场最强有力的倡导者。他在著名的《人类的奇迹(1955)》中说,科学表明,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存在一种逐渐的进化过程,这个历史与基督教的观点自然地吻合,那就是,人类未来将发展到一个最高的终点,按照泰阿德的观点,也就是变成某种类似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自己不会能说这四种立场只有一个正确,而其它三个都是错误的。如果一定要做出什么结论的话,那是读者自己的事。对于我来说,知道每一种立场都有它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就足够了。比如现任教皇约翰.保禄二世(John Paul),尽管他在教条上是非常保守的,但是他支持科学,与他的前任教皇和天主教牧师一样,他是哥白尼派!因此他坚定地遵循对话的传统。相反,尽管泰阿 德.德.查丁的立场有着许多支持者(特别是自由的路德派),他的著作在他活着的时候却不许出版,因为教会认为他的思想是亵渎神灵的。
在明确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和判断罗素的《宗教与科学》一书。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判断与评价。罗素是对立论的强烈支持者。正如他在书中陈述 的那样,对于他来说,宗教与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各自用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去占领同样的领域。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是一场科学已经取得了决定 性胜利的战争,而且这 种结果是所有善良、理性的人应该深深感激的。随着宗教的失败,迷信、压迫和仇恨也消失了。而伴随着科学的凯歌出现的,是理解、自由和博爱。古典派学者基尔 伯特.姆瑞(Gilbert Murray)把罗素的这本书选进了他主持的一套丛书里,毫不奇怪地,罗素在回复姆瑞的约稿时,要求「出版者要保证容许他涉及罗马天主教堂不希望公开的事 实」(1933年9月30日的信)。
事实上,第一次审稿就没有过关。我猜想罗素当时的立场比在这里表述的更复杂、更有趣味,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反对和支持对立论的人都 应该阅读《宗教与科学》。这本书的论述清晰有力,对主要论点阐述详尽而无疏失,对立论的支持者从中受益匪浅。另外,正像罗素自己指出的那样,在写作此书的 时候,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正发展到顶峰,反对宗教(拜神的和世俗的)的斗争从来没有结束,还需世代努力。对于那些反对对立论的人,或者对于那些接受它但是反 对罗素的人,《宗教与科学》更应该引起他们的注意。要想明确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你必须了解对手的全部长处和弱点。没有任何其它人把支持科学、反对宗 教的立场表述得比这本书更加有力。当心,它会说服你改变自己的信仰!
《宗教与科学》从历史入手,以中世纪以来的科学事件为线索,展示了宗教首先在物理学家面前如何步步退缩、而后又在生物学家面前逃避躲闪。在叙述了更多的历史事实、特别是那些与医疗有关的事实之后,作者开始触及更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涵盖了诸如自由意志、决定论、神秘主义、宇宙目 的论以及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这些广泛的论题。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论题条目,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它有一个令我费解的重大疏漏--它没有对弗洛依德 (Freudian)的理论对传统基督教关于自由和罪孽的思想的冲击作一个全面的讨论。对于一个曾经创办了前卫实验学校,并且认为性不是罪恶的、也不是暴 力的根源的罗素来说,这种疏忽尤其令人费解。我猜想,罗素可能与某些人一样,认为弗洛依德的理论尽管很有见地,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使之可以与 他在书中讨论的那些伟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以及达尔文的成果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宗教与科学》的前半部是好的,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卓越的,但是后半部则更加出色。这当然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哲学问题是罗素的领地。一个美中不足 是,罗素对科学史的处理,过多地依赖了第二手数据,他趋于片面地依赖十九世纪好战者的论点,在论述科学与宗教在精神领域的斗争时,好战者们有意识地把科学 描写成胜利者。
罗素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宗教统治集团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压制是件坏事,而日心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和进化论的最后胜利是值得庆贺的。当然,现在看来他们 是正确的,但是更细致的研究表明,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总是一面倒的,并非科学总是骑士,而宗教总是被屠的龙。比如在生物学上,达尔文就大量吸 取了当时安革拉自然神学的东西,他的自然选择机制所要回答的有机体的适应性原理,就是受了他在大学时代阅读的阿什狄肯.帕莱(Archdeacon Paley)的论断的启发,帕莱的论断说,有机生命最显著的方面是它的结构像是设计出来的。我怀疑离开了基督教,还是否会有达尔文主义。要想彻底歪曲和歧 视一种立场,你必须像达尔文的「走狗」汤姆斯.亨利.胡克斯莱(Thomas Henry Huxley) 那样,全力打击他那个时代的教会。我非常希望能有读者向罗素指明,比较解剖学家之父乔治.库沃
(George Cuvier)从来就不是「天主教的典范」。出生在德法交界的一个边界省份的库沃是一个新教徒,他一生都在谨慎地躲闪着日益强盛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设置的障碍。
当罗素阔步走进他所熟悉的哲学领域时,这些并不重要的错误便很容易地被淡忘了。关于医疗的一章是深刻的,尽管罗素反对宗教权力的许多论证已经深为人们孰 知,但是像计划生育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对个人道德准则的立法的影响,他六十年前的激辩,仍然像发生在六天之前一样生动、多彩。正是这一点使罗素的对手不敢 贸然进攻,因为他确切地显示了,把道德仅仅建立在对圣经只言词组的理解上是多么的危险。就在上一个世纪,人们还在告诫女人在生产时不能使用麻醉剂,因为阵痛是上帝对夏娃罪孽的惩罚。
最富有趣味的是接下来关于灵魂、永生、 自由和宿命论的章节。你可能会以为,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对这些问题,罗素将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当然,他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纯思维的精神现象。类似 的,罗素当然也会反对任何种类的绝对自由,相信科学的规律是唯一的规律,人类只是不可知的命运手中的玩偶。如果你认为上面所说的观点就是罗素的观点,那你 就错了。一方面,罗素不偏爱于头颅之内或头颅之外的游魂,也不仅仅重视没有大脑的躯壳。对于他来讲,头脑和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东西。另一方面,罗素对 于严格的法则主宰和任何形式的传统自由意志概念同样持谨慎态度。我们即不是完全的玩偶,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自在之体。
在对待肉体、思维和灵魂的问题上,我猜想有多种因素影响着罗素的思维,一个是把思维和物质当成同一个基本东西的二元论哲学,另外一个是被他称之为「中立一 元论」的理论,后者是他的著作《思维分析》中的要论题。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主张,大概是关于能量和物质互相转换的理论,它表明在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并没有 一个明显的界线。行为主义对这个理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如果思维和行为具有一个本质上的同一性,那么把思维归结于行为的科学就显得比较合理了。但是,毫无 疑问,罗素热衷于他自己的立场,因为即不仅仅偏重于物质也不独遵精神,使他即反击了受柏拉图影响、相信灵魂不灭(精神不依赖肉体而存在)的基督徒,也抵制了相信死后肉体复活(同一个灵魂附在不同物质上)受保罗影响的基督徒。对于罗素来说,这两种选择不仅仅是错误的,纯粹在概念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对待决定论和自然法则主宰的问题上,罗素对那些以为从现代物理中、特别是从原子状态不定性的理论中找到了新自由度的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罗素并不否定 物理学,他只是讨厌把现在对物质的了解说成是终极真理。可能真有某种现在还不了解的新自由度,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如何,即使说得委婉一点,量子论 的不确定性与自由意志之间也没有很强的关联。但是罗素关心的远远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他发现,整个的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误导。按照经验论的传统,通过 内心感觉与反映──内省,罗素发现,找不到一个先验的、决定自由行为的「意志」的痕迹。像戴维.休莫一样,他并不想否认,有些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被控制的, 而有些时候又不受外界的影响和控制。某些行为是自愿的,而另外一些行为是不自愿的。超出这个范畴,在缺乏对论战对像任何真正的经验的情况下,问题和答案都 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神秘论的一章是饶有趣味的,他对神秘主义竟然怀着出人意料的同情。我猜想部分原因是由于罗素自己曾有过强烈的感情经历,至少其中的一个他确信是真正的 奇迹。但是,最终罗素还是否认了神秘主义可以引导到一个未知的自由度,一个出乎正常思维和感觉的范畴。他特别反对那种认为这个新领域给宗教信仰提供了左证 的说法。他指出,神秘经历不仅常常打上了报告者自身文化的烙印(比如新教的神秘主义者就不会看到圣母显灵),而且神秘主义的主张(比如超脱时间的存在)本身完全经不起严密的逻辑验证。
在我看来,在宇宙目的论一章中,罗素的论证,是反对宇宙及其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论证中最精彩的。毫无疑问,它仍然具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尽管我们已经不 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那样,热心于发展一个较好的国家,但是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通过人类的努力或者通过制约人类的努力,泛泛而言,对于这个世界,或者 具体的说,对于我们人类自己,都在朝着一个不断改进的方向不断地发展是合乎情理的假设。这也是一种受到科学支持的信仰。正如史提芬.翟.高德 (Stephen Jay Gould)展示的那样,只要你阅读任何一本关于进化论的流行书籍,或者去一个博物馆,都会使你相信,是生命的进化导致了人类的出现,而且非常可能一个更 加美好的明天在等着我们。现在,我们再回到罗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对这种乐观的愿望泼了大量的冷水。「如果赋予我无限的能力,并且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去试验,我不认为人类是值得赞美的最后选择。」回顾人类本世纪的丑行,谁能对此反唇相讥?
最后,罗素转向了科学和伦理的问题。他赞同一种「伦理的情感理论」,事实上正是罗素在1915年一篇关于战争的伦理的文章中,重新提出这个理论的。这个理 论认为,当我们说「杀人是错误的」这种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是否如此。我们不能把「杀人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与「草是绿色的」这样的话等同,我们说 「草是绿色的」这句话时,的确认为(对或者不对)草在客观上是绿色的。但是在伦理的问题上,没有一个超越现实的「错误」就「放在那儿」,而且正好能和杀人 对上号。「杀人是错误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我不喜欢杀人」,可能还包含对他人的劝诫:「不要杀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发现,这种理论具有某种严重的困境。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不道德的。无论我是否关心事实,杀人的确是错误的。大概纳粹不认 为杀害犹太人是错误的,但是那确确实实是错误的,即使整个世界最后全部划入了德国的版图,也不能改变这个结论。否则,只能表明你道德的空虚。我们也许不能 回答有关伦理的情感理论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伦理判断所指的对象是什么,人的伦理判断包含的是一种客观真理,就像 我们谈论草的颜色一样。当我说「杀人是错误的」时候,无论你和我或者鲁道夫.希特勒怎么想,它的含义是明确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非常复杂的了,我不能装做自己了解它们。道德判断的对象到底是什么,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 是这个问题。我不是说没有办法取得进展,只是认为罗素在他的《宗教与科学》当中,对此没有做出理应有的、进一步的论述。无论我们如何从他的思想和行为来评 价他的道德,他以科学为依据的伦理的理论是不能使我们信服的。这并不是说罗素的反对者就是正确的,也不是说他所想的、做的完全是错误的。其实即使反对他的 人也承认,在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表现了比伯特兰.罗素更大的道德勇气。最有意思的是,罗素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并且面临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时候,他自己(特别是在他的《伦理和政治中的人类社会》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试图发现为什么一个否认道德的客观标准的人 会对邪恶产生彻底的憎恨。
这就是《宗教与科学》一书涉及的范围,尽管它可能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却充满了刺激。在完成这篇引言之前,我必须声明一下,在某种意义上,罗素是一个非常 复杂而有趣的人物,远远不是你在粗略地阅读了《宗教与科学》之后,看到的那个单纯的宗教反对者。首先我提请读者注意,在本书的结尾部分,罗素基本同意,现 代宗教和科学已经找到了一种和谐并存的方式,我认为他也会同意,其它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是这样。这种关系的建立可能完全以宗教的妥协为代价,但是他至少向 我们展示了宗教与科学由对立向对话转变的希望。可能即使对罗素来说,教皇约翰.保禄也可以放下心来了。罗素同时也警告人们,要反对没有神灵崇拜的宗教,他 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宗教。
我要指出的第二点是,伯特兰.罗素作为一个人,在他漫长的生命中,表现了一贯不向虚伪的上帝(神的或者是人的)妥协的品德,他从来不会仅仅因为某些东西在 心理上有诱惑力就去相信它。他从来不向盲目的命运妥协,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意义,他努力探求我们可以理解的自然真理,他对人类充满关心和热情。罗素 从禁欲主义者和他所喜欢的哲学家身上,找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哲学,罗素非常喜爱的荷兰理性主义者巴茹施.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就是这些哲学家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在某些方面,罗素与这样一种正统的神学家非常相近:他完全地、绝对地拒绝任何形式的自然神学,他满怀喜悦地接受科学提供的见识,他认为科学 与宗教在用不同的语言回答不同的问题。丹麦思想家索任.科克加德 (Soren Kierkegaard)给了这些神学家以极大的启示,对于他们来说,信仰的出发点并没有理性的支持。人类的祸源在于我们远离上帝,经验世界本身没有意 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真正的意义。信仰是荒唐的而且需要一个升华,这也正是信仰之为信仰的原因。所谓的意义只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也就是犹太思想家马 丁.巴伯(Martin
uber)所说的「我-你」的关系,而不是科学中「我-它」的关系。
尽管伯特兰.罗素与这种观点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他从来没有做出升华,我不认为他曾经试图做出这样的升华。但是如果我自己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信仰者,我会发现《宗教与科学》对我的信仰具有不可思议的支持。对于罗素来说,它是论证的终结,但是对于我它仅仅是开端。
第一章 冲突的根源
宗教和科学是社会生活的两个侧面,前者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历来重要,而后者在古希腊及阿拉伯社会暂短地闪烁了第一抹光辉之后,在十六世纪又猛然显得重要起 来,从那时起科学不断地注入了我们生活的理念与制度之中。长期以来,宗教与科学一直在冲突中,只是在近期的几年,科学才不断地显示出胜利者的风姿。但是借 科技传媒布道之利,近来新宗教在俄国和德国再度兴起,科学与宗教之争似乎又像科学新纪元之初一样胜负难定。重新审视传统宗教与科学冲突之范畴与历史又显得 重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