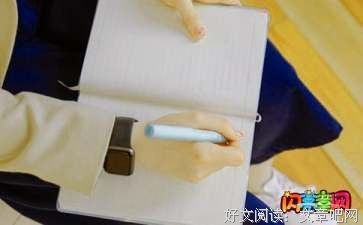
《七缀集(修订本)》是一本由钱锺书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1,页数:1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七缀集(修订本)》精选点评:
●精彩好讀!
●好好看
●高山仰止的钱锺书啊!为了阐明某个观点,哪怕是简单的观点,钱老也用着星罗棋布的例子堆砌在那,就好像“泡泡攻击”(偶尔还掺杂着小幽默),让阅读的我应接不暇。钱锺书是语言的大师,也是学术的大师,古今中外、文史哲艺皆通,这种人不用“天才”论之也无词可论了。当然这种写论文的方式我辈不会用也不可能会用,只有膜拜、膜拜、膜拜;再读的《七缀集》,比初读时多懂了一些些东西,但心中依旧只有膜拜。
●七缀集二十年间第三次看了,一次比一次更自如地看,这一次几乎有余暇去看看注解。关于读历史企图看到故事的评论,引为同志。博览都做不到,就想泛型化一个历史观,谈何容易。
●这才是钱钟书最好的书.有系统的书.他的别的书都只是一位"照相式记忆"患者的不是太成功的自疗过程.
●补记
●所言在理,举例方显真功夫。
●令人愉快,智慧之珠连缀在一起。
●比较早的一个小册子,属于比较浅显易懂的那种
●读过钱锺书之后,还做什么学问呢?
《七缀集(修订本)》读后感(一):翻译
读书笔记235:七缀集
属于杂凑的一本集子,主题也没太多相关性。
商务出的林纾翻译集手头倒是有几本,看了个开头就不愿意读了,明显感觉是删节本,看作者说他不到删节,给凭空给你加内容进入,这已经不是翻译了,是再次创作了。民国时候鲁迅就写了好几篇吐槽翻译的文章,钱小时候能看到林纾的书已属难得,等到学了英文能看原著,翻译本基本就看不得了,我不知道他对杨绛翻译的小说评价如何?
林纾是不懂外语的,所以所有译作都需要别人先翻译成中文,他再润色,他古文极好,早期译作质量在当时来讲,还属上乘,后期就不行。对于译者,最高境界自然是能够原封不动的把原著搬过来,没有讹误,但是做不到,语言有差异。信雅达目前是奢望,读者只求信,这一点现在都不容易了,翻译工作现在都是低价速成,中心出版社算是其中典范了,对它我是又爱又恨,出书很快,质量很差。
《七缀集(修订本)》读后感(二):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版本
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有一个出了名的盗贼,人送外号克利克[1],并且认为永远也不会有人抓到他。这个盗贼很想结识另一个与他同样出名的外号叫克罗克的盗贼,想与他联手作案。一天,克利克在一家酒馆吃饭,同桌坐着一位陌生人。克利克要看时间的时候才发现怀表已经不翼而飞了。克利克想:要是这人能不被我察觉而偷走我的表,那他一定就是克罗克。他回手就偷来了那个人的钱包。陌生人要付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钱包也没了,便对同桌的人说:“看来你就是克利克了。”
另一个答道:“那你一定就是克罗克喽。”
“对。”
“好极了,我们合伙吧。”就这样两个盗贼联起手来。
两个人进城,来到了由侍卫严密把守的国王宝库。他们挖了一条通向宝库的地道,盗走了宝库里的一些东西。国王眼看着宝库被盗,却找不到一点盗贼的线索,就去找一位关押在狱的盗贼,人称灰浆盆,国王对他说:“你要是能告诉我偷宝库的人是谁,我就放了你,还封你为侯爵。”
灰浆盆答道:“这一定是克利克和克罗克联手干的,他们是两个最棒的盗贼。不过,我有办法抓住他们。您下令把肉价抬高到每磅一百里拉,谁还去买肉,谁就一定是盗贼。”
国王依计把肉价抬到一百里拉一磅,没有人再去买肉了。好不容易来人报告说有一个修道士到一家肉铺买过肉。灰浆盆说:“这一定是克利克或克罗克化装的。我也化装成一个乞丐,挨家挨户去乞讨,谁给我肉吃,我就在他家的门上划一个红色标记,这样侍卫就能抓到他。”
但是当他在克利克家门上划上红色标记时,克利克发觉了。克利克给城里所有人家的门上都划上了同样的标记,结果灰浆盆一无所获。
灰浆盆又向国王献计说:“我不是跟您说过他们是两个很狡猾的人吗?但是,有人比他们更狡猾。您这么办:让人在宝库台阶的下面放上一桶滚烫的松树油,进去偷东西的人就会掉下去,我们便可以坐等收尸了。”
克利克和克罗克不久就把偷来的钱用光了,只好再去宝库偷钱。克罗克摸黑走在前面,结果掉进了桶里。克利克看到朋友掉进松油桶死了,就想把尸体捞出来带走,但怎么也捞不出来。他只好砍下克罗克的脑袋,带走了。
第二天,国王到了现场,说:“这次抓到了,这次抓到了!”可是,只找到一具无头尸,没法辨认身分,也无法断定谁是同谋。
灰浆盆又说:“我还有一计。你让人用两匹马拖着这具尸体在全城示众,听到哪里有哭声,就一定是盗贼的家。”
真的,克罗克的妻子从窗户看到丈夫的尸体被拖着游街,就又哭又嚎起来。克利克也在那里,他立即意识到这样会使自己暴露。于是,他开始摔盘子,砸碗,并且打克罗克的妻子。正在这时,侍卫们循着哭声进来了,看到的却是一个妇人打碎了盘、碗,而男人给了她几个耳光,妇人就哭了起来。
国王无计可施,便让人在全城贴出告示说,谁有本事偷走他床上的床单,他就原谅他的偷盗之罪。克利克听到消息就来了,说自己有本事做到。
晚上国王脱衣上了床,手里拿着一杆火枪等着盗贼。克利克从掘墓人那里要来一具尸体,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到王宫的屋顶。等到半夜,克利克用绳子把尸体吊在国王寝室的窗户前。国王以为这就是克利克,朝他开了一枪,又看见他带着绳子摔了下去。国王跑下去看看人是不是死了。可就在同时,克利克从屋顶下到国王的寝室,偷走了国王的床单。克利克被国王赦免了,而且因为他已经无所不能偷了,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蒙费拉托地区)
[1]这篇故事中的两个盗贼的外号“克利克”与“克罗克”都是形容断裂、破碎声的象声词。
《七缀集(修订本)》读后感(三):三看
二十年间第三次读到它,再没有前两次的层层阻力和咬牙拼下去的狠劲。有的是一层又一层的活泼泼的阅读趣味——钱锺书发现的趣味,我在他的言语中不觉会心一笑的趣味。大约五年多前,我读张爱玲的一本选集,张爱玲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有关海盗穆里斯青的故事,让我莫名其妙,我总觉得那个故事甚至不必讲上一遍。这个集子最末一文,翻作三段展开的窃贼故事恐怕当年读来同样昏昏欲睡,莫名其妙。
对比钱的文章,这次给我感受最大的是他的丰富。好的文章,不仅要启智,还要增长见闻。这样的文字,任谁看也不能再视作一根鸡毛,至少是根像模像样的鸡毛掸子。
鸡毛掸子之论,我觉得不见得算作不敬。以钱的阅读资历,是近现代最有资格做一个集大成者,开宗立派的人的。但钱没有这个心思,甚至鄙薄这种眼里只有所谓全局,旋律的空阔想法,这一种想法,我深许之。
但钱的学术上的途径只怕也与大环境有关。在他的可能有所创造的盛年,只允许有一个主义,一种文艺史观。一部部作品削足适履,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里套。钱的举动,不失为一种温和的反抗。如果果真钱先生没有留下足够有见地,可传世的名篇。这是为政者的耻辱。
好的文章,要见引用。引用当然也指引用他人的言论,但重点是要见到他人对你的文章的引用。为了达到更高的引用率,如钱钟书这样的丰富是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就是靓到闪瞎任何人的狗眼。我现在一直奇迹于某些诗文。这些诗文作者远非著作等身的大家,但唯一传世的一两篇作品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奇峰突起,耸入云霄一般。比如枫桥夜泊,比如洞房昨夜停红烛,一首诗,比得上别人连篇累牍的一部部全集,选集。
曾文正说,为人要有志,有识,有恒。拿来谈论读书也是一样。有志则为之不懈,有识则见解日增,有恒则所学所得渐渐累积,一旦有所用,则左右逢其源。钱钟书是文正公这三个期望的最好代表。
阅读趣味的表述,这书表露地相当真切。一个人一生中能从书籍里找寻到的快乐,这本书里至少描述了大半。
一个很大的疑问,郎佛罗,钱钟书很是不屑,但郎佛罗的那首诗极像是我所能写出的版本,我也许读诗太少,诗品太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说理诗就不好呢?
以红楼梦诸女子评点朱夫子的诗为例,对郎费洛的评论也许不难解。这首诗里的郎费洛活脱脱就是西人面目的朱夫子,恨不得将人捉到他的课堂上听他讲授人生哲理。这种诗,诗品低下也许就在直露浅白,没有遮掩,又达不到西风颂那样热烈的程度。两头均不占,所以显得浅薄无文。钱先生写作时也犯了普通人写作时常犯的错误,自认为一些事情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其实,离钱先生故去有二十年了吧,不解此理的反是大众。
插补几句话,人生一世,大约在青年时期,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似乎领会终极原理的狂喜期。有极少数人,会放而不归。死咬住几句断简残章不放,自以为大道至简,至圣无言。似乎整天坐下喝西北风就可以于天地交通,甚至如层出不穷的诸位大师一般,竟可与天地参了。
亚圣也说过,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似乎做学问与小孩子拍皮球,过家家一般稀松平常。
求其放心对不对?对,但这好比写作业削好了笔。事情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大道至简对不对?文正公说,譬如为人,只要守住傲惰两病不犯即可,够簡了吧。但这仍然只是开始。一个人不傲是要潜心求学,虚心求教,不惰是为了处事不急不躁,勤奋用功。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够傲也够懒。两病皆犯,自以为有所得,不明之甚。
千古江山,历历英豪,置书榻上,其人若亲目。怎么会有人放弃这样绝佳的享受?
虚室独坐,笔意纵横,满腔感慨,书之而后快。一个人又怎么会推脱掉如此美妙的经历?
学不可以已,兹事真可乐矣。
《七缀集(修订本)》读后感(四):值得细读
这本书是20多年前买的和读的,因为前些日子买了几套书,书架子又显得拥挤了,感觉又有必要优胜劣汰一些,忽然翻到这本书,感觉20多年过去,脑子里还有些印象,于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消耗一段光阴,记录上一段吧。 钱钟书的著作里面,这本书是比较特殊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大部头的,并且是文言文的,而本书是现代语体的,只有七篇文章,但这本书的份量似乎比他的篇幅要重一些。 先说我不太满意的地方,一是这本书的序言,感觉有点矫情。钱钟书写的序言,我认为比较好的是管锥编的序言,简单明了。二是这本书的编选有点问题,本书虽然自称“七缀”,却是分为两片,一片是谈艺,一片是说翻译。 我对其印象最多的主要是谈艺部分,从框架上看,谈艺应该从《通感》开始,《心经》里标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感受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因为真如只有一个,因此六感必有相通的地方。通感是一个神经心理学问题。
本书谈艺,只谈了诗画二艺,谓二艺有相通的地方,“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倒是老生常谈,但他提出第一流的画风(清淡)是第二流的诗风;第一流的诗风(沉郁)是第二流的画风,却是一种很高明的见解。只是没有探求原因。
对诗风,他进行了南北东西的比较。南北方面“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汉传佛教里面,禅宗大概算是约简的,而唯识要数深芜了,净土则是简而不约。东西方面,则是东方婉约,西方豪放。中国最豪放的诗人在西方也算是婉约的,西方最婉约的诗人在中国也是豪放的。而“诗可以怨”恰恰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骚体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从心理的角度看,骚体类似于腹诽,是一种婉约的表达方式,表达的通常是不满,实际上就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骚体诗是文人墨客的较高级的表达骚情的方式,而对于不会做诗的黔首愚民,便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文化,诅咒文化。无论是诗可以怨,还是无诗只能诅咒,既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必然要有其政治社会基础的支撑,在这骚的国度,于此自然也不便公开讨论。但无论是高级的骚诗还是低级的诅咒,显然都是有感而发,甚至带着一股狠劲,其风格自然是沉郁的,难以清淡。
别的可以不说,有一个社会背景不可不说,那就是科举取士文人治国,因此怀才不遇文人相轻便成为骚的保留题目了。
从心理卫生的角度看,骚是不利于心理健康的,久之必然引起抑郁症,进而自杀。据说那神秘的诅咒巫术也是双刃剑,害人往往也要害己。如果骚而成诗,便成了一种传染病,对读者的心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要治疗这种抑郁之症,有一剂良药,便是避世。避世就是要纵情山水,于文人便有了山水画。既然是要避世,要治疗抑郁症,这山水画自然要清淡,而不能沉郁。
清淡的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上品,但在西方却恰恰相反。西方美术的上品是人物,并且是不清淡的,但也未必是消极的沉郁,而是人性的释放。
但抑郁症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的,中国的骚人虽然服用了山水清心丸,劳骚的毛病却没有除根,他们要在好好的山水画上题诗。
在画上题诗的可以称为文人画,当然这里指的是在创作的时候题诗,而不是像乾隆皇帝一样在前人作品上面题诗,前者是创作的一部分,后者仅仅是为了表明到此一游,是一种破坏文物的行为。诗书印是文人画的三绝,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矫揉造作,是一种矫情。画上的诗书印实际仅仅起一种装饰作用,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墨迹,文字的内容与画的美学效果无关,有关的仅仅是文字的多少大小、以及在画面上的排列。这有点像清真寺里的阿拉伯书法。当然,文字的内容也不能乱写。
《七缀集(修订本)》读后感(五):读《七缀集·林纾的翻译》01
读《七缀集·林纾的翻译》01
钱钟书的这篇文章讲到他小时候读林纾译的一部小说,说里面的一段有问题,那该是翻译问题,不过钱老没有说明白。当时他就这个问题问过家里人,他们也答不了,这里面的人自然包括他爹啰。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老师巨子的钱钟书还是认为有问题。可见这是钱钟书耿耿于怀的老问题了。不过我们可以不要管这个问题的名称或类别是什么?比如是什么“中项不周延”、“指代不明确”等等,这些名称可以都不要,因为这样的文法问题在中国的古籍里简直就跟在秋天拾落叶那样容易找到。我就根据钱老本人的引文和评论,认为是钱老的中文阅读理解有问题,而原著和林纾的翻译都没问题,不过这是我的断言,因为我没有读原著,也不知道内陆有没有这部原著。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辩一辩的。我先把钱老的引文和紧接着的评论抄如下,作为我对钱老辩论的基点或对象。咳,先人苦啊!后人不依不饶,他她却不得吱声。虽然在今天,这个辩论是我隔空喊话,但是我也会“下去”的,后生也可以让我说不出我的反驳话。不过有所谓“自有公论”,网上的蜂蚁不都是大春绿吧?于是谁不同意我的意见,那就坦坦翘翘地上台来,高峰沟壑我不论,银样镴枪头我必摧折之。所以阿狗阿猫想好了再来上我的枪!我只要求不管男女老少,尤其对男子,伸不出甲鱼头颈的,就《本草纲目》去吧,让老李指导侬。懂了吗?
为了便于讨论,我对林纾的译文和钱老的评论都做了标号,分别是“林X”和“钱X”,两者是对应的。
林纾译文的下半段是这样:“[林1]然狮之后爪已及鰐鱼之颈,如人之脱手套,力拔而出之。少须,[林2]狮首俯鰐鱼之身作异声,而鰐鱼亦侧其齿,尚陷入狮股,狮腹为鰐所咬亦几裂。如是战斗,为余生平所未睹者。”
抟扶摇按:这里的最后一句可以不论。我抄它,是为了我需要的引文的确是引完整了。
[钱1]狮子抓住鳄鱼的脖子,决不会整个爪子象陷在烂泥里似的,为什么“如人之脱手套”?[钱2]鳄鱼的牙齿既然“陷入狮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狮腹”。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的大人也解答不来。
同样,我们也不要管钱老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下面是我的辩说了。
关于[林1],所谓狮子的爪子已经抓住鰐鱼的脖颈,这表明鳄鱼已是仰天躺了。我们人的头颈,有明显的“前脖”和“后颈”之分,比如自刎割前脖,而斩首则从后颈砍下去。人的“前脖”和“后颈”有分别,是因为这一圈的皮肉可以视为无差别的,都是软软的,只有皮肉之下的骨组织有差别,比如喉头和颈椎。但是鳄鱼不同。它虽然全身是鳞甲,但是背部的比腹部的硬许多。至于狮爪已经陷入鳄颈,这表明狮子已经对仰面朝天的鳄鱼的软档下“手”了,不论鳄鱼的仰面是主动的战术攻击还是处在给狮子翻弄过来的下风,在这一点上,狮子已经占据战术上游了。钱老质疑林纾为何翻译为狮爪像人脱手套那样地从鳄鱼的喉部里拔出来?这表明钱老以为这“脱手套式”的拔该是很轻松的,仿佛手从烂泥里拔出来。其实钱老这是只知其一而未通其二。戴手套,有的或有时可以很宽松,比如只分出大拇指的防冻手套。钱老生活在北京,即使没有戴过这种手套也应该是司空见惯,不至于熟视无睹吧?本文的南方读者如果难以想象,那就去看一个集《林海雪原》吧!但是医生、护士为医疗卫生与安全而带的乳胶手套就得紧裹指掌,还有比如我军仪仗白手套,甚至平民使用的内衬手套。等等这样的手套脱下来是要费点力气的,不像前一种宽松手套是可以“甩”而脱之的。鳄鱼的喉部虽然有鳞甲,却毕竟柔软些,狮爪可陷。不过鳞甲毕竟有钳制力,加上鳄鱼的肌肉,再加上鳄鱼激烈抗争,所以狮子要拔出陷爪,再陷入另一处,以此造成更大的伤害,它拔爪子是要用力气的,仿佛脱出紧固手套一般。我们于是可见,钱老对林纾的这个翻译的反驳是失败的。
关于[钱2],要命的是钱老没有想到狮鳄此番斗,两者的体位是69,正相反。于是鳄鱼咬狮子的屁股,当然也可以再腾出嘴来咬狮子的腹部。狮子腹部的皮囊毕竟软于它屁股的。这里说的鳄斗狮,就好比说“泰森打裂了对方的眼眶,又几乎把对方的下巴打脱臼”。这是先后两次的动作,虽然林译鳄斗狮时没有写出鳄鱼两次咬狮的转换过渡词语。但是我们应该首先按照逻辑去理解,正好比我们理解电影的蒙太奇:前一镜头是A军发起冲锋,后一镜头是AB两军尸横遍野。这里可以完全不要厮杀的过程这种长镜头,便可以叫我们自动联想起攻防的激烈,几乎同归于尽。由此可见,钱老对林纾的这个翻译的指摘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他儿时的家人和钱老自己成为“老鬼”了,都没有读懂这段恶斗的描写。
我不知道指出钱钟书先生的一则阅读理解的不通究竟对不对。不对的话,自有公论。好谈善吹钱钟书的人多得跟蜜蜂蚂蚁一样,但是真正认真读钱著的真不多,多的是长舌妇那样嚼舌头的男人,我自信女人很少读钱著。而假如我的这则批评居然成立了,那么我会很开心。毕竟,要从钱钟书的文章里找出点瑕疵来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何况我并非研习文史哲的,恰恰是因为我欢喜钱钟书的文史哲文章,这才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读过的他的文章,这才如同“书读百遍其理自现”一样地看出我自以为是的一点破绽来。
� �T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