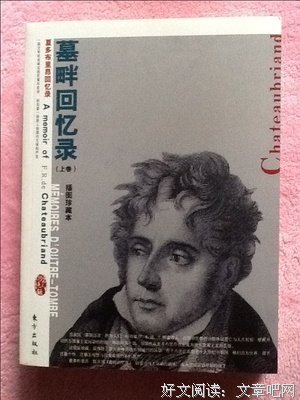
《墓畔回忆录》是一本由夏多布里昂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0元,页数:1946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墓畔回忆录》精选点评:
●这样的书绝对是值得典藏,可惜东方出版社非常不负责任的编辑们,你们真TM是出版界的败类,两三百块的一套书,几乎每一两页就有错别字。
●他的文字细腻而浪漫,似一妙龄少女围着你翩翩起舞,靠近你,给你温柔的抚摸,嘴角那一抹微笑简直能勾魂摄魄。
●喜歡夏多布里昂,真正的貴族。
●夏多布里昂符合我对浪漫派作者的一切想象,最爱读他写自己的童年(大致作家们在年迈时回忆起自己的幼年和青春时期,都会投掷出最温柔和深情的目光,迟缓地、小心翼翼地用笔记录如蝉翼般易碎的梦幻),好几次看到他写他家族的城堡、家人还有如影随形的孤独时,热泪都在眼眶里打转。读完这本书我几乎认定自己彻头彻尾“浪漫主义”。不过当人不可避免地卷进时代的车轨中后,便显得渺小、无力、徒劳,后半本关于政治、权力更迭和对世界的探索,反而没那么可人了。因而减星。
●唉,夏多布里昂的文字太美了,隔着时间与语言的屏障看去依旧浪漫瑰丽,果然这就是浪漫主义大手的实力吗
●购入
●这应该是夏多布里昂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吧……
●之前读过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一下被那种浓郁的抒情与诗意吸引住了,彻底爱上夏夏。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搜罗夏夏的各种书,这套《墓畔回忆录》就是在孔夫子上用了80元买来的。十分认真,正襟危坐,准备一顿饕餮盛宴。但是从一半起,无法压抑心中一阵阵涌起的失望。《阿达拉》中极具风情的优雅华丽丝毫不见踪迹,译者似乎只把能够成书作为首要任务。我不知道这厚厚的三大本书两位译者用了多少时间,但我始终认为,作为夏多布里昂的巅峰之作,他不会写得如此平淡无味,如此貌不惊人。只要读过《阿达拉》的人都明白夏多布里昂的水准。我只能说,夏夏
●我还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
●适合在秋天的下午读
《墓畔回忆录》读后感(一):回忆之回忆
塔古斯河美过那条流经我村庄的小河 / 但塔古斯河却又美不过流经我村庄的小河 / 因为塔古斯河不是流经我村庄的小河。(佩索阿《牧羊人•二十》) 这几句诗像极了阐明读者与他所阅读的书之间的隐秘关系的妙语。阅读和人生是否可以了无痕迹溶化在一起从此难分彼此?我想是可能的,只要你把文本阅读中的一切带进你的生活与生命,阅读就可以展示了卡夫卡所说的那种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的力量,比如,当你阅读一个人的回忆录的时候—— 我有这样一种体验,读回忆录最好是秋天;秋天是独独属于阅读“回忆录”的季节。尽管纪德曾经很轻蔑很颓唐地过说回忆录永远只有一半是可信的,但是我通过翻动书页想要知道的,并不是“答案是什么”,而是“问题是什么”——于是当我想要走进“另一个不同既往的作者”,可以暗自期许也能诧异地悄悄对他说:“那竟然也是你?”好了,就在这时,你发现了没,是不是就像佩索阿描述的这样?想要在窸窣作响的书页背后巧合似的撞上这样的运气,可由不得我们读者,还得靠他(作者本身)。 秋天阅读回忆录,就暗示着你相信一切回忆必定都有一个饱满的开端:“它如同我们的落叶般的岁月,它如同我们的落花般逐渐枯萎的年华,它如同我们的云彩般飞逝的幻想,它如同我们的逐渐变得暗淡的智慧,它如同我们的阳光般逐渐变得冷漠的爱情,它如同我们的河流般冻结的生命。”(《墓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91页)这段话是如此清晰地指明了我所期待的方向,以至于自此之后每次看到与这段话相似的语句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读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的第六节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而只有拒绝的东西才可能给出存在于可能性中的东西,黑暗拒绝可视性,而它也同样可以保持视觉:在黑暗中我们看见了众星。”
《墓畔回忆录》读后感(二):进攻,文学女青年
题记:社会才是人生的巴别之塔!
一个美女捏起一只绿油油的提子,轻轻地放入她那鲜嫩诱人的嘴中,马奶子、软温新剥鸡头肉、颤巍巍这些勾动人欲的词语突然浮现在我的身体中,我的心里忽然有一股暖流,穿过小腹,直达下体,欲望从身体隐藏的深处露出了一个小头,偷偷的窥视这个世界的美色,原来,欲望一直都在,只是你没有注意罢了。
夏日即将过去,刚从重庆回到苏州,重庆到了七点半,天空依然高亮,美丽的山城在景观也不逊色于苏州。苏州已经有点早晚凉了,早上起床,秋风已经将凉意渲染到身子上,提醒着秋日的临近和深入,一如那曾经游腻在身上的香舌所带来的清凉。早晚凉再过十几天,桂花就要开了,香气飘荡在水面上,园林中,整个城市又将在桂花的香气中沉浮,秋天,一个美丽的季节。念及此,心里顿时舒服着起来,匆匆奔波的心情顿时又安然如护城河的水,缓缓的映发着天空的清透和灵性。
夏多布里昂,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旋,当年某人在描写雨果时,在描述雨果年幼的志向时,说雨果在小学作文课上曾喊出:“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的话之后,我虽然对他充满好奇,也了解了他的生平,对他的作品却毫无了解。终于,在一本外国小说上再次看到主人公开始翻译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我终于下了决心,到蓝色书店买了一套。也许好久不看散文了,也许是以前读的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太短了,我曾经一目十行的看书方式在读《墓畔回忆录》时只能如陌上花香,缓缓归:每看一两页,就得停下思索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为自己死亡所写的书,让我感受到了蕴含在其中浩瀚澎湃的激情,以及那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启蒙人如此深刻而绚丽的文字。
到最后,只能在和朋友探讨小杜的诗歌中偶尔思索,云容水态谁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小杜可以如此自喻,夏多布里昂若知道这句诗,估计也会如此自喻。突然想到大学时,一个老师带的一个研究生很执拗的认为高启和外国一个写情色文学出名作家类似,搞的导师狼狈不堪,被学院引为笑谈,成为文学院文学研究上的一个谈资。如今,我也有这种趋向了,总算明白那个执拗的研究生心理了,纯粹是爱屋及乌,在自己喜欢的两个作家中寻找共同点,就是那种希望和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成为情侣一样的心理。
毕业数年,同学之间或有联系,或有了无音信,亲疏之间,已然在这社会上湮没于茫茫人海中。物欲横流,人心诡谲之时,人生的关系又怎么能如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永恒以至延续。突然想起当时在网上码字时与众多文学男女青年打情骂俏的场景,如今也风云不再了。那些文学女青年们,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一手键盘,一手书籍,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在我们相隔千里的垂涎中,翻腾着那些美妙却又引发原罪的字符。
总是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拜伦,那个被女人诅咒却又心甘情愿被勾引的魔鬼?为什么不是小杜,有着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为什么总是不能享受到男人和诸神的欢乐?现在神女遍地都有,谁愿意做那寡居的女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一手诗稿,一手摸向坐在自己大腿上的文学女青年的时光已经荏苒不再。现在的文学女青年们,有了阅尽世界的眼光,尝遍男人的身体,一切都已成为青春的经历,当某个男文青色咪咪的盯着她,要求那非分之想时,她会大吼一声:“滚,让你阿肖克尔的脑袋去撞西西弗斯的岩石吧!”
《墓畔回忆录》读后感(三):夏多布里昂,对于一个时代的祭奠
对一个时代的祭奠
本书的篇幅在我读过的书中可以占据一个之最的名头,两千页的文本即便对于小说也会显得过于冗长,然而对于人的一生岁月来说已是极大的浓缩。我们从来到去,期间对于这人世每一个凝望都是永恒深重而富含个人意义的,文本所要达到的重述的企图相对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片段性的临摹以足以让我们在作者的情怀感召之下重返昨日,进入历史的深处,见证一个时代的沧桑。
夏多布里昂是作为欧洲浪漫主义兴起时的法国浪漫主义先驱的名义进入文学史中,对于浪漫主义我也仅只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因为一方面对于文学史标本式的研究没有多大兴趣,文学的历史对于我来说就是各种经典的传承。另一方面鉴于时空的隔绝,对于当时法国的人文精神状况没有具体的感知或概念性的把握。这双重无知使得我无权对于本书的文学史地位及当代影响力作出任何评判。然而文本的流传是超越官方论调而基于大众的精神需求的,我们作为后来人,除却生理特性的一脉相传,更是承载了以往历史的恢宏的内涵,文本是我们得以窥见过往的重要路途。
如果说夏多布里昂仅因其浪漫主义先驱的名号在文学史上留名,那么他就被紧紧的凝固于他所在的时代,我们说到他就像说起很遥远的事,一些列的因果递进使得跟我们脱离了直接关联。而恰恰是本书,在众多类似的命运与生活的重复中真诚的叙述,让他得以进入我们时代的视野,进入后代读者的生命与生活当中。正是这种超越性让本书在近两百年的今天依然不失去其新鲜的效力,依然对众多的生命传递着对生活的恒久的感受力。
本书的超越性一方面源于回忆录或自传这种题材本身,对于存在我们有太多的困惑,而生与死的感慨是文人数千年不变的主题,这种发问贯穿着每个个体的日常反思。当作者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无疑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所做的对短暂人生的超越性尝试,对于自身存在的铭刻无疑抚慰着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跟血脉的传承一样坚不可摧的信念:借以存在形式的转换而保留某种本质。由此,跟大理石所宣示的一样,文本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真实的人生,一个真实的故事,像你我一样有真切的喜怒哀乐,悲伤时一样掉下眼泪,有过切实可感的幸福与困境,静静的等着在你我的情感中的再次现身。而超越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对时代生存状况的超脱,本书中大量关于政治生活细节性的描述可能让读者感到烦闷,而我们作为一个听故事的人,想要得到全部的故事就只能保持耐心,他所说的正是他在意的。政治以及舆论的公共影响力是作者刻意寻求的,是自我认同的信念根基。而夏氏的敏感多疑造就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特质(这种特质可以在作者激情平复之后的自我反思中窥见,虽则其后被拥有强烈归属感的宗教情感所平复),一种激烈的欲求与冷冷的超脱总是同时根植于生命的每一件事物当中。一边享用自己的情感一边又冷漠的摒弃它。而这种特质跟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极为相符:激烈的情感总是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平复,然而又不同于长久的平寂。
当然人都有诸种性格上的弊端,夏氏在多处的描述中展露了自己慕求虚名的本性,这也是人的通病,不过也因此让我们能够跟真切的了解其本人。一种高度情感色彩的渲染贯穿于文本始末,虚假的热情是难以持久,因此可以从中看出夏氏对于整个时代的一种稳固信念,而作品的丰富性正在于支撑起信念的社会基础的飘摇不定,随之而来的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作品的精华正在于对个人生活的感慨应和以对世事的哀叹。正如时代对个人的超越,个人命运也超越于生活中片刻的喜悦或悲伤,在一种哀叹之中我们得以将人生做一个整体的反思,这也是作为一个人终究要面临这种宏大的命题,而夏氏的文笔及对生活的真挚情感相得益彰,完美的展示了个人的孤独本性及人世的变化无常,此种感慨将会在任何一个时代触动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墓畔回忆录》读后感(四):回忆录都是站街小姐,赤果果的勾引
就连卢梭那么赤诚的忏悔录都被人诟病有矫揉,美化自己的成分,谁会怀疑其他人的回忆录的不会把自己美化成一个他希望被人接受的形象呢?
那些指摘夏多布里昂这本回忆录夸张,不实,做作的人,大可不必或于认真。
毕竟回忆掺杂二两悲喜,浇筑二两后悔和遗憾,和以流逝的时间之水,构成生命这道五味杂陈的高级料理,才是真正的完美。
近日看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呓》,看完许久不能平静,我在日记中写到,梦中见到了张岱,因为梦里跟着高端玩家过了一把奢侈的骄奢瘾。再一本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
同是对逝去岁月的百科全书般的全景记录,新旧朝代更替的夹缝中存在,我为张岱着迷,却不得不承认与夏多布里昂相比,其格局逼仄,狭窄的多。
当然不能过多的责怪张岱,毕竟非人力所能抗争的,大时代大社会的局限,固来为我们民族所缺失。
作为一个特别热爱拍摄废墟的摄影票友,居然在几百年前,有一个叫做夏多布里昂的家伙,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探索过一座座死去的废墟之后,我又被召去目睹一座座活着的废墟”。笔译者说到,在夏多布里昂的笔下,废墟体现着过去的时间,当它与人的目光接触的时候,它又和现在的时候联系了起来。因此,废墟比尚存的完好建筑更有更深的意蕴和美。
仿佛在废墟中升起了光亮,在踽踽独行的失落中,有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向我伸出了手……
蒙田是我超级喜欢的散文家,《墓畔回忆录》也作为夏多布里昂的偶像也是多次出现。
启蒙时代的蒙田写作方式有很明显的过渡,即从哲理性散文向写景叙事的过渡。
我曾好奇为何启蒙之前没有对自然的描写,后来明白那是因为这之前自然还只是上帝的附属品,当科学和文学发现了自然,才真正的发现了人。
什么时候自然成了独立的存在,人才能真正的在上帝面前不再只是一个奴仆。
很显然,到古典主义时期,这一个过渡都还是未完成,接力棒注定会传到浪漫主义的手里。
这时期音乐界出了贝多芬,从古典主义大跨步走进了浪漫主义时期,宣扬着自由平等和博爱,一种史诗一样的音乐赞歌,宏大开阖,不再囿于巴赫平均律一样的,在上帝面前虔诚卑谦,而是像英雄一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神奇的19世纪,音乐家也好,文学家也好,都有着科学家一样的魄力和心胸,相信自己可以主宰着未来,相信自己是天赋异禀的天选之人,坚信自己指引他人穿越黑暗责无旁贷。
鲁滨逊还只是发现了自己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人,这种自信到了19世纪,人可以是神。
所以夏多布里昂说出“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时,会是一张多么严肃的认真脸,雨果和巴尔扎克对夏多布里昂崇拜,也是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文人的责任的深切认同。
当然,这也是浪漫主义后来为人诟病的很重要一点,有一种自绝于人民的形而上学的尾巴,一直尾大不掉。
龚古尔说他原意拿人之初以来所有的诗篇来换取《墓畔回忆录》的头两卷。
我想说,谁又不是呢?
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录部分,真真觉得是神来之笔。
夏多布里昂很多写作手法的创新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作家,包括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时间的绵延写法可以说是相当超前的。
从墓里发出的腐朽的声音,这一未来的视角的审视,虽不像尼采从棺材中发出的怒吼,但也是直指人心的。
他的童年回忆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欧石楠,毛榉树,灯心草,雨燕……每一种植物,每一只动物,都是活力满满,都是生命的绽放,就是在这样的生命蓬勃绽放里,我仿佛回到了看《呼啸山庄》的回忆里,即使凄风苦雨,灯黄虫鸣,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然而正因为拖着那条大拖尾,后面的夏多布里昂的文字开始乏善可陈,也许正如他对自己定义的精分一样,一会儿是共和派,一会儿又是波旁派,复杂成就了夏多布里昂的多面性,也造就了他的不彻底性,拥抱过自然的热爱,早年的怀疑主义者,到母亲去世后,便退回上帝的怀抱,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赞美基督的诗意和美,相信永恒的时间之光,这何尝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自己也十分看重的对贵族身份热爱。
所以他才会那么强调预感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的咆哮,盖住了他降生时的哭声。
这种美化自己出身的自传,在他嘲笑的中国人身上才屡见不鲜,比如屈原。
即使他不是一个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捍卫正统王权,但从一个独立的人来说,他屈原不能和他相比,因为夏多布里昂身上是人复杂性和时代蜕变过程中阵痛的集中展现,是可以被原谅的时代所限,而屈原身上太多的虚伪。
《墓畔回忆录》读后感(五):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散论
2004-4-22 下午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雨果老人家年轻时说的,夏多布里昂是谁我本来都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就是他老人家。法国也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当拿破仑兄用武力征服欧洲男人的时候,又来了个夏多布里昂以浪漫征服欧洲的女人了。所以雨果少年时这样说倒也符合少年心性,征服女人可是每个发情期的少男想做的。
上面说的虽是人之常情,但也有点龌龊了,下面言归正传。看到雨果这句话,就想起当年年方十岁的张居正曾在家宅井旁仰天长叹,道:“若王守仁先生死,我张居正以何人为师?”都是孺子猖狂的气度,虽是猖狂却也显示出两个未来大人物少年时的鸿鹄之志。也许更多的人想起的会是刘邦项羽观看秦始皇车队仪仗时说的那些什么大丈夫当如斯、或是可取而代之等话吧,不过咱题目上说的是文不是武,没说要么成为霍去病要么一事无成,或是要么成为成吉思汗要么一事无成。
在如今这个还算安稳的中国,像拿破仑兄那样靠武力横扫世界是很难的了,也就只能靠金钱或是像夏多布里昂兄用浪漫打动女人的心了。看过他的书的人国内看来不多,不过他的文气学得倒是不少,都非常浪漫了,在经历中享受爱情。当然,和夏多布里昂有相似的经历的人也没几个。所以看现在的文章,都有一种偏软的感觉。尽管作者们都不乏才气,却只能是文人气十足或是痞子流氓气十足。
在网上看的书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很佩服的就是小椴写的《杯雪》了,里面古文的知识让我都想为《杯雪》做笺注了。不过就豪气上看,虽是武侠,文章还是被几位主人公的文人气削弱了。袁老大是位豪气干云的人物,可惜也被小椴的古诗文弄得太文绉绉的了,和金庸先生的几部好书比起来真的是像少年骆寒的九幻虚弧剑走偏锋,文气苍茫而偏柔弱。情义天下大业体现的是南宋的苟且偷安,也许这就奠定了文气的基调吧。
九州的设定者们的梦想是要开中国奇幻史诗作品先河,凭着他们的作家群里各位作者的功力,再加上有时间有金钱的支撑,应该可以成功的。只是当他们开始卖弄学识和才气的时候,那种金戈铁马挥手补天裂的壮志凌云就有点被削弱了。《九州飘渺录》中让我看得热血沸腾的不是其他,而正是很少有那种文绉绉的战场描写,细微而入骨,真实残酷杀声阵阵。其实,写这种文章古文的运用不要太多,有时只要一句话就能石崩天裂,让读者有长虹贯日之气势。九州的一系列文章作者的才气都太好了,其中有一位是写《悟空传》的今何在,所以和《杯雪》一样,文气冲淡了应充斥在全篇中的豪气。当然,网上有这样的书,可以说上是我们读者的一大幸事。其他好书网上应该也不少,只是我无缘相见,其他自己看到的一些书也只能说一般了。
读书人说豪气,让我想起了一句“文人读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自古文人胸中有天地,豪气跃然纸上者多矣。如太史公的好奇和自身被去势后对豪气的向往(有点对他老人家不敬了)使专诸、荆柯等以武犯禁的刺客名传千史,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然真正是文韬武略双修的倒也没见几个,此时无事也来数数看。
曹操算一个,不管是奸雄还是能臣,建安风骨在他的带领下,刚健豪迈夹杂着对人生个性的追求开启了三国鼎立的风云大幕,临槊赋诗,对酒当歌,豪杰也。后来,有个高适,唐诗边塞诗之冠军,献策肃宗,于平定安史之乱有较大功劳,却知之者不多。明代有了个王守仁,对此人在文学上成就知之不多,但其哲学上一句“不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汝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可以想象到那颗敏感的心,在平定那能搞得风流才子坐立不安的宁王之乱等军国大事时还能关注到一朵花的玄学意味,借花寓意,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和禅宗的佛祖拈花微笑并驾齐驱,却也可以望其项背了(我对哲学史没啥研究,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故后世对他的敬仰之情是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数百年后又出了一个曾国藩,八旗子弟懦弱无能,太平天国长驱直入,他率领的湘军保住了大清的江山,也有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此事功过历史自有评述,但是他的文章也被前辈学者钱仲联在编辑明清散文八大家时收录,可见其文采武功皆属一流了。还有一位是刘基伯温,大明开国第一军师,也被收入了明清八大家中,作为中国历史民间传说种种传闻中隐约与诸葛亮双峰并峙的智慧的代表,在人们口头传诵的还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文采武功。
说起八大家,就不能不说唐宋八大家了。不过对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反而不喜欢,诗歌韩愈的我也不喜欢,虽然喜欢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喜欢柳宗元的《江雪》等诗,但于唐文还是喜欢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游桃园序》等文,可能是他们虽然开一代风气之先,但文中还是奇崛险怪,或是幽暗难明,没有脱离中晚唐诗歌的那种已呈衰落的文气。宋文喜欢的倒是不少,欧阳修、苏轼是最爱,读起来风骨盎然,意味十足,圆润丰满中又筋骨刚健。当然,先秦两汉魏晋更是文章的祖师爷,我辈自是景行行止,高山仰止。
看完上面自己对韩愈柳宗元的叙述,不觉有点汗颜。想起李清照早年在一篇《论词》中对前辈的评价说温庭韫韦庄等是郑卫之声,流靡之变;对后主父子虽说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但前面一句“语虽奇甚”,估计也是不满;说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殊、欧阳修、苏轼虽学际天人,然词却是“句读不葺之诗耳”,不协音律;晏几道、秦观、贺铸、黄庭坚也被他批的不说是体无完肤吧,反正也是不入方家之眼的说法。当时看到后,吓出一身冷汗,李清照竟然如此睥睨臧否前辈,真乃女中豪杰也。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上吧,想想自己想做过什么:
曾经想过要么做解放军,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杀人不眨眼救人于水火千里独行的大侠,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乔丹,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无为的老子,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AC米兰的主席,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色狼,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成为夜御百女的黄帝,要么一事无成;最后想到的是要么成为江中无水,要么一事无成。那现在我不就是江中无水吗!突然就感觉很有成。
再说法国,今天看到一系列法国作家的名字,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佐拉后心中一股热流涌出,可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心理很不痛快,因为没人说大仲马,只说他的儿子小仲马。唉,刚开始了解法国除了知道女人和男人一样很开放(不象中国只许男人开放,就不许女人开放)外,就是从大仲马书中了解的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阿芒得骑士》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达达尼昂、阿瑟斯、波瑟斯、阿拉密斯那时是天天挂在嘴上,还挥着根胳膊长的竹枝就像挥着金箍棒一样说是西洋剑。当朋友们为爱斯美琳达和卡西莫多所谓的超越肉体的爱情如痴如醉的时候,我却在为达达尼昂们为情义忠诚一剑走千里而热血奔腾。说到这,又说到豪气上来了,看来像我这个文弱的人渴望豪气是因为自己百无一用吧。
说道文弱,比我更弱的是普鲁斯特,得了哮喘不能见光,写的文章也不是豪气干云的那种,可那半部《追忆似水年华》就让我痴迷感叹了几年,以后还得继续感叹下去。不知道整部书看下去我会不会自卑得跳水以祭他。意识流流得顺溜溜的,把整个法国上层贵族和普通人生活的场景在历史的长河中开出个支流,让它慢慢地流得四平八稳,流出了个先锋文学的祖师。其实写东西用心的人都知道,要想写好就要让自己文章的思绪顺着自己的想法想水一样流出来,是激情的就井喷,是柔情的就细水长流。像我之所以会写出这篇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在一本书上看到夏多布里昂,就流出这么一堆废话了。
今天在路上看到美女穿着短袖,露出雪白的胳膊,正在意淫的时候,想到所谓的红颜白骨,刚准备谴责一下自己色狼的心。又想起所谓境界,不管是佛家还是道家的,都讲究顺心循性而行。如果我不色美女的话,不就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吗?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人生三大境界,最后一重境界我私自改成了“蓦然回首,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这才符合“空明”的境界。不过说回来,境界是靠自己的修行,不是靠压抑。如果什么时候我真的能看美女和看平常人一样,那说明我真的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如果压抑自己不去想,不去看,不去做,则说明现在还不行,还是个小和尚(哈哈),要努力修行。
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我的少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没说出什么可以让人说这像个大人物说的话出来,也就只能拿以前老先生说的话来凑数了。唉,没得流了就不流了,说了这么多也该喝口水溜达溜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