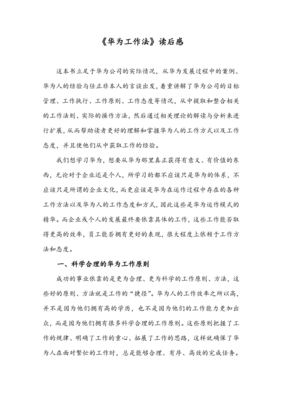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是一本由(美)杰里米·里夫金 / 特德·霍华德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大32图书,本书定价:2.05元,页数:2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精选点评:
●打着物理规律的名头胡说八道 尽然表扬毛时代中国穷的对得起地球 这作者脑子进水
●貌似专业的民科书籍。
●承认自己的有限,让自然的进程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上自由展开。停止自我欺骗,无止境的追求进步和不朽的尝试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明白熵的道理,就像明白每个人都会死这个道理同样重要,也同样被忽视。我们害怕承认最终的寂灭,因为那会让人失去自我。而自我从来就是一种卑微的幻想。承认那无可挽回的死亡吧,也许我们还能更明智的在生的有限时光里做出最符合“爱”的选择。
●师大人大2372/6058。匪夷所思,感觉就是在控诉传统能源业的暴利而已。印数100000册。
●“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
●懂得了熵,就懂得了这个世界。
●有意思
●。。。凑了好多字 。。。
●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示是,讓我意識到,自己自從運動以來,認知發生的一系列模糊的變化,原來是從非再生能源型的世界觀(與之對應的是機械論世界觀,高熵、工業社會……)轉為一種平衡的、流動的循環型能源觀念。世界觀起了變化,生活自然不同了。雖然書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生成,不乏絕對之言,但卻給人以好的思考。誠如作者所言,本書將注意力集中在作為過程而非作為最終狀態的熵上,從這個地球能量消耗/消費的狀態,我們的注意力應該最終轉移到涵養自身,如何減少損耗,如何處理精氣神的盈虧,以及明白在這消費世界里為何及如何“自發的樸素”,作者最後,說到東方哲學,宇宙,以至於──“愛”,是推己及人。
●老书。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后感(一):摘录
一个人每年需要吃掉 300 条鲑鱼,这些鲑鱼要吃掉 90,000 只青蛙,这些青蛙要吃掉 2,700 万只蚱蜢,而这些蚱蜢要吃掉 1,000 吨青草。
理查德·威尔金森在《贫困与进步》
牛顿力学原则、笛卡儿的数学和培根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世界观。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试图在这些基本观念上组织起客观世界。 这三种观念的中心思想是观察中的绝对可重复性(科学方法)和一切过程的绝对可逆性(普遍的数学和力学过程) 。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后感(二):第两千零一颗石子
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装满石子的容器,你闭只眼,把石子从里面拿出来。
一颗,两颗,三颗……一千九百九十九颗,两千颗。可当你伸手去拿第两千零一颗石子的时候,可能碰到的只是空旷的容器底。
这本书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消极的思想,你也许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可能每一个现代人都免不了会这么想。但是谁能保证新能源一定会出现,谁能保证技术一定会带人类走向美好未来,谁能保证我们的路是正确的,谁能保证……
最后乐观的人乐观如故,悲观的人依旧悲观。
但我觉得,这本书提出的思路,是值得我们一读的吧。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后感(三):越来越多的疑问---这也是混乱?
读这本书的感觉:
1、除了最后的一两章,前面的很多涉及领域,作者几乎没有乱讲,列举事实基本没有太多争议。
2、略微遗憾之处是过于粗略,个人认为应当学学莱布尼茨“执着”,在行文中多一些细微和数据的支持。
3、本人不甚同意关于生物方法为社会开辟新能源和新材料的警告,当然,还没有找到作者的《谁来扮演上帝》来看看。
4、熵定律和混沌理论应该联系起来在一本书里展开就好了,我认为这二者千丝万缕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后感(四):不是评论,就是写点东西
写东西还是很困难,因为一些零散的东西在自己的大脑里很难搭出一个完整的构架。
打翻的牛奶回不到杯子里,破了的杯子无法复原,水往低处流,时间过去不会重来,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自然规律。在这些规律的背后,还有着能量的涌动。
能量自发的流动只有单一的方向,总是不断地统一和平均,这些没有差异的能量,是无法用来做功的,所以对于人类来讲,就是没有用的。
熵是用来度量混乱程度的,从大的方面来看,人只会把地球搞得越来越混乱。桌面上的东西只会越来越乱。但是假如桌面上只有很少的东西,就很容易保持整洁,所以我在生活中开始奉行了一个准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后感(五):熵与奇点的故事——一些不相干的话
读了,不懂,使劲挠墙,也无法改变我是物理白痴的事实。
看到SFW上的科普文章,提到人类史的奇点云云,突然想起某年见过一篇论文,把singularity这个词用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
80年代盛行过“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从学者到官员,从气功大师到平头百姓,都会吹一吹这三论,仿佛是万能膏药,“论”到病除,无比神奇。此外,还流行过一个字――熵。
好些个文学研究者把“熵”吹得玄之又玄,个个俨然文理兼修的牛人,跨越多学科咻咻咻,轻捷得如同在跨自家门前的地毯,其实都是从这本书里扒来的。
他们有没有读明白该书的要义,同为文青的我,是很怀疑的。不过用一个概念化生的比喻义做构架文学史的基础,这么浪漫的事也只有文青才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