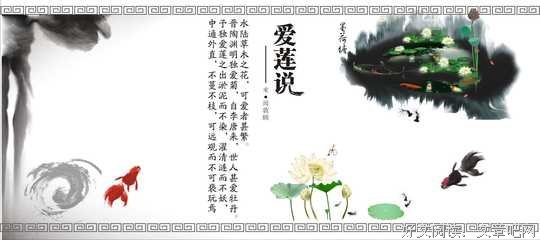
《日本的世界观》是一本由[美]马里乌斯·詹森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点带面的大家小书,语言表达精炼,文笔一流,以极小的篇幅勾勒近代日本的世界观。因为主要面向美国读者演讲,谈及对西方的认识颇多。
●今天才拿到书,虽然还有不足,但觉得还挺好的。很好的普及书,言简意赅。副标题“两百年的变迁”因为cip上没写,没法放在封面上,不过文案应该可以显示内容
●马里乌斯·詹森的这本小书选取的三个时代的三个人为代表(杉田玄白(1733-1817)、久米邦武(1839-1931)和松本重治(1899-1989))来作为话题的聚焦点,但是这三者都只是引子,作者的聚焦点是这三个人所代表的三个时代,杉田所代表的是从古典日本及中国影响下走向西洋影响及开放,久米所代表的是从倒幕维新到帝国时代的歧途及此时的日本人的国际观,松本是长于帝国时代留学欧美的国际派,见证了从战败废墟到战后奇迹的变化;三个人三个时代也是日本三个国际观的典型变化时代,结合丸山,小熊服用更佳。
●美国人真是善于研究民族心态,《菊与刀》也是美国人的作品。日本脱亚入欧的心态值得反思。
《日本的世界观》读后感(一):随手记
随手记:1.彬田玄白观看西洋解剖,认识到中医的谬误,翻译荷兰解剖学著作,是推翻日本传统世界观的象征与原动力 2.在近代前,中国是日本唯一且始终产生影响的国家,而日本并未完全吸收,且一直尝试保持自我独立,更像是是一种“欲拒还迎”的态度3.进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清朝,都同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彼时(1637)的日本严禁国内基督教的传播,而在国内掀起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但是由满族政权主导的清国,使得日本明确的讲“中国”与中国文化相区分,也就是“华夷变态”世界观的逐渐形成。4.18世纪的日本文人开始摒绝来自中国的文化影响,不仅是儒学,还有佛教。他们致力于直接阅读儒学经典而非阐释书籍,并且在日本神话,文学中寻求日本民族纯粹的个性——纯洁、自然,无拘束,恰好与儒学的条框相反。借由对日本的肯定而将对中国的抵制合理化
《日本的世界观》读后感(二):《日本的世界观》读书笔记三则(三)
要想厘清20世纪前30年日本的世界观,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詹森坦言自己尚不确定,假如詹森这样的日本史专家都不确定,那么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一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已经迅速崛起的国家何以跌入战争的深渊。
从结果上看,陆军大将石原莞尔似乎是对的,因为日本1945年战败,但他的理由是“日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断送在心理战和政治战上获胜的机会”,詹森认为,“失败是由于日本不能构想出能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贯性世界观”。我同意上述两个人的判断,但这不能构成战败的所有原因。一个国家,一场战争,一件事情,一个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多方势力的博弈和斡旋造成了1945的战争结局。
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扩张是一个重要原因,英美对日本的疏远是另一个原因。因为前者,日本意识到,不在东南亚地区抢占先机、分一杯羹,最终将一无所得;因为后者,日本被推入了军国主义的怀抱。
詹森研究了所有关于战争决策的会议记录,他发现,“矛盾和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仅根据策略而不是战略的决策”,有的会议记录一厢情愿地设想旗开得胜后的状况,有的语焉不详,不负责任,总之日本被向前追溯七十年里的顺风顺水冲昏了头脑,以为所有的危机都会化解,走向最好的结局,但这次显然不是。
战争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战前的紧张气氛弥散其间,仍能感到纸上有风雷激荡。海军大将永野修身说:“政府判断,如不开战必将亡国。即使开战也有可能亡国。然而,一个国家在这种困境下如不战斗则会丧失其精神,就已经走向末日了。”他所谓的困境指的是日益减少的石油供应,要在军用燃料足以支撑初期战争的时候,努力攫取更多的石油。这是战争的物质动因。讽刺的是,当时的石油储备只够1979年的日本用几天。
日本战后的恢复速度是惊人的,其原因自然有美国的支持,也有自己的争气。在政治和军事上,美国要维护它在亚洲的安全地位,日本是唯一的选择;在经济上,拥有工业潜力的日本对美国举足轻重。日本从美国购买技术,大力发展经济,日美双边贸易总值战后不久就达到300亿美元,仅次美加,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经济国家。
对于战后“时势”的应对,日本的反应巧妙、坚定而且合理,它没有沦为美国的“小弟”,而成了被美国尊重并且不可或缺的伙伴。1977年的数据表明,日本gdp世界第三,达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收入不计算石油国家的话,已经位列世界第十,出口量以惊人速度增长,令美国贸易出现赤字,波音飞机曾经轰炸过的这个岛国,现在却在替波音公司制造零件。
导致战争灾难的冒险主义和苦难经历渐行渐远,詹森写道:“日本的船只载满由高薪和勤奋的日本工人生产的货品,空前地涌进世界各个港口。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地把握住眼前的机会,避免了吹嘘和风头,并抗议他们可选择的机会真的不多。”
这是一个美国史学家对日本由衷的赞扬,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合卷之际,心情复杂沉重,如果说读史可以增长智慧,那必须是抛开了情绪的阅读,面对日本,很难抛开情绪,那种敬佩中又夹杂着痛恨的感觉实难描绘,我想日本最值得学习的一个是强烈的学习欲望,一个是上下同心的精神,在各个时期,他们都有明确的世界观,并为他们的祖国不懈奋斗。
《日本的世界观》读后感(三):《日本的世界观》读书笔记三则(二)
二
至于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日本通过“走出去”,并且认真分析对照,已有前所未有的明确认知,其结论为:西方民族有不安和浮士德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东方立足于“人性善”,这就导致西方制度较为健全,因为它假设人是坏的,而东方制度欠缺,且在财产保护一点,东西方差异殊甚,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是一切制度之根基。
在宗教方面,日本受到欧美的影响(甚至是责难),一方面撤销了基督教禁令,一方面鼓励出国。允许基督教存在一方面是源自中国的儒释二教式微,但更多的是日本发现基督教同样具有教化人心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在教育方面,日本用于留学的预算一度达到文部省总预算的21%,通过留学,一些知识领域稀缺人才得以迅速补充,而紧随其后的,是缩减大范围普遍性质的留学,支持成熟学者出国,使他们的西方知识得以巩固和增强,并回馈祖国。
以女留学生津田梅子为例,回国后她就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女子大学;前面提到的伊藤博文,作为使团的副使,后来成为了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首相和枢密院议长、明治宪法的设计师,耶鲁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
和对西方的尊重、学习相反,使团亲眼目睹了东方的不公、怠惰、腐败的社会现状,对东方充满了悲观失望,“日本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中国文明与风雅的尊敬丧失殆尽”(p72)。福泽谕吉在《劝学书》里,对中国人所抱有的对外国的顽固冷漠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这在《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里,慈禧太后动辄贬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一事可以得到印证。
伊藤和福泽等人是当时日本的先进群体一员,他们早已认清现实,对中国不再盲目崇拜,但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可能还尚存对传统中国的敬意,不久之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爆发,千万士兵亲身感受中国的衰朽,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亲朋好友,这些印象“固定成为一种对他们所蹂躏的国土上的国民的傲慢,甚至是蔑视”。
书读至此,作为中国读者,其羞愤无以言表。
一国衰微,被人蔑视,一人如不求上进呢?还不是一样?在中国的使馆区,国中之国,日本使团亲眼目睹其干净、整饬,使馆之外脏乱差横行,鸦片馆林立,这样的国家,恐怕很难被人瞧得起。
本书作者马里乌斯.詹森在书中充满对日本的敬意,作为被学习的国度,从不会对真正向学的国度鄙夷,反而充满赞赏,这也是老师喜爱努力和勤学的学生的原因。
更难能可贵的是,马里乌斯.詹森以一个治史者的严谨,提醒读者切勿舍本逐末,岩仓使团固然传播了先进文化和经验,但是留守日本的高层早已开始断断续续的维新举措,维新不是自使团始,而是说,使团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马里乌斯.詹森对历史事实的敬重,不因某事件的特殊性和猎奇而有所偏颇,这是一种史学家的可贵精神。
作为岩仓使团的书记官,久米在90岁时回顾一生,他说,“我的第一个三十年目睹了自古相传的封建割据的崩溃,那时我们的眼界局限在小郡邑之中,把区区所见当做宇宙。我的第二个三十年看见了日本统一,并且置身于列强之林。在最后的三十年,我见到日本作为列强之一,维护着世界和平。”
久米在1931年逝世,他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及后来日本身陷轴心国的战争旋涡,陷入穷兵黩武的暴力时期。日本没有维护世界和平,相反,他们破坏了世界和平,但是抛开战争不谈,日本的改革之路如此迅捷,简直是一步冤枉路都没走,甚至战后重建之迅速,都让人咋舌,这些建设成就,让人敬佩和羡慕,也让人不断探究其原因,期待借助他们的经验回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谁不愿自己的祖国强大呢?
《日本的世界观》读后感(四):《日本的世界观》读书笔记三则(一)
《日本的世界观》一书看得艰辛缓慢,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日本专家,《剑桥日本史》的主编马里乌斯.詹森,本书初版于1979年,分析了两百年间日本从封建落后小国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的原因,以及日本民族思想演变。书分三部分,分别选取三个时代的三个重要人物,以此折射日本的社会变迁。这三个人物分别是:18世纪的杉田玄白医生,19世纪的久米邦武,(岩仓使团的书记官),现代的新闻人松本重治。
遗憾的是,第一部没有看进去,近些年读书的注意力、理解力都大大下降,这是个可悲的事实,需要经常在书上做些注解、笔记、或者重点部分涂亮,用这些方法才能勉强读进去。
但是从第二讲《求知识于世界》开读也无妨,我一向赞成重读,从重读中得到的收获不亚于初读,我相信自己必将重读这本有价值的书,届时除补上第一讲外,第二、第三讲也一定会获得新的领悟。
1868年,年幼的明治天皇颁布《五项誓文》,郑重声明“求知识于世界”,日本大开国门,派出人数众多的岩仓使团赴欧美游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体和经济等方方面面,仅初次到达华盛顿的使团,就有77人之众,使团从1871年开始走出国门,1873年结束,历时漫长。之后又派出多个使团,涵盖各行各业,这些出访者大都成为后来日本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鼓吹者。考察内容涵盖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教育、工业、交通通信等各个领域,源源不断的使团和曾经的“遣唐使”一样,学习了欧美工业革命之后的先进文化并带回国内,日本渐渐与欧美发达国家搭建了桥梁。
而此时的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后,“在国际威望序列上,中国的地位迅速下降。这部分是因为日本人知道外国对中国的评价,而在他们造访依据条约开放的中国港口外围后则加速了这一变化。他们在上海的见闻使其深信,类似的丧权辱国绝对不能在日本发生。”
由此可见,日本的学习精神、反思精神实在惊人,比如三次出访的福泽谕吉,回国后编写了简明易懂的小册子《劝学篇》,普及西方进步学说,鼓励努力与勤奋,起到了开启民智的积极作用。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策动了推翻幕府的革命,伊藤博文则成了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主要设计人。
当然,使团成员并非全部学有所成,其中一个,回来就发动了叛乱,还有一个,无论如何不认识阿拉伯数字,找不到自己的宾馆房间,好说歹说,大使才开恩放回国。但一件事情是否具备先进性,要看主旨和大势,大多数使团成员通过学习大有收获,并且赞成推进稳步而温和的改革,这就够了。
其中一个使团逗留美国205天,他们不忘创建新日本的使命,决心从政府形式中识别出其可能包含的现代化政体的核心,这一点非常值得敬佩:既学习,又扬弃,寻找适合本国的道路。他们的报告充分体现了日本人严谨务实的作风和卓越的学习精神,那就是擅长看到问题的核心和国家的实质,关注更深远的趋势:
使团关于美国的报告有397页,英国443页,因为英国在国土面积、历史和生产力方面更适合日本效仿,德、法各200页,俄国100页,因为“俄国的文明程度似乎是西方国家中最低的。它的产品粗劣,贸易与工业受外国人操纵,国家财富由专制政府和贵族垄断,农民生活的穷困状态令人震惊。愈向欧洲东部走,文明程度似乎愈低。”
反观此时的中国,慈禧太后也派使团出访,使团归国后对慈禧太后进行汇报,主张改封建制为君主立宪制,慈禧太后也表示同意,但是“预备立宪”的时间长达12年!漫长的过程让人怀疑君主立宪的诚意,而且错失了国家发展的良机。
中国就是这样和日本拉开认知和思想上的差距的,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最大的差异,就是认知和思想的差异,思想决定行动,明治维新已经箭在弦上了。
《日本的世界观》读后感(五):徐静波评《日本的世界观》|两百年来日本在世界中的抉择
一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 Jansen,1922-2000)所写的《日本的世界观》(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旧著,初版于四十年以前。书的副标题叫“两个世纪的变化”(Two Centuries of Change)。题目很大,副标题也很大,我书评的题目也不得不起得很大。他讨论的是1770年代至1970年代两百年中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决定了日本在当时及以后的航路,也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命运。世界观真的很重要,它体现的是对他者(同时包含了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认知和判断,无论就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将在根本上决定或改变其自身的命运。 詹森的著作实际上是三次演讲的文稿,只是薄薄的一百多页。他自己也明白,要在这有限的篇幅内讨论如此宏大的话题,显然很难详细展开。但是詹森谈论得很好。作为一位出色的日本研究家,他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宏大视野,用不多的话语,就把日本这两百年来对世界认识的变化、以及据此所营造的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詹森或许未必与东亚和日本发生关系。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他主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史,1943年毕业后即进入军队服务,接受日语训练,1945年随占领军进驻日本三年,由此兴趣从欧洲史转到了日本史,回国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后来出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以《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 Sen)的论文(1954年出版)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了几年后,于1959年起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十年以后出任新组建的东亚研究系第一任系主任,1977年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主席,并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出版的著作有《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1961年,已有中译本)、《日本与中国:从战争走向和平1894-1972》(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年)、《德川幕府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okugawa World,1992年),以及本书等。此外他还主编了很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已译成中文出版的《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因其在研究日本方面的卓越成就,1991年当选为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1999年被天皇授予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在日本他被认为是“亲日派”,不过我的感觉是,詹森并无情感上的亲日倾向,他只是一位从西方立场来审视日本的研究者。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深湛的学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使得詹森对研究的对象善于从宏大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以我个人看来,他的学识似乎在赖肖尔之上。在《日本人的世界观》这本主题宏大的著作中,他选择了杉田玄白(1733-1817)、久米邦武(1839-1931)和松本重治(1899-1989)来作为话题的聚焦点,其实书中对人物落笔并不很多,想必是想通过这三个人物,来展现出其所代表的三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及认知的转变对日本的意义吧。下面,就围绕这三个人物以及这三个时期,分别展开一些评述。
二 大航海时代以前,日本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东亚,确切地说,差不多就是中国,以及作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媒介和桥梁的朝鲜半岛。日本人知道佛教来自一个叫天竺(印度)的遥远国度,也想到那里去看看,比如1187年第二次来华的僧人荣西就向杭州的中国官员提出,希望到西域去巡礼,但当时南宋已失去了对西北地区的管控,无法开具通行文书,因而未能成行。因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日本人眼中的他者,差不多就是与自己同一人种的东亚人。十六世纪中叶及以后,沙勿律(F. Xavier)等传教士陆续登陆日本,其时欧洲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新发现也随着欧洲人的东进而被带到了东亚,传入日本的途径还包括稍后从中国传来的西方新知识,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G. Aleni)著的《职方外纪》等。十六世纪末期开始,丰臣秀吉及后来的德川幕府为了政权的稳定,除了限定在长崎一隅做有限贸易的荷兰人和中国人之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并摈斥任何的西文书籍。那时,日本人也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称南来的欧洲人为“南蛮人”,比如称天主教堂为“蛮社”等。不过到了1720年,比较开明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对荷兰商馆多年来在定期觐见中献上的西文书籍产生了兴趣,觉得只要无涉宗教,也可以打开看看,这就有了后来“兰学”的兴起,其标志就是詹森书中提到的杉田玄白等翻译的《解体新书》(1774年刊行)。 杉田玄白原来只是一个地方上儒医,同道中有一个叫前野良泽的医家,四十七岁的时候跟着当时的兰学家青木昆阳(写过《番薯考》《和兰文字略考》等)学过一点荷兰语,也到荷兰商馆的所在地长崎去游过学,获得了荷兰人根据德文翻译过来的《解剖图录》,和杉田他们一起翻阅了以后,觉得大开眼界。他们原来学的都是汉方医,虽然也讲五脏六腑,却从来不知道什么形状、长在身体的哪个确切部位,而这本书里却用透视法画得清清楚楚。恰好某日他们一起去看了一个女囚的尸体解剖,实状竟然与书中所画的一模一样!这让他们感慨,至少在医学知识方面,欧洲人远在中国人之上了。于是他们决定以这本书为蓝本,再参考其他几种荷兰文的医书,花了三年多的功夫,完成了《解体新书》。杉田本人其实并不通晓荷兰文,但序文和注解都是他写的,也就成了主要署名者。在后来的日本书刊中,都说杉田等把荷兰文翻译成了日文,而实际上是汉文,即汉语的文言文。那个时代学医的,习读汉文医学经典是入门的必修课。《解体新书》的序文中写道:“阿兰之国,精于技术也。殚心力,尽智巧,而所为者,宇宙无出其右者也。故上自天文医术,下至器械衣服,其精妙工致,无不使观者爽然生奇想焉。”《解体新书》的问世,可谓标志着日本兰学的真正成立,更重要的,是让日本人开始明白,在欧洲,还有一个完全不亚于甚至高于中国的知识世界。 这样的认识,得到了来自欧洲的新的地理知识的支持。1713年,新井白石出版了地理著作《采览异言》(1803年,山村昌永根据获得的新知识大幅度地增补了这部书,完成了《订正增译采览异言》),这部书主要参照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的标注基本上都沿袭了利玛窦的汉译名,它让日本人明白了世界并不是只有中华及其周边。新井白石后来又撰写了《西洋纪闻》,后来广为流布。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主要有箕作省吾编译的《坤舆图识》(1845年刊)、《坤舆图识补》(1846-1847年刊)等。 在《解体新书》出版、兰学兴起的同时,日本还出现了一种贬斥传自中国的儒学和佛学、抬举日本本土文化的“国学”。兰学与国学的路径虽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归,那就是要动摇一直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的地位。在订正增补本的《采览异言》中,叙述的重心已从中国和亚州逐渐移到了欧美,且对中国的称谓由带有敬意的“中华”改成了平视的“支那”。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坤舆图识》和《地学正宗》,亚洲部分的内容分别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九,对中国的称谓也一直是“支那”。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和人口的多寡为基准,用相扑的名位排列法加以排序,东西两边最高的分别是俄国和英国,“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很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据鳥井裕美子「近世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232-247页)。 由此可知,《解体新书》本身虽只是一本医学书,却标志着日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他者的范围从原先的东亚扩展到了地球仪上所展现的整个世界,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必须仰视的上国,原先被视作蛮夷的欧洲,或许更具实力。 不过,这一次世界观的变化,还只是停留在认知上,并未伴随着实际的重大行动,因为幕府依然对外实施着锁国政策,而西方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随意进入日本。 三 然而,在江户时代末期(即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日本人所获得的有关世界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书本和图录。由于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不要说去海外做实地的考察,连洋人也几乎见不到。当然,在更早的时候,日本人是去过一次西洋的,那时德川幕府还没有成立,丰臣秀吉也才刚刚掌握权力,1583年有四个日本少年曾受西部大名的派遣,跟着传教士到欧洲去游历了七年,可是等他们回到日本时,丰臣秀吉已经在1587年对传教士连续发布了两次驱逐令,因而这次东亚人首次游历欧洲的重大实践,竟然就宛如泥牛入海一般,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这一情形,在詹森书中论述的久米邦武的时代,就完全发生了变化。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以更为强大的七艘军舰在1854年第二次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迫使日本人打开了国门。兰学传来的新知识以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的消息,使江户末期的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大变局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之后一系列汲取新知识的行为。 1857年2月幕府设立了“蕃书调所”,一开始还把西洋看作“蕃”,但几年之后就改成了“洋书调所”,剔除了所有的蛮夷意识。这是日本第一所学习和研究西洋的学术教育机构。1858年8月,幕府在长崎设立英语传习所(不久在横滨也开设了这样的学校),后改为洋学所,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也就是说,还在中国人与英法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着力培养通晓西洋文明的新型人才了。1860年2月,日本人用购自荷兰的一艘一百马力的蒸汽机船定名为“咸临丸”,由日本人掌舵,跨越太平洋驶往美国访问,这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前往北美。舰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胜海舟,后来成为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也作为同行者。这是日本人在近代第一次正式出访外国,目的是与美国方面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书。这些日本人在美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亲眼见到了文明程度相对比较高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1862年11月,幕府第一次向荷兰派遣了十一名官费留学生。这比中国第一次向美国派遣留美学童早了十年。1865年5月,幕府向法国派遣了官员,以调查国外的军事情况,这差不多是日本官方第一次派人去欧洲,这些人将近一年后回国,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和对西洋文明的新认识。这一年,幕府还把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汉译的《万国公法》引入日本,当时日本的中上层人士都可直接阅读汉文,翻刻后在日本大量印行,日本人对国际法的知识,最初差不多就是始于此书,而它在中国本土几乎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官方考察团前往海外,虽然试图与西方修改1858年签署的一系列通商条约是目的之一,但后来则完全变成了一次长达二十个月的海外考察。詹森在书里特别提到了新政府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最高层官员加入了考察行列。正使岩仓具视是公卿出身的右大臣,副使是推翻幕府的功臣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四十六名成员中,有后来出任帝国大学总长的渡边洪基(二十五岁)、外务大臣的林董三郎(二十二岁)、递信(邮政)大臣的野村靖(三十岁)、内务大臣的内海忠胜(二十九岁)、司法大臣的山田显义(二十八岁)等,作为副使的伊藤博文当年也只有三十一岁,平均年龄约三十二岁。显然,这是一个能够吸收新知识的年龄层。一行还包含了五十九名留学生(女性五名)。考察团1871年12月23日坐船从横滨出发,1873年9月13日返回,一路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分别会见了各国的最高领导人,乘坐了当时日本还没有的火车、轮船,参观了政府机构、工厂、学校、医院、监狱等,实际体验了议会的辩论,在奥地利时还恰逢万国博览会举行,一行目睹了各国的物产和先进制造品的集中展示。返国途中,一行经过了苏伊士运河所在地的埃及、也门的亚丁、锡兰(今斯里兰卡)、西贡(今胡志明市)、香港、上海,不仅亲身体验了当时远高于日本的欧美文明,也目击了亚洲的落后和殖民化。铁血首相俾斯麦对他们的一番话,使他们意识到了《万国公法》的背后,实际上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支配着世界。此后日本在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跨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日后明治新国家建设的基本构想,主要来源于这次海外考察。 詹森书中述及的久米邦武,只是这次考察团的随员之一,担任书记官,年轻时曾入德川幕府官办的昌平坂学问所研习儒学,有很好的汉文功底。后以权少外史这一较低的官职加入明治政府,三十二岁时随岩仓具视考察团一同出行海外。如果没有日后由他执笔撰写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他或许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了。这部著作共一百卷,分为五编,印成五大册于1878年出版,不仅留下了一部极为重要的官方记录,也为一般民众了解西方开设了一扇宏阔的窗户。此书至今仍然一版再版,不仅出了现代日文的译本,甚至还在2002年出版了五卷本的英文译本,是今天研究明治维新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久米邦武也因而得以留名青史。 需要提及的是,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没有类似的海外考察团。可以算得上第一个官方使团的,应该是1868年由美国退役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正使的俗称“蒲安臣使团”吧,担任副使的两名中国人是官衔较低的志刚和孙家谷,另有近三十名随员,多为同文馆的学生,还配上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作为协理,实在是有些滑稽古怪。历时两年八个月,游历了欧美十一个国家,志刚和孙家谷等人分别撰写了《出使泰西记》和《使西述略》等,结果几乎都未能进入朝廷要员的法眼。直到1876年底,才正式派出了郭嵩焘一行出使英法,郭根据在欧洲两年多的体验撰写的《使西纪程》,差不多是一部可以与久米邦武的考察实录相媲美的优秀著作,却遭到了同僚的诋毁和朝廷的压制,他本人在返国后也因此失去了所有的官职。 久米邦武撰写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极为详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尤其是引领国家走向的领袖人物对世界的认知,他们在服膺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认同了近代世界的丛林法则,并把中国完全移出了仿效的范畴,不仅如此,考察团在香港、上海的体验,开启了近代日本高层俯视中国的目光,由此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决定了明治国家未来的航路,也昭示着二十世纪以后的歧路。
久米邦武
四 詹森的第三篇演讲稿写的有点长,论述的时间段涉及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末,而要谈论的人物松本重治,也是到很后来才出现,笔墨更少,事实上,松本重治也很难充任这段岁月的代表。我觉得,这八十年的日本,恐怕很难放在一个框架内谈论,实际上这是两个时代,以1945年为分界点。 先说一下此前的。诚如詹森所说,这一时代的日本,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跌宕起伏地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代初期,吉野作造这样具有人文情怀和民主思想的思想家,有力推动了大正时代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的主张,在知识人阶层中也赢得了不少共鸣者。但总体而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所酿成的国家主义乃至极端的国家主义,是这几十年的主旋律,军部、大多数政客和财阀,以及在教育灌输和舆论的鼓动下激扬起来的大部分民众,基本上都是国家主义者,无论此前是脱亚论者还是亚洲主义者,都把日本的国家利益置于所有价值的最高端。其结果,便是帝国主义的正式登场和法西斯主义的日益抬头。这时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便是自己必须要充当一个主角,一个至少可以在地区乃至世界的主舞台上支配他者的主角。这样的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行动,结果把日本这个国家和全体日本人拖进了坠落的深渊。 松本重治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去美欧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学习数理经济学、威斯康辛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经济思想史,四年以后回国。在大学短期任教以后投身媒体,1933年至1938年以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长的身份在上海待了五年多。他的教育经历培育了他的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但国家主义最终还是占了主流。在上海期间,他充当了日本当局与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集团试图和解与合作的媒介人。他的使命,还在于说服对方接受日本的要求。他与近卫内阁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虽然他没有极端的行为,在日本战败以后,还是被占领军当局开除了公职。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记录了自己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后来有中译本出版。
松本重治
詹森在书里将他列为三个论述的人物之一,也许是因为在松本的身上集聚了多重的思想影迹,也许是想让他来代表1945年以前日本人的世界观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松本未必具有代表性。也许很难给松本的思想贴上单一的标签,但总色调是比较温和的。而战败前的日本,却并不温和。野村浩一教授曾直白地指出:“近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47页)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是日本人的世界观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日本在1945年时完全走向了毁灭的歧路,是它在二十世纪以后——事实上在明治中后期就开始了——世界观出现明显错误的结果。这一点,詹森似乎没有说清楚。 战后日本人的世界观,也交织着各种色彩,但和平主义成了主流,美国人的强有力的改造以及日本人自己的努力,使得日本在战后培育起了比较健康的社会肌体。大多数日本人已经不愿意再次卷入大规模的战争。战后的发展证明,和平的方式也可以获得希望的东西。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它与西方世界发生共鸣,美国更是它安全保障的支柱,但是在地区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合作上,中国及东亚诸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邻邦。有机会的话,日本依然想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毕竟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做后盾。它试图在和平的框架内保持一种有选择的平衡。 开放、富有理性、具有良好平衡感的世界观,不仅对日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