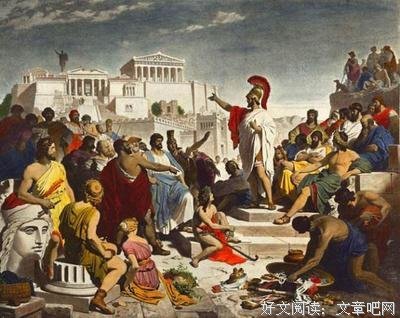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是一本由阿里斯托芬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5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精选点评:
●斯瑞西阿得斯一语成谶,苏格拉底最终正是被判渎神(两个罪名之一,《云》中作为诡辩家的苏格拉底也的确败坏了斐狄庇得斯的品质)而死,不得不说,阿里斯托芬的这篇喜剧倒是映照出了苏格拉底悲剧的人生结局。
●选读《阿卡奈人》 如果说叙述是一杯鲜榨果汁,阿里斯托芬加了一杯水,又加了一大杯。
●六个剧本,加知堂译《财神》,目前读过的阿里斯托芬。
●《云》读毕。“苏格拉底:(自空中回答)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但,“一只壁虎打断了他一个伟大的思想。”
●埃斯库罗斯看了会沉默,欧里庇得斯看了会流泪/笑点和影射经过漫长的时间、跨越空间和文化隔阂、以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形式呈现,确实褪色不少,甚至有点晦涩,但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现场是多么火热,就像我们今天津津有味地听栋笃笑一样,译注帮助很大,努力还原了笑果!尊敬罗先生。
●除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这本,还看过张竹明先生翻译的版本,对比两者,罗念生先生翻译得更文雅,一些比较露骨色情的话被换了种表述,因为没有时间看洛布,所以我也不清楚谁的翻译更加写实。如果不是看过张竹明先生的,绝不会理解喜剧黄暴的特点,尤其是《吕西斯特拉特》,可惜罗念生先生没有翻译,无法看到两者的对比。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最富象征和联想的诗人,无出其右;他的喜剧是最高级的喜剧,现如今的荒诞或是象征喜剧都是对他拙劣的模范…《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地母节妇女》《蛙》全都非常棒,放在如今上演也是很好的作品,并且不仅仅是喜剧,不仅仅是为逗观众,还都有深刻的内涵,《阿卡奈人》渴望和平,《骑士》反对寡头政治,《云》嘲讽空谈主义,《马蜂》反思当时诉讼成风,《地母节妇女》讽刺当时妇女们的道德缺失,《蛙》可能是最早的比较文学论著吧…在他的作品里从没有对残疾人和地位低下者的模仿,也没有世俗的家长里短,矛头直指当时的达官贵人和文学泰斗,他崇尚自由民族,反对强权暴力,在他的戏里或许充满了火药味,但这可能也是当时社会最需要的一颗苦口良药…世纪文景错字怎么这么多,编辑审稿真不仔细…
●开篇必有屎尿屁,再加点“搞”来“搞”去。讽刺的同时不忘自嘲保命,诗人聪明的很。粗俗看得快无语时再秒严肃,严肃过头再退一步,对于诗人来讲可能玩乐才是一种生活态度。译本注解很多,解释了很多“梗”,这点很好。
●看的时候在内心爆笑不已,做个像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喜剧诗人真好啊,可以肆意玩弄嘲讽自己崇拜的或是蔑视的一切。
●目前就只看了《云》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读后感(一):无营养的读后感字数超出短评,
再次膜拜罗念生的翻译。 全书总体渐入佳境。蛙一剧确为极品。述论结合。同时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理解拉辛的一些作品。受益匪浅。 唯一让人感到不适应的是书的排版,注释全与正文分离放在后面,阅读起来非常不便,往出版商在日后的版本中能加以完善。 书摘:你这样在故作深沉的诗句里 和没有意义的对话中 浪费时间
真是再清楚不过的蠢行为。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读后感(二):《云》
《云》讲述了一个希腊土地主娶了个城里娇惯的贵族小姐,生了个爱花钱的儿子。儿子爱买豪车,欠了一屁股债。父亲想学习苏格拉底的诡辩术来抵债。学好了诡辩术,债到倒是抵了。父子发生口角,儿子打了父亲。儿子却用这种方式诡辩,他打父亲是正确的。 虽然几千年过去了,当今更是奉行个人利益,到处诡辩代替事实。我们不再思考事情本身,因为没有确定的“事实”。多元文化让我们理解每个人眼中的“事实”都不一样。于是无论怎样判断真善正邪和是非曲直的价值观都可以接受,只要可以成功。这对教育伤害最大,我们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儿童?
PS:书里描写的苏格拉底和真实的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人。面貌性格和所持的观点都不一样。据说,阿里斯托芬也认识苏格拉底,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黑苏格底。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读后感(三):《马蜂》《骑士》笔记
【马蜂】老父亲菲罗克勒翁身为陪审员对打官司非常狂热,他说「我乃是万人之主!」,而他儿子布得吕克勒翁则千方百计阻挠他,这个过程很欢乐。后来还专门开了一场审判狗的法庭,就很滑稽。退场的螃蟹舞放舞台上应该也是挺有喜剧效果的。这对父子俩的名字也值得注意,“克勒翁”是个政治煽动家反对同斯巴达人议和,父亲名字意为“喜爱克勒翁的人”,儿子名字意为“憎恨克勒翁的人”,所以这部喜剧也是带有讽刺意味在里面的。 【骑士】这篇依然是讽刺政治家克勒翁的。剧中克勒翁被喻为一个硝皮匠帕佛拉工,是德谟斯(代表雅典人民)的管家(激进民主派),经常各种贿赂诬告非常卑鄙。而在仆人们(指将军们)的安排下,一个出身平民的腊肠贩将去夺取其政权。中间腊肠贩和帕佛拉工对线互怼过程非常逗。而最终德谟斯意识到了帕佛拉工一直以来的欺骗,抛弃呆滞而逐渐清醒,在腊肠贩帮助下从一个丑老头变成美少年,成了希腊王当家做主。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读后感(四):从云端下降的哲人
《云》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作品。这部剧以苏格拉底为主角,通过塑造半真实半虚构的苏格拉底形象,表达了对城邦政治与家庭生活、哲人与普通人、哲学与实用技艺等多种矛盾关系的思考,并暗含了对哲人的警醒:哲学的正义不仅在于追求纯粹知识,更在于将这些知识在俗世百姓中传播。哲人是追求真理的圣人,也是携带火种的殉道者。
《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斯瑞西阿得斯是一位娶了阔绰城镇太太的贫民,为了赖儿子斐狄庇得斯欠下的债款而送他到苏格拉底那里学习诡辩术,最后债主的确被赶走了,儿子却也变得不敬长辈,甚至殴打父亲。在故事结尾,斯瑞西阿得斯一怒之下以“不敬神”的罪名烧掉了苏格拉底的房子。
斯瑞西阿得斯与苏格拉底之间的矛盾是推动故事发展并最终达到高潮的主要动力。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哲人与俗人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体现在思想层面。施特劳斯在《苏格拉底问题六讲》中提到,阿里斯托芬的剧作观众是“醉酒后率性而壮实的乡下汉子”,即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斯瑞西阿得斯正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们是务实的人,既不代表愚蠢或无知,也不代表善良或单纯,对知识或政治也有自己的见解,追求实用而非纯粹的知识。苏格拉底则是哲人的代表,他对知识有纯粹的追求,以至于完全忽视尘世的生活,甚至尘世的道德与正义。他在《云》中第一次出场时对斯瑞西阿得斯说:“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在空中行走,在鄙视太阳。”在云端的哲人眼中,知识与灵魂是最终的价值,而肉体与俗世的唯一意义就是被舍弃。
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什么?《云》中苏格拉底醉心于自然科学,甚至研究肚子放气这样的问题也不以为耻。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否定了对诸神的信仰,他却并不是无神论者,而将一切自然现象都归于自己信仰的“云神”。这说明,在苏格拉底的认知中,仍然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精神代表,以赋予自己的知识以价值。换言之,绝对的自然科学无法产生意义或价值,只有哲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实现正义。这是阿里斯托芬隐晦的批评:自然科学这样的“新知识”是不正义的,因为它颠覆了来自神话的伦理道德,剥夺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正义的探讨是哲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正义就是做正当的事,在《克力同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行为正当的方法就是遵守法律,导致他被判处死刑的并非是法律的不公正,而是人的不公正。因此,为了保证人们都做正当的事,就必须保证法律的正义,也就是必须保证立法者的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回答:只有正义的政体才能选出正义的立法者,即哲人王。要做到这一点,哲人就不能只居于云端之上远离俗世,而必须要下降到人间,将哲学的正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实现对普通人的教导。这样一来,哲学就被从天上带到了人间,其关注对象也从世界本质转移到了人本身,“政治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云》中苏格拉底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在第二场的结尾,斯瑞西阿得斯将儿子带到苏格拉底面前请求教授知识,为了证明斐狄庇得斯很聪明,他说儿子很小的时候就会“架房子、凿小船、造皮车”,但这些俗世的技艺恰恰是被苏格拉底所鄙夷的。因此他请出两种逻辑后自己就离开了。苏格拉底这种态度是当时许多哲人的写照:他们推翻了俗世中普通人的信仰,却不愿教授新的信仰、新的知识。《云》中苏格拉底将正义与不正义摆到斐狄庇得斯的面前,却不教授他变得正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正义获得胜利,反而害了他自己。吊诡的是,斯瑞西阿得斯本来找到苏格拉底就是为了学会不正义的知识,达到目的后却将随之而来的祸患怪罪到苏格拉底头上,甚至以“不敬神”的名义对他下达判决,类似的判决在几十年后的雅典法庭上再次上演。剧中的情节在公元前399年的审判中变成了现实,不得不说这是莫大的讽刺。
苏格拉底与斯瑞西阿得斯之间哲人与俗人的矛盾,还体现在身份层面。苏格拉底的哲人身份在城邦中格格不入,为其他人所不容。《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对人们控诉:“梅雷多为诗人出气,安虞多为工匠和政客报仇,吕贡为演说家翻案。”无论是诗人、工匠还是智术士,无论是民主派、寡头派还是僭主,苏格拉底不归属于他们任何一类。他们都各自代表了自己的利益,但哲人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正义,因此他们几乎注定了要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走向悲剧。苏格拉底的人生就是一出完美的悲剧,最后的死亡是这出悲剧的最高潮。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录,苏格拉底其实在进行法庭申辩以前就已经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了,“苏格拉底的用意只是要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既没有对神不虔敬,也没有对人不正义;他不但不想乞求免死,反而认为自己现在死去,正是时候。”他在《斐多篇》中也表达了对死亡的欣然接受,因为这代表了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获得永恒的幸福。事实上,这种观点反而更加体现了哲人的悲剧性:他们下降到俗世只是出于责任感与使命感而对现实进行的妥协,实际带给他们的是痛苦,这种俗世的痛苦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彻底消泯。
不过,规避政治、逃避城邦生活只是《云》中苏格拉底的态度,并不是现实中苏格拉底的态度。在《会饮篇》的结尾,阿尔希比亚德的陈述为我们勾勒出了苏格拉底对政治真正的态度:他热爱雅典,屡次作为重装步兵为雅典出战,并在对十将军的审判中作为主席唯一反对公开审判。真实的苏格拉底并不像《云》中那样鄙夷世俗政治,正相反,尽管看到了雅典民主的许多弊端,他依然对自己的城邦怀着最赤诚的爱。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政治的秩序是人类灵魂秩序的外化,政治体制不只是政治机关的组织及统治方式,更是人的生命态度与生活方式。那么,这似乎与《云》中的哲人形象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古希腊哲人积极参与政治,必然积极参与生活,也必然热爱生命,他们的生命又怎么会是悲剧性的呢?死亡又怎么会对他们有更高的价值呢?苏格拉底又怎么会在参加《申辩》前就寻死呢?
其实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因为,哲人的“寻死”不是真的热爱死亡,而是坦然面对死亡后对生命的确定感;哲人的“不参与政治”不是真的逃避政治活动,而是他们不会像政治家一样在世俗的、利益的层面参与政治,是在更高的正义层面参与政治;哲人的“悲剧”也并不是注定要遭受政治陷害,而是他们必然下降、必然接受世俗审判的命运。
死亡对于哲人意味着什么?政治对于哲人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不是绝对的肯定,也不是绝对的否定。如果说苏格拉底珍惜生命是因为他相信神赋予了他生命,那么在古希腊宗教被抛弃的现在,哲人就不会热爱生命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使哲人热爱生命的“神灵”并不必然是实体的神祇,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执着、一种对正义的使命感。苏格拉底选择人类,是耳边神的指引,更是由心中更高理念赋予的使命感所驱使。但是,哲人不是神,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即使苏格拉底也无法改变一个小小的雅典城邦;他明白,自己只是前仆后继投入历史长河的无数哲人中的一个,这是他命定的悲剧,但却是一种宏大的、伟大的悲剧。从此,哲人自云端下降。
两千年前,哲人在云端与俗世之间选择了后者;两千年后,哲人却为现代社会所不容。在《苏鲁支语录》中,苏鲁支自甘堕落人间,见到的是令人鄙夷的现代社会和安于奴隶道德的末人。尼采将人类比作超人与动物之间的绳索,他笔下的“超人”不再是哲人那样重视灵魂的圣人,而是重视肉体轻视灵魂的权力者、战斗者,这正是哲学没落的写照:尼采对世界宣布“上帝死了”,这句话也可以改作“哲人”死了,现代社会中智慧不得不让位于权力,正义也不得不让位于利益,旧时的哲学已逐渐走向落幕。在哲学的落幕中,大众眼里的哲学家也逐渐褪去了尊崇,真的被视作了《云》中那样滑稽的样子;而《云》本来批判的自然科学反而取代了哲学的价值,被普罗大众趋之若鹜。如今《云》以如此一种头脚倒置的方式成为了现实,令人不禁唏嘘。
如《理想国》中返回洞穴的先行者,哲人注定要从云端下降到俗世,他们也的确如此做了,这发生在两千余年以前的转折开启了人类文明崭新的一页,也将“正义”的理想永远地注入了哲学的灵魂,这种理想直到近现代,在对人权的追求中依然清晰可见。这也是《云》所表达的正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