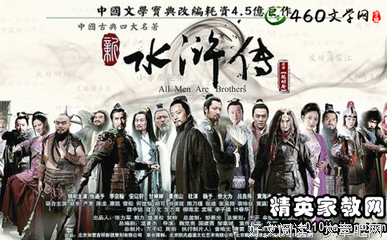
《Midnight in Peking》是一本由Paul French著作,Penguin USA (P)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GBP 16.28,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Midnight in Peking》精选点评:
●很神奇的故事,因为没看介绍直接开始看,刚开始以为是一部小说,没想到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故事的主人公很执着,而作者能寻到这么多细节复原历史也相当不容易。
●听完了,感觉不错。老北京,英国人,凶杀案。BBC Book of the Week。资源在此帖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321084/
●根据书里面提及的场景去寻找故事当年发生的地方,很有意思。
●融合了我最爱的两个元素:谋杀和 北京。在一个充满杀戮的年代,个体的死去还具有何种意义。
●有一群人衣着楚楚,地位尊崇,暗地里却是狩猎年轻女性的豺狼虎豹。这群人在1937年的北平存在,在如今仍然伺机蛰伏,不分国界,不论贫富。Keep sharp and watch out!
●心惊又心碎的故事。其实超级瘆人,一想到这一切就发生在二环的近现代...发誓再也不读这类题材了。
●So far the book has been entertaining
●另外的角度看老北京及那段历史很有意思,女孩的父亲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好看
●【藏书阁】陈年的旧作,居然成为今年的热点之一,在友邻们的推荐下扒到了原版,然而拿起放下,又拿起又放下,一个月也没有读完,最后只花了一个冬日的午后,在有着明媚阳光的咖啡馆里一气读了四个小时而完结!外国鬼子笔下的旧日北平,本来就稀有,再加上妙龄白种少女被谋杀的噱头,作为岁末的收山之作,确实再合适也不过。从冰山中一角,作者慢慢地给我们看到了洋人圈子里地下的隐密世界,最受人尊敬的牙医,原来做着诱骗良家少女的勾当,而租界侦捕们的效率低下,直接导致陈冤不得雪,最后在日本子侵华的大事件下不了了之,只可怜了伊的老父,却继续执着地调查下去,而结果只能给了我们一个不能结案的谜底。
《Midnight in Peking》读后感(一):1937年的京城洋味儿
一口气读完了还处于pre-launch阶段的Midnight in Peking,整体感觉不错,有点民国末期兵荒马乱的那个感觉。
书的主题讲的跟兵荒马乱差点有点远。故事的主人公是个退休外交官的养女Pamela,涉世未深突然被发现暴尸街头。住在今天的东郊民巷、当时的外国使馆里的人们本已为近在卢沟桥的日本军队担忧不已,又因该起谋杀残忍程度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中英两国警探/侦探联手侦查,而最后案子竟然还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解开的。
该书有趣之处在于Paul French真的很用心地查找了不少资料。作为对历史只有粗浅了解的国人,我感觉书里对于那个年代的描写还算准确。字里行间也能氤氲出1937年的京城味儿。
跟Jo聊天的时候得知,当年Pamela下葬的英国公墓就在今天的京广桥。每天来回两次,刺激。
《Midnight in Peking》读后感(二):《午夜北京》让我真切地生活在北京
这是今年完成的第二本原著 《Midnight in Peking》,午夜北京。讲的是1937年1月7日在北京发生的一桩真实的案件,原英国外交官也是一个汉学家的唯一领养女儿被杀,尸体被残忍肢解,内脏被掏空,弃尸东便门箭楼(原来叫FOX Tower)的事情,这桩谋杀案的惨绝人寰的程度令人发指,当时轰动中外。而且案件本可以告破,但是因为当时时局复杂却不了了之,直到本书的作者Paul French在近80年后告真相于天下。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离我上班不远的地方的所有地名景物都鲜活起来。比如说公交车每天都经过的明城墙遗址(Tartar Wall),东便门箭楼(Fox Tower)盔甲厂胡同,船板胡同,东交民巷,读过这本书才感觉我们生活的北京对于我来说不再是虚飘的地名的组合,而是感觉你是活生生的生活在一个你能洞见历史的而又熟悉的环境中。
有时我认为我们和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成介于旅游和扎根之间的一种状态。旅游,你只是浮光掠影的看,你并不属于那儿,也并不真切了解那儿。而在某个城市生活你只是从生活的实用原则上与这个城市发生关联,比如说哪儿有消遣的,哪儿有购物的,哪儿有好吃的。
而当你读过这本书,对你生活的城市的北京有了更多的认知,让你更真切的感受到你是生活在这座蕴含着沉重历史又鲜活的城市里,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的感觉。
《Midnight in Peking》读后感(三):关于此书的一些杂感(有剧透,慎入)
其实后来想想也觉得有意思,四个多月前,我第一次玩译言,论坛ID用的是我豆瓣ID的英文版,也就是EthanLau,我翻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经济学人上关于Midnight in Peking的书评。说来也不怕诸君笑话,那篇文章基本上是无人问津,只叹自己才疏学浅,功力还不到家吧,总之我的翻译处女作就是这样灰头土脸地诞生了。
但有一点绝对是大实话,那就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篇书评时,我就下定了决心要弄到这本书来看,而当我翻译完整篇文章时,我想,此书我是非看不可了。
通过这篇书评,我对这本书内容的大概也基本上摸了个透彻,故事的主线贯穿整个了中国最为动乱不堪,民不聊生的数十年,然而我很佩服Paul French的一点就是,他竟然可以将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用一种扑朔迷离,朦胧梦幻的奇幻主义色彩的手法表现出来,这不仅没有淡化现实之严峻,反而更增添了一抹悲凉,冰与火交织般的史诗感。
作为一个新闻传媒的寻路人,我从心底里由衷地赞赏作者治学严谨的写作风格和亲身投入实践精神。书的最后几章曾写到,受害人Pamela之父Werner先生由于警方以及英国大使馆方面在侦破此案的行动中互相推诿,乃至某些官方人员还受贿而隐瞒犯罪事实而导致此案不了了之的原因,Werner亲自潜入老北京的底层社会,A.K.A书中屡次提到的underworld,广派人手,搜集证据,最终完全推翻了警方之前基本上是胡谄出来的案情总结,可历史的悲剧性总是和个体的悲剧性交织在一起,Werner整理出来的一大箱关于此案真实来龙去脉的文件资料在被寄回英国后,竟然因为种种原因,根本就没有被人注意过。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作者Paul French在某次阅读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闪耀中国时偶然发现了Pamela一案,他当即决定要为此案进行一些创作,哪想到,在查阅文献时竟发现了当年Werner留下的那些资料,他通过对与案件相关的实地走访调查,以及大量地采访与研究,终于完成了Midnight in Peking一书的写作,按他自己的原话说,他在创作过程中的动力来源,不过就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尽管这个公道,迟来了七十年。
兵慌马乱,战事连绵,八百里白骨遍地,四海内饿殍飘摇。在那个年代,无论谁的命运,都是和动乱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人可以完全遗世独立,众生与我有何干。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不论这个时代有多么险恶,不论人心有多么冷漠甚至恶毒,我们也要像南周的新年献词中所说的一样"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至少我在书中看到的,不论政府当局有多么冷漠无情,不论恶人们有多么衣冠禽兽,但至少,真,善,美在这世上,是永远存在的,它有可能在冠冕堂欢的大殿里,也有可能在简陋的小巷里,它有可能在庄严的厅堂里,也有可能在昏暗的小酒馆里。
我一直都相信,不论是书中的那个时代,还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都是一个黑暗与光辉并存的时代。
正如书中扉页上所题写的那句话一样,"The belief in a supernatural source of evils is not necessary,men alone are quite capable of every wickedness."
《Midnight in Peking》读后感(四):高欢评《午夜北平》︱不要在午夜问路,怕走到城墙暗处
东南角楼之夜色
文︱高 欢
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03/18/2019
北京的美轮美奂与杂乱无章、时髦与土气、历史与现代往往都近在咫尺,让人在二环内暴走时,时而惊艳时而叹气。如今我已这般熟悉这个城市,每当在电影和书里辨认出地标时,就有奇妙感受。
比如说,《邪不压正》电影中提到的白人少女帕梅拉凶杀案,尸体发现地就在我夜跑目的地东南角楼下,我常在那边树下拉伸做俯卧撑。电影中,兰青峰与李天然的养父亨德勒医生在明城墙上发生争执,并将他扔了下去。这城墙旁的小径也是我跑步的路线。所以,只要张开想象的翅膀,夜跑就变得越来越刺激。
电影中暗示亨德勒医生就是凶手,但在历史中的原型并非同样的下场。
2011年出版的Midnight in Peking (《午夜北平》)根据历史上真实案件所写,归类为非虚构写作。作者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 最初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注解里读到这桩奇案:死者的家和斯诺夫妇的家非常近,斯诺夫人海伦为此感到十分紧张。之后,弗伦奇就查阅当时的报纸、北京上海香港伦敦的档案,以求获得真相。为了调查,除了北京之外,他还去了相关人物涉足的上海法租界和天津寄宿学校。虽然北京内城已拆了许多,相关地点大多还在,于是他还设计了一个语音导览,看完小说,可去实地考察一番,想象或缅怀,相当有意思。
谋杀案的各种元素都很吸引眼球: 经历丰富为人古怪的父亲、城墙边夜里活动的狐仙、酒吧妓院和西山天体营、“下等”外国人的混乱和犯罪、故意妨碍调查的英国外交官、未能伸张的正义,乃至困境中仇人的狭路相逢。
193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遛鸟老人在东南角楼下发现了退休英国外交官维尔纳(E.T.C. Werner)的养女帕梅拉(Pamela Werner)的尸体。她的血几乎已经流干,人也被砍得面目全非。因传说有狐狸精出没,角楼曾有狐狸塔的称号。不过,那个清晨,只有野狗围绕帕梅拉身边。
尸检是在三公里外的协和医院做的:她死于头部钝器袭击,包括心脏在内的内脏都被干净利落地取走,留下的仅有胃。应该只有医生或猎人才有这样的技术,野狗吃人决不能这般齐整。她下身被捣毁,一般的性虐狂大概也下不了这样的重手。钻石手表还在,说明杀人目的不是抢劫。细节太血腥可怕,警察将其保密,但后来消息还是泄露见了报……
夏天某个闷热的星期日,我也骑着共享单车,将书中说到的地点走了一遍,下图中10到12是我添加的。
《午夜北平》导览地图
帕梅拉,住在盔甲厂胡同(2),离交通繁忙的北京站(1)不远,拐来拐去,忽然就到了。书中说他家是1号,但由于胡同门牌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重排,现在的1号不是当年的1号,我在胡同里走了九遍,以寻找蛛丝马迹。既然说她家的大宅已被拆成三家,那么那个最气派的大门也许就是她家的,其余的门都像是破墙打洞的违章搭建。
今天的盔甲厂胡同 (2)
可能是帕梅拉家的大门 (2)
胡同另一头,有个中安宾馆,墙上有巨大标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写作地旧址。是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曾经住在这里,书中说他家是个有好几进的四合院,还有山东大汉保镖。他们生活豪华,常常举办派对。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再,盖起了楼房。宾馆大堂里陈列着老照片,电视机里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作为最先访问陕北并积极报道的西方记者,他们声名在外。电视里说,他们事业发展差异太大,终于在1949年离了婚(但是谁又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盔甲厂胡同里,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1935-1937 年住所旧址 (2)
海伦·斯诺曾怀疑,戴笠为了阻挠他们的报道和出版,想要暗杀她,只是手下杀错了人,于是邻居家的帕梅拉遇了害,她们长得还真有点像。但是军统局下手一般都是手脚麻利,一枪毙命,帕梅拉却不是这种死法。
海伦·斯诺;帕梅拉·维尔纳
盔甲厂胡同的另一头有个小旅馆门口,种着恣意的花,由此往东折向泡子河东巷走一会儿,豁然开朗,面前是草坪树木:这一高于二环路的绿地也是明城墙遗址公园的一部分,拾阶而下往南,就能看到高大的东南角楼。也就是说,死者的家距其被发现之地走路不超过十分钟。
东南角楼(3)于明朝初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上去参观,看看关于北京城的展览,还可以俯瞰北侧的北京站,绿皮火车来来往往,相当文艺。如今角楼下有老槐树,洁白的玉簪花吐露芳香。可是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一块废地和大运河的遗存水沟;十九世纪的清代,外国人的坟地也在附近,野狗出没,所以这真是一个午夜抛尸的理想地点。
二环路旁的东南角楼(3)
上城墙,看东南角楼(3)
东南角楼下的玉簪花 (3)
沿着与之相连的明城墙(4)往东漫步,会经过以前的京奉铁路信号所和一小段枕木,春有各色梅花绽放、冬有落尽叶子的树枝装点清冷天空。这段城墙在书中被称为the Tartar Wall (鞑靼城墙),将北京的内外城分割开来。清代北京的内城,主要住着旗人,所以英国人将内城叫做the Tartar City(鞑靼城),南边的外城主要是汉人住,叫做the Chinese City(汉人城)。城墙上可以走人可以骑车,眺望城内城外不同风光,令人向往。
春天里美貌的明城墙遗址公园(4)
北京的城墙经历了各种毁损,这也是仅有的几段遗存:1916年先有个环城京师铁路,把城墙打了个大洞,该洞现在是上角楼的收费处大门。民国期间,北京的城楼又被拆了若干,城墙上也新开城门,以疏导交通。1949年之后再是大规模的拆除。比起角楼墙上八国联军留下的刻字,这破坏力可是大多了。
二十世纪初为了修铁路在城墙上打的洞,现在是上角楼的收费处大门,人们在此跳广场舞 (3)(4)
明城墙公园走到西边尽头,北侧马路对面有后沟胡同。走进去,会先经过亚斯立堂(Asbury Church),它是被义和团焚毁后1904年重建的。圆形的礼拜堂有深色木制天花板,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来,温馨可爱。这座基督教堂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亚斯立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之相交的船板胡同,在书中叫the Badlands (5),或许该译作“坏坏之地”?这里最初是一片空地,外国兵在此操练打马球,一战以后才渐渐造起房子,理论上是中国辖区,事实上是三不管地区,所以,“下等”的外国人 —— 主要是从苏联逃出的俄国白人、德国中欧逃出的犹太人、各国逃兵 ——聚集于此,廉价旅馆、酒吧、赌场、妓院林立,街上都是皮条客和姑娘。作者认为,帕梅拉就是被凶手及若干男伴骗到这里杀害的。她才十九岁,有些叛逆,对成人世界有些兴奋好奇,以为自己去的是节日派对,结果是个妓院,不从之后发生争执,被杀,血流干、脏器去除后,再被人用车拉到角楼下抛弃,这段路不到两公里。
船板胡同28号据说就是凶杀现场,然而现在就是一堵墙和门窗,正对着东交民巷小学的后门。如果胡同门牌号都有重排,那也未必就是这里。如今胡同里只有普通人家和小旅馆,住店客人很有可能是旁边同仁医院外地病人的家属。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看不出这里曾是个红灯区。
所以,物理消除真是一种抹去记忆的好方法。
船板胡同28号,可能的凶杀现场(5)
与船板胡同呈三十度角的还有一条苏州胡同(6),我倒是第一次去。书中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还有算命杂耍、代写书信的,属于典型的红灯区旁配套商业设施。这也是帕梅拉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并在此吃了生前最后一顿饭。正当我叹息现在这里没啥看头时,迎面走来一人,头上顶着一碗方便面。他走到我身后,我转身偷拍了他的背影。一旁警车里的警察笑着对我说:“发网上去?”
苏州胡同头顶方便面之人(6)
出了苏州胡同,大街对面是东单公园(10),据说这里是帝都著名的男同性恋聚集地。一进门就是假山,插着牌子“禁止此处小便”。为人民服务的雕塑旁,人们跳着广场舞。小山脚下有个露天理发摊儿,顺着小路我就上了山,看到了凉亭和沿途散坐着的人们。打扰完毕,我出公园,去高大上的东交民巷走一遭。
东单公园(10)
东交民巷以前是使馆区,进去需要验证身份。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外国人都躲到这里避难。此地的西式建筑大多是全国重点文物,不过很多仍是政府机关,在围墙大门后,不太看得到。能去的有警察博物馆和法院博物馆,分别是以前的花旗银行和日本正金银行大楼,值得一逛。
东交民巷的法院博物馆,以前的日本正金银行大楼
东交民巷前法国邮政局
法国教堂圣弥额尔堂(Church of St. Michael)旁是前法国使馆(7),门口有大石狮,门内有假山。西哈努克亲王在世时长期住这儿。帕梅拉被害前曾在里面的滑冰场玩耍,之后骑车回家就失踪了。这里离凶杀现场船板胡同只有一公里。
前法国使馆(7)
作者推断的凶手是美国牙医普伦蒂斯(Prentice),就住附近,在大冬天莫名其妙刷了墙,不知为什么,窗门也大开着。他对警察说不认识帕梅拉,然而却有给她看牙的记录……从帕梅拉日记里也能看出,她也去过普伦蒂斯组织的西山天体营——就是大家都不穿衣服的派对(《邪不压正》里也提了一句)。那个时代就这么开放,真有点重口味。
附近还有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Lits) 旧址(11),北京旧时最洋气最高级的饭店,各国使者及北京的上流人士在此住宿、餐饮、交际、娱乐。在没有手机联络的时代,帕梅拉貌似也在前台收取了一张别人留给她的纸条。该饭店是历史上一些著名事件的发生地,只可惜1988年一场火灾将其烧毁,重建的宾馆就再无看点。
正义路上的公安部是当年的英国领事馆(8),可以远远地在入口瞄一眼。帕梅拉的中国通父亲维尔纳是个英国外交官,脾气古怪,和上司、同事的关系很差,一直被派去各种不怎么样的地方任职,退休后就回北京继续他的中国研究。他的养女被杀,是个轰动的涉外案件,由天津过来的苏格兰场探长和中国探长共同调查,可是总碰到各种无用乃至误导的线索,让人意识到水很深,阻力很大,不能影响大英帝国的脸面。维尔纳最初就是在英国领事馆从中文翻译做起,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多年以后,他又在这里参加了养女的案件审讯,草草收场,说凶手是个未知的中国人。
这位老父亲不甘心,花费重金自己侦查,并如同信访群众一样不停申诉,要求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帕梅拉于1937年1月被害,到了7月就是卢沟桥事变,北京到处人心惶惶,外国人、中国人,能走的都走了,谁还来管这个。
然而他的申诉,包括一百五十页的长信,都留在了英国的国家档案馆中,再无人理会,直到多年后保罗·弗伦奇 读《红星照耀中国》后想起来做调查。《午夜北平》重构了这一案件,并生动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风貌。
再往西就是前门23号前美国大使馆(9),当初他们倒还给了维尔纳一些相关线索。大门在前门东大街上,大院里现有餐厅、高级表店和爵士乐场。马路对面有漂亮的铁道博物馆(12),也是当年的正阳门火车站。以前所有到北京的旅客都在此出站,抬头看见美丽壮观的正阳门,大概都会对帝都心生敬畏。1937年,那位耿直的探长从天津初到北平,他还不知道即将接手的是怎样一桩必须不了了之的案子呢。
正阳门老火车站漂亮的钟楼 (12)
作者在书中基本认同维尔纳的调查结果,然而牙医普伦蒂斯的后人表示反对,设立了网站对维尔纳本人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一些反证。1943年日本人将滞留北京的外国人送往山东的集中营,维尔纳和普伦蒂斯还在那里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该是多么尴尬紧张的时刻。
然而,这还是一桩悬案。如果帕梅拉还活着,正好一百零一岁,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只是她死于非常时期,正义到现在也没能伸张。
1936年有个驻华美国军官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出版了一张《北平历史地图》(A Map and History of Peiping),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地标和风俗,非常好玩。鉴于帕梅拉是1937年1月被杀,这张地图应该也是比较忠实地展现了她所处的环境,以下地图局部就是本案相关地域范围。
《1936年老北京风俗地图》(学苑出版社2010年重印)局部
作为一个熟悉北京对它又爱又恨的上海人,在我时不时发牢骚吐槽北京各种不便的同时,又每每被其深藏的历史、美丽的古建公园和有趣的地名深深吸引。不知不觉在这里也呆了好几年,真是吓一跳。作为一个过客,我比当地人更彻底地扫荡北京的大街小巷,说起来如数家珍。读完《午夜北平》,看看老地图,再进行一次理论结合实践的骑行漫步,帝都的风景或面目全非或风情依旧,真让人感叹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还可以看看以前写的:
英雄不必完美 死而无憾就好
高欢︱那些选特朗普当总统的美国乡下人
欢迎关注毛羊言欢,长按二维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