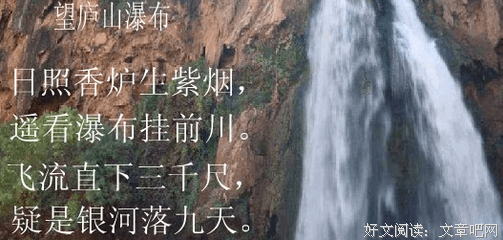
《Statesmen and Gentlemen》是一本由Robert Hymes著作,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69.95,页数:3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Statesmen and Gentlemen》精选点评:
●A localist approach
●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可能科举相关部分稍微有些不赞同(比较偏向黄老师的科举社会)。总体来说确实奠定了一个方向吧。现在做地方还是要看作者分出来的七大类人,真的很厉害。
●很难读
●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向韩明士屈尊
●不得不讀之導師的書
●治社会史者当如是~
●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宋代帝国精英自我再生的模式与他们的社会网络如何从侧重中央资源变成了侧重地方资源。书里讲的localist turn应该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背景中来理解。
●hymes成名作。大學時候讀過,為了論文再看一遍。與當初印象無異。可見我對local community studies無愛其來有自。整個argument建基在對cracke的批評之上。然而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要之亦不免以偏概全之病也。
●其实很多国内包括台湾的大佬们,对韩明士的批评之所以难看,就在于他们说不出口的一句话:韩明士有道理,但,不完整。——韩在学术史上承担一个最重要的点就在于,家族不一定非要做官,它可以像公司一样通过族产投资分成来维系同居关系,在社会竞争中保全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不是都像买彩票一样去培养进士——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统治很松动(大佬们批判完之后就会把结论摆回到“统治依然很完整”这个更愚蠢的点上)如果一个统治完美无缺,那怎么会出现农民起义?即使到后来明清最强大的时期,依然没有停止过农民起义,某国的五六十年代都出现了农民起义,难道说这些时期都是统治松动的时期么?韩的不完整性是任何作品都会存在的,但他的学术史意义实在是让后来者受惠良多。
●很有见地,硕士论文准备写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出中译版啊!!
《Statesmen and Gentlemen》读后感(一):可行性報告
宋史研究能否像明清史研究那樣進入地方史的層面?robert hymes這本書很好地囬答了這個問題:不僅可能,而且可以很漂亮。這就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與意義。
怎樣進入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在該地紛繁蕪雜的史料載記裡摸爬滾打,並且看出端倪?這本書給出了一些章法:關注科舉、家族淵源、婚姻、宗教、地方公益事業及羣眾性公共項目等等,這些正是突入該地域,研究精英階層的突破口。牠也告訴我們研究非精英階層也是研究的一個方面,可是可行性太低。
hymes同學對史料的搜尋用力極深,其勤奮讓人歎服。然而在論述過程中還是讓人覺得史料單薄,可以想見研究難度之大。
前不久我還跟helen同學說起hymes,說他對於現有材料挖掘能力很強,而且即使沒有見解也能言語滔滔。這本書也集中體現了這一點。即使說一些沒有太大把握的話,hymes同學也能說得周全。而在一些斬釘截鐵的話後面,他又提醒讀者過猶不及。說話滴水不漏,這是hymes同學的行文風格,也是他的思維特點。
包偉民同學在唐研究第十一卷上有一篇該書書評,發言極精彩,看過這本書的朋友一定記得再去看看那篇書評。
書中論點或可商榷,但是這本書告訴人們研究宋朝地方史不但可能而且前景光明,這纔是本書價值核心所在。
《Statesmen and Gentlemen》读后感(二):地方精英研究方法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xv, 379.
Through his investigation of Fu-chou from the Northern to Southern Sung dynasties, Hymes demonstrates the continuity of elite and their separation from state. He believes there are two transitions: of T’ang-Sung and of Northern-Southern Sung.
y constructing local elite genealogy, Hymes studies how these elite families behaved in examination, office, migration, marriage, defense, social welfare, and religious life. He tries to discover their behavioural patterns and reasons behind.
Hymes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local history study in medieval China.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is book. He also shows how to approach a local elite community.
Chinese shih does not correspond perfectly to Hymes’s elite. Also his construction of elite genealogy includes a too wide range of family members and generations, which helps to form his ‘continuity of elite’ belief. Third, although warning us of local uniqueness, he does not stop applying his discovery in Fu-chou to the state of Sung. Last, his pi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state is too simplified, which is refuted by later studies, e.g., Huang Kuan-chung’s study on local military forces in Southern Sung.
Further reading:
kinner, G. William.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 Regional Analysis. Ed. Carol A. Smi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vol. 1, pp. 327-64.
Lo, Winston W. “Circuits and Circuit Intendants in th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f Su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31, (1974-75), pp. 39-107.
ao, Weimin. Songdai difang caizhe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1.
Chaffee, John.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Society (960-1279).”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62.
Hartwell, Robert.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1982), pp. 365-442.
《Statesmen and Gentlemen》读后感(三):“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鲁西奇)
2006年第5期——“小”国家VS“大”地方
中国图书评论 2006-08-11 10:24:29 阅读 次
【主题书评】
【主持人语】 以考察“小国”的方式考察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容易把自秦到民国的中国描述为“中央集权国家”,仿佛每个国民都受制于国家。但从社会史看,国家权力到县就几乎停住了(县为最低一级政府),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及庞大人口(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绝大部分)实由地方乡绅集团、宗族、乡规民约等中介管理,具有高度自治性。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乡镇自治体是惟一真实的政府。 低产值的农业和低赋税的政策,使国家财政无力供养过多官员,也无法让有限的官员承担全面有效管理,而地方自治体起到了地方管理功能,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成本。乡绅并非无知无识之人。既然仕进机会有限,那么,在历次科举考试中落第的大量士人仍留在原籍(卸任官员也大多返回原籍),构成地方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为各地保留了人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分散于各地,而非涌向几个中心城市,有利于各地的均恒发展。 政府若直接管理国土庞大、人口众多、各地情况迥异的一个国家,就必须把部门齐全的行政机构一直设立到村,这不仅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造成巨大财政负担,且摧毁了地方独特性(传统、地方组织、语言、习俗等),管不好不说,还破坏了各地社会生态,而且管理的成本也太高了。 程 巍
“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 □鲁西奇
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Robert Hy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一 或许是因为王安石和汤显祖的缘故,抚州的名声,似乎远没有临川大———很多人知道王安石与汤显祖是临川人,却很少有人会把他们与抚州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王安石之被称为“王临川”的“临川”,是指临川郡,亦即抚州,并非指临川县。宋代的抚州临川郡治临川县(即今抚州市临川区),领临川、崇仁、宜黄、金溪四县(南宋分崇仁置乐安县,故领五县),大致包括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及崇仁、宜黄、金溪、乐安、东乡诸县地。
抚州自古即不处交通要道之上,而田畴良美,物产丰富。曾巩《拟岘台记》谓:“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蛑之菑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可谓礼乐之乡。而“其俗风流儒雅,乐《诗》、《书》而好文词”,故其“人物盛多”,“冠冕一路”,号称多士。北宋时代,抚州所出的著名人物,除王安石外,还有晏殊、王安国(安石弟)、谢逸、邓考甫、聂昌、欧阳澈诸氏。其中,不仅王安石、晏殊位至宰执,居庙堂之上,得纵论国是,决断朝纲;聂昌、欧阳澈亦以忠君爱国自许,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或以书生而历戎行(聂昌),或伏阙请愿而见杀(欧阳澈),均以一腔热血,竭忠尽智,报效朝廷;即便是王安国、邓考甫辈,也都志在千里,心怀家国,临事不苟,而不以一己一家为念。
然至南宋,抚州士风却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论南宋抚州人才,自以金溪陆氏兄弟为最。陆九渊及其四兄九韶、五兄九龄都是著名的思想家,尤其九渊以所谓“心学”成就为一代宗师,得与理学大师朱熹相比肩。陆氏兄弟虽均步入仕途,然或为时甚短,或久居下僚,位不过知军之类的地方小官,距离庙堂国是乃有千里之遥。这虽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陆氏既强调“发明本心”,“保吾心之良”,自然在主观上无意于仕途之进取。不仅如此,陆氏的行为取向在南宋,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至少在抚州,更多的士人留在了自己的家乡,经营家族或地方事务,而不是奔向王朝的政治中心,想方设法报效国家。 正是从这里出发,韩明士(Robert Hymes)观察到:两宋时期,士的志向与心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北宋的士大多怀有报效朝廷、忠君报国的志向,因而力图出仕中央、甚至不惜为此脱离故乡的话,那么,到了南宋,虽然并不排除仍有不少士子胸怀跻身庙堂之志,但更多的士子则把扎根地方作为自己的首要取向。韩明士说:
在南宋,“地方性”具备了新的意义:精英们不再关注国家的权力中心,也不再追求高官显爵,而把注意力转向巩固他们在故乡的基础方面,于是,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出现了一种精英“地方主义”……无论是婚姻圈、居住方式、捐献方式,还是“留在家乡”的策略———这使得南宋的家庭与北宋的移民形成巨大反差———都表现出立足于当地的倾向。[1]
这就是所谓“士的地方化”。它主要有三方面的涵义:
首先是士绅阶层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用包弼德(Peter K. Bol)的话说:“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却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这些家族输送了官僚和科举考试的应试者。”[2]虽然读书—赴考—出仕仍是这些家族成员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但学识只是他们需要关心的诸多事项中的一个方面,“士掌握学识只是为其彼此的身份认同提供部分依据”;而官位也不再是确定其士大夫身份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当官,而且事实上,这些家族的确也只是偶尔产生一些官员。但他们必须是地方社会的领袖,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对地方学校、书院投资,控制入学的机会;带头修建和布施当地佛寺、道观以及地方性庙宇,组织、领导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及其他地方公共工程的兴修与维护;他们参与、有时领导着私人组建的地方自卫武装,在征税和组织劳役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在赈济饥荒等地方公益事业中作主要的贡献;运用习惯法和协商手段解决地方社会内部(家族内部、家族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争端。[3]这里关键的变化在于:士绅不再必须做官,或者以做官为指归。也就是说,做官或准备做官不再是进入士绅阶层的必备条件。当然,读书还是必备前提,但读到怎样程度、具备怎样的学识却并无一定之规。这使得“士绅阶层”的边界趋向于模糊化,其范围也大幅度扩大:比如,粗通文墨而热心地方公益的乡村土豪和商人就可能因此而被纳入“士绅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士的地方化”不仅意味着士绅阶层的扩展,更重要的乃在于它实际上已成为“地方精英”的同义词。换言之,士不再仅仅是国家(朝廷)的官僚和候选官僚,而主要是地方社会的“精英分子”。
其次是士绅阶层与国家的疏离,或者说是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of elite from state,包伟民教授在《唐研究》第11辑上发表的书评将之译为“与国家分道扬镳”)。士者,仕也;士大夫既要入仕为官,或以入仕为指归,自然需要附丽于国家(实际上是王朝)之上。而按照韩明士的说法,南宋时期的士绅阶层不再必须做官或以做官为追求目标,自然而然地就与国家(南宋王朝)产生了某些疏离感———这种疏离在北宋时既已出现端倪,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展。韩明士说:
我使用“separation”这个词正是为了强调这是一种正在变化中的进程,而并非已形成定局。显然,南宋时期的诸多变化———精英策略的转变以及国家权力的相对衰弱———都促使地方层面上精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与明朗化,巩固并强化了精英身份与社会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不再仰赖于国家的承认与证明,从而逐渐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当然,这种独立性并非全然是新生因素。一方面,人们开始使用拥有的财富、权势与威望作为标准来界定精英阶层;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包括了那些通过朋友、亲戚和其他组织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员。即便是在北宋,士大夫阶层也并不等同于官僚阶层或拥有功名的阶层。到了南宋,已经非常清楚,精英的身份是由他们自己界定的,从而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4]
这里的关键是:士大夫(或精英)的身份不再需要国家(朝廷)的给予、承认或法律证明,而是由他们自身界定的,换言之,“士”(或精英)是那些被地方社会所有其他的士(精英)承认为士(精英)的人。士(精英)不再是一个从国家法律上界定的群体,而是一个从社会角度界定的群体。这样,地方社会(它又是由士绅阶层所掌控的)就取代国家(朝廷),成为界定士绅(精英)阶层的主体。
士的身份界定既然来自地方社会而非国家(朝廷),那么,士绅阶层的行为取向自然也就由以国家(朝廷)为指归转向以地方社会为指归。这就产生了“士的地方化”的第三层涵义,即士绅家族的经营策略从全国转向地方,呈现出“地方主义”倾向。在本书第三章中,韩明士花了较大篇幅,描述了抚州精英在北宋与南宋不同的婚姻模式:北宋抚州精英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素有声望的家族缔结婚姻,至少也要考虑对方是否为品官之家;而南宋抚州精英的婚姻圈则基本限于本县,想法设法与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族联姻,而不太计较其是否为品官之家。这种婚姻模式的变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士绅经营策略的方向性变化,而勿论他们的政治追求已由庙堂之上的国家(朝廷)政治和中央权力转向本县本乡的权势制衡与角逐了。
由此,韩明士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将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他认为:应当把唐宋变革视为“双重变奏”,即紧随着士绅阶层构成人员的变化之后,士绅(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与经营策略也发生了转变。士绅阶层的平民化主要发生在唐宋之际,其标志是世家大族的衰落;而后一个转折则“区分了南北宋,主要是精英的经营策略从全国转向了地方”。“这不是一幅平民崛起的社会画面,而是关于一个精英阶层的描述,这个阶层基于地方,组成这一阶层的家族在想办法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流动中中落,这种中落来自不能代代为官、以及祖业被分割的压力。”[5]姑且不论抚州精英的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也不论抚州精英的这些变化在怎样的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凡此,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实证研究),仅就对“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拓展以及突破王朝体系的社会发展观而言,韩明士揭示了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一个侧面:士绅阶层走向“平民化”之后,又进一步走向了“地方化”。这种演变,至少作为一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
二 “士的地方化”理论(或假说,或阐释模式)并非韩明士所首创。他在本书绪论部分即坦承,他的研究乃是对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关于帝制中国中后期(宋元明时期)社会转型理论的一种实证与深化。郝若贝在他著名的长文《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革:750-1550》中论述说:自晚唐至北宋时期,人口与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完全可以形容为一次“人口爆炸”和“经济革命”,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对全国范围的政治社会结构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其中在政治控制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迫使中央政府“下放”权威,具体表现在“路”的出现和“县”的独立性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即使不是倒退,也趋于停滞了。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的职业官僚阶层日趋没落,被地方性士绅家族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帝制中国中晚期专制政府权力衰退论。这一理论,在韩明士与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主编的论文集《燮理天下:走近宋代的国家与社会》(1993)之绪论中,有更清晰的表述;而包弼德在《唐宋转型的反思》一文中则作了简要概述,即:相对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一般认为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超过了1亿)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小了———与唐朝政府在土地控制、劳动力与贸易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宋朝政府的权力变弱了,变成了一个“相对小的国家”。“国家小”了,就给“地方的扩大”留下了空间;反过来说,地方精英的存在,也是“小国家”之成为可能的前提。“从长远看,中央政府不能取消地方精英所处的中介立场,他们处在从事生产的平民和地方上中央任命的权威之间。在南宋,要臣(leading officials)鼓励地方的士人(即精英分子)成为负责地方社区之社会与道德状况的领袖。地方的精英家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政务非正式的参与合法化,他们篡夺了地方政府的特权,或填补了有为的政府在退缩后留下的空间。”而在本书中,韩明士专辟一章(第八章),集中讨论南宋抚州地方政府权威衰落的具体表现,认为正是由于“国家在地方事务中的退缩,才给那些地方富豪或者说地方社会的领袖们打开了一个可供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并给他们扩展自己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机会。”[6]
这是“士的地方化”的第一个原因,也是其前提条件和客观背景。相比之下,第二个原因则主要是出于士绅阶层的主动。如所周知,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学校教育的日益普及(特别是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在宋代,受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其直接结果是: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即便取得了功名)都有做官的机会。显然,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也是迫使士大夫们留在地方、转向地方事务的原因之一。而从士绅家族的角度来说,选官制度的变革使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再能保证世代为官,而家族人口不断膨胀,又使得他们维持其财产的能力一直在削弱。然则,在这种家族不能以仕宦为业的社会里,如何保全其家族的地位、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不致中落,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显然,一个家族良好的经济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促使士绅家族着意于经营“家产”,而最为稳妥的经济利益当然是在家乡,特别是家乡的土地。家族成员既集中居住在家乡,家族经济利益也集中在家乡,而家族财产之多少更关系到他们在乡里的地位,士绅家族经营策略的重心理所当然地是在家乡了。因此,“一个家族应该教育他的成员,努力保持和睦,与地方官和其他要人保持良好而端庄的关系,仔细管理家族财产、不动产、佃户和奴仆。”[7]而对于那些经济上没有依靠、“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的“士”来说,“取科第,致富贵”固然是上上之选,但其成功之希望既属渺茫,则或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或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或习句读、为童蒙之师,乃至“医卜星相、农圃商贾,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8]而所有这些职业,均需立足于本地社会。
因此,“士的地方化”既是国家在地方上的权威相对退缩、权力相对缩小之后,需要地方精英填补这些权力空间这一总体趋势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士绅阶层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及维持其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而长期经营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明士特别强调它主要是士绅家族经营策略转变的结果。那么,士绅阶层究竟是如何走向地方化,或者说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演变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地方精英的呢?
首先是要留居在自己的家乡,这是扎根地方的首要前提。韩明士指出:“北宋时通过科举和入仕而取得成功的抚州家庭,大多长期或短期移居到宋帝国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而南宋则不同。一个士人做了高官后可能会移居他处,但1127年以后,没有一个抚州的高门大族举家搬离抚州。”[9]虽然这种变化也可以作出别的解释,但它确实反映出南宋士人居住方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是要在本地经营自己的家族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不动产(住宅与地产)固不必论,我们来看一看不动产(浮财),它主要来自商业经营。南宋商业的高度发展及其地方化倾向,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士绅阶层的参与一定与此有关:因为没有更大的财富,就很难支撑士绅家族持续不断地发展;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地产分割对家族利益的伤害以及农耕经济在财富积累方面的局限,都促使越来越多的士绅家族或其部分成员投身于商业活动;而商业经济不断向深度发展的结果,也是越来越趋向于地方化———换言之,士绅家族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地方性的,反过来,这些地方性的商业活动强化了参与其中的士绅阶层的地方色彩,促进了地方经济体系的发育、形成与成熟。
第三,是要在本地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士绅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官僚关系(那是北宋士绅阶层着意经营的网络,其中心在中央)、教育关系(在中央与地方各有一半,在中央的那一半附属于官僚关系;在地方的那一半,主要是师友关系)以及婚姻关系等(当然,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陈寅恪先生尝谓:“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宦,俱为社会所不齿。”[10]当唐、北宋时代,士大夫之婚姻苟不结高门或高官,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降低沦落”,更不利于仕途之进取。于是婚姻关系乃往往附属于官僚关系网络,而因为官僚关系的指向在中央,故其婚姻关系的总体指向也是向上的、全国性的。至若南宋,官僚关系在士绅家族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既大为降低,士绅阶层的婚姻乃主要在师友、本地望族、经济往来对象中选择,于是婚姻关系乃越来越与教育关系、经济关系相重合,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地方性。
第四,是要参与、组织与领导地方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介入乃至主导地方政治。对此,韩明士在本书第四章“地方防卫”、第五章“社会福利”与第七章“庙宇建设和宗教生活”中作了详细阐述。其中,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地方公益领域本来就是专制国家权力较少也不愿干预的领域,且不必论,地方防务却本是国家的禁脔,士绅阶层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侵夺了国家在地方上的权力(即便国家已无力行使这种权力),而这确又是“士的地方化”最重要的表现领域之一。韩明士说:“在抚州的大部分地方,并没有出现常设的本地私人武装以填补国家留下的空隙,只有当其家乡面临直接的危险时,士绅们才会投身于军事活动。如果不是政府无力派遣军事力量有效地控制乡村地区的话,金溪义军也不可能得到蓬勃发展,但义军的形成与发展,显然也是建立在地方特点之上的。并不是在国家退缩的所有地方,都有地方精英自动地去填补它。”[11]关键在于地方精英要自发地去填充国家权威退缩所遗留下来的权力空缺,主动经营地方防卫力量。被动地自保山砦与主动地营城据垒,虽然表面看来非常相近,但其性质却有根本性差别:前者主要是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缺,而后者却主要是利用此种缺失以经营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当家乡遭遇威胁时,北、南宋的士绅阶层都可能会组织地方武装以求自卫,其细微但却意义重大的差别,正是在这里。
第五,是要逐步认同地方社会的信仰,亦即实现信仰的地方化。至少在理论上,士绅阶层的信仰需要与国家正统信仰相契合;在北宋,大部分士绅阶层也确实做到了或试图做到这一点。但在北南宋之交的变局中,抚州士绅阶层的信仰取向却与官方的正统取向发生了很大偏离:当时,朝廷推行神霄派道教,而抚州地方精英却更倾向于认同地方性的三仙信仰———三仙(三真君)最初只是崇仁县的地方神,其权威并非如正统信仰中大多数神祇那样,来自其高贵的出身(门阀贵族的折射)、天界的官僚或曾是地上的高官,而是来自个人化的知识传授、自我修养、德行和宗亲关系,其生前与成仙后和朝廷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对这样一个神祇的信仰,在南宋时期逐渐从崇仁县传播开来,成为抚州地方社会的主流信仰,这显然得到了地方精英的支持。关于这个问题,韩明士在本书第七章中只是约略提到,直到2002年出版的《道与旁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才作了充分阐释,但其理路却是一脉相承的。
凡此,均显露出士绅阶层的主动性。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主动的选择,士绅阶层逐步走上了地方化之路;而士绅阶层(精英)的地方化,使地方社会具备了更切实而丰富的内涵,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经济、社会、文化网络乃至权力网络;这种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网络形成之后,必然相对稳定,也必然表现出相对于国家权威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正是所谓“大地方”的实质。因此,“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的形成是同步的,而士绅阶层与国家的疏离,和地方社会之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
最初注意到乡村聚落的“空心”现象,是基于对村落面貌的观察:在不少村落,因为近二十年来新建的房屋大多集中在靠近公路、或贴近市镇的方向上,原有村落的中心(在南方很多地方,往往是一个祠堂)地带只剩下无力改建新居的老户,房屋倾圮颓败,或者干脆废弃了,从而使村落呈现出两三面新屋集聚、老中心却衰败空寂的面貌。后来,随着观察的不断深入,才逐渐认识到这种“空心村”现象还有着多元的表现形式与丰富的社会内涵:凡是“有一点能耐”的乡村青壮年都离开了村子,只剩下“老、弱、病、残、幼”,还有“土豪”和“地痞”,有文化、讲道德、能在乡村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精英分子”确实是微乎其微了。
不管怎么说,从南宋及南宋抚州的士绅阶层,一下子说到今日乡村社会及乡村中“精英分子”之匮乏,这个“跨越”还是太大了些。但这里却正隐含着一种长时段观察的视角:南宋以来,随着士绅阶层的地方精英化以及“地方精英”范畴的不断扩大,乡村的“社会精英”在长期的总体演化趋势上呈现出一种姑且称之为“去文化化”(这个词很有些生硬,但想不出更好的表达)与“土豪化”现象,即越来越远离“士”的本义———读书做官,忠君报国,越来越倾向于仅仅使用“财富”和“权势”来作为界定“精英”的标准,一步步地抛弃读书、文化教养以及附着其上的道德修养、伦理观念。显然,“地方精英的土豪化”可以看作“士绅地方化”的进一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其演化的必然趋势;而“地方精英的土豪化”加剧了乡村社会内部的紧张,激化了各种矛盾,是促使明清以来特别是晚清以来乡村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中国乡村“文化精英”的缺失或许可以说是这一长期趋势不断演进的结果,城市化进程不过是促进了这一趋势的演进而已。
还是回到纯粹的学理上来吧。士绅的地方精英化———地方精英的土豪化,这一立足于地方社会主导或领导力量转型与地方社会演变的思考方式,促使我们把南宋的变化与其后元明清时期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应当是韩明士及郝若贝等人的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学术史意义。张广达先生说:“郝(若贝)—韩(明士)说主张划出北宋南宋之间的分野,研究趋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后世中国社会的连续性。诚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还有延续……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会诸多因素的滥觞。因此,郝—韩说宁将北宋视为唐代的延长,也要把南宋和后宋时代密切相联系。”[12]实际上,这一研究理路,近年来已得到北美中国史学者越来越多的认同。200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论文集即试图以这一研究理路为基础,希望对宋元明时期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作出说明,从而将西方中国史学者已经熟悉的帝制中期(唐宋,7-13世纪)和帝制晚期(明清,1550-1900)中间的所谓宋元明过渡时期的地位突显出来。
那么,对于元明乃至清代的历史发展来说,究竟哪些因素是“南宋的遗产”?我们知道,任何判断都可能引发相反的意见,而每一种意见又都有很多至少看起来非常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学术研究不能永远回避做出判断。我想,就本文论题有关的内容来说,或者有三个方面可以约略言之:
首先,是强有力的、专制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或者直截了当地表达为“专制的‘小国家’”。这里,“国家”之上的三个界定词甚至“国家”本身都可能引发无穷的争论。较少争议的或许是“专制”;而如果承认它是“专制的”,那么,至少在表象上,它也是强有力的,“生杀予夺,在予一人”,孰能谓为“软弱无力”?同时,虽然“帝制中国中晚期专制政府权力衰退论”自始即受到强有力的批评,但即便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也不能不承认:相对于高度膨胀的人口总量和日益壮大的经济总量而言,国家权力机器至少在规模上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国家权力不及(无力“及”与不愿“及”)的领域越来越大。就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的渗透而言,虽然尚有待证实,但如果说宋元明乃至清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较之于汉唐为弱,可能不会是一种谬之千里的判断。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判断有其合理性,即帝制中国中晚期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那么,就必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的“大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要而充分的代价”?
其次,是由地方精英主导的、有一定相对自主权的地方社会,亦即所谓“大地方”。这些地方精英集团虽然此消彼长,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亲疏、互相利用与冲突也各有不同且历有变化,但他们盘根错节地立足于地方,自我赓续,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独立性:朝代更替虽然会影响到地方某些家族的兴衰,但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却并不因朝廷更替而兴衰。国家权力欲有效地控制地方,必须程度不同、方式不一地仰赖于他们的合作与支持。他们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虽然主要是国家权力所不及之处,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在很多领域,比如地方防务与地方社会冲突的解决方面,他们会与国家权力发生或大或小的冲突,从而清晰地表现出其相对独立性。如果这样一幅图景历南宋元明清而具有某种普遍性,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大地方社会”又是如何消亡的?显然,地方精英的土豪化加剧了地方社会内部的紧张,是导致其衰亡的内因。
最后,是知识阶层逐渐“转向内在”。这里忽然使用“知识阶层”这个词,是因为地方化之后的士绅既不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自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而土豪化的“地方精英”更是蔑视读书,惟财富与权力是尚,全与知识无缘。但总是还会有一些人,不识时务地思考着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命运与实质。然而,国事自有天子圣裁,州县之事自有“青天大老爷”作主,乡曲是非自有土豪劣绅为之“武断”,家事不足为,余下的,就只有修身养性、澄心悟道、思古怀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参考文献 [1][3][4][6][9][11]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210-211, 8-11, 212, 209, 113-114, 150.
[2][7]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11。 [5]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 [8]袁寀,袁氏世范,卷中,第23页。 [10]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2:112。 [12]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11),第52页。
《Statesmen and Gentlemen》读后感(四):【转】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地方史”研究方法与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
精英们“地方化”了吗?[1]——试论“地方史”研究方法与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提 要:本文以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一书为例,讨论“地方史”研究的方法。韩氏此书以南宋江西抚州的精英阶层为例,探讨中国帝制后期社会转轨问题,认为抚州精英存在着一种从北宋的面向全国政治,向南宋的以经营地方基地为中心的家族策略转变的现象;南宋抚州的精英们与国家“分道扬镳”,开始“地方化”了。有人称韩氏此说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文献记载、个案典型性与长时段考察方法等方面的考察,认为韩著存在明显的论证失误、论证对象典型性欠明确、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一些长期性趋势认识不足、全局观察欠缺等问题,因此他的结论尚需进一步论证。本文的讨论表明:地方史研究方法在具有其观察深入、以小见大等可能的长处的同时,也在如何解决文献记载不足、处理个案与全局关系等多方面,对研究者的学识与能力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历史学每一次比较显著的进步,必然伴随着研究取向的更新,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以新方法研究新材料之“新方法”。近些年来,“地方史”研究取向在欧美学界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深入观察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变迁,解剖麻雀,以小见大,就其方法论层面看,实有超乎前人之处。已经问世的不少地方史代表性著作,成绩显著。
不过,俗语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任何一种新兴的研究取向,相比于旧方法固有其优异之处,也难免会有某些不足。地方史研究取向,扬弃传统的“宏大叙事”式写史方法,将视角从全局转向局部,在深入观察此一局部方方面面的同时,是否会带来某些“一叶障目”式的弊病呢?值得重视。本文试以美国学者韩明士(Robert P. Hymes)所撰《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为例,[1]对此略述已见。
借一本近20年以前出版的论著来说长论短,似乎有失公允。但考虑到这些年来韩著的持续影响,我们的选择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无的放矢。
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韩著的基本内容。
韩著全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八章。序论阐述了全书论题的意义,开宗明义,首陈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关于中国帝制社会中后期历史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2]并介绍了作为“地方史”研究对象的南宋(1127–1279)江西抚州的一般背景,以及作者关于南宋抚州“精英”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第一章主要是通过扩大对科举士人社会关系网的考察,来证明作者关于宋代地方“精英”概念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传统论说关于宋代社会流动性估计的失误;第二章讨论南宋抚州精英家族的起源,并提出了官职对于精英身份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看法;第三章描述抚州精英在北宋(960–1127)与南宋不同的婚姻模式,认为北宋抚州精英倾向于全国范围的散发型婚姻模式,到南宋,抚州精英的婚姻圈基本限于本县,因此反映了北宋与南宋之间精英家族策略的变化;第四章基于前面三章的论述,提出宋代精英家族策略变化的思路,认为从北宋到南宋,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呈现有“地方主义”的倾向;第五、六、七章,以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各方面的事例,来进一步证实前面关于精英地方化的思路;第八章集中讨论南宋抚州地方政府权威衰落的现象,认为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中退缩,才使得精英们相应地在那些领域“犹犹豫豫或急不可耐地”填补权力的真空。最后是结论部分,作者归纳全书的讨论,明确指出他的著作共有三个主题: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页210)。“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种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页210–11)作者认为他的第三个论题“最为重要”,他还将把第三个主题明确地表述为“精英与国家的分道扬镳”。“不过只是到了南宋,精英身份的独立性以及自我认可特性才变得最为清晰”。(页212)
美国学界对韩著曾发表过几篇评论,虽个别学者有一些含蓄的异疑,总体上此书被认为是一部地方社会史研究的杰出论著,备受赞赏,[3]在其出版当年,即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The Joseo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3年,韩明士与施诺考瓦(Conrad Schirokauer)合编了一本题为《经世治国》的论文集(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出版,共收录10篇论文,包括韩氏自己关于元代抚州精英婚姻模式的研究。此书再次阐述了他在前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界定出了一个“中层空间”(Middle Space)(见序言第52–53)。这个中层空间,当然就指“从力求出仕中央官职转向巩固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的地方精英。[4]近年来,韩氏的论点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接受,并被应用到他们各自的研究之中。1998年5月,包弼德(Peter Bol)在提交给北京大学汉学研究国际会议的论文中,已将韩氏的论点描述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5]
本文举韩著为例,当然并不是为了全面评述此书,而是因为这部其结论已被誉作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的著作,其所反映的关于地方史研究视角的长处与不足比较具有代表性。下文主要从资料搜集的困境、个案的典型性、局部的变化与长时段趋势的关系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关于文献记载
如前所述,地方史研究的长处是将观察聚焦于某一特定地区,集中精力,发掘与论题相关的所有史实,因此常能较其它研究方法为深入。同时,也理应更为全面,而不是象某些“通观全局”的论述,常有对不同地区的文献记载“按需所取”的嫌疑。如韩著,其对宋代抚州文献的搜寻用力之深,有目共睹,近年相关论著或无出其右者。它不仅将南宋时期关于抚州的文献搜罗殆尽,而且还征引了不少南宋以后的文献。
尽管如此,尤其是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中前期的研究论题,由于传世文献有限,局限于某一区域的研究,是否有足够的记载来支撑它,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难题。因此,如果说通论式著作易于出现片面取材的弊病,在地方史研究中,由于文献记载的捉襟见肘,则更容易出现勉强拼凑、推论失实的问题。韩氏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类似的现象。
韩著对其核心的概念“精英”一词的界定与讨论,资料不足的困境就反映得比较明显。
关于精英的概念,是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根据这一理论,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是社会的主导阶层。精英集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因此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上下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以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为代表的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而对于精英阶层的界定,社会学家们一般都采用财富、权势与威望这个三个衡量标准。不过正如韩氏非常恰当地所指出的,落实到针对南宋抚州社会的分析中,财富、权势与威望这三个标准仍然具有不可捉摸性,需要将其具体化。为此,韩氏提出了他自己的关于南宋抚州精英阶层的七个具体标准:1、官员;2、通过州试的举人,或其他有资格到京城参加省试者;3、寺观资金或土地的主要捐助者;4、修建学校、书院、藏书楼、桥梁、水利工程和园林的组织者或主要捐助者;5、地方军事组织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的地方慈善活动的组织者或领导者;6、通过朋友、师生、学术同仁、诗友等关系组织在一起,或由前述一至五项聚成团体的人;7、一至五项人的亲戚和姻亲(页8–10)。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界定。正如李弘祺所指出的,当韩明士批评柯睿格(E. A. Kcrake)等人由于将精英的家族成员只界定在直系近亲的范围之内,低估了进士及第者中有一定家世背景者的比例,从而高估了科举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时候,由于他将精英的范围放得如此之宽泛,以致不管家族的联系隔了多少代都包括在内,并且将“社会联系”也包括到精英的关系网络之中(页46),“以至实际上不可能有非精英之抚州平民获得科举功名”。[6]这样一来,至少从逻辑层面讲,他对前人的批评意义也就失去了意义。
韩明士之所以尽力放宽精英阶层的范围,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为了藉此扩大搜寻史料的范围,解决论据不足的困难。所以他很坦率地称上述精英概念为Working Definition(页10),我想将其译成“实用定义”可能比较恰当。“实用”也者,因需而定者也。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韩明士为了“实用”尽力放宽精英集团的范围,他显然无法回避这一史实: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精英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界定标准的,那就是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衡量的身份地位。例如商人,尽管可能富甲一方,但受国家法规的压制与社会观念的贬视,却很被时人视为“精英”。所以,尽管他一方面说“只要他在抚州有那么一点出头露面,我就将他列入精英的行列”(页10),另一方面,又宣称“‘士’这个概念,与本书所界定的精英之定义相当吻合”(页7)。“在我的实用概念中作为‘精英’的所有各类人,不管他们是否据有官职,出现在资料中都属于士”(页53)。这显然是强为说词了。有可能列入前述7类人的如商人,尤其是女户,当然不可能属于士;即如官员,他们的亲属或姻亲,也不一定就是士。这无需论证。
更清楚地反映研究中史料不足困难的,是韩氏复原南宋抚州精英家族的工作。由于抚州地区宋人宗谱之类文献全无存世,韩氏得以依据的,大多只是宋人墓铭、传记或其它相关记载中提及家族联系的只言片语,实属不易。因此他在研究中不免存在借助想象来弥补记载不足的情况。韩氏一共复原了73个南宋抚州的精英家族,以及9个他认为由于记载不明确、尚无法确定的精英家族。但正如已有评论者所批评的那样,韩氏对抚州精英家族的复原,经常仅凭相同的姓氏与地域而将其归为同一家族。例如乐安县董氏,韩氏将地志所载董姓进士列入此家族的唯一论据,就是他们同为乐安县流坊人(页238–39)。[7]再如乐安县招携寨邓氏,在韩氏的考证中,支持其精英家族地位的唯一论据,就是地志所载绍兴、景定、咸淳三次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的四位邓姓士人都是招携寨人,因此在韩氏看来,他们当然都是一个家族成员了(页233)。[8]
类似推论方法的应用,在对记载中往往只见姓氏的女性家族归属考证中表现尤为明显。如韩氏考证俊仁县何尧家族与詹崇朴家族的联姻关系,所引两则记载,仅言何梦龙和何湛娶了詹氏女,未言明是何处的詹氏,作者认为虽然不明确,但仍有可能。其实当时墓铭传记书法的惯例,如果是大族出身,通常都会明确其家族关系。另一条记载,说何尧与詹崇朴交好,其两女“适饶,适詹”,也并未明言嫁于詹崇朴的子弟,[9]韩氏却认为当属确实无疑(页91–94)。又关于俊仁县罗点家族与宜黄王氏的联姻,韩氏引据陈造《江湖长翁集》三五《太孺人王氏墓誌銘》为证(页58)。其实铭文中明言王孺人“早孤,随母饶氏适崇仁之王氏”,早非宜黄王氏家族中人了。
似此仅凭姓氏来作推论的现象,书中其它部分也多有见到。如第六章考证精英家族对地方水利工程的介入与控制,共列举四则关于水坝建设的记载,都被认为系由地方精英家族出力建成(页169–170)。其中金溪县陆家堰,因其位于三十六都,而陆九渊家族恰好居住于此,[10]因此陆家堰当然就是陆九渊家族介入地方水利工程的最好论据。同理,四十三都的葛家堰与十九都的黄家堰,[11]因金溪县葛氏(家族复原表第34)居住在第四十四都,[12]“善人”王士良家族居住在第十八都,[13]都与上述两堰相邻,因此这两个堰也就必然为这两个家族所建了。此外,宜黄县崇仙乡戴家堰之与居于同一都的戴氏家族、以及小乐家堰之与霍源乐氏家族的关系,当然也按同一原则来推论了。
韩氏的研究,认为前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论述,仅据存世宋代登科录所反映的直系近亲来考察他们家族的背景,有所不足,因此强调应将姻亲以及其它相关的家族联系包括在考察的范围之内;[14]同时宋代抚州家族经常“成群”地崛起(页80),进入精英阶层。因此他十分重视考察抚州精英家族相互之间的联系网络。这当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考察起来并不容易。众所周知,宋代家族制度行小宗之法,君子之泽,五世而竭,宗族联系网络有一定的范围。相应地,姻亲关系也必定有其世俗认可的范围,不可能无限延伸。所以了解精英家族相互关系的具体情形是必要的,但存世文献却常无法满足研究的要求,于是韩氏大多只能仅凭只言片语,如某氏与某氏为“族人”,或某氏之远房宗女嫁给了某氏,就强令古人承认他们相互间本来可能并不存在的“网络”关系。如韩氏讨论俊仁县李刘家族(家族复原表第36)与游氏的关系,引游德洪“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姓女孙”一节为证。[15]但族姓女孙与李刘家族的关系是否的确近得足以形成“网络”呢?不得而知。其实,韩氏在考察中,除血缘、姻亲关系之外,将“社会联系”也考虑在内,更无从确证。有的时候,就完全出于推测了。如韩氏在考证了俊仁县李氏、陈氏(家族复原表第4)、罗氏(家族复原表第41)与当地大族吴曾家族(家族复原表第67)的联系之后,[16]说:“正如金溪县的例证一样,并无资料证明他们涉及一些共同的事业;但我却认为,这一家族群体的形成可能与其显赫的邻居吴氏的联系有关。”(页79)下文就进一步得出了精英家族经常“成群”崛起的结论。
实事求是地说,韩氏关于南宋抚州精英家族及其网络关系的考证,恐需进一步验证。
韩明士与施诺考瓦所编《经世治国》论文集二、关于个案的典型性问题
地方史研究另一可以想见的困难,在于个案是否具有足够的典型性:从局部地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意义吗?选题之初,研究者当然会首先用心于此。例如韩氏在序论中首先论述了抚州作为宋代南宋新兴地区的典型性,包弼德也将抚州案例的普遍意义限定于“南方地区”。这些所涉及的都是指全书的总体结论,其实局部与全局的矛盾,体现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
韩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认为宋代抚州精英家族的婚姻策略从北宋到南宋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北宋时期倾向于形成面向全国的散发式婚姻网,到南宋,转变为倾向于大多在本县范围内缔结婚姻关系。这一实证性的考察结果又成了韩氏提出从北宋到南宋精英家族策略转变的主要论据,即从北宋时期的追求全国性政治地位,追求朝廷高官位置,到南宋转向以巩固他们在地方的基地为主要策略。与这一现象相应的,是北宋时期抚州身为高官的精英家族为配合他们的政治追求,多移居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地区,而南宋时期抚州的精英们则很少移居外地。
假设韩氏前述考证全都可靠无误,这里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证实:抚州精英阶层的婚姻行为、以及关于抚州精英阶层婚姻行为的文献记载,是否属于例外?在赋予抚州的结论以普遍意义之前,对相似地区作一定量的取样重复验证,实属必要。不过无论是韩氏本人,还是美国学界其他同仁,看来都无暇或无意于此。
其实,由于抚州地区北宋与南宋传世文献的数量差异,两个时期所谓精英婚姻模式的差异,并不可能如韩著所描述的那么明显。其它一些地区的文献记载,也并不一定完全能与韩氏所描述的抚州模式相呼应。笔者粗考南宋与抚州相类似的明州地区情况,
说明:绍熙元年(1190年),明州升为庆元府。为行文方便,本表仍统一标作“明州”。笔者无暇考证上述表中传主配偶属于“本地”的17例中,非本县的共有几例,凡其配偶籍贯为明州地区的,全都列为本地。即便如此,仍有1/3以上的案例属外地婚姻。由于明州地区未留有足够的关于其北宋时期精英家族婚姻状况的文献记载,难以前后比较,但仅从南宋的情况看,与韩氏所描述的抚州案例,有较大差异。
在关于两宋时期抚州地区精英阶层不同婚姻圈范围的实证性论述之后,韩氏还描述了他们其他方面婚姻行为的变化,如认为在北宋,人们择婿选妇,以官职为重,而到南宋,则只注重财富、家世、学术、以及地方名望(页87)。这无疑与学术界关于宋代精英阶层婚姻行为的认识,存在不少差距。[17]而且前人的评论也已经指出,韩氏关于南宋婚姻重财的论述,在其所引证的五则文献记载中,至少有两侧属于误读,[18]此外关于抚州北宋精英群最成功者多徙居外地、而南宋则多留居本地的记述(页113),似也不一定具有特别的普遍意义。南宋时期,由于国土日蹙,江南地区进一步开发,人口密度提高,精英们的移居空间自比北宋为小,其与北宋的比较本来并不一定与韩氏的结论有必然逻辑联系,但南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的达官贵人移居行都临安府附近地区。南宋初年由于战争影响而从北方移居南方的人口自不必说,当时的湖州地区,即以达贵聚居闻名。人称湖州“高宗皇帝驻跸临安,实为行都辅郡,风化先被,英杰辈出。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衣冠雾台,弦诵驰声,上齐衡于邹鲁,至如城邑墟市,精庐相望。”[19]南宋末年周密(1232–1298)也说“吴兴(湖州)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并列举了“南沈尚书园”等园林36处。[20]
另有一些北南宋之间的差异,或者纯由记载的偶然性造成,同样不具有普遍性。韩氏为了佐证他所描述的北、南宋之间精英阶层婚姻行为变化的模式,还讨论了抚州精英居住地、别业以及他们所捐助的公共建筑所处的地理位置,引用两则文献记载,来证明北宋精英们多倾向于在不同的县境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居住地,南宋精英们则相反,“倾向于将他们的居住地、别业以及捐助对象集中在相对较小的一个县境范围之内”(页111),因此这说明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倾向。前人评论早已指出,仅凭两则记载来作此推论,不免过于单溥。其实,由于租佃关系发展等原因,我国唐宋以降,形成了地权集中而属于同一地主的地产分布却呈零碎化的趋势,南宋尤甚。因此精英们在不同县境拥有地产、别业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如南宋翁功世,“家建宁府崇安县之白水村”,其祖上却“有别业金陵(江宁)”,翁功世平时就居住在金陵别业,淳熙元年(1174年)去世后,也就葬于江宁县了。[21]这就不仅不在同一县境,更不在同一路分了。又殿中侍御史尹穑本为兖州人,南宋初为避战乱移居江西信州玉山县,却有别业在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岁往来邑中”。[22]尹穑的别业也与他的居所不在同一路分之内。所以南宋时期精英们“别业乎旁州”的现象,[23]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韩氏所举抚州的事例,看来应该是文献记载不全所造成的。退一步说,即便假设那两则记载所反映的抚州地区的情况属实,从全国范围看来,也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韩氏在第五、六、七章分析了南宋抚州精英们的种种社会活动,以进一步论证全书的结论。其中有一些也由于未能注意局部案例是否具有全局意义,而使论述流于无的放矢,如第五章关于地方武装组织的讨论即是。韩氏认为南宋时期,由于抚州的地方政府无力控制农村地区的防务,因此当地发展起了一些由精英阶层所控制的地方武装,这在他看来当然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政府权力的衰退与精英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可是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地方武装的兴起,多存在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南宋时期南方地区常受北方女真族军事威胁,而且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疆域内部各类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也较北宋为频繁,地方出于自保,建立私人武装,有时甚至受到政府的鼓励。南宋初年朝廷发动地方组织抗金义军,就是明证。换句话说,抚州地区在两宋时期前后地方武装存否的差别,与其说是出于精英与政府对地方控制力量的一进与一退,还不如说是当地外部环境变异所致。南宋抚州地方武装一例,并不具有必要的普遍意义。其实由地方豪强[24]建立并控制地方武装,也绝非仅是随着所谓南宋精英阶层“地方化”之后才有的现象。如据黄宽重的研究,至少在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动乱,“豪右大姓为了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三辅、河南、荆州、东郡、清河、赵郡、中山国、南阳、陈留、渔阳、安定和北地,都先后出现据坞堡为守的地方自卫武力”。而且“宋代以前的自卫武力,多由民间自动聚集,官督民办的团体较少。魏晋时代,北方由豪族领导,据坞堡以抗外敌的自卫武力就是典型例子”。到宋代以后,“除由民间自动集结而成之外,尚有官督民办者”。[25]文献中此类记载颇多。如唐肃宗至德初(756年),河朔之民反抗史思明的叛军,“所至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子仪)、李(光弼)军至,争出自效”。[26]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据知定州滕甫上言,提到“今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等户,习惯便利,与敌人无异”。[27]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也在知定州任上的苏轼(1037–1101)上奏,请增修当地民间的“弓箭社”:“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髙下,户岀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岀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28]若按韩著的逻辑,我们是否需要将“自存性”精英阶层出现的时间向前推移呢?
就逻辑而言,不具有普遍性的论据无法说明韩氏所希望论证的一般性结论。
包弼德将韩明士的观点定性为美国学界的通说。三、关于“长时段考察”
利用地方史个案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期的社会变迁作“长时段的考察”,是韩氏的一个主要目的。他在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应该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视为“双重转折”,第一个表现为精英阶层组成人员的更替,第二个则是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变化,即“从全国性到地方性策略的转变”。“第一个转折可能发生于唐宋之间……第二个转折将北宋与南宋区分了开来”(页216–217)。这一假设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如能确立,自有相当意义。
欲通过局部变迁来作长时段的考察,在研究中时时注意一时一地的变化与整个历史长河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韩著的论述,多有顾此失彼之嫌,显示了地方史研究对全局性观察能力的苛求。
韩氏的观察方法,基本是通过将南宋时期抚州精英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北宋时期作对比,来得出结论,十分简单明了。如果我们的理解无误,韩著之所讨论的,并非仅仅局限于从北宋到南宋这一朝一代的变迁,而是着眼于中国帝制后期社会演变的总趋势,那么,这里所涉及的“长时段考察”,可能还需要我们关注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
首先,韩氏的基本结论,强调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衰退,精英阶层的地方化以及他们与国家的“分道扬镳”。[29]如作者本人所坦陈的,这主要来自郝若贝的观点,可能还受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界所流行的关于中国帝制后期专制政府权力衰退论的影响。[30]就某种程度而言,此说有为“中层空间”说张目的倾向。如何评判“中层空间”说,自是另一问题,不过提到国家权力衰退论,不免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古代国家是从宗族组织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它生产的初期,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还比较有限,很大一部分权力仍掌控在原始宗族组织手中。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发展,总趋势是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基层渗透,不断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代。例如就地方行政而言,从先秦的分封制,到秦代确立郡县制,经过后世数次反复,才消除分封制的残余。宋代以前,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为县级政府,到宋代出现监镇官,在县级行政之下,新地方行政级别开始萌芽。元代确立行省制,近代最终确立县级行政之下的区级行政,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全面加强。这一过程虽不可能直线行进,必然会有起伏与曲折,不过衰退论者如果想要确立他们的论说,必须考虑如何处理与这一总趋势的关系。数年前,已有学者的专门研究,批评由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提出的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官僚建制的密度在稳步缩减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地方官僚系统,除由中央政府所委派的品官外,还应包括本地招摹的胥吏,以及由官员个人雇用的慕僚与家人。这后二者的数量都在激增,所以史实可能恰与施坚雅的论点相反。[31]
韩著详加论述的不少内容,如地方官劝谕赈灾之困难,如地方豪强逃税抗税等等(页157–163、204–209),以之来说明南宋时期国家权威的衰落。书中虽略为涉及了一些北宋的情形,却未能说明南宋时期的这种现象,较之前代究竟是更为严重了,还是相对减轻了?总之,韩氏的研究仍为局限于一朝一代的考察,若将其视野略作拓展,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全过程来作考察,或者会有新的体会。前述关于地方武装的讨论,即可为一例。又如关于地方赋税征收所反映的国家权威盛衰问题,地方豪强与国家争夺财赋的斗争,可谓中国古代国家行政永恒的难题。由于赋税制度的更革,总体看,前期主要表现为地方豪强与国家争夺劳动人口,即所谓荫蔽人口,东汉魏晋南北朝地方大户荫户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众所周知。隋初大索貌阅,唐代中期括逃户,都是国家试图将这些荫蔽人口重新控制起来的努力。自中唐推行两税制以后,国家赋税制度呈现“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的新格局,[32]国家与“巨室”的矛盾才显得尤为突出。韩著所征引的几则关于南宋抚州地方豪强逃避赋税以及不愿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关于赈济灾民的要求等事例,或者可视为部分“精英”们在新财税形势下对政府的抗争。如果学界关于南宋地权高度集中的倾向性意见不误,[33]南宋时期国家财税多数仍当出于占有大部分地产的精英阶层,韩著所引例证所涉及的当属少数地方豪强。其实南宋时期地方赋税大幅度增额的事实,[34]说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仍相当有力。韩氏由于不了解南宋时期地方赋税多出于杂税与附加税,且其总量数倍于北宋的详情,其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南宋抚州由于精英们逃税抗税,正税大幅度缺额,和籴等项目仅为弥补正税缺额等论点(页204),有违史实。
其次,与前述相应,在讨论与北宋相比较、南宋地方社会出现一些新现象的时候,韩氏似乎忽视了中国帝制时期的一个基本规律:每一个专制王朝无例外地存在前盛后衰的现象。一个新王朝建立的前期,政治相对清明,正常行政秩序基本能得到维护,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较牢;到后期,随着政治不可避免的腐败与行政秩序的混乱,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趋于松弛。所以,某一特定王朝后期秩序混乱现象是否必然昭示着“长时段”的意义,还有待于其与后一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如果仔细分析南宋以后各朝新建初期的行政措施,尤其是明初国家抑制江南富户的种种史实,韩著所描述的南宋抚州政府在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各方面的“退缩”,或曰“地方官府在多数情形下处于自生自灭的况态”(页202),恐怕只是南宋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所呈现的阶段性困境,而与“长时段”无涉。
复次,从“技术”的层面看,前后期的历史比较还存在一个文献记载是否对称、即比较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是否拥有数量与质量基本相等的史料的问题。由于历史研究须以历史资料(主要是文献记载)为基础,而存世文献中关于人类历史前期的记载的数量,总是远不及后期的那么丰富。宋代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存世文献远比前代为丰富,不过相比而言,北宋文献总量仍少于南宋,尤其是现存涉及地方社会的方志、笔记小说与文人的文集,更是如此。因此当我们发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常常难以判断它属于“新”历史现象,还是前期早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在存世文献中第一次露面。这时候判断的准确与否,就有赖于史家的学识了。
韩著第七章的结尾部分,引用陆九渊《石湾祷雨文》,其中有云:“盖闻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国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职守,谁敢奸焉。然辅相不任爕调,以吏事为责;守令无暇抚字,以催科为政;……故祈祷散在庶民,徧满天下,久以为常。法有其文,官无其禁,亦其势然也。”[35]这段引文,明显有为前面三章所讨论的地方事务中政府与精英势力的一退一进关系作总结的意味,无非是指如防务、水利、救济、宗教等等一系列地方事务,当地方行政秩序正常之时,“国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职守,谁敢奸焉”。到南宋,随着地方政府权威削弱与其从众多地方事务的退缩,才“祈祷散在庶民,徧满天下,久以为常”,由精英阶层来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了。
可是,通过推崇先王圣政来批判现实政治,实为中国儒生最一般的文化基调,陆九渊的《石湾祷雨文》无法用来证明北宋与南宋之间抚州地方宗教事务方面的上述变化,大约勿容异议。韩著试图通过征引此祷雨文,以及其它少量的文献,如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二关于修桥补路、兴建水利当为县官职责之语(页174)等,来证明北宋时期抚州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可是实证性记载明显缺乏。韩氏看来对这里资料的不对称性有所意识,因此他将北宋政府的行政称为“理论的职责”,又说“我们对北宋时期桥梁建造的情况近乎一无所知”,在水利工程方面,“例证相当缺乏”(页175),但有意思的是,这却并未妨碍他通过征引现存南宋的记载,来得出国家权力在这些领域退缩,而精英们进而控制这些领域的结论。坦率地说,如果认为南宋时期抚州地方的许多事务,如兴建桥梁、小型水利工程等等,都由精英们介入其间,在这以前则全由政府负责,恐难令人难以相信。令韩氏感到最有力、并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论据,是北宋熙丰变法时期在地方推行的一些水利工程建设等措施,但韩氏显然未能意识到熙丰变法所表现的宋王朝前盛后衰现象,当时许多工程其实并非全由政府自己兴建,以及地方官为迎合朝廷夸大数据的情况。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氏还点明了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作为抚州精英原型的两位人物,即北宋的王安石(1021–1086)与南宋的陆九渊(1139–1193),将他们相互比较,以显示北宋精英面向全国政治的倾向,以及南宋精英的地方性(页216–217)。但他看来并未意识到将一位位极人臣的宰相与一位大多数时间在家乡教学的下级官员对等起来作比较,是多么的不合适。这当然也是我们所说的资料不对称的另一显著例证。
总之,如欲真正从“长时段”的取向来考察抚州案例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趋势,需要完成的研究工作当远比韩著所阐述为复杂。
李锡熙立足明州,挑战韩明士的观点。(Negotiated Power: The Stat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Twelfth-to Fourteenth-Century China. By Sukhee Lee. Cambridge四、余 论
综上可见,地方史研究的方法绝非仅着眼于个案,将其分析得透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想要准确地复原个案的历史,有时仍有必要参照更为广泛的历史记载,切忌想当然地仅凭少量文献主观臆测。如何认识从个案所得出的结论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更是一个难题。一般讲,一定数量的重复验证必不可少,可惜目前学界着意于此者实为鲜见。
若说前人的评论主要是肯定了韩著的成绩,那么本文看起来更多地是在讨论它的另一方面。如果本文在结束前必须对韩著本身提出一些总括性的评论意见,那么笔者以为还有几点需要关注:
其一、“观念先行”。正如韩氏在其序论中即已表明的,他的研究是为了在地方史的层面为其师郝若贝的观点提供具体的论证,因此他的研究明显带有目的论的特性。如果用另一更为直白的表述,就是所谓“观念先行”。为了服务于这个“观念”,以致忽视史实的主观推论过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其结论的可信性。前文的讨论已多所议及,书中其它部分类似问题尚多,再举一例:在第七章,韩氏有一个考证:乐安县招仙观“绍兴以来道士杜、谭、李、曽、詹、陈、董、许相继主祈禳事”,[36]乐安县精英家族中也恰有李、曽、詹、陈、董各姓,因此韩氏就认为这些道士必当出于这些家族;又许姓,淳祐二年(1242年)乐安县有许应昌者进士及第,因此许姓道士看来也与精英阶层有关;唯杜、谭两姓,在乐安县精英群体中找不到相关家族。考虑到招仙观旧基在县境东五里外,绍兴十九年(1149年)乐安设县后才迁到现址。其旧基理应在宜黄县境,而宜黄县精英群中恰有杜、谭两姓(页184)。就这样,招仙观历年相继主祈禳事的各位道士都与当地的精英家族扯上了关系,因此这也就成了韩氏证明精英家族主导地方宗教事务的一个例证,只是未知读者是否会信服于这样大胆的考证。
其二、逻辑疏漏。与前述第一点相似,韩著也许为了急于要证明自己的论点,逻辑疏漏时有所见,如前文指出韩著关于精英概念的界定,既想尽量扩大其范围,又强调他们都属于“士”,实际造成了概念的移换,即是一例。不过最为明显的例证,当属韩著对精英家族策略转变原因的分析。韩著认为南宋抚州精英家族策略转向关注地方,是因为原先的策略不再那么值得追求,并也已不再那么切实可行。前者指从北宋后期起朝政受党争影响,高官地位有相当的危险性;后者则指由于南宋参加科举人数剧增,赢得科举的成功已不能得到保证(页121)。但韩氏显然没有考虑到:首先、象北宋中后期那样激烈的党争并不是恒定的现象,亦即南宋朝政并非长期受如此激烈党争的影响,它不可能成为精英阶层家庭策略转变的长久原因;其次、南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确实比北宋成倍增长,[37]且同时期人口的增长却远未达到与其成正比的程度。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相对人数与绝对人数都大幅度增长。但这本来是精英家族争取入仕、积极介入国家政治的表现,怎么倒反成了促成他们“地方化”的原因了呢?
其三、西方史观的影响。如前所述,韩氏的结论有为“中层空间”张目的倾向,因此在他的描述中,国家的权威与精英阶层的势力在南宋抚州地方成了相互排斥、你退我进的关系,完全排除了相互合作共存的可能性。这中间显有西方社会史“国家与社会分离”理论的影子。撇开“中层空间”不谈,书中其它部分西方史观的影响也时有显现,如第七章关于宋代国家或精英对宗教的“整合”(Integration)说即是。在传统中国,专制国家确曾努力控制宗教,但似未见曾试图“整合”宗教。将北宋两次佞道之事与南宋理学家们为推广自己的学说而建立先贤祠的努力,比喻成前后两次试图“整合”宗教的努力,就清楚地显露了西方宗教史对韩氏思路的影响。
那么,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到底有没有“地方化”呢?或者说南宋的精英们究竟呈现了哪些与前代不同的新特征,我以为这仍是一个有待于深入探讨、而绝非已可以形成“一致的看法”的问题。不过坦率地讲,不管今后探讨的结论为何,本人以为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目标并未变化,所以要“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参预国家政治,参加科举,投身仕途,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若认为以这样的儒生集团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这一假设之大胆,为本人之所不及。
注释:
[1]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韩著”。
[2]参见韩著第5–6页,及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of China, 750–1550”,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2卷第2期(1982年),354–442页。以下凡引韩著者,均不出脚注,仅在正文夹注其页码。
[3]参见Joseph P.McDermott、Thomas H. C.Lee(李弘祺),以及AndrewLo关于韩著的书评,分别见载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 Vol. 51, no.1(Jun., 1991), 333–357页、Journal o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 vol.109, no.3 (1989), 494–497页,以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25, no.2 (1989), 384–385页,以及其它的一些评论。
[4]参见韩森(V. Hansen)关于此书的评论,载Journal of Sung-YuanStudies, 第26卷(1995年),229–250页。
[5]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Reconsider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Change),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64–265页。后经修改,见载于《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63–87页。
[6]李弘祺评论,第494页。
[7]王建中修《(同治)永丰县志》卷十五《选举·进士》11页,同治刻本。
[8]《(同治)乐安县志》卷七《选举乡举》。
[9]吴澄《吴文正集》卷七四《故宋文林郎道州判官何君墓碣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七。中华书局点校本。
[11]《永乐大典》第54册第14页引程芳《(同治)金溪县志》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本。
[12]同前注。
[13]谢逸《溪堂集》卷九《故通仕郎晏宗武墓志铭》。豫章丛书本。
[14]参见李弘祺评论第494页注3,韩明士之前已有学者提议应从更为广泛的家族的范围、而非仅从个人出发来研究宋代的社会流动性问题。
[15]《吳文正集》卷七四《游竹坡墓誌銘》。
[16]韩氏关于这几个家族相互联系的考证也颇多可疑。如罗点与吴氏的关系,引洪迈《夷坚乙志》卷二《罗春伯》的文字为证:“罗春伯点,抚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馆于邑人吴徳秀家,受业者数辈。”韩氏推论说:既然洪迈在这里以字号指罗点,所以“邑人吴德秀”之“德秀”极可能也是字号。而俊仁县吴氏家族的吴沆等四兄弟字号中都有德字,因此这个“吴德秀”看来也是吴沆的兄弟或堂兄弟。于是韩氏断言:罗点与吴氏家族联系的论据看来是“颇为可靠的”(页302注100)。即使假设韩氏的考证无误,这个字号里有“德”字的吴德秀是否能够与吴沆的家族扯上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何况为什么这里洪迈对罗点姓名与字号并称,对吴德秀却未书其名呢?实际上按《夷坚志》的书法,这里吴德秀当属此人的姓名。
[17]参见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相关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李弘祺评论,第495页。
[19]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风俗》。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
[20]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呉兴园圃》,中华书局点校本。
[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一《司农寺丞翁君墓碣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22]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五《奉直大夫陆公墓志铭》。参见《宋詩紀事》卷五二“尹穡”条。四部丛刊初编本。
[23]曹彦约《昌谷集》卷十八《从兄云梦县尉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按韩氏的标准,他们当然属于“精英”。
[25]黄宽重《从坞堡到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原刊联经出版社《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后收入氏著《南宋史研究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43–388页。前引论述见第344、355、356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至德元载四月甲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28]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四部精要本。
[29]原文作“the separationof elite from state”。
[30]参见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C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相关部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英文原版,叶光庭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1年。
[31]参见魏丕信(Pierre- etienneWill)《18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荒政》(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ècle)1980年巴黎法文原版,徐建青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2]王柏《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金华丛书本。
[33]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相关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相关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5]《陆九渊集》卷二六《石湾祷雨文》。中华书局点校本。
[36]吴澄《吴文正集》卷四七《乐安县招仙观记》。
[37]参见贾志扬(JohnChaffee)《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相关部分,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原版,台湾东大书局1989年中译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