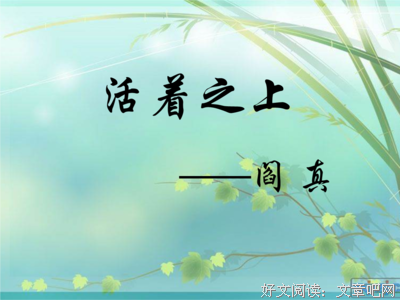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是一本由黄进兴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精选点评:
●简单扼要
●不錯不錯不錯
●可作教材观,浅入浅出~~
●庞卓恒,黄进兴喊你回家喽
●这是黄进兴作为传统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是一批判性探讨。黄历时七年写成,从脚注和参考文献的数量可见还是花了极大的功夫。介绍了福柯、海登·怀特、德里达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其作为一个基本了解参考读物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读的收获很大,现在觉得那个年代写成如此不宜。
●一堆课程读物;研究生课程居然跟本科一样多,很久没看没写感兴趣的东西了,无奈。
●垃圾书。满嘴跑火车。文理表述也和余英时的其他弟子相差太远。不是余门裙带和学历兼通中西的教育背景,他不该有这么高的地位,院士荣衔,更是有冗授之嫌。
●粗扫一遍,并细读了福柯哲学和史学阐释的部分。
●评述之作,以今日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言略有过时,不过仍不失为一本浮光掠影的好书,参考书目加一星。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读后感(一):史无定法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的一个思潮。目前,学术界对其还难以赋予一个简单准确的定义。在学术上,它跨越领域众多,内容包罗万象。要为它下定义,殊非易事。
后现代主义兴起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史学在内。它大有摧毁各学科原有的体系之姿态。
本书以福柯、海登·怀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为中心进行讨论。后现代主义给中国史学研究既带来许多全新的视野和方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虽有开疆辟土之功,但自身也有诸多缺陷。比如,福柯解消主体的意图,在处理历史、伦理、政治诸多问题时,他的如意算盘注定是失败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在于它看准了各学科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的弊端。笔者以为,任何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它都是脱胎于旧思潮。新思潮要想与旧思潮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不管主观上如何努力,但恐怕在客观上还是徒劳。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学术生涯及其实践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回到史学研究。史学的任何一个问题,不是都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或任何一种理论就可一举解决的。正如本书附录二中所言,“史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学术史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往往有了新的实践尝试,才渐渐产生新的方法和新的方法论,进而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一股新的思潮。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是胡适那句说得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读后感(二):对危机最好的回应是建立在理论的创新上
书中对福柯、海登怀特、巴特、德里达四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首先作者分析了四人思想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以一种作者对文本主体性的丢失与作者作品矛盾性的批判而收尾,这种方式没有说服力,不可否认,后现代对史学的批评是有合理性的,如果要进行批判,首先要承认这种合理性然后再建构与之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一说一,与后现代展开理性上的辩论,我认为一种趋近真实的事件必须包含对象多元、史料多元等要素,类似破案,所有的历史证据摆在面前,一一辨伪,然后再分析线索,探究真相,在这点上,《历史三调》的方法论是有启示的,史学危机显然是在科技实用与经济优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但史学自身并没有实现创新,以一种躲起来的姿态研究新文化史跟注重小人物的社会史,颇有一番小楼内绣花的姿态,作者认为如果要应对史学危机,必须注重更深层次的原典,这又让我想到了顾颉刚的中国古史的层累地造成的学说,我认为在一个开放的历史环境下,历史记述对象与作者的多元性可能有助于历史真相的认识,首先历史不是科学,其次,越古越真,还是越近越真,这两种都不具有逻辑理性,对历史最重要的是解读,解读各种史料,而方法论必须是多元具到的,辨伪、线索、动机分析、史料本身事件与论跟意的区分、思维意识来源等等,尽信书不如无书,史学若想取得生存权,必须努力找寻本身的理论框架,若没有一套可信服的构建,纵使打出新史学或各种名号,也无助于本身地位的衰落。 福柯《知识考古学》敲响了历史的丧钟,历史的本质乃是断裂,不相连贯,而史学的吃紧之处即在观察断裂之外。 史家的语艺行为,历史虚构性的真谛。 第四章阅读理论与史学理解 移情领会 挪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解读史料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本体论: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本体的接触,援用“对话”的模式,以仿真文本与读者互动。 巴特与德里达,认为“文本”即由符号编织成,将时间化的文本作为语言符号无限地戏耍。 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关注符号或文本的“失意作用”,而较少措意“沟通”与“效度”的问题。 第五章 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里达对传统史学的冲击 比尔德与贝克对兰克的科学史学的攻击:史实部分:质疑史料的形成过程中掺杂许多偶然的因素;例如史料幸存的程度与真实的过去殊不成比例,复加上记录者的成见、阶级、性别与利益往往令史料染上有色的薄膜。 价值判断部分:参照架构与意见情境蕴涵着史家不免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或个人主观的际遇。 文本的阅读悉由“延异”运作所操控,凸显异质性,否定同一律,解消历史的指涉作用。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读后感(三):后现代主义与史学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近现代历史开始了。近现代历史即是一部现代性萌芽、发展、扩散和固定史。(约14世纪至今)现代性精神——人文主义、宗教世俗化、理性、国家、科学、工业化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因”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概念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点,从中世纪没有主体性的人,发展到启蒙时代主张人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权利,主张人是有主体性的,待理性的火焰平静下来后,人们又开始反思人的本质,主张理性的过程中,人是不是已经把人性给束缚住了呢?于是新的一场反思开始,否定现代化的成果,主张回归人的本质,是为后现代思潮。(20世纪后期)
现代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弊端丛生,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欧美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建筑师开始思考都市文明、思考城市化,他们声称城市化过程已经束缚了人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异化”了人。这些反思因着同时代的其它思潮,例如机器的异化、战争的恐怖、电子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加速,二十世纪中期很多国家都进入了动荡期,慢慢的渗入了文学和哲学,随后又扩大到其它学科上。后现代浪潮就像一场海啸,席卷吞噬了几乎所有学科,导致了一场学科危机。
后现代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推崇尼采,所以称呼尼采(1844-1900)为后现代主义祖师爷应该是恰当的。(对尼采不熟)尼采应该是后现代思潮中一个重要的点,从启蒙运动中,卢梭埋下了浪漫主义的线索,发展到尼采,之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这股思潮终于被引爆。福柯、海登怀特、巴特、德里达纷纷发声。可以说,现代人的许多思考特质可以说即是后现代的烙印,如个性化、价值观多元、非主流、强调感性、恶搞、无厘头等等。
后现代主义是个延生性概念,史学属于稍后被波及到的一批;它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门学科存在的根由,在史学中就是要否定史料的真实性,宣布历史之死。
后现代史学冲淡了史料的价值,从而否定了史学求真的目标,并基于史料的虚构特点,向前一步追求史料解读的多元,追求叙事上的美(既然价值不在求真上,那就求美吧),甚至主张建构历史,即从当下的问题出发去研究过去;后现代史学着眼点也就随着对主流史料的否定转移到了“非主流”群体上,于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一下子扩大了,甚至历史写作者也一下子变多了;历史的虚构性还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后设叙述上,使得历史有了目的性、连续性、宏大叙事、结构功能和有意忽略事实的特点,后现代史学为打破意识形态的框框,申明历史是断裂的,哪有申明理性进程,过去才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层累的”。于是后现代史学接连发出了人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的口号,使闻者惊心变色。
史学可以说是从史料出发,到后现代这里,着眼点变为了文本、语言,甚至进一步,符号,也就是从客观(历史的指涉、对应)到了虚构(历史的建构),甚至不过是符号的游戏。
中国史学的发展感觉落后着西方一拍,我们还在为社会科学史学摇旗呐喊的时候,那边后现代已经攻城略地了。
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对史学的一次洗礼,经过一番否定的史学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但这股思潮对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的否定,史学该何去何从?拒绝改变从来就不是历史学的态度,但出路在哪?留给我们这代、后几代历史学人的任务可是太重了。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读后感(四):扔掉魔戒(摘抄)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12月。
由于个人成长的教育,盖属现代史学,因此必得预先涤除成见,做好精神位移的准备,以便就教于后现代的大家,故心灵备受煎熬。在完成拙著之际,仿若佛罗多(Frodo)上魔山,终得将无比诱人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扔下深渊,顿感超脱清爽。
若说三年的爬梳,个人有任何心得的话,那就是在知识论上,若现代史学旨在“追忆往事”,那么后现代史学,一言蔽之,则是主张“往事不可追忆”(the disremembrance of past)。读者在掩卷之余,自可知心体会。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后现代主义”(pastmodernism)系世纪末西方文化的一个殊相。它包罗万千,且无雅俗之分;在学术上,更跨越各个领域,是故要赋予一个简单的定义,并非易事。
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
真实的疯狂永远受压抑而沉寂不语的。(24页)
“考古学”,乃福柯一贯治史的秘方,从早期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即宣称;他无意写下“疯狂”一语的历史,代之却是沉寂的考掘。他甚至一度想以“结构主义的考古学”作为《事物的秩序》的副题。然而只有在后来《知识考古学》这部理论性的著作方得一窥“考古学”全貌。
要之,“考古学”于福柯,别有含意。一方面非如其希腊字源所示,寻求“初始”;另一方面,亦非如当今习用的深层“考掘”。“考古学”旨在探究论述的制度化或其转换,经界定表层论述关系,而毋需探索隐微、深沉的人类意识。
福柯复刻意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考古学”标榜的是“空间”(space)横面的安置,而非“时间”(time)的纵面的序列。试举其例,《临床医学的诞生》开宗明义便表明该书关注的是“空间、语言、死亡。它是攸关凝视的行为。”所以,“考古学”重视层次分明,而非纵贯的连续。德勒兹于评述《规训与惩罚》一书也说道,福柯与其说是位历史学家,毋宁说是位新式地图的绘制者,如此评论确有所见。(27-28页)
(天开:朱大可主编:文化地图,亦可视为知识考古的一种结果,甫列出各类文化并列的地图,并重视文化的空间,而非时间。)
福柯攻讦“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误以追本溯源为旨趣,其实本源、源起皆渺不可知。历史的本质乃是断裂、不相连贯,而史学的吃紧之处,即在观察断裂之处,这才是历史的大经大脉所在。
按“连续性”(continuity)实系传统历史命脉所系。祛除了“连续性”,则传统史学势将土崩瓦解,“进步”(progress)、“连贯”(cohesion)、“因果关连”(causality)均将无可思议,更遑论统合性的“整体史”了。(28页)
首先,“系谱学”绝非谈空说玄或凭空臆测。它与传统史学皆得仰赖大量的史料爬梳,方能察觉历史的脉动。所不同的是,传统史学深陷目的论,误以历史趋向既定的目标;或者执迷同一律,视历史为同质的历程,以恢复事件的根源为职志。
其实,事物的本质系歧异性(difference)的。“系谱学”遂以侦察事物的崛起、断续与转折为窍门。换言之,“系谱学”重视事物曲折、颠簸的“由来”(descent,Herkunft),而非一路无碍的“源起”(origin Ursprung)。(34页)
于福柯而言,“虚构”是无可避免的,即使他的书写纯属虚构,但并不意味真实(truth)逃逸无踪。虚构得以无中生有,制造真实,比方说基于政治的现实,人得“建构”历史,使政治变成真实的;反过来,基于历史的真实,人可以“建构”未来的政治。(42页)
柯林伍德:
每一个现在都拥有它自己的过去,任何想象地重建过去,都是以重建现在的过去为旨归。
(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revised edition ,p.247.其实柯林伍德与克罗齐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柯氏以研究罗马时期的不列颠闻名,克氏则专长近代意大利史。)(136页)
海德格尔复曾经如此开示过:
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
(Martin Heidegger,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B.Barton,Jr.and Vera Deutsch(South Bend,Indiana:Gateway Editions,Ltd ,1967),pp.60-61.(208页)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
梁氏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依照资料形成之早晚先后,区别资料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直接史料”意指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即已成立的资料。在史学论证过程中,“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
(228页)
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斯年(1896-1950)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6)
其实只要稍要对照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年至1514年拉丁与日尔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尤脍炙人口。兰克说: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
(Leopold von Ranke,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uk,1973),ed.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p.137.)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识”(wie es eigenlich gewesen),被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235页)
傅斯年: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5。)
胡适: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胡适,《胡适文选》,台北,1967年,页360。)
扩展阅读: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李泰芬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1939)。
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1979)即采纳了不少“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其内容不论在质或量上都较旧著要完备许多。另一本稍早的著作,许冠三的《史学与史学方法》(1963)亦把这些影响表现得十分显明,他说:
可是,我们今日的要求可就是严格了。除开所治领域的历史知识而外,史学家还得具有其它许多科学知识,“常识”是不够的。史学家的“共同必修科学”可以多到如下各科:
(1)逻辑学与方法论
(2)社会科学,或称行为科学,最主要的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
(3)自然科学
(4)哲学
(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香港,1963年,下册,页207。)(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