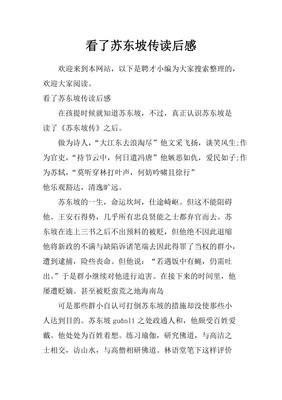
《剩余的时间》是一本由[意]乔治•阿甘本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剩余的时间》精选点评:
●哈哈哈阿甘本好可爱,本雅明登场了
●给译者一朵fafa,承前启后,恰到好处没有太多自我发挥。
●完全看不懂。。
●还不错
●亟待重看,不予评论。
●这本书是阿甘本的神学课程讲义,以政治哲学解读罗马书,从一个一个概念入手,对于罗马书进行解读,标题中的两个关键词 剩余 和时间,也是解读的重点所在。在阿甘本看来,基督降临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在此之后的时间与我们之间的关联。这些问题,对于国人还是太遥远了。
●第一次读的感觉还不错,现在对这个主题没什么兴趣了。我总感觉自己在晦涩的历史的哲学门前转来转去,进去坐下来,喝了一杯水,觉得无聊至极又离开了,可能不是它们有意要把自己弄的晦涩,玄妙,像康德黑格尔(阿甘本相比之下还是清楚得多),可能只是我太浅薄了。
●厉害是厉害,扯认知科学就有点鬼畜了吧
●龟速读完,赞译者。…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太多了。。不过不能被困于他的字句,语言与律法,潜在与现实,过去、意向与现时,要抽丝剥茧地慢慢理清关系啊。
●以阿佩利斯分割线重新解说末世论澄清了或许是偏见的偏见?略维特的确将弥赛亚主义等同于末世论。而在莫尔特曼对时间的韵律性理解或本雅明的“共时性”那里阐释弥赛亚要精微的多。理解基督教帝国阻挡末世论的努力是不容置疑的,这取决它以永恒之前的千禧年对自身进行的理解。是故罗马帝国破灭后的信仰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剩余的时间》读后感(一):剩余
作为剩余之民,生活在今时并使得救赎得以可能的我们,是拯救的“前提”。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正因此我们不是作为一种剩余而得救的。弥赛亚的剩余之民已经超过了末世论的全体,而且是无可挽回的;正是这种无可挽回才反而让救赎得以可能。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想到eva 并且非常感动
《剩余的时间》读后感(二):阿甘本或帕甘本或者其他——读《剩余的时间》札记
本文首发2019/4/17【四季书评】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5857.html
阅读阿甘本暗示了某种危险。在他层层叠叠对于文献的扫除过程中,一些古旧——或者起码是貌似久远的东西仿佛在逐渐显露出端倪。这让人联想到阿拉伯故事里擦拭魔灯的动作形象,你细致地擦拭魔灯的表面,时时勤拂拭,你逐渐被一些烟雾所笼罩……你并不知道你将面临什么境遇,甚至你难以分辨这一切是不是彻底来自阿甘本自身的障眼法。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疑虑之中,究竟是阿甘本注保罗,还是保罗注阿甘本?
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保罗书信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奠基性质的弥赛亚主义文本的地位”,从而阿甘本采取了一种本身就属于弥赛亚主义的写作形态。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历史主义的宏大志业。而在弥赛亚式的写作中,这一切被集中于《圣经》本文、保罗书信、《罗马书》直至《罗马书》的首句之中。以弥赛亚的方式来还原弥赛亚文本,就写作风格而言构成了一种封闭结构。这一切是去历史化的,以至于读者不可能将其置于常规的历史境遇中来加以阅读。这对读者构成了最初的挑战,他要求读者和他一起共同置身于一个弥赛亚主义的境遇之中,让时间自身的张力还原为整体阅读中始终保持的精神张力。尽管他不断强调《罗马书》里的经典开篇需要被仔细拆解,但同样也暗示了他这个拆解本身也应当回到相同的文本处境中去。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类似的做法被称为“注疏”,我们知道,“注”本身有灌注的意思,而“疏”也表明了拆解、疏通的行为。这里暗示了人的更新和分别,读者首先要对自己的阅读主权加以负责,是选择放弃历史主义的世俗时间,还是依旧留在这片大地上?
要是保罗书信作为弥赛亚文本的含义确实获得了还原,那么阿甘本的文字也毫无疑问也必定是属于弥赛亚主义的。同样,假如保罗书信能够以弥赛亚文本的方式来加以拆解,那么阿甘本显然也同样如此。若是一个源自历史主义的拆解,怎么可能洞察弥赛亚文本的质地呢?阿甘本是狡狯的,和保罗一样,他以一种二律背反的方式对读者的整全性提出了要求;同时,在拆解文本的过程中,再对这种整全性逐渐加以摧毁。
我们看到,在阿甘本所倡导的文本索隐过程中,暗藏了和弥赛亚主义同质化的宇宙论。当保罗在面对犹太传统、以及阿甘本在面对保罗传统时,都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不断自我镜像化的宇宙论之中。这个宇宙论旨在召唤我们自身——或许作为外邦人?——在历经弥赛亚时间中的漫长苏醒。要是我们同样操起阿佩利斯分割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在阿甘本同样在保罗的灵-肉传统之后,又作出了新的区隔。
这个区隔的界限来自于一个被人文主义浸染的世界和另一个犹太弥赛亚主义之间。在前者的传统里,阿甘本列举了一系列肇事者的名称,包括哲罗姆、路德、韦伯、阿多诺和布伯等。尽管未必去详细追溯其缘由甚或动机,但阿甘本直接宣称这串名称在对于弥赛亚主义的掩盖过程中所形成的层层堆积。他们以一种世俗时间里逻辑的严整性掩藏了保罗文本本身内在原初的基本张力,此处的世俗时间造就了日常理性,唯独阿甘本澄清,“若非”(hos meh)立场才是弥赛亚时间的准确逻辑。读者都熟悉阿甘本,这个“若非”实际上是他所提出的诸如“例外状态”、“牲人”、“剩余”等概念的核心逻辑。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并不出奇的概念不过是法式生命哲学的一系列后现代影子,但阿甘本将其辩护为来自保罗书信的历史回响。
这一串隐秘的弥赛亚线索隐藏在整个写作传统之中,从保罗到瓦尔特·本雅明,而阿甘本却试图来捕捉出隐藏在棋盘背后的侏儒小人。历史可怕的吊诡在于,那些试图去捕捉侏儒小人的人,最终往往被侏儒小人所擒获,反而成为其装置动力的全新部分。在阿甘本谈及本雅明的部分里,他指出了本雅明在“引文”背后所暗藏的神学逻辑,而他本人对保罗的注疏,实际上是以更多的引文来构成。无论是“引文”或是“注疏”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伪装形式,其背后依旧是来自于犹太弥赛亚时间的久远召唤。
在最终的天启降临之前,弥赛亚时间展现为一系列当下的碎片——这仿佛早就是来自现代哲学的陈词滥调,若是那样的话,阿甘本的著作就构成了一种彻底的自我重复。这是一种面向自身的福音传递,你面对镜子来传讲福音。阿甘本,保罗的仆人,奉召来传讲弥赛亚的福音。或者说,镜面本身就代表了这道阿佩利斯分割,区别了两个保罗、两个阿甘本,或者两种时间。
这是一个阿甘本,这不是一个阿甘本,这幅象棋又把回合交回到读者的手里。你听到的是侏儒小人的冷笑还是十字架上的哀哭,更简而言之,是存在还是死亡。你不妨粗俗一些,将存在看作马克思·韦伯的“Beruf”,或者选择(hos meh)的保罗主义,“说Beruf者,即非Beruf,是名Beruf”。阿甘本从对于诗歌韵文的溯源中找到了弥赛亚福音的痕迹,要是你在为阿甘本溯源的过程中仅仅停留在历史主义的空间里,那总不像是好的理想读者。当然了,一个理想读者,总要像不是一个理想读者,反之亦然。但是,只有真正的理想读者,才可能洞悉其中的秘密。
可以说,弥赛亚式的写作总是在自反和重复中进行。在这个问题上,谁都爱引证卡夫卡的短篇“法律门前”。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在卡夫卡的故事里,全篇只不过是为最后一个瞬间的出现而事先铺陈的连篇废话。只有最后的时刻代表了意义和时间的全然爆炸。当最后一个时刻降临时,此前的一切都被否定,化归乌有。同样的寓言形式,在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小说《渴望健康的人》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只不过后者在叙述和文学性上更强大的特点,恰恰削弱了作为弥赛亚文本的表达力量,正如阿甘本在批判阿多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好像’的形式下把弥赛亚事业审美化”。这一指责,事实上同样适用于本雅明,以及阿甘本自己。一旦落入历史主义的语境之中,美学化几乎是必然的命运。我们知道,基督的来临总是背负着十字架而前行的。每一个弥赛亚主义的作者,总要背负起十字架的命运。在卡夫卡、本雅明、朔勒姆或者朋霍费尔那里,读者似乎都看到了显明。在巴塔耶、布朗肖或者阿甘本那里,我们还在等待吗?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肉身消亡的激进问题,真正所牵涉的不过是写作自身的折射出的忧伤感。作品的标题叫做《剩余的时间》,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身处“剩余的时间”中的阿甘本,一个“剩余”的阿甘本。只有在自身的剩余性获得表征的时刻,他的论述才真正获得其独特性。这样说,唯有被纳入一个去独特化的自我重复的系统之中,他的独特性才能得到彻底彰显。这就像保罗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划分一样,阿甘本说:
“活在弥赛亚中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弥赛亚生活呢?弥赛亚降临时刻的结构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保罗的问题,也必然是我们的问题。”
这才是问题。对保罗来说,罗马之路不是问题,唯有大马士革之路才是真正的问题。扫罗没有问题,保罗才构成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之路只是弥赛亚时间中无数当下之路中的任意一路,罗马书信也不过是无数历代文本中的任意文本,但大马士革之路仅此而已。要是缺失了大马士革之路,扫罗始终是扫罗,阿甘本也不过是阿甘本,谁都无法辨识《罗马书》,更无人来辨识阿甘本的絮絮叨叨。但是弥赛亚总是在人所未知的时刻降临,直到阿甘本宣布:我,Agamben,又叫做Pagamben,……
或者其他。
尤雾
2019年4月5日星期五
《剩余的时间》读后感(三):剩余
阿甘本认为,整个《罗马书》文本的含义都浓缩在了开头的那句话:Paul,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called to be an apostle,seperated to the gospel of God(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作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这句话又可再浓缩为“剩余的时间”,换言之,那是超越了时间的时间,是真正的时间,属于默西亚的时间。保禄书信无疑是在宣告默西亚时代已经来临。
阿甘本通过诠释罗马书第一句话中的每一个词,得以抓住整个罗马书的核心要义。
“剩余”的意思
剩余,首先是从划分开始的。罗马书的表述有一种很明显的划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选民与外邦人。划分尤其是通过犹太律法进行。在犹太人的世界,法律的基本划分是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在犹太人的历史中,法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划分建立起所谓的真正的继承犹太人血统的天主选民。在这种背景之下,保禄却要直言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罗马书的普世意义贯彻始终,默西亚本就是属于“大公”的。默西亚需要消除这种人为的法律划分,保禄对法律的批判也因此在罗马书中达到顶峰。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对于耶稣所说的“不是废除法律,而是成全法律”就不会产生困惑。
书中有段精彩之处,即默西亚的箴言可以看作是阿佩利斯分割,把法律划分为二。保禄通过灵肉之分,把所谓犹太人法律的划分再彻底地划分,即划分本身的划分。正如保禄所说的:“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罗9:6)。于是犹太人这个群体有了显性的犹太人和隐蔽的犹太人。在阿佩利斯分割的效果下,原本犹太人法律的划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变得模糊,不可分辨。这个效果同时也是默西亚意义对法律的划分引入了一个剩余部分。这个“剩余”不是指数量上的,我们得从认识论上来理解。默西亚意义划分出来的余数,不能被归于原法律划分之下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而是双重否定之下的第三项。默西亚主义的划分并没有达到共相,相反,却是一致的不可能性。划分本身的划分,为普遍和特殊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保禄学说里的大公主义与现代普遍主义迥然不同,其本质上不是消除一切差别的原则。默西亚的使命召唤不是要给每个个体提供另一种身份,而是在其个体自身内产生张力——不能被归于任何一种非灵肉的划分。大公主义(默西亚的普世意义)既不是要消除一切差异,也不是要触及终极的根基,只是一种剩余。
剩余之民
阿甘本认为保禄从以色列先知那里复活了“剩余”这个词。先知的语言里也存在着某种悖论似的东西,先知面对以色列选民说话,仿佛这是一个民族的全体,但与此同时又宣布只有一部分剩余之民才能得救。理解悖论似的先知预言,如果只是以为这个“剩余”是数量,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同样也要从默西亚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剩余之民既不意味着全部以色列人也不是指其中的一部分。剩余之民是指一个状态,剩余之民不是转向未来,好似一个带有末世论意味的阐释。剩余关系到了当下的经验,尤其从保禄的语境里更能够体会到默西亚主义,正是这个经验定义了“今时”、“此刻”。就是在当下经验到的,决定了剩余之民的产生。
剩余之民不属于末世,而是意味着当下的得救。其意义是一种不可撤销的情形,也可以理解为当下的我们已经得救了。默西亚的拯救是一次而永久的有效,超越了末世,这亦是天主恩宠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被拣选的以色列子民与被拯救的以色列子民是一回事,都是剩余之民。以色列子民不再是从法律划分上去理解,而是从默西亚意义的角度理解。以色列民族,不再是狭隘的指向犹太人,而是指向了信从福音的万邦。剩余之民,正是以色列民族的本质。
剩余的时间
一个非常容易出现的误解就是把先知的预言、天国的启示理解为时间的终结。末日,顾名思义是最后的一日,有关末日的讨论形成了末世论,甚至把它与默西亚主义混淆了起来。当末世论迅速地演变为世俗的末世论,这种混淆是较为普遍的。
这里不妨先思考一下,保禄为何称自己为使徒而不是先知?使徒与先知的身份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先知所讲的都是预言,而使徒所说的是默西亚的到来。先知的预言必须保持沉默,但使徒的宣告则说明了预言已经实现。由此我们理解,默西亚的时代或默西亚的时间不是某个终末的时间点,而是指现在,是终末的时间。终末的时间意味着它自己的减少。这种减少,又再次让我们看到“剩余”的涵义,对时间划分的划分。默西亚的到来,是天主的拯救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把人类的时间划分为默西亚之前与默西亚之后。我们现在通用的纪年法“公元”,原意就是基督纪年,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开始。在儒略历与额我略历中,在耶稣诞生之后的日期,称为主的年份(Anno Domini,简写为A.D.)。而在耶稣诞生之前,则称为主前(Before Christ,简写为B.C.)。当时间自身被划分时,默西亚时间就是停留在了那两种时间当中的时间,默西亚的时间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每一个今时、此刻。
虽然默西亚的时间是世俗时间的一部分,但不是说默西亚的时间与世俗时间完全一致。为了让读者弄清楚这一点,阿甘本借用了语言学家居斯达夫·纪尧姆的时间概念——运作时间,来以此说明默西亚时间的特征。简单来说,每一种通过心智活动的思想,都蕴含着一种运作时间。无论这种心智活动有多快,总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就算一瞬间的念想,那也是需要同样真实的时间的。默西亚时间就好比这种时间,往往容易被忽略,也很隐蔽,但它不属于流俗时间,不是从外部加进来的时间。如果说人类历史本身是时间的表象,那么默西亚的时间是一种时间内的时间,与表象的时间不同。我们凭借这种时间内的时间,从而获得了自己的表象时间。换言之,表象时间正是基于这个隐蔽的内在时间而被构造起来的。正因如此,默西亚时间才是唯一真实的时间,它超越了一切时间的表象。它在表象时间(或称之为历史)内运作,我们凭借它走向终点,也就是人类历史走向了自己的终点。我们所能真正把握的,不是表象的时间,而是真实的默西亚时间。默西亚时间是世俗时间的一部分,更是永恒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余数,与两边时间划分相关联,它同属于这两部分,但又不完全是任何一边的时间。所以,阿甘本认为把默西亚时间理解为末日之后,恐怕有些不妥。
默西亚事件已经发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得救,但尚未圆满。已经-尚未的悖论存在着默西亚主义独有的张力。我们从运作时间的概念角度去理解,才能看到默西亚“当下”或“今时”的真正意义。本雅明说:“每个瞬间都可能是让默西亚走进来的小门”。默西亚事件的发生和存在是时间延长了的临在。默西亚拥有他自己的时间,他同时也让表象时间成为他自己的,并将其实现。表象时间终究会被默西亚时间终结,这个终结是剩余时间的缩进,而这个过程就是默西亚救赎的实现。那意味着在时空的有限性中,天主对世界的拯救将全部完成。理解默西亚时间的意义,对理解天国的到来很有启发。
默西亚的法律
天主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诫是立约之法,也是救恩的应许。使徒传报的福音是应许所承担的默西亚时间的盟约形式,是新约。我们有一种印象,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禄,在谈论法律时,都充满了矛盾和悖论。耶稣诠释了法律,让这旧约中的法律看上去好像是被废除了。在罗马书中,保禄亦有对法律的严厉批判。我们难免会产生困惑,信仰是反对法律的吗?
法律、信仰和应许彼此之间密切相联,默西亚时间的到来绝不会叫天主的应许落空。哪怕犹太人将天主诫命演变为僵硬的形式法律,这种法律自身也存在着超越规范性的东西,并且无法还原到规范层面。这就是最纯粹的法律,信仰之法。所以犹太人的律法并非一无是处,或曰毫无信仰的精神。默西亚的来临让法律中的规范性层面不再起作用,唯有这样,纯粹的法律才会被突显出来。犹如法律中被掩藏于深层的潜能得到了激发和实现。保禄把这称之为法律的废止和保留,实质上是摒弃僵化的法律实践,复活法律的内在精神。如此,默西亚的法律不能再通过法律规范层面的执行来定义。因此,信仰并非对抗法律,亦非对法律的否定。
默西亚时间作为一种运作时间在表象的时间里引入延迟,默西亚的法律作为信仰之法、纯粹的法律,它在演变为僵化的法律中也引入了废止,即一种停滞。通过延迟和停滞,让默西亚时间和默西亚法律得以被我们所把握,这种把握恰恰是一种开放性。
默西亚时间终结了表象的时间,默西亚法律成全了原本的法律。
《剩余的时间》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第一天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这本书的目的:“首先,这个讨论班课程意在恢复保罗书信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奠基性质的弥赛亚主义文本的地位。”(p1)
陶伯斯《保罗的政治神学》(2004),“由于我们也同样主张把弥赛亚降临的时刻解释为历史时刻的一种范式”(p3)
保罗所使用的希腊语,“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说明,保罗的语言以及他的犹太-希腊群体,和18世纪的西班牙籍犹太人文化以及19、20世纪的德裔犹太人文化,作为构建着犹太散居地的一支来说,都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p5)“他的语言既不是真正的希腊语,也不是希伯来语,同样不是所谓的‘神圣语言’(lashon ha-qodesh)或世俗方言,而这就使得他的语言极其引人注目(尽管我们现在还未触及到罗马书在弥赛亚主义中的地位问题)。”(p6)“对保罗来说,时间的缩减,‘剩余’的时间(林前7:29:‘时候减少了’)表征着弥赛亚的超越地位,他是唯一真正的时间。”
保罗的名字paulos
参考亚伯兰到亚伯拉罕(被高举的父亲,繁多),撒莱到撒拉(我的公主,一位公主)的名字转变,是一种身份的更新。
“保罗”的意思是“小”,而“扫罗”则是皇族名字。“改名实现了由使徒清晰而坚决地表明过的、决不妥协的弥赛亚法则,根据这条法则,在弥赛亚降临之时,软弱和卑微的事物会战胜世俗界以为强大和重要的东西(林前1:27-28)。弥赛亚把专有名字从人身上拿走,从那时起,人就只能有个非正式的名字,一个昵称了。自保罗以后,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只是记号signa,只是别名了。”(p13)
奴隶的名字都是主人一时兴起给起的。“在弥赛亚的召唤使一个自由人变为‘主的奴仆’的时刻,使徒必须像一个奴仆一样,失去他的姓名,不管是罗马名字还是犹太名字。”奴隶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境和罗马语境中的细微差别。“对保罗来讲,doulos不仅意指世俗法律下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指这种状态在和弥赛亚降临事件的关系中所发生的转变。”罗马法大全,所有的人,不是自由民就是奴隶。
“在保罗那里,‘奴仆’得到了一个特定的含义(正如在’基督的仆人‘中,或是相当于门1:16说的‘高过奴仆’)。‘奴仆’一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作为弥赛亚降临的结果,一切由法律法规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对自由和奴役间的区分,届时都将荡然无存。”(p16)
第二天 奉召kletos
马丁·路德把这个词翻译为beruf,被韦伯采用,这是一种世俗化的转变。原本只是指从上帝或弥赛亚那里派来的任务,通过路德,开始有了现代的职业含义。“在路德看来,世俗职业正是上帝寄予人的命令,使其完成相应于世俗地位所加诸其身的种种义务。”kletos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和今天所谓的世俗“天职”毫不相干,韦伯如此分析。(p26)
天职与废止(Vocation and Revocation)——这一部分写得精彩,在p29。不详细记录。
分析另外一个词,林前7:29-32 hos me(要像不),这是关于弥赛亚生活的一种表述法,也是kletos的终极意义。
“天职不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地点因此它可能与人们在其中蒙召的实事状况相符合,但也由此原因,它从头到底整个地废止了这种状况。弥赛亚的神圣天职宣告了一切事业的无效。它以这种方式定义了对我来说似乎唯一可以接受的职业。一个废除了每一项具体实事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呢?这显然并不蕴涵着用一种更正当的事业取代一个不太本真的职业。……”(p29-30)
“保罗对比了读财产的弥赛亚式的使用usus;因此以要像不的方式驻留在事业中,就意味着不要把事业变成一种所有权的客体,只要能用它就行了。因此对保罗来讲要像不不只有否定的内容,恰恰相反,这正是世俗职业的唯一可能的用途。弥赛亚事业不是一项权利,也不提供某种身份,而是一类可用但不可占有的潜在性。和弥赛亚联系起来,生活在弥赛亚中,意思是通过要像不的方式让渡每一种律法-实事的所有权(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自由人/奴隶、男人/女人)。然而这种让渡不导致人们获得一个新身份,‘新造的人’无非就是对以前身份的使用,让它接受弥赛亚的感召(林后5:17)。”(p34)
邓斯·司各脱借自阿维森纳的关于偶然性的戏谑笑话:否认偶然性的家伙应该被一直折磨到他们承认本可以不被如此折磨。(p49)
第三天 分开aphorismenos
“保罗在把自己定义为aphorismenos,即一个被‘隔离’的人时,他以一种尽管有些残酷的反讽口气,暗示和自己身为一个法利赛人的过去已经一刀两断了。他说到这件事,而且用另一种隔离的方式否定它,这种隔离已不再是按照律法来讲的隔离,而是按照弥赛亚的福音来讲的隔离。”(p58)
第四天 使徒apostolos
参考居斯达夫·纪尧姆的《时间与动词》,对于时间的概念的理解。“人类的心智经验到时间,但它并不拥有时间的表象,为了表象时间就必须求助于空间规则。随之而来的是,语法表象动词时间的方式是把它画作一条无限长的线,由过去和未来两个片段构成,两者中间被当下一分为二……”(p81)
kairos和kronos,p85-86
《希波克拉底文集》说,“在kronos中有kairos,而在kairos中没有多少kronos”。一个重要的字汇表达。
预兆typos,可以指印记,雕刻的肖像,原型或草图,甚至抽象的形式、风格、体系等等。很好的字汇分析。
诗歌与韵律,这个部分挺好玩的。不详细记录。
第五天 传神的福音
第六天 传神的福音
“信仰”(或信任)是一个人对他者享有的信用,是对他者信任的结果,是把自己像抵押给他那样托付于他,让这种抵押把我们连结在忠贞不二的关系内。因此信仰就像信任一样,是把我们让渡给某人,是对某人的信任,因为我们代表他人享有的信任就是我们拥有的信仰或信用。(p141)
信仰与誓言在古代密不可分的关系。
erit约——这一章比较难懂。
开端,抑或尾声……
(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
再附上关于通用希腊语的一篇笔记。写于2016年11月——
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Παῦλος δοῦλος κλητὸς ἀπόστολος ἀφωρισμένος εἰς εὐαγγέλιον θεοῦ.
这句话总共10个单词,发音如下:paolos dulos yesu kristu kletos apostolos aforismenos eis iuanggelion theu.
会发现这些单词读起来似乎是押韵的,就是词尾很多发音一样的比如os、u等,这不是巧合。
古希腊语和任何一门语言一样,都具有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先说语音。古希腊语语音非常简单,会读24个字母就会读单词,而且能读文章了。因为,基本上,每个字母都有固定的对应发音。
再说词汇。这是古希腊语比较令人抓狂的一点,就是词汇量大。汉语常用词语大约3万个,足以表达各种语境。但是古希腊人词汇有20万个。为什么这么多呢?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思维精确,近似词语非得严格区分不同的含义,最常用来说明的一个例子是“爱”(love),中文关于“爱“这个词的表达被公认是比较贫乏的,但是古希腊人发明了agape(神圣之爱,圣经常用),philia(兄弟情谊,比如费城、哲学),eros(男女之爱,欲望),storg(亲情之爱),还有近似的epithumia(欲望之爱,偏于邪恶)这五个词,当然不止这五个。另一方面是因为希腊语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则有“态”“语气”“人称”的变化,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只需要变化词尾就可以互相转换,比如agape是名词,agapao是动词,agapetos是形容词“亲爱的”。这种变化有多少呢?古希腊语老师说,你能记住两千种词尾变化,古希腊语就入门了。
语法的复杂和词汇是相关的。名词有阴性、阳性和中性三种。有单数、复数。并且,名词有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五种格。也就是说一个名词,如果词尾变化了,它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就不一样了。比如开头的例子第一个单词paolos(保罗)是以os结尾,必须记住这个词的词性(阳性)、格(主格)、数(单数),否则翻译就出错了。这是根据什么判断出来的呢?就是这个os词尾。所以这是一个单数阳性名词,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因为他是主格)。
继续看第二个词dulos(奴隶),是不是很熟悉os结尾呢,对,这也是一个阳性、单数、主格的词。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个主格词,那岂不是有两个主语?稍等一下。第三个和第四个词,yesu kristu(耶稣基督),有没有发现不一样?词尾是u,这和词尾是os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两个名词,都是阳性、单数,但是它们是属格(又叫所有格),用法近似于形容词了。修饰前面的dulos这个单词,所以连起来就是yesu kristu的dulos。
那么,现在出现了两个主语词了,谓语在哪里呢?找动词就好。第五个单词kletos(被召的)和第六个apostolos(使徒)我们跳过,因为它们也是单数、阳性、主格,和前面两个主格并列的主语。这下子就出现三个主语单词了,是不是很热闹呢?
第七个单词aforismenos(被派遣),动词终于出现了,这是谓语。别看他的结尾是os,就把他和前面的名词词尾os弄混了,其实这是动词的os结尾,代表这个单词是……(此处需要强烈注意)完成时态、被动语态、 分词、主格、单数、阳性!这仅仅就是从词尾os看出来的!为什么是主格、单数、阳性呢?因为要和前面的主语(还记得吗?也是主格、单数、阳性)相搭配,所以主语谓语都得是主格、单数、阳性。而时态、语态也要通过词尾来看。得亏这儿没有人称(有六种变化)和语气(四种变化),不然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单词翻译为“已经被派遣”。
把前面的这七个单词连起来就是: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被选召的使徒,已经被派遣……
期待下文的自然会问:被派遣干什么呢?最后三个单词eis iuanggelion theu,第一个是介词,正好把前面“被派遣”和后面要做的事情连起来,要做什么呢?就是iuanggelion theu,通过跟前面一样的的语法分析,我们就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神的福音。所以,整个句子的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通过以上分析,这个句子无论是翻译成德语、法语、英语还是汉语,可能在某些单词上会有些不同选择,但是,说实话,就算你想把这个句子翻译错都不大可能了,因为每一个单词、每一个词尾都提醒你,这个句子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古希腊人形成极其精密的哲学思维与他们语言中的这种精确性是有关系的,他们说话不会含糊。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中国的例子。比如“你吃饭了吗?”同样是这五个字,如果我们用不同的语序来处理,所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你,吃饭了吗?”“吃饭了吗,你?”“饭,你吃了吗?”所以不能单纯用主谓宾结构来分析这个句子,虽然主语是你,谓语是吃,宾语是饭,但是说话的时候强调的词不一样,含义就不一样。这一点在上面我们举的古希腊语例子当中就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古希腊语要表达情绪,会使用“呼格”这种词尾变化,所以,还是语法上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以上举的例子是两千年前通行于地中海地区的通用古希腊语(coine greek),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古典希腊语,古典希腊语可是比我们上面列举的例子在语法词汇上更加复杂,也就更加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