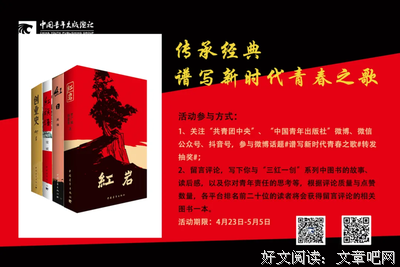
《三种文化》是一本由杰罗姆·凯根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4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种文化》精选点评:
●很痛苦的读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然后我直接跳过前几章,直接看的最后两章。感觉作者的逻辑布局很差,一段话会掺杂多个不相干学科的例子,堆砌感很强,没有清晰的目录结构,作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写作框架,而且结论都是些很空洞的东西,仅仅了胜于无。作为大学人文读本稍显艰涩,作为研究视野认识拓展文本,显得较为鸡肋,一篇长文即可讲清楚的事情,堆成了一本书。
●心理学家为了证明一目了然的情感判断,使用庞大的数据;经济学家忽略显而易见的常识,挑拣听话的例子塞入数学模型。
●有许多地方还不甚理解。
●内容基本是各学科分支的介绍。对于如何磨合三种学科,只是模棱两可地提出了包容和谦卑等主张。
●作者是学心理的,前边几章涉及到了许多生物和社科研究,不太好懂。相比较而言,人文学科和最后一章好懂得多。写这种书不容易,作者往往要有多学科的研究经验。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种共同体,可以互相学习,但是不要尝试统一,因为它们是三种文化
●美国如是,中国也如是,自然和人文学术之间的裂痕不断的加大:一词多义现象最为普遍。。。。这本书最好的在于它的时代比较接近于现代,而且数据比较清晰。自然科学家典型的忽视非字面的引申意义。这个翻译者的文化水平值得商榷,很多关键概念的翻译显得没有文化
●在这本书上纠结了三天,总之和我期待的差距很大。一开始对这三种文化的比较超级有兴趣,一头扎进去马上就淹死了——完全不知道这句话和上句话有什么联系的感觉!!完全不知道这些段落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思路,每句话也要反应半天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和题目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你到底在说啥?经常列举了一堆某人的某研究,但是有啥关系啊?! 肯定是我的水平不够啊!!!可是作者作为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对这么广泛的题目进行论述,会不会有些力不从心? 反正我是frustrated and confused了。(私以为翻译肯定没把这书看懂过 = =) ps,最后作者怀疑200年的三种文化共同发展都没有使人类生活的更好 Orz
●诚如作者所论述,三种文化各有其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贡献,评价三种文化不能割裂开三者间的联系,在三种文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种文化的特质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我猜作者大概是社会科学的背景吧
《三种文化》读后感(一):三种文化——对两种文化的补充
我们对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印象很深刻,也一直将学科草率地分为“文科”和“理科”两类,往往忽视了一些同时具备文理两科性质的“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即社会科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不断壮大,自然科学仍处于人类文化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则日渐丧失其地位。这些现象,在凯根的书中得到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凯根对文化的现状并不满意,他最后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学术研究的话题,分析了三种文化内部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冷漠和冲突,强调回归大学的传统使命,加强三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三种文化》读后感(二):文化演进之路
1959年,C•P•斯诺在“瑞德讲坛”(Rede Lecture)发表了现在十分有名的《两种文化》的演讲,这是对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事实的反思:智力生活分成两种文化,一边是艺术和各人文学科,另一边是诸自然科学学科。从那以来,另一种文化,通常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第三种文化,即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专业领域已经变得重要起来。杰尔姆•卡根的书刻画了这三种文化中每一种文化的各个假定、词汇和贡献,并论证说:每一个共同体所使用的许多概念的意义对它自己的方法来说都是独特的,因为证据的来源有助于意义的形成。本书总结了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我们理解人类本质的贡献,并怀疑以下流行的信念:生物学过程是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种文化》读后感(三):文化演进之路
本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对某种“科学主义”的批判,即有些人把个人的一切缺点都归之于基因或遗传,许多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数学模型看成解决人类或各个国家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它不可能变成自然科学,要不就得改名字,不再叫社会科学了。世界上真的存在像物理学那样的“纯粹的”社会科学吗,研究人的行为怎么可能离开对人的关怀或忽视人的因素的作用呢?物理学能预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几分几秒发生日蚀或月蚀,有哪门社会科学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做到,人类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不会有当前仍在发生作用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了。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信非常有助于我国学者更全面地形成关于三种文化的作用的观点。
《三种文化》读后感(四):从“两种文化”到“三种文化”
在金斯利•艾米斯著名的校园小说《幸运的吉姆》一书最开始的部分,有一个令人捧腹的桥段:拼尽全力想要在某大学历史系争得教职的年轻教师吉姆•狄克逊,与掌握其生杀大权的威尔奇教授坐在汽车里讨论他的一篇题为《论1405年至1485年间造船工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的论文,威尔奇教授对狄克逊在自己论文价值上的含糊其辞表示了极大的困惑:“你,唉,文章有什么价值你自己都不清楚,那怎么行呢?”
对威尔奇抛出的这个要命的关于研究价值的问题,狄克逊的口头回答是:“是的,我不清楚,教授。”
但他真实的想法却是:“恰恰与此相反,狄克逊却觉得自己对文章的价值,从几个方面来讲都是很清楚的。首先,可以简单地说文章毫无价值;其次,文章的价值在于对历史事例进行了发疯似的盘根究底,而在罗列事例时却又发狂似地使文章写得枯燥乏味……”
突然迸射的激烈反讽,以及吉姆在装模作样的学术交谈背后内心的抓狂(写这种历史论文已经叫他抓狂,更何况还要回答关于研究价值的烂问题),使读者在看到这一段时大概都会笑出声来。而对那些对大学里所谓文科学术研究抱有怀疑的人而言,读到这段文字,大概会感谢吉姆以这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吧!
《幸运的吉姆》被认为准确地捕捉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气味”,吉姆无声的反抗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正如该书中文版前言中指出的:“吉姆与威尔奇父子的冲突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具有更广阔的含义,即它是吉姆代表的(中下阶层)社会势力与文化或文化的精英性的冲突。”或者可以说,吉姆以自己的方式向当时大学中的传统精英文化发起了一场正面攻击,并最终取得了个人的胜利。
在艾米斯的小说出版之后6年,1959年,另一位大学文科精英文化的反对者,C.P.斯诺,在著名的题为《两种文化》的公开演讲中,批评了“文学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不理解。尽管在演讲中他一直试图用“两种文化的分裂”或“互相不理解”来表明自己超越两种文化并试图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但是他对技术科学及专业技术教育的亲睐显而易见,这背后当然也有没有在演讲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对所谓文学知识分子的敌意。
无论是《幸运的吉姆》所代表的新兴社会(工商业)势力对大学文科精英文化的反动,还是《两种文化》所揭示的自然及技术科学家与文学知识精英的对立,两位作者矛头所指的似乎是同一个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大学内外学术及话语权势的消长。小说中的吉姆很幸运,他最终得以从大学的泥潭中脱身,投奔企业界,并成功地抢走了文化精英的女朋友。而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艾米斯和斯诺也有着与吉姆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大学里待过(斯诺曾在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艾米斯也曾在大学教书),但两人“墙外开花”后,都脱离了大学,而在围墙之外找到很好的饭碗,艾米斯成为畅销作家,斯诺更成为著名公众人物。
时间又过去了50年,其间,《两种文化》引发的讨论热潮甚至在中国都已褪去,艾米斯也有了诸如戴维•洛奇这样的校园小说继承人,2006年,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这让他想起了这本书在50年前出版时引发的热议,以及这50年中大学和学术界的各种新变化,于是,便有了眼前这本《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斯诺的两种文化,是指“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种群体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而凯根的三种文化,则加入了在西方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繁荣发展的社会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语言学(可能会令某些学科的学者不满的是,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甚至通篇都未被提及,大概凯根认为这些学科不能成其为学科)。凯根在书中介绍了三种文化各自的关注对象、证据来源、所使用的概念、语义网络等,并指明了这些学科对人类智力进步及整体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这些学科自身面临的困境。
与斯诺的《两种文化》相比,凯根在《三种文化》中的论述更为丰富、严谨。他不像斯诺那样在心中暗暗设定一个“靶子”,而是近乎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对三种文化展开讨论。当然,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身份使得他不可能完全隐去自己的立场。在前言中,他提到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三类学科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自然科学家可以得到慷慨的给予,提供给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资金却相对少得可怜,这种不对称创造了身份上的差别,侵蚀着分权原则,驱使着两种较无优势的文化采取防御性的策略。”
作为“较无优势的文化”的一分子,凯根这本书中也是他“防御性策略”的体现。他对社会科学所作贡献的申辩令人印象深刻。在第三章中,他用了一节的篇幅,谈论“社会科学的贡献”。或许因为专业背景所限,他提到的贡献,例如“纠正生物学和人文主义者的错误信念”、“重新评价人的不同发展阶段”、“驳斥人的早期经历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等,似乎大部分是心理学的贡献。
在讨论了社会科学对人类理解自身和社会方面的智力贡献之后,凯根提到的社会科学自身的问题更值得注意。正如他在前言中提到的,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科学黄金期,社会科学家一度认为“他们的思想可能解决某些折磨着这个社会的棘手问题……然而,把弗洛伊德的概念与更加以经验为主的行为主义的各种严格的观念拙劣地综合起来的做法太脆弱了,无力实现他们的愿望……最终,该脚手架倒塌了,社会科学家失去了一件保护性的理论外衣。”社会科学既无力发展合理的理论来解释社会问题,又“缺少大家一致同意的概念和研究重点”,并且“有过早放弃某个问题的习惯”。后面这个问题似乎更严重。他形容为“许多社会科学家就像充满异国情调的集市中不耐烦的游客,从一个摊位奔到另一个摊位,不断地被另一个摊位上更加吸引人的手工艺品所迷惑。”因为兴趣点转移得太快,对某种现象的解释便无法形成智力上的累积进展,这严重制约了社会科学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凯根似乎在提醒我们:要想缓解目前三种文化的隔阂,要想提高“较无优势的文化”的地位,以及与优势文化抗衡的能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首先应该反思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做大做强”,别再“打肿脸充胖子”,那样不仅会被优势文化鄙视,连公众也要看穿你虚假的学术外衣。
作为一项包罗万象的总括性考察,本书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研究者的论述比较少。但是,我们对一个学科、一种学术文化的信念,从根本上说,是对这个文化中的人的信念,更直白点,是对在这个学术体制中讨生活的人的信念。可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凯根用了很多口舌来说服读者,要承认“较无优势文化”的贡献啦、要加深对三种文化的理解啦,等等,在我脑中久久徘徊的,竟还是吉姆那副玩世不恭的死样子。
他就在那里,在威尔奇教授的汽车里,发狂似地大喊:“我的论文根本没有任何价值!那不过是混饭吃的垃圾!一件学术强迫症的产物!”
参考书籍:
杰罗姆•凯根 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两种文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金斯利•艾米斯著,谭理译,《幸运的吉姆》,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