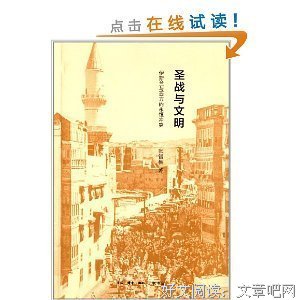
《圣战与文明》是一本由张锡模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圣战与文明》精选点评:
●将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两条线合并成一条,理论性很强,适合中东学入门。可惜只写了这三部曲第一部作者就去世了,但是渊博浩瀚的世界史积淀,不愧为登辉的文胆
●以往的历史教材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实在是少得可怜,直接将中国与西方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断层现在一提起中东,一提起伊斯兰,我们想到的大多是石油、恐怖主义、战乱,完全是标签化的刻板印象,中东(包括近东)作为连接亚欧大陆两端的枢纽,其历史应该得到重视。 第四章应该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了,尽管关于原理的论述读起来比较烧脑,但确实是很有收获的;第六章则给我一种疲累感。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值得认真“啃”的书。
●学究气十足,但写得极为清楚。可惜三部曲只完成一部,张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梳理史实 短小精悍 台湾作者 后面几章印刷错误较多
●历史造就。
●意外发现,惜乎作者心愿未筹,10星高赞!
●讲述了伊斯兰教从兴起,壮大,扩张到衰落的历史,同时阐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的价值观和国家体系观。伴随着殖民运动的开展,以及欧俄两大强权的争霸,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被强行植入了伊斯兰世界,这造成了如今中东地区,中亚地区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不断。伊斯兰文明在强盛时给予了西方以知识与包容,但在其衰弱时,来自西方的回报却只有掠夺与分裂。伊斯兰教靠着众生平等的思想联合起了欧亚众多民族而崛起,但后来在意识形态上却因为不能统一各种教派思想,在世俗政权上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帝国政府,在国家体系上又面临欧洲民族主义带来的版图破碎化,而逐渐衰弱至今。归根结底,相比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的人的彻底解放,穆斯林的个人意志至今仍然被禁锢于宗教的意志之下,宗教思想的停滞不前导致整个伊斯兰社会的保守与败落。
●这是伊斯兰角度的世界史,未曾如此深入中西亚那片土地一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任何土地似乎都存在一层厚厚的政治雾霾,历史上某些时刻某些人物的一个举动,可能我们当今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汽车,手机都可能是别的形状。可惜本书只写到一战,后面这一百年的历史变数,更为激越。
●真的超级好看
●作者是以世界史的视角写中东史,同时大量使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分析方法,让人时时都有醍醐灌顶的快感。力荐!
《圣战与文明》读后感(一):伊斯兰需要一场宗教革命
讲述了伊斯兰教从兴起,壮大,扩张到衰落的历史,同时也阐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的价值观和国家体系观。伴随着殖民运动的开展,以及欧俄两大强权的争霸,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被强行植入了伊斯兰世界,这造成了如今中东地区,中亚地区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不断。伊斯兰文明在其强盛时给予了西方以知识与包容,但在其衰弱时,来自西方的回报却只有掠夺与分裂。伊斯兰教靠着众生平等的思想联合起了欧亚众多民族而崛起,但后来在意识形态上却因为不能统一各种教派思想,在世俗政权上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帝国政府,在国家体系上又面临欧洲民族主义带来的版图破碎化,而逐渐衰弱至今。归根结底,相比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的人的彻底解放,穆斯林的个人意志至今仍然被禁锢于宗教的意志之下,宗教思想的停滞不前导致整个伊斯兰社会的保守与败落。不来一场宗教革命,伊斯兰很难有复兴的希望。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多做活塞运动和女人的子宫上,面对穷凶极恶的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只是徒增肉靶耳。
.
《圣战与文明》读后感(二):内外的分化与结合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内容是jihad和civilization四五百年的历史,“文明”在我们现实中属于褒义词,在这部书中应该理解为中性词。也就是说,文明的褒义性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发扬的(取经日本)。jihad即圣战,是中东穆斯林对内外的划分—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civilization即文明,是欧洲基督徒文明对内外的划分—文明和savage。我们可以依此类推,得出华夷之分是中国汉人对内外的划分。
本书徐徐展开了对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的记录,指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自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正如同基督教一样,覆盖的范围和民族越广,因此而产生的宗教也就越分裂。两个巨型宗教在不停地膨胀、碰撞中发展。伊斯兰教最早出现平等意识,早期欧洲的文明也经过中东的火炬点燃了,然后欧洲内部的对抗和对伊斯兰文明的对抗逐渐使得欧洲实力越发强盛,诞生出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也日趋激烈,合纵连横在欧洲乃至亚细亚地区一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欧洲的高度发达文明湮没了伊斯兰文明的高度,以state意识和民族意识冲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欧洲内部的竞争日益向外围世界展开,在炮火声中拉开了近代史。
《圣战与文明》读后感(三):关乎伊斯兰,更关乎欧洲
本书作者生前计划写作《伊斯兰与世界政治》三部曲,本书为第一部,所覆盖的历史时期始于伊斯兰兴起,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全书七章,去掉第1章导论与第7章结论,中间主干部分有五章,其中第2、3章主要讲伊斯兰,第4、5、6章其实主要讲欧洲。这里的“主要”讲谁,首先是看讲述的对象是谁,但有时候这些对象是同时登场、相互影响的,那么这时就要进一步看,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谁是更主动的一方。
第2章整体上讲伊斯兰教的兴起。前半章大部分是讲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近中东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后续各种历史发展所起到的最初始的先决作用。近中东既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起源地,也是伊斯兰文明的起源地,于是这一部分也就包含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早期互动。后半章才开始讲伊斯兰教的诞生,讲到四大哈里发之后的什叶派与主流路线(应该就似乎后期的逊尼派)的分裂为止。讲这个分裂既是揭示伊斯兰诞生之初的一种“先天不足”,还可能是为了在三部曲的后续内容中讲当代什叶派国家与逊尼派国家的矛盾做一个铺垫。
第3章是最纯粹的“主要”讲伊斯兰的一章。从早期的阿拉伯帝国,到随后的奥斯曼土耳其、萨法维波斯、莫卧儿印度三大帝国,对外扩张主动施加影响的一方是伊斯兰。但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宗教上的统一与认同,与现实中语言、部族、乃至教派(此类冲突在这一历史时期还不强烈)的多样性,又形成难以化解的矛盾。当整个伊斯兰世界对外扩张之时,还能靠着不断地分享战利品来保持内部团结,一旦扩张停止,内部多样性带来的分裂就在所难免。阿拉伯帝国在超出阿拉伯半岛之后就难以为继,而当整个伊斯兰世界达到顶峰覆盖西起东欧北非,东至中亚南亚这一广阔地域时,也必须以三大帝国来共同支撑。作为对比,我种花家几千年历史中固然分裂时期也不算少,但大一统王朝总是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疆域内断续相继,前后呼应,逐步强化了对统一的认同。
第4章开始,叙述的“主要”地位转移到了西欧身上。即使本书三部曲是以伊斯兰为“主要”的,即使在前两章中讲伊斯兰兴起时完全可以略过与之同时期的混乱的中世纪欧洲,但从这一章起,推动下一阶段历史前行的力量已经在欧洲形成,对伊斯兰的叙述也已经绕不开欧洲了。作者在后续的章节中逐步展示了西欧国家体系中多个关键要素的形成,在本章前半章重点展示的正是其中第一个要素“主权国家(state)”体系的形成。这其中又包含着从“属人主义”到“属地主义”的国家界定方式的转变,国际关系上的相互认同(解决体系内部问题),打着“文明开化”旗号的对外扩张(解决体系外部问题)等多方面问题。虽然本章后半章提到了阿富汗的兴起,但这也是整个伊斯兰衰落大势下的小片段,不过是伊斯兰世界中大配角和小配角的争斗,而历史的主角已经变成了西欧。
第5章和第6章内容的更像是一体。但第5章正如其章节名“原理的转换”,除了部分的叙事,但更重要的在于论理。所论之理,正是从上一章“主权国家(state)”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nation)”,以及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的民主/共和主义。所叙之事,则是从莫卧儿印度开始,到奥斯曼土耳其为终,其共同的主线则是讲英国和俄国(部分时间也牵扯到法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展开“大竞赛”,欧洲大国之间来回上演军事与外交攻防,夹在中间的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在外部承受着竞赛双方的撕扯,在内部则承受着西欧“民族国家”新体系的冲击,逐渐风雨飘摇。
第6章继承着第5章的叙事,讲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境遇,如何在萨法维波斯、莫卧儿印度、阿富汗、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地区不断重现。所以我认为这一章标题“伊斯兰与世界政治”起得并不是太好,如果换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世界大竞赛下的伊斯兰全面崩塌”。这里还要特别注意一下巴尔干、高加索等地,这几个地方在地缘上其实都属于欧洲的范畴,但在今天它们却有着一个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相同的属性——火药桶。换言之,在这两百多年打着文明开化旗号,输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中,获益的也不过就是西欧的那几个大国和俄罗斯,而遭殃的不仅仅有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有一大堆东欧小国。这时再想想我种花家,要感谢自身基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共识与汉民族独大的人种主体,也要感谢在地缘上处于英俄“大竞赛”的远端,还要感谢进入现代之后胜出的共产主义道路依托阶级划分而具有超越民族的属性,最终能在今天延续了大一统,而没有出现太严重的分裂。
但这样的故事仍在继续下去,虽然作者已没法再写三部曲的后作了,但他在本书的第1章导论就揭示了——当今世界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对苏联-俄罗斯(近几十年来还得加上我种花家了)的围堵,其实也就是两百多年前英俄大竞赛的延续。但两百年前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由西方国家自己讲述出来的,表面上非常动听的“主权”“民族”“民主/共和”等理念,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建立在对外侵略、奴役、牺牲他国的基础之上。而那些被征服、被“文明开化”的国家,在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之时,就简单套用西欧民族国家这种新体系,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所以我种花家在政策选择时也更应该慎重,走好自己的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东欧到伊斯兰世界的麻烦不断,在近几年正以欧洲绿化、恐袭频发的形式,让那些早年对外侵略作威作福的西欧强国们自食恶果。许多表面上由伊斯兰世界而起的冲突,早年的麻烦制造者都是欧洲自身。所以,这本小书,关乎伊斯兰,更关乎欧洲。
《圣战与文明》读后感(四):近代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互动
本书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作者是已故的台湾中山大学副教授张锡模,比较理论化,后半部分不太好读。主要写的是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和西方世界体系的冲突和互动,重点探讨近代西方形成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伊斯兰世界,而伊斯兰世界又是如何应对与变革的。作者在《自序》中说到,他是想借助理解伊斯兰世界,然后来检讨和反思当代的世界政治秩序观,并指出当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中蕴含着导致这种体系崩溃的关键因素:权力和正义的不相关。 一、伊斯兰发展史及其相关概念 作者先是简要叙述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历史:从穆罕默德创教、四大哈里发,再到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再到近代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萨法维王朝(1501—1763)和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并重点叙述和分析伊斯兰的世界观和政治秩序观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在伊斯兰世界里有两大最基本的原理:“安拉是唯一的真神”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根据第一条原理,穆斯林必须皈依、信仰与遵循安拉的启示与教诲,而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中介,是穆斯林个人与安拉的直接关系,因而伊斯兰教没有像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那样的教会体系存在。而第二个原理则则规定着所有穆斯林之间的水平关系,即安拉的启示由其使者,并且是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传达,并且所有穆斯林之间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穆斯林都必须遵奉五功与六信,所有人都必遵从真主的教诲。伊斯兰教自诞生起,《古兰经》里就不仅规范着穆斯林的精神生活,而且对他们的世俗生活也作了诸多规定。更重要的是,在部落林立的阿拉伯世界里,因为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从而不同家族、氏族和部族的阿拉伯人才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了阿拉伯帝国,并不断向外扩张。在伊斯兰的世界观里,世界分为“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顾名思义,伊斯兰之家就是指由所有穆斯林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而战争之家则是指除伊斯兰世界之外的由其他宗教和文明所组成的世界。按照伊斯兰教的理想,伊斯兰世界是要逐步扩大的,所有穆斯林都有义务向外传教,到最全世界都会变成“伊斯兰之家”。而将“战争之家”转变为“伊斯兰之家”的努力,也就是不断地将世界“伊斯兰化”的行为,被称为“神圣的奋斗”(Jihad),这也是圣战的最初含义。而把穆斯林描绘成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古兰经》,强迫世界史所有人都接受伊斯兰信仰的的形象是不对的,那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人为丑化穆斯林而塑造的。事实上,非穆斯林并不总是被迫改宗伊斯兰教,有些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的魅力而自愿改宗,如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的萨珊王朝后,原本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纷纷改宗伊斯兰教,正因为伊斯兰其教义里崇尚公平正义和人人平等的精神,远比波斯社会严格的阶级分野更有魅力。如果说倭马亚王朝时期整个阿拉伯帝国还是以是不是阿拉伯人作为区分不同等级居民待遇的重要标准,那么到了阿拔斯王朝时这一标准边已不存在,这时帝国的统治原理已经换成对于伊斯兰的信仰与否,彻底成为基于共同的伊斯兰信仰而形成的伊斯兰共同体,与其说它是阿拉伯帝国,不说是伊斯兰帝国。 本书重点叙述的是近代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与互动。近代的伊斯兰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种种战争与分裂,逐渐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教派,还有乌拉玛集团这样的宗教学者团体,以及基于《古兰经》而形成的伊斯兰法律体系。此时的伊斯兰世界主要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帝国这三大帝国。在此时的伊斯兰帝国里,统治者利用乌拉玛集团来强化个人的极权统治,乌拉玛集团便成为整个社会力的核心转轴。在三大帝国统治后期,由于“伊斯兰之家“作为统一性概念与三大伊斯兰帝国长期分立的事实,还有伊斯兰共同理想与统治者自身腐化以及帝国本身的衰退之间的矛盾,导致穆斯林之间的政治认同产生危机。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崛起并逐渐向东方扩张,危机中的伊斯兰世界体系遇到西方列强的殖民支配,伊斯兰法统治论与伊斯兰价值遭到西欧国家的冲击与否定,大大加重了伊斯兰世界的危机。 二、西欧国家体系的建立及发展 西欧国家体系的建立始于十五六世纪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冲突,确立于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书中有关国家体系的讲解如下: “所谓的国家体系指的是国家(state)相互关系的总和,整个体系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的横向关系所构成。其成立与运作乃建立在国家主权(sovereignty)的概念、国际法原理,以及权力平衡政策等三个基石之上。在这个体系中的基本单位是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这些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原理,形式上由国际法规范,实质上则以权力平衡政策作为体系成员彼此互动的最核心考虑及外交活动中心。在此一体系中,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中心,至少在法律形式上是如此,即法律上各个主权国家皆平等。” “主权国家体系的特色是:这是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而非由人民所构成。主权国家的国家(stato)原型是起自于意大利国家体系,后经由马基雅维利(Niccol Machiavelli,1469—1527年)的理论化,指涉及统治者及其统治机关的组成,而其统治对象是特定领土(territory) ——不动产,并基于对于特定领域的支配,进而支配居住在该领土上的人民。国家对于此一领土及领土之上人民的总体支配,对内享有最高属性,对外具有排他性,即所谓“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原则。以一统治者及其统治机构对于特定领土及其上之人民享有排他的、绝对的、永续的权力,在法兰西理论家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年)于1576年出版的《国家论六卷》(Les six livrex de la republique) 予以理论化之后,便渐次被接受后而称为主权。” 可以看到,主权国家体系中所谓的“国家”指的是“统治者和统治机关”,并不包括该国领土及领土上的人民,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对象。这样一来,再经过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于统治技术的的阐述,政治问题就完全变成了单纯的权力支配问题。因此,自文艺复兴发现了人的价值以来,再经过宗教改革,西欧社会打破了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世俗权力收归于君主,再通过主权国家体系的建立以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对于权力应该如何运作的阐发,西欧的绝对主义王权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并积极对外进行殖民扩张。 在西欧主权国家体系崛起并对外扩张的同时,“文明”的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武器。所谓的“文明”原本是指法兰西宫廷圈统治集团的风尚,用以区别于宫廷之外社会大众的“粗鲁不文”,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与进步史观相结合,并在其概念中加入了“主权国家体系”以及这些统治主权国家的绝对君主之间的一套游戏规则——“国际法”。从此,“文明的欧洲”取代了“基督的欧洲”,而这些君主主权国家的共识就是正义(即宗教,就是基督教,最终的基础是上帝)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因此由西欧国家奠定的世界政治秩序观的基本立场就是不得以神的神圣名义来干预主权国家的运作,唯一的神圣性来自于王室,而王室的所有权(领土)不容(平民)侵犯。因此,在西欧国家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时,就利用这套理论来合理化他们的侵略行为,以“文明”的名义去对非欧洲地区进行“文明开化”。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理论首先就冲击到伊斯兰世界,由于文明概念的存在,这场冲击就不仅要求受到冲击地区的人民从肉体上被征服,更要求其在精神上也必须向来自西欧的征服者看齐与效法,这就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三、西欧国家体系对伊斯兰的冲击 就在近代伊斯兰三大帝国逐步衰落之时,经由工业革命洗礼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逐渐入侵和瓜分伊斯兰世界的领土,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在英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大竞赛”之下,波斯与阿富汗沦为英俄两大国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与对方建立权力平衡而设置的“缓冲国”。由于领土不断被分割与殖民,奥斯曼土耳其也沦为“欧洲病夫”,成为列强眼中的“东方问题”。同时,西欧的主权国家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冲击,“君主主权”被“人民主权”所取代,革命政府又进一步将“人民主权”转变为“国民(nation,民族)”主权,这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所有人从君主转变为抽象的民族。从此,国家的主人翁、国家领土的产权持有人就变成作为抽象集合概念的民族,民族国家诞生。 在欧洲列强的强权冲击之下,奥斯曼土耳其开始进行改革自救,但无论是其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还是在政治上作出想把“伊斯兰帝国”转换成欧洲式的“多民族国家”的努力,在各种原因之下终究没能成功,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瓜分与肢解。在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冲击之下,伊斯兰世界原有的世界秩序观逐渐被抛弃,同时,由于引进了更为排他性的民族国家理论,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各个民族都产生了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用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支配以及其他势力的压迫,这样,奥斯曼土耳其最终走向了分裂解体的结局。 奥斯曼治下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希腊,接着,巴尔干半岛的众多斯拉夫语系民族纷纷谋求建国独立。在巴尔干半岛,由于缺乏民主共和机制,在列强的干预及各自领土与民族矛盾的不断冲突中,造成民族的定义与领土范围的主张越来越带有强制性与恣意性,于是民族主义退化成更为排他的种族主义。“大希腊主义”、“大保加利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等“大”型的民族主义纷纷出现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领土要求,于是,巴尔干半岛逐渐变成欧洲的“火药桶”。此外,土耳其语言民族主义也出现了,而突厥语系涵盖的范围除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更是包括了中亚、中国新疆、乃至北亚部分地区,这样造成土耳其民族主义很快走上了大(泛)突厥主义的道路。 四、伊斯兰世界的应对 在伊斯兰世界逐步被西方主权国家体系冲击,并逐渐被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影响与改造的过程中,除却因自身的衰弱而被征服之外,对于穆斯林来说,他们原有的伊斯兰世界观从根本上被否定,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危机。在基督教的理论中,并不认为世俗权力和必须以上帝作为理论根源的正义之间必须有直接关系,所以天主教会可以与各种林立的世俗政权并立,当基督教世界的某一政权被穆斯林征服时,这种政治上的危机并不会转化为宗教意识上的危机。继承罗马法而来的近代西欧法律体系,认为法律根源于社会契约,因而法律只规定人的外在行为,并不管控人的精神世界。然而与此相反,伊斯兰法并不是来自于人类,而是来自于真主安拉的启示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传信,因而它不仅规范着人的内在精神,也规范着穆斯林的外在行为,两者无法完全分离,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权力与正义直接相关。遵循伊斯兰法是穆斯林的基本义务,而政府的运作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必须以维护伊斯兰法为前提。 因此,在面对欧洲国家体系压迫与殖民扩张时,伊斯兰世界便遇到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伊斯兰共同体的衰弱是否意味着伊斯兰信仰本身的弱?即便是,这也不能推翻“安拉是唯一真神”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两条根本原理,于是伊斯兰力量的衰弱就被归因于穆斯林对伊斯兰的理解不够正确和深入,以及对伊斯兰的实践做的不够好。这些成为前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的的主要出发点。 其后,这股思潮又进一步发展,在复兴传统与实行欧化之间诞生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运动。但是,在此运动中,伊斯兰一直以来存在的两大原理之间的矛盾又凸显出来:领导人原理与信徒平等原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因为“安拉是唯一真神”,这就要求所有穆斯林必须遵从安拉的启示,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那么就应该遵从穆罕默德所传达的安拉的启示,这就是“领导人原理”;但另一方面,穆罕默德毕竟也不是神,而且伊斯兰教规定所有穆斯林都人人平等,这就是“信徒平等原理”。权力与正义的直接关联、领导人原理与信徒平等原理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对欧洲国家体系对伊斯兰世界造成的冲击,而当思想侧重于团结穆斯林来抵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时,伊斯兰信仰的精神便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差异,凝聚起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来保卫伊斯兰共同体,而当思想侧重于改造穆斯林社会时,便不可避免地让位给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如果缺乏民主机制,势必会造成像巴尔干半岛那样失败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困境。 五、尾声:欧洲国家体系的困境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还说到欧洲主权国家体系自身的困境。欧洲国家体系在打破基督教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此政治生活由人类自己管理,不再仰赖神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绝对主义王权坐大,兴起了绝对主义的主权国家体制。随后为了制约专制王权,又经过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的理论阐发,清算了绝对主义王权思想,建立了人民主权论的思想体系。但是与伊斯兰世界不同,源自西欧的主权国家体系没有将正义与权力联系起来,尽管在国内的权力运作受到自由主义和各种相关机制的制衡,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却未能建立起能够制约强权国家滥施暴力的相关机制。在西欧国家体系向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曾将将阿富汗、波斯和巴尔干半岛等弱势地区打造成大国之间的缓冲国,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但其最后不但没能避免冲突反而使得冲突更加升级和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说明了主权/领土国家体系的运作中所蕴含的体系性危机。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其中涉及的内容却很多,而且叙述的精准简练。书中既有对伊斯兰发展史的梳理,对伊斯兰的宗教与政治理论作深入的解读,又对近代三大伊斯兰帝国和欧洲列强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作出精彩分析,并重点介绍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以及伊斯兰世界所作的回应,最后以“权力与正义”的理论视角考察并指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欧主权国家体系各自面临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