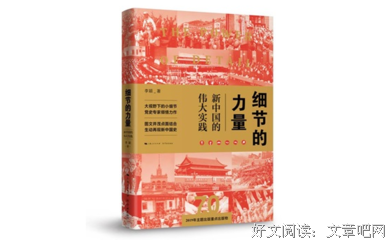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一本由[加]C.B.麦克弗森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精选点评:
●非常不同寻常的解读,(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尽管可能有所夸大,但我还是基本相信这种解读的力量,洛克的部分写得很精彩。
●囫囵吞枣其实没怎么看明白,争取有机会再读一遍
●哪里有卖的?
●really perfect. 尤其喜欢对霍布斯和洛克的解读。 但是,对霍布斯的解读,私以为忽略了当时的群众运动。而对洛克,则忽略了“改良”土地这一关键概念,也就没有注意到更确切的资产阶级性质,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型的大地主。
●清晰的解说
●当成解经书看的,对十七世纪英国政哲,尤其是霍布斯的堪称劲爆的解读;洛克财产权部分文本扎实(但推论部分还是糙),其他的有些草率了;结语的结论有意思,但批判太短了,应该在其他作品中展开了,期待继续翻译出来,这本书翻译的不错,王涛老师果然是行家哈哈 ps马克思很多观察确实很有洞见,但遗憾的是后来的共产国际不重理论就成了教条,好东西就被西马拿走用辽;这个意义上麦克弗森就是写了本复刻版《英格兰内战》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论证自由主义的缘起与缺陷所在,比起教条式的马克思,麦氏著作显然更有学理性,也更有意思。看他和伯林、萨托利的论战就更有趣了,甚至于有人都认为麦氏不是所谓的“西马”,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证的liberal。可惜我的读书报告写得挺没意思的,唉,3、4天赶出来的粗糙活,居然也没被导师骂。
●西方语境下的 只看了洛克部分 不知道是翻译还是我脑子的问题 看起来有些绕
●好看
●从圆桌派听到这本书,再追过来看,世界上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解析霍布斯部分,能帮人理清楚几个影响很久问题的思路,其中争斗与猜疑部分,其实很亲切,分明就是大刘的“黑暗森林”和“猜疑链”理论,值得去慢慢啃的书。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读后感(一):《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C. 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基本主张: 十七到十九世纪之间的英国政治思想有着潜在统一性,可称之为“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前言);社会预设对于十七世纪政治理论有着重要作用但并未得到重视4,这些理论家并未陈述全部预设的原因包括(读者理所当然有着相同预设5;作者并未意识到6;故意隐藏7),所以分析工作应该集中在作者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一不一致而非逻辑上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将被我们当作寻找预设的线索8
第二章 霍布斯:市场的政治义务
·霍布斯之所以可畏不是因为他难于理解,而是因为他的学说那么清晰、那么绝对,却又是那么令人生厌9
·对霍布斯的攻击:唯物论和政治理论的关系如施特劳斯1963;心理学原理和政治理论关系并不一致,但正如奥克肖特说不应该奢望在霍布斯身上找到对十七世纪作者来说实属陌生的融贯性11。
·霍布斯的自然人实际上是社会人、文明人,证明:描述的都是社会中的行为(如插上门、内战);自然状态的起因竞争猜忌荣耀都是社会中有的【此处论证草率】22-27;霍布斯笔下缺少的正是文明生活的全部物件,自然人就是仅仅去除了法律束缚的文明人30。
·霍布斯的困境:是否是所有人都天生渴望更多权力?施特劳斯将其处理为两种对权力的追逐,其一为非理性的,其一为理性的45;(麦克弗森的解释)说明其除了生理设定之外还需要社会预设,霍布斯或多或少有意识将其作为他的社会模型48-9;霍布斯的社会模型即“占有性市场社会”,即人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人的精力和技术是他自己的,并不是其人格不可分一部分50.
·霍布斯的彻底全新立场:柏拉图以来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从人的能力和需求中间接推断出来的,即从人的能力需求推导出假设的自然目的或神的意志,再从自然目的或上帝意志推导出人类义务和权利;但霍布斯反转了这一假设,堪比伽利略的贡献,即仅仅从人的运动这一事实推导出权利义务;不可能从外部或上部来施加一个价值体系,拒绝为人的需求加上道德差异。
从这个角度,其政治学说和唯物论的联系就明确了:78-9运动对每个机械装置都是平等必要且运动之外别无他物;所以在基本和纯粹的层次上,人这一机械装置都有运动的权利;而由于之间运动减损的持续冲撞,那么纠正措施(即一整套道德性义务体系)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一推论使得从事实推导出权利义务成为可能
但是,运动必然排斥其他运动的设定并未出现在其唯物论中,必须引入新的市场预设。80
·批评霍布斯:其没有看到市场社会中的阶级凝聚力能抵消碎片化力量,因此误导其结论:自我持续的主权机构是必要的。95【此前麦克弗森论证自然人为文明人,推论自然状态为文明状态;但此处忽略了自然状态本身为了消解阶级等约定的逻辑意义】
第五章 洛克:关于据有的政治理论
·对洛克的错误解读
立宪主义:洛克的国家实际上是合股公司;强调洛克为了保护财产权对政府的限制,而不强调其赋予政治社会对抗个人的极大权力。
对此相反的解读则认为个人无权利对抗多数主权,所以洛克不是个人主义者(W.Kendall)。这一解读也有问题,其将多数民主原则附会进洛克的思想中了。
→我将论证洛克对十七世纪人性和社会本质存在特定先见;他对这些先见做了非历史性的普遍化202-4;第五章移除了自然法的限制,将自然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基础上,然后又从财产权利中移除了一切自然法的限制,成为无限据有的自然权利。207
·无限据有的论证
货币移除了其最初对个人据有正当化论证中的固有限制:1腐坏限制,货币可以不断囤积,洛克的重商主义主张(将土地和货币用作资本;货币投资原材料)【此处论证不足。逻辑上,货币作为作为食物腐败的克服,能否解释成反过来移除了限制?如果能,那么后面必须加一段洛克本人对无限制的明确态度的材料,但此处的材料是洛克的其他文献:《论降低利息》】212-3 所以洛克超出需要的占有欲既不是守财奴的囤积欲,也不仅是消费更多不同和令人愉悦的商品欲,而是积累更多资本的欲望。216【洛克的爱欲解读】(洛克的推论:可以假定人类可以拥有商品经济而无需一个正式的政治社会;货币契约有效性不应归因于国家,而应该是人的自然理性)218-9
2充足性限制
3假定的劳动限制。一个人的劳动是他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可以自由地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224;洛克的论证:sect28、在自然状态中就存在大块地产;自然状态中基于自然权利的财产权在政治社会中依然有效。225-7
·→洛克的成就
“一个人的劳动归他自己所有”是洛克财产学说的根本创新,这为整个资产阶级据有提供了道德基础;随着两个初始限制被移除,这随之就成了对不平等财产的自然权利和无限个人据有自然权利的正当论证;同时,个人的据有权优先于社会的道德要求(如慈善等社会义务)的观点就被削弱了。230
·自然权利与理性能力的差别
《政府论》一开始对人性的表述和对人性的分析并没有暗示一种阶级差别预设。但随后的自然状态中,不平等财产已经导致了不平等的权利241;在理性能力上也有差别,因为理性行为的实质是勤勉的据有,完全的理性就只能为无限积累的人独有(依据,财产权第一阶段劳动有彼此蕴含,共同构成理性行为;第二阶段后劳动就不再意味着据有,尽管据有意味劳动)243 ;勤勉的据有者并不贪婪,侵犯她的人才是贪婪的,所以洛克对贪婪的谴责是他“无限积累是理性能力的实质”这个预设的结论而非否定246
·自然状态的矛盾
一方面是战争状态的反面,一方面又等同于战争状态【此处含糊,没有文本;驳 战争状态是一对一,自然状态是自然人的共存;所以削弱以下论证】洛克没有采取一个立场250。洛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头脑里有两个社会概念,虽然逻辑上冲突(平等的无差别生物;根据理性能力划分的阶级),但源于同一个终极源头。252 这一含糊不清与相互矛盾,准确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心理:要求形式平等与实质权利不平等 256,;亦即他尝试用普适性(非阶级)术语来表述带有阶级内容给的权利义务260.
·解读其他矛盾
1合股理论。将洛克笔下国家解释为合股公司的理论不再成立,因为合股者的多数决议约束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雇员;而雇员不能以所有者参与运营 261
2多数统治与财产权。联系背景,洛克的理论是在内战期间提出,一切有财产的人都认识到将两者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洛克的多数统治和财产权主张并不矛盾,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是“多数人”和政治社会的正式成员。262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根本上说洛克的个人主义在于个人成为他自己人身和能力的自然所有主,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但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必然是集体主义(在主张政治社会高于个人的意义上),只有在积累财产中才能实现,所以必然牺牲其他个人的个体性;要使其运作,政治权威必然高于个人。265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天平两端而无需考虑社会发展阶段是一种肤浅且误导的观念;洛克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此时的个人主义越彻底,集体主义越彻底
4立宪主义。洛克旨在捍卫扩大财产的权利而非个人对抗国家的权利266
总结:洛克不可能意识到,他所捍卫的个体性同时是对个体性的否定;我们在刚刚开始了解到个人自由的重大可能性的脑中是找不到这一认识的;矛盾就在那里,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他,更遑论解决。而十七世纪自由主义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主张自由和理性的个人是良善社会的判断标准,而其悲剧在于这个主张必然否定半数国民的个体性。271
二十世纪的困境在于当市场社会的结构不再为我们从占有性个人主义预设推导出一种有效政治义务理论提供必要条件时,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还必须使用这些预设。283所以要么拒绝占有性个人主义预设,但这样的理论将不真实;要么保留它们,但这样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义务理论。284
评论:当成解经书看的,对十七世纪英国政哲,尤其是霍布斯的堪称劲爆的解读;洛克财产权部分文本扎实(但推论部分还是糙),其他的有些草率了;结语的结论有意思,但批判太短了,应该在其他作品中展开了,期待继续翻译出来,这本书翻译的不错,王涛老师果然是行家哈哈 ps马克思很多观察确实很有洞见,但遗憾的是后来的共产国际不重理论就成了教条,好东西就被西马拿走用辽;这个意义上麦克弗森就是写了本复刻版《英格兰内战》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读后感(二):【转】弗兰克·坎宁安: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导言
Crawford Brough Macpherson (18 November 1911 – 22 July 1987)克劳福德·布拉夫·麦克弗森(Crawford Brough Macpherson)这部广受好评、名至实归的作品所采取的总体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麦克弗森孜孜耕耘于政治与经济问题被看作是紧密联系着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这也是哈罗德· 拉斯基(Harold Laski,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指导了麦克弗森的研究生学业)的研究方向。麦克弗森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本科学生,而自1935年直到1982年退休,他是该系的一名教授。在多伦多,他最为杰出的长辈同事是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英尼斯对大宗商品贸易在塑造加拿大国家方面的分析,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学成就。英尼斯亦被认为是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先驱者,他用这个理论为政治经济学增添了文化之维。我们必须将麦克弗森置于这个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之中。对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来说则更是如此。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处理了(在17 世纪英格兰要求经济政治改革的)平等派运动的观点,和在同一时期为士绅主导的共和国声辩的詹姆斯· 哈林顿的观点。麦克弗森把他们的理论置于英格兰当时正在经历的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中来加以考察。他主张,这一变革既促进了一个“占有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出现,同时又被这种世界观的出现所强化。按照这种世界观:
人的实质是免受任何关系(为自己的利益而加入者除外)束缚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只有出于其他人自由的需要才能被正当地限制。个人是他自己人身的所有者,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他有让渡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不得让渡他的整个人身。社会是一系列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政治社会是一个用以保护所有者和有序调节他们之间关系的契约性工具。(第269 页)
这一世界观在麦克弗森所谓的“市场社会”中具体实现了;在这一社会中,市场关系“塑造了或渗透进了一切社会关系”,劳动力被视作劳动者(他们以其工作能力换取工资)的“可让渡的占有物”(第48 – 49 页)。显而易见,麦克弗森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刻画,融合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元素。政治社会履行着保护和调控市场社会的必要经济功能。占有性个人主义信条提供给了人们下面这个标准化灌输而形成的自我形象——能力归自己私人所有且只对自己负责的自由个体。
本书不仅或不主要致力于诠释经典;它是麦克弗森为了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去理解和解决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而对这些观念的起源所做的研究。把这一作品与麦克弗森此后的著作——特别是《民主理论》(Democratic Theory,1973 年)和《自由民主的生命与时代》(The Lifeand Timesof Liberal Democracy,1977 年)——配合阅读,可以说明他的这个目的。从1962年出版《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到撰写这些著作的这一段时期,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已无处不在,足以软化资本主义市场更为坚硬的边界;而有人就会质疑,麦克弗森反对市场社会的理由是否过于夸张。在今天,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遗产(看来)还有充足的力量能够挺过经济危机(正是这份遗产使经济危机变得可能),所以占有性个人主义处处会遭遇到它。因此,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麦克弗森对其起源的考察,可谓正当其时。本书布局直接明了:麦克弗森根据下述前提来解读关键性文本,即我们最好将关键性文本理解为明确或隐含地表达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各个方面。由于这些解释与对文本的常规理解背道而驰,所以他通过细读文本来支撑自己的分析。
对霍布斯政治理论的一种传统理解是:处于前政治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是自利的权力追逐者;由于缺少政治约束,他们就处于相互战争的状态中。霍布斯自称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原则推导出这个论点,而麦克弗森提出了下述相反看法:霍布斯是把他在17 世纪英格兰看到的文明特性归给原始的自然状态:“自然人就是仅仅去除了法律束缚的文明人。”(第29 页)在这种文明状态中,一切经济互动行为开始由市场促成(而非由习惯或中央政治分配促成),而“权力”特指人们相对于另一个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强制其他人将他们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使用权转让给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欠缺这种强制能力)。所以说,自然状态效仿了市场社会。假使这样一个社会完全不受调控,它就会自我毁灭。霍布斯看不出市场社会内部有什么办法能确保调控,所以他规定市场社会完全服从于一个政治权威。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麦克弗森突出了霍布斯下述鲜明主张:“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麦克弗森的解释是,对霍布斯来说,一个个体是诸项能力的集合,而能力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一个权力市场”(第37 页)。
写到平等派时,麦克弗森质疑了他们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名声。他反而首先将他们视为个人自由的拥护者—在他们那里,自由意指“一个人对他自己人身和能力的所有权”(第142 页)。平等派确实为人民票选政府而奋斗,但对他们而言,选举权仅限于那些保留了对自己能力使用权控制的人。这既排除了赤贫的领取施舍者,也排除了“雇工”,而雇工主要是让渡了其能力使用权以换取工资的工人。这就把选举人比例限制在当时英格兰成年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与此相似,哈林顿不仅剥夺了赚取工资者的选举权,他甚至还剥夺了他们的共和国(他极力主张消除共和国内部的阶级均势)成员身份。因为哈林顿为士绅声辩(麦克弗森将士绅视为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所以霍布斯那里没有的阶级分析因素就被引入其中了。按照麦克弗森的观点,这是解决霍布斯面临的“如何调控一个市场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它考虑到了统治阶级(它能够为保全社会而约束自己)的凝聚力。
通过聚焦洛克的财产权概念,麦克弗森将洛克誉为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democracy)和个人权利的拥护者。对平等派来说,人们的能力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如果他们没有其他资产,他们就要出卖其能力的使用权以换取工资。洛克还有一个更宽泛的财产权概念——把财产(property)描述为一个人的全部生命、自由与财产(“地产”),还是将其仅仅描述为一个人的财产(possessions),洛克对此摇摆不定。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摇摆为洛克的政治观点所不可或缺。人民(即复数的人,men)出于保全其财产的目的,缔结契约形成政治社会。只要这里指的是广义财产,它就适用于社会中的所有人,所有人就由此受政治性法律的约束。但是,这些法律仅仅是由那些持有狭义财产(即在财产/estates 意义上的财产)的人通过的,因为洛克还把选举权限于拥有私人财产的人。(第247 – 251 页)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打算保留自然法所蕴涵的那些先前的道德传统。尽管人们通过“注入其劳动”于物品上而获得财产权,但自然法规定,为避免腐坏,他们不能把多于其个人能利用的东西据为己有,并且必须为其他人留下“足够的和同样好的”。麦克弗森通过说明洛克如何找到去除这些限制的方法,证明了洛克有资格被当作一位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家。按照洛克的说法,随着货币(人们可以积累货币,而货币不会腐坏)的发明,人类通过“默示同意”允许人们积累多于个人需求所要求的东西。其后果是放松了“为其他人留下足够的和同样好的”限制。此外,洛克提出了涓滴理论(thetrickle-downtheory)的早期版本,即生产率的最终提升将会惠及每个人。麦克弗森认为,洛克并非宽宥贪婪的囤积,而是在为以贸易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据有行为声辩。(他提到,洛克不仅是位理论性的重商主义支持者,他还在贸易公司持有大量股份,包括奴隶贸易。[第253 页])
麦克弗森主张,其研究进路的一个优点是提供了一种方法,以说明他处理的理论家们所存在的表面不一致之处,如何能够—即使不是被克服,至少是—被理解。针对霍布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全然自利的个人如何能够将其权力交给一个共同主权者。洛克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身处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如果被一种道德自然法支配,那么他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政治社会来强使人们做出道德行为。麦克弗森断言,不去抽象地思考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市场社会的参与者,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按照麦克弗森的解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无休止的市场竞争状态。参与到这种竞争中的人能够认可,一个主权力量是防止竞争变成相互毁灭所必需的,而这与他们的利己竞争行为相符。他们会明白,主权者的存在不仅与他们的持续竞争相一致,而且对这种竞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按照麦克弗森的看法,对洛克而言,自然状态包含一种阶级差别,工人阶级这部分不如资产阶级那部分有理性,因此不能理解道德自然法。要确保社会中的不那么理性且不那么道德的部分“维护和平”(第241 – 247 页),就需要政治社会的约束。
毫不意外,麦克弗森左翼而离经叛道的分析激起了来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约翰·邓恩(John Dunn)、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和其他等人的很多批评。批评者主张,霍布斯和洛克不是自觉的资本主义辩护者,而将这些人描述为不自觉的辩护者,则是在主张一种模糊不清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理论。17世纪的英格兰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哈林顿笔下的士绅忠诚于贵族。洛克不赞成无限制获取。霍布斯关注各式各样的权力,而不仅是或不主要是麦克弗森所处理的那些权力。麦克弗森没能解释,共和主义者在他所处理的那段时期围绕公民美德展开的重要争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这类批评。这个导言无法公平地处理这些争议。有些批评针对的是麦克弗森对其理论的较早表述,他在本书里做了回应——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其回应的合理性。读者还可以利用两项有用的研究,它们研究的是对麦克弗森解释的挑战:一项来自赞成批评的詹姆斯·塔利,另一项来自反对这些批评并为麦克弗森辩护的朱尔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
至于麦克弗森的方法论,他无疑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原理。市场社会被分割为阶级,其中有些人必须以其劳动力换取工资;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洛克和其他人所表述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世界观正反映了这一点。不过,在一些重要方面,他的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麦克弗森的政治右翼批评者常常指控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那些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批评他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主要感兴趣的是经济市场的政治和文化,而非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关注。他明确抛开了对市场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任何特别理论”(第48 页)的思考。他没有提及社会革命理论。麦克弗森的研究进路也不是一种片面的进路或过于简单化的进路。他承认,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念“既归因于他对基督教自然法传统的理解,也归因于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同等程度的理解”(第245页),而没有主张洛克的那些基督教观念只不过是心存怀疑的装点门面。他没有主张说,17世纪的自由、权利等此类观念导源于市场社会中的占有观念,而是主张说“占有观念有力形塑了其他这些观念”(第3页)。
为了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书置于麦克弗森的总体工程中,我们应关注该书的一个主题,即他有关政治道德的论述。到了霍布斯的时代,人们已经无法指望通过诉诸“假设出来的、充斥宇宙的意志或目的”来为调节人类事务提供指导,而麦克弗森主张,这些事务开始被市场力量定性。每个人都平等地服从市场;而为了避免彼此毁灭的混乱,每个人都认识到需要服从一个统领全局的政治权力。对麦克弗森而言,这种服从是一种义务,它“可以被称为审慎义务,同样也可以被称为道德义务;它是市场人能够认可的最高道德”(第87页)。如此看来,霍布斯是从假定的社会和政治事实推导出一种道德准则。麦克弗森用了几页篇幅来为这一推导辩护(第81 – 90 页)。正如他所指出的,大卫·休谟主张(而且,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是当代大部分主流哲学家都同意),没有人能够仅仅从有关非道德性事实的陈述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种表达道德规定的陈述。此处对麦克弗森观点的一种解释(或者可能是一种重构,因为他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某种混淆)是,尽管他使用了诸如“推导”和“有效性”等专门的逻辑术语,但他头脑所想的不是有关伦理学的哲学理论,而是某种常识道德。在霍布斯的时代,对人们来说,把政治规则诉诸神之准可的做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忠诚于一种监督市场关系的世俗权力则说得通。如此一来,霍布斯的义务观就“具有特定的历史有效性”,也就是说,它适合于市场社会(第13 页)。
在本书结论部分,麦克弗森回到了这个主题。他在那里说,尽管占有性个人主义预设在今天仍占优势,但“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从中推导出充分的[道德]原则了”。常识性观念要具有实际道德力量,就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对市场力量的平等服从被所有人认为是“正当和不可避免的”,以及“在所有那些有权选举政府的人中间”的凝聚力。由于出现了一个自觉的工人阶级以及普遍的选举权,这些条件不复存在。不同阶级争夺政治权力,而且并非所有工人都把市场看作一个平等的公共场所。因此,现代自由民主理论面临着以下困境:市场社会留存了下来,但是从市场社会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文化推导出共同道德观所需要的条件却没能留存下来。(第271 – 275 页)麦克弗森猜测,或许,核灭绝威胁会为形成一种霍布斯式的“不安全状态的平等”意识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并由此带来全球性的(如果不是一国之内的)凝聚力。那些在20 世纪60年代早期至少已是青年的人并不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测,因为当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高得惊人。麦克弗森的夫人凯(Kay)是加拿大和平运动的一位重要组织者,而麦克弗森那时想要出版系列讲座集《真实的民主世界》(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1965 年),部分原因意在鼓励缓和。这种想法类似于今天人们有时对隐隐逼近的环境危机所表达的看法。
无论在核威胁下可能出现过什么样的平等意识,也无论对环境污染的恐惧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平等意识,我们都难以看到,它们如何能够以麦克弗森所希望的方式让自由民主理论和文化得以重生。相反,现在似乎有三个替代方案。其一,寻求对非自由民主选项的共识性接受。其二,抛弃“道德观必须反映那些当下人们共同理解的境况”这个观念,并倡导普遍适用的规定,无论其是否体现于日常道德中。其三,在现有的自由民主政治文化中界定非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范围。这正是麦克弗森在其后续作品中所采取的方法。他从事政治思想史分析工作,其目的是说明自由民主思想是由两种相互竞争的倾向所组成。一种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另一种是非占有性人类潜力的平等发展这样一种民主观。因此,他撰写后续作品《民主理论:论文重淬集》(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就是要论证,如果抛弃《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书所呈现的那种占有性个人主义遗产,自由民主还如何能够坚持自我。
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
2010年9月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读后感(三):【转】韩潮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罪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出版后不久,一位评论者曾经说,此书带有某种布道的使命,因而多少损害了其智识价值。麦克弗森或许被激怒了,他在回应的文章中称,他拒绝接受这一“诋毁”。麦克弗森承认,一部受惠于马克思的理智洞见和道德洞见的作品确实很可能会被马克思主义的布道热情毁掉,但是他并不认为他本人的这部著作带有这种布道的热情,此书的确受惠于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但并没有受惠于作为布道者的马克思。相反,评论者本人的“敌意”或许并不来自文本解释的分歧,而是源自某种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偏见。
1962年的知识氛围完全不同于当下,我相信,必定是某种智识力量的说服力,才使得以赛亚·伯林在同一时期的书评里坦诚,尽管他不同意麦克弗森的解释,但却感佩于麦克弗森的才智。麦克弗森的智识武器,党棍们用起来必定是那种既无效又让人没办法信任的蠢笨招法,而在麦克弗森这里,却充满着技巧、力量和惊人的理智效果。
但麦克弗森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颇有争议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从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语言里,这个词语毫无疑问是麦克弗森本人的发明。他后来承认,这个词实际上受到了托尼(R. H. Tawney)的《贪婪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的启示。麦克弗森在伦敦政经学院读书期间在导师拉斯基的引介下认识了同在该学院任教的托尼,受其影响颇深。如果托尼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麦克弗森同样也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的道德关怀乃至于学术语言实际上都延续了拉斯基、托尼一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他的学术训练基本上是英式的,他可能只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从没有通读过《资本论》。他的著述中很少引用马克思,也几乎不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剥削”一词,只在提及掘地派领袖、基督教共产主义者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时用过两次。
托尼:《贪婪社会》但是,在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上,麦克弗森却惊人地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衣钵——那就是近乎于历史决定论的解释方式。与麦克弗森私交甚笃的以赛亚·伯林一早就看出了麦克弗森受托尼影响的一面,但伯林同时指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真正创新的一面却在于,在麦克弗森眼中,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顿乃至于洛克竟然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这个论断今天看来或许既熟悉又陌生,在伯林所厌恶的那种政治语言里,这个论断当然屡见不鲜,但是在今天的学术语言里,这个论断却几乎消失殆尽了。麦克弗森本人没有使用这样直白的表述,但伯林之所以用“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这种近于揶揄的表述,还是多少表明伯林对麦克弗森学术取向本能地不适,或许在他看来,包裹在麦克弗森精致学术语言里面的东西,其实质却无非是这样一种老派的意识形态判断。
麦克弗森的论断毫无疑问是冒犯性的,他在学理上挑开了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自由主义的自我认知总是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无涉的政治理论,那么麦克弗森无异于断言——恰恰相反,至少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是自由主义的必要前提。自由主义自认为对普遍人性辩护在麦克弗森那里被还原为“资产者”的特殊辩护,并且,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对“资产者”的辩护支配了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的自由主义观念。十七世纪以降的自由、权利、义务乃至于正义观念,撇开以“资产者”为原型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C. B. 麦克弗森(1911-1987)麦克弗森毫无疑问也是克制的,他并没有采用老派马克思主义的训诫口吻,他尽可能将批评的锋芒收敛在充分精细的文本解读中,或者说,他尽可能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摊开在自由主义本身的学理论证层面。但即便如此,从效果上来看,麦克弗森的分析方法无异于从字里行间的罅隙里迫使自由主义者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或者说迫使自由主义者承认并且直面他们的历史原罪。因此,麦克弗森的研究终究还是激怒了不少自由主义学者,例如萨托利就完全不能接受麦克弗森的学说,在他看来,麦克弗森的理论近于空无一物。
撇开意识形态争议不论,在我看来,真正在智识层面构成挑战的是,在麦克弗森笔下,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顿、洛克这四种背景、立场、言说方式迥异的政治思想竟然分享了同一个前提、同一种预设。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麦克弗森此书好比是一部侦探小说,四起谋杀案竟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在麦克弗森的理论出现之前,平等派的立场近于早早被压抑的激进民主派的声音;哈林顿是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共和派乌托邦主义者,数年之前,托尼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 )关于十七世纪士绅阶层的论争刚刚将他从遗忘中挽救出来;洛克是有些资产阶级气象,但此前几乎没有人认为,洛克只是为资产者的权利辩护;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霍布斯,在传统的解释里,霍布斯无论如何不会与局促的资产者搭上边。但麦克弗森毋宁是说,所有这些解释都只是摸到了皮相,透过各种蛛丝马迹,我们完全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令人惊叹的一致性。
克伦威尔在英国伯福德为平等派设立的纪念石碑麦克弗森的侦查手法有些看上去是纯粹历史性的。比如他发现,平等派并非像此前主流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主张所有成年男子都具有选举权,他们事实上将雇工和乞丐的选举权排除在外。但麦克弗森的敏感不止于此,他注意到,学界之所以漠视平等派对选举权的限制,实是因为平等派尽管将近七十万英国公民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但却总是堂而皇之地主张“一切生而自由的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这一具有迷惑性的主张往往让人以为平等派是所有人平等的自然权利的主张者。麦克弗森并不只是想指出平等派的矛盾性,在他看来,恰恰相反,事实上平等派并不觉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像“自由人”有什么矛盾,因为,在他们的自由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潜台词——接受施舍、订立雇佣契约会造成对他人意志的依附,当乞丐和雇工丧失或让渡了支配自己能力的管辖权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再是积极行使权利的“自由人”了。麦克弗森据此断言,平等派从没有主张过所有人平等的自然权利,他们主张的毋宁是某种特定的“进取者共同体”(community of enterprisers)的自然权利。
哈林顿这种对语词含混性的敏感还体现在麦克弗森对哈林顿的分析中。麦克弗森注意到,哈林顿的“士绅”归属极其模糊,当哈林顿谈论“哥特均势”解体时,士绅阶层属于人民,当他谈论同时代的政治状况时,士绅阶层又成了贵族。麦克弗森追随托尼的观点认为,哈林顿的含混性其实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士绅阶层崛起的洞察,因此,不是哈林顿将士绅从“人民”移到了“贵族”之列,而是士绅阶层将自己移置到了“贵族”之列。在这一意义上,哈林顿毋宁是最早洞察到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政治思想家。
当然,麦克弗森最重要的武器还是对思想家论证结构的审查。在对哈林顿思想的分析中,麦克弗森发现,哈林顿的土地法观念和他的均势观念存在着矛盾。哈林顿一方面认为只有维持土地的均势,才能建立永久持续的平等共和国,但另一方面他却将英格兰的所有土地分配给其中的五千个公民,而将其余的五十万人排除在外。麦克弗森认为,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哈林顿的平等共和国实质上只是机会平等的共和国,土地法并没有排斥阶层的流动性:通过勤勉积累财富向上流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平等者”!因此,麦克弗森再一次发现了与平等派的“进取者共同体”相类似的预设,在他看来,这个哈林顿式的平等共和国毋宁是带有典型资产阶级平等观念、且将市场关系置于首位的“机会国家”(Opportunity States)。
霍布斯这种对论证结构的体察同样体现在他对霍布斯和洛克的分析中。将霍布斯不可思议地与资本主义牵连在一起的是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解释。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非是真正的“自然”状态,而是已经渗透了社会性的因素,甚至就是以十七世纪的占有性市场社会为其自然状态的模型。他发现,霍布斯自然状态推演环节存在着某种缺失,从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机械论的人性观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出自然人何以要胜过其他人,而弥补这个相关性缺失的则是霍布斯的荣誉观念和权力观念。麦克弗森当然了解,荣誉或虚荣是一种古老的人性,但在他看来,霍布斯的“荣誉”是一种特定的现代类型的表达,即无休止地追求得到他人认可的优越性。他注意到,霍布斯毫不避讳地使用一种市场化的模式描述这种个体关系——“人的价值和其他东西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依赖于他人的需求和评价”……“对人来说,决定身价的是买者而不是卖者”——如此等等无不体现了霍布斯对于资产阶级虚荣的洞察。麦克弗森据此指出,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中描述的人性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质就是十七世纪初兴的占有性市场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而没有这个市场化的预设,单从机械论的原子化个人根本无法推演出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麦克弗森充分肯定霍布斯的意义,他在其后的一篇论文《霍布斯的资产者》里曾经说:“即便是那些根本不同意霍布斯的理论的人,也会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其实我们都对霍布斯充满了畏惧,因为他对我们了解得太多。”换言之,霍布斯洞察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隐秘,他是所有这些将资产者人性转化为普遍人性的学说的起点,并将这一洞察传递给后来者。
洛克对麦克弗森而言,洛克并不是这个后来者序列的终点,他在后续的研究中一直将“占有性个人主义”推进到休谟、柏克乃至于边沁那里,洛克只是这个序列的中继者。洛克固然是所有这些思想中似乎最靠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物,《政府论》下篇对财产权的辩护是洛克笔下最明白无误、最有影响力的论点之一,但麦克弗森并没有重复这些固有的论点,他试图证明,洛克不止是一般意义上财产权的辩护者,而且还是“无限财产权”的辩护者。
麦克弗森的洛克研究有一个著名的断言,他说,“洛克的惊人成就是将自然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之后又从财产权利中移除了一切自然法的限制”。麦克弗森发现,洛克最初依据自然法对自然状态中的财产占有施加了一些限定,如为他人保留生存的条件、禁止浪费、通过劳动确定财产归属,而在货币引入之后这些限定统统被取消了,占有取代了劳动的位置。于是,洛克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分裂成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和占有没有分离;在第二个阶段,占有和劳动相分离,占有成了勤勉和理性的标志,占有的合理性支持了“无限积累的合理性”。麦克弗森认为,洛克的矛盾在于,他预设了两种不同的人性:前一个阶段,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理性能力和平等的自然权利;而在后一个阶段,理性、勤勉且拥有财产的人其理性能力要高于那些不那么勤勉、不那么热衷于积累而只是为了生活下去的人。后一阶段呈现出来的理性能力差别,在麦克弗森看来其实质就是一种典型的、十七世纪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观念,通过这种观念,洛克事实上悄悄地取消了自然权利的平等性。
洛克:《政府论》这一惊人的大胆断言尤其体现在麦克弗森对洛克式政治社会的分析之上。谁有进入政治社会的资格?麦克弗森说,对洛克而言,存在着两种答案:一种是所有人,另一种是拥有财产的人。这两个答案同时存在、同样正确,尽管相互矛盾。洛克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他对财产一词广义和狭义用法的含混使用让他没有使之明确化。对洛克而言,没有财产的人可以说既在政治社会之中,也在政治社会之外:政治社会需要资产者的明示同意,但对于无资产者来说,默示同意就足够了。当然洛克并没有刻意让平等的自然权利论证转化为阶级正当性的论证,但他的表述确实有可能让平等的自然权利合乎逻辑地演化为差别化的阶级权利,从而为此资产者的自然权利铺平了道路。
至此,当霍布斯的市场化虚荣人性、平等派的进取者共同体、哈林顿的机会国家以及洛克的差别化阶级权利四种智识形象慢慢重合起来,叠映为一幅一以贯之、且错落有致的图景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真正智识力量才真正呈现出来。
麦克弗森的思想史方法论可谓独树一帜。麦克弗森给出的并不是经验性的历史信息,而是作者没有说出的某种历史预设。麦克弗森对这四种政治思想的解释,几乎遵循了这样类似的解释模式——霍布斯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然状态描述事实上沿用了市场社会的模型;平等派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由人”并不是全体人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他的均势理论之成立依赖于机会国家的建构;洛克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然人叙述可能导向差别化阶级权利——所有这些预设都并非出自作者笔下,甚至,或许本出于作者的意图之外,作者只是在不自觉中沿用了这些历史预设。
新版《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毋庸多言,这一方法论极为大胆,也极为危险。为什么十七世纪的政治理论家没有说出他们的预设?为什么他们如此一致地保持了沉默?麦克弗森提出了三种可能:其一、作者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说出其全部预设,尤其是在一个时代视为常识的某些观念;其二、作者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其理论的预设;其三、作者可能出于某种迫害的风险而隐藏了他们的观点。
麦克弗森的第三种论点以及他在脚注中对施特劳斯的援引近乎于以喜剧的方式提示我们,或许存在着某种“隐微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当然只能一笑了之。但这并不能否认麦克弗森方法论总体的严肃性,撇开第三种解释不论,麦克弗森的整体思想史构思是超越作者本人意图的一种思想史探究方式。这种超越主观性的思想史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历史氛围下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绝非绝对不可容忍。麦克弗森的方法确实不同于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也不同于施特劳斯学派的文本自足主义,如伯林所感知的那样,其方法大体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但考虑到麦克弗森后来甚至一度用“西方的民主本体论”(Western Democratic Ontology)这一极其哲学化的表述来称呼“占有性个人主义”,其方法论也未必没有回归洛夫乔伊的倾向。
从剑桥学派的立场来看,麦克弗森的方法当然有巨大的问题:斯金纳认为麦克弗森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非历史的”;邓恩说,麦克弗森笔下的这些作者几乎就是以二十世纪的“隐性墨水”写就的;拉斯莱特最为激烈,他认为,阅读麦克弗森的著作,仿佛让你感觉被蒙住了眼睛,带入了一条黑暗而狭窄的小巷,这是用既定模型研究思想史的后果,麦克弗森更应当被视为教条的经济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既不能算哲学,也不能算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弗森的这部著作诞生于剑桥学派初兴的六十年代初,塔利甚至认为,剑桥学派后起的一系列研究正是伴随着对麦克弗森式图景的怀疑。或许,语境主义的首要对手恰恰正是麦克弗森。
剑桥学派:斯金纳、邓恩、拉斯莱特然而,剑桥学派的解释在历史语境的还原上或许更为准确,但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历史解释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在剑桥学派的解释模式中,存在着“语境自足主义”的巨大困难。比如,剑桥学派的美国建国史解释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难题:这场所谓共和主义的革命何以在建国后立即被国父们放弃了?什么样的历史力量导致共和主义理想滑向或过渡为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史学派、马克思主义乃至于传统的洛夫乔伊式观念史研究都要比剑桥学派更适合长时段的、涉及语境转换的历史解释。麦克弗森的方法论当然也属于这些与剑桥学派的方法论相抗衡的一种,在他的笔下,从霍布斯到边沁的两百年历史分享了同一种历史预设,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超越语境的方法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充分体现了这一方法穿透主观修辞和主观意图的智识力量。在今天极其窄化的思想史研究氛围中,相较于因语境的封闭性而陷入“语境自足主义”的思想史方法,或相较于因文本的封闭性而陷入神秘主义的思想史方法,麦克弗森的研究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除了方法之外,麦克弗森对十七世纪四种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在每一个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弹,可以说,在每一个领域,麦克弗森的反对者可能都要远远超过其支持者。霍布斯的虚荣观念究竟是传统贵族的荣誉取向还是资产阶级的市场取向?平等派限制选举权的主张是不是基于寻求与独立派联合而不得已做出的妥协?哈林顿是不是仍旧在马基雅维利式的共和主义公民意义上讨论财产问题?洛克是不是支持无限积累的财产权?塔利甚至说,除了边沁之外,麦克弗森一一拈出的、从霍布斯一直到埃德蒙·柏克的那些思想家都远远称不上“占有性个人主义者”。
但具体领域内的争议并没有妨碍麦克弗森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成了一个具有足够经典性的“大概念”,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解释。相较于剑桥学派提供的早期现代政治思想的解释,麦克弗森理论的历史解释力如果说与之不相伯仲的话,那么“占有性个人主义”对当代政治思想的启示则很明显要更胜一筹了。
麦克弗森理论的历史解释力之所以很大程度是有效的,在于他把握住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当代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在其形成过程中,是先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其后再逐渐掺杂了民主的成分。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相结合之前,自由主义已经以不民主的方式存续了约两百年。在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取消之前,没有选举权的公民确实曾享有自由主义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各种自由权利,这一历史事实尽管不符合我们当代的现实经验,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麦克弗森学说的历史效力也就在于此,在他看来,直到十九世纪当理论家确信“一人一票”不会影响财产权或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的存续时,自由民主的观念才真正被接受——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什么原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在这里。
麦克弗森著《民主理论》(1973)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生平与时代》(1977)麦克弗森曾经说,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包含着两种互相反对的可能性:一种是强者可以通过遵循自由市场的规则而压制弱者;一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平等有效的自由去发展自己的能力。两者都意味着自由,但两者相互反对。前者实际上就是指十七世纪以降的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自由竞争观念;而后者是麦克弗森所推崇的、从密尔那里开始萌发出来的“非占有式的”、或发展式的自由观念。麦克弗森的历史关怀由此很明显指向了当下,对他而言,我们今天还仍旧吮吸着十七世纪的狼奶。并不是一人一票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十七世纪的毒素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只要人还没有充分拥有发展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这个矛盾就一直存在。麦克弗森后期倾向于用“能力转移”(Transfer of Powers)的概念批判十七世纪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试想,一个今天被“996”耗尽了的职员,他怎么可能是他自身能力的占有者?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对自身能力的支配权转让给了资产者?而同样身处禁锢中的我们是不是仍旧处于十七世纪?
无论如何,麦克弗森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更何况,当多元主义介入其中,当平等和差异性被糅合在一个谱系里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素朴性已经经过了重要的修正。我们完全可以从麦克弗森徘徊于密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身影中捕捉到蛛丝马迹。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从微小的裂隙开始崩塌的分裂。施克莱(Judith Shklar)曾经说:即便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专一、永久且忠诚地结合在一起,但终究不过是一场“权宜的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但我怀疑,如果他们并不相爱,其实,我们也丝毫不能指望他们彼此之间的绝对忠诚。毕竟,自由主义还注定要背负着那个有欠于民主的原罪。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读后感(四):【转】张新刚: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读之辨正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4期
【摘要】本文考察并分析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政治理论的解读。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详细阐述了人际间围绕权力的竞争,但这种权力竞争必须引入市场社会的预设方能成立。在这一社会中,道德义务可以从人的平等权利和市场社会中推衍出来,主权者也是市场社会良好运转的保证。但是,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并没有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产生的阶级分层和对立。本文从文本和逻辑等角度对麦克弗森提出的市场社会范式及其对霍布斯新道德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性评析,认为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思想中自然哲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主权者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值得充分肯定且富有启发意义,这为我们理解霍布斯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键词】霍布斯 占有式个人主义 市场社会 麦克弗森
一、麦克弗森对自由民主理论的诊断
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是加拿大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其理论工作集中于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和诊断,并致力于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促进社会全体成员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中,霍布斯的思想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是其构建自己政治理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因素。为了更好地定位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释,本文有必要先对麦克弗森整体的理论努力进行简要交代。
在1976年回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者的批评时,麦克弗森袒露了自己“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就是构建自由民主理论的修正版,这一修正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我希望这一理论能够更加民主,同时能够挽救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等同之后而消失了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①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和体系构建可以进一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由民主传统的系统清理和反思,特别是对从霍布斯到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批判性解释,他将这些政治哲学家的理论统称为“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在麦克弗森看来,当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很多缺陷都是来自于占有式个人主义,而要修正自由民主传统,首先就要对其理论根源进行清理。麦克弗森在理论上有破有立,在找到病根之后,其理论工作的第二部分就是重建民主理论的基础,即把人从功利的消费者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行为者和创造者,注重人性的发展。
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在20世纪的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各派似乎都不甚满意麦克弗森。有学者将麦克弗森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对政治思想史进行了错误的诠释,还有人批评他对自由主义进行攻击,更有人认为他的观点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还不彻底。而将他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也对其表达了不满,认为他赋予了个人主义太多意涵和任务。另有关注麦克弗森政治理论历史性特征的学者,如剑桥学派的学者,认为他对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语境分析太过笼统。麦克弗森著作的丰富性使得对其理论特质的把握本身成为有争议的问题,那么他的理论立场究竟是什么呢?总体来看,麦克弗森一方面对密尔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改造;另一方面,在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又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理论资源。所以,麦克弗森认为自己既不是通常称谓的自由民主论者,也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替换自由民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麦克弗森自己的话说,他“整体接受并倡导自由—民主社会以及由密尔和19-20世纪唯心主义理论家阐述的规范性价值,但拒斥当前的自由—民主社会和国家,因为它们没能捍卫这些价值,或者说无力实现这些价值”②。
在了解了麦克弗森的系统理论体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地把握霍布斯在其政治理论中的位置。霍布斯是麦克弗森批判性反思的自由民主传统中的重要政治思想家,在这一批判性传统中,麦克弗森还阐释了英国平等派、哈灵顿、洛克、休谟、伯克、边沁、密尔等思想家。但在这些思想家中,霍布斯是第一位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核心特征的思想家,霍布斯开启了他所谓的“占有式个人主义”的理论源头,同时也开启了存在内在困境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可能也正是基于此,麦克弗森给予了霍布斯较多的关注,曾多次在不同的文本中探讨霍布斯与现代自由—民主传统的关系,以及霍布斯在20世纪的意义。在为霍布斯的企鹅版《利维坦》所作的导论中,麦克弗森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霍布斯与当今世界的关联。在他看来,霍布斯的著作在当今仍值得阅读的理由有三:首先,我们的世界被权力的难题所困扰,而霍布斯是系统分析权力的思想家;其次,霍布斯的首要关切是和平,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重要议题;最后,霍布斯将其政治体系构建成了科学,他试图将科学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麦克弗森进一步指出:“我们生活在市场社会中,我们的行为、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由市场的需求所塑造。我们是资产阶级的人。”③而霍布斯用科学方法来构建的人与社会的范式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范式,结合上述三点,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就可以被理解为对资产阶级权力与和平的科学分析。通过将霍布斯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范式中,麦克弗森一方面展示了霍布斯思想在17世纪的独创性和深邃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也指出,霍布斯的思想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市场社会。由此,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到了20世纪不断地受到挑战,“我们不可能期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科学,还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④。
简而言之,在麦克弗森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占有式个人主义成功地将个人效用最大化,但是自由民主社会却无法实现人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这也是市场社会无法摆脱的内在局限性。在麦克弗森的“占有式个人主义”思想史中,霍布斯是重要开启者之一,考察霍布斯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下自由民主理论的难题有着重要意义。在麦克弗森看来,身居历史环境中的霍布斯政治思想究竟是如何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特征,以及存在哪些必然的内在局限的呢?下面我们就转向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政治思想内在脉络的阐释。
二、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
从文本上看,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集中在从人到国家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构成了其分析的要害。正是从前国家阶段的人性及人际关系的阐释中,麦克弗森发现了霍布斯学说背后隐含的市场社会前提。
1.人性与人际关系
如大多数霍布斯研究者一样,麦克弗森注意到,霍布斯在进行政治分析时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欧几里得式的几何演绎法,因为这种方法不能为政治科学找到自明的前提。麦克弗森提出,霍布斯实际上采用的是伽利略的“综合—分析”法,用霍布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要素入手,然后看看它的出现、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正义的起源,因为对事物的理解,莫过于知道其成分。”⑤麦克弗森注意到,霍布斯在不同的政治文本中将人和钟表这样的机械进行类比,要理解国家这个大钟表的运转,就要先了解人。
在《利维坦》第一部分对人的机械论分析中,麦克弗森看到了现代科学在霍布斯人性学说中的应用。麦克弗森指出,霍布斯将人还原为由感觉器官、神经、肌肉、想象、记忆、理性等构成的机械装置,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人所有的行动都可分解为身体和心智的基本运动,并且从宽泛意义上说,人体就是自我运动、自我引导的质料(matter),因为“人体中有维持其运动的欲望或努力”⑥。麦克弗森暗示霍布斯对人的这一表述,即人对自己的持续运动有内在要求,实际上是在政治分析中完成了伽利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假定一个静止的物体,除非有外物推动,否则它将永远保持静止,并且只有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才会持续运动。伽利略却认为运动中的物体除非有外物阻停它,否则将一直保持为运动,其运动并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持续作用。”⑦在给出人的科学理解之后,麦克弗森洞察到,仅靠机械论的人性规定,并不能推导出国家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外部刺激进行自我运动,不和别人发生关联,那么是不需要国家或社会的。要理解霍布斯理论中从人到国家的必然逻辑,就必须从对个人的机械论理解推进到人际关系中对权力的争夺上来。
按照霍布斯对人的机械论描述,麦克弗森总结出人的动机行为进阶:
(1)人由欲求和厌恶所驱动,所有的人都会不停地寻求自己欲望的满足,不同的人对权力、财富、荣誉的满足度是分不同层级的。
(2)人的权力就是他当下拥有的,能在未来获得对其来说是好的东西的手段。
由(1)和(2)可得出:
(3)每个人必须总是寻求拥有一些权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主动追求和别人一样多,或者超出别人的权力。
到此为止,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理论还没有涉及真正的人际关系,一切看起来还都是比较和谐的,但是,此后,霍布斯给出了“自然权力”和“获得的权力”的定义:“自然权力(原始权力)就是身心官能的优越性,如与众不同的膂力、仪容、慎虑、技艺、口才、慷慨大度和高贵的出身等等都是。获得的权力则是来自上述诸种优越性或来自幸运、并以之作为取得更多优势的手段或工具的权力。”⑧麦克弗森从“优越性”这里看到了霍布斯从人到人际关系过渡中的重要变化,即从个体化的自我运动和欲望的满足转变为人与人的比较。这是一个关键的过渡,由此得出了后续结论:
(4)每个人的权力都抵抗和阻碍其他人权力的效果。麦克弗森认为这一结论是很彻底的,即人的权力可以被简要界定为超过别人。
(5)所有获得的权力就是对其他人的权力发号施令。
(6)有些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7)基于以上几点,霍布斯最终推出关于人性的结论:“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若不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⑨
上述7点将霍布斯从个人到人际间权力斗争的逻辑清理了出来,麦克弗森从中发现了逻辑的缝隙,即从(3)到(4)和(5)的过渡并非自明,也就是说,并不能从霍布斯对人的机械论分析中推导出人自己的权力一定要优越于别人。麦克弗森认为:“你可以从社会中或自然状态中普遍的权力斗争转到主权者的必需上面,但是你不能从作为机械体系的人直接转到对权力的普遍斗争上,或自然状态上。”⑩霍布斯如果想要证成人际间权力的普遍竞争,就必须添加新的条件,这新条件来自对社会的观察。麦克弗森从此推断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人的自然状况并不是与文明人相对立的“自然”人,而是其欲望已经文明化了的社会人;第二,自然状态下的人际关系实质上是已经建立了社会关系之后的人际关系。
2.自然状态与市场社会
既然单纯的机械论人性观不能推导出《利维坦》十一章(既上述第7条)的结论,麦克弗森就为霍布斯加上了一条重要的假设。自然状态下的人实际上是已经社会化的人,自然状态也并非真正的“自然”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熟悉思想史的读者看到这里即会联想到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批评,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曾富有洞见地指出:“考察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一直感到有必要尽可能回溯到自然状态,但他们没人达到了自然状态……我们绝大多数哲学家甚至从未动脑筋怀疑自然状态也许从未存在。”(11)由此,卢梭严厉地批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战争状态,认为这么做的根源是将“自然人”与“我们见到的人”混为一谈。 从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把握来看,麦克弗森与卢梭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与卢梭想要构建真正的自然状态不同,麦克弗森则将精力放在了解释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上。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并拥有文明人欲望的人,在所有法律和契约约束消失了之后所处的状态”。为了获得自然状态,霍布斯“摒除了法律,但并没有摒除人的社会性行为和欲望”。(1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社会或国家解体后的状态,并不是19世纪人类学家将自然状态历史化后为我们描述的事实性的“原始社会”。自然状态成为霍布斯的逻辑建构,如同霍布斯的“分析—综合”方法所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想象国家或社会解体之后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人的状况。麦克弗森进一步区分了“反社会性”(anti-social)和“非社会性”(non-social),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不是非社会性的,而是反社会性的。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似乎也支持了麦克弗森的洞察,比如在《利维坦》第十三章中,霍布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在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就足以使彼此互相摧毁)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13)此外,引起争执的三个原因,竞争、猜忌和荣誉,都带有非常强的社会属性,这三个要素只有在缺乏公共权力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麦克弗森由此得出结论:对于霍布斯而言,自然并不与社会或国家相对立,恰恰是从对社会中人性的分析中,霍布斯推导出自然状态必然成为战争状态。不仅如此,麦克弗森还进一步指出,霍布斯人性洞察中的社会性因素并非是随意的,也即并非任何社会下的人性都能推导出霍布斯笔下的权力斗争和战争状态,只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符合其理论努力,这就是市场社会。在麦克弗森看来,后者是霍布斯政治分析中隐而未现的核心预设,可以进一步从权力的市场分析中得出。
自然状态下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战,人们围绕权力进行得一望二的追逐,这些都是霍布斯的文本所明确指出的。麦克弗森除了得出权力的普遍对抗外,还进一步分析了人际间更为细致的权力关系。他根据霍布斯对价值的表述,发现了市场化价格这一要素。在《利维坦》第十章中,霍布斯这样界定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他的力量时,将付与他多少。因之,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旁人的需要与评价。善于带兵的人在战时或战争危机紧迫时价格极高,但在平时则不然。学识渊博、廉洁奉公的法官在平时身价极高,在战时就不免逊色。对人来说,也和对其他事物一样,决定价格的不是卖者而是买者。即使让一个人(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尽量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但他们真正的价值却不能超过旁人的估价。”(14)在这里,麦克弗森发现,在霍布斯对于价值的规定中,人对别人价值的估量是要和对自己的估量进行比较的,对别人的尊重或轻视是根据对自己的评价和估量而定的:“互相评价的表示一般称为尊重或轻视。高度评价一个人就是尊重,低度评价则为轻视。但这里所谓的高低,要以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估价来理解。”(15)麦克弗森将之解释为“由接受者主观认为的尊重是对其价值的自我评价和市场评价间的差异”(16),这就是竞争性市场的本质特征。每个人的价值通过别人给予他的尊重得以彰显,其价值由他人对其权力的观念决定,同时也决定了他人对其权力的看法。这样一来,“尊重就不简单是接受尊重的人和给出尊重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接受尊重的人和给予他尊重的所有其他人的关系,所有其他人是指与他运用自己的权力有或远或近关系的人”(17)。每个人,只要和实施权力的人有关系,就会独立地对该人的权力作出判断,并且与自己的权力进行比较,在相当数量的人给出自己的判断时,该人的权力也就具备了客观的价值标准。在麦克弗森看来,这种情况要能成立,只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权力都被视为商品,商品是指通常完全为了交换的事物。在市场中,每个人都是奔着权力来的,要么是作为供给者,要么是作为需求者”。(18)
这样一来,麦克弗森在《利维坦》中发现了客观性价值,即人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的,其标准是该人的权力对于他人所能带来的好处。换言之,每个人的价值就如同市场决定价格机制那样被塑造。在自然状态下,当谈及每个人的价值或价格时,麦克弗森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谈论售卖自己的权力或购买他人权力。由此,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权力定义是中性的,同时,基于机械论的人性观也无法独立推导出自然状态下权力的相互竞争关系,要达至霍布斯的结论,就必须加上社会性的条件。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这本质上是市场—价格机制,自然状态下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权力的市场决定关系。在完成这一转化之后,霍布斯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创立一种社会机制:一方面保障权力的正常竞争,但同时又不会将整个社会带向毁灭。麦克弗森通过将自然状态和社会混淆,而提出用市场社会来保证和平的竞争关系。
人与人进行权力竞争但同时又能不摧毁社会,这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麦克弗森给出的答案就是“占有式市场社会”(possessive market society)。那么,究竟什么是占有式市场社会呢?麦克弗森的定义是:“占有式市场社会与传统或等级社会不同,没有对工作和奖励的权威性分配;这一社会也不仅仅限于对产品的市场交换,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如果要为这一社会确定单一标准的话,那就是人的劳动力是商品,即人自己的精力和技能不被视为他人格的内在部分,而是被视为财产,在对其的使用和支配上,人可以自由地以某一价格转让给他人。我称之为占有式市场社会是为了强调其作为完备市场社会的这一特征。占有式市场社会同时也暗示了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市场商品,市场关系塑造或渗透进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所以我将之称为市场社会,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19)
通过将人的权力和追求权力的手段还原为市场社会中的商品,麦克弗森用市场关系替换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激烈而残酷的权力竞争似乎与市场中商品的交换有着较大的差别,麦克弗森必须进一步解决市场社会中竞争的性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中的竞争实质是大企业主必须利用不断扩张的资本来获得更为低价的商品,竞争也就成为了人将他人权力化为己用而非自己的权力为他人所用的手段。麦克弗森采用了马克思式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解释,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土地和资本向部分人手中集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而社会分化之后,掌握资本和土地的资本家实际上掌握了受雇佣者的劳动力,也即个体最为本质的那一部分。进而,失去劳动力所有权的人要不断地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剩余的占有式权力(possessive power)。
在市场体系中,每个人都拥有某些权力,至少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市场性竞争是个体间在不同层面的全面而持续的竞争,每个人都被抛入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根据自己的付出而获得应有的份额,市场决定了每个人的价格。麦克弗森对市场社会中人的权力的界定,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力的界定有着契合之处,权力既被理解为个人的能力,同时还包括进一步获得未来善好事物的手段。正是从这些契合之处,麦克弗森大胆地推论,霍布斯实际上描述的就是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
3.利维坦及其局限
以市场社会的视角,麦克弗森为我们重新解释了利维坦的正当性。与霍布斯自己陈述的利维坦的首要目的是保障人的安全略有不同,麦克弗森更多地关注利维坦保障财产的经济逻辑。麦克弗森提醒我们,虽然主权者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安全”,但这里的安全并不仅仅是生命的保存,而是包括了生活的满足,即每个人都有合法的产业,而不怕别人或国家的侵害。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完全是从经济思维来构想主权者的责任的,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图景。比如在对税收的讨论中,麦克弗森认为自己找到了霍布斯的资产阶级底色。在《利维坦》第三十章中,霍布斯首先澄清了征税是为了使得国家有能力保卫公民,征税应该是平等的。但是,麦克弗森发现,霍布斯还是区分了富人与穷人,“只是富者另外还雇用贫者,所以便不但由于自己、而且也由于更多的其他人而负有债务。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就可以说税收的平等与其说是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均等,倒不如说是要取决于消费本身的均等”(20)。因为有些人通过统领更多的劳动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财富,他们消费更多,由此也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赋,在麦克弗森看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税赋观,即税收的合法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获得个人财产。
在关于国家的其他描述中,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国家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其政治思路也是要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比如,霍布斯将劳动力自然地视为商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标准。此外,霍布斯还不满于前资本主义的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认为事物的价值只由市场决定。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不仅看到了市场社会的发展,而且将其视为正当的,其他任何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市场社会逻辑面前都已失效。按照这一论断,霍布斯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代言人,敏锐地把握到社会的变化,并用新的科学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了符合新的社会形式的政治形式。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者读到此处肯定会生出一个疑问,按照麦克弗森的逻辑,如何将霍布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霍布斯似乎并没有提出阶级分化,而是建立了主权者直接和每个个体建立关联的现代政治。麦克弗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霍布斯理论的内在缺陷。
这一理论缺陷反映到霍布斯理论中就是对主权者本身的理解,无论主权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会议,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都没能够看到市场社会将产生自身的阶级分化。换言之,霍布斯试图通过利维坦构建一个中立的人为代表是富有欺骗性的。伴随资产阶级市场社会而来的,是购买资本和劳动力的资产阶级与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主权者不可能成为市场般的自动机制,而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拥有较多数量财产和资本的人恰恰需要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来保障其财产权。霍布斯看到了市场社会给人带来的平等,但忽视了市场社会下和平的权力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就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用麦克弗森的话说:“霍布斯看到了阶级,但是没有看到阶级团结的政治重要性。可能是对平等的痴迷使得他没能从科学想象中认识到这一点。他看到了资产阶级秩序的首要特征:其运转需要法律平等,其合法性需要平等的道德设定。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秩序形成后的特征:它必然导致阶级分化和阶级团结。”(21)
三、麦克弗森解读的局限与启示
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读还有很多细节性的阐释,但是经过上面的简要考察,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麦克弗森整个解释的努力方向。他在霍布斯对人性的机械论描述与战争状态所要求的人性之间找到了理论缝隙,并从中插入了霍布斯自己也认可的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得出的人性结论。麦克弗森将自然状态下人的社会性进一步扩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用占有式市场社会替代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用市场社会所塑造的社会人性补足机械论人性,同时用历史决定论为霍布斯政治哲学强加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背景。在将霍布斯界定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先驱的同时,麦克弗森也发现,霍布斯虽然在新的社会形式下构建了保障和平竞争的政治理论体系,但仍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理论本身的束缚。总体看来,麦克弗森的这一解释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色彩,恰恰因为麦克弗森较强的解释预设,导致了这一理解在上个世纪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本文此处并不试图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读进行面面俱到的评析,而是就其中的几个关键性议题进行重新评估,以期发现麦克弗森解释范式的局限与启发。 首先,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占有式市场社会,并且和当时的英国社会勾连起来,为此,他提供了三处文本证据。但是,坦白地讲,麦克弗森所找寻的文本证据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第一处文本出现在《利维坦》第二十四章,在讨论国家的对外贸易时,霍布斯说:“人类的劳动也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可以营利的商品。”麦克弗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从文本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对劳动的描述,而非在自然状态中,故而不能用来佐证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就持有此观点。相比起来,麦克弗森更为看重第二处证据,即霍布斯关于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讨论。霍布斯认为:“正确地说,交换的正义是立约者的正义,也就是在买卖、雇佣、借贷、交换、物物交易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分配的正义则是公断人的正义,也就是确定‘什么合乎正义’的行为。在这种事情中,一个人受到人们推为公断人的信托后,如果履行了他的信托事项,就谓之将各人的本分额分配给了每一个人。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分配,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公道。”(22)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在这里讨论的是正义的市场概念,所有的价值都还原为市场价值,正义本身也就还原为了市场概念。但是,这段文本在《利维坦》中实际上是被霍布斯用来界定建国过程中契约的性质,而并不是描述自然状态中权力的市场竞争关系。第三处文本是在《利维坦》之外,麦克弗森还试图进一步将霍布斯还原到17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考察霍布斯论述英国内战的著作《比希莫特》,认为霍布斯所描述的英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社会。而麦克弗森提出的这一文本证据就更加外在了,能否用《比希莫特》中对英国描述的片段来证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是有待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极少提及英国的现实政治。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地方推论,霍布斯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时,并非只考虑一国一时,而是在处理更为普遍和长久的现代政治命题。
以上对几处文本证据的反驳实际上揭示出用占有式市场社会来解释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外在性,即如果按照霍布斯自身的文本逻辑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麦克弗森的这一预设过强,而丧失了对更广泛文本的解释力。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麦克弗森关于霍布斯理论中人性和自然状态的理解,就会遇到更为艰难的理论问题。根据前文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文明社会中法律和共同权力被移除的状态,换言之,自然状态是国家或社会解体后的状态。与自然状态的社会化相对应的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也是带有很强文明属性的社会人。更具体地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性实际上是占有式市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下的人。这一理解在方法上并没有偏离霍布斯的“分析—综合”方法,但是在实际解释中却有着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麦格弗森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自然状态是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的,并且这一社会性的特色是个人财产和权力的竞争。当他引入经济逻辑来界定社会性的时候,实际上把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残酷性给抹杀了。换言之,受过市场社会洗礼的人,是很难在撇除法律和共同权力的情况下必然产生激烈而普遍的权力对抗的。在麦克弗森不断用经济逻辑替代生命的保存这一生存逻辑的时候,也取消了霍布斯理论脉络中从自然状态到战争状态的必然性,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如果自然状态下的竞争没有那么残暴和无序,为什么人还需要从自然状态前进到国家状态呢?更进一步的批评是,如果自然状态真的是法律移除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自然状态最有可能演化为基于阶级分化的阶级统治状态,而这恰恰是麦克弗森批评霍布斯没有意识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通常状态。
除此之外,麦克弗森对于人性的阐释也很难获得霍布斯文本上的支持。在麦克弗森的整个解释框架中,市场社会不仅是理论的总体背景,而且实质性地塑造着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但是,根据他的解释,在自然状态中,人是受过市场社会塑造和文明教化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适合于过国家或社会生活的,并且首要的是商品的消费者。但是,霍布斯对此恐怕要持不同的看法。在《论公民》的第一章,霍布斯开宗明义地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在自然的意义上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命题,并且在后来的补注中解释道:“人是可以变得适应社会的,但不是通过自然,而是通过教育。”(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霍布斯虽然承认人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着一些社会性关系,但是这种社会性并不足以强大到保证人可以自然地过上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自然状态的解释,还是对人性的解释,麦克弗森的立场都过强了,以至于会损害霍布斯自身从人到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契约—利维坦的政治演进逻辑。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麦克弗森对道德义务和权利的解释,这也是霍布斯20世纪研究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已经对霍布斯具有道德学说达成共识,但对其道德学说的性质却有着诸多争议,正如麦克弗森在《占有式个人主义》一书中所注意到的那样,像施特劳斯(Leo Strauss)、泰勒(A.E.Taylor)、奥克肖特(M.Oakeshott)、瓦伦德(H.Warrender)等重要的霍布斯解释者都花了很大力气解释这一问题,而与这几位不同的是,麦克弗森提出,霍布斯是从事实推导出道德义务。麦克弗森提醒我们,纵览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权利和义务往往是间接推导出来的,以往的理论努力总是要借助“自然”(nature)或上帝的意志来决定人的道德义务和权利。如果缺乏外在的力量,人是很难设想义务理论的。但是这种情况在霍布斯这里有了决定性的倒转,他不再从外部世界寻求义务的根源,而是从人的内在中寻求。根据霍布斯的机械论理解,如上文阐释的那样,人是试图永远保持自身运动的装置,有着寻求自身持续运动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人这么做只是物体世界的规律,而无需外在强加某项特殊的道德体系。
麦克弗森从每个人都需要持续运动这一点看到了权利的来源,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持续运动的权利”。此外,这种要求自己身体持续运动的权利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除了来自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平等外,市场社会的预设也提供了另一种平等,“市场的假设使得霍布斯能够说人在不安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因此推出道德义务的必需性”。(24)在麦克弗森眼中,霍布斯在道德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阐释了符合市场社会的平等的道德义务观,这不仅将传统靠外在力量规定的价值观基础替换掉了,并且还终止了存在着等级差序的道德体系,也就从实质上消解了预设人之不平等的传统社会。基于自利和自我运动、自我引导的道德原则是能够被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接受并适用的原则,而这恰恰是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要义。
麦克弗森指出了霍布斯道德平等的两项重要因素:唯物主义机械论和市场社会。但是,在这两项因素中,后者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用麦克弗森的话说,“只有社会像市场社会这样碎片化,人才有可能被视为自我运动装置的个体”(25),只有在市场前提下,霍布斯才能将现代自然科学应用到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中来。此外,市场的存在才使得新的平等成为可能。传统的等级社会对不同阶层的权利的规定是不同的,并且需要超越性价值来维持社会的有效运转。市场社会自身带来了客观化的价值评价,即人的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而市场机制是客观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到别人头上。换言之,在麦克弗森看来,是市场社会的历史属性作用于作为装置的人,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人性,才使得霍布斯能够如此构建其理论体系。
麦克弗森的这一理解颇为新颖,并且试图将霍布斯的新科学层面的事实纳入到道德考量中来,但是,这一理解的解释力也存在很大的局限。下面,让我们看一下霍布斯在《论公民》和《利维坦》中是如何讨论权利的。
在《论公民》中,霍布斯第一次提到权利,他说:“如果一个人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命免遭死亡,这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应受指责,也不是与正确的理性相悖的。可以说,不与正确的理性相悖,就是按照正义和权利去行事的。‘权利’这个词确切的含义是每个人都有按照正确的理性去运用他的自然能力的自由。由此,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26)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如此讨论权利和自然权利:“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因为人们的状况正像上一章所讲的一样,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凡是他所能利用的东西,没有一种不能帮助他抵抗敌人,保全生命。这样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是这样。因此,当每一个人对每一事物的这种自然权利继续存在时,任何人不论如何强悍或聪明,都不可能获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许人们生活的时间。”(27)
从霍布斯的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权利概念要比麦克弗森的解释丰富得多。从机械论身体的自身维续可以为权利找到一个最初的起点,但是霍布斯笔下的权利与人与人对抗背景下的自我保存有着内在关联,并且霍布斯明确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对每一种事物,包括别人的身体,都拥有权利,这是麦克弗森所无法解释的。人对万物拥有权利实际上也消解了麦克弗森基于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预设,以及对自然状态社会性的理解。
以上两点对麦克弗森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霍布斯的角度来谈的,即如果按照霍布斯本人政治理论进展的逻辑来看,麦克弗森的解释存在预设过强和过度阐释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弗森并非忠实不疑的霍布斯学者和研究者。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试图揭示的那样,对于麦克弗森来说,解释霍布斯并非其首要的理论关切,他所要做的是用占有式个人主义来梳理17世纪以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从中找到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和缺陷,并为当下的民主理论找到新的可能性。在理解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所做的“六经注我”式的解释之后,站在霍布斯文本的立场对麦克弗森解释的细节错误进行批评的意义并不大,毕竟霍布斯只是麦克弗森本人政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其晚年对自由民主理论正面的修正上。
尽管麦克弗森不能被完全视为忠实不疑的霍布斯学者,但是并不表示他对霍布斯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事实恰恰相反,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思想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他对霍布斯的关键性“误读”实际上是看到了霍布斯政治逻辑难以逾越的困难。在这些关键性的地方,麦克弗森有意采取了一种符合他自己理论建构的解释路径。麦克弗森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对于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霍布斯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富有启发性。在笔者看来,麦克弗森为我们揭示了三条值得认真对待和继续阐发的线索。
第一,麦克弗森正确地把握到霍布斯政治哲学中自然科学与社会性分析的缝隙,即从纯粹的唯物主义机械论理解的人性是很难自然过渡到后来对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的讨论的。用霍布斯的话说,关于公民和国家的研究一方面是其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另一方面也可以撇开前两部分(第一哲学和物理学、论人)而单独写就。虽然霍布斯在《论公民》中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而在《利维坦》中采取的是前一种方法,但是通过哲学把握的人性与通过观察人而获得的人性结论之间存在着张力。在其背后,进一步的理论命题是:第一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洞见在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麦克弗森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发的社会决定的。如果这一解释难以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梳理和把握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自然哲学要素和人文主义元素就是非常必要的。在20世纪对霍布斯的解释中,施特劳斯对霍布斯人文主义的面相做了较多的阐释,但是霍布斯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仍然有待深入发掘。 第二条线索是麦克弗森对市场社会的平等这一重要特征的揭示,无论用市场社会来解释平等是否成立,麦克弗森确实揭示出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传统政治是基于等级和人的自然差别的,而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消失了。在麦克弗森的理论中,这一传统与现代的差别被表述为传统社会与市场社会的差异。在新的占有式市场社会中,没有对工作的权威性安排和权威性奖励;契约有着权威性的定义,并且是被强制的;每个人都理性地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劳动的能力造就了自己的财产,并且财产是可转让的;土地和资源由个人所有,也是可转让的;有些个体想要比他们已有的更多的利益或权力;有些个体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能力、技能或财产。现代政治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必须面对平等的个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现代政治的这一特征最初是由马基雅维利系统阐发的,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对“人民一贵族”的发现就开启了这一进程,直到19世纪,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最终系统阐释了平等与民主的本性。在思想史的进程中,霍布斯通过建立主权者与每一个个体的直接联系的方式,最为形象而深刻地阐释出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麦克弗森在这一点的理解上可谓抓住了要害。
第三条线索是对主权者性质的理解。按照麦克弗森的逻辑,霍布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本质,即掌握资本和劳动力的资产阶级统治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利维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我们对照20世纪另一位深受霍布斯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解释,就可以看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施密特看来,霍布斯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将国家即利维坦的道德中立化以及机械装置化,而当国家变成了一架机器之后,就不再具备任何价值属性,这将最终导致现代政治的内在困境。麦克弗森和施密特的理解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两人对于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即现代政治和主权者背后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规定性。麦克弗森为霍布斯的现代主权者加上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批评的那样,麦克弗森的理论强加是颇为牵强的,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社会在17世纪并非主流,也不是霍布斯这一代哲学家思考的首要命题。只是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系统思考现代商业社会下的政治问题。但是,麦克弗森的时空错置并不代表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恰好揭示出霍布斯机械国家的另一面。因为,按照霍布斯自身的观点来看,现代的主权者最终仍要落在自然人身上,而不能完全成为一架机器。这样一来,中立化的机械如何与带有很强自然属性的人发生关联,现代国家除了公共安全的提供之外,是否还应该以及是否有能力谈论实质性的价值问题仍是我们现代人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
纵览20世纪的霍布斯研究,麦克弗森独具特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其霍布斯研究主要用意并不是针对霍布斯提出新的阐释范式,而是要将霍布斯纳入他对西方自由主义及民主理论的反思之中。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说,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为我们重新考察现代政治的发端提供了重要契机,他通过引入竞争性市场社会和占有式个人主义,为霍布斯提供了崭新的理解范式,这一理论预设过强的解读成为麦克弗森自身理论构建的重要起点。如果回到霍布斯的政治逻辑,我们会发现,麦克弗森在市场社会的引入和新道德范式的讨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这些阐释上存在的问题是霍布斯自身思想内部所包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导致的。透过这些明显带有麦克弗森个人特征的阐释,我们看到他对霍布斯关键议题的深刻把握能力。在这些关键点上,后来的研究者需要认真对待麦克弗森打开的阐释空间以及提供的线索,因为正如麦克弗森所言,在今天继续阅读霍布斯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我们自身仍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C.B.MacPherson,"Humanist Democracy and Elusive Marxism:A Response to Minogue and Svacek",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76,Vol.9,No.3,pp.423-430.
②C.B.MacPherson,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and Other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6.
③④⑥(21)C.B.MacPherson,"Introduction",in Thomas Hobbes,Leviathan,Penguin,1968,pp.9-12,pp.9-12,p.28,p.60.
⑤(23)(26)[英]霍布斯:《论公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7-8页。
⑦⑩(12)(16)(17)(18)(19)(24)(25)C 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p.77,p.18,p.22,p.38,p.38,p.38,p.39,p.48,p.79.
⑧⑨(13)(14)(15)(20)(22)(27)[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72、93-94、64、64、269、115、97-98页。
(11)[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