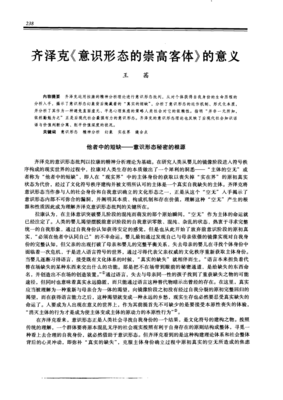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是一本由[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需要再读
●译本里用来理解前后文关系的关联词太少了,虽然在英语语境里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中文语境里会有很多歧义= =
●起效的永久失败。缝合点。
●意识形态是实在界征兆。齐泽克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拉康式阐释极具爆发力,他的笑话是从哪里搜集来的,看起来渗透着原乐。
●还算是十五年后的大规模重译···竟然能把黑格尔的基本概念译成这样,说一句无知无识不学无术也不过分~~译后记那语气一种愚蠢的中二~~ 如果能补上拉康的基本概念解释就好了。值得多多研读。
●解毒之书
●一个提醒,先看齐泽克的笑话,不然这书啃完,笑话就不好笑了像吃屎。回到黑格尔这座高山上为其增加了马克思的实践性和积极,以及拉康的无意识和分析图式作为调停,改造了意识形态,也就是康德以来一直没有完善的「我们以为感知的客观世界」。从我读书意图也就是了解意识形态上,我对这书满意了,可另一个角度,本书并非哥白尼式的创见,而是自己真诚地明确了只是对旧框架进行修补的一种托勒密化。还有我真的对齐泽克硕喜欢张艺谋的老片子这件事有意见。
●2017.11.3- 2018.8.19-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读后感(一):开帖挖个坑慢慢填
没别的意思,只因这本书肯定是要再版的,为校对工作尽绵薄之力尔。
这本书里所有的「决断」都是观念论哲学在国内通行译法的「规定」(英文determination,德文Bestimmung)。该词的意思是我们人为对对象所作出的概念上的规定。
这本书中所有的「超验」都是目前国内通行译法中的「先验」(英文transcendental,德文transzendental),在康德原文语境下指「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不过现如今该词已经延伸出「某物的可能性的条件」的意思了。而原书中所有的「先验」都是通行译法中的「先天」(拉丁文a priori),康德语境中意为:先于经验的且在经验世界中普遍必然的某物。
173:第四行,英文标错。 p174:第二行,对照原文(二版p154)可发现,这里说的是“根本的不对称”(fundamental asymmetry) p177:第一个引文中,不是我们的当代人,而是“their contemporary”,即卢梭的同代人读不懂卢梭写的书。第二个引文的最后一句,直译过来是:被压抑者只有在某个既定时刻,已经是一个东西时,它才会是一个东西。 p179:第二段第一行,“理想主义”应为“观念论” 以下为自己的草稿之后再补充完整 p81 through并非通过 p70 renew 重新开始 漏句子 p39 相信自己已经相信了的 p95 207 应该而非必须 p206 impossible p128 hypnotic voice p173 discontinuity p280 无限 各种 as such 二版原文250 有限 几乎所有的in so far as都译错了,这是“因为”的意思。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读后感(二):否定性與唯物主義
為了不被鎖,直接發鏈接算了:
qq.com
庸俗的唯物主义(不如说是恋物癖)把物质当成了某种可以触碰的自明的东西,但是,唯物主义之所以不等于实证主义,就是因为它不是自明的,而是破坏自明性——与其说唯物主义是肯定物质,不如说是承认物质是不可迴避的——物质本身就是否定性的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读后感(三):我为什么要读齐泽克
几年前,在看哲学类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变态电影指南》的片子进入了我的视野,一个胖胖的大胡子用一些我很喜欢的另类话语解读电影。
后来我在方所看书的时候,偶然从马克思一栏中翻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被他神经质的表达吸引,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齐泽克,就是楼上的齐泽克。
如此说来,齐泽克吸引我应该是必然,毕竟我也很变态。
但是阅读齐泽克并不是一件有阅读快感的事情,他的作品习惯反讽,反讽的前提是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否则,就只能感觉他在笑,我在尴尬。
齐泽克的这本书,于我而言难点很多,包括其一,主语问题。大概是语法结构的问题,译者在文末也有提到,齐泽克的用笔习惯有些特别,于是你明显能感觉到文中的句子不知道它的主语在哪里。以前言为例,因为主语的错位,我曾长时间滞留在这里,不知如何进行下去。因为你能单独看懂每个句子,一旦联系上下文,便不太知道主语该从哪个句子中提取,就如同对黑格尔的描述,我无法判断他是褒是贬。
其二。对黑格尔的认同,以及对康德的讽刺。对我造成的困扰,倒不是他明显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什么的唯心,唯物。而是他对黑格尔无所不包,登峰造极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另类解读的辩护。以齐泽克对马克思的革命观的警惕,以及对后马克思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的赞同,这是很难理解的。对康德的讽刺倒还好,毕竟康德本身就拖着形而上学的尾巴。
其三,引用拉康时大量符号化阐述。
然而这本书里也有我想要认识和试图理解的东西。其一,是阿尔都塞对拉康的主体性的误认是如何完成的。其二,极权的崇高客体是如何在社会大行其道的。其三意识形态是如何掩盖社会真相的。
齐泽克的专长似乎是与寻常理论作对,比如他会说对黑格尔无所不包的批判是老生常谈,说指责弗洛伊德泛性主义是陈词滥调,经典的意识形态在狗智主义面前武功尽废,信仰不是私密内在,而是外在的,幻觉位于现实一方,构建我们的现实,掩藏不可能的实在界的创伤性内核。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设定为内容和形式,在他看来是寻常庸俗的解读,过分简单化。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因为齐泽克的书,艰涩不易懂,所以才免去了审查的灾难。
对我而言,整本书都好像在阐释“黑格尔把认识论上的无能转化为本体论上的不可能”。
康德是哲学面目全非的掘墓人,其重要功绩就在于对人认识上无能的确认,确实他把人不能认知的东西,都划出现象之外,作为物自体存在,连接现象和物自体的方式是审美。这是我以前获得的知识。
齐泽克看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崇高,一种否定的消极之维,去调停二者的矛盾,这种调停,于齐泽克而言,就是消灭对抗。
这就像社会矛盾在李泽厚先生的审美之维之下,奇迹般的达到了大同一样。
言下之意,还是有真理存在的,尽管超出我们的认知,但作为一种绝对的律令,它成了淫秽的服从。
然而,本体轮不可能,本质背后一无所有。
如同齐泽克一再提到的犹太人的例子,纳粹把犹太人视为入侵者,视为社会矛盾的一个征兆,一个无法抚平的凸点,是因为社会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犹太人成了欲望的幻想框架,进入了主体的欲望。
我们要做的是阐释这个征兆,穿越幻想,知道除了意识形态的欺骗,其实什么也没有。
正如崇高客体的欺骗。它只是原质偶然性的占领了大对体匮乏的空位,它只是大对体匮乏的显现,我们必须要明白它什么都不是。
一切意义都是回溯性的建构,时间并非线性的,进化论试样的前行。
它总是不断重复,遵循主人能指的委任,重新获得意义,就像大话西游的月光宝盒一样。另外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齐泽克看来,仍然有形而上学的在场。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要做的就是破坏社会,哲学等一切的整体性。
就像资本的局限就是资本自身一样。
破坏的并不是可怕的的力量,它是推动社会,或者说社会正是围绕着它存在的,它就是不可化约的实在界硬核。否认它的存在,或者说把它倒置为一个能指,比如外来人——犹太人的入侵,都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可能,这就是善的凝视。
我们必须明白,很多我们以为的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都是日常生活的局限,是我们的移情幻想,总是催眠自己假定存在着真理,认清局限,和认识自己认识的不全面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不是去消除鸿沟,才是我们走出意识形态幻觉的途径。
另外阿尔都塞对拉康主体性的误认,我暂时的理解是,阿尔都塞的主体是在符号化结构中被大对体异化的主体,而拉康那里,因为主体和大对体都存在着匮乏,所以主体在实在界还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确保自己不是空无一物。
齐泽克这本书里还有好多重点,我没法把他们全都联系起来。这篇读书笔记就写到这吧,再写我要轰,真的太难了,这套题太难了。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读后感(四):拜物教与公私之辩
现在看来,当下最大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者是被人演绎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而是拜物教——除了消费和商品之外别无他物。这种拜物教看起来是一种物质世界的规律,但是其起点恰好是完全反唯物主义的——拜物教已经预定了消费和市场规则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这里和资本主义的运行——它所创造的人的自我意识吻合: 在某种程度上,人就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对他们来说,只说“我是我”就足够了。人是首先在他人身上看到并认出自己的。彼得只能通过拿他与作为同类存在的保罗进行比较,才能确立他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因此,只有在保罗扮演自己的角色、展示自己的性格时,在彼得看来,保罗才成了那种类型的人。 ——《资本论》 这样的误认(misrecognition)除了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可以发生在“物与物的关系”中。马克思在谈及价值表现的形式时,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只有把商品乙作为自己的参照物,商品甲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商品乙成了商品甲的等价物。在价值关系中,商品乙的自然形式(商品乙的使用价值,它的实证的、经验的属性),可以用来充当商品甲的价值形式。换言之,商品乙的躯体成了商品甲的镜子,商品甲可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简单来说,商品拜物教的“意识”使得资本主义自身已由主体之间的关系转至“物与物”的关系:以统治和奴役(如主人与其奴隶等)的人际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再一目了然; 用马克思的精确概括说,这种关系在“物与物即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外表下”,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一旦挖掘某个陷入拜物教的人的心理最脆弱,即其依托于消费和物质享受的表层幻象——拜物教徒并不是掌握了物质,而是被物质掌握,而困在物表象之中,变成了受物关系支配的资本主义的症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要想反复消解它自身的根本性的、构成性的不平衡,就要与这种矛盾达成妥协,唯一维持自身的方式就是永不停息地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悖论:资本主义能够把它的局限,把它的无能为力,转化为它的力量之源:它越是“腐烂”,它的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为了生存进行内部革命:资本主义只有对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不断进行革命,才能死里逃生,倘若“保持不变”,它必死无疑。 除了四种话语,拉康还提出了资本主义话语。主人能指在资本主义的辞说中被安置在真理的位置,它被缩减为一个概括主体的能指划杠。在从主体到它缺失的中介化中,这个强制意味着这个在大他者括号中的赌金,通过扭曲,主体处于媒介的位置,但是媒介可能沦陷于屈从在“空”、主人的这些词和事情的疯狂中。这里没有一个主体的部分能够逃避在一个仅仅趋向于无穷无尽的消费中证实的东西。在债务之外却没有自由,因此总是奉献给操纵、控制、适应、估价。 这个暗中操纵一切的东西存在,只是他不直接现身。消费主义最大的诡计是顾名思义的——消费就是欺骗,而这个最大的欺骗者能够借助消费来继续生产。消费主义作为最大的“生产者”,它“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也就是个人和个人的分离。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个体的内外之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以外部性这个词为例,他们把企业的个体完全视作一个可以自主以与企业外分离的主体,事实上只要谈到所谓的外部性,就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强制分离,在企业法人这里则被视为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这样就能给资本的无限增殖保驾护航。新自由主义更是登峰造极,他们要求的“小政府”实际上是面对企业(资本)利益的时候变小,而在所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者面前,将治理功能(硬性的镇压或者软性的收买)发挥到最大。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出,为什么个人主义的外部不成为其外部。在康德《何以启蒙》中,与“私”截然相对的“公”所要表达的是:“私”不是指与公共联结(communalties)相对的个人,而是指某人认同这个公共制度性的秩序;"公"是某人的理性践行这个跨国界的普遍性,因此,悖论在于,个人是作为单一个体分享“公”领域,而"单一的个人”是从他的实体性的公共认同中抽离出来的。不仅如此,他甚至与自己的实体性的公共认同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成为彻底的单一的人,只有寄身于各种公共认同的间隙,才是真正的普遍的人,那么,个人的外部到底是他者,还是以他者呈现的我?回答这一问题的依然是大他者——这个从自我意识的挣扎求生中“跳出来”的“人”,它进行符号编码来使得意指系统的建立与运行成为可能。 大他者是必然性的化身——它是来自人的无力本身,而人进入社会之后,大他者就已经密锣紧鼓地编织着符号秩序,而为了维护这一秩序的稳固,它则成为了现实的神祗——也是那个推动欲望的不可见的手。这和市场拜物教徒的认知非常像,他们同样机械地复读着“看不见的手”的万能,以及时刻消失在一些人手中,又集中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的私有财产(隐性的掠夺)。 民族国家的悖论也是如此,与其说民族国家是民族解放的产物,不如说是新的压抑的产生。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面具,却是以各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和边界为基础的。而这里面的大他者如影随形,它以一个例外者来建立普遍秩序——不管是哪个国家所建立的例外论(如美国),都是强行使得落后民族卷入世界市场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新型民族当中,这一原初压抑的产物便诞生了另一种民族国家——被殖民者的创伤却塑造了新兴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它所产生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剩余享乐——主权神话就是起到了这一可望不可即的兴奋,只有爱国者才能够享用,但是,一旦无法维持全球化和国族的神话,那就会导致崩溃——这一方面是客观的、不可控的灾难,这并非自然界的不可抗力,资本主义的不可调解的矛盾才是动力因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受压迫者的军队。而现在的腐朽的教会是不会揭示这一真理的,即使保罗早就说过:“上帝已经安排了这样的机体,对劣等成员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哥林多前书 12:24),作为“军队”的共同体通过对等级制度的倒转来实现批判性的平等——也就是打击“富有”、“卓越”或对任何可能的自恋位置的拜物教。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读后感(五):不过我还剩最后一章没看,先存一下
感觉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总结一下就这三板斧。我是觉得我读书读岔了。
关于主张:主张总是武断的,总是瞧不起人的。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用以下这句话表述:【你不知道你生活的痛苦来自何处,让我来告诉你。】相当于:【你活得懵懵懂懂,只有我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哪怕最谦逊的主张,都暗含着对其他主张的不谦逊的批判。因此主张总是建立在贬低人的基础上,不贬低人的主张是不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主张总是蕴含着言语暴力。)区别只在于这一主张是暗搓搓地贬低人,还是明晃晃地贬低人。那当然选明晃晃地贬低人。暗搓搓地贬低人是为了让你相信,而明晃晃地贬低人只会激怒你。显然,比起面对朋友,我们总是对敌人保持着更犀利的洞察和批判。只有意识到非暴力主张的不可能,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非暴力主张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抵消其中所蕴含的暴力。
关于政治中立:政治总是不中立的,任何一种政治观点都意味着对其他的政治观点的批判。哪怕看起来最中立,或者最政治无涉的观点,其实都是在说【你们都是被政治意识形态俘获的,因而都是偏激的,只有像我这样不参与政治,才是最正确的政治观点】。其他的政治观点充其量都只是在反对与其相反的政治观点,而政治中立反对的是全部的政治观点,因此政治中立是最偏激的政治观点。而激进政治立场由于明目张胆地表现出其激进内核,我们反而能对其保持警惕。只有意识到政治中立的不可能,我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中立,也就意味着对哪怕完全对立的政治观点抱持宽容和交流对话的意愿。
(差不多也因为这个窝现在更喜欢讲述而不是展示的小说,就比起假装整个故事在自我运作,还是作者现身明目张胆地摆弄词句干预故事比较真诚。。)
彻底批判的关键就在于拆解掉整体,揭露整体的不可能:整体真理不存在,任何整体都不存在,因此任何宣称自己掌握了整体真理的主张都是意识形态幻象。而关键就在于穿越这一幻象,暴露出背后的创伤性内核(忍不住要用,学术黑话超酷的!),所有创伤性内核都等同于《海伯利安》里那个神学故事: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上帝借这个要求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你为我无条件牺牲,你还能继续信我吗?】国家向饭圈女孩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我要你为我牺牲爱豆,你还能继续信我吗?】同样,民主自由向自由派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我要你为我感到被人群孤立,你还能继续信我吗?】
也就是说,重点就在于揭露这一要求是无条件的,无回报的,是纯粹的牺牲,是无意义的苦难。基督教围绕着这一创伤性内核建立起的是上帝爱世人的幻象:【虽然你为上帝牺牲了,但上帝爱你啊。】国家主义建起的是国家发展的幻象:【虽然你为国家牺牲了,但随着国家发展一切现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和改善,因此牺牲是有意义的。】民主自由建起的也是同样的幻象:【虽然你为民主自由牺牲了,但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救中国,因此国家力量的最终失败便是你的回报。】幻象赋予现实苦难以意义,赋予世界的丑陋以想象的天国。必须穿越这一幻象,直面创伤性内核:上帝不爱你;国家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样民主自由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并不必然会增大问题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加缪的西西弗斯:推石头的意义就在于推石头本身,而推石头本身为什么有意义?哇这么壮美一个悲剧形象你都不信。你美学力不行。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的信奉者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信仰的是重幻象。饭圈指责西方媒体是被操纵的,这很好,那么按理说解构的链条是无限的,解构一个就等于解构全部,他也应该往下推,得出【我国媒体也是被操纵的】这一结论。但没有,有东西挡住了这一回身审视:信仰的窄门。【越过窄门的人拥有无比的信心,他不会也不需要往外看】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越过窄门的人拥有无比的信心,他不会也不需要往里看,看看自己到底在信什么。因为一旦他往里看了,那他也就退出这道窄门了。】
知道幻象的存在和穿越幻象之间存在区别。(窝要拿乔碧萝举例了窝好害怕)很明显,直男消费并从中获得快感的是【乔碧萝好看】这一幻象,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乔碧萝不好看(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直男の单纯),或者至少存在着不好看的可能性?他们选择不去相信。换一个场景:【我知道他不爱我,但我不愿相信,所以我仍然假装他爱我并且这样去爱他。】直到乔碧萝露脸了,也就是暴露出背后的创伤性内核了,幻象才轰然倒塌,直男收获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破灭留下的废墟是一样的:无非是创伤性体验和外围者的放肆大笑。
意识形态的信奉者身处半知不知的状态,亦即【知道但不相信】,因此他们没有被彻底异化,仍然保有批判性。也就是为什么窝看的一篇讲帝吧出征的文章里写:出征者往往对外表现出民族主义,对内表现出现实批判主义。这个月为疫苗事件发声,下个月出征脸书。
这也是意识形态为什么无法通过言语和逻辑驳倒,它的幻象构筑在信仰这一核心上。你可以指出幻象上的漏洞,但无法指出核心有问题,因为信仰是不会被理性玷污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核心是崇高客体(又一个超酷的!!),因此是不死的,表述如下:苏联确实是场灾难,但并不代表共产主义有问题,只要我们好好搞,共产主义还是能实现的;这届政府确实不行,但这不代表民主有问题,只要我们下次投票好好投,问题还是能解决的;社会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问题,但这不代表国家主义有问题,只要我们给国家力量以岁月,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不是说崇高客体就不会受到经验现实的冲击,只不过这种冲击无法通过语言和逻辑论证来完成,只能通过个体创伤。冯古内特讲他和战友回国,都不会聊起战场上的事,即使想聊也不知道怎么说。创伤和信仰是同构的,他们都无法诉诸理性,或者为语言所纾解。它们只是在那,构成了个体生命的沉默内核。如果创伤的痛苦大过了直面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所带来的痛苦,那么意识形态幻象也就被撕破了。只要铁拳足够重,说不信就不信。问题是,很多时候铁拳只不过把人从某个意识形态捶到了另一个意识形态,从对某物的无理由相信转成对某物的无理由否定。考察一下某些自由派的心路历程:【xx事让我意识到了国家是不可信的,渐进改良是不可能的。】可严格来讲xx事只是个经验个案,要把它升华到否定整个体制的地步,这一飞跃如果不靠信仰力我觉得真的办不到。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会因为爱泼斯坦事件不再相信民主自由的。德国战败后,东德很多纳粹主义者转成了共产主义信徒,这一无缝切换讲的便是信仰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东西可信。
(考虑一下这个表述:【这个国家都干出这种事了,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地相信它呢?】崇高客体就是这一执。或者换个表述:【这事都把你生活搞得一团糟了,你怎么还不释怀呢,你怎么就不能放下往前看呢?】齐泽克讲创口正在杀死我,但是没了这个创口我就什么也不是。那我当然要执了,如果都没我执了,那岂不得遁入空门。当然保持这一执的前提往往就是把坏事归结为对面意识形态的传播学运作,这又揭示出某种矛盾了:既然对面意识形态有传播学运作,你信的这个就没有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它没有所以我信它,而是我信它所以我选择性失明。【我爱他,所以我假装没看见他这点小心思。】)
穿越幻象的意识形态批判问题是敌我两伤的。传统上,批判资本主义这样讲:经济危机,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可能靠改良解决,所以要搞共产主义。批判共产主义这样讲:走向极权是共产主义的必然逻辑,所以不能搞共产主义。而现在穿越一下幻象:没有固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都有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样要么就导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谁也不信,要么就是【国外也这样】的反正要信一个,不如信主流意识形态抱团取暖。阿伦特讲她一辈子也没有信过一个意识形态,她爱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问题是人类也不存在啊,你要爱人,就意味着既要爱犹太人也要爱纳粹分子,既要爱国家主义者也要爱自由派,既要爱受害者也要爱加害人。这爱也太痛苦,太难了。
或说:我只爱值得爱的人,我相信我朴素的正义观。那问题当然也是朴素并不存在咯。不是因为这一正义观是朴素的所以我相信,而是因为我相信了,所以它是朴素的。对于左派来说,实现共产主义难道不是种朴素正义吗?难道他们会承认阶级是种理论建构,而不是朴素地、一直存在着的?他们还真的会承认,齐泽克不就是左派嘛233.左派习惯于互相伤害,说话又好听,窝最喜欢里面了。
只有悲观主义者才不相信意识形态幻象,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讲,正因为他没能相信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因此悲观了起来。《年轻的教宗》里,前期裘花说神父都是懦夫,因为他们不敢爱人,不敢面对爱他人所可能带来的痛苦,因此转而爱上帝。搞的就是这种批判。不过这剧里裘花之所以秉持这一观点是因为过去有创伤,后来随着创伤逐渐和解(这一和解也是通过新的创伤达成了)回归了正统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讲相信意识形态的是正常人,不相信的才比较容易得神经病。
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出发:【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所以要吃鸦片是因为资本主义太万恶了,所以鸦片有必要,等到实现共产主义就不用鸦片了】;现在的批判表述是:【意识形态是人民的鸦片,之所以要吃鸦片是因为日常现实充满对抗性充满矛盾充满不完美,而且这些东西很可能会继续充满下去。】
齐泽克为民主做的辩护也是基于这一批判之上的。辩护的不是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而是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不可能的民主:【掩藏我们称之为形式民主(联系上下文指的是选举)的彻头彻尾的非理性的特征,是徒劳的:选举时,社会转入了随机过程。只有接受这样的风险,只有准备把自己的命运移交给非理性的运气,民主才是可能的……民主使一切种类的操纵、腐败、蛊惑人心的统治等成为可能,这倒是真的。但一旦我们除去了诸如此类的畸变的可能,我们就会失去民主本身……】这真的不是在劝退吗233
这里的重点不在民主而在真正:社会的真正面貌是对抗性的、分裂的、争吵不断的、存在结构性利益分歧的。它割裂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不得不靠暴力(武装暴力或者意识形态暴力)才能组建成共同体。只有民主才能反映出这一真正的社会面貌,而不是捏造出某种人民的真正利益、社会共识、公序良俗。民意不存在,只有【人民随机发出、摇摆不定的意见,这样的意见屈从于各种煽动和混乱】。只有当某样事物想要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时,人民才存在。
问:为什么相信民主?
答:因为民主是唯一真诚的社会形式,它不建构美好幻象。不民主国家隐藏起自身政治的黑暗腐败,隐藏起政治决策中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虚构出一个人民的真正利益以它为盾和矛。而民主国家就比较厉害了,它(一定程度上)露给你看。我们应当相信这一真诚。
(窝好像知道窝为什么信这一套了,这不就窝的恋爱观嘛。。恋爱里唯一重要的是真诚。。)
不过窝觉得这一辩护存在问题。反驳1:既然不存在人民的真正利益,那么为什么存在社会的真正面貌呢?既然整全性的真理不可能,那么很显然这所谓的社会真实面貌也只能是一家之言,可以表述为名言1:【我说不过你。我不说了。我保留意见。】或者名言2:【后现代又不止齐泽克一家(干嘛一定信他)。】
反驳2:虽说民主没有建构美好幻象,但它给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意义幻象:【我们要追求政治自由,不是政治自由能够提供什么美好保证,而是政治自由本身就有意义。】那么名言3来了:【政治自由到底有什么好?】这问题当然可以回溯到上面社会的真正面貌上,进而回溯到反驳1,但本身问出这个问题就足够糟糕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根基只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上而不是政治共识上才会足够稳固,因为知识的特性就在于会被反复质疑。你很难想象一个基督教徒整天闲下来就思考上帝存不存在,不然也太信仰失格了。只有遭遇重大危机了(比如亲友去世),他们才会迫不得已思考。齐泽克:【所以,尽管事实上只存在例外和畸变,普遍的民主概念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虚构,依然是符号性事实,没有它,形式上五花八门的有效民主就无法再生产自己。】窝觉得整个启蒙运动就是场实现民主自由信仰之跃(由政治共识飞跃成政治信念)的神学运动,你国错过了窗口期又不巧赶上后现代那还有啥好讲的等大洪水好了。所以你国80年代貌似形成了政治共识的那拨人到现在仍然照样整段垮掉(不,窝不知道,窝瞎讲的)。
在这个意义上窝感觉齐泽克批判的没德里达彻底,因为仍然要靠一个虚构的普遍民主,以及对这一民主概念的信念。德里达讲【无共识的共同体】,彻底是彻底,听上去像无政府主义,怎么讲,梦里什么都有。
(窝没看过德里达,也没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书,只是单纯用窝的朴素智商想了想,感觉不大行。)
(后面第三章开始将拉康和德里达的区别了。窝不懂拉康,也不懂德里达,窝啥也不懂,就不大想往下看了。)
(还有齐泽克对革命的辩护,窝也没怎么看懂,好烦哦)
woc写到这感觉整个都讲岔了,就快感、剩余快感这么酷炫的词都没用上感觉好亏。窝觉得这里面有个转移,现代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传统的神学信念上的,而是建立在快感之上的。比如基督教是建立在上帝存在这件事上的,一旦上帝不存在,那我也就不信教了。但是爱豆就不是这样了,饭圈清楚知道自己的爱豆是卖人设的,实际上他们本身就参与了爱豆媒体形象的建构(刷热度,冷处理负面新闻),但没关系,爱豆真人和人设不一致没关系,人设不塌就行。这里重要的就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真假值,而是意识形态是否能提供快感。这里的快感必须做个很诡的斯德哥尔摩症式的理解:不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愿意忍受他的虐待;而是因为我受了他的虐待,所以我(不得不)爱他。虐待不断创造着爱意。因此,追星的快感也来源于爱豆和其人设之间的张力:不是因为我喜欢我的爱豆,所以我不愿意看到他人设崩塌,所以我拼命刷热度;而是我不愿意看到他人设崩塌,所以我拼命刷热度,所以我喜欢他。
(话说窝不太理解人设崩塌这回事。粉爱豆难道不是因为爱豆长得好看吗!)
这里面有一个虚位以待:正是有了我的参与,这一幻象才能成立。国家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国家主义许诺的幻象和现实之间存在距离,这一距离召唤着他们去建设国家,也正是在这种被激发出来的建设热情中,意识形态快感产生了。《真探》里拉斯特讲宗教为什么能吸引人:正是因为教徒会感觉【啊,这整个教义都是在讲我,都是为了我,都是在等待我。】
意识形态幻象是一套提供意义的体系,古典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只需要接受幻象抛出的意义就可以了,现代人就比较厉害可以自己取用体系中的资源从而创造意义(如饭圈将中国重构成阿中哥哥,它本身和官方的较为严肃的意识形态存在差距。而对于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也必须将大帝重构成维尼熊,自身的意识形态才能更好传播),这就是个饭圈逻辑:我本身就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创造和变形,我对意识形态的虚构性一清二楚,但没关系,真不真不要紧,爽就完事了。应当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信奉理解为文学评论,或者更进一步,是伪书评。这本书存不存在不要紧,我这不把书评写出来了吗。换个场景想一下:我们完全可以一边大呼【哇这片子好套路啊】一边看得津津有味。
再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搞对抗、分裂的不一定是敌人,对抗分裂也可以,而且必然同样存在于朋友之间。朋友和陌生人有了矛盾,找我站他,那我当然站他我又不认识那个陌生人。但如果是我的一个朋友和另一个朋友之间有了冲突,那我就很为难了。这正是我们应该将自己放置的位置:夹在两个朋友之间,矛盾不已。
问:可我和朋友之间有友谊啊,我怎么可能将某个和我无亲无故的人设想成朋友。
答:仔细考察一下这段友谊就会发现,实际上它充斥着偶然和巧合,实际上说不准你们就没能成为朋友。因此,你不该对这段友谊看得太重,它不过是巧合的叠加而已。同样,你也只是偶然降生于这个国家,说不准你就降生在其他地方,因此,花太多时间爱国也没意思。实际上,再仔细想想,好像任何东西都没理由去爱(逐渐失控……总之,就像那谁讲的,要【严肃对待自身信念中的偶然性】。一旦你尝试去处理这份偶然性,你就会与你的敌人亲切起来。(可能)
虽然转变最后还是要靠创伤性体验完成,但窝觉得这种理论批判的意义就在于铺路吧。就好像我整天在你耳边叨叨他明显不爱你他明显不爱你,事先种下怀疑的种子这样,虽然不一定能结果,至少也是种希望吧。毕竟现代人的命运就是不抱希望地行动。推石头嘛。只不过加缪没有讲的那些:腰酸背痛、鞋里进了石子、身上一股汗臭、以及石头滚回山脚时西西弗斯漫长而孤独的下坡路,都得由我们来经历。
(显然这也是种意识形态幻象,只不过美学形象取代了神学形象。这应该是快感和崇高客体的最终诠释:美学象征。西西弗斯为什么能表明我们的境况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愿意搞这种自我感动。我们没有理由去爱,但这不代表我们就没有爱。爱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