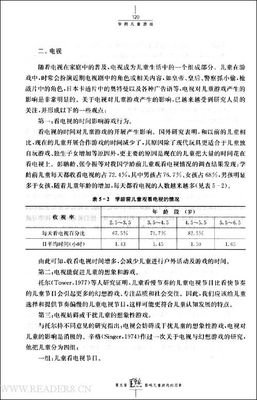
《小镇生活指南》是一本由林培源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80,页数:202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镇生活指南》读后感(一):普通的读后感
只是一个语文不及格的普通大专学生,写得糟糕见谅,后续应该会更新
奥黛
小说的第一篇是以“奥黛”为名的文章。奥黛的意思虽然没有在文章中完整地给出来,但那时通过文章描述,我们可以明白是指越南姿娘的民族传统服装。奥黛在这篇文章中起到了串联全文的作用。小说中关于奥黛这一件衣物引发的事件,我印象深刻的有阿雄通过奥黛治好了他因为战争而引发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导致的勃起障碍(这一部分的描写让我有一些阅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的感觉),还有阿雄让特殊行当服务业工作人员穿上来服侍他,以及最后的幻觉段。不过我认为“奥黛”这个标题并不仅仅是在指越南姿娘的传统服装这一层意思,更可能包含有“越南姿娘陈文瑛“这一个符号的意思。
在叙述上作者使用了双线叙述法,一条线是越南老婆跑了之后的描写,一条是阿雄是怎么认识陈文瑛的前因后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悬念及新颖感引人入胜(虽然也不新了就是)。按照内容分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阿雄和陈文瑛认识之前的部分;二是阿雄和陈文瑛相处期间的部分;三是陈文瑛跑路了之后的部分。这三部分的篇幅安排都很恰当,没有过长而起了“喧宾夺主”的副作用,也没有篇幅过于短小而使得描写过于苍白无力,每个部分都有不错的剧情来进行很好的填充。
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两个,即:阿雄,陈文瑛。阿雄这个形象代表着普通的潮汕中年男子,表面上是一个没有宏图霸业想要实现,只想着努力的过好自己的普通的每一天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养蜂人养一天蜂的角色;实际上却是一个因为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士兵,因为战争而引发了PTSD而勃起不能的悲情角色。他很想让自己从ED中恢复过来,但是用尽各种方式都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治疗不好这份源自越战的PTSD。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当他看到穿着奥黛的女子的时候,他惊奇的发现,自己的病好了!这一个剧情段落要分析的话可以联想很多,ED象征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陷入了绝望,而看到穿着奥黛的女子后恢复过来,似乎象征着,只要还有女人可以cao生活就还有希望,就还有盼头。(这么说似乎有一些渡边淳一的意味?)陈文瑛从人物形象上来看,她有着吃苦耐劳,勤劳能干,不甘心于命运的优点,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悲情的女子,作者通过对她过去经历的适当留白使得读者对她的过去颇感兴趣,她何以沦落到要漂洋过海来“卖身”给一个之前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就像是今日的乌克兰一样,作者可能也有着国弱被人欺的内涵吧。
那么,这两个不幸的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到幸福吗?作者通过孩子的流产,给了这一个问题,一个令人无奈的答案。
文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句子有:“好像越南话和潮汕话之间只隔了一层膜,只要轻轻的一捅,就通了。”“当年没搞死你们越南人,今天轮到你来搞我!”“甜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为什么还有人喜欢甜食?”
《小镇生活指南》读后感(二):小镇里的尴尬人
拖了好几天,这一篇不能算书评,最多算一篇非专业读者的读后杂感。面对文学,我始终觉得自己还站在门外,也喜欢站在门外,好像走在一条繁华大街上,橱窗里琳琅满目,我就隔着玻璃看看。和时装换季一样,文学的潮流也在不断变换,林培源在后记里说,他从“新概念”时期算起,写小说也超过十年,不断地迷失又发现,这种感受我很熟悉,创作中遇到迷茫,如同待在一间停了电的屋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灯再亮起来。
在《小镇生活指南》里,作者在故乡的时间里打捞故事。在《姚美丽》里,突然出现一个熟悉而遥远的歌名,我才意识到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一类女性的形象好像永远不老,烫着波浪卷发,开游戏厅,美发厅或者餐厅,性格泼辣外向,她们出现在各种小镇故事里,半明半暗的一个符号,天然地带有八九十年代的气息,仗义泼辣下面藏着寂寞。姚美丽的形象特别像我家楼下超市的老板娘,黑丝高跟鞋,波浪卷发,低胸上衣,跟几个员工说说笑笑,讲自己如何能喝酒,声音很大,有一次在深夜的车库里遇见她,整个空间都回荡着她的高跟鞋声。她不是本地人,假如她还在家乡,可能又是一个姚美丽。
另一个很感慨的故事是《秋声赋》,一桩少年人的悲剧,因为父母不能供他上大学,考上了也不能去,打击之下,渐渐精神失常,最后被父母锁在楼梯口,变成了一个“楼上的疯子”,是不是每个小镇或者乡村都免不了有个疯子?阿秋的坠落是一点点地下滑,中间相亲那段很有希望,翻过来又是一场空,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当进入一个上升或者下降的轨道,所有聚集起来的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摆脱不掉,挣扎不了,最后阿秋的世界就塌缩成一根铁链。读到结尾,我会想,这样的人,父母照顾一辈子,当父母老了,不在了,会怎么样?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恐怕会经历另一次看不见底的坠落。
一些人伦上的悲剧,是住在城市里、享受完善福利的家庭不能想象的。比如《水泥广场》结尾处,那个摆菜摊的老妇人,拿了儿子透过慕云给的钱,照样挑着担子送菜,儿子跑路了,不会再回来看她。这些事是不是也在每个小地方发生呢?我奶奶家从前有个街坊,他儿子在九十年代跑到上海,好几年不回家,有一年写了封信,这位爷爷把儿子写给他的信给所有人看,我奶奶都能背一段,开头是“爸,请您原谅不孝的儿”,直到老人去世,他儿子都没回来过,街坊们都传,说他儿子犯事了,这种八卦,越是捕风捉影,语气就越是斩钉截铁。在大家都互相认识的地方,流言是一张谁也逃不出去的网,大人们闲聊,小孩留心听的话,就能听到邻里之间的好多故事。中国传统的乡镇是一个熟人社会,一家有事,不一会儿就全知道了。《拐脚喜》里的张寡妇就是一个活在围观者目光里的人,这个人物名字就出自他者的视角,连读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旁观,看她先被“我”的母亲骂,后来又去骂儿子的女朋友,在充满偏见的环境里,自己也成了偏见的一把刀,仅凭面相就判定儿子的女朋友不好,继而大吵大闹,最终活成了一个尴尬人。
作者说写小说的要义在于“不忍”,不忍则意味着“同情”和“平视”,在这本书里,作者几乎是隐身的,隐在这些小镇的人物之中,不是岸上观鱼,而是潜入水中,自身也是一条鱼,故乡对他是不设防的。作者从听到的、看到的人和事中间剪取一些侧影,构成一本小镇故事集。在潮汕风俗和当地美食的后面,还有这些平凡而可叹的生活,不仅仅是清平镇,是所有小镇的微缩模型。
《小镇生活指南》读后感(三):小说故乡,或潮汕故事集
《小镇生活指南》,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从“新概念”时期(2007—2008)算起,我写小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作家,不仅事关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不长也不短的时段里,我曾经不断地迷失,又不断自我发现:发现一个未知的世界,和一个同样未知的我。写小说就是这样,起初你听从内心的召唤出门远行,途中小径分叉,迷宫环绕,最后你穿过窄门,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乌托邦。小说便是我的乌托邦,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随物赋形,经验和艺术感知力,是它赖以维继的基础。
至今,短篇小说依旧是我观察世界和文学的一块显微镜。我心目中的短篇小说大师,有鲁迅(《呐喊》《彷徨》)、詹姆斯 · 乔伊斯(《都柏林人》)、舍伍德 · 安德森(《俄亥俄,温斯堡》,也译作《小镇畸人》)、奈保尔 (《米格尔街》),以及奥康纳(《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他们的小说作法不同(19 世纪末的都柏林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不一样,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中国更是判然有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围绕着“城 - 镇 - 乡”这样的空间结构来叙述。在这个空间里,作品和作品相互缠绕、生长,形成了一个繁复的小说宇宙。这样的小说,是我偏爱的,它们有根,有灵魂的落脚处;这样的小说,有着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的“原型故乡”。我既用中文阅读它们,也用英文阅读它们。离开了熟悉的语境,以另一种语言进行阅读,这种方式,我称之为语言中的流浪。它的好处是,我得以借此反观现代汉语的写作,或者借用苏珊 · 桑塔格的话来说,保持“感受力”,警惕历史的残留物对汉语的侵蚀和污染。
《小镇生活指南》中收录的作品,大部分写于 2012 年到 2017 年间,它们代表了我对文学最初的认知和理解。重新修订时,除了去掉个别累赘字词,我并没有对它们做太大改动。一篇篇重读下来,仿佛看到时间行过的足迹,也看到初习写作时投掷的巨大热情。
2012 年起,我开始集中精力写短篇小说。此前的创作,多是练笔。那时我在广州读研,课业压力不大,除了读书,时间都用来写作,到毕业前,攒了十几个短篇。后来这些作品都找到了归属,陆陆续续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
那时对写小说有一种亚里士多德说的“迷狂”,每写一篇,都铆足了劲:对语言极其苛求,反复增删、琢磨,只为营造一种独特的行文和腔调。同时,我又对这种素朴的现实主义有所倦怠和不满,于是又自行“分裂”出另一种风格,追求文体的实验,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大量挪用一些互文、元叙事的伎俩——多年后,这批带有传奇和寓言性的小说,被辑录成一部名叫《神童与录音机》(2019)的集子得以出版。两种风格看起来并行不悖,不过说到底,它们都发轫于同一个“原型故乡”。
这个原型故乡,离城市很远。写进小说时,它是一个虚构的潮汕小镇。在这个意义上,称这部《小镇生活指南》为“潮汕故事集”并无不可。
潮汕故事集成立的第一个因素,和语言有关。
在我们的常识里,京派、海派等小说,是文学版图里清晰的地标,它们有开疆拓土的先辈,也有亦步亦趋的后人,哪怕是粤语小说、台湾文学,都有各自容易辨识的语言标记。因此,写作一部潮汕故事集,一直是我的梦想——不过将它放在其他地域小说的坐标系,好像意义并不大。潮汕方言异于现代汉语,它并非“言文一致”,一些口语没有对应的字,一些方言的用字如果照搬进小说,恐怕会让别处的人读得云里雾里。我的做法是,只保留个别的潮汕方言用词,将其植入叙事,像蝉蛹一样,蜕掉累赘的外壳,露出真身。不过这样一种语言,是经过裁剪和修饰的,它们附着于小说表面,尚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风格,这是《小镇生活指南》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语言是最大的公约数。
写作这批小说的时候,我会有意无意地背离“传统”的讲故事方式。当然,小说脱胎于口述和讲故事的传统,完全背离讲故事,会陷入另一个极端,一个由实验、互文、呓语、迷宫组成的“反小说”的世界。
“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和故事有着很大的不同,故事可以是小说的蓝本,但绝不能变成小说的囚笼。小说有内在的文体要求——叙述视角的运用、人称的选择、氛围的营造,以及细节的刻画等等。这些,大多是传统的“讲故事”所不看重或有意无意忽视的。不过写小说和“讲故事”并不相悖——毕竟《小镇生活指南》里的篇目,都在讲故事,而讲故事,总是要倾注于人物。《奥黛》《秋声赋》《青梅》《水泥广场》 《濒死之夜》……这里有被生活抛弃的年轻男女,有衰老无力的中年男性,新的、旧的,或多或少都有我生活的小镇印记。在这些小说里,我避免用一种“传奇志异”的方式讲故事。毕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用小说满足读者的猎奇,无异于自断后路。
小说生来并不是为了与故事竞争。
我是从潮汕走出来的小镇青年,生活经历和其他人大同小异,如果非要找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选择了写作,选择了文学。十几年来,我一直辗转各地求学和生活,从写小说,到做学术,从珠三角到北京(中间又美国访学一年)……从地理空间看,我离潮汕故乡越来越远了,但在小说中,在情感认知里,我和它反而越来越近。
写作者面对世界,会冒出一个疑问: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之于这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是我生长其中的潮汕大地。另一个疑问是,我在小说中“虚构”的潮汕小镇,多大程度提供了“真实”?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会经历学徒期,在这个过程中,他会犯错,会走弯路。他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伟大传统”的调教。阅读是一种调教,生活也是。
写作这篇“后记”的时候,疫情尚未结束,我滞留在潮汕老家,从城市的“侨寓者”,变成了小镇的“异乡人”。这是生活的馈赠,它给了我再度和故乡“相处”的机会,也让我再度回望并整理过去。
这便是这部潮汕故事集的由来。不介意的话,请把它当作一个小说学徒全部的努力。
林培源
2020 年 3 月 12 日
(备注:此为《小镇生活指南》后记)
《小镇生活指南》读后感(四):他记录下了小镇中人的悲欢离合和倔强
我极少看新概念出来的那一批作家的文字,因为我始终觉得“疼痛的青春”是他们的标记。但这次读到林培源的这部潮汕短篇小说集,让我为自己曾经的偏见汗颜。
林培源的这部书完全跳脱了青春的模样,把眼光放到了生活的故土和普通的人,他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人生。他写人,写的虽然是区别于芸芸大众有故事的人,但同时他们又是在小镇中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仔细想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的集合,但又特立独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指的就是这个样子吧?
书腰、外封、本体,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是挺好的,有一种地下漫画的感觉。雄,一个参加了越战又买了越南新娘的养蜂人。他自卑,所以在人前不停地夸大自己参加越战的经历,但实际上这段经历带给他的只有心理疾病。梦中的越南女人让他受伤,现实中的越南女人让他痊愈。他和她在争吵之后,慢慢接受了对方,但一件奥黛打破了这种平静。奥黛是面镜子,让女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对故乡的情,而流产坚定了她的决心。她始终不属于他,不属于这个小镇。而他最终只能永远地失去了她,连怀念也随着老旧的相片变得模糊。
蓝姨,一个为子女操劳一辈子受了一辈子累的女人。她爱她的子女,但和老派的乡村妇女一样,更多地是显露于外为他们做事,而少于交流。她慢慢步入老年,半辈子为家庭操劳,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腰杆,熏黑了她的手指。从乡下来到城市,找不到一个能说体贴话的人,只能对着好友的女儿流泪。最后的断指究竟是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她回到了乡下的家里,继续着她的生活。只是就像她酿的青梅酒,岁月蹉跎之后,生活给她留下的回味只余苦涩。
庆丰,一个棺材匠的儿子。他是所有地方都会有的什么事都听老婆的那种普通人,唯一让他不同的是他的父亲。由于父亲的职业,让他承受了压力,甚至觉得一辈子没有出息。但在他懦弱的外表下仍尊敬着父亲,只是因为社会和家庭让他无法选择,不能反抗。寻找父亲最后一具棺材让他从桎梏中挣脱了出来,想起了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才明白永远失去了最爱他的人。
慕云,一个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女人。她是孤独的,失落的,只能在广场舞中寻求众人一起给她的温暖错觉,在广场舞中远离生活的不如意。她害怕着带给她心理创伤的老六,但再次相遇后,这种害怕随着把老六塞给她的东西带给老六母亲而消失在空气中,反而又生出一些好来,只因为她知道这个生命中的过客虽然再也见不到了,但他是这么信任她,在心里还是有着她。
姚美丽,一个骑重机车的女子。她是寂寞的,又是热闹的,她是坚强的,又是软弱的。在一个偶然的日子,不经意的一瞥,让他和歌舞团的哑巴司机邂逅。因为他是哑巴,她愿意在他面前倾诉,她回忆自己的过去,讲诉自己的经历,但也就只是这样了。邂逅,再分开。相遇,再离别。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过客。她渴望着爱情,但又怕受到伤害,只看着别人的悲欢离合,给自己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那一年。
顺伯,一个在一座破烂小庙里当了一辈子庙祝的老人。他善良,又胆小。会为了一个路人叫出他的名而心怀喜悦,会为了路过的一个小女孩哭红了眼而担心。他拔牙时由于牙医的失误晕倒了,醒来后反而找自己的原因。在生活中这样的老好人总是吃亏的,他最终似乎看开了生死,明白了世间万物被规限在小小的世界中无法挣脱。被炸死的乌龟的世界是放生池,他的世界是这座小庙,病人的世界是那个冰冷的病房。所以最终他把放生池的水放了,让鲤鱼能够脱离禁锢它的小小世界,就像把自己从命运中摆脱了出来。
老胡,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裁缝。在中元节这一天,他的儿子被拐,明明知道是谁拐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儿子。原有的平静生活无影无踪,曾经对儿子严厉的画面反而占据了脑海。这时候,他后悔没有好好对他,失去之后才知道珍贵。在失去儿子后,反而与相隔甚远的妻子接近了,只是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故事中隐晦地说了他和儿子已阴阳相隔,每年中元节给儿子做新衣服时,他是否和他的妻子一样也见到了长大一点的儿子呢?
张寡妇,一个卖酱油支持家计的女人。她曾经可以过上最美好的日子,但丈夫的离世让一切都变了。她不识字,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所以她不想大富大贵,只想儿子能够安安稳稳、平安一世,她只愿生活不再辜负于她。她会为了她心目中儿子的未来去狠命抗争,但最后还是被生活打败,失去了他。对她来说,所有的原因可能源于房梁上的那一双破鞋,让命运捉弄于她。
阿秋,一个疯子。他曾经是聪慧的,字写得好,读得出书,考上了大学。但也因为父亲的一句“没钱”让他失去了希望,痴了。他可怜,自己的理想被家庭打碎,被亲人抹灭,亲手撕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把自己的聪慧一并破坏。往后从温顺的痴到狂暴的疯,也只是伤口上又被插了一刀而已。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他也让父母亲失去了他们的心头肉。
他,一个罪犯。他信命而失命,他的恶来源于他的无依无靠,传承自他的父辈。他自认与父不同,但最终落得同一下场,让生命归于那条途经小镇的河流。他始终无名无姓,只存在于这篇文字中,但他又真实地为小镇中游走于夜晚的人留下了一个注脚。也许,默默无名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作者笔下的所有人都经历着生活带给他们的挫折,而在对他们的生活缓缓道来的同时,还勾勒出了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人的一生,10个短篇不仅仅写了10个人,更是写了小镇中的大多数人。他们一生背负了太多的东西,虽然如此仍挣扎着在这世上活着,“太苦了”。
作者的签名,感谢!最后说一下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文章吧。此次收录的10个短篇,其中4篇曾被收录于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三条河流》中,2篇曾被收录于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中,只有4篇以前没有在单行本中收录过。由于书中没有每部作品的初出,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习惯,将每部作品初出和曾收录过的单行本做一说明,其中《拐脚喜》未查到相应初出,望熟悉的读友告知。
《奥黛》/《山花》2014年第4期(曾收录于单行本《钻石与灰烬》) 《青梅》/《青年作家》2014年第3期(曾收录于单行本《第三条河流》) 《躺下去就好》/《西湖》2013年第11期(曾收录于单行本《第三条河流》) 《水泥广场》/《小说界》2017年第5期 《姚美丽》(原名:《姚美丽,或一九九七的歌舞团》)/《江南》2017年第3期 《他杀死了鲤鱼》/《文艺风赏》2013年第9期(曾收录于单行本《第三条河流》) 《最后一次“普渡”》/《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2期(曾收录于单行本《第三条河流》) 《拐脚喜》/(能力有限,未查找到初出) 《秋声赋》/《作品》2015年第2期(曾收录于单行本《钻石与灰烬》) 《濒死之夜》/《文艺风赏》2015年第11期
《小镇生活指南》读后感(五):从“小镇做题家”说起,我们该怎样谈论小镇?
最近“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火了。“小镇做题家”出自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指的是依靠“题海战术”从小镇走向“985高校”的一群人。当他们走向城市里的高校以后,发现家境、外语口语、社交能力、生活水平,甚至是毕业就业环境远不如人,由此喟叹自嘲,“吾乃five(废物)”。这不由地让人想起了前两年电影市场大火的时候,应运而生的“小镇青年”一词,小镇青年在成为电影市场观影主力的同时,也被诟病成了品味格调不高、喜欢看“烂片”、审美情趣底下的人群。与此同时,文艺作品中的“小镇青年”形象也多被塑造成颓废、崩溃、废柴、焦虑、亟待被救赎的形象,而“伤心”是弥漫其中的情绪主调。“小镇”被默认成经济基础差和社会地位落后的代名词。这些年来,跟“小镇”有关的词,似乎都代表着狭隘、落后、失败,“小镇”逐渐走向了污名化。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逃离小镇”才代表了“追求”和“正确”,留下来的人意味着固守闭塞和偏见,愚昧和无知。带着这样的刻板印象,小镇成了人们羞于谈及的话题。当小镇意味着偏见的时候,小镇的现实环境和生活的真实模样被遮蔽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镇生活指南》的出版,无疑是一部“小镇生活偏见解蔽指南”。小说以林培源的故乡潮汕作为“原型”,用10部短篇小说“拼贴”出一个虚构“故乡”——清平镇。不同于以往文艺作品中,“小镇居民”们自怨自艾、一蹶不振的形象的是,生活在清平镇的居民“看尽人的孤独、世事难料,身体里仍有一股和生活纠缠厮打的劲儿”,他们深陷生活的泥潭中,对抗困境的方式既不是听之任之、自甘堕落,也不是“屌丝”逆袭、buff(辅助技能)加持,而是福贵式的“想要好好活下去”,是生命的本能和韧性,是我们“沉默的大多数”的隐忍而伟大。与之对应的是,小说集中,既没有极具戏剧张力的场面,也没有刻意刻画具有戏剧效果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林培源是在有意规避电影化的故事效果,他有意在很多能被塑造成戏剧冲突的地方,以主人公“意识”为转折,打断、压制和淡化矛盾冲突,借以让清平镇呈现出“寻常”的特点,让小镇居民呈现出“平凡”的风貌。由此,当读者进入“清平镇”的时候,将不再设防,自然地褪去对小镇陌生、刻板的印象,穿梭于熟悉的街巷,看的是街坊邻里的“熟悉”故事。
“熟悉感”,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体验“到此一游”的角色带入,一旦读者接受了这种“熟悉感”,产生共情,便会立即觉察到随之而来的“陌生感”。林培源像是一位善于运用推拉镜头的导演,在拉近、带入读者,以求解蔽小镇的同时,他还有意制造一种距离感、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站在小镇以外的角度,打量小镇。而这种“陌生感”的制造,靠的是怀旧氛围的营造。所以,在阅读小说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怀旧感。怀旧是带有个人主观意识的回忆和记忆,隐含着个人与公共生活空间的双重视角。文艺理论家哈琴认为,怀旧兼具疏远和拉近作用,在将想象中的过去带回眼前的同时,也将我们从当下流放了出去。可以说,林培源以静止的清平镇为地理横向坐标,勾连起想象的过去、开放的未来两条纵向正、负坐标,让流动、变化的时间渗透其中,书写“当下”的意义。这正是林培源“推”和“拉”的方法,也是林培源谈论小镇的方式。正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所说,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的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做了阐释。探究《小镇生活指南》中的“怀旧感”,怀念的是什么、为何怀念?是谈论“清平镇”绕不过的话题。
《小镇生活指南》中的怀旧视角首先聚焦于对潮汕风土人情、小镇文化的构建。当下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与科技的发展,养蜂人、裁缝匠、制棺人、庙祝、神婆、游戏厅老板、越南新娘等身份早已成为都市人日渐模糊的记忆。与介乎现代化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小镇相似,他们一方面符合介于都市人与乡村人之间的“小镇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因落后或狭隘被城市化进程所淘汰、遗忘的“过去”,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职业身份能够唤醒读者的“怀旧”回忆;除了人物身份的建构,潮汕地区的方言的使用也是林培源召唤读者故土情节、怀旧情绪的策略,潮汕方言反复出现,使潮汕文化众目具瞻,亲切可感;此外,小说集对于潮汕地区的民土风情、农业传统、饮食传统和婚丧嫁娶等传统,亦有描摹。如《青梅》对潮汕地区的饮食文化的描写、《水泥广场》有对潮汕地区婚嫁习俗的描摹、《姚美丽》中潮剧的穿插、《他杀死了鲤鱼》对潮汕地区游神赛会传统民俗活动的描写、《最后一次“普渡”》对潮汕地区“七月半”的记录、《拐脚喜》中对潮汕地区“驱鬼”文化的描写、《濒死之夜》对潮汕人民鬼神信仰涉猎……归纳这些职业、语言、民俗传统的相似性,可以发现它们皆带有“怀旧”底色。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时代“淘汰”的职业、被城市遗忘的方言、被快节奏生活打乱的地域民俗正在走向消失,而林培源想要保留的是人们对于潮汕小镇文化的记忆。
怀念最直接的方式是“回忆”。“回忆”是把流动的时间注入相对静止的空间中的“行为”。以《姚美丽》为例,“他们称姚美丽作‘美丽姐’,但谁也说不清姚美丽的真实年纪。”姚美丽如同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一般,不老、不死,目送着“日子水一般流过来流过去。”她常常以静止的姿态陷入过去的回忆之中,凝视流动的时光,小说中,“她回头看坐在腌臜的游戏厅里的自己,像一尊凝神的雕像,那些走动的、打游戏的人,只剩下一双眼在暗中发光。”在这里,她像一个静止的坐标,凝视流动的小镇人成长。而在姚美丽去戏院看戏感到厌烦时,她起身“站在座位最后一排的走道上”打量着舞台与观众席的时候,实际上是“俯视”芸芸众生的“参照物”。小说结尾,坐在摩托车上的姚美丽仿佛乘坐了“时空穿梭器”,自由地穿梭于往后好多年、这一年、好多年前之间,“万物倒退,而她朝前移动。”狭小逼仄的游戏厅容纳了小镇芸芸众生的进进出出,不老的姚美丽见证了小镇的历史和未来。除此之外,《奥黛》里的阿雄靠一张照片“回忆”了自己的大半生、《躺下去就好》里的庆丰靠一口棺木“回忆”了自己与父亲的一生、《青梅》里以“我”的视角“回忆”蓝姨的一生、《水泥广场》里以慕云的视角“回忆”了自己及老六的一生、《他杀死了鲤鱼》里的庙祝因为牙疼不断“回忆”十五年前的历史与自己悲惨的一生、《濒死之夜》中他自杀前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回忆”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个体的行为,但人物的行为动作必定发生在典型的社会环境背景之中,因此,“回忆”带有个体和公共社会生活双重背景,而在主观回忆中,社会背景作为“回忆”的“无意注意”,则更具客观真实性。相对静止的主人公通过“回忆”连通了涌动的历史,静止的清平镇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可以说,“变迁”是小说集隐含的主题。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林培源以怀旧视角讲述清平镇的过去,体现了他对“当下”的体认。清平镇不仅仅是一个虚构、孤立的文学地理坐标,林培源将之放在社会发展、历史发展、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通过“对比”,关照小镇在时代发展和变迁中产生的问题。如在《拐脚喜》中,第一次进城务工回乡的庆喜意气风发,而小说的结尾,他与挂在门上的雨靴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前、后庆喜形象的对比,小镇留守青年的出路问题,呼之欲出。与《拐脚喜》相似的是《秋声赋》里的阿秋,从一开始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去”的奋进青年,到连翻遭遇命运挫折,最后“像条狗一样被拴在楼梯口”彻底疯掉,是林培源对于小镇青年人生出路的追问;《他杀死了鲤鱼》中萧条的老庙与周牙医诊所明亮的色调的对比、《水泥广场》中的水泥广场与车来车往的国道之间形成的对比、《躺下去就好》中的棺木里的安静与雷雨声的嘈杂产生对比、《姚美丽》中沉默的哑巴和滔滔不绝的姚美丽形成对比,这几组关系不仅是林培源对于小镇之于“世界”的位置的思考,更是对于“留下来”还是“走出去”的发问。除此之外,《青梅》和《水泥广场》中对小镇中年妇女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最后一次“普渡”》和《躺下去就好》中对小镇劳动力问题的讨论,无不是“当下”意义的生成。就此,林培源不仅为谈论小镇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弥补了南方写作的空缺,形成了他的潮汕文学地理坐标。
写于202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