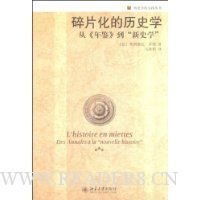
《新史学讲演录》是一本由王晴佳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元,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就任长江学者之大陆高校演讲集,视野和思路延续其前著译,议论浅显,举证随意,有利快餐便览,前沿速成。虽亦不乏超出前著之“本土化”反省议论,但由于对新文化史的成因和政治效果理解偏狭,导致有关中国史学不必亦步亦趋之论不得要领。后附记叙张芝联郭圣銘两师文倒颇可读。
●重复的地方比较多。说从大写历史转向琐细边缘的历史写作是因为世界大战后的颓废反思,感觉也比较一家之言。对妇女史相关的观点不赞同。
●对新文化史的兴起及性质有精辟简明的论述,其中提到的研究书目很有用;对近代民族国家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区分,也很到位。新文化史入门必读!
●对于我这种史学门外汉来说,是一本颇有助益的小册子。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介绍,是值得推荐的好书。扣一星,一是略罗嗦;二是确实不算精彩绝伦,如对文化史的发展轨迹虽然叙述清晰,却力度稍欠;再如对计量史的衰落只是一句话,没有较好的阐释。
●扫盲,该早两天读。(期末厌学的锅)
●反省民族国家史学
本书所称的“新史学”,除了与新文化史、全球史等的展开以及“大写历史”的势微有密切的关联,也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研究人员的“草根化”和“反智”的社会风气相关。著者认为,与其追随那些源自西方、反映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学潮流,还不如充分尊重历史的多样性,根据性之所近,借助自身的文化特质和历史积淀,选择研究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历史问题,进而反观西方,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如此所获得的研究心得,更能全面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通常是以其“在地化”(glocalization)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
《新史学讲演录》读后感(二):史学史入门读物
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书,随意翻翻,发现这本书是介绍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小册子。是整理的演讲录。
读毕此书,我对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全球史有了初步的了解。重要的是了解了新史学兴起的背景。人们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上帝死了。近代的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发展成了多元发展。历史碎片化,但全球史又是宏观叙述的复兴。史学也在多元发展。
但本书是由演讲记录改编而成,内在逻辑会有些欠缺。我们也不能苛求什么。总之这是本很好的入门读物。如果想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还有看他的著作,文章。及其他经典的书籍。推荐北大出版的历史的观念译丛,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新史学讲演录》读后感(三):自下而上的新史学
作为讲演录,它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新史学的发展情况。普及者有两种,一种是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做到家喻户晓;另一种则是既浅显地阐述又深刻地理解,引发对其的兴趣,引导方向。我觉得本书是后种,让人看后不释手。
作者有较高的文学涵养,古诗、比喻……恰当又能调节气氛。新文化史的特征也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以尊重事实为基础,一改叙述的沉闷笔调,让人耳目一新。
新史学的发展,由研究大的支干转向研究小的细节,与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结合,强调科学性,以小见大地证明、得出结论。这与社会分工细致,学科的渗透越来越强是分不开的。同时,全球化的趋势在近百年越来越强,于是眼光从西方中心转向世界。费正清“西方挑战,中国回应”言犹在耳,此时已把中国的近代化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又有声音“中国与西方处同一时代,不分古代现代近代,拥有各自的发展轨迹。”
大写历史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抓住主干。但容易让人质疑,为什么一定正确呢?于是在各种问题中,小写历史产生了,它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论证,研究社会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的推动力。着眼于公众,于是也强调“口述历史”“集体记忆”。它质疑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这种声音自下而上地反省和完善。同样是战争,美国国内不愿参战的民众质疑西方文明是否有权利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这放之全球,挑战的更是霸权思维。
个人对个人权利的坚持,是西方民主的基本特色。游行示威等干预政治,都是自下而上的思维。历史长河是滚滚向前的,但个人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新史学关注个人、集体,虽是淙淙小溪,终会流成那长带的完整。
《新史学讲演录》读后感(四):新史学如何兴起
尽管新史学的特征之一是以琐碎取代宏大的演进史观叙事。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一本讲述新史学的史学史书籍,却仍旧是以宏观的历史视角入手的。在作者看来,新史学的兴起其实与世界格局的转换密切相关。
近代史学传统,乃是民族国家史学。而新史学范式的兴起,则是与此对峙。前者约莫是沃尔什所言的思辨历史哲学,而后者则相当于分析历史哲学。
近代史学的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启蒙思想家号召历史的写作,不仅要记录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希求对这些时间之间的关联和趋向做出解释。这种理论的语境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假设历史学家与牛顿等自然科学家一样,都应该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其背后隐含着的,是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在这种自豪感下的西方权利书写。其中,兰克学派虽然看似专注于考订史料、用政府档案写作民族史、国别史,其本质无外乎认同只需“如实直书”便能展现这种文明。而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人,虽然看似是兰克学派的敌对者,但其长时段的研究,仍是本于宏观的考察解释历史发展的进化或退化。
当然,这种宏大叙事的传统还可以追溯至基督教的“大历史”写作上。尽管看似是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但作者认为其根源便与奥古斯丁一致:即世俗的王国最终要进入上帝之城,因此历史时期王对人类提供的和平与秩序,其实只是上帝之城到来之前的小历史而已。这种连续性的观念恰恰就是思辨历史哲学的精髓。
而新史学范式的兴起,则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走向衰亡的危机感。这种科技发展的危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随着冷战的思维与局面,导致了后现代思想的产生。西方中心论的没落,原本的西方主宰权利丧失,那么原本历史认知的问题也就浮上台面。这伴随着的有对语言的怀疑,要求在一定的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语言。注重叙述的精细与完美,而非解释历史。其特征则如芭芭拉·瓦因斯坦所言:“向文学叙述靠拢,注意精致的描述,基本放弃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常常伴随着处理孤立的小事件、小人物,来企图解构原来的解释框架。
当然,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史研究也渊源有自,比如20世纪初德国兰普勒希特和英国的巴克尔和日本的津田左右吉,均专注于民族精神的写作,将写作从国家扩大到民族,勾勒文化的特征。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以后,人类学领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也刺激了新文化史的产生。其特征之一便是寻找特定区域蹲点,深入当地文化和人的行为,去除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比如人类学家格尔茨就提倡厚叙述,即认为“人的行为一定要放在这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方能理解。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而已,因为它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p56)其排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说,而认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都必须通过语言沟通和文化体系来表现。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则是语言学转向,即认为语言不在透明,语言有内在结构,意在言外。因此注意观察带有文化象征的活动仪式,以图分析语言真正的意思。最终,一方面是新史学微观化的研究风潮,当年鉴学派第三代掌门人勒华拉杜里,用细致的人口学、社会学描述《朗格多克的农民》通过论述农民长期停滞不变的生活方式来源于文化传统,这种细致的区域史研究已经初露端倪。而《蒙塔尤》的写作则转入心态史,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史研究的展开。
最后,倘若我们跳出这种史学史学术内部的讨论。我认为作者这一叙述更在于点明一个道理,其也相当于为新文化史找到了一个正当性。诚如81页所言:
近代史学——民族国家史学,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的反映。如果要突破西方中心论,就必须要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规范。因为民族国家为西方历史的产物,如果一个非西方人用这个视角来考察历史的轨迹,就是用西方的视角来过滤自身历史的多样性,也就不免削足适履。因此,只是体系和学科建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的,相反,它们都反映了一种强势文化的优势,抑或文化的霸权。近代英国的培根讲过”知识就是力量“,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反其道而行之,说“知识就是权力”,在英文里,力量和权力都是power。福柯认为所谓只是系统,其实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权力的产物。
但由此,我却不禁思考,如果说知识系谱就是权力,那么看似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权力叙事的新文化史是否也同时也暗含着另一种权力的表征?一种直接的图景是,新文化史乐于关注的床肆之欢,这不就是底层社会最广泛的话题之一吗。然而问题在于,它却并不见得是庶民权力的兴起,或庶民试图摆脱精英的过程。因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感一直萦绕着我,即这种接近文学叙事的写作与琐碎事物为切入的研究风格,总透着一股子在小酒吧咖啡馆把妹的气氛,或者是酒过中旬饭局上文化人的显摆,他们真会关心底层么?当然不会。这又使我联想到在我国版本学领域,大抵多是有钱子弟收到稀见版本才能在席间聊以谈资的学问,由此观之,这种权力的兴起语境倒更复杂起来了。
作者:王晨光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新史学讲演录》读后感(五):平庸
剑桥大学彼得 ·伯克 (Peter Burke)教授的题名为 “Ranke:theReactionary”的发言。如果翻译过来 ,就是说兰克是一位逆潮流的史家。
预示了他以后研究兴趣的转向。伯克指出 ,在兰克以前 ,也就是 18世纪启蒙运动时 ,一般作品都基本上是宏观的文化史。伏尔泰写了《论世界各国的风俗》,这本书一般比人看做是世界文化史。再比如 ,启蒙运动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爱德华 ·吉本 (Edward Gibbon)所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显然是一部宏观史。他在书中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 ,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这就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军事衰落等等。吉本是从文化 ,宗教上来看这个问题。文化一般上是比较宏观的。一般而言 ,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地区 ,看到另外一个文明 ,大致上会注意这一文化的不同和特点 ,然后才会描述他们的政治制度。所以,伯克的论文就是说兰克扮演了一个反潮流、或逆潮流的角色,或者是一个类似修昔底德的角色,把原来 18世纪宏阔的文化史的研究,紧缩到政治军事史。
列奥纳德 ·克里格尔 (Leonard Krieger)与其他两位学者在 1960年代初撰写《历史学》一书的时候 ,就指出科学史学可以是注重历史的规律性 ,也可以注重历史史料的考证与核实 ,从而建构历史叙述。换句话说 ,科学史学有 “史观学派 ”和 “史料学派 ”之分。兰克就是后者的代表 ,也就是方法论上的科学史学的代表。
20世纪初年的兰普勒希特和英国的巴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都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兰克只研究一批政治 ,军事外交的精英 ,想以此来勾勒世界历史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的做法是不够的。兰克比较注重国家 ,而兰普勒希特比较注重民族。要想勾勒或者概括德国的这种精神与英国和法国的不同 ,一般只能从历史上来谈。巴克尔的做法也很相似。他希望把民族史学的写作从国家扩大到民族 ,把眼光略为放大 ,将英国民族文化的特征讲出来。
受到兰普勒希特启发的日本史家 ,提倡写作 “民众史 ”,后来变成了 “文化史 ”,其中以津田左右吉的研究 ,最为著名。津田左右吉的研究 ,与当时的中日冲突也有联系。他讨论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 ,而其目的是勾勒日本文化的特征。
默顿对功能主义理论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方法论里面,尤其是他提出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观点。“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而统一性的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的一切观察到的一致性。”
布罗代尔的得意门生、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最早写了《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 ,是他的博士论文 ,用细致的人口学、社会学的方法,详细描述法国一个省的农民生活 ,希望能揭示虽然时间跨度有几百年,但当地的农民生活 ,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而拉杜里认为 ,这种长期停滞不变的生活方式 ,主要源自文化传统。
拉杜里也主张 “长时段 ”的考察历史 ,注意他所谓的 “结构 ”(structures)的持久性和对历史变动的长期制约。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拉杜里比较注意的是这一 “结构 ”在文化层面的表现 ,而布罗代尔注意的是地理环境。
吉尔茨 (Clifford Geeertz),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实证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提倡的所谓“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就特别注重研究一个文化的体系,认为人的行为 (相互沟通、交往和联系),一定要放在这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方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而已,因为它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context)。
相反 ,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的著作 ,考察的是重大的、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 ·汤普森 (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 ,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汤普森是将“文化 ”引入史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美国当代史家琳 ·亨特 (Lynn Hunt)是一位公认的领军人物。她在 1989年和 1997年,分别编写了两本书 ,现在都成了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读书 ,那就是《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的转向》。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人看了后一本书的题目 ,以为亨特要号召超越新文化史 ,以为美国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 ,没有几年就翻新花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亨特的第二本书 ,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为了做新文化史而做新文化史 ,而是要对 “文化 ”这个概念及其用途 ,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透彻的分析 ,既看到它的用处 ,也看到它的内在不足。这是一种有益的学术检讨。
田先生是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 ,其专业其实就是社会人类学。他在文革以后 ,长期在海外研究 ,著述很多。我曾经有幸在一个场合 ,有缘与他在海外重逢。他在《男人的焦虑和女人的贞节:明清两代伦理观念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 ,其实理学家的女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观念 ,虽然在明清以前就提出 ,但真正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要到明代中期以后。所以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交流 ,有一定的时间差。
包筠雅的书文化研究 ,以福建的四宝印刷行业在清代的发达为对象。她的《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宝的书籍交易》,牵涉了许多问题 ,都是 “新文化史 ”关心的问题 ,如男女的识字率、书籍印刷与普及教育之间的关系、书籍作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状况等等。包筠雅指出 ,四宝印刷的书 ,希求薄利多销,大都是为了符合一般读者的需要 (如科举考试、休闲阅读等 ),所以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
伊格尔斯教授的一篇经典的文章 ———《德国与美国思想中不同的兰克形象》,发表于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 ,其中指出兰克在德国史一个唯心主义的史家 ,而到了美国 ,则摇身一变为一个实证方法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了。其实兰克在东亚的形象 ,也大致属于后一种。对于兰克 ,民族国家的出现体现了 “上帝的意愿 ”(态度、科学考订史料 ,都是这一历史观的产物。德国史家恩斯特 ·舒林 (ideas of God)。所以兰克写作民族史 ,背后反映了他的整体历史观。因此如果我们把兰克视为一个客观主义的、只讲考证史料的史家 ,显然有所偏颇。在兰克以前 ,没有人只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来写作历史。近代以前的史家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一般视野都比较宏阔。
原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杜赞奇 (PrasenjitDuara)的《从民族国家里拯救历史》,颇有启发性。他的观察就是 ,现在的中国人 ,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近代中国的兴起 ,就是民族主义的结果。但其实在中国受到西方侵略、欺辱的时候 ,中国人还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抵御这种侵略。有些有名的近代民族主义者 ,如傅斯年、毛泽东等人 ,都曾考虑过采用地方割据主义 ,也有其他人为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努力 ,那么我们写出的历史 ,就表现为一种目的论。换句话说 ,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从 A到 B,那么发展的线索是开放的、多元的。最后从 A到 B走了哪条线 ,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而且肯定不是直线。史家需要展现这种历史的多元性、偶然性。
查克拉巴蒂写了一本《把欧洲区域化》( 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书 ,号召大家走出西方中心论 ,也就是用西方文化的过滤镜来考察文化变迁的做法。
美国的中国史家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以研究清史闻名,但她最近有一本新著《什么是全球史?》,并在其中做了这样的观察:历史学家可以分作两种人,一种专注对原始史料的考察,在其基础上写出专著,企求说明一个或几个现象,而另一种人则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做宏观的研究,力图发现和揭示历史演进中因果关系的模式 (patterns)。可见,宏观史学、世界史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各个文明几乎都有代表作。具体而言,目前流行的全球史的前身,就是世界史(word history)和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前者又分两种,一是以往史家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其历史十分悠久。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古希腊的希罗多德 (Herodotus)、西欧中世纪的奥托·弗莱辛 (Otto,Bishop ofFreysing)和伊斯兰世界的塔巴里和伊本 ·卡尔顿 (Ibn Khaldun),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二是近世以来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基础上尝试写作的世界史,以 18世纪英国史家集体写作的普世史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史家写作的世界史为典型,虽然后者对前者多有批评。
彭慕兰文章的题目是 ,“社会史与世界史 :从日常生活到变化的模式”。他在文章中对他用的 “社会史 ”,做了一个界定 ,认为有三个侧重点。第一是有关日常生活 ;第二有关社会、团体和国家的关系 ;第三有关社会运动。从他的说明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 “新文化史 ”。而彭慕兰认为 ,这三种社会史 ,其实都可以与世界史产生互动,而有趣的是 ,他认为第一种社会史,也就是最能代表历史碎片化的史学,最容易与世界史交流。彭做了两点解释,第一是这种历史研究 ,主要考察寿命长短、消费水平、初婚年龄、生育率、升学率、犯罪率等等,而这些课题,出现在许多社会,几乎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容易比较。第二,这一类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学,关联最少,因为它注重的是性别、城乡、机械化和非机械化等课题的比较,显然比国别之间的比较,更为容易。第二种社会史考察各种集团 (社会团体、政府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也很可以采取世界史的眼光,将相似的集团的构成和行为 (如港口城市的发展与水手生活)做比较研究。在彭慕兰看来,第三种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相对比较难一些。但他指出,许多社会运动,其实都受到一种跨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废奴主义等等。最后彭慕兰还认为,如果要研究前近代的历史,全球史家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个帝国的构成和行为,因为比如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沙俄帝国统治西伯利亚和奥斯曼帝国控制巴尔干地区,有不少可比之处。
文艺复兴无法成为近代社会的标志的看法。辛塞尔指出,这些新的尝试,在她评论的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而同时,这些著作都试图比较近代社会到来以后,妇女经验的不同和相似之处。这一经验的共同之处在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一般都造成妇女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妇女的自主权、生育选择和活动范围,都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限制。当然,这种恶化与限制,又是存在地区差异的。而且各地区妇女的对应之策,也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在中东地区, 妇女在公共场合 ,被要求佩戴面纱 ,遮住脸庞。但这种遮盖 ,其实又为妇女的自由活动 ,提供了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而对这些历史经验异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正为妇女史和世界史的结合 ,创造了条件。
伏尔泰的《论风俗》(Essai sur lesmoeurs)一书与兰克的世界史,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前者有全球的眼光,而后者则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