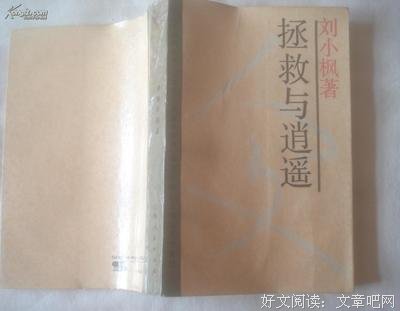
《拯救与逍遥》是一本由刘小枫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刘小枫这本书真的像刘再复所说的:让人着迷。他对西方思想下的功夫超过了当代诸多学人,虽然邓晓芒比他扎实,但没有他有灵性,谈哲学显得“讷”一些,小枫这本书有些当年李泽厚先生那些书的感觉:让人放不下手。
●虽然后来我走出来,离这本书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它打开了我之后的人生。 可惜的是近些年刘小枫教授的转变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诗人的自杀
●扫清障碍,确立基督教的信仰,这大概是这本书的目的了。嗯,第一版在哪?
●果然重看就脱粉了。搞了点现象学的东西来分析中西文学。夹带私货,传教立场太明显。文笔很好。中哲部分看着有些尴尬。
●读书如抽丝
●劉老師讓我在理性地比較閱讀中,收穫了一種作為平凡人的不適感,無法質疑他的深度,只能檢點自身。只不過,如鯁在喉的一點是:凡在歷史維度中出現的哲學、思想、藝術或是生活方式,本就是來安慰有著“惡”的人生的,安慰到了個體的人,撫慰了他個人“惡”的人生,便是成功。遑論安慰有高下之分,執於一端,不也再入了惡的圈套?如不然,我不會在眾多的書中尋求任何的安慰。
●没看过第一版,不知道其前后思想有多少转变。 本书在各种文人哲人之间交互叙述,最后提到反对虚无主义。
●看了五六十页,觉得没什么必要再看下去了,可惜了这么好的装帧和纸张,虽然是打折时买的也觉得肉疼……
●4.6 此书厚重而不艰涩,虽多有绕语,但不乏柔动与深刻的命运发问。书中所提文诗哲皆有所涉猎,儒释道耶的浸入,虚无主义的缠绕,信仰依托地悲剧呼告,都曾是我自身命运的挣扎与思渡。年轻时期的刘偏向于西方基督神学的拯救,文字不免情感化,属于非理性哲学的流溢。 轻视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的涵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读过德国古典哲学回过头来,此书学术价值较低。
《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一):拯救与道遥书评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屡次删改,我看的是第二版。在图书馆读绪说时,整个人都有震撼感冲击感,因为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提出。 这本书不着眼具体的诗学或哲学问题,而是选择直面那些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最深切的恐惧。是否要担当现世的恶,承认世界的荒谬?历史或者有其规律,是否意味着就要为其辩护?爱还是可能的吗?是否应该坚持美好的信念?是否还要坚持意义的追寻?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十分震撼。 至于刘小枫先生的解决,自不免有其立场,有些观点我也不是十分认同,尤其是比较《红楼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节。以基督救赎的立场批判贾宝玉的出家未免过于偏颇,贾宝玉是人而非神,悲剧性正源于爱与温情的被摧毁,是“到底意难平”而非真的看透了生死。另外关于鲁迅是“希望中的绝望”也引来了中文系寝室的吐槽声,毕竟,我们是认可鲁迅“反抗绝望”的提法的。 但总体上,这本书许多观点很有创见,很值得一读
《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二):个人记录
这本书非常具有启发性,刘小枫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出发论述东西方思想价值判断的冲突和取舍。这本书的整体论述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但我认为最出彩也或许是最让我引发共鸣的一章还是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它是整本书的线索,是其精神主旨的揭示,它直言如是的困境:“为了信念而活的诗人终于自杀了,虚无主义已侵入诗人的骨髓,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进入了末日审判时代”。 但同时这本书也有不足,整本书宛若一部大型阅读理解,部分观念主观性过强。且《天问》一章的旁征博引让我觉得略显臃肿,大可精简一些。故我们依大可以批判的观念去审视这本书,毕竟著书固然还是一个人的主观看法,但是其中提出的严峻的冲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诚然是需要我们不得不进行颇为沉重的思索:面对人生来的欠然应如何找寻绝对的精神?故何处为完满,何处为终结,何处为救赎? 有个豆友总结地很好:“虚无主义戴着“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甚至“人道主义”等面具悄然登场。人们在现世找不到意义的支点便自欺欺人地认为现世的生活毫无意义。人的精神被抛到了虚无之中,现世的生活变成了接踵而至的苦难的洗礼。” 而对于我而言:我不需要在虚无之境逍遥,我需要被完满的精神所拯救!
《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三):读后小结
作者坦言从是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展开对中西精神内在的探讨。从西方精神的拯救与中国精神的逍遥二元对立中,作者以诗人这一特殊角色为切入点,通过屈原的自杀引出诗人自杀是对自身信念的无助而引出儒道思想与基督思想的不同乃是对超验世界的承认与否,然后通过屈原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荷尔德林与陶渊明,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比,鲁迅与卡夫卡的对比中反思中西精神特质的不同及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指涉的是中西方精神气质上诗人对自身信念的认知及其信念背后的本根性依托的可靠性。最后作者批判了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同时也指涉出实际上庄禅思想在本质上同样是虚无主义的,继而提出作者本身对一切虚无主义的巨斥。
可以看出,作者首先有一个价值立场,即世界是恶的,而上帝则代表着希望与爱,且只有上帝才能代表希望与爱,只有超验世界的存在才能使人摆脱此世的恶,继而实质上是唯有通过上帝,人才能得救,从这一角度来说,作者本质上是基督精神的,且他所要维护的是基督精神的绝对性与原始性,而绝非经后世解读过的所谓的上帝。
作者提出了很多问题,语气略显激烈甚至初读让人觉得作者充满了戾气。但是引发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尽管作者在前言中表明他所追寻的是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并非中国传统儒道的也并非是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但是在论述过程中,这种表明的是西方基督精神中上帝所构造的超验世界的优越性,就算是其绝对精神的塑造,可以说作者的绝对精神也是建立在西方基督上帝的视野基础上的,是对中国儒道精神的反叛甚至是一种不屑。
《拯救与逍遥》读后感(四):神恩之爱
(这不是一篇严格的书评)
: 先说些题外话,却也是这本书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并且深思之处。从周国平到刘小枫,学习西哲的人,或者更应该说,或多或少领受了西方哲学精神的人,都抱有一种相似的“偏见”,那就是认为中国哲学需要彻底的反省,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是缺乏反思精神的。这一点,从历史、文学、哲学上可以找出很多例证。另一点是论当今中国哲学的格局,太过狭小,正如刘小枫所说,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学问,它是指向永恒的,所唯一需要负责的对象是人类的普遍精神。而当下时代所面临的本质问题并非中国哲学的复苏或者话语的重建,而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如何面对虚无沉沦的精神的又一次拷问。从这个角度讲,这需要一个纯粹的灵魂,像《中庸》所说的,秉承对世界与自身的坦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摒除种种外在观念价值的束缚,只为聆听存在之音。也就是刘小枫所说的,
既然作为现象学-解释学的人文科学关涉的是历史中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必然要求个体精神“主观地”追问。个体精神追问可谓“形式”的主观性,“形式”在这里意味着心灵的生命感受力、敦厚的精神品质、深切的价值感、明细的理性审辨力。“形式的”主观性把偶然的自我化解为普遍的自我,因而是价值普遍有效性的显现的基本前提。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们的心胸和视野若只局限于一时一地,精神是绝对不会向他们打开自身的大门,存在也绝不会向蝇营狗苟之辈呼唤自身。刘小枫的这本书,问题比结论更加重要。
灵魂的一切自然的运动受物质万有引力一类的规律制约。唯有神恩例外。——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启蒙的真相是人凭借理性获得了上帝的权柄,在世界的宝座上加冕为王,却没有获得承担这份权柄的能力,或者说,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份权力而来的沉重的责任。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近代的历史,理性越发巩固自身的权力,却也发现越发难以承担伴随这份权力而来的责任。如果虚无是世界的真相,正如薇依与刘小枫所认为的,是上帝凭借耶稣(一个绝对无辜者)之死来承担起世界的虚无,化虚无与罪恶为神圣之爱的救赎,那么人类理性面对世界的虚无也只能巩固自身的疆域,像傲慢的君主拒绝理性之外其他存在的可能,而希冀理性疆域内的现象之物可以赋予生命精神的力量。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
启蒙教给了人们自由,或者说,精神经历了德国古典的时代,她给人们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自由,而理性高扬又沦落的时代则又告诉人们一件事情,人的存在是一种重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信仰的重负也植根于存在的重负,当人们认识到世界与自身虚无的本性,或者说在人类理性视野寻觅不到绝对精神的现状,在这个时候,人们要想超越到有之彼岸上,即便是上帝来降临恩典到孤苦的灵魂身上,灵魂也需要与神一起跨过,一起去承担部分的世界之无,这是存在的重负。人只能孤独的去面对世界,人只能孤独的去面对上帝,那么承担世界之无的有之上帝也和无之世界一样,是一种深深的重负。
可以说,基督教揭示的具有普遍性的一点是,人的存在必须从重负开始,无论是世界虚无的重负,还是不完美的世界本身罪恶的重负,或者哪怕是一滴无辜眼泪的重负。如果人们承认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哪怕有人相信人有永恒的灵魂,无论人们是这两者中的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外在世界,外在世界中自己漠不关心的芸芸众生,对于自身的存在也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与我们同时代的一个无辜生命被罪恶杀死,也是我们身上一部分的死亡。他们的不幸与苦难,并非对于我们没有意义,或者毫不相关。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一点,其实也就否认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意义的可能。个体与世界互为彼此的镜子,而生命与其说是一个活动的肉体凡胎加上一个思考的心智或者灵魂,还不如说是这一世本身,是灵魂与世界相遇本身。
从这一点出发,人面对初始之境的重负,必然无法逃避,必然只能承认人天然的不完美与残缺。承担是唯一的出路,无论是借助上帝与神秘启示的背负,还是自我的背负,哪怕是觉醒了的灵魂希冀的自我幻想与欺骗也是一种背负。道家退守原初之境,希冀小国寡民,形容枯槁,心如死灰,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却也无法改变人的真实处境,无法改变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的悲惨世界。道家以道超越道德善恶,也取消了道德善恶,杀人者无罪,因为人终有一死,这是天道轮回,人间的大化流行、命运无常也是大道的一部分。生命在世界上希求的是全身,如果全不了,那就顺应自然吧。这样的退守宛如一个幻梦,是一个魔法,但是可以让相信这个梦的人的生命得到安慰。而创造这个梦的人,看透而甘愿沉迷其中的人,则像一只只鹏鸟,扶摇而上九万里,看似洒脱自由,实则鲲鹏之翼重如千钧,这是背负的代价。而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所有的儒者其实最终都会像他们的创始人孔丘一样,颠沛流离,宛如丧家之狗,正如绝对精神在人间世之外,理想的个体也不容于世。不过,古人追求修身之至善之境,希冀人人成圣,而道德修养和学识的提高似乎可以抵达圣贤之境,个体的圆融与生命的完满,也就是修得一颗纯然光明的心,玲珑剔透,凡尘不染,即使人间苦难,心会同情流泪,却不改心的圆满。于是,面对苦难世界,儒者最后也并不会痛苦,相反和乐融融,浴乎沂,风乎舞雩。而这样的圆融何尝不意味着某种向世界的妥协,承认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承认无辜生命的惨死也并非无意义。毕竟,这是历史王道的一部分。大概也因为如此,中国哲学总能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境遇成就圆融,也就丧失了它本初之心的批判性、理想性与超越性。
而相比中国哲学精神,原初的西方哲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秩序的完满蒙蔽了苦难的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的宏伟体系,都是光明粲然的。柏拉图没有给最低级的存在留下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也围绕着神来旋转。不过,在后来,耶稣登场,他给奥林匹斯山巅的理性之真带来了零落成泥碾作尘的人间悲苦之爱,道德之善的本质由此被爱俘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千万篇章,希腊哲学的辉煌殿堂都比不过一个普通人在十字架上无辜而死。这并非上帝的恩典或者神的旨意让前者变得卑微,而是道德本应如此。只有爱可以成为道德的主宰,只有爱可以为善加冕。
这种对于卑微个体所倾注的爱与尊重,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西方更为深刻的传统,也成为理性、自由的精神的底色。法国大革命所传递的启蒙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如果没有最后的博爱,前两者只能成为空言。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如此。于是在中世纪的千年时间,基督教爱的上帝被置换成了理性的上帝,从奥古斯丁乃至于最早的新柏拉图主义开始,教会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有一天理性的上帝要被打倒,因为在理性的角度而言,其实最高的主宰并非上帝,而是理性,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规则,即使祂是超乎人类的绝对理性。可既然是理性就必然会被人拉下神坛,成为黑格尔眼里的绝对精神。于是,尼采说上帝已死,而爱的上帝由此重生。
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超越,追求真、善、美,追求完美,追求彼岸,超出这个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本质或许就是爱,她可以扎根在最苦难的时代里的最卑劣的土壤,她不在意是否残缺,不在意崇高或者卑微,不在意超越或者腐朽,都相同地爱着。她不束缚生命伸展自由的双翼,也不试图去指引或者规定自由的方向,她不会束缚生命一定要留在此岸人间,她只是承载,只是承担,用儒家的话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对于生命与精神来说,乃至于对于真、善、美、自由与彼岸来说,爱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爱,面对不完满的人世,生命可以选择自我了断,而精神则可以纯粹的超越,建立起纯粹理性的国度,像黑格尔一样,以绝对的精神建立完满的体系。可是理性最终会发现这个体系并不完满,最终会崩溃。毕竟人活在世界上,人的存在是世界的镜子,存在是人的牧者,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本质是世界赋予的,而世界赋予人的还有她自身。人不可能拒绝世界之爱,她甚至比超越更本源的烙印在人身上,甚至超越也只是爱的一部分。
人首先是爱之存在,其次才是思之存在。(舍勒)也因此,没有爱的人,不会圆满,或者说,当人没有觉察到自身的爱时,他就还没有认识自己,也就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彼岸的道路,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初的伊甸园。同时,也只有爱可以承担起世间每一滴无辜眼泪的重负,否则真理会被压弯,道德会失去光辉,彼岸终成镜花水月。而这样的真理并非直到今日才发现,从人类文明诞生初期,爱就与真理一同诞生。孔子说:“仁者爱人。”所谓“仁”,并非高远玄妙的天理,而是人间的爱人。耶稣说:“爱人如己”,又有那句流传千古的爱的箴言:“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于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诞生了,哲人的心无法包容和承担世间的丑陋、罪恶和苦难,他们或者独善其身,自己以历史王道让心灵纯然光明,或者逍遥避世,无为化蝶在梦中和泪醉酒狂欢。他们依旧有所恨,诛杀少正卯,或者互相攻讦。而宗教圣徒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间更多的真理,却可以包容这个世间一切的罪恶、丑陋和苦难,没有人在他们眼里是绝对的罪人,每个灵魂都可以通过忏悔而得救,所有的苦难都会得到交代。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大部分属于宗教圣徒,剩下的才属于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等其他人。 这种现象暗示了某种被人忽略的真理。
面对人的存在的重负,被启蒙所揭示的人的存在的责任,承担的力量隐隐指向了基督教所贡献的爱的精神。当人爱这个世界,就可以负担起这个世界本身的“无”和罪恶,并且会有更强大的面向未来的希望。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上帝,理性之外的无尽疆域真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与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还值得人活下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人间世里生长的爱。而她可能是人身上最神性的部分,最不可解释的部分,最超出理性之外的部分,却也是最切近的部分,最相信的部分,最卑微的部分。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人的王冠。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圣经 · 哥林多前书》《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五):分类摘录
先说一下,这是一本相当好的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不过由于懒,我只对一些好的有趣的观点做一个分类摘录
中西比较:
7.现当代儒生何以不愿让中国的道德直观与西方的神性直观、理智直观来一番争辩?
9.中国哲人恰恰需要像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待自己的传统思想那样,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清理,才可以谈论道德形而上学自足的可靠性。
10.哲学难道仅仅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辩护?
17.“寻根”和“认同”的说法,基于一种精神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听任历史的偶然摆布
22.展开对话的基础只能是共同语言。
23.道德-超脱精神与科学理性精神无话可说,双方虽然冲突,却没有可能构成一种公共语言。
24.本世纪初,忧国的文人智士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其时,西方虚无主义文化思潮盛行,某些去欧美观光的中国智士以为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下场,证明了西方价值毁灭的现实,决意拒绝西方文化,返回东方的精神故土
31.精神冲突的对话是20实际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
儒家根本是德感,表现出来是乐感。基督教根本是罪感,别表现出来是爱感
审美:
37.启蒙理性摧毁了神性的根基,审美主义才会出场,审美理性是启蒙理性的结果
审美主义代替了最高价值
自杀:
42.通常的自杀一句这样的信念: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诗人的自杀不依据这样的信念,否则使人就不会自杀。诗人的自杀不依据这样的信念,否则诗人就不会自杀。诗人的自杀与其说是依据信念所发起的最后冲击,不如说是对信念的彻底绝望发出的求援呼吁
44.诗人笔下的人物可以为了信念而死,诗人自己却生来是为了信念而活的。加缪说得对,确实不曾有过为形而上学问题而死的人
44(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里洛夫用自杀作为条件与上帝交换位置。“我必须开枪自杀,因为我自己的意志的最高点就是自杀。”)
49.自杀者把自己的不幸视为最高的,无视上帝在为整个人类受苦,等于辜负了上帝的赎情
51.到的社会学的定量分析确实达到了严密的精确,随着这种实证定量分析地合理化,世界中的意义问题被排除了。……道德社会学之考虑社会的事实,人在这种事实中抛付的鲜血和眼泪被作为事实接受下来。
52.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杀是产生虚无感的人向世界强行索求意义的一种手段;在黑塞看来,自杀意味着放弃自我完善,要求返回母体、返回上帝、返回宇宙,从死亡而不是从生存之中发现拯救者
63.叶赛宁自杀前割破手腕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在这种生活中死亡不是新鲜事,而活着也不新鲜
诗歌:
54.真正的超脱和厌世拒绝语言的世界,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
415.布鲁克斯和华伦《理解诗》:诗人意欲戏剧性地体现出人对生活在一个世俗化世界、亦即毫无宗教意义的世界里是怎样感觉的。但对于现代的读者,主要的困难在于他自己已过于世俗化,看不出诗人说些什么
理性与信仰,上帝:
60.(舍斯托夫:“用流血的头拼命撞击铁的理性大门”)
68.上帝的隐遁是必然的,人必须经历黑夜中的漂泊,才会懂得上帝的救恩,否则即使上帝近在咫尺,人们也视而不见
123.即便在绝望中回到上帝怀抱,也不是人性之所能及的,而是上帝亲临人的绝望处境与人一同绝望并承受诱惑时带给人的恩典。
138.托尔斯泰《忏悔录》:我希望我能认识那个不可知的事情之所以是不可知的,并不是因为我的理性这样要求是错误的(我的理性要求是对的,因为离开了它,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是因为我认识到我的之理的限度。我希望这样来了解: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能让我看出它必然是不可知的,而并非某种我的义务必须信仰的东西。
216.荷尔德林感到,以历史哲学和自然者需面目出现的思辨神学无异于在断绝与基督的上帝的关系
248.一旦经验理性不能遏制支持自己的怀疑,就会使自己陷入疯狂,知道其中必有新的东西出来成为上帝,成为理性的根据(基础)。这种在疯狂中出现的新上帝就是生物激情、历史法则或虚无的实存情绪。
255.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来自东方之光,它将知音下放盲目的,失去基督的人类
269.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且确实与真理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书信选》
270.律令伦理学不懂得内在的人,只知道从社会关系来规定外在的人的生活
308.上帝作为父的形象被暗中勾销,人与上帝的相遇不再纯粹是信心的激荡,也使理性的推论。上帝的形象变成了自然界的超验实体
323.理性拥立的天国不能建立在无辜的眼泪中
(神的权威会剥夺存在的自由)
333.理性的上帝是没有基督的上帝,在理性的上帝面前,人的自由意志才变得坚硬而脆弱
416.海德格尔的临终之言是,哲人不能把上帝思想出来,思想只能唤起期待
历史理性:
248.对于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基尔克果给予了坚定的反驳;历史理性只会导致荒诞。一旦不能相信荒诞反而不能活时,荒诞就成为最高的理性
(历史理性是不是恶魔,把历史中的恶都赋予意义是不是很恐怖,把一切都纳入普遍必然的历史进程,让一个个感性血肉之躯去填充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是否正当?)
325.必须驳斥对生活的认识高于生活、对幸福规律的了解高于幸福的历史理性主义
绝望与虚无:
61.绝望总之是对不得不相信的价值真实的不信任,对必须确信的意义的怀疑,所以才呈现为不可跨越的深渊
62.疯子领着瞎子走路
412.艾略特的空心人: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互相依靠,头脑里塞满了稻草。唉!当我们一起耳语时,我们干涩的声音,毫无起伏,毫无意义(艾略特不称颂空心人理应是人的信念,不声称世界的荒漠是人的精神滋养的来源)
荒诞:
马尔罗《人的状况》: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
378.大地需要荒诞的荒诞感,才堪称荒诞信念或荒诞哲学
383.荒诞人的信念看起来悲观之极,其实充满了一种人性的自豪感
反抗虚无,反抗荒诞:
75.现代的沉溺诗人的审美幻想是:明明自己随同世界的沉落一起坠落,却自己认为在反抗
儒家:
92.自然世界的秩序奥秘也靠君子人格的修养来把握,所谓参赞化育,与天地参的内圣精神。历史社会和自然宇宙的秩序都内在于君子人格之中
儒家里的君子有自信人格和自足意志
97.君子人格的意志几乎就要成为天的意志了。但礼为君子的一直自足提供了根据,也为其划定了界限
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99.也许这就是中庸的辩证法,你用自己的良心去悟吧,尽心知性就懂得如何选择了
102.如此看来,中国早已有唯意志论,这就是君子人格绝对自足的全能。幸而儒学重中庸,毕竟有君臣之序、君王之位以及历史王道的限制。否则不知会出现多少唯意志的风云人物
103.即便说三代之时真的有神性意志的上帝观念,也被儒学杀死了。
134.天问,是对王道神义论的质疑
135.德感作为性体论之根基乃是生命本源自盈无缺的精神意向,一种充盈的生命永恒复返的无穷感
191.原儒把价值实在的根据建立在生命的本然欲念和目的之上,使超越性的价值实在变成全然内在性的欲求,把超验的价值变成血缘——生理——心理的欲求,就植下了价值虚无、诋毁价值的种子
道家:
227.个体精神在清虚孤寂的自然事件中要得到心灵的安适,还需要积极的游心于意、即个体心智的适意游戏
儒道:
104.儒道两家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上是一致的,只是去向不同,一个要弘大生命,一个要归于生命的本然形态
125.儒道互补对君子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否则不知多少君子会死于非命。……无论儒还是道,个体人格都是不假乎外而足乎内的。……如果不承认隐遁逍遥,不仅君子的一直自足难以维持,他自己的存在方式本身也难以维持
127.一旦君子懂得儒道互补的大秘密,屈原的困境就消除了。
186.原人性与人性是中国式的解释学循环
罪感,基督教,社会以及其他
162.利他主义往往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式。利他主义把他人当做目的的同时,实质上把他人变成了手段……我借助于你达到我的生命感的升华,通过你进入我意欲企达的目的的状态。
163.爱不会依附于我,以至于把你视作内容、对象,爱玉立在我与你之间。所谓同情,根本上说乃是与上帝同在的共同感情
173.与其说人本主义的觉悟是对人性的赞美,不如说是对人性的诅咒
193.自足的本然生命的欲念和目的不仅成为政治关怀遭到否定时否定政治关怀本身的根据,也是使个体不至于为政治关怀的毁灭发疯的原因
200.这里的德不具有伦理的含义,而只是本然生命的含义
247.基督教的新约取代犹太教的上帝与人的旧约关系,就是要让上帝与人的新只爱关系代替律法
249.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成品,自由的历史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成品
360.卡夫卡: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类都来抓他,但武术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
爱与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留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362.在卡夫卡看来,恶有三种形态:自然而、习惯恶以及为善和正义作恶
拯救与逍遥:
226.大乘佛教要求菩萨在进入真如境界之前重返恶的现实,对劫难世界中的云云生灵有深切的关怀,如此大宏大愿,也不过要把人救渡到一个许诺彻底解脱的存在状态(存疑)
233.(禅宗)“自性清净”就这样勾销了佛陀深味;解脱无需再以大慈悲的解救行动为前提
235.禅宗把印度佛学中的宗教思虑清除得干干净净
250.要么确证理性承负现世恶的可靠性,要么返回神本精神,要么靠神话来承负恶,确信根本虚无,然后靠荒诞来生活
(赞颂吃我的事实是什么?)
368.耶稣没有政府,没有胜利,没有成功,诚如巴特所说,除了悲惨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成就。然而,在基督事件中,现世中的人性重新碎裂成两半,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成了人可以凭此与上帝的救恩重逢的信物。
397.实证地运用理性,最终取消理性,生存的法则让位于冲动及其本能,尽管美其名曰生命激情
情:
243.整部红楼梦不过是一部情案:情能否在大荒无稽的世界中重新确立。
244.石头本来无情,又何以能够禀情;如果定要补情,何以又非得是石头
255.红楼梦的意义首先在于:信奉解脱的精神发现了生命中有不可解脱的东西
266.提出情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唯有红楼情案……淫在这里标明的是一种生存世界的基本动力
(注意曹雪芹对庄禅精神的怀疑)
273.对于曹雪芹来说,女性的干净是一个超越地象征
284.正是庄禅精神使曹雪芹的新人重新变为石头,使他最终不能摆脱恶魔的追逐,也使中国诗人的冷漠素质愈为深厚
鲁迅
347.觉醒的冷眼有什么了不起呢?难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
刘似乎认为鲁迅是更加的石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