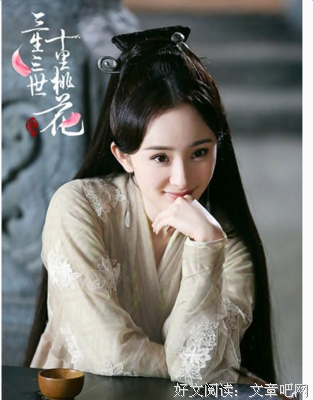
《奇来前书》是一本由杨牧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80809-0823
●啊……終於到了。三十二開剛剛好,要比洪範版小而更順手。不足在於封皮不加膜……
●川寒西岭千秋雪是骗人的,在成都看不见山,可是我又何必羡慕花莲人能有奇莱山呢。故乡不必有山不必有水,只要有回忆就好了
●多半是因为杨牧曾经在我心里的位置,才翻开这本书,确实是如假包换的杨牧的文字,精致细腻悠远绵长,华章丽句婉约迂回,可这一切优点在今天的我读来却让人起腻,营养贫乏,我意识到杨牧已经不适合我了。
●美。
●真好。
●2018.087 “当文字留下,凡事就无所谓徒然。”无论欣赏不欣赏,笔墨终有痕迹。中国应当庆幸自己的文学传统还在港台一片传承发扬。
●大概悠长人生里难免会有幻想,我们也都是从这样的少年时代发源。第一次真实地接触花莲的山山水水。
●在杨牧面前简直词穷...
回忆起那个暴雨的下午躲在书店里看“山风海雨”的情形,昏暗的光线、潮湿的空气特别适合,对于太平洋西岸那座小城的想象--避世,日据年代后短暂的宁静,小城花莲(自然状态下)的光与色,细微与庞杂的物与事,都被杨牧节制又诗性的文字缓缓地收入段落中,瞬息间这些气息又散发出来,飘在这个暴雨如注的江南小城的书店中,让我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恍惚,所谓语言对抗时间的说法,不过如此。
诗人是诗人和诗人的孩子。
生于斯,长于斯,杨牧将花莲的美描绘的淋漓尽致。从不同的地方,去叙述了自己成长的故事。在山中玩耍,在山中看这个时代的缩影,去疑惑,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一样,我们总会盼着长大,却去思考成长中的许多未知不可测,然后在一次次的辗转反侧中得到“山的启示”,获得成长。
作为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散文家,杨牧把诗人的特性在书中小时候的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唯美的文学,华丽的词藻,绘画出的不可见的一种扑面而来的让人沉浸其中的感觉。
华美的词藻是否会使得一本书华而不实?可能会晦涩,但绝不会无法读懂,一种绝美的意象在之中形成,尽管看不懂之中的某些文字,可一切早就在你面前铺开。这可能就是vr一般的沉浸式体验。
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一种冥冥之中却又模糊不清的映像在脑中出现,指引着你前行的道路。
《奇来前书》读后感(三):脉望馆札记 之 :「無所事事」的美麗
這個話題當然不是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行徑,乃是想說一類文章。
廣西師大出版社終於引進印行了臺灣作家楊牧先生的兩本「近似」回憶錄《奇萊前書》和《奇萊後書》,書衣設計頗見匠心,仿佛油畫質地的同一幅山景一彩色,一灰白,前者似乎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錦瑟華年,後者則是屏除絲竹入中年後的沉鬱了。說這書「近似」回憶錄,是因為所收文章並不像齊邦媛先生《巨流河》那般依歲月流轉一樁一樁寫來,從涓滴細水終於大河前橫,而是揀定若干個主題,自由分章寫成,鬆散而自由,篇目之間自然也少不了草蛇灰線,或暗或明,從翩翩年少,敏感多思,寫到漂流異國,求學問道。
說楊牧的這兩本書具有「無所事事」的美,是因為作者鑄煉文字的手段高超,樂此不疲地把文字本身也當作目的了,人們盡可以順着其文字組成的河流悠遊而下,反倒不那麼在意作者在談些什麼了,莊子說得意而忘言,此處便是得意亦得言,換句話說,他是把散文當成詩來寫。就像作者在書裏借一位詩人之口說:「音樂在一切事務之先。他給詩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詩是音樂。……你們若是讀過魏爾侖就知道,他的詩可以說是一片和諧之音,能引人走向夢幻迷濛之境。」楊牧的這兩本書大部分篇雜都具有這樣的音樂美。
在臺灣比楊牧略早一點的余光中先生便是此中高手,早年的散文大品,黃鐘大呂,撲頭蓋面而來,中文典雅駢儷的傳統加上歐風美雨的恣肆汪洋,余光中把白話中文煉就成一顆照破山河的燦燦金丹,讀他的《聽聽那冷雨》,《逍遙遊》,《鬼雨》,《南太基》諸多名篇自然而然會被他的駭浪洪濤漫濕震撼。
他們的文章當然有思想,有理念,然而文字亦是不捨放棄的一葉扁舟,野渡無人而輕舟自橫。順時光河流回溯,五四以來其實已有這一脈支流汩汩未絕,讀一讀廢名、鶴西、林庚這三家的詩文隨筆,他們也尤其沉溺於這無所事事的對文字遣玩的意興之中。隨手抄一段鶴西的《房子》:「我也愛看雨中的房子,仿佛越是大的雨,它越能不慌不忙地承受,一個個雨珠只助成它談吐之好看罷了。黃昏溫靜,積水盈庭,我們看那燈火闌珊處,不正是其婆娑的倒影嗎?或有如此時,風沙俱起,則它又最是一個無可躲避的風塵中客,一任其磊落之胸懷來肩負了。」他寫了什麼嗎?好像什麼也沒寫,只是一段一段的印象,一段一段的意識流,光影明滅,音律和諧,打成一片融合的氣象。
如果再往古代去尋找這一傳統,那便是庾子山的抒情小賦和李義山的《無題》七律,「樹入床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寥寥數語,把尋常日子薰染得活色生香。楊牧先生的兩本「奇書」,實在續得起這樣的文采風流,只是今日太忙太亂太懶太累的人們還有無足夠的耐心與敬意去賞讀玩味,也實在是個問題。
《奇来前书》读后感(四):关于《奇来前书》
杨牧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是从一个朋友嘴里,他是杨牧的忠实粉,每次和他谈论某个作家时,他都以杨牧作参照系,有一次拿来作比较的对象甚至是陶渊明。他现在台湾新竹清华读研,我猜测这其中部分原因和杨牧有关。在他的影响下,我买了《奇来前书》、《奇来后书》和《杨牧诗选》,去年读完《杨牧诗选》觉得不错,用词华丽别致,语调也非常柔和。但是读《奇来前书》的时候,我却难以用同样简单的几个形容词来表达我的感受。
刚读的时候,我真想把这本书直接丢掉。一个句子兜兜转转老半天,好不容易读到句号,却还弄不明天他在说什么。比如序言第一句:
“那些曩昔旧事当中犹闪烁存在于记忆的,在不断隐显迭代的过程里,有些属于矇昧,矇昧所以恐惧,和认知,以及认知带来的喜悦。”
假如这些句子出现在诗中,我大概也就半懂不懂的吞下去了,可是它却出现在一本名为“文学自传”的散文集里,于是我陷入纠结。我把诗歌看作是汉语的实验场,对一切几乎是“语词新作”的文字都能报以赞赏,至于小说与戏剧,也能理解一些几近疯狂的探索。但是,散文,或许我还是太落伍了,一直以为“清楚明白”的底线至少能让散文来保守,于是在守旧思想的捆绑下,我第一次弃读了。这一弃,就是一年半。
之所以在最近把这本书重新捡起来,是因为怀疑自己的傲慢。或许我不应该用那么浅薄的傲慢来对待一位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且我也好奇,他到底好在哪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继续往下读。
于是第二重难关出现,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认识字了。在这本书中会遇到这些词语:“窅窱”、“疗夐”、“雝然”、“黼黻”。不要问我上面这行字是怎么打出来的,我查的是《王力古汉语字典》!除了这些完全不认识的字,有一些词,你明明认识,比如“乙乙然”、“定定的”,却绞尽脑汁也不知是形容什么情状。
还有第三重难关,极度私人化的叙述,使人无法与作者产生共感。他写大海、写台风、写母亲,都是文字的精心排列,而读者只能凭着几个词语的勾连想象一些画面,但这些画面都如云中厮杀,看不真切,更不会萌生感动。这些叙述,或许只对作者个人重要,甚至只对作者的想象及美感的养成重要,但那仅仅是他的私人感触,外人看了,也琢磨不出门道。于是,给人一种空洞矫情的观感。
冲破三重难关之后,果然见到天青云破处的幽微光亮。若说,杨牧是把文字当生命在经营,或还不足以表达他对文字的沉溺。他自己写到“文学是生命的全部”,甚至还说,“我怀疑,有时爱是手段,字才是目的。”一个对文字偏执到这种程度的诗人,写起散文来可以想象会精致到什么程度。
《奇来前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语气如此贯通,读起来毫无违拗的文字。无论用词多险、句子多长,也无论看起来多么错落庞杂,只要一读,就仿佛抓住了主旨,一路猛进,华丽流畅,美感丰沛。想起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说的,“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奇来前书》,或许真有空洞的嫌疑,但绝对不是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
豆瓣上对杨牧的短评只有85条,也分两极趋势,要么盛赞其美,要么贬斥其空洞。依稀记得有一条说,汉语是杨牧的奴隶。有些过头了,实际情况,杨牧是文字的奴隶,一生奉献给文字,埋首雕琢,像个孤僻的老匠人。
读这本书,对我最大的益处,是正视自己的傲慢与偏狭。一开始我用了多少污言秽语咒骂这本书,如果没有坚持读完,我或许依旧像个没有教养的小孩子,只会说,这个不好,丢掉!
《奇来前书》读后感(五):花莲的华兹华斯?(林楮墨译)
花莲的华兹华斯[1]? 2015.8.25 丹尼尔·伯施 《奇莱前书》,杨牧著,陶忘机、黄瑛姿译,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96页,198-204[2] 副标题为“年轻诗人的教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版本的杨牧《奇莱前书》集结了三卷独立且篇幅短小的回忆录,这位备受推崇的台湾诗人,是24本书的作者,亦是2013年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英文读者将在本书中读到杨牧早年成长的生动记述(他在日据时期出生,本书贴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也将有机会使自己的批评意识复杂而深刻——杨牧和其他作家希望有一天会将视为“台湾文学”,而非地域性的“来自台湾的中国文学”。 杨牧的自传性诗化散文,如他的诗一样,通过对台湾风光、植物、动物的细致观察来进行比喻和象征。虽然潮湿、光线、微风的气味——年轻杨牧的经历——是具台湾特色的,他的主题却完全属于全人类的。每件趣闻都围绕在深情回顾本土的现实中,所以我们阅读的作品,的确是一部台湾文学,尽管只是本译著,然而我对《奇莱前书》中雄健的文章之沉溺,与我曾阅读佩皮斯日记、卡夫卡日记或是某段蒙田随笔时的感受一样深刻。我给他的回忆录描绘出以欧洲为中心的联结网,既然这能够使我感受到杨牧作品的才华显然迥异于西方,我相信,这也证明了杨牧的成就并非(任何贬义下)“地域性”的。杨牧与西方作家及文本有过一些渊源——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3]拿到博士学位,业已将叶慈[4]的诗迻译成中文,并曾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5]的成员。我希望这并没有削弱我对一个“新生”的台湾文学的尊敬。例如,当我说自己钟爱他对华兹华斯《序曲》[6]中“偷船”部分的修订,我觉得那并不仅仅因为我察觉出了二者的相似。 下面华兹华斯的句子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受喜爱的一些段落: 一个夏夜(在她引导下), 我发现一艘系在柳树上的小船, 在一个岩洞中,它寻常之归宿。 我径直解开绳索,踏进船里, 远离水岸而去,一件隐秘之举。 不安的愉悦,回声响彻山间, 我的船前行着,两侧留下小小的水圈, 在月光中漫不经心地闪烁, 直至消溶成一道白练。 但此时,我像一位自负技艺的摆渡者, 为了直接抵达终点,将目光汇聚 在一座嶙峋山脊的顶端, 那是我视野内最远的边界,远处 只有繁星和灰蒙蒙的天空高悬。 她是艘精灵似的小船,我积极地 将双桨插入无言的湖水,划水时当我起身, 小船即如一只天鹅在水面漂浮, 这时,就在挡住我视线的峭壁后, 露出一座险峰,黑暗而巨大, 仿佛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举首。 我一再击水,那阴森的形状, 在我与繁星之间愈发滋长, 紧随我身后,如同一个生物, 似乎有自己的目的,缓慢有节奏地运动着。 我以颤抖的双桨调转船头, 透过无言的水面,取道重回柳树遮蔽之所, 让我的小船停泊在岩洞里—— 穿越草地回家,心情沉重而落寞。 但在我看到那景象之后,一切对于未知 生命形态幽暗暧昧的意识,在我的思维中 萦绕多日,黑暗吞噬我的思绪, 谓之幽僻或空旷的荒原,那些熟悉的形象 没有残存下来:树的倩影、海天美景 与田野之绿意。但是那巨大有力之体, 不像人类那般生活,白昼在心灵中缓慢移荡, 夜里来侵扰我的梦乡。 (序曲·卷一,357-400行) 从《奇莱前书》开头的几行中,我们得知杨牧,像华兹华斯一样,感知到本土的风景仿佛同他倾诉——后来我们明白了当他越出这片社会的边境时,他频繁地收到此般指示。在年轻的华兹华斯带走不属于他的船之时,没有道德权威走来与之交谈。山在和他对话,他们根本没有明明白白地反对他古怪的举止,而且,有一天正处在学生时代的杨牧逃课了,他独自停留于一艘租来的小船上,在他同学常到的校园里的桥下划了一天,可想而知,他的同学不能或看不到桥下的他,但是群山、河水和海洋似乎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与华兹华斯一道,他的一举一动既是儿时的贪玩,也是文学的修辞。在杨牧的版本,一个亚热带版本中,对于华兹华斯而言若隐若现的山既是火山的峰顶,也是一堵水墙…… …我张望河水,一面高声对木寮里那瘦高男人说:“我的脚踏车怎么办,假如我租一个钟头的船?” 我听见熟悉的乐曲,自远处漂浮。 那人又说:“好了。”他再度俯身到我背后,使我疑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当我回头查看刹那,正感觉船身向前拐动,而我看到他是用右手猛力一推,嘴巴快意地喝道:“去也——”小船于是脱离石梯码头,平稳而舒畅地投向河心。 这河来自西望俨伟,苍冥的山群,但并不深入远脉当中,我曾经回溯它的源头,后来,在一个炎炎的夏日清晨,我曾经骑脚踏车循岸前去,午前就到了。那时我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河的源头那么窄,可是浅浅的水流又那么清澈,透明?大小石头错落散置。好像是山神水鬼和木魅花魂竞相安排的,梦幻的展示。是的,窄窄小小的水流两边长满灌木和藤蔓,密叶间迸生一串串雪白累累的花,我不确定那花的名字;河床更像是筛净的珠盘,镶簪了翠玉的边。泉水下来以后,依旧清浅,可是河床忽然扩大,但那只是台风来时山洪爆发的倾泄,平时它悄悄流淌,有一种宁谧沉潜的样子,并不引起你的注意。这河接近美仑水势渐大,于是深情地环小山南麓绕过,缓缓无声,流洗那接连不断的芦秆,野芹,春堇,水姜。这一岸巨大的凤凰木将叶影和花荫重叠地投进水面,有时甚至将叶子和花蕾纷纷坠落,轻轻飘上悠闲的流波,浮沉而去,那么慢,大树后高筑的护堤斜坡也长满了野花——堤外就是花莲老街上聚居的人家,但我还是不太相信那样源自一筛净的珠盘,并且镶簪了翠玉的边,那样清浅的梦幻的展示,竟也以它沸洊之声势教人心存畏惧,在凤凰木后筑起一条长长的,长长的护堤。我可以听见那歌声持续不断对我传来。是河水的音乐吗?或许是我心神深处激荡出来的创作,如此汹涌,如此澎湃,如此轻柔,沉郁,无所不在,又像一种回响,随时即将消失于无形。 我的小船犹豫片刻,不知道应该向什么方向行进。这河到了下游,水面变得出奇广阔,而且那一边对岸陡然升起,如断崖,前后数百尺之遥,连绵,自西而东,引导流水在这里遽尔歇止,仿佛不期来到一森森的古潭,忽然腼腆宁静,只能暗中低吟那重复的,熟悉的调子。这一带河水,曩昔在乡里中号称“陆军港”。 我打着双桨顺流而下。我知道前面不远就是海,心里有些害怕,但也许喜悦居多。 “假使,假使现在忽然山洪暴发?” “大水狂泻自山岑高处,以无比的快速赶到,汹涌向我的单舟扑来。即使它不当下将我打入水底,也足以用它的重力攫我往河口翻滚滑落,浮起来,沉下去,迎向咸腥的海水,在第一波山洪和海浪不期相遇的重击下,昏晕过去。于是我像一片断根的水草在太平洋不即不离的澳隈里飘荡,在彩色小鱼群中颤抖,在珊瑚礁间摇摆,而终于慢慢地,像水草一样,在大海不可拒绝的激情舐吻之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被洗得干干净净,透明的精神,无重量的灵魂。” “你早已经死了。” “第一次死不算。”我说:“我被急速赶来的冷泉拥进怀里。那时一切都太匆忙,出其不意是不是?我不知道那是恐怖还是甜蜜。我不知道那是悲伤,还是喜悦。那说不定就是一种舒适,在温柔的清水里放松地死去,像云霭,春草,丝绒,像永不休歇的上升的咏颂,一种奉献,皈依。然则就让它来吧,让山洪赶到,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将我带去,在我还保有完整的真情和不着边际的爱的时候。我是多么纯粹,清洁,若是如此纯洁可以死去,在飞禽走兽和昆虫的祝福声里,在鱼虾水族的抚慰,草木花卉的垂顾里,就让我死去吧——无知觉的死,或许并不能说是死。” “什么死,才算是真正的死?” “什么死才算……” 这时我的小船刚穿过大桥下两座桥墩间的水道,像长脚蚊不自觉停驻在急湍上,被流波托起下送,仿佛有歌声依依相伴,细如天使的叮咛,又完全是静,船尾的水纹粲然开放像一束春花,即刻枯萎,流落,然而反复不懈,始终不曾散失。 “什么样才算?” 但是我听见别的声音,在我自我缱绻的盘问之外,高处接近大桥北端是脚踏车下坡纷纷刹车一阵急似一阵铰链磨击发出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学校放学的声音。他们应该已经降旗完毕,听完训话,解散回家了。九百个男学生拥出来,甩着完全一样的书包,颜色一样,重量也一样;帽子在头上,在手上,或者像我把它塞进书包里,这一天我没有参加降旗。我从午间开始就觉得坐立不安,心中浮沉着不成型的诡异的调子,好像隔着高大阴森的古墙,深院里有人对我悠悠沉湎地吟唱,一首破碎的,然而仿佛是特定的可辨识的,谨慎的歌,以难解的文字发音,但偶然突出些熟悉的表情,又似乎是我醒睡之间时常听到的。我左右张望。远天,海浪,匍匐的山,老得不能再老的榕树,扶桑,美人蕉,屋顶下那一天比一天膨胀的蜜蜂窝。“怎么样才能把自己放开,自由,解脱,与众不同?”我反复对自己提出这样没头脑的问题,然后困顿不堪:“怎么样才能证明我与众不同?”黑板上写满了专有名词:启蒙时代,领主,农奴,工会,迦里略,锁国政策,救赎券。我从游泳池边的小道降落台阶,缘操场一头紧靠着高耸的石墙向前走,书包挂在左肩,帽子在书包里,小心不要一脚踏进排水沟,过升旗台,从新植了凤凰木的斜坡蹑足转入脚踏车棚,轻轻开锁推出我的车,双手扶好越过小门,没等到在另一头补车胎的老金发现,我已经疾驶而去。 “假使现在山洪暴发呢?” “大水要很久才赶得到这里。” “假使,就是假定假使,刚才不久以前已经暴发了,而现在它正好汹涌赶到,对你迎面扑来,现在当你打桨回舟……” 大水将淹没我,使巨大猛烈的力将我和我可悲的小船打翻,沉没水底。没有人知道我就这样沉没了,死了。那个瘦子一定闭嘴不提我租船的事;一个人上课时间带书包来划船,神魂颠倒的样子,太阳都下山了还守着大桥墩不动。他知道最好别提。问老金?老金说好像听见有学生降旗以前就到车棚来过,的确可能有的,但他忙着帮许老师补轮胎,擦车,来不及注意是谁。不过人们也许根本没想到问老金。我沉下去,在水底翻滚几次,很快就冲出河口,投向大海。 小船搁浅在沙滩,船底朝上。 这似乎是很好的结局。或许不能说是结局——是一个开始。我被远远赶到的大水带走,进入渺茫,阴凉,辽阔。那无限神奇,澎湃的空间,如此丰美广大,已经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关于作者: 在1998年,丹尼尔·伯施凭借对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反复刻画而作的四首诗获得波士顿评论诗奖,他的作品刊登在诸如Poetry, Slate, The TLS, Agni, Berfrois, The New Republic, The Huffington Post, The Fortnightly Review, 和The Paris Review等杂志上。他的诗集,《熔炉》(Crucible)在2002年由Other Press出版,他的八行两韵诗《八度音阶》(Octaves)可在beardofbees.com上免费下载。丹尼尔在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梅里马克大学、核桃山艺校和埃默里大学教授写作。 (林楮墨译) 译注: [1]华兹华斯:即William Wordsworth,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2]198-204:本文所引哥大社版英译杨牧《奇莱前书》页数。 [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译柏克莱加州大学,简称UCB。 [4]叶慈:即William Butler Yeats,另译叶芝,爱尔兰著名诗人。杨牧1997年于台北洪范书店出版其编译的《叶慈诗选》。 [5]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67年成立,由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与其妻子,作家聂华苓二人创办,是全世界首个由一间大学举办的全球性作家交流计划。 [6]《序曲》:华兹华斯叙述自己心灵发展各阶段的印象、感受和思想的诗体自传,写作始于1799年初,并于1805年完成,开创了自传诗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