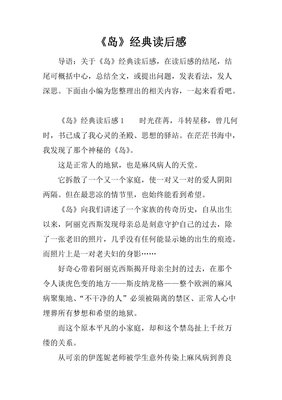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是一本由[马来]张建德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读后感(一):王家卫的电影
本书主要是从《旺角卡门》《阿飞正装》《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等王家卫的作品,来描述的。从这里有很多是讲述王家卫的创作手法, 利用当时的技术,规避一些关于摄影的壁垒等。王家卫的的台词像是一种格言,又像一种飘离的诗,里面不乏幽默,文学味很足。他通过他的人物的讲述,来叙说一种城市疏离的感情、一种过去的缅怀、一种多重视角里的变奏。《东邪西毒》、《堕落天使》里,还是《重庆森林》、《花样年华》里,都会有一种自恋、幽怨、恶毒式的语言在他的电影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据介绍他拍摄的电影没有一部写好的剧本,而是边构思边拍摄,慢慢的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和自己的独有的特点。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读后感(二):《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让“把玩”光影的人成为某一个人的光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让黯淡在时光里的记忆重新鲜亮。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我因什么缘由看了这部电影,某个片段触发某个记忆点,光怪陆离的是电影还是我自己。王家卫的电影总是能一眼辨别,暧昧的光影,晃而不乱的虚实,经典的港风色调,用数字排列逻辑的台词,组成了别有一番韵味的影片。王家卫的电影记录光影,叙述时空交织产生的好坏故事。他在拍故事,而我们在看他拍故事。曾和朋友模仿过王家卫的电影风格,用快门、光圈调节,试图记录下城市的夜色,虚杂的噪点和青鸦的光,即使模仿宣告失败,但那晚的城市、霓虹灯光、街边招牌、车水流过的嘈杂和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笑,都被印刻在数码中,不会过期。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读后感(三):满足了!入伙不亏的程度!
这难道不就是一本王家卫爱好者的必读刊物吗!
之前关于王墨镜先生的专书好像也并不多,比较著名的比如Gary Bettinson的《The Sensuous Cinema of Wong Kar-wai》,还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以及影集《WKW》,但从很实际的角度来说,上述书要么贵、难买,要么难读,要么又贵又难买又难读,anyway这本书我终于是等到了。
标价才60元啊,朋友们!封皮也很好看,嘻嘻~
说书的内容。张建德对王家卫的分析,咋说呢,对我而言,他给我提供了太多太多我很有可能永远都想不到的角度来对王的影片进行阐释,理论很多,却并不枯燥。这种阅读感觉蛮奇妙的,有真实的“跳出”感。
另外本书以王的作品来结构章节,英文版截止到《2046》,中文版还增加了《手》《蓝莓之夜》《一代宗师》。
满足了满足了(家卫迷妹,合上书本面露微笑)
我之前读过张的英文本,硬读当然也读得懂吧,但是,自己理解和苏的译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的丰富度,那简直就是俩文本了——我是想说可能不会有人比苏翻译得更好。
拿到这本书可是能足足高兴一整天嘞!
最后,我永远爱王家卫。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读后感(四):哪些作家影响了王家卫的电影创作?
王家卫往往被认为在影像美学层面做出了重大革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他的电影一直引领着一种美学风潮,受到全世界影迷的追捧。这个现象与王家卫的电影展示出的深厚文学根底不无关系,从他为人津津乐道、高度文学化的对白可见一斑。那么,王家卫电影的文学滋养从何而来?近期出版的《王家卫的电影世界》给出了某种解答。
普伊格是对王家卫影响最大的作家
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在众星云集的拉美文坛并不引人瞩目,他不从属于“爆炸文学”团体。虽然一生创作了《蜘蛛女之吻》《丽塔·海沃斯的背叛》《伤心探戈》《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等八部长篇小说,普伊格的世界声誉直到晚年才真正建立。《蜘蛛女之吻》是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电影,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
普伊格一生颠沛流离,曾在罗马学习电影。他最初的梦想是拍电影或当编剧,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以写作谋生,普伊格经常说:“不是我选择了文学,而是文学选择了我。” 因为由衷热爱电影,普伊格的小说带有鲜明的影像色彩。譬如他喜欢借助人物对话推进叙事,《蜘蛛女之吻》即是典范——全书从头至尾都由人物的对话组成。普伊格广泛吸收通俗小说和各类现代艺术的滋养,创造了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与此同时,普伊格的小说往往聚焦于阿根廷社会中下层普通人,同性恋、罪犯等边缘群体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这也是他与“爆炸文学”作家们不同的地方。
王家卫深受普伊格的影响。他曾在访谈中提及,“南美作家影响我最大的是写《蜘蛛女之吻》的那个作者(曼努埃尔·普伊格)。到了现在来说,对于我拍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正是他。最好的是原著小说。不过他最好的作品不是《蜘蛛女之吻》,他最好的作品是《伤心探戈》,很伟大的作品。在他之后,我就没看过什么伟大的作品了。”这是非常高的赞誉,如同马尔克斯在读过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后发出的由衷感叹——“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王家卫和普伊格的缘分,由对王家卫的电影事业有提携恩情的谭家明促成。正是谭家明把普伊格的《伤心探戈》介绍给了王家卫,王家卫读后爱不释手。“根据谭家明的说法,王家卫尝试通过将这部小说的结构运用于他的影像来掌握它。”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作者张建德甚至称 “王家卫或许就是香港电影界的普伊格”。
在张建德看来,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可被视为《伤心探戈》的松散改编。据他分析,王家卫根据演员的情感驱力重新诠释了《伤心探戈》,“通过独白式对话和允许人物拥有自己的情感空间”。并且,在以意识流的方式表现人物思想方面,《阿飞正传》和《伤心探戈》都颇具实验性而又细致入微。“王家卫善于拿捏普伊格小说结构中看上去不相关的元素之间微妙的关联”。
《阿飞正传》里有一个镜头是张国荣对着镜子凝视自己漂亮的脸,这让张建德联想起普伊格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丽塔·海沃斯的背叛》中写到的一位年轻人,小说里也出现了年轻人对镜子梳理卷发的描写。这种联想乍看起来或许显得牵强,但两者暗中的联系也并非绝然没有可能。
《春光乍泄》与普伊格另一部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有松散的关联。《春光乍泄》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先,王家卫想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改编为电影。但在制作过程中,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改编虽然未能实现,《春光乍泄》对病态性欲的关注还是让人想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中充斥的色情描写。这说明,《春光乍泄》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有着十分隐秘的联系。
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花样年华》的灵感来源是刘以鬯的小说《对倒》,已被很多人知道。《对倒》写一男一女的故事,男人从上海移民来香港,女人则在香港土生土长。《花样年华》讲述的也是一男一女的故事,一个是有夫之妇,另一个是有妇之夫。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的片尾字幕里还特意感谢了刘以鬯。
刘以鬯在2018年6月去世后,王家卫在微博引用刘以鬯小说《酒徒》中的话“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来纪念这位香港作家。很多大陆读者正是通过王家卫的“引介”间接知道了刘以鬯的存在,但刘以鬯在香港实则鼎鼎有名。刘以鬯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被认为与金庸齐名。王家卫与刘以鬯一样,先是在上海出生,后又移民香港。两人都对海派文学情有独钟,这或许让王家卫在初次阅读刘以鬯的《对倒》时一见如故。
刘以鬯的《酒徒》被认为是香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开头令人过目难忘——“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如果熟悉王家卫的电影,这种绵稠、细密的语言实在很像王家卫的台词。陈子善称“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花样年华》首映后,一本叫“对倒-花样年华写真集”的书在香港出版,书中的图片选自《花样年华》中没有出现的镜头,文字则来自刘以鬯的《对倒》。王家卫在该书前言中写到,“对我来说,Tête-bêche(法语词汇,意为对倒,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不仅是邮学上的名词或写小说的手法,它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王家卫说,“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其他作家对王家卫的影响
除了普伊格和刘以鬯,科塔萨尔、村上春树、金庸、雷蒙德·钱德勒、加西亚·马尔克斯、太宰治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影响到了王家卫的电影创作。张建德认为,《阿飞正传》在借用《伤心探戈》的人物和情境外,可能还调用了其他文学资源。比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小说里涉及记忆和遗忘的幻想让人想起《阿飞正传》里张国荣扮演的旭仔。
村上春树的另一部作品《遇到百分百的女孩》则影响了《重庆森林》。“金城武饰演的害着相思病的警察以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喃喃回忆,或许是村上第一人称叙述的延续。”张建德认为村上春树对王家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王家卫标志性的独白反映了村上春树小说的对话风格;其二,两人都认同叙事是对记忆的重述。
此外,王家卫也深受科塔萨尔的影响。张建德便认为,《春光乍泄》与科塔萨尔《跳房子》的关联,实际上胜过了普伊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春光乍泄》的英文片名是“Blow-Up”,这也是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一位王家卫极为推崇的导演,两人曾执导短片集《爱神》)的《放大》的英文片名。巧合的是,《放大》改编自科塔萨尔的《魔鬼涎》。
其他一些显明的影响不必多说。《东邪西毒》改编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是一次极富创意的个性化改编。“《东邪西毒》既可以被合乎情理地视作一部改编自金庸小说的影片(尽管是激进的改编),又是一部武侠片(尽管并不遵循这一类型的陈规)。”《堕落天使》的片名来自《圣经》,明显指涉了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和科塔萨尔《跳房子》中“蛇社”的成员。
总之,王家卫通过援引电影(更多是新浪潮教父戈达尔的电影)和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以及半文学资源(歌曲、诗歌等)等,将其融汇为一种高度鲜明的个人风格,从而成就 了“一种以电影化的风格讲述故事的感性”。这位拍片没有剧本,把拍摄周期不断延长的香港导演,事实上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