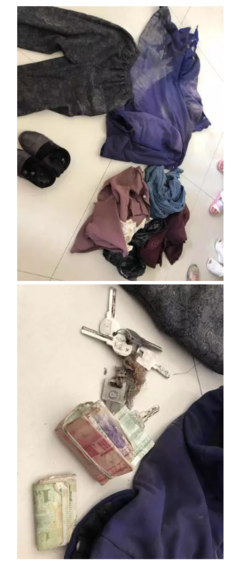
《身份的焦虑》是一本由[英]阿兰·德波顿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身份的焦虑》精选点评:
●看来我对焦虑已经想了蛮多了,这本很无聊
●自己的思考,自己知识和看法的梳理;我喜欢这样的书。我喜欢波西米亚。
●读当代作家发现还是需要读原典,否则没有办法与作者对话,也没有办法去更好地理解他在此处论证地用意。不过还是可以仔细聆听他对原典的见解。通读下来每页都做了标记却让我没有想法有点难过难解
●详细分析身份的焦虑的起因和解决方法,前面起因精辟,后面解决方法略松散。劝自己不焦虑这种事,说起来道理很多,实际上要的是修炼和参悟,一本书能梳理思路,解决还远谈不上。
●1. 对身份的焦虑,其实是对关系的焦虑。自身在每一段关系中的位置,最终汇集成了身份。 2. 焦虑的首要原因是过大的自我。宗教和艺术,都是在通过感知自我的渺小而获得平静。 3. 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可用芒格的一句话概括:得到一样东西的最好方式是让自己配得上它。用这个视角看自己,会倾向于不断成长;用这个视角看别人,则可能变得势力。
●“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内容丰富的一本书,值得一看!)
●大概讲了为什么和怎么做;怎么做总结起来大概就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降低欲望值、更注重精神,去关注哲学和艺术等没有明显等级划分的东西,更正确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和世界等等诸如此类。[End]
●Kindred spirits 读了几页亲吻与诉说才发现这本和旅行的艺术是多好的译本,非常符合作者的前言。
●重讀德波頓的《身份的焦慮》,還是能獲得很多的啓發~
●哎。。德波顿啊。。就那种精神上想偷懒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的书啦
《身份的焦虑》读后感(一):你就是想太多…
没我想象中那么难读,但也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天。(感觉得重温)很受启发的一本书,从各个方面剖析了我们焦虑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往小了说,焦虑是因为期望值过高,虚荣势利不知足,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往大了说,焦虑跟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意识、物质需求、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等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读完反观自己,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闭塞,除了书、话剧,就是工作。对物质要求极低,不认识那些名牌,对奢侈品也没兴趣。衣服有几件能轮换穿就够了。所以好像之前都没有焦虑过。但近年来,开始焦虑,因为会想要强求一些事情,会想要我把别人看得多重要别人就把我看得多重要(但这是不可能的),在某些事情上也会略微在意别人的看法,偶尔会有不好意思怎样不好意思怎样的情况出现,偶尔会有“如果我那样做,TA会怎么想”的顾虑。
看完这本书有种被当头棒喝的感觉。想要找回之前那个不怎么焦虑的自己。其实仔细一想,人终有一死,这一生何其宝贵,何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跟着自己的心走就行。你可以没有限度的追求物质和权势,你也可以过得很佛系,粗茶淡饭诗书一生。不用攀比,过自己的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没有人可以干涉你的人生,你也没权利去对别人的人生品头论足。能做到这些,或许就能避免焦虑吧?
《身份的焦虑》读后感(二):Status Anxiety
这本书更多的是在系统的整理身份焦虑的由来以及如何抵抗这种不自主的令人痛苦的焦虑。
我们对身份的渴求来自于对“爱”的渴求,即让他人重视自己,获得他人关注。(这一点与阿德勒的优越感有点类似),资本革命以后身份与财富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造就了一大批势利者,更加重了人们对身份的渴求,与此同时近代社会物质上的巨大进步与商业宣传,最终将人们的物质欲望推向了高峰,民主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贵族制度的瓦解,也让人对地位的期望越来越高,使得“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地位与理想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这让我们的焦虑甚至多于封建时期,与此同时精英崇拜制度的确立导致产生了一种现象,认为富人不仅富有而且比别人优秀,贫穷的人即使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成为了社会中最低下的存在。但是这个制度忽视了外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过分注重物质财富,忽视内在品德的重要性。
解决方法则是,说几个印象深刻的,一摆脱对他人评价的过分看重,“ 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 ”二去寻求另外的价值体系,你不必为了迎合主流价值体系而将自己拧成麻花,你可以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证明生活的成功。
《身份的焦虑》读后感(三):悲剧是更好面对现实的方式
德波顿从分析身份焦虑的原因开篇,后半部从哲学、艺术、宗教等几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可以“解决”身份焦虑的方式。思路清晰,旁征博引但却也会让人有隔靴搔痒不得其解的困惑。
书中让我自己最受触动的是作者关于“悲剧”的叙述。无数的人说了无数次“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这句话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但德波顿的叙述让我有了一些思考。他在书中说,悲剧“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讲述伟大人物的失败故事,而不带任何讥讽或评判的语言”,它使得读者能够不贸然地评判这些英雄的所作所为,使得读者更加谦卑。报纸也好,当代自媒体也罢这类体裁擅长“把别人定义为心理变态、怪物、失败者和输家...对人的理解处于一个极端的状态”,而悲剧则具备了更多的复杂性,用一种对他人最为尊重的表达方式叙述他人的故事,“它认为人们在丧失尊严的同时,不应被剥夺让别人听见他们心声的权利”。其实优秀的喜剧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用让我们发笑的方式接近我们,让我们产生与主人公的共情,去了解他的故事,理解他的行为,体会他复杂的境遇而不是轻易地褒贬,站在道德的高低俯仰。
当遭遇焦虑时,无论焦虑感来自于与同侪的比较,或是外界的言语,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观察周遭也观察自己而不轻易褒贬,我们才能更清楚我们的处境,看清引起我们焦虑的源头。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因素压根不值一提。当然也会存在实实在在的压力,这样的观察仍旧有利于我们从情绪中解放出来而更关注于事情本身。
从小的教育让我太容易把事情的失败归咎于自身的顽劣,把一些成功总结为自己的聪明。事常有成败,对于自己的评价总也起起伏伏。尝试着不去褒贬自己而转向事情本身我想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相当多的无谓焦虑吧。
《身份的焦虑》读后感(四):德波顿的焦虑解药
德波顿谈到废墟的观点挺有意思。废墟或者说遗迹预见了人类文明与社会的消亡。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的报仇雪耻的美妙感觉。这种感觉会减弱人的焦虑。我想这就是末日或遗迹相关的作品受欢迎的原因吧。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另外宏大的自然景观或巨物,同样能减缓焦虑,如果说废墟代表了无限时间,那么巨物即代表无限空间。与之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与巨大的物体景物相论,人和人的差距显得微不足道,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
德波顿也提出了死亡的想法对焦虑的影响。死亡的想法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身份的焦虑》读后感(五):一些总结
1.
焦虑起因:成年人羞于启口的是他们对社会之爱的渴望,我们需要被关注、被尊重,被蔑视和无视的痛苦甚至高过身体上的痛苦。
解决方案:承认社会对某个人的评价是不公允的,大多数人都受意识形态控制,其能力和动机都不支持他客观的评价一个人。无视他人的眼光,坚守自己的价值抉择,可减少对身份的焦虑。
2.
焦虑起因:在看似机会均等的现代社会,人们认为财富意味着品质,即有钱人代表了勤奋、智慧等优于常人的品质,那么穷困就意味着对个人能力品德的否定,获得loser这种称号的耻辱。
解决方案:悲剧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正是因为主人公跟普罗大众一样,拥有一些高贵品质,也拥有缺陷。错误的时机或某一刻弱点的暴露即将他推向悲剧的深渊。我们对失败的认知,应该更具有同理心,并不一定是当事人的咎由自取,而可能是处境的必然性。
那种所谓没个人只要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的言论是不切实际的,大多数人不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这不妨碍他们自己认为按有意义的方式过完一生。
意识形态和商业上润物细无声的宣传,在我们不经意间定义了我们对价值的认知。需要有意识的克服这种心态。
3. 波希米亚
波西米亚人认为生存的意义在于体悟事件,通过孜孜不倦的观察和艺术化的表现。这与我的人生目标,感受世界探索美不谋而合。精神上,我可以称自己为波希米亚人。
波希米亚的价值体系是脆弱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对财富和成功的赞颂让其受到伤害。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卢梭,逃离到不受污染的净土。另一些人谨慎择友,只与价值观相近的人交往。这使我又不禁怀疑,如果诱惑是如此强烈,价值体系是如此脆弱,波希米亚人是否像他们宣称的那样纯粹。如果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被送到他们的面前,等待攫取,他们是会欣然接受,还是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