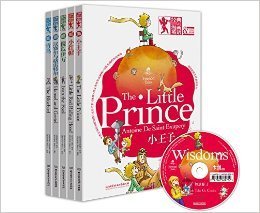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本由[俄] 索尔仁尼琴著作,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元,页数:3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精选点评: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
●世界如此,我也只能把我那本箱底裡的貨拿出來推薦給大家了。我看的是英文版,中文版是否刪減我就不知道了。
●拖拖拉拉,断断续续,几个月才看完。或许是译者的原因吧,很多句子看上去絮絮叨叨,含含糊糊,却不明其意。翻了翻人民文学版的,好像顺畅很多,也许应该看看那个版本。
●索翁成名作,阅读《古拉格群岛》之后的延伸阅读。批判力度自然不如那部,更显平静而隐晦,也因此得以出版。最后一句很有杀伤力,这样的日子要有3653天
●我想斯大林没有禁止《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有可能是这部作品对当权者的批判讽刺并不明显,甚至还能解读出一丝“教人乐观安于现状”的意味。
●本以为要写一个人的苦难就要写他的不幸,原来写他所有幸运的集合是更深的苦难
●再也不要回到那个被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支配的极权时代。
●苦役营的一天生活很苦,所以共产主义也很苦。
●3653天
●和《陆犯焉识》差不多一起看的,两本书同样是描述在恶劣环境中劳改的生活,但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读后感(一):集权专制的丧歌
这部短篇小说集,类似于中国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但是更加直白,更加坦率,而没有替当权者遮掩。
赫鲁晓夫能够发表这种小说,真是极大的失策啊,难怪苏联完蛋的这么早。
全书没有任何指责当权者的言语,只是用广大百姓悲惨的生活白描统治阶级的残酷,这种控诉方式更加深入人心。
共产主义和那吹一样是集权专制的典范啊,佩服佩服。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读后感(二):大海般平静的愤怒
个人以为,这个短篇是索尔仁尼琴最出色的作品。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尚未象写《第一圈》的时候那样让愤怒堵住自己的心灵,还可以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不公。而恰恰就是这种平静,更能让人感觉到作者深深的愤怒与悲哀,就如同我们面对大海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深藏的力量涌动一样。
作者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字一句批判当局批判制度,但是无言的批判却又无所不至无处不在。对环境的描写也好、对劳改的描写也好,作者笔下的一切都逼迫着读者去体会、去思考、去反省。这几乎就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后来的《癌症楼》也难以望其项背,更不用说《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了。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读后感(三):索尔仁尼琴小识
索尔仁尼琴曾经让我十分佩服,那种情感类似于一个孩子面对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所怀有的敬畏与渴望:夜幕中它是一个太阳在我的双掌间如硬币燃烧,让我触及到了灵魂的肃穆。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他流亡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美国小镇生活18年后,坚持写下的那部长达数千页的《红轮》,我发现他的影子借着黄昏就隐没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在声嘶力竭地呼喊。我读了四五十页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我的触觉在匆匆逝去的寸阴中钝化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是如同死去了一样变得惨白(甚至还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厌倦与疲惫)。我们中间出现了体积庞大的空无,阻断了我们通向彼此的路途,我对这些事情都能理解,但是我却无法感知到他在堕入永久黑暗时的感受了。因为我不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与绝对的黑暗与光明了,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令人悲哀的证实:永远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当敌人最终消失时,却成为他曾反对的那种人。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和写作,没有摆脱与他敌人同构的思维方式。此时,我更愿意赞同同样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作家布罗茨基的说法:“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这也就可以说,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是善恶交织,光暗错杂的,都是呈阴影状的(另一个俄罗斯作家说,“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文学不提供明晰完整的解释,也非为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文学是认知世界的独立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抑或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文学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写作与阅读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感受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诸词之后的宾语,都是文学的累赘;它们是文学的入侵者与劫掠者。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读后感(四):别了,索尔仁尼
今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索尔仁尼琴 于8月3号去世了,这些日子被奥运和格俄之战的报道充斥着,突然看到这个消息不禁一惊,在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路上,又有一位贤哲陨灭,坦然讲我并不完全赞同索尔仁尼琴 的观点,但是他的文字依旧可以成为一枚思想的指针。为缅怀先贤,特别把其生平简介,贴列于下:
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 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读后感(五):迟到的致敬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脏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说来惭愧,在他去世之后我才开始读这位敢于直言,为俄罗斯奉献一生的作家的作品.就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与迟到的敬意吧。
1962年,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品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从此出名。历史真的很会开玩笑,在那样的社会局面中,这样的类似"伤痕文学"的作品能够出版实属不易,竟然还能得到政治家的推崇,,又在盛行几年后禁止出版,真对前苏联政府能够坚持这么久报以由衷的"赞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主人公伊凡在苏联集中营服刑的一个普通的一天.从白天起床,到吃饭劳动,一直到晚上入眠等待第二天的到来,索尔仁尼琴不厌其烦地极其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集中营的真实:被扭曲的人性,对遥遥无期的未来的迷茫,或是漫漫无期地等待死亡......
综观全篇,索尔仁尼琴始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客观的叙述方式协作.他没有一字一句批判当局的制度或是社会的黑暗,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也是以平静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不公以及周围无辜狱友的不幸。而恰恰是这种客观的描述,却呈现出无处不在的无言的批判;恰恰就是这种平静,更能让人感觉到作者深深的愤怒与悲哀.无论是对环境的描写,还是对劳改的描写,作者笔下看似未注入任何情感的一切都逼迫着读者去体会、去思考、去反省.可能是由于其自身频繁的牢狱经历,使得描写极具真实性,一幕幕场景如同在清身经历过那般清晰.索尔仁尼琴利用底层百姓的写照,这样的控诉方式更震撼人心。
伊凡虽身陷管制严苛的集中营,确仍拥有私藏物品:一把小勺,自己磨成的小刀.这样的物件是不允许犯人私自拥有的,这得益于伊凡平时的小心谨慎得以留存.冒着关禁闭的风险,伊凡坚持顶风作案,收藏这类物品.在那样的专制之下,严密的审查之下,还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专制还真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啊.这使我联想到,不管在哪个专制统治之下,总会有一小部分人逆大风向而行,也总有人能像伊凡的那把小勺一样,在兢兢战战中存活下来.(好像有点扯.)
索尔仁尼琴和他笔下的伊凡截然不同:他不会像伊凡那样一天天得过且过,等着25年的牢狱结束,有他在的一天,他就会为他所信奉的真理呐喊,如普京在索尔仁尼琴获得当年的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专程去他家中拜访时说得那样:“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在距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关于永恒性的主题,而是对一个特定时间段的反思,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是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对前苏联的叫嚣,还是时代的记录者.(或者说是一种类型的历史的纪录,在其中看到了太多的历史的复制)即使是现在,阅读他的作品仍能给人以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