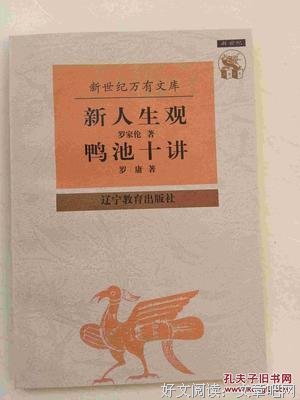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是一本由罗家伦 罗庸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10元,页数: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精选点评:
●本书受尼采的影响很深,新人生观部分说教感比较强烈,鸭池十讲的几对辩证概念很有意思,总体而言煽情大于说理,但还是甩思修教材好几条街了。
●绝品~
●虽不能完全赞同其观点,但那个时代强有力的跳动的脉搏还是让人很振奋。
●20180319-20180330 说教味重了 许多观点在现在其实也没什么了 所以看着闷 当然 可以想象 放回写作的年代来说 应该是很有指引作用的
●五四一百年之际,读该运动中干将的著作,竟有一点触目惊心。太激进了,有一点尼采,甚至有一点纳粹,但语言文字是极好的,7分吧
●还是那句,“侠出于伟大的同情。”虽然有片面之嫌,但我喜欢他把中华价值至于世界文化范畴来解读的思路。面对五四时期的学者,心有戚戚焉。
●鸡汤人生哲学
●今天才知一百年前的著名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罗家伦起草的。这书是十几岁时买的,只翻了翻,结果是我没上P大,还因此退了学,后来就失学了
●今日依然 可以作为药石针砭
●《新人生观》很适合给青年人打鸡血!《鸭池十讲》讲的是儒家文化。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读后感(一):《鸭池十讲》育人先做人
短篇却有大道理,收入了罗庸先生十篇演讲稿
从儒学到做人和,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温文儒雅的形象。对古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无我是最高境界,做到很难,保持好学之心,时刻自省。
平时要善感敏思,不能让愚弊常驻。教育重在启发学生思维能力,功利物化不可取。
虚静之心了知万物,一切学问要从根本入手,之一而万毕。
境界贵在有意象,诗歌字画等一切艺术的核心。物境,事境,情境,理境逐层上升,最高是情景交融的无言之境。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读后感(二):新人生观之评论
对不起罗老,我是下载的版本,内无鸭池十讲部分。新人生观也只有140页,不知道是否是全部。然而,就我所读的部分而言,感慨良多,受益匪浅。
本书作者罗家伦,民国时期北大高材生,五四学生领袖,学贯中西。23岁时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研究院。后游历欧洲如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学成后归国并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 31岁时以少将军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定居台湾。
本书成于1942年元旦,真真是70年前!当时正值抗战艰苦之时,国难当头,时运维艰。他写这本书有振奋国民精神与意志之意。可作自省、培养健全人格之用。
节录如下:
“整个人生的目的,就在求自我的实现。什么是自我的实现(self-realization)?自我的实现就是自我的完成(perfection of the self),也就是充分的发展自己,充实自己,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笃实光辉的境地。”
“现在中国文化方面,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高尚的中国文化,渐渐的少人了解,而优美的西洋文化同时又不能吸收。纵然学会了西洋一点应用的技术,或是享用物质文明的习惯,但是对于西洋文化在人性上表现的精微美丽之处,丝毫没有得到。中国文学的修养尚且没有,何况西洋文学的修养。”
“世间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书。我们可以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有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和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深刻,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书。这就是英文中所谓‘灿烂的书’(brilliant book)。无智慧的书,往往材料堆积得如蚁丘一样,议论虽多,见解毫无。纵然可以从他得到消息,却不可以从他得启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这就是英文中所谓‘晦塞的书’(dull book)。”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读后感(三):何以疗救
几十年过去,两本在今天看来尤其显得单薄的册子,重新排印合成一本出版,在于里面的议论似乎对今天仍有所镜鉴的作用。[1]
今天谈高等教育,甚至笼统地愤懑于整个的教育体制的,几乎言必称联大,动辄昆明。可惜,联大当年的先生们,似乎对于教育和学生,也未尽满意,否则也难得这样一本不厚却也多多少少靡集了劝导讲演的册子。
罗家伦留洋经历多一些,他从启蒙以来的西方找解药。今天的西方政体与西南联大时期的西方并无根本性的不同。今天的西方一样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国内与国际不容易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至于当时与日本结盟成为轴心国的德国,又何尝不是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的一部分?如果“西药”是灵验的,今天的西方应该无比和谐,1940年代的德国应该与整个西方世界携手前行,共渡时艰。
罗庸的国学功底大概深厚一些,他从古圣先贤里找解药。然而,今人仰慕的联大与“当年的大学生们”,在当时的联大人眼里是痛心疾首,怒其国家危亡之际尤不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古圣先贤,又可真是春秋汉唐宋明的古圣先贤?如果“中药”有用,中国自西汉尊儒以降,且不论改朝换代、中原易主,有多少争霸、割据、生灵涂炭、不绝兵燹?
在西南联大谈爱国,谈青年的理想与责任,多少是容易的。国都内迁千里,偏安巴蜀。中国人刚刚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家,没有多少年被一个“落后”的帝制国家几乎逼到了绝路。这时的中国,无非是国家与民族的存亡。青年人谈理想、抱负,难免以维护国家为一切之基础。抵御不了侵略,作了亡国奴的青年,恐怕更无所谓理想可谈了。面对青年的颓唐,什么样的苛责与劝勉,都还显得理所应当。
当,外部的侵略消除,内部无畏的争斗结束,国家归于日复一日的平寂之中。青年是不应当庸庸碌碌,然而,青年又应当做什么?
我说,古圣先贤未必有用,因为他们没有保下中华民族两千年太平。然而,孔孟之道是人道。孔孟之道,总的来说,讲道理。虽然,举孝廉、二十四孝的故事,都难免时而怂恿人虚伪。孔孟讲爱有等差,宣扬孝悌,合乎人伦亲亲之常。孔孟承认君子爱财,惟应取之有道。孔孟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人做事需有同理心。这些和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无私无我,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古话说,蝼蚁尚且偷生。后来,保护木材而送命,大为宣扬赞美。到了这个程度,人已不成其为人,简直就是少数人维持大社会运转的工具了。凡人均被要求高尚,高尚地甘为他人的“螺丝钉”。苏联人早了二十多年,搞这一套虚伪的崇高,磕磕碰碰、头破血流。我们依然前仆后继。当这条路走不下去,不得不抛弃的时候,孔孟也早已作泥灰奔流不回。
于是乎,有人扯起“国学”的大旗,要为孔孟招魂。然而怕是招不回来的。俄罗斯人大概是幸运的,社会主义的联盟瓦解了,上帝还在。当“崇高”在中国破产之后,潮水退去,满眼都是自私与利用、勾结和背叛、谄媚及狰狞……
今天的高等教育,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精致与粗糙的利己主义者,在钻营与钩心斗角里争取“成功”,为世界奉献了一个不问精神只谈物质,不论契约只看得失的臃肿而又经典的样本。
[1] 杨扬.出版说明[M]//罗家伦,罗庸.新人生观·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读后感(四):诗的境界
境界就是意象构成的一组联系。意向是一切艺术的根源,没有意向就没有艺术。凡艺术必本于现实,而一切现实不得称为艺术者,就因为艺术是在现实上加了一番删汰练绎的工夫,又加了一番组织配合的想像,这手法即是意象。
现实有具体的存在,而境界则存于艺术家的想象中,所以它可以神变无方,不拘一格。因此,我们可以说,境界是一切艺术生命的核心。
文学不离语言文字,而诗是最纯粹的文学,所以诗的境界也就是最纯粹的艺术境界。照此而论,诗就是艺术,其实不然。原来诗除了意象之外,还有音律,格式,许多元素。意象创造很难,而音律格式则学会甚易,有些没有境界的语言文字也可以假借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诗境的问题也就头绪纷繁了。
大概没有艺术修养的人,眼中所见,唯有物境。这和初有知识的小孩差不多,只会看见个别的具体事物,而不会说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诗的角度上讲,那些只是照顾了韵律而堆砌事物的诗就在此类,即使像韩愈那样加些巧妙的手法,但是在诗的本质上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比物境略高一筹的是事境,那是较为注意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说明其联系者。写景的句子,本也属于事境,但能入诗的写景语必须兼有感情,至少也要能在景中表现出作者的感觉,或是事物的动态。如王维的“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便被称为体物甚工,就因为写的出动态来。
比事境再高一筹的是情境,原来一切的感情必有所托才能表现,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单纯的歌哭是不容易表现的,此所以情语必须兼是景语。彼此分数的多少,便有刻露与含蓄之分,而在艺术的原则上说,含蓄高于刻露。也就是说,寄托越深远,便是表情越深远。
驾驭情境之上,而求超出,便是理境,文学的界域与哲学的界域就在这里分途。守住文学界域而参入理境,可以使意境更高,但太高了,也可以使文学的温情变得枯冷,是人读了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若舍弃情境而单纯说理,那就脱离文学的范围了。如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诗境的最后是无言之境,非但情景交融,兼且物我两忘,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传为千古佳句。 说理诗完全在于理智,而真诗所需要的是感情。感情期于合,理智期于分,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之境,由理智出发是无法达到的。理事无碍,仍需经过感情也。
综合上面所说,诗的境界,下不落于单纯的事境,上不及于单纯的理境,其本身必须是情景不二的中和。而一切物态,事相,都必须透过感情而为表现;一切理境,亦必须不脱离感情,所以感情是文学的根本。“诗以理性情”,其意在此,音律格式,不过是诗的皮毛而已。
注:上文摘自《鸭池十讲》中的《诗的境界》,罗庸 著
罗庸的文章,读上去并没有郭沫若那边天马行空,也没有闻一多那般诗情画意,从第一眼看去并不能立刻抓住你的心,但若是耐着性子读下去,那种深入浅出不紧不慢却富有条理的叙事说理的笔法,全让你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喜欢上他。
罗庸就活了50岁,至今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他学生整理的两本书《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习坎庸言》是他的学生整理的他的人生教诲,先期在台湾私印出版,此次终由新星出版社在大陆公开发行。《鸭池十讲》是他在西南联大期间的讲课实录,之前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曾收录,与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新人生观》合为一书,其内容主要讲究文学研究的志趣与境界。
罗庸即使在他所处的时代,也算不上一个大师,名气也不大,但就是通过那简短的两句小传,依然可以认定他是个知名学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系主任,一种说法的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而那时候他才40出头,如果长命一点儿的话,以后也不会比徐复观,牟宗三这些人差。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大师在学术层面上都有自己的好恶,对自己喜欢的大加赞扬,对自己不喜欢的横加批判,然且又都受其时代背景的局限,想做到纯客观的讲述,大体是很难实现的。而罗庸在这方面是我所读到的中,做的最客观的一个。
从《诗的境界》来讲,你可以看出罗庸对自己喜欢的魏晋文学的诗句赞许很多,援引也很多,但是他却没有很郑重的提出就是魏晋的就是好。他的讲习更多的会举一些通俗易懂的生活中的例子,有时会联系一些古文诗句,但也多是脍炙人口的句子,让人一看就有共鸣,说的很浅,却讲的很深。别有一番味道。
罗庸所谈的这几重文学上的境界,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上,推而广之,同样能运用在音乐上,戏剧上,乃至是为人做事上。创作一首好的乐曲,一个意象的确定也是很重要,使得观众可以动情,可以幻想。戏剧更是如此。至于人生,也就是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层层递进,层层抬升,不管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学,最后所追求的还是“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