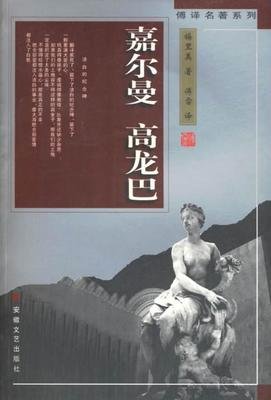
《傅雷谈翻译》是一本由怒安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页数:2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傅雷谈翻译》精选点评:
●傅雷无疑是小说领域最伟大的翻译家.此书见出这样一位大翻译家如何通过刻苦努力,把自己从一位拙劣译匠变成创造家.但对一般读者而言本书只够两颗星.
●阅读时间:2小时25分钟。冲着前半部分,给个五星!
●“不过我敢预言,那些翻译一定是坏透的。能译费尔丁的人,你我决不会不知道。你我不知道的人译费尔丁或朗斐罗的,必不会好。”
●谈翻译的部分确实太少了。
●书信内容占了半本,阅后感慨颇深,也多有启示。
●虽然读到后面有些不爽,但翻译的心得还是很受用的
●友人談傅雷與翻譯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
●只有前面一点是傅雷谈翻译,后面一大半都是别人谈傅雷
●致敬傅雷先生。
《傅雷谈翻译》读后感(一):可惜内容太少
本书是傅雷的与翻译有关的书信集。也收录了一些对于傅雷的翻译的研究和评论。
内容很短小。对于翻译很有他的真知卓见。只是傅雷作为一个实践者,不愿意过多地谈论翻译。很是让人不过瘾。
关于傅雷的翻译,我曾经读过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两遍。是我读过的翻译作品中最好的之一。其优美流畅的文笔,必将给你深刻的印象。
《傅雷谈翻译》读后感(二):傅雷很好,出版社很为难,读者很不爽
就整本书的结构而言,后半部分的对傅雷翻译的研究文章完全可以去掉。
不过这样的话,可能这本书也就没有出版的可能性了,因为全书关于傅雷谈翻译的文字相当少,可能也就3到4万字吧。
我给出“推荐”评价的理由是,就冲傅雷这三四万字,就值回书价了。至于本书中对傅雷翻译研究文章,如果不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不读也罢!
《傅雷谈翻译》读后感(三):文本增殖一例
傅雷的翻译要诀无外乎本书封底专门引出的那一句:“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这听上去似乎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背地里却暗含着这么一层意思:译者有评断何谓 “纯粹之中文”的权力。
对自己的译事再怎么谦虚,在这个评断权力上,傅雷似乎不打算松口。所以他可以断言“老舍在国内是惟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1951年),可以抱怨“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1951年),甚至他的谦虚本身也与之相辅相成:“近来我正在经历一个艺术上的大难关,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一九五七年前译的都已看不上眼),脑子却笨了许多”(1962年)。敢情是单只有手艺会受到年龄的负面影响,品评高低的话语权却只会越抓越牢。
可嘴巴毕竟敌不过拳头,话语权终归要向武权低头:“对马列主义毫无掌握,无法运用正确批评之人,缮写译序时,对读者所负责更大”(1965年)。当是时,恐怕是无力再“诋毁”伟大中国人民的普通话是毫无文艺价值的“伪语言”了。
“以一种定义来体会一个事物,无论定义多么随意,都是在拒绝这个事物,是把它变得乏味而多余,是在灭绝它。精神把自己浪费在自己命名和规定的东西里了。”——萧沆
千年文事,不过一场贴标签的流水牌局。
《傅雷谈翻译》读后感(四):@金圣华…@傅雷@宋淇… #翻译#
雷的职业是翻译士,打怪多年,还刷过法兰西副本。总的来说,他是个很注重自己ID名誉的玩家,不像某些玩翻译士的,玩到后来怪也不打了整天泡坛子里灌水赚积分吊马子。雷只在那儿发过两篇帖子,《<高老头>重译本序》和《翻译经验点滴》,他试图在里面告诫众玩家:打怪和互喷完全是两回事。后来,TBC被停了服,WLK又一直“忘了开”,大家便把战场移到了坛子里。就这样,毕业多年,专精“人间喜剧”的一代名号,霎时变成一枚人见人欺的“江湖小虾米”。管理员们呢,都去抢“大灾变”的代理权去了。怎奈何,此等憋屈,投诉无门,雷愤然删号,曰,老子不玩了!
后来的后来,“忘了开”终于还是被邓老开了,只是“大灾变”还是“等着吧”,闲着也是闲着,游戏周边便丰富起来。有人合计着整本“翻译士攻略”来卖。时过境迁,“一代名号”变成“江湖小虾米”又变成“一个传说”,这些人想起了雷。说干就干!见雷的帖子少,他们就去翻旧服务器里雷的那些私信。遗憾的是,十年大姨妈,许多数据已经救不回来了,其中就包括雷发给另一对高级玩家伉俪的那些。唉,多好的噱头,文案!宣传!腰封!可惜可惜。一番复制粘贴下来,这攻略不足百页,零零碎碎,相关性也有限。不过,雷既已是服里的传说,有没相关性就不成问题,有没两百页这才是问题。于是,他们又跑去搜罗其他翻译士玩家谈起雷的帖子,有的没的,小开本,凑够两百来页,齐了。
《傅雷谈翻译》读后感(五):瞎谈傅雷谈翻译
初一暑假有一项作业就是看《傅雷家书》写读书笔记,于是乖学生如我从头到尾啃了一遍傅老写的信件,从音乐谈到翻译,从翻译谈到生活,以小见大放眼全球。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他给乖儿子傅聪写的那些关于钢琴演奏的建议。当时不知道有个东西叫 “逼格”,只觉得钢琴跟自己还沾点边,所以读书笔记写得还挺来劲,可惜现在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当时也不知道,若干年后跟自己沾了点边的又岂止钢琴。
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实在有待提高,遂去图书室借了本《傅雷谈翻译》。前半部分是傅老写的关于翻译的文章,也包括给乖儿子聪哥以及很多人写的信札,主题无一例外都是翻译,不是关于翻译方法就是关于自己的翻译经历,偶尔夹杂着老先生的抱怨。书的后半部分是旁人对傅雷唱的赞歌,或中肯或无聊,甚至有不少关于法语翻译的探讨,我仅凭兴趣学过法语的一点皮毛,这部分内容便一扫而过(说的好像之前都看得很仔细一样)。这些文章有种翻译专业毕业论文的无趣且迂腐的调调,瞥一眼便是一种痛苦,不禁让我担忧自己明年要写出个什么鬼。其实借这本书时,我的本心是积极向上的,可惜书的内容和编排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重复和繁冗,这种感觉在读《傅雷家书》时好像也曾有过——“克里斯朵夫”散落各页到处都是。
傅雷:“怪我咯~”
傅雷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的完美主义仅适用于翻译之外的领域,所以关于这点我很敬佩他。《致梅纽因》里他说:“翻译之难,比起演奏家之演绎往昔大师的杰作,实在不遑多让。”
恕我不能苟同,私以为翻译比演奏难。也许他说的是“完美”的演奏吧。
陈伟丰《谈傅雷的翻译》让我对傅雷译的《贝多芬传》充满期待。陈写道:“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边研究音乐史,边译小说的: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傅雷自己也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对此我倒是相当同意的。
总之傅雷很厉害啦,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