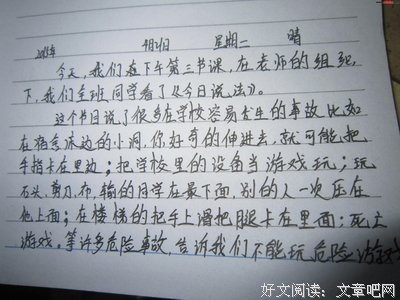
《赤子》是一本由余光中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赤子》读后感(一):文字的磅礴和婉约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很久之前,读过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最有名的乡愁反倒是没有记住,对《独白》中的这一句,只觉惊为天人,这一次有幸读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更是对余光中先生的行云流水的文字,叹为观止。 整本散文集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行走、观点、创作以及回忆。 一、行走 在行走这一部分,可以看到江南的婉约和北方的豪迈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两者碰撞出一种奇妙的美感。很久之前一直觉得婉约和豪迈是两个格格不入的风格,但是在余光中先生却很好的将这两种风格结合在了一起。 “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英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读到这里时的震撼之感,无比自然的从绵延细雨的烦闷感转折到了惊涛骇浪的压迫感。并且读起来有一种诗歌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行走这一部分有几篇文章写在葛底斯堡,远在异国他乡,是不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光和氛围,但是,当读到这一部分的文字时,可以感受到那种古典和现代文明的碰撞。 当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之前看过的《爱、死亡和机器人》中《祝有好收获》那一集是讲在赛博朋克的背景下一个聊斋志异般的故事。 完全不觉得有任何的违和感,反倒会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去书写,原来还可以这样去表达,新奇和华丽。 读的时候,仿佛捧着一颗无比炽热,又无比澎湃的心脏一样,无数的情感从书中喷薄而出,是不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不然非疯了不可,需要歇一歇,将情绪缓上一缓,再去感受。 二、观点 这里可以看到,余光中先生深厚的文学底蕴,观点冷静,情感克制,大幅度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引经据典,用大量的知识来支撑的,读罢,更是觉得崇拜。 “幽默是荒谬的解药” 三、创作 总觉得带着森然之意,后来看到文中提到了李贺,才恍然大悟,李贺的诗意象有些也是别的诗中常见,但是放在李贺的诗中,就自带特色。 余光中先生也是如此,用词意象别具一格。 “雨地里,腐烂的薰草化成萤,死去的萤流动着神经质的碧磷。不久他便要捐给不息的大化,汇入草下的动土,营养九茎的灵芝或是野地的荆棘。” 创作的最后一篇名为《焚鹤人》,写带着三个女儿一起做风筝,似乎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想到了意外离世的舅舅,以及舅舅为自己做的那一只风筝,全文并无一字在着笔写悲痛和伤感,但是通篇读罢,只觉得满纸怅然 四、回忆 在回忆里,可以更加深层次的看到余光中先生的可爱之处,看到他岁月里的烟火气息,看到他的友人以及其中的情谊,看到余光中先生的赤诚和儒雅。 最后说一下,书的装帧,书的颜色很好看,是漂亮的米色,有同色的浅浅凹下去的赤子两个字,书并不是很大,19cm*13cm,正好可以放在随身的包或者大一点的口袋里面,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一读,正好合适。 在正文的前面有余光中先生和夫人的照片,还有余光中先生的一段手稿
《赤子》读后感(二):《赤子》:原来文字也可以美得如此惊心动魄
《赤子》引言: 你不是谁,光说,你是一切。你是侏儒中的侏儒,至小中的至小。但你是一切,你的魂魄烙着北京人全部的梦魇和恐惧,只要你愿意,你便立在历史的中流。在战争之上,你应举起自己的笔,在饥馑在黑死病之上。星裔罗列,虚悬于永恒的一顶皇冠,多少克拉多少克拉的荣耀,可以为智者为勇者加冕,为你加冕。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得够久,你是空无。你是一切。无回音的大真空中,光,如是说。这是我在余光中《赤子》散文集里的《逍遥游》中摘抄的一段文字,我反复阅读、朗诵,还发给朋友,原来文字可以美得如此惊心动魄、荡人心魂,余光中大师不仅仅是乡愁诗人,原来我们还错过了那么多美丽的文字。
我有种想大声说出来、叫出来的冲动,不停给他人安利,这些叙述像是写出了我们的心声,你不是谁,你是一切,你是全世界。他描写星空浩瀚的字句被烙印在心底,又仿佛在我们眼前用文字描绘出一副浩瀚宇宙的景致,美丽得令人绝望赞叹,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而万籁俱寂时,终于能倾听到心底的声音。
夜来听雨声:说起来,我也是最喜欢听雨的,可我没听过余光中大师笔下,雨打瓦片的声音,雨打梧桐的声音,雨打芭蕉的声音,我不曾注意过春雨绵绵和秋雨潇潇,不曾和人共举一把伞,行走在雨幕里,而这些作者用文字给我编织了一个梦,一个关于雨的梦,关于古老中国的雨景,关于他的思乡之情,关于那些青苔深深的记忆。
而那句“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又向我们阐述了一个现实,过去已经回不去,我们只能在回忆里缅怀,在文字里追忆,听听那冷雨,那雨声一点一滴都似乎打在了心上。
雨会再来,雨季会再来,可是过去不会再来。
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我都有些不忍翻页,这文字太美,而这感情太悲伤,在字里行间倾泻而下,我在这冬日的夜晚,仿佛能够听见那来自遥远过去的雨声,淅淅沥沥、一点一滴,徐徐飘进我的梦里。
因为看见过这样美好的文字,所以我们笔下的文字都美好了起来。
我朋友曾经问我,你看了这么许多书,记得有多少?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吗?
坦白说,看上去好像真的没有,可就当它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竹篮在打水的过程中,一遍一遍清洗,一遍遍得过水,就这样循环往复,心灵的竹篮被清洗得干干净净,而我们的灵魂和笔下的文字也是,在这无用功里,变得越来越美好。
因为我见过这么多美好的文字,我的笔下也似乎因此而美好了起来。
而阅读过像余光中大师这样好的作家,写出的美好的文字,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用游历他走过的的地方,和心灵的感悟,整个人都仿佛脱胎换骨。
我从不曾知道,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斯美好。
End。
《赤子》读后感(三):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余光中
说起余光中,你一定会想到《乡愁》这首诗。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
一张邮票,浓缩了作者对祖国的深深地思念,对故乡的无比的眷恋,直击无数游子的内心,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共鸣。这首诗也成了余光中的代表作。
但是,你若是把余光中仅仅看作一位诗人,那么你便是小瞧了这位伟大的作家。《乡愁》这首诗不过是他花20分钟,随手写下的。
除了写诗,他还写散文,文学评论,翻译,这被他笑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因为文笔华丽浪漫,风格迥异,也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
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2017年12月14日,余老在台湾逝世,享年89岁,在海峡两岸引起发无数人悼念。
在文学创作中,相比他的诗,余光中的散文更是挣破了格律的束缚,天马行空,文笔秀美。比如那篇《逍遥游》,从星空起笔,展开联想,引经据典,《诗经》《老子》《庄子》《山海经》中经典名句迎面扑来,连放荡不羁的李白,诗中鬼才李贺都被他拿来布景。文学修养稍微欠缺的人,会一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法消化,产生晦涩难懂之感。而懂他之人,会跟他一起冲破时空的屏障,畅游在无垠的宇宙中,来一番逍遥游!
而余光中的另一篇《听听那冷雨》,让人跟着淅淅沥沥的雨,从厦门到金门,从江南到大洋彼岸,体味人生不同岁月中的不同境界况味。
余光中出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厦门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美国多所大学,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因此,余光中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戏称“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他的文学深受中西方的影响,兼具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和西方象征派的风格。
余光中的散文集《赤子》,撷取了他一生散文中最精彩的25个篇,共十二万多文字,带领读者从行走、观点、创作、回忆等四个维度,去领略这位刚柔并济,学贯中西的学者的人生经历!
其中,既有他童年求学的模糊记忆,也有他乡游历的点点滴滴,有关于文学创作的独到观点,也有思念祖国的绵绵深情!
读余光中的散文,你会更加了解他笔下的文字魅力。
《赤子》读后感(四):山河岁月的赤子情怀
1、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
提到余光中,或许浮现在大家印象中最深的便是《乡愁》,的确,他是一个将大陆视为母亲、台湾视为妻子、香港视为情人的第一位文学大师,故也称其为乡愁诗人。
一首《乡愁》让我们在小学课文中认识了这位诗人余光中,那时候不懂乡愁的滋味,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首诗总是会在耳旁想起。
如果把余光中仅仅称之为乡愁诗人,那说明我们对这位老人还不够了解。
余光中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著名的散文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余光中把自己的写作分为四度空间,他遨游在自己的写作四度空间里,他曾说:诗是我自己写的,散文是为读者写的,评论是为朋友写的,翻译是为家人写的。
余光中对自己的期许是,在中国文字的烽火炉中练出一颗丹来。
文学大师梁实秋曾经这样形容过他的这位学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诗与散文,相当于余光中的两只眼睛。
最近在读余光中的《赤子》,便是从余光中一生创作的散文中撷取约12万字的优秀代表作品,其中有论述自己独到的文学观念,有记录自己异乡生活,有追忆大陆当年的童年往事,也有感性记叙自己旅行点滴。
读余光中先生的散文,会有悠闲自在之感,就像一位前辈娓娓为你道来他的生活感悟,又并不是为了说服、教训,自在而畅快。
2、唯有看书写作摆脱寂寞与空虚
余光中在《赤子》回忆篇中的《金陵子弟江湖客》里说到:他当年同时考取了两所大学,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一心向往背上的他最后却选择了去往南京。因为当时是抗战胜利后的两年,北京正处于战云密布,身为独子的他被母亲挽着手臂留了下来。
他在学校里的时候,性格内倾,甚至有点胆怯,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因此书籍是他唯一的消遣解闷之物,他读的书很杂。那时候的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几乎很少去亲炙名流,仅有的一次写信给胡适请教问题也未曾收到回信。
后来在美国定居的时候,身在异乡的他也时常倍感寂寞,那么老先生是如何摆脱空虚的困扰呢?答案还是看书、写信,如他在《望乡的牧神》中所说: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像一段雏形的永恒。我几乎以为,站在四围的秋色里,那种圆溜溜的成熟感,会永远悬在那里,不坠下来。终于一切瓜一切果都过肥过重了,从腴沃中升起来的仍垂向腴沃。每到黄昏,太阳也垂垂落向南瓜田里,红橙橙的,一只熟得不能再熟下去的,特大号的南瓜。日子就像这样过去。晴天之后仍然是晴天之后仍然是完整无憾饱满得不能再饱满的晴天,敲上去会敲出音乐来的稀金属的晴天。就这样微酩地饮着清醒的秋季,好怎么不好,就是太寂寞了。在西密歇根大学,开了三门课,我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写信。”
雨果说:“各种各样的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作用下,仿佛烤在火上的纸一样渐渐燃尽。”
3、山河岁月里的赤子情怀
本书名为《赤子》,“赤子”是指刚出生的婴儿,后比喻热爱祖国,对祖国忠诚的人。
都说普罗旺斯是梵高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海南岛是苏东坡的,那么余光中呢?
回溯余光中先生的过往,却会发现,这位老人最为难得的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保留着一份赤子之心。
老先生从大陆离开时,他只带走了一张残缺的地图,“看着它,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他开始爱上画地图,通过这个独特的方式派遣对故土的眷恋。
至20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后,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飞回大陆,在与大陆告别的20个年头里大约有五十多次的往返记录。
他说:年少的记忆全都埋在这块“雄鸡状”的土地上,归乡是一种执念,也是对记忆的一次次唤醒。
最喜欢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